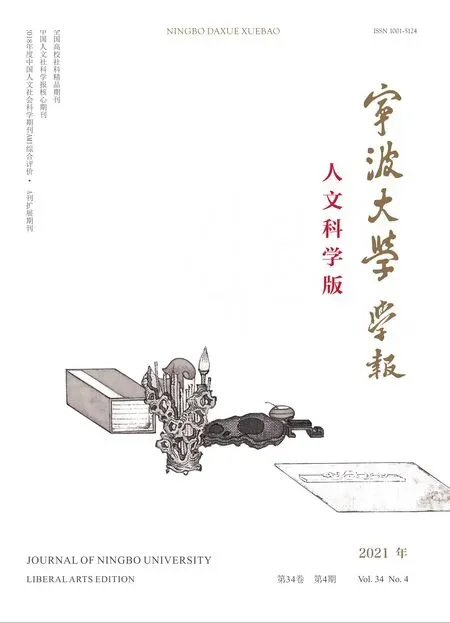拉金城市诗歌中亲密空间的异化与救赎
吴燕飞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300)
菲利普·拉金是英国运动派诗人领袖,其诗集《北方的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和《高窗》,受到英国诗歌界的广泛好评。在我国,关于拉金诗歌的空间研究有陈晞的《城市漫游者的伦理足迹——菲利普·拉金的诗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拉金创作年代是二战后英国城市复兴和扩张的高峰期,他的大部分诗歌记叙和描述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其中亲密空间是极为重要的主题和叙述对象,“房间一词在拉金1945 年后写的24 首诗歌中出现了35 次”,类似的其他用语“家”也频繁出现[1]151。本文试解读拉金的诗作,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探讨城市中亲密空间(personal or intimate space)的异化和救赎。
一、亲密空间及其异化
亲密空间指工作和社交之外的,个人生活中较私人化的空间。亲密空间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于由经济决定因素构建的社会空间;给人带来在家的感觉,即自在感;具有治愈潜能[2]20-21。广为认可的亲密空间为家宅空间,包括房间及周边的院落等。甜蜜温馨的家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舒适感。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描述了家宅作为庇护所的种种温暖和想象;但在拉金诗歌中,家、卧室、花园等许多亲密空间的意象却充满了压抑、悲哀、孤独、束缚等特征,并非心灵的美好居所,也抽离了让人再续生命活力的空间功能。这虽然与拉金个人的悲观特质密不可分,诗人曾说:“如果说我受欢迎,我想那是因为我常写不愉快经验剥夺丧失之于我,如水仙花之于华兹华斯。”[3]30但更是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城市重要构成部分的亲密空间难以摆脱城市整体的异化影响。
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活动、人的类本质(即作为物种的人和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疏离和对立,失去自主性[4]50-52。在此基础上,埃里希·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人性异化”,即作为心理体验方式,个人在这种体验中使自己疏远起来,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而自己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5]120。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从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角度揭示了造成异化的原因,并将人与创造物的疏远、人被创造物奴役作为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据此,将“亲密空间的异化”界定为:受商品社会的物化力量影响,人创造的亲密空间在其体验中却失去了为自身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和舒适感的亲密功能,并反过来令生活在其中的人倍感痛苦孤独,相互疏离,或造成自身的割裂。
所有空间都具有多重特性,受列斐伏尔影响,苏贾在《第三空间》中提出空间的三元辩证,认为空间可分为:物质的、精神的、以及“发端于传统二元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然而也超越了这两种空间”的第三空间[6]31。本文试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分析城市中亲密空间的异化,并从精神层面探讨拉金面对空间异化的救赎之路。
二、亲密空间在物质层面的异化
存在于城市大环境之中的亲密空间,必然受到城市扩张的各种影响,无法避免物质层面的异化,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城市布局和建筑的迅猛变化使亲密空间日益缺少自然元素,影响城市居住者的体验。摩天的现代公寓取代了传统的家宅院落,城市已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拉金在《去了去了》(Going,going)中哀叹:“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它还会存留——/总觉着,在这所城镇的远方,/一直会有矿业和田园,/村里的孩子们会在那里爬树,/像是它们不曾被砍倒;而当那些旧的部分退去,/阴郁的新楼宇到来时,/……更多的房子,更多的车位……”诗中,被车位包围的阴郁楼宇缺少田园和矿场,更缺少动植物等自然元素所带来的生机,缺少孩童嬉戏的空间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意趣。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炉边蟋蟀》中将拥有一只在火炉边唱歌的蟋蟀看作家的宝贵特征,传统家园无法离开带着生命气息的组成元素:如动物和植物。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巨型空间阻隔了自然,吞噬了亲密感[2]107。城市公寓虽隔绝风雨,却也阻隔了阳光,无法像传统家宅那样与自然充分互动,无法让作为“自然存在”的人(马克思语)从大地和四季更替中获得力量和重生。如巴什拉所言:“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7]31逃离遂成为“盒子”居住者之心声,如在《告别之诗》中(Poetry of departures),诗人写道,“他撇下了一切”,“我们都恨家”。
其次,城市规划中为了交通和生产便利而进行的功能性条块分割使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遭到严重破坏,呈现千城一面刻板样貌,也使城市居民的体验变得僵化,难以感觉内心与城市过往的联结。在《去了去了》中,拉金叹息雕花的唱诗舞台、草地、乡间小路、老街等都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阴沉的高楼、高速公路、停车场、餐馆等没有太多文化传承的标准化城市空间。以外表和内部皆雷同的城市高楼为代表的,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空间,切断了城市居民与过往文化的脐带,破坏了城市居民的“地方感”,“就身体的存在而言,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地方感到心满意足,这个地方要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和氛围”[8]。拉金在《告别之诗》中坦率地表达“我讨厌我的房间……还有我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是经济社会强制性的生活节奏,是钟表时间和标准化空间对所有个体的条块化无差别统治,故而秩序井然的城市空间日渐走向异化,亲密空间亦然。
再次,现代城市中,不断加剧的流动性使普通工薪族“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只是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是那么变幻无常”[9]18,他们无法熟悉和习惯自己的居所,持久稳定的亲密空间已成为奢求,因为亲密需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布里尼先生》(Mr.Bleaney)就描述了一个工人压抑逼仄的居所,“带花的帘子,轻薄和破旧”,“那扇窗子露出建筑工地狭长的一瞥/杂草丛生,弃物散落”,“高椅子,六十瓦灯泡,没有/门后的挂钩,也没有防暑和箱包的地方”,“发馊的床”;布里尼先生不禁哀叹:“我们的生活丈量着我们的天性/而到了这一把年纪仍然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租来的盒子。”盒子似的出租屋内外都散发着荒凉的气息,轻薄、破旧、杂乱,无从令人体验归属感和安全感。根据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个体的自我感先行认定个体的经验应该是属于个体自己而不是某种远离个体的东西[5]118-120,但反复搬迁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结果主宰了个体的体验,在这里,情感与空间是脱节的,租客与破败荒凉又陌生的居所空间有着巨大的心理距离,无法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联系,他们只身面对无所依靠的当下和陌生破败的房间,因此他们的居所虽名为亲密空间却早已失去亲密的功能,不能被统合纳入个体经验,也就无法带来舒适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三、亲密空间在精神层面的异化
个体在精神层面的异化会影响空间的构建,最终导致亲密空间的异化。空间的精神性,由与之相关的人(如建造者,使用者,居住者)赋予。家宅等亲密空间因“被人所体验”“被想象力所把握”,而具有了“空间的人性价值”[7]27。但在城市中,人们每天忙于上班,闲暇时又被卷入消费漩涡不能自拔,亲密空间只是这些循环中的小小一点,除去睡眠,人们在其间的活动越来越少,因而家在城市人的心头似乎丢失了许多原有的亲密性与安全感。从赋予空间价值的人的角度分析亲密空间在精神层面的异化,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商业化和个体化,是城市人受商业化裹挟的心灵异化,是原子化社会(格奥尔格·齐美尔语)中城市陌生人的不断出现。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的商业化导致人与金钱的关系日益紧密、人与人的关系日益疏离,导致亲密空间异化。商业化中消费主义的影响必然使城市人屈服于商品世界成为消费者或生产者,而人的其他身份则被淡化,偶有提及乃至被渲染,也是为了促成消费。并且,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继而空间又把消费主义关系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10]。城市空间的使用也围绕着消费,在这种异化的空间内没有消费力的人不值得关注。拉金以广告为主题的诗歌——《本质的美》(Essential beauty),描写一个房间般大小的广告牌遮盖了一个贫民窟,却展示着一个富裕、温暖、优雅的家庭生活画面,“一把银餐刀插入金色的黄油”,“几张软沉的沙发”“酒杯”“散热片”,“只露出四分之一身材的猫/依偎在温暖垫子上的拖鞋旁”。诗中,广告画描绘的温馨家宅和贫民窟的空间对比,冷酷地揭示了城市中把温情作为糖衣炮弹的商业手段和社会对现实生活中苦难的漠视。人们会得到商家的殷勤,但消费过后,就只剩擦身而过的漠然。正如马克思“劳动异化论”所揭示的:城市人首先是异化了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其次,城市人与群体是缺乏认同的;再次,城市人自身是分裂的。受商业化影响,现代城市人过着分裂的生活:一方面“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接受延迟满足”,同时“又宣扬享乐、瞬间快乐”,“要在白天‘规矩正派’,晚上‘尽情放松’”[11]5。“消费社会在屏蔽那些无法被纳入其生产—消费链条的贫民”[12],人们在工作和消费之间摇摆,而无暇顾及其他更重要的人和事,更不会关心被广告牌遮蔽的贫民窟,宁可被广告牌中塑料花一般的假象亲密空间蒙骗。如拉金在《蒙骗》(Deception)中所说,“那些贫民窟,那些岁月,将你埋葬”,“只要欲望主宰一切,金融指数就会疯长?/因为你根本不会在乎/失魂地躺在床上的你,会比他更少受欺骗/当他蹒跚爬上令人窒息的阶梯/一头闯入欲望满足的荒凉阁楼”。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加剧了财富与情感的断裂,甚至邻里间的空间都被小酒吧、咖啡店等侵占,人们无法躲避商业化带来的异化影响,面对欲望的主宰,灵魂爬上窒息的阶梯、荒凉的阁楼,无助地消化这欺骗。被漠视甚至被有意掩盖的贫民窟,是这类异化亲密空间的特例,但即便是普通的居所,也被消费关系的洪水冲击着,城市中的人际荒凉感和疏离感也被投射其中,“陌生人危机”(齐格蒙特·鲍曼语)导致亲密空间精神层面的异化。
人不但是消费者,其本身也成了商品。人们甚至认为所有感情到最后都是金钱的变现,使亲密关系失去情感基础。如《钱》(Money)这首诗所示:“钱责骂我说:/‘你为什么让我无谓地躺在这里?我是你从未享有过的财货与女色。/你只需开几张支票就能得到它们。’”列伏斐尔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时说,“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商品的外化——掌握了绝对力量”,他把这现象称为“货币崇拜”[13]54。在商品化洪流里,在所有的城市空间中,钱都闪烁着令人失去理性的邪恶光芒,可以购买财货,甚至女色。另一首以广告牌为主题的诗歌——《阳光灿烂的普莱斯塔廷》(Sunny Prestatyn)更形象地批判了钱财和女色之间这种扭曲的关系,“请来阳光灿烂的普莱斯塔廷/招贴画上的少女笑着说”,“酒店/像是展开在她的大腿和/齐胸伸开的双臂之间”。女性身体被物化和商品化,成为刺激男性消费者的性暗示,使亲密关系的异化难以避免。而金钱算计是城市人最关注的话题,甚至在情人之间也是如此。
在《致希德尼·贝彻》中(To Sidney Bechet)拉金写道:“恰当的谬误在所有的耳中苏醒/为有些人建立了一个传奇的街区/有阳台,花篮和四方舞步/每个人都在做爱后平分账单。”对钱的神往充满了亲密空间的所有角落,从而让亲密空间变成一种空洞荒凉的所在,令城市人经历精神层面的异化。
不仅金钱利益会造成两性关系的冷淡,现代社会中人的个体化使家庭内部也难寻充满温暖和慰藉的亲密空间。拉金《这人就是自私》(Self’s the man)描述一个中年男子的抱怨:工作一天回到家,晚饭后又得钉钉子、刷客厅、看小孩,忙得无暇读报,家需要他提供的面包,挤压他的个人时间,却不能给他理解和慰藉。如马克思在“劳动异化”论中揭示,商业社会中个人是满足他人需求的工具,而无法与其他个体产生亲密和认同[4]42-50。城市中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使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在日常工作中很少交集,无论行为轨迹或是思路想法。城市人日益退缩到个体的堡垒,放弃交流也就意味着放弃丰富空间精神性的尝试。夫妻、父子,各怀心事,只不过是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最后只能逃离,正如《家这样伤心》(Home is so sad)的叙述:“家这样伤心。还是被抛弃时的样子/……瞧瞧这些画,这些银刀叉/这钢琴凳上的乐谱。还有,那花瓶。”天伦之乐、家庭关系,是家之温馨最必要的精神元素,却被商业社会的现代性机器绞杀,因而陌生感即便在家人之间也并不罕见。此外,现代城市中,个体的经济独立亦进一步催生了为数众多的“单身家庭”(即到了结婚年龄而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的独身人士一个人生活的家庭)。因此,作为亲密空间的家里放置了刀叉、乐谱和花瓶,却无法安放城市人疲惫的、等待安抚的身心,亲密空间的精神内涵却日渐空洞。
亲密空间的异化虽发端于城市物质空间的性状变化,最终还是因为居住者和使用者精神层面的异化而日益加剧。安全感,这种“家”的标志,并非来自可能的物质养育,而是来自于精神上的肯定[8]。当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投身商业化的洪流,成为漂浮在城市汪洋中的原子化个体,而减少对爱人、家人、自身的情感关注,人际的熟悉感、互联度大幅降低,亲密空间的精神异化必然无法阻挡。
四、救赎异化的亲密空间
拉金对城市中亲密空间的关注,在21 世纪的中国仍有现实意义。因为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城市迅速扩张,以绝对的优势甩开农村,成为绝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虽然在城市中居住要面对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但要人们再回到农村既不现实也非理性,农村的美好也许只是一种怀念中的存在。现代人要做的是如何使在城市中的居住变得更美好,对抗城市亲密空间的异化。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探讨了有利于个体本真自我成长的亲密空间(personal space)的构建,试图唤起人们超越异化、突破二元对立思维的意识”,途径包括:性,梦境,和崩溃[14]。救赎需要个人的精神层面的调整,亦需要社会的精神层面的调整。
首先,缩短人和自然的心理距离。人和自然在20 世纪的工业化城市中是一组极度扭曲的关系,拉金也把接近自然当成解决城市生活困境的重要方式,但是拉金一生都在城市生活,是一个“城市游荡者”。他的选择,不是像华兹华斯和梭罗那样隐居湖畔,而是将自然看成一种人居环境的元素,不时出行到乡间或海边怡情山水,或者就近在公园漫步(如《去海边》《夏日夜曲》《春讯》《在草地上》等所示),甚至是公寓窗户之外有疗愈之效的一瞥。当人们读到《伤心的脚步》(Sad steps)总会莞尔一笑:“撒泡尿后又摸回床上,/我分开厚厚的窗帘,被疾飞的云/和月亮的干净惊吓。//四点钟:花园依着楔形的影子静卧在/深渊的、被风收拾的天空。”无眠的城市人从毫无生气的房间看见花园、飞云和明月,被自然纯粹的美所打动,“忧伤”似乎慢慢消解。McNamee 认为此诗是诗人自己与诗中叙述者在望月时的对话:一方面是生存的严峻真相和痛苦,另一方面是将生活渣滓提炼成金子的能力,最终诗人从先验的自然美获得勇气和韧性,重获内心平衡[15]。自然的美,对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人,总是疗效甚佳。比起纯自然,拉金秉持的是一种“人化自然”观[16]210。城市中的园林、绿地和公园正是这一类被人类驯化的自然,且常存在于步行距离,城市环境是一个荒野与文明的两极范围之内波动的光谱[17],看到这些城市自然并用心感受,是缩短人与自然的物理和心理距离最便捷的方式。
现代交通工具和诸如路桥的基础设施之便利,也缩短了乡野和城市的空间距离,在技术上促成城市和自然的空间融合。拉金确实为这样一座桥创作了诗歌《生者之桥》。诗中的桥联结了“孤立的城市”“码头”“炼油厂”和“小山”“宽广麦田”“农庄”以及“遗失了许多世纪的乡土生活……今天似乎又重新拼接、打开,/全部复活在这一道单拱里,/与世界相连”。因此,自然元素更突显的乡村和荒野对现在移动能力强的城市人而言,在物理距离上已不是大问题。一旦唤醒城市人内心对自然的发现,以及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自然因素也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对抗异化亲密空间的治愈力量。
其次,调整城市中的人际距离。除去自然这一层面,在列伏斐尔眼中,异化的解决之道是成为“完整的人”,包括两个方面:“人与他自己的统一”和“个人与社会的统一”[13]69。可是由全球化和个体化这两种社会进程所合力主宰下的城市人每天都生活中陌生人的包围之中[12],陌生和冷漠是人们在城市中必须佩戴的面具,甚至也有其正向的价值,即意味着城市人的共同利益:互不打扰和隐身机制[18]44-48。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和城市环境的快速变化,都会加剧人群的拥挤和个体的疏离,接纳这种互不打扰的疏离,会减少不必要的烦恼,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应变。但是,在亲密空间之内,用以维护高品质亲密关系的两个手段:性和爱,仍然是改变冰冷压抑的异化空间的最受推崇之方式。拉金虽然一直保持单身,并在早年创作了许多批评婚姻、嘲讽爱情的诗歌,但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有不少歌颂爱情渴望亲密关系的篇目,如《阿伦德尔石棺》(An Arundel tomb)、《周一来做我的情人》(Be my valentine this monday)。在《爱情》(Love)中,拉金探讨了真爱的本质:“爱情的难点在于/要足够的自私:/在于有那种盲目的执着/去打扰一个存在,/仅仅为了你自己……然后是不自私的一面——/你怎会甘心/把另一个当成头等大事……不管是好是歹,/爱情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合适的……”此诗揭示:爱的本质不只是自私的占有欲望,更多的是不自私的关注,将对方“当成头等大事”。这与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的概念“成熟的爱情”是一致的,其要素是给予、关心、责任感、尊重、和认同[19]7-35。给予和索取的差别正是创造和匮乏的差别,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没有带来满足,乃是因为消费主义的洗脑,让人们时时处于虚假的匮乏和渴望之中。而亲密关系中相互的给予和关注因其建设性而带来认同和满足,这已是客体关系学派的心理学家的共识。总而言之,疏离和亲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若与陌生人的疏离所腾出的空间能培育为数不多却深沉而富于意义的亲密,也是现代城市人理想的选择,亦是救赎亲密空间的良方。
最后,是对个体内在性的重新认识。孤独是城市人最常有的精神体验,它必然会带来痛苦,但绝不是一种全然无用的经验,它可以让我们抵达所珍视之物的核心,与灵魂对话,与神秘而无限的宇宙融合。自笛卡尔的时代以来,内在性(internality)不只是应对或逃离现代性的方式,更是评估并抗衡现代性的精神源泉[2]207-208。而内在性,必然是在一个人孤独并内省之时最为显著。无独有偶,在弗洛姆看来,孤独和自由是如影随形的双生子,两者与人的“个体化”过程同步[20]15-25;既然自由已经成为现代人不可能抛弃的核心价值,人们仅有的选择就不是逃避孤独,而是接纳并用“自发活动”(也称原创性和创造性劳动)去克服孤独带来的痛感[20]162-175。拉金在一个人的房间通过对孤独的咀嚼,写下诗篇。最终的事实证明,孤独中成形的事物,或许也能救赎孤独,因为他的作品总能穿越时空的阻隔,慰藉无数现代城市人的灵魂。拉金作为一个城市游荡者,他的文学创作即使一开始可能是对孤独的补偿,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为他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构建方式,并摆脱纷乱琐碎的现实束缚,将局促孤寂的亲密空间转向诗意的存在,进入超越的世界,回归本真自我。可以说拉金通过他的自发活动,即诗歌创作,成功地调动了内在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甚至消解了疏离和孤寂造成的亲密空间异化。
五、结语
“空间是被在空间里发生的活动的整体所激活的。”[21]200拉金的观察和描写,深入刻画了现代城市中亲密空间异化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受城市扩张激流中外部空间环境迅猛变化、流动性加剧的物理性影响,又受到城市生活的商业化和个人化等精神方面的牵引,最终亲密空间无法带来安全感和自在感,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反而束缚了城市居住者,令人产生逃离的渴望。但另一方面,他的创作也蕴含解决这种城市生活困境的救赎之道。理想状态下,居住者可经常地与居住环境中及外围的自然元素充分接触,缩短与自然的心理距离,消解异化,寻求健康亲密空间的构建。对城市中人际关系的差别化调整,使疏离和亲密得以共存,并应对不同的人际领域。此外,充分调动个体的内在性,用创造性活动来面对孤独,回归本真自我、实现自我完整,亦可充实丰富亲密空间的精神性特质。如此,通过精神层面的努力,把个体和代表宇宙力量的自然元素融合在一起,把个体和创造融合在一起,把飘摇不定的个体和亲密他人联系在一起,以抗衡现代城市空间中的异化力量,救赎被异化的亲密空间。
——读菲利普·拉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