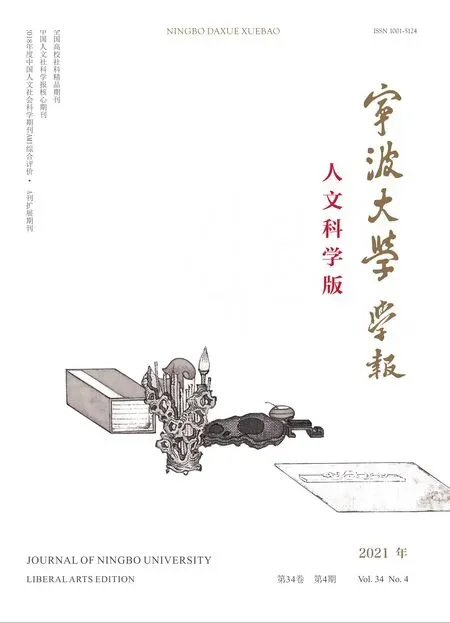来集之《两纱》的版本及其评点
张玉梅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来集之(1604-1682),字元成,原名镕,号元成子,别号倘湖,浙江萧山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曾任安庆府推官,太常寺少卿,兵科给事中,曾组织安庆军民守城抵抗张献忠,后又成功劝阻左良玉劫掠当地百姓,政绩显著。来集之入清后不仕,潜心著述,时人称其“倘湖先生”。其所著杂剧《两纱》,包含《女红纱涂抹试官》(简称《红纱》)、《秃碧纱炎凉秀士》(简称《碧纱》)两种,后附《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简称《挑灯剧》)。学界对《两纱》思想内容已有较多瞩目,对其版本和评点的关注尚少。
一、《两纱》版本
来集之的《两纱》,今存明末灯语斋和清初倘湖小筑两种刻本①,其形式和内容上均有较大不同。
《两纱》,灯语斋刻本。9 行20 字,版心题“灯语斋”,分上、下二册。
第一册内容为:(1)《红纱自叙》,元启、是生评语;(2)《碧纱自序》,冶子镕(来集之)、王中郎、式如、朱茂伯评语;(3)朱茂伯《读两纱小引》;董仲徽、孙济之评语;(4)朱鞏之《两纱剧小引》,杨叔祥、式如、是生评语;(5)《两纱例》(六则);(6)《总目》;(7)双叶图六幅;(8)《女红纱涂抹试官》,卷端署“胥江来镕元成著,兄道程式如评”。
第二册内容为:(1)《秃碧纱炎凉秀士》,卷端署“胥江来镕元成著,兄道程式如评”,四出,每出有出数,出目分别为《木兰花发院新修》《惭愧闍黎饭后钟》《树老无花僧白头》《而今方显碧纱笼》;(2)《跋红纱碧纱》,樊楚蘅、安生评语;(3)《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卷末附郑振铎藏书印,该本正文有毛笔题词。
《两纱》,倘湖小筑本。9 行18 字,版心题“倘湖小筑”②,与灯语斋本有多处不同。现将灯语斋刻本和倘湖小筑刻本卷前内容差异描述如下(表1):
从刻本款式、题署、序跋、题辞等比较发现:倘湖小筑本对灯语斋本作了语言表述的修改,使内容更通俗易懂,如“出一”改为“一出”,“出四”改为“四出”,插图标目以剧中曲词或出目表达。灯语斋本《两纱例》没有细分《红纱》《碧纱》,倘湖小筑本则用“以上《红纱》”“以上《碧纱》”说明,体现了刻者的细致用心。
倘湖小筑本对题辞序跋做了大量删减,两篇《小引》、一篇《跋》,皆删之。去除朱茂伯、董仲徽、孙济之、杨叔祥、樊楚衡、安生等人的名字,增加元启评点。此外,对作者和评者的题署作了改动,将“来镕”改为“元成子”,“道程式如”改为“式如子”,由名改为字号。
序跋题辞的编排顺序上,灯语斋本将《红纱序》《碧纱序》排在首,次为《小引》《两纱例》《总目》。倘湖小筑则是将《红纱序》《红纱》剧并置,《碧纱序》《碧纱》剧并置,两剧目录独立编排,更清楚明了,方便观览。
来集之在《碧纱自序》中透露《两纱》的创作时间:“岁丙寅,予负笈古耶溪畔,月魄不归,花魂无主,情魔既绕,才思亦抽,因取王明敭‘碧纱笼’故事,稍为谱之,以了前《红纱》一案。”丙寅,即天启六年(1626),来集之自称“以了前《红纱》一案”,则《红纱》创作时间应早于1626 年。毛奇龄《西河文集》收《故明中宪大夫太常司少卿兵种给事中来君墓碑铭》一文,其中称:“(来君)府试拔第一,时年二十七,始附学,于是作《两纱》剧。一《红纱》,谓纱障目眯五色也;一《碧纱》,则纱蒙其旧所为诗,贵与贱易观也。”[1]可见在时人眼中,《红纱》《碧纱》以《两纱》之名共同流传。
明末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收录来集之《红纱》《碧纱》《闲看牡丹亭》三剧,归为逸品。其评《红纱》:“闻来君方少年,何愤懑乃尔?”[2]似乎表明是从别处听说此剧,或许当时已有灯语斋本《两纱》附《挑灯剧》的流传。《远山堂剧品》未收录来集之的《秋风三叠》,可能是因为《秋风三叠》创作于入清之后,祁彪佳未得见闻的缘故。倘湖小筑是来集之入清后隐居倘湖时的室号,倘湖小筑本将《秋风三叠》与《两纱》合刻,刊刻时间应在清初,晚于灯语斋本。
二、倘湖小筑对灯语斋本的文本改动——以《碧纱》为例
倘湖小筑本重刻《两纱》时,对内容也做了较多改动,主要体现在《碧纱》剧中。
(一)曲词的变化
来集之花了不少精力对《碧纱》的曲词重新打磨。有的保留绝大部分原词,仅在个别地方修改,如第一出【红绣鞋】:
挂长虹马嵬匹练,洒清露金谷寒烟,奏凄风琵琶塞上入呼韩。雨淋侵霍小玉,云惨淡步非烟。则问那洛甫章台讨书缘。(灯语斋本)
挂长虹马嵬匹练,洒清露金谷千年,奏凄风琵琶塞上伴呼韩。雨淋浸霍小玉,云惨淡步非烟。则问那洛甫章台,几曾见人月圆。(倘湖小筑本)
这两支曲所用意象基本一致,皆有长虹、马嵬、凄风、琵琶、呼韩、霍小玉、步非烟、金谷、洛甫章台。倘湖小筑本最后一句将“讨书缘”改为“几曾见人月圆”,更合律,也多了一层人世悲欢的忧伤。
有的对曲文字数进行扩充,曲意表达更加细腻。如第一出【一煞】:
漂母曾经饭,王孙犹腼腆。况山僧不养的个书生惯。数声儿钟响,催香绩一弄花兰。且闭关,晓风残月暮雨朝烟。(灯语斋本)
汉漂母,曾轻饭;韩王孙,犹腼腆。况山僧不养的个书生惯。他辰钟暮鼓,百八声闻八百课。我鸟啼花落,三分春色一分怜。这投斋可是书生活计么?恨夜漫漫何时旦。纵取尽三百厘,伐檀坎坎,终不如十亩间,桑者闲闲。(倘湖小筑本)
来集之不受曲牌字数和音韵的限制,将39 字扩充为98 字。倘湖小筑本中展开描写僧人敲钟做功课与王播闲情赏花的对比,并以“桑者闲闲”,写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有的是相同曲牌,但曲文完全有别,如第二出【倘秀才】:
你那里道俺腌臜满腹无奇货,我却道你个蛇腹为心的念恁南无慈悲话,颠倒的谎喽啰。贪的净瓶,嗔的鹦哥,痴没煞了普陀。(灯语斋本)
你学不得袛园长者,施金布地颇。学不得鹿苑仙人,割肉餧鹰饿。只不过臭皮囊水带泥拖。(倘湖小筑本)
面对上座和尚的辱没,灯语斋本中王播显得无奈而略带酸腐,倘湖小筑本中却以佛家故事训斥座上和尚没有慈悲精神,并直言骂之为“臭皮囊”,其激愤不平更加突出。
(二)宾白的改动
倘湖小筑本重刻《碧纱》时,来集之对人物宾白也多作修改,角色塑造更为丰满。
《碧纱》宾白的改动一是在原本宾白的基础上略作改动,大意不变。如第二出【一煞】最后一句宾白:
这秃厮,量也不晓的俺这样银钩铁画的妙法儿。(灯语斋本)
这秃厮,你那晓得俺这样银钩铁画的妙法儿。(倘湖小筑本)
又如【白鹤子】宾白:
你们寺里的钟也有好处,你们却不晓得。(灯语斋本)
你们寺里的钟尽有理会处,西方之道由声闻而入,你们却不晓得。(倘湖小筑本)
二是同一人物在相同情境中所说宾白截然不同,如第二出:
【滚绣球】央及煞弥陀祈求的活佛,不问俺下稍结果,则今朝于意云何?(僧云)佛是眼睛大哩,你便饿杀哭杀在他莲花座下,也一灵不动,只当不知。(生背云)今日午时了,不意被众僧奚落至此。这和尚们委实的狠如强盗。(灯语斋本)
【滚绣球】我看他恶狠狠的手来摩,冷闪闪的眼来簸,明明聚集了强梁一伙,我倒做了个忍辱禅和。(僧云)到此地位,你便不是禅和,也不得不忍辱了。你来要我们的饭吃,我又不来要你饭吃,怎反骂我是强梁。(生云)你们骗人钱钞,饮酒宿娼,背地狗猪鱼鳖无所不吃,只怕比强梁还狠些。(倘湖小筑本)
灯语斋本用“狠如强盗”,表达王播被欺侮的不堪境地。倘湖小筑本王播唱词对上座和尚的凶狠、冷酷进行批判,又在宾白中通过王播之口,指出和尚犯戒施恶,无恶不作,言语犀利,揭露更胜。
其后,上座和尚驱赶王播:
(做推出门关门介云)推去书生贫户,关来和尚法门。他去乞云乞雨,我来为雨为云。(灯语斋本)
(做推出门关门介云)【集西厢】我门掩重关萧寺中,你伯劳飞燕各西东。我斩钉截铁尝居一,你且受用辣辣林稍落叶风。(倘湖小筑本)
可见,来集之对灯语斋本中自创的联句并不满意,转而从《西厢记》中摘录出与情节贴切的曲词。
(三)杂剧结构的改动
灯语斋本《碧纱》四出无楔子,倘湖小筑本重刻时,改为四折一楔子。
灯语斋本第二出《惭愧闍黎饭后钟》,除上场宾白外,包括【一半儿】(四支)、【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白鹤子】【四煞】【三煞】【二煞】【一煞】【快活三】【朝天子】【耍孩儿】【五煞】【四煞】【三煞】【二煞】【一煞】【尾】二十二支曲。
倘湖小筑本在第一出后加【楔子】,曲文包括灯语斋本的上场宾白和四支【一半儿】,并将第一支【一半儿】明确为【仙吕·一半儿】。第二出以【正宫·端正好】为第一支曲,并在【白鹤子】前加入几句上座和尚的宾白和一支【笑和尚】,将【尾】改为【尾声】。
《碧纱》剧第一出写王播在木兰院中看到木兰花开,自抒情志。第二出写惠照寺上座和尚思谋赶走王播,想出饭后敲钟的主意。众僧饭毕,王播至斋堂,已无斋可食。于是与上座和尚一番争辩,最后题诗被逐。倘湖小筑本将上座和尚施展计谋一段设为【楔子】,四支【一半儿】都是众和尚唱曲,分别写出他们“一半儿平民一半儿盗”的秉性,以及吃饭时、撞钟时、准备轰赶王播时的心理,是相对独立的剧情,也是情节转折的关键。
第二出以“生携木兰花上”开头,主要写王播面对众僧的羞辱而气愤,剧情更加集中,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因而在灯语斋本第二出首的眉栏处,有手写评语“此段从改本好”,评语中的“改本”,应指倘湖小筑本中增设【楔子】。
倘湖小筑本第二出增加【笑和尚】一曲,是王播面对上座和尚给自己扣上“吟几首歪诗,打一回呆坐,恋酒迷花,受人唾骂”的无端辱骂,愤怒得几乎无言,他唱“道我咿咿咿咿七言诗常向口内哦,道我呆呆呆只□□□向蒲团坐。道我冷冷冷冷面皮只好受人间唾,道我软软软软心肠跳不过爱水河,休休休,怎便的该折挫,是是是是我不曾合掌念弥陀”。曲中连用多组重叠词,以“呆、冷、软”等字眼形容书生的软弱无能,对空有抱负却遭际不堪的王播心中所受激荡表现得入木三分。
倘湖小筑本对【楔子】的设计,不仅是为了杂剧体制的完整性,也出于对情节转承的考虑,改后效果更佳。
(四)情节的改动
《碧纱》本事出于《唐摭言》: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3]
来集之保留故事本来面目,增加了细节,设置了冲突,丰满了人物,并穿插木兰花的开落,使木兰仙子见证王播与和尚的恩怨,指引恩怨的化解。灯语斋本没有遵循王播本事中的“二十年前”,改为“三十年”,如木兰仙子上场时说“转眼又三十年”,王播坐镇江淮回忆“俺王播三十年前在惠照寺中受尽了多般奚落”等。倘湖小筑本重刻时,统一改回了“二十年”。
倘湖小筑本第三出关于木兰仙子情节的设计,与灯语斋本差异很大。
灯语斋本第三出,王播住木兰院时,曾折木兰花插于净瓶,并吐露情思。木兰花受其情缘,后来修成正果,准备脱胎而去,临走前想要调停王播与和尚的恩怨,于是化作烧香妇人来到寺中。上座和尚年老不见客,木兰花神于是对一个搭讪的小行者委婉指点,吓唬小和尚王播将焚烧寺院、捕杀僧人,化解之道是“一味腼腆趋奉而已”,并细陈以纱笼笼题诗、供奉之法,劝和尚持护王播题诗,以消其忿,最后化成一阵散落的木兰花而去,木兰花树憔悴。
倘湖小筑本第三出,写木兰花神得道后,邀请菊神、桃神、松神等道友一起参证,点化上座和尚。几位花神在树林中对话,有意让上座和尚偷听。先是各花神询问解脱之法,木兰花神指出不能受贞心、名利之累,道破势利人心与修道的关系,称王播是仙官下谪。其后诸神同游,赏王播题诗、题字,指出“文人自家爱惜,如山凤凰之于尾,翡翠之于羽毛,麝之于香”。后众仙乘彩云而去,木兰花树焦枯。
虽然都是木兰花神点化上座和尚,但来集之在两次处理中却表现出了迥异的思想。灯语斋本中,他的态度是谐谑的、活泼的、讽刺的,其中多有诨科,反映了明末时期雅俗博弈中的俗趣。如木兰花神对小行者说自己的心上人不在,小行者就劝其另寻他人,甚至要求“把小行者作一后进附在同盟”,与《西厢记》【闹斋】所描写和尚“僧不僧,俗不俗”行径一辙。小行者得知对方是王播后,打诨说道“他原当初有些鬼头脑,专一贯勾引夫人”,刻画出其世俗心理。最后说“俺只道老和尚的眼瞎,不晓得秀才就是丞相。却谁知我小和尚的眼也瞎,不晓得女子就是神仙”,两个“眼瞎”,对比出两个和尚的势利越礼。而木兰仙子对小行者说“奉承势利的人,那里管得自己头脑”,更是对当世趋奉之相的深刻揭露。
倘湖小筑本中,来集之杂糅诗词中的各种意象于花神,其唱词联系诗词来塑造高洁的品性,如菊神“室庐鸱尾凝霜,篱落蟹鳌对酒”,桃神“武陵渡中鸡犬”,是“留心前度刘郎”的“玄都观桃神”,木兰神是“堕露起爱于骚径,兰舟艳称于词客”。来集之在倘湖小筑本中多以仙道思想表现情节,如木兰仙子上场时说:“只可怜寺中当年上座,今已年老灰颓,昔年势利之热肠,总属无知。今日衰残之暮景,尤为堪愍。且与诸道友死参活证,令各俗人酒醒梦回,那贫而失路的未必可欺,那富而有势的未必堪慕。树无花,则有色者未必胜于无色,僧白头,则有生者未必胜于无生。”俨然一番勘破尘世的偈语。【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两曲,唱出幻灭的心理:“看破了世上机关”,“跳出了是非场”,“那有掀天揭地的事业,那有镕金铸古的文章。则见争名的在朝堂,争利的在湖海,更有那争功的在战场。都一般的鸟飞兔忙。不得有个落叶归根,那能够长久的日暖花香”。
有研究认为,来集之作《两纱》是有感于现实,“来集之‘两纱’皆与科举有关,一为揭露科场弊端,一为展示中举前后人情冷暖之巨大反差。体现了作者希望革除科举弊端以挽救社会的古道热心”[4]。从第三出的情节对比中,可以看出灯语斋本《碧纱》中确有不少对势利之风、炎凉之态的讽刺,但倘湖小筑本则体现了较浓的出世思想。第三出上场宾白,灯语斋“可知的于佛有缘”,倘湖小筑本改为“可知的出世有缘”,用“出世”代替“于佛”,避世之心更加突出。入清之后,来集之“削发入山,课耕种,训儿孙,负惭林下者又数十年”[5],康熙十七年(1678)曾被举荐入博学鸿儒,他也“力辞不赴”[6]。因而,《碧纱》的主旨,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抒愤讽世。
三、灯语斋本和倘湖小筑本评点的异同
灯语斋本《两纱》与倘湖小筑本《两纱》都保持着明清戏曲的评点传统,但两次刊刻的评点内容差别很大。《红纱》的两次评点均为来道程所评,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碧纱》评点者一为来道程,一为来元启,两人的评点侧重各有不同。
(一)来道程《红纱》评点
灯语斋本《红纱》和倘湖小筑本《红纱》,评点者都是“道程式如”。来道程(1600-1673),来氏大房第十六世,与四房十六世的来集之关系甚密,《萧山来氏家谱》中的来道程小传即为来集之所写。道程幼时即禀赋不凡,“授以唐诗数百首,客至,朗诵如悬溜,众咸器异之”[7]。他和来集之都“早著文誉”。自从在一次文社相识后,便“欢相得也”。来集之自言“大抵予诗文与公交相点定也”,在今存《倘湖遗稿》中,存有多篇来集之为来道程所作的序、赠诗,来集之《南行载笔》《南行偶笔》《两纱》中皆有来道程序或评点。
灯语斋本《红纱》旁批三十七则,出尾有音释、出尾评。倘湖小筑本《红纱》旁批五十四则,出尾有音释、出尾评、总评。两本出尾评相同:“几池砚水一样笔尖,涂抹试官似鞭策小驴牛耳。真所谓笔落鬼神愁。”倘湖小筑本多一则总评:“排调若雕龙虎绣,方驾士衡;敷词如金谷桃园,连镳实甫。岂从米家之一峦,抑亦成都之三峡?”总评以陆机、王实甫的文辞和米芾的画境为对比,以称赏来集之的杂剧词曲之胜。
1.评点内容比较
倘湖小筑本保留灯语斋本旁批二十五则,另有三十七处评语与灯语斋本相异。评语的不同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所评对象一致,但字体书写或内容相异:
(1)灯语斋本【么篇】旁批“笔阵奇恣”,倘湖小筑本为“笔阵奇资”;
(2)灯语斋本【鹊踏枝】旁批“忙里闲情”,倘湖小筑本为“入情”;
(3)灯语斋本【村里迓鼓】旁批“好仙诗”,倘湖小筑本为“仙诗”。
以上第一、三则应属刻工之误,或异字,或脱字,第二则是评语内容的改动。
二是灯语斋本有,倘湖小筑删去的旁批有九则:
(1)(上场宾白)……俺本姓胡,这些秀才就顺口儿教我做个胡涂。(旁批)未能免俗。
(2)(上场宾白)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旁批)作家。
(3)(上场宾白)也有叫我白丁秀才的,也没有别字。(旁批)偏是白丁会中黄甲。
(4)【么篇】……教他堕泥犁,吞不尽铁丸万斛。(旁批)此时也定要归罪红纱。
(5)【那吒令】……似这般昨日肥,却怎生今日瘦。(旁批)化工。
(6)【寄生草】(第一支)……(白)翻空不做题目,甚合俺的意思。(旁批)好文章。
(7)【寄生草】(第二支)……(白)这番不用着我的红纱了。(旁批)脱换都好。
(8)【村里迓鼓】……送得五百两茶果银子在此。(旁批)贱价。
(9)【么篇】……谁知我却检些书札的高下,银子的轻重。(旁批)下流得掺文柄,应是造化忌才定了个文字的优劣。
以上评语是因为脱漏还是评者有意删除,已难知晓。其中第三则和第九则对科举弊病揭露太过犀利,恐为清代当局不容。且来集之中进士后,担任过南京同考官,也是试官身份,不宜再用“下流得掺文柄”这样尖刻的评语。
三是倘湖小筑本新增,灯语斋本所无的旁批有二十五则:
(1)(上场宾白)(净扮试官上云)文章无价,究也凭不得主司。(旁批)金针度矣。
(2)(上场宾白)文章有价,究也凭不得。(旁批)四句西江吸尽。
(3)(上场宾白)……都道我当初有些盛名,□(窓)下揣摩已熟。不想我今日词章久别。(旁批)真语。
(4)(上场宾白)……毕竟文字也不识的,只取些笔意罢了。(旁批)试官妙诀。
(5)(上场宾白)……以银买试,何不以试卖银,因势起官,怎好有官忘势?(旁批)《演连珠》耶?
(6)(上场宾白)……我只是帘分内外,关节通风。一星星的(旁批:天成趣对)七十镒而受。
(7)【么篇】……(宾白)自征辟谊衰,孝廉道废,天下奔于词赋。(旁批)可叹。
(8)【么篇】……(宾白)若论究竟豪杰,到底飞腾,止争迟早。譬诸混豹于鹿,试其文彩则殊,久且从而变化。(旁批)物理纤悉,殆犹杜工部之诗、张茂先之赋耶?
(9)【混江龙】……他则念鹏飞天外云千里,我则问他豹隐山中雾几秋。(旁批)藻矣,而劲工矣,而不觉其工。
(10)【油葫芦】蜡烛风残点点流。那瘦炉烟一缕抽。那一个不捻断髭须仰着头,眼非蒙看不出天横斗。(旁批)非老山人出游,一泒熟路,安能摹画至此?
(11)【油葫芦】……(宾白)渐觉的青巾零落,无能复理;蓝袍破碎,殊为可怜。却又一谋谋做了蒙师,和那些小学生朝朝点卯。(旁批)秀才读此,有不堕泪者,非情也。
(12)【那咤令】……似这般昨日肥,却怎生今日瘦。谁敎你前日风流。(旁批)噬哜何及?
(13)【鹊踏枝】耕着砚儿畴,仗着笔儿矛。这贡院也不是一个寻常所在,分明是六道轮回,一霎时的变出个马卒公侯。(旁批)可作一部《劝学文》。
(14)【鹊踏枝】……(宾白)(仙云)呀,却原来这试官是有眼无珠的,也不消红纱罩着。(旁批)近来试官,恐不消用红纱者颇多。
(15)【寄生草】这的是珍珠载,怎撞着盲贾收。土埋千载干将绣,泉沉万轴绞绡绉,尘封百宝瑚琏陋。(旁批)工致而艳,实甫有之,汉卿不及也。
(16)【寄生草】迷高下,混薰莸,似你这样眼睛看文章呵,便似那鼓矇师,夜认虫鱼籕。(旁批)酷似文长律诗。
(17)【胜葫芦】……看邪做直,将无做有。倒与那些好文字做冤仇。(旁批)试官好借口。
(18)【么篇】……倒不如蟠木先容,不论根株朽。靠自己的有七言诗句,靠祖父的有两行顿首。(旁批)二对不减《三渡城南》。
(19)【么篇】……(宾白)孤寒的只怕主司不公,有抱负的只怕主司不明,都说我做试官不至如此,及至做到试官,却又忘了。(旁批)骂秦桧,笑卢杞,今古一辙,真堪喷饭。
(20)【后庭花】他冷甘甘虀和粥,似苦行僧耐着晨昏昼。受满了冰雪三冬苦,投至得风涛万里秋。(旁批)《霸亭秋》风味,数行托出。
(21)【青哥儿】……直穷到那石鼓岐幽,禹字岣嵝,万国齐州,三岛十洲,兽韵呦呦,鸟语鸲鵃,麟凤龙龟,蠓蠛蜉蝣。(旁批)《玉镜台》有此雄壮,逊此幽灵。《四声猿》有此险奥,逊此光华。
(22)【寄生草】金马门将身困,长安陌见花羞,怎敎那苏秦归当得个妻僝僽。(旁批)极势利,极炎凉的是妻妾。
(23)【幺篇】……只是文章到底一般同,还问他年运胜当年否?(旁批)眼前至理,似施元美派头。
(24)【赚煞】……谁道个不遇离娄遇瞽瞍,屈折了笔下蛟龙,埋没煞字中蝌蚪。(旁批)奇语。
(25)【赚煞】……俺这一匹儿薄红纱也遮不尽试官羞。(旁批)一句话尽题目。
2.倘湖小筑本《红纱》评点特色
来道程两次评点《红纱》,在倘湖小筑本和灯语斋本中具有一脉相承之处,体现在从制文角度评点戏曲,如灯语斋本中有“作家”“好文章”“脱换都好”等评语,倘湖小筑本增加了“金针度矣”“《演连珠》耶”。来道程虽无举业,但他钟情于科举制业,《倘湖遗稿》卷六收《式如兄手录自订制业序》,即是旁证。来道程以作文的思想评点《红纱》,既是诗文词曲艺术融通的体现,也是其热衷文章之事的心灵体验。
倘湖小筑本《红纱》中,来道程增加了二十多则评语,体现出灯语斋本所不具备的特色。
一是以诗文名家作比。灯语斋本《红纱》评语,没有直接对作者来集之杂剧造诣的称赞,也没有用前代名家名篇作为比附对象,仅仅就剧情而评论。与之不同的是,倘湖小筑本评语对前代人物作品多有引用,如:“物理纤悉,殆犹杜工部之诗、张茂先之赋耶”,“透脱活现,杂之子瞻表联中,应难分别”,“工致而艳,实甫有之,汉卿不及也”,“酷似文长律诗”,“《霸亭秋》风味,数行托出”,“《玉镜台》有此雄壮,逊此幽灵。《四声猿》有此险奥,逊此光华”,“眼前至理,似施元美派头”。
来道程的评点比附兼及诗赋词曲,从诗赋之杜甫、张华,到杂剧之王实甫、关汉卿,以及施元美(应为“施君美”或“王元美”)、徐渭等一系列名家,以及沈自徵《霸亭秋》、关汉卿《玉镜台》、徐渭《四声猿》等作品,都被拿来衬托来集之曲文的高明。
二是情节上对试官判卷着眼更多。《红纱》以试官判卷为主线,灯语斋本评语注意到试官的糊涂势利,在富豪之仆和显宦之仆前去贿赂时,评以“转口快”“是听人情惯家”,指出试官在钱财和势力面前丧失公正。关于试官判卷的心理,在第一支【寄生草】试官说“翻空不做题目”处,评“好文章”,是从科举制艺方面评。倘湖小筑本评点对“试官”这一形象着墨颇多,仅在试官上场时,就有增加了六则评语,除前文所列“金针度矣”“《演连珠》耶”外,还有对试官的“文章有价”评以“四句西江吸尽”,对试官入仕后疏远词章评为“真语”,对试官不识文字而以文意判别评为“试官妙诀”,对试官“帘分内外”收受贿赂评其“天成趣对”,【胜葫芦】试官“看邪做直,将无做有”,评其“试官好借口”,【么篇】试官自言做试官后不公不明,评其“骂秦桧,笑卢杞,今古一辙,真堪喷饭”。
这些评语不是针对《红纱》中的糊涂试官一人,而是具有普遍性。刻画出原来真才实学的试官,通过在官场、科场浸淫,成为了用“妙诀”而不是用“红纱”判卷的常态。正如【鹊踏枝】中评到“近来试官,恐不消用红纱者颇多”,试官的不公正、不廉明似乎已经成为不言而明的现象。
(二)《碧纱》的两种评点
入清之后,来集之积极入世的思想消退。他著书隐世,对《碧纱》剧作了大量改动,并请胞弟来荣评点。由于文本的改动和评点者的更换,《碧纱》评点在两次刊刻中差异很大:灯语斋本旁批五十九则,倘湖小筑本旁批十二则,其中相同的评语只有第四出【双调·新水令】旁批“纱帽偏会俗人”。灯语斋本每出均有音释、出尾评,倘湖小筑本仅保留了第四出的音释、出尾评。
1.来道程对《碧纱》的评点
灯语斋本初刻《两纱》时,来道程对《碧纱》的评点较《红纱》更为用心,其中不乏见解。一是将《碧纱》纳入戏曲类作品,和经典曲家作品比附,如:第一出【红绣鞋】旁批“轶关驾郑”,第三出【乌夜啼】旁批“临川点头”,将来集之的剧作与关汉卿、郑光祖、汤显祖比附。同时,来道程从音韵、作法、关目、当行等方面作评,如第一出【中吕·粉蝶儿】旁批“韵甚,媚甚”,涉及曲律、合韵。第二出【滚绣球】旁批“这些都是饶舌,却不如此,便不成戏”,从戏曲创作时要考虑通俗性、趣味性、大众性的角度作评。第三出【牧羊关】旁批“的是女郎口角”,反映了对人物当行的追求。二是评点中透露对来集之的理解、同情。如第二出【耍孩儿】旁批“字字感愤淋漓”,第三出上场宾白旁批“元成或是王播后身”,第三出【哭皇天】旁批“谁记得我元成心事”。来集之作《碧纱》时尚未中进士,扬名之前的读书人所体会到的心酸、压抑,多与《碧纱》中王播所受侮辱相通,来道程此类评语,都是对来集之知己式的的体贴关心和深厚情感。
灯语斋《碧纱》中,可见来道程从诗文角度作评的趋向,这在倘湖小筑《红纱》评点中有所发扬。如第二出【朝天子】旁批“这等拙诗此时便该笼着”,第三出【梁州第七】旁批“好脱胎”,反映出来道程对诗文制艺的严肃,以及用文章技法评戏曲情节的自然融通。
2.来荣对《碧纱》评点
来荣(1616-1657),字元启。其父来舜和去世时,来荣年仅十一岁,后依兄集之以居,“昼则虀粥同盘,夜则风雨联床”。清朝建立后,“谢去举子业,不求仕进,闲闲十亩以终其身”[8]。来荣布衣而终,没有著述存世。倘湖小筑刻本中,元启评点了《碧纱》和《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两种杂剧。
来荣对《碧纱》的评点仅十一则,多是对剧中某句曲文、宾白的感发,没有承袭戏曲评点的通常视角,显得非常随意。如第一出:
(生扮王播上云)……倒是一个“十有”先生,那“十有”是:有琴,有剑,有舌,有笔,有天幕,有地席,有随地之江山供我题咏,有弥天之鸟雀助我笙歌。还有两件是,有僧人可倚,有木兰花可玩。(旁批)前八件空的却实,后二件实的反是空。
剧中王播以为安居惠照寺,但却被奚落驱赶。因此来荣评“后二件实的反是空”。
又如第二出【滚绣球】“我待要口吟芳草招公子,手折丹花眺影娥”,来荣评“何等骚雅”。曲文中使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和汉武帝玩月影鹅池的典故,来荣看来,既是文词的骚雅传统,也是王播精神飘逸的写照。
(三)《挑灯剧》评点比较
《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简称《挑灯剧》)在两次刊刻中,文本差异很小,倘湖小筑本在上场宾白前增加了一曲【意难忘】,灯语斋本无。评点方面,两本旁批都是六则,但评点对象和评语均不一样,灯语斋本评语有:
(1)(上场宾白)旁批:透出情关。
(2)(上场宾白)旁批:女菩提现空说法。
(3)【商调·山坡羊】【前腔】旁批:只得埋冤。
(4)【五供养】旁批:细香瘦影。
(5)【玉山供】旁批:可怜煞人。
(6)【川拨棹】【前腔】旁批:杜陵花也应溅泪。
倘湖小筑本评语有:
(1)【意难忘】宾白旁批:最上机锋。
(2)【意难忘】旁批:缁衣黄冠何处开口。
(3)【商调·山坡羊】【前腔】旁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又增一重罪案。
(4)【江儿水】旁批:语上伤心。
(5)【五供养】旁批:异想奇情,钻心透骨。
(6)【侥侥令】旁批:略将冷雨一点,他人便痴讲大半幅矣。
如果说《碧纱》的评点,来荣在倘湖小筑本中只是闲淡描写,远逊于投入颇多精力的来道程,那么在评点篇幅短小的《挑灯剧》时,来荣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他选取来道程评点过的曲词,却表达了异于来道程的独特感受。虽然总体上两人都以“伤情”为评点中心,来荣的评语更深入人心。他对《挑灯剧》的重视,还体现在旁批之余的出尾评:
道心佛骨,尘境俱空,小青可以死矣。山水空蒙,呼之或出,小青殊未死也。死于情,生于文,文与情相与轮回,而小青因之。弟元启。
来荣在出尾评后署留姓名,体现他对来集之的恭敬,也反映他对这段评语的审慎。小青故事自明末开始流传,广为文人喜爱。来集之的《挑灯剧》仅写夜读《牡丹亭》一幕,对小青遭妒、不幸身死的情节未作介绍。来荣的评语超出了《挑灯剧》的文本范围,是他对才女小青的深深同情。他看出小青身心空寂,死亦无憾,而她的情思载于文词,虽死犹生。小青是情的化身,也是文的本体。
来荣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长期生活在兄长的关照和光环之下,他选择默默农耕,孝悌为上。来荣对《碧纱》描写科举人生遭遇的剧作不感兴趣,对抒写才情的《挑灯剧》颇为偏爱,为了解其文学兴趣有所助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来集之早年作《两纱》附《挑灯剧》,灯语斋付刻时,诸多亲友题辞作评,其族兄来道程对《碧纱》评点详细,《红纱》《挑灯剧》颇简省。入清后,来集之对《碧纱》文本做出大幅修改,包括曲词、宾白、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其中多有仙道思想,与灯语斋本多谐谑、讽刺不同。来集之“晚岁读《参同》,与黄冠往来,终非苦县之学”[9],或许是《碧纱》描述仙道思想的一个来源。
倘湖小筑重刻《两纱》附《挑灯剧》,与灯语斋本在行款外观和题词序跋等方面都有不同,评点更是不同。来道程对《红纱》增加诸多评语,不仅将《红纱》与前代名家名作比附,分析其中的音韵、角色等,还善于从文章制艺角度评点杂剧。来荣评《碧纱》《挑灯剧》语言简省,在比较中不难发现其对《挑灯剧》中小青才情与不幸的倾重。
《两纱》从灯语斋本到倘湖小筑本,《碧纱》的文本被注入了新的寄托和内涵,但评点却由多变少,缺少新意。《红纱》的文本没有变化,但评点由少变多,反映了来道程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变化。《挑灯剧》的评点在两种刻本中基本平衡,体现了评点者的不同趣味和思维。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原文,均出自国家图书馆藏灯语斋本《两纱》(善本书号:17020)和倘湖小筑本《两纱》(善本书号:12415),后文不赘述。
② 国家图书馆藏倘湖小筑《两纱》三种,善本书号:12415(言言斋藏书),04107(吴梅藏书),00598(与《秋风三叠》合刻,存《红纱》),三者内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