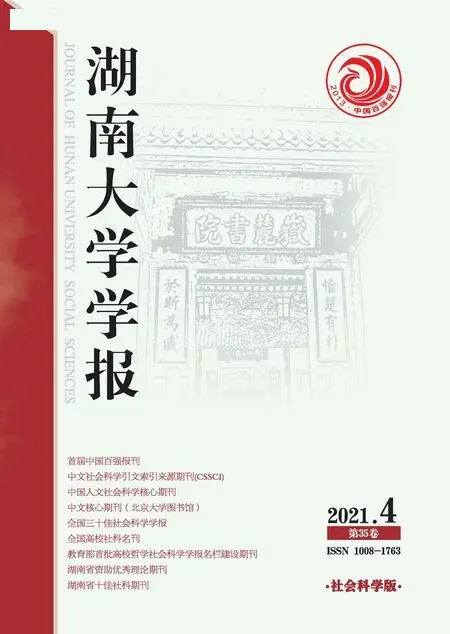论林语堂小说的感觉叙事*
李 珂,肖百容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本文所谓的感觉,是指人体器官的各种体验,具有个人性、非系统性和短暂性特征。感觉没有经过提炼和综合,具有原初性和个人性,同时是非公共性和非理性的,不可能通过集体传承下去,无法形成系统,也难以作为历史保留下去。由于它的这些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理性精神和美学追求格格不入,因此中国文学基本上否定以感觉作为叙事的中心。现代作家大多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其创作的重要宗旨,按理不会排斥叙述感觉,可惜真实的文学史不是如此,现代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依然是以西方的新“道”对抗中国传统的旧“道”,以道反道,虽然文学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文学叙事的风格依旧没有什么改变(1)新感觉派小说是个例外。不过在它那里,感觉一般只是修辞手法,不是叙事的动力甚至宗旨。而且,新感觉派小说所写的感觉往往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群的集体记忆,不像林语堂小说所写的常常是具有个别性的个人感觉。。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人在事件面前细微的身体反应,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心理反应,没有多少作家去关注。他们对于事件的叙述,往往是直接上升到情感反应的层面,甚至是直接上升为精神层面的书写。林语堂不属于这一类型。他是最注重感觉叙事的作家之一,而且形成了特色。所以,虽然林语堂小说总是标榜其宗旨是宣扬道家、佛家或儒家等,正如唐弢先生所言,其小说人物类型化,没有鲜明的性格[1],却依然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印象就来自作家对人物生动、具体、个别化的感觉书写。
一 感觉决定事件
一般来说,情感与思想是小说中事件的起点和落脚点,也是事件进程的原动力,感觉只是陪衬和背景。可在林语堂的小说叙事中不是这样,感觉往往成为事件的缘起、转折和终点。《京华烟云》里中秋之夜的木兰“陶然半醉,微微有点儿蔑弃礼法,使木兰真正感觉到自我个人的独立存在,为生平所未有。她谈笑风生,才华外露,心中愉快。上床就寝之时,觉得自己完全摆脱了平素的约束限制,毫无疑问,是由于酒的力量。躺在床上时,生平第一次体味到她是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生活,而确实是有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那么一个世界”[2]292。我们从上引文字中很容易可以看到,“微醉”“陶然”“愉快”等词描绘的是木兰的身体感觉和灵魂体验;是和立夫的爱情使她找到全新的感觉,回归了自然之我。后来关于木兰的爱情婚姻故事都是以这一晚的感觉为基础展开的。《朱门》里的杜氏兄弟为是否放水救济农民问题争执得像仇人似的,谁都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最后却因为一次晚宴化干戈为玉帛。晚宴的菜肴是春梅烹饪的,她高超的厨艺引起兄弟俩美妙的口舌感觉。“酒使他肠胃大开,他心情爽朗多了,美味的鱼翅也使他开怀不少。等香菇炖肉端上来,他充满手足之情。”[3]276白天时的剑拔弩张气氛,以及冲天火气被稀释了。在这里,主人公的感觉延缓了故事的发展速度,虽然最后兄弟俩还是闹翻了,但因为这一时的肠胃感觉,使事件变得曲折起来。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杜柔安,是作者倾力打造的一个形象。和描写木兰一样,林语堂从她的感觉世界入手来塑造她的心路历程,深入细致地揭示她的人生轨迹。小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她所感受到的怀孕的恐惧、焦虑和道德上的羞辱感受,然后又描绘她经历这些痛苦之后所体会到的初为人母的欢乐和欣喜。首先是身体上的感觉,随后上升到精神体验,“柔安透不过气来,她对身体从来没这么敏感过。内衣胸罩越来越紧,胸部更加丰满,正是生儿育女的前兆。不管她吃得够不够,睡得够不够,体形却一天天扩大。傍晚她洗了一个澡,她决定不戴胸罩了。她觉得舒服些,连浴衣也不扣。她站在镜子前,心里有着成熟妇人的感受”[3]299,以及灵魂的愉悦。这是杜柔安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感觉不仅是事件过程的“决定者”,也是事件意义的“赋予者”。在林语堂笔下,感觉不只是停留在身体层面,还和人物的精神层面息息相关。木兰的爱首先通过自然身体的感觉表现出来,然后上升到精神层面。木兰之前由于种种束缚,在荪亚与立夫之间,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只能做出传统文化品格的坚守。当立夫被抓后,独自探监后的木兰,“立了一刹那,似乎犹豫不定,转向右,走了一小段儿。她的腿有点儿瘸,心噗嗤噗嗤跳,忽然颤抖了一下儿。她几乎都没法儿站稳,站住喘喘气儿。倚在一根电线杆子上”[4]304。对立夫安全的担心促使木兰冒险夜闯北京卫戍司令部。西方文化中的爱情至上又让她进入感觉的自由状态,犹如激荡奔涌的潜流,不可抑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个人主义的,个体牢牢地附着于家庭和阶层。林语堂对他自己生活过的中国社会和传统更是了解,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承载着不少的社会角色。“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5]203如何去掉这些角色对我们的束缚呢?林语堂认为,只有在全新的感觉冲击下,个人才能冲破一切,找到自然真我,而爱的感觉就是其中之一。他让他最钟爱的人物木兰,在爱的强烈体验里找到冲破束缚的力量。不是爱情的伟大,而是爱情的强烈的快乐感觉刺激,改变了木兰对世界和万物的看法,尤其是让她认识到了自我和外界的真实关系。于是她真实地去爱立夫,也细心地去体会个人的孤独和爱的绝望。小说中关于木兰、孔立夫、莫愁等的爱情叙事线索多头、情节复杂,但是一切都是围绕木兰的感觉起始、铺排开来和延展下去的。最后木兰下那么大的决心想要离开北京去杭州生活,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在情爱里所体会到的那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觉。孤独让她希望离开吵闹的北京去杭州,“住在西湖边儿,过个简单平静的日子”[4]271,像苏东坡那样半隐半市。
个人感觉苏醒是一个人获得自主的表征之一,因为一旦个体感受力增强,他的生命力就会随之增强,他的个人意识便会全面觉醒。但是漫长的历史一方面使人类摆脱了野蛮与兽性,另一方面也让人类远离了生物性感觉,或者刻意拒斥生物性感觉。在这种所谓的进步与文明里,人类生活得越来越“体面”,却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快活。从文明里“醒觉”成了寻找感觉的必要前提,而保持感觉的正常和敏锐则是人的“必修课”。例如,“在睡过一夜之后,清晨起身,吸着新鲜空气,肺部觉得十分宽畅,做了一会儿深呼吸,胸部的肌肤便有一种舒服的动作感觉,感到有新的活力而适宜于工作;或是手中拿了烟斗,双腿搁在椅子上,让烟草慢慢地均匀地烧着。”[6]130这种诗意的惬意,就来源于身体的直接性、敏锐性的感觉,林语堂意识到感觉快乐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一切快乐都来自感觉,“精神的欢乐须由身体上感觉到才能成为真实的欢乐”[6]140。把感觉快乐强制性地去掉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是空虚的便是畸形的。
林语堂非常喜欢“放浪者”。他认为:“人类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6]13。 “放浪者”追求的是去除文化与文明对真我的遮蔽,展示自然之自我。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扮演“角色”,而角色是外在强加于人的,具有强迫意味。诚如歌德所言:“你就是你的表现。戴上卷曲的假发,将鞋跟提高几寸,你还是你,不是别的。”[7]78不能把假发和高跟鞋变成本质,不会因为一副假发或一双高跟鞋而发生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说一定有变化的话,那变化的是外在人的“角色”看法。林语堂书写人物的真实感觉,就是为了反对传统社会角色对人的束缚。他大部分小说都以反角色压制为线索安排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最终意义指向感觉的恢复和感觉的升华。
二 感觉的升华
在重大事件里,人的感觉被发现和释放出来,并实现生命的升华。而林语堂所谓的重大事件,不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个人生命感觉角度来说的。
感觉来自外界的刺激,其中主要包括一些重大的客观事件。林语堂的小说叙述人一生发生的关键性事件及其带来的各种感觉。但是这些感觉有深刻与浅淡之分,深浅之分决定于事件的大小。生与死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对于自由的个人来说,它们比任何社会性大事件留给别人的印象更深。林语堂特别爱写生与死带给人的感觉。林语堂在《朱门》里通过描绘和分析杜家小姐柔安的分娩感觉,写她成长过程的一个节点:她由分娩的身心快乐体会到了自然的神圣,从此挣脱了道德的压制。她的身体完全放松,精神完全自由。这种快乐和放松也是她对新生小生命的爱意表现和未来憧憬,她也由此上升到对普遍生命的热爱和理解。虽然人物的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但它会以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方式对她的未来发生影响。个体生命将感觉安置在身体的某个地方,永久储存起来,然后每到关键时候就会将其释放出来。林语堂小说经常写人物在关键时候沉溺于感觉世界里,他们不以外在的有形行为应对外来刺激,而是寻找感觉,体悟生命,获得解脱或提升。林语堂小说对女性分娩感觉的书写,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里女性缺席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作家重精神情感轻体验感觉的传统,给读者留下更加真实和深刻的印象。
林语堂既写生的喜悦给人带来的快乐感觉,同时也写死的痛苦给人带来的恐惧、悲伤和绝望与希望。最让人产生切肤之痛的就是亲人的死亡,“丧亲”就是由于所挚爱的人的死亡而引发的丧失体验。这是身体上及心理上的强烈痛苦感受[8]358。到了一定年龄,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丧亲之痛。亲人之死带给人的种种感觉,对个人当然是沉重的打击,会留给你终身难忘的痛苦。不过,丧亲之痛感给人的也并非一味都是负面影响。为了适应斯人已逝的世界,哀者也必须面对其他的衍生压力,学习此前由逝者负责的技能,恢复日常活动,继续生活,投身于新的活动及目标[8]359。心理学家雷雳的话辩证地揭示了丧亲事件对于个人存在某些积极方面的意义,丧亲之痛可以导致人身体和精神各方面的严重失常,但是它又可能促进人的修复和成长。据库不勒·罗斯等学者分析:“完成了悲哀过程的人会继续向前,更健康地生活,而那些没有经历彻底的悲哀过程的人则仍时时想着死者,精神无法自拔。”[9]632和现代许多作家如郁达夫、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一样,林语堂也喜欢写死亡。但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不同,他写死亡不是为了表达个人情绪、批判社会现实,而是为了表现人的成长历程,把死亡之痛作为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翻越的障碍。所以,他特别注重描写这种痛苦的感觉。他从不在死亡事件发生后直接写人物感受到的痛苦,而是从其独特感觉入手表现其心灵和精神上的成长。比如在《京华烟云》里,木兰的女儿阿满参加学生爱国游行被杀后,她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怒骂刽子手。作者此处笔锋突转,不写木兰的激动情绪,而是写她对感觉的细细品嚼。木兰缓缓地打开记忆,回忆起自己人生中许多重要的瞬间带给她的感觉。她从童年开始追索,将人生中的大事件与自己当时的感觉联系起来,一一回味。这个过程是静穆而漫长的,她的心灵沉浸在对生命中那些“剧烈瞬间”的感受之中。木兰由对这些瞬间感觉的回忆,悟透了生与死的秘密,理解了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刹那和永恒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就代表不朽的生命。”[4]270瞬间感觉之中就有永恒,木兰超越了女儿之死对她的致命打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她不再痛苦,反而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和看法,开始享受日常生活,感受世上事物的美好。“有时在下午,她甚至和孩子们一同去捡柴,自己亲手折断树枝子,这时锦儿在一旁看着,微微地笑。这对木兰都有诗意,因为很新鲜。”[4]349它表明木兰的心灵已经摆脱了女儿之死带给她的痛苦,开始学会用这种日常感觉的体验,摆脱外界的侵扰,捍卫身心的快乐。感觉的发现、升华及延展是林语堂小说叙事的逻辑链条。
感觉是真实的,有时也是可怕的。《红牡丹》中的红牡丹,是个感觉崇拜者,虽也善良,关键时候却漠视道德的束缚。她敢作敢为,热烈追求自己喜欢的一切,尤其是情欲,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她的权利。在和白薇、若水谈话间,牡丹公开宣称,“在爱情上谁要什么理性智慧?所要的是火般的热情和坚强的肌肉”[10]269。小说叙述了她几段疯狂的情爱故事:与金竹产生肉体之爱,精神上崇拜堂兄孟嘉,然后厌弃了纯粹的精神之爱,喜欢上强壮的傅南涛,又试图与已为人夫的安德年出走私奔。万平近认为,林语堂笔下的牡丹“是一个风流放浪的现代西洋女子”[11]234。牡丹的行为全是感性的冲动,谁也无法劝说和阻挡她,包括她的父亲。但是,安德年儿子之死和自己濒临死亡边缘的经历带给她强烈的震撼,成为她感觉追求路上的转折点。尤其是小鹿鹿之死,引起了红牡丹的内心挣扎和冲突,最终她决定向所谓的“善”屈服,与安德年分手,不伤害那个已经丧子的女人。牡丹所经历的这些“特别的死亡事件”,给她带来了“剧烈的欢乐与痛苦”,在一系列强烈的刺激和碰壁之后,她慢慢走向成熟,对生命产生了豁达的态度。她的性情趋于沉静而平和,她的精神进入自由的境地。
在林语堂的小说中,人物在感觉上得到释放的另一方式是“去我”。“去”是一种丧失,不过丧失的是“小我”,是陷入感觉迷醉中的自我,所以它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获得,是一种感觉的升华。人物获得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物超越了自我的束缚,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如果我们认为中秋之夜木兰发现自己爱上立夫一事,是她自我感觉觉醒的表现,那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在逃难路上的所见所闻给予木兰的是精神的觉醒。“姚木兰想过‘平民生活’,但很快就被现实生活所打破。”[11]192茫然而艰难跋涉的难民、炸毁的大桥、露天旷野、路边无食而亡的妇人,头戴钢盔、威风凛凛、斗志昂扬的中国战士,“上战场,为家为国去打战,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4]494。那震撼人心的歌声,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使木兰觉得“一个突然的解脱,深深在内,非语言可以表达”[4]495。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深重灾难的国家,中国战士的爱国热情,木兰毅然决定放弃自我的小世界,投身民族救亡的队伍里,则是她在感觉上的升华。木兰的心受到深深的震撼,她感到自己解脱了。她从什么东西里解脱了呢?三十年前木兰发现自我之后,就一直在追求完美的个人生活。但是她却遭遇了与立夫分手、女儿被杀等一连串事件,备受刺激的木兰和丈夫荪亚迁居杭州,可是杭州的如画山水却也不能抵挡外来事件的冲击,她的丈夫有了外遇。林语堂安排荪亚有第三者,其目的就是对木兰陷在自我感觉之中,脱离群体,只活在自我世界里的行为的否定。另一方面,他让痛苦的木兰在群体里重拾生命的快乐。不过这个群体与以往给予木兰种种社会角色压抑的群体不同了,它不是一个利益群体,也不是一个政治群体,更不是一个宗派群体;它不会让木兰迷失自我,反而会让她的感觉升华,找到生命的皈依。百姓的受难和群体的伟大深深震撼了她,她心甘情愿交出了自己,开始做一个“英雄”(2)“英雄”本是一个群体性称呼,木兰的行为纯粹出自个人自我的愿望,所以此处加上引号。。木兰从“小我”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感觉世界的升华。小说写她的感官再一次变得异常敏感,她也恢复了对人事的新鲜感,这种升华使她能够既身在尘世又能超越世俗社会,内心无比自由和舒畅。
在林语堂的小说中,对于这些在重要事件里感觉得到升华的人物来说,不是外在世界埋没了“我”,应该说“我”就是整个世界。作者安排木兰在战乱中跳出“小我”,让她最终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感觉到无比的愉悦,实现生命的超越,是有特别的、深刻的寓义的。这种境界的“去我”,不能归结为迫于社会角色压力的道德完善行为,而是完全的生命自我完善的行为,是主体和客体交融而非对立的状态。融汇在众人之中的“我”与所有人都是和谐的、融洽的。个人汇入历史长河,自我的故事似乎在此就要结束,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像木兰人生中经历过的其他重要的瞬间一样,都给她带来全新的身体感觉和精神愉悦。这是真真切切的肉体感觉,既是一刹那,也将会永恒。
三 林语堂感觉叙事的意义
首先,林语堂的感觉叙事深度诠释了新文学的个性解放主题,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程序,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演变出发[12]43。林语堂的小说发现了人的感觉的重要性,揭示了个人感觉的发现与释放在追求人生幸福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林语堂区别于传统作家甚至其他现代作家的地方。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个性解放的主题,对新文学做出一定的贡献。他穿越了虚伪道德和社会政治的迷雾,直逼个人最本然的存在。对于感觉的发现和表现,使人的品性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从而把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揭示出来,展现给读者一个个富有体温,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这是对中国文学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充满道德说教色彩的封闭系统的反叛。在那样一个系统中,值得肯定的人物被作者往上“提拔”,一层又一层,离根基越来越远,没有外在养分可以吸取,自身也无再生能力,生命力越来越弱。在这种小说中,推动故事情节的总是道德角色和社会理想,是集体性事件,而在林语堂的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则是自然人性,是个人事件。这种自然人性的发展轨迹并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自然程序,而是人物复杂个性的展示,变幻多姿又真实丰富。而在传统小说中,人物的个体感觉被抽除了。比如《三国演义》讲述“蒋干中计”的故事,全然不讲周瑜、蒋干的感受。其实,如果加入对两人的感觉叙述,小说将会丰富有趣得多,也能刻画出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但是为了突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小说放弃了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共名的要求把他们的内心矛盾和前后不一的感觉排挤了出去。
其次,林语堂的感觉叙事赓续和创新了传统。对身体快乐与精神自由之矛盾与统一问题的探索和阐释,体现了林语堂对人生的认识深度。林语堂在《八十自叙》等文章中都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存在状态,声称自己是“一捆矛盾”[13]245。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矛盾存在状态并无多少困惑,反倒是一脸自豪。原因之一在于这捆矛盾容纳了林语堂的人生价值观、生态观和现代观。对感觉的肯定即是对个人本位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肯定,而追求感觉的升华和超越则是对五四以来个性思潮的反思,显示出林语堂试图在个人和群体、自我和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个体即是自由的,也能和他人、他物和谐相处。林语堂的感觉叙事集中火力攻击传统理性,又对无视社会群体规则、放纵个体自我的行为予以否定,这显示了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复杂而深邃的认识。林语堂的小说在对感觉的肯定和否定之间安排情节,设置人物,营造情感氛围。《红牡丹》既是对牡丹充沛生命活力和叛逆精神的张扬,又是对她盲目任性的性情的委婉批判。他先让她的生命激情充分展现,让她获得前无古人的欲望满足,包括生理的和精神上的,后又让她面临前所未有的悔恨恐惧和感觉混乱。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苦难,红牡丹生动鲜明的个性和情感特征随着这种起伏有致的情节变化凸显了出来[14]398。《京华烟云》中的木兰、《风声鹤唳》中的梅玲也被做了同样的安排。这些人物是立体的、复杂的,作者的情感态度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富有张力的。
林语堂关于感觉的发现和自由的冲突与统一的观点,显示出他在充分尊重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又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过这种警惕与传统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迥然两异,它是一种认识上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纯粹道德上的固执保守。这样一种认识又让林语堂区别于欧美持现代主义文艺观,尤其是自然主义文艺观的作家们,在他们看来,现代的文学作品应该任凭人的感性肆虐、宣泄,不要加以节制。林语堂在这一点上继承、融汇了中西文学传统,同时又超越了中西文学传统,体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情怀。
最后,林语堂的感觉叙事弥补和纠正了新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某些偏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个性解放,但是其大部分作品具有观念先行的毛病。比如爱情小说,往往很少写爱情的细腻感受,而只热衷写爱情宣言。尽管五四小说主题里爱情主题的数量占据绝对第一的地位,但是读者对其中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是模糊的,不熟悉的,因为他们的情感世界本来就是不具体不清晰的。个人生命体验进入新文学作品,但在大部分作家那里只是概念化描写。书写个人,就要书写个人生活,而个人生活离不开绝望与希望,欢乐与悲伤等身体内部的感觉活动,这些感性活动就组成了人的感觉世界。到了林语堂的小说中,人物的感觉被凸显出来,他们不仅在感受和体验着生命的欢乐和悲苦,而且,他们往往还要刻意表达甚至张扬自己的各种感觉。每个人物的感觉世界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比如《京华烟云》里的木兰。作者宣称她是道家的女儿,但有意思的是,通过小说细节,我们还是能发现她与生活在尘世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具有非常个人化的喜怒哀乐。或者说,作者并没有把她铸成一个理想的模型,而是写成了一个生动的“她”。她没有本来拥有的质素,她的属性在尘世生活中发生着万花筒式的变迁。木兰性格丰富,亦道亦儒,非道非儒,洒脱灵动。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细致地叙述了木兰内心世界里的“紧张”感觉。她在社会赋予她的角色与对自由的追求里焦虑、矛盾、挣扎着。虽然木兰对自己的“紧张”感觉的来源是不自知的,但她清楚地感觉到了作为女性的被压抑、被束缚的痛苦。她渴望做个男孩子,无拘无束地生活,那样她才觉得完全自由,而不是现在这样处处受制于人。林语堂对木兰“紧张”感觉的叙述,就是对个性初醒时期一个女性真实感觉世界的表达。小说里一系列的叙事,都是围绕木兰内心的“紧张”感觉铺开的。走失、与立夫相恋、分手、南迁等,这些事件连在一起,充分展示了木兰的“紧张”感,而“紧张”感又把这些看似零碎的叙事集中起来,不至散逸出去。从《风声鹤唳》中的人物丹妮身上,可以进一步佐证林语堂感觉叙事的特色。丹妮,原名梅玲,在个人生活上也曾放荡不羁。她曾想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具有博雅这样优越条件的男人的妻子。但在民族抗战的热潮中,通过与难民的接触,她从感官上受到了冲击。她无比激动地说:“大家的形象都不再是个人。我们似乎融入——一个生死圈中。禅宗的顿悟不就是如此吗?”[15]361她觉得她不再是一个人,感官的体验强烈到使她无法不与他们一起感受磨难和残酷的现实,无法不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渴望食物。在另一方面,她也从这些原本她认为丑陋的人的身体上感受到了美的存在,这些身体勤劳、勇敢、充满韧性,不时散发出生命的神性。感觉的冲击改变了丹妮的幸福观。这就使得林语堂小说的叙事显得独特而富于变化,不至于陷入相爱—反抗—失败(出走)的模式之中去。
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不与自我自然属性作斗争,个人获得了解脱和自由,走上了愉悦的道路。与欧美小说中那些痛苦地走向自主的人物不同,林语堂的小说一般不安排事件以对人物进行心灵的拷问。尽管他小说里的人物也会经历坎坷,需要克服诸种障碍才能获得快乐,但他们在人格上是独立的、自足的,他们主动面对磨难,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傲视一切,客观的困难因而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们的反叛行为虽然激烈,却不会与社会完全对立,不会撕碎传统伦理,不会对包括自己的父母亲在内的所有人进行报复,林语堂的小说一般不会去写弑父事件。但是,既然以反抗社会角色对人的压制为重要主题,林语堂的小说也不能不写人物对家庭角色的反叛,只不过他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往往被淡化处理,比如《朱门》里杜家兄弟的矛盾就被春梅的美食消淡了。而且林语堂几乎不写父子(或父女)冲突,最多是叔侄冲突。如《朱门》中的柔安,她与父亲关系很好,她走向自我的道路是从反抗叔父开始的。她从记者李飞那里知道了人应该自主独立,在爱上李飞的同时也准备寻找自我。觉醒的她发现了叔父的虚伪,也感觉自己在叔父家舒适的生活充满暗礁,于是决心行动。最后,她离开了那个束缚她的家,离开了叔叔杜范林的掌控,获得自我身体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和新文学大多数作家不同,林语堂没有把“压迫者”的角色交给父亲。这一方面是他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他的感觉叙事的特点决定的。文章开头谈到过,感觉是个人化的、非群体性的,所以来自感觉世界的压抑与反压抑也是个别化的,不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冲突”,而只是具有个别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以撕裂人类最自然的情感为基础而获得升级,成为吸人眼球的大事件。《京华烟云》中曼妮的变化就具有典型的个别性。丈夫死后,她安安静静地呆在深院里,不喜欢外出,也不喜欢和外界交往,一心遵从礼教,做贞洁寡妇。这时候的她,自以为能够压制个人欲望。但被木兰带着一顿疯玩之后,礼教的束缚慢慢从身上脱落,她找到了自己,内心感到了自由,表情显得轻松愉快了。不过小说叙事没有按照现代小说的模式进行,她不是从此走向反叛之路,而是从容地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内心自主了,却依然不与外界产生明显冲突。林语堂没有在曼妮身上寄予宏大的理想,只是把她作为一个具有特性的女人来叙述。林语堂的感觉叙事是那样平静,这和中国新文学甚至西方现代文学都不同。他没有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伤害群体的根本道德原则,可是却在一定的深度上开掘前行。林语堂的感觉叙事与他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密切相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