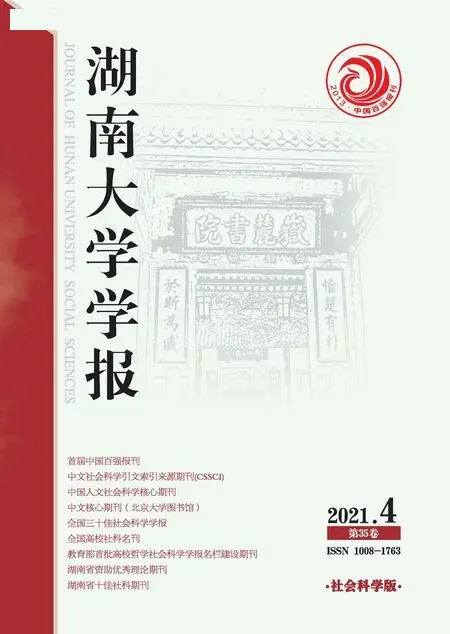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历史*
武志勇,刘子潇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公元1世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燕地》中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1]。中国和日本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其层面之广阔深厚,其内涵之丰富多彩,其影响之深刻全面,是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缘上的接近与文化上的深度交融,促进了中日两国密切的交流往来。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悠久。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日文的《老子》译本达到74种,相关研究论文349篇,研究著作93部(1)“老子思想域外传播与接受”课题组统计了2020年4月以前世界主要语种包括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的《老子》译本、研究著作情况。。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流传与积累,其译本数量与著作成果颇丰。本文试图梳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历史性传播轨迹,并对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一 地缘的接近和文化的深度交融是传播的有利条件
(一)地域的接近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陆地资源稀缺。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独特位置,导致海啸、台风、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其族群的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其关注重心。
国力的强盛,可以促使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上的接近,为老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古代中国,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发展上,一直领先于日本。中国唐代,政策的开放、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开明,吸引着万邦来朝。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学习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宋元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及京杭大运河的重修,我国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中日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密切。在两国长期的经济往来与政治互动中,华夏文明与道家典籍逐渐传入日本,并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二)文化的深度交融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熏染与滋养,对中华文化兼收并蓄。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以前日本的文化发展,得益于对古代中华文化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其中,汉字的传入、禅宗的兴盛及遣唐使的助力,推动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
1.汉字的文化联结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日本汉文教育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日本社会阅读中华典籍,包括《老子》原文的文字障碍。中日文化的深度交融体现在对汉字的共同使用上。文字作为一种抽象媒介,是文本世界建构与表达的核心元素。受众往往通过阅读文本,在脑海中形成文字符号所描摹的意义载体,进而完成对于陌生事物的概念认知[2]。正如摩尔根所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3]。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凭借古代中国的强盛国力、文化魅力,在东亚地区被广泛接纳和使用。《日本国志》曾记载:“日本古无文字, 而有歌谣, 上古以来, 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 乃假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 如古《万叶集》所载和歌, 悉以汉字填之。”[4]汉字填补了日语书写方式的空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官方文字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在普通民众中也普及开来。汉字传入日本,成为中日在文化上的联结纽带,促成两国十分密切的文化交往。
日本的汉文教育历史悠久,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汉文教育史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5]。公元1世纪中叶,日本列岛已经出现并有人使用汉字[6]。公元6世纪至12世纪,是日本汉文教育的萌芽阶段,日本皇室与贵族成为学习主体,圣德太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自幼习内教、学外典。在广泛吸纳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他对道家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和研究。《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评赞圣德太子:“亦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在这里,“三玄”指的就是《老子》《庄子》《周易》。由此可以证明,圣德太子曾研习老庄之学。江户时代,汉文教育延展至日本民间,汉文教科书应运而生。明治时代,汉文成为初中教授的科目之一。日本社会努力学习汉字、接受汉文教育,为老子思想及其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建立了良好的文字媒介基础。
2.佛教东传的纽带作用
在精神文化层面,日本的佛教文化被深深打上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烙印。早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禅宗就已传入日本。镰仓时代,先是荣西两次入宋,嗣法虚庵怀敞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后又有道元入宋,嗣法长翁如净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自此,禅宗开始作为独立宗派在日本发挥影响[7]。禅宗由于适应了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治上的需要,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作为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原本就与道家多有相通之处[8]。日本中世的禅僧对待道家典籍怀有开放的态度和高涨的研究热情,一批关注老学的禅僧由此出现,入宋僧圆尔辨圆、吉田兼好便是代表。圆尔辨圆撰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1353)记载了有关《老子》的内容。吉田兼好在《徒然草》(成书于1336-1392年间)中提到“与人无争,枉己从人”“书籍如令人赞叹的《文选》《白氏文集》、老子的篇章和南华经等”,表明当时日本僧侣的精神生活甚至价值观念受到老子思想影响。佛教的东传成为老子思想与著作顺势向日本传播的纽带。
3.日本遣唐使的助力
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中介人”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与“自我叙述者”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却与其有着类似的观察视点,是构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9]。日本遣唐使便是活跃的“中介人”。他们将大量的中华典籍(包括道家典籍)带回日本,扩大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自汉朝起,日本便和中国开始遣使交往。公元57年,中国与日本进行了第一次官方交流活动。盛唐时期,日本以朝圣者的心态向唐朝学习先进文明。自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 唐太宗贞观四年) 六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出使唐朝起,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 (公元894年, 唐昭宗乾宁元年) 九月止, 日本共派出了19次遣唐使,跨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唐朝盛行的“崇道”之风深刻影响着日本使节。奈良时代,吉备真备曾两次跟随遣唐使团入唐,将大量的道家典籍带回日本。平安时代,日本遣唐使来华愈加频繁,持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内在思想精髓。“入唐八僧”之一的空海,在《三教指归》《文境秘府论》中对《老子》《庄子》原文有所引用与论述。
此后,宋元时期中日民间密切的贸易往来,明清时期中日交往,均加强了华夏文明及道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二 老子思想在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特点
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一千四百多年,各个时期的传播特点各不相同。
(一)7至17世纪:自上层社会开始的老子思想传播
日本飞鸟时代,老子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圣德太子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其中所谓的“当色”,即指将紫、青、赤、黄、白、黑六色,分别配于德、仁、礼、信、义、智六阶。六字之首的“德”配以“紫”,这种以紫为上的观念便是中国道家所崇尚的。604年,圣德太子制定与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五条“绝餮弃欲,明辨诉讼”的说法,与老子所主张的“少私寡欲”、清净无欲思想是相通的。而其“绝餮弃欲”的表达方式,则可能来源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0]。《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或多或少地浸染着道家思想。
奈良时代,日本士人对老子人生哲学的崇尚与道家词汇的广泛运用,表明老子思想已逐渐被日本知识分子接纳,渗入日本文化,产生社会影响。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成书于712年。作者安万侣对混沌初开、天地形成之始的阐述,深受道家思想的启发。他将“无名”“无为”等具有道家色彩的词语引入《古事记》,汲取并内化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念。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于751年完成。收录在其中的116首诗作,频繁引用诸如“无为”“至德”等体现道家精神的词汇和典故。魏晋时期,尊崇老庄的竹林七贤成为《怀风藻》中诗人们追捧的对象。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秉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成为《怀风藻》中身在官场、厌倦名利诗人的向往境界,引领着他们去追寻无欲无求的超脱心境与自由适意的生活。古麻吕《望雪》诗句“无为圣德重寸阴”,山前王《侍宴》诗句“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藤原总前《侍宴》诗句“无为自无事,垂拱勿劳尘”便是明证。越智直广江在《述怀》中所写“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表达了对老庄之学的崇尚与对自在生活的追求。留学僧释智藏在汉诗《秋日言志》中写道:“因兹竹林友,荣辱莫相惊。”其中,“竹林友”便指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荣辱莫相惊”的人生态度,明显来源于《老子》十三章中“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如惊,是谓宠辱若惊”。日本汉学家蜂屋邦夫指出,古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方面直接阅读了老庄的著作,一方面以竹林七贤作为六朝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理解六朝时代的思想[11]。竹林七贤成为日本士人认知、理解老子思想的桥梁。上述史实表明老子思想被当时日本文士所推崇,并熏染其精神生活。
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897)、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4)、具平亲王注解的《弘决外典钞》(991)、藤原明衡的《本朝文粹》(1037-1046)等著作,直观地呈现出当时日本社会对于道家经典的阅读与借鉴热情。
镰仓时代,《老子》注释本增多。除了平安时代流行的《老子》河上公注本、《老子》王弼注本外,以贾大隐的《老子述义》、玄宗注《道德经》,以及林希逸口义释本为代表的“口义”本,行文通俗易懂,逐渐在日本社会流行。
17世纪以前,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传播态势。飞鸟时代,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日本上层社会传播,圣德太子是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圣德太子崇信儒佛,此时期日本社会对于道家思想的接受与理解较为零散与肤浅。自奈良时代开始,老子思想逐渐渗透至知识分子阶层,构成其精神生活的一大侧面。平安、镰仓时期,明白晓畅的“口义”本实现了广泛传播。
(二)17至19世纪中叶:《老子》注本在日本流传开来,诠释角度多元
17-19世纪,也就是日本的近世时期。江户时代中期,幕府的财政危机导致整个统治阶层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为了缓解这一经济难题,统治者实行了诸多干涉农民生产生活的措施,加强征收农民的贡租。农民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农民起义频发。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同样反映在思想领域中。随着德川体制的动摇和衰落,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乃至整个儒学,也开始显露出其弊端。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呈现由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趋势[12]。提倡“无为而治”“无欲无求”的老子思想,突破儒学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控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精神慰藉。
江户时代,从事老庄研究的各类学者和老庄注本有169家,其中研究《老子》者多达91人[13]。林罗山日译的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1868),导致河上公注本几乎在日本绝迹,转而被林希逸注本所替代。此外,林罗山还著有日文注释本《老子抄解》,将老子思想作为一个独立思想体系进行研究[14]。海保青陵与东条一堂分别著有《老子国字解》和《老子标注》。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不再局限于对《老子》原文的简单复述,而是将老子思想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这一时期老学的发展,离不开徂徕学派的倡导与推进。荻生徂徕重视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并善于阐释和运用老子“道”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作《辩道》(1654-1911)开篇提到“道难知亦难言,为其大故也”,这来源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经世论上,荻生徂徕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看做“圣人之道”的重要补充,认为“与其轻率地施以拙劣的治疗,不如行老子之道”。另外,荻生徂徕的安民观念是“使民安稳,所谓安稳,就是无饥寒盗贼之患,邻里可信,其国显于世界,其家安居乐业,如此渡过一生”[15]。这与《老子》在第八十章所描述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具有相通之处。同时,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渡边蒙庵的《老子愚读》(1743)、服部南郭的《老子考》、广濑淡窗的《老子摘解》等,均为徂徕学派研究《老子》的代表著作。
近世时期,老子思想与著作以注本的形式在日本社会流传开来。这一时期,《老子》译本数量颇丰,诠释角度较为多元。
(三)19世纪中叶以后:老子思想与著作影响学界和社会多个方面
1.二战之前
作为一场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现代化变革,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全面现代化之路。二十多年间,日本日渐强盛的国力与繁荣发展的经济,导致国内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迅速蔓延,传统伦理道德渐失,社会精神生活危机日益凸显。为了着力恢复日本的道德意识,回归社会的淳风美俗,日本学者试图在《老子》中寻找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慰藉。
这一时期,涵盖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和平成时代,老子思想与著作传播广泛,日本哲学界、文学界均深受影响。
首先,老学研究成果丰富。1900年,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出版。他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在序论、纯正哲学、实践哲学(伦理、政策、用兵、处世论)和结论四部分,对《老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1915年,宇野哲人在《支那哲学史讲话》中,对《老子》中的“本体论”“伦理学”“政治论”进行了论述,讨论老子的宇宙观。1921年,京都大学创办了《支那学》学刊,标志着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确立,也表明日本对中国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6]。作为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和奠基者,武内义雄坚持考证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相关文献进行逐一考证。他的《老子原始》(1926)、《老子研究》(1927)行文措辞十分严谨,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贡献的杰作,也是日本现代学人研究老子思想的奠基之作。小柳司气太的《老子讲话》(1927)、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展开》(1927)、《关于〈老子〉研究法》(1933)、斋伯守的《支那哲学史概论》(1930)及鹈泽总明的《老子的研究》(1937)等,都是日本现代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伊福部隆彦从宗教学视角,撰著了《老子精髓》(1941)、《老子眼藏》(1942)、《老子道讲话》(1943)等专著。狩野直喜将考证学与思想史相结合,从“老子传”“老庄学派的起源”“老子的学说”三方面展开老学研究。长谷川如是闲则采用“inside”和“outside”兼在的社会学方法,对《老子》进行研究。他认为《老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日本文化创新需借鉴的一种思想资源。
其次,是对文学的影响。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将老子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我是猫》(1904-1906年间)、《虞美人草》(1907)曾多次出现“无为而化”“老子曾说过”之类的语句。他在《三四郎》(1908)、《其后》(1909)等作品中,提出了“则天去私”,体现了老子“少私寡欲”“道法自然”“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观点。哲学家西周曾说:“物实为阳极,虚为阴极;其于色,白为阳极,黑为阴极;其于知觉,热为阳极,寒为阴极;其于光,明为阳极,暗为阴极;其于有机性体,生为阳,死为阴……”他关于宇宙进化与自然界发展的观点与老子阴阳学说存在相通之处。中江兆民吸收了老子辩证法的思想,坚信“大”“小”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人们的努力和创造,身体之“小”必能转化为才能之“大”。他力图以此思想来提高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促成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时期《老子》译本的数量也在增加。小柳司气太的《日译老子》于1920年出版之后,分别于1924、1935、1940、1956年再版4次。山田爱剑的《新译老子谈话》(1925)、西田长左卫门的《老子》(1927)、广濑又一与清水起正共译的《英日双译:老子、大学、中庸》(1933)及关仪一郎的《老子注集大成》(1942),均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译本。
2.二战之后
日本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均面临着反思与重建。老子所倡导的“利万物而不争”“自然无为”“无欲无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的思想,与当时日本民众强烈反战的情绪十分契合。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日见频密。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热络互动,是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此阶段《老子》日语译本的数量增至49本。1954年,诸桥辙次的《老子讲义》出版。之后的五十多年间,该书再版5次。奥平卓于1964年出版的《老子》也有4次再版。小川环树的《老子》(1978)、守屋洋的《新释老子》(1984)、深津胤房的《老子细读》(1994)、新井满的《老子:自由译》(2007)、加岛祥造的《老子新译:来自无名领域的声音》(2013)、田中佩刀的《〈老子〉全译》(2019),也是日本现代时期的主要译本。
与老子思想相关的研究著作也纷纷面世。1945年之后,日本所发行的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有91本,代表作有田所义行的《老子的探究》(1959)、大野实之助的《老子:人与思想》(1975)、大滨皓《老子的哲学》(1986)、志贺一郎《老子正解》(2000)和安富步《老子的教诲》(2017)等。
日本全面现代化以来,《老子》的日语译本与相关研究著作实现了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老子思想与著作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三 结 语
通过审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传播活动,可以发现其传播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良好的地域优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东传日本的有利条件。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地理上的接近性,于飞鸟时代便早早接触老子思想。历经千余载的传播与沉淀,老子思想已渗入日本文化的多个层面。
第二,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一员。日本民众长期使用汉字、接受汉文教育,减少了其阅读《老子》原文的识读和理解困难。
第三,在老子思想与著作的东传过程中,禅僧和来华使节开放的文化态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兼容并包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加速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也促进了日本的老学研究。
第四,日本民众精神层面的需求推进了老子思想与著作的东传。具有普适价值、倡导“无为而治”的老子思想,成为剧烈变动时代和艰困时期日本民众的精神慰藉。
第五,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老子思想与著作,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