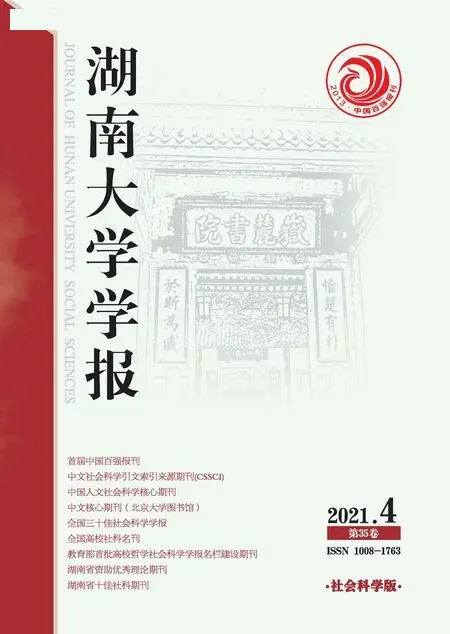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张 天 杰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浙江 311121)
清中叶兴起的常州今文经学派,致力于阐明《春秋》公羊学,并以公羊学解释群经,而《论语》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寓意于《春秋》,还体现在《论语》之中。刘逢禄(1776—1829)曾说:“《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1]451故而,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开始以公羊学解《论语》,到宋翔凤(1777—1860)的《论语说义》,基本完成了以公羊学解《论语》的探索。其他如戴望(1837—1873)的《戴氏注论语》、王闿运(1833—1916)的《论语训》、康有为(1858—1927)的《论语注》则在常州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一系列的《论语》学著作充分说明了《论语》一书在清代今文学家心目中的地位[2]140-165。
其中的刘逢禄与宋翔凤,同为常州今文经学家庄述祖(1750—1816)的外甥,庄、刘两族同为科举世家,他们的姻亲关系特别值得关注[3]37-52。庄述祖则是庄存与(1719—1788)的侄儿,庄存与著有《春秋正辞》等,庄述祖则著有《夏小正经传考释》与《尚书今古文考证》等,他们都没有《论语》学的著作。庄述祖对于刘、宋两位外甥非常器重,曾说:“刘甥可师,宋甥可友。”[4]13268这两位对于今文经学的发展,确实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刘逢禄著有《尚书今古文集解》《左氏春秋考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谷梁废疾申何》等系列的《春秋》学著作。他的《论语述何》二卷作于嘉庆十七年(1812),对于宋翔凤当有较大的影响。不过,《论语述何》卷数较少,内容也较为单薄,只能算是开启公羊学解《论语》之学风,而宋翔凤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论语说义》十卷则颇成体系。此后的戴望则深受刘逢禄和宋翔凤的影响。他说:“望尝发愤于此,幸生旧学昌明之后,不为野言所夺,乃遂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5]252只是戴望的以公羊学解《论语》,渐渐远离“说义”,又转回到了注疏的体例,故名《戴氏注论语》。至于再往后的康有为《论语注》公羊学的因素更弱,增加了许多西学的因素。所以说,以公羊学解《论语》,创立“说义”之体的宋翔凤,因其书的自成体系而成为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部。
宋翔凤(1777—1860),字于庭、虞庭,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的为学与其他汉学家一样,都是从文字训诂入手,早年受长于考据的父亲宋简(1757—1821)的影响,后又跟随其舅父庄述祖,得常州庄氏今文经学之传,后来又游学于段玉裁(1735—1815)而得许郑之传,故宋翔凤也常以朴学自居,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朴学斋”。宋翔凤《四书》类的著述多为传统的朴学,如《论语郑氏注》《孟子刘熙注》《孟子赵注补正》《四书释地辨证》,属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辨之类;而《论语说义》与《大学古义说》则属于今文经学,多有发明微言大义。他另有综合性的《四书纂言》四十卷,则包括《大学注疏集证》《中庸注疏集证》《论语纂言》《孟子纂言》,亦属于前者。宋翔凤其他的重要著述还有《五经要义》《周易考异》《尚书略说》《小尔雅训纂》,以及学术札记《过庭录》等[6]。
作为今文经学家,最代表宋翔凤学术特色的当为《论语说义》,此书又名《论语发微》,刘宝楠(1791—1855)等后来的学者多有引用。宋翔凤曾说:“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传,自七十子之徒递相授受,至汉时而不绝。”[7]7也即今文学传自七十子之徒,故他们所传的《春秋》与《论语》得“圣人之意”。至于为什么他在完成了《论语纂言》之后,又要写一部《论语说义》,他自己在《序》中说:
《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蒙尝综核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7]1
孔子在《论语》之中传达了微言大义,也即“性与天道之言”,故而解说《论语》当“寻其条理,求其旨趣”,从而发明“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宋翔凤还认为汉代以来诸家的注解,与《论语》之微言大义“时合时离,不能画一”,故而他在已经完成了“综核古今”的《论语纂言》之后,重新删繁就简,“别录私说”以成此书。所以在《论语说义》之中,他的重新解说最具个人特色。然而学界对《论语说义》如何以公羊学进行群经互证,并建构会通一贯的士大夫之学等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 《春秋公羊传》与《论语》之“微言”
在宋翔凤看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就是指:
《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7]18
《春秋》继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无敝,是谓能久。然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录内略外;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见世,见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7]109
“三科九旨”等,与此处说的“张三世之法”,都是公羊学家所谓的《春秋》“书法”,比如讲社会依照“三世”而进化,“传闻世”即“据乱世”,此时《春秋》之“书法”为“录内略外”,详录国内之事而略述国外之事以作区别;“所闻世”即“升平世”,则为“内诸夏外夷狄”,也即必须区别诸夏与夷狄,区别文明程度;“所见世”即“太平世”,则为“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就连蛮荒之地也得以教化故“若一”。若是懂得《春秋》之微言大义,就能“百世可知”,也即能平治天下。
今文学家以《春秋》来解《论语》,为什么必须用《春秋公羊传》呢?宋翔凤曾指出:“《左氏》所载,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义也。”[8]150他在《论语说义》中也说:
所谓“其文则史”者,谓左丘明之书也。丘明为鲁太史,自纪当时之事,成鲁史记,故汉太常博士,咸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求《春秋》之义,则在《公羊》《谷梁》两家之学。[7]98
《春秋》虽有三传,但《春秋左氏传》重在记录当时的历史事实,所以在今文学家看来则不能传《春秋》之微言大义,传《春秋》之义的只能是《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两种。宋翔凤的《论语说义》援引以《春秋公羊传》等今文学的典籍为主,不过在论及史实之时,则也有援引《左传》,故对于古文经学也不偏废。比如,关于太姒去世的年龄,若据今文家说《文王世子》所记当已百余岁,而据古文家说《周书》则年五十耳,于是宋翔凤指出“揆之事理,古文说是”[7]129。可见,宋翔凤以其朴学之底色,以事理而考辨今古文经学的矛盾之处。比如,宋翔凤在论及《论语·阳货》“子之武城”与“公山弗扰以费畔”两章之时,就以《公羊传》为主,附之《左传》,从而说明其“张三世”的观点: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公羊》说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说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谓文公继所传闻之世,当见所以治衰乱;昭公继所闻世,当见所以治升平;哀公终所见世,常见所以治太平者。于此之时,天必于此之时,天必示以除旧布新之象,而后知《春秋》张三世之法。圣人所为,本天意以从事也。北斗运于中央,中官之星也,盖除旧布新于内,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国,内外秩如,所谓治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故见除旧布新之象于明堂。有星孛于东方,文王,房心之精,在东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将兴周道于东方,而天命集、仁兽至。故天所以三见其象,而《春秋》之法备矣。[8]210
此处列举了文公、昭公、哀公三个时期,分别“有星孛”,《公羊传》直接说明“孛”就是“彗星”出现,《左传》则说“除旧布新”,然后宋翔凤再以公羊学来加以说明,文公为“据乱世”、昭公为“升平世”、哀公为“太平世”,三世之间则是轮流更替。而天上彗星的出现,则是预示“除旧布新之象”,由此则说明《春秋》“张三世之法”,是圣人“本天意以从事”。最为关键的则是“明文王之法度”“有星孛于东方”,说明“兴周道于东方”而“明文王之法度”,因为文王为“大辰”、为“房心”,故据明堂之位而除旧布新,“内诸夏而外夷狄”。
宋翔凤往往还认为只有以公羊学解《论语》,才能确切地理解。比如,《论语·学而》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
道,治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继体为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当没身不改,难以三年为限。惟人君治道,宽猛、缓急随俗化为转移,三年之后不能无所变易。然必先君以正终,后君得有凉暗不言之义。苟失道而死,则为诛君,其子已不当立,何能三年无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学,无博士所传;经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系《闵公》篇于《庄公》下,博士传其说,曰:“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传曰:“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论语》微言与《春秋》通,明三年无改之道,以示继体为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谓七十子丧而大义遂乖乎?[7]11-12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主要针对“继体为政者”,子继父位而成为人君,治道必当注意宽猛、缓急,故不可随意变易;三年之后则又当随风俗而有所转移。若泛论父之教子,那么“父之道”必当“没身不改”,不必以三年为限。在宋翔凤看来,孔子此条原本针对“继体为政者”这一“微言”,只传于今文学家,也即《公羊传》之《闵公》篇,指明其为“封内三年称子”等,而其具体依据则是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观点。
《论语说义》以《春秋公羊传》来解释《论语》,另一特色就是将《论语》多章还原于春秋的历史语境,并以今文经来加以发明,同时也有对古文经的批评。比如,《论语·八佾》中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句,宋翔凤首先引《白虎通义》,比较了《公羊传》与《左传》,也即古、今文之间的差异:
《白虎通·礼乐篇》:“天子八佾,诸侯四佾,所以别尊卑。乐者,阳也。故以阴数,法八风、六律、四时也。八风、六律者,天气也,助天地成万物者也。亦犹乐所以顺气,变化万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传》曰:‘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诗》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谓也?佾者,列也。以八人为行列,八八六四人也。诸公六六为行,诸侯四四为行。诸公谓三公、二王后;大夫士北面之臣,非专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谨案:此今文家说,春秋时皆言女乐二八,亦诸侯四四之数,《左传》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说,服虔遂解为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说,非也。[7]26
《白虎通义》继承董仲舒等公羊家的学说,对于“八佾”的由来及其意涵都作了细致的讲述,且与《公羊传》和《诗传》互证,由此很好地说明了当时鲁国季氏礼乐之僭越。而宋翔凤则特别强调《左传》以及服虔解“八佾”的错误,用以说明古文家说之非。另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宋翔凤以《春秋》之《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比较,然后在小注中指出:“《左传》以闰月不告朔为非礼,此刘歆窜入,与两家立异。《左氏》不传《春秋》,凡释经之处皆歆窜入也。”[7]47这也是在说明古文家说之非,此处不再赘言。接着宋翔凤结合“八佾”的问题详细说明了鲁国当时诸侯、大夫之间相关礼仪的具体情形,然后指出《论语》此章,孔子“盖为文公言之”,也即鲁文公之世,孔子“显斥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孰不可忍”之事,而隐含了对鲁文公的批评:
文公敢薄先王之制,敢乱继统之法,荒谬惑乱而为君,是之谓不仁。……季氏于是时出,而僭天子之礼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于文公之世。《论语》显斥季氏,而深没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7]33
鲁文公之世“继统之法”混乱,“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故而其臣子季氏“僭天子之礼乐”。所以宋翔凤特意指出《论语》“显斥季氏,而深没文公”,孔子的批评虽不明说,而实际则隐含了这些微言大义。接着“季氏旅于泰山”一章,宋翔凤指出:
《春秋公羊》说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封内者,则不祭也。”若季氏旅于泰山,则非祭泰山。……季氏专礼乐征伐,妄谓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为旅,几于新莽之受命,充其僭天子之量,又何所不至?《春秋》之作,乌可已乎?[7]34-36
宋翔凤更近《春秋公羊传》而强调季氏为“旅”,不可称为“祭”,不过季氏的狂妄,“旅于泰山”也是僭越之举动。将《春秋》与《论语》互证,在《论语说义》一书中极为普遍,就《八佾》等篇来看,确实能将《论语》之义理说得更为明白了。由此二章可知,宋翔凤对于《论语》的解释,建立在他研究《春秋公羊传》以及《白虎通义》等今文家著作的基础上,从春秋历史、政治出发,把握了孔子师弟问答的语境,故而其发掘《论语》之微言,也就更能言之成理。
在《论语说义》一书中,《春秋》大义确实是随处可见的,贯穿全书。我们先来看其书之首末,都围绕《论语》之微言而展开论述。《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章,宋翔凤说:
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弟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立学之义,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时习”,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有朋自远方来”,谓有师有弟子,即秦汉博士相传之法;“人不知而不愠”,谓当时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当素王,则又何愠于人?……《礼运》记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先王兴学以治人情,圣人设教以维世,故作君作师,统绪若一也。[7]4
在他看来,孔子虽受命作《春秋》,但其本人的微言则存于《论语》之中。由于体例限制《春秋》记事为主,故许多微言只得寄托于《论语》。其首章“时习”之义就是上古之学校教导士人的方法;“有朋自远方来”则是说为学必当有老师、有弟子,后来秦汉时期的博士相互传习也就是如此;最后“人不知而不愠”则是指孔子“设教以维世”“作君作师”,然而只有“天”知道孔子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六位君子一样,“受命当素王”而继续“君子之号”,春秋之君臣则无法知道孔子之“受命”,那么孔子又会“何愠于人”呢?另外,到了最后的《论语·尧曰》一篇,宋翔凤先是联系《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章,对孔子之微言,联系公羊家的“通三统”之义,加以重新诠释:
此孔子微言也。……是中庸之为德,乃自古圣王相传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为至也。文、武既远,斯理绝续,五德之运,将归素王,故孔子叹为“民鲜久矣”,而己当应其时也。[7]108
“中庸”之德,作为古来圣王相传的大法,自然普通小民无法知道,周文王、武王之后,此德归于素王孔子,而孔子以及后学则将之记载于《论语》与《中庸》之中:
故《尧曰》一篇,叙尧、舜、禹、汤及周,而继之以“子张问从政”,言“尊五美,屏四恶”,皆本执中之义而用之。复继之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与而受之,见素王之成功,遂发之于此,则孔子受命之事显然可知矣。……《为政篇》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明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于三正并冠以“春”“王”,盖知其所损益,则三代之理自见,其或继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于《周礼》。礼,今文家所传具在,惟知礼而后可以作《春秋》,以为后世有天下者之则,故圣人所以为百世师也,终之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以见《论语》一书,皆圣人微言之所存。[7]217-218
《尧曰》章的核心思想,在宋翔凤看来就是“执中之义而用之”,也即“中庸”之道;最后“不知命”章,则是在讲述孔子受命为素王之事。于是他又联系《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章,说此即“明三统之义”,夏、殷、周三代所传之理,记录于《春秋》。关于子张之问,宋翔凤另外还说:
素王受命之时,子张能知之,故问受命作《春秋》之后,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谓三百年也。孔子为言损益三代之礼,成《春秋》之制,将百十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盖以春秋继周,而损益之故遂定,虽百世而远,孰能违离孔子之道,变易《春秋》之法乎?[7]24
孔子受命为素王,子张已知,故而才问“十世”,孔子则回答如何损益三代之礼;子贡也已知,所以说通过损益三代之礼、乐,知其政、德,孔子将之记于《春秋》,指引后世则不止十世、百世,世世代代都不能违背。所以说《春秋》之外,就是《论语》一书记载圣人微言最多,特别是“礼”学。《论语》最后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和“不知言,无以知人”,这些不仅仅在说君子之道,还表明《论语》所存的是圣人微言。故《论语说义》全书最后,宋翔凤说:
赵岐说曰:“从孔子后百世上推,等其德于前百世之圣王,无能违离孔子道者。”其说与继周之义相为发明,吾故曰:仲尼没而微言未绝,七十子丧而大义未乖。盖其命义备于传记,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学深思者之所任也。[7]219
因为赵岐也说《论语》末章,在讲孔子之德等于“前百世之圣王”,所以宋翔凤进一步推论,说孔子“继周之义”,也即承继周代之德而为素王,故《论语》全书,都是记述作为素王的孔圣人之微言大义。孔子去世之后其微言并未断绝,七十子去世之后大义也未消亡,因为他们讨论“性与天道”等微言大义都被记载于《论语》之中,历经千百世而不被泯灭,于是真正需要好学而深思的,也就是《论语》一书了。所以有学者强调“素王”说是宋翔凤《论语说义》的核心[9]。
需要补充的是,在注解《论语》之时,宋翔凤希望学者从各章文字之中,多把握其中的“微言”,体会孔子之为“素王”,故必须注意“罕言”与“无言”之处。在该书末尾处,就说明了“《论语》一书皆圣人微言之所存”,指出“子贡以夫子之文章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为二”“子罕言利于命与仁”“予欲无言”等章都是“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7]218。宋翔凤认为“罕言”“无言”都隐含了“微言”。不过此处先看《论语·宪问》中的“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一章,宋翔凤在按语中说:
此孔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不得闻,又何能知“莫知”之叹?子与子贡互相发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际。际者,上下之间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浃,王道备,治太平以上应天命,斯为下学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传》曰:“末不以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尧、舜与天合德,孔子亦与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尧、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7]178-179
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贡又说夫子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莫我知也夫”的感叹,孔子与子贡、子夏等“互相发明,以探天意”。在宋翔凤看来,则还是希望读者在《论语》中体证天意,“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际”;与春秋时代的人事、王道一起体证,也即《春秋公羊传》所说的《春秋》大义,然而事实上孔子本人是与尧、舜一样与天地合德的,也即“知天”的。还有《论语·公冶长》中的“夫子之文章”一节,宋翔凤曾反复加以阐述:
《诗》《书》《礼》《乐》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隐以之显。《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见至隐。天人之际,通之以性,故曰“性与天道”,所谓“与”者,天人相与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则离道,圣人能率性则合道。道者,天道,戒惧乎不睹,恐惧其不闻,性与天道之学也。……则《春秋》斯作后之所传,有《礼运》《中庸》诸篇,畅明旨趣,时七十子者莫不闻。所谓不可得闻者,谓举世之人不可得闻,非自谓不闻也。[7]89-90
就《六经》而言,《诗》《书》《礼》《乐》四经,是七十子都能精通的孔夫子之“文章”;《易》与《春秋》则只有如颜回等少数弟子能精通,都是“性与天道”之学。因为《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前者由隐而显,后者由显而隐。孔子《春秋》成,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易》则只有好学的颜回能得而闻之。宋翔凤说:“故孔子系《易》,独著颜氏之子,《易》备一至十之数,惟颜氏得闻之。”[7]87“学《易》如颜子,乃可谓好学也。”[7]101所以子贡所谓“不可得闻”,是在说“举世之人不可得闻”,而不只自己感叹。关于“性与天道”之“微言”,《论语·子罕》中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宋翔凤作了进一步阐述:
尽此篇之文,皆以说圣人微言之故也。罕者,稀也,微也。罕言者,犹微言也。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存于几希之间,通乎绝续之介,故不可得闻者,谓之微言。与者,相与之际也。夫子赞《易》修《春秋》,弟子不得闻。……孔子存微言之教,以为百世之师者,备于“利与命与仁”之中矣。[7]132-133
在此章之中,解析的也是《论语》中的圣人微言,宋翔凤说“罕言”就是“微言”,也就是说《论语》的“性与天道”,本来就是“微言”,“存于几希之间,统乎绝续之介”,也是夫子“罕言”的,才是“微言”。孔子“赞《易》修《春秋》”,本是为了保存其“微言”,弟子们往往不得与闻,因为孔子的目的是“以为百世之师”,而功利、天命、仁义等具体的思想则也在其中。还有“予欲无言”章,则也可以作为补充:
无言者,微言也。子贡恐学者以无言为不言,故发问以明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即“无言”之谓。而性与天道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离、震、兑主四时,而七十二候环生于其中;《春秋》四时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鸟兽,皆统于阴阳终始,故四时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与天道者,微言也。观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后知微言之传,必明于天人之际也。[7]212
在宋翔凤看来,“无言”即“罕言”,都是指“微言”,子贡要学者明白“无言”并非“不言”,所以才会发问,而孔夫子“天何言哉”则指明其中的“微言”在于“天人之际”。再依宋翔凤的解释,《易》与《春秋》正好可以发明“天人之际”,比如“《易》以坎、离、震、兑主四时”,“《春秋》四时具”等,都是在说明“性与天道”的“微言”在此二经之中。至于孔子受天命“应素王之运”,还有《论语·为政》中的“五十而知天命”一句,宋翔凤说: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则命有尊卑。大夫命于诸候,诸侯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胥此命也。孔子知将受素王之命,而托于学《易》,故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盖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穷理尽性,知天命有终始。大过者,颐不动,死象也。孔子应素王之运,百世不绝,故可以无大过。[7]17
“天命”,宋翔凤认为就是指孔子受素王之命,其方式为学《易》,也即“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因此而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还可以无大过;“运”,百世不绝,故可以无大过,也即“从心所欲不逾矩”。宋翔凤接着还说道,孔子晚年志在复东周,所谓“《春秋》继周而作,百世可知”,就是以《春秋》追尧、舜之隆而已。
二 《周易》《老子》与《论语》互证
宋翔凤《论语说义》也不只援引《春秋》,另有许多引《周易》与《老子》以解《论语》的,其实也即其所认为的“微言”之处。
本文先看以《周易》解《论语》的几个例子。《论语·八佾》“韶乐尽美尽善,武乐尽美未尽善”章,宋翔凤以乾、坤二卦之《文言》等展开诠释:
《易》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群龙,众阳之象,圣人相继,有治无乱,尧、舜之事也,故其乐亦以九成。六,阴数。坤“用六。利永贞。”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六有龙战之象,文王与纣之事也。故乐以六成。《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尧、舜之时,直乾,积善之家也。禅让之际,天下比屋可封,民之恒性无不全善。此《韶》之所以尽善也。商周之间,直坤,其民比屋可诛,积不善之家也。征诛之后,殷之余黎陷溺其心,若在涂炭,天下未宁,余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尽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继治世言之也,乾之义也;言性未善者,为救乱世言之也,坤之义也。[7]65
引用《周易》乾九“群龙无首”及“尧舜之事”,坤六“龙战于野”及“文王与纣之事”,然后认为尧、舜之时暗合“直乾,积善之家”,而商、周之间则暗合“直坤,积不善之家”。故《韶》乐尽善尽美,“性善”,为“治世”;《武》乐则尽美而未尽善,“性未善”,则为“乱世”。这些论述其实与用《春秋》解《论语》发挥其中微言大义,功用是一样的。类似的还有《论语·子罕》中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
《易》以元、亨、利、贞为仁、义、礼、知,而乾为信,乾,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陈王道,故终之以公即位。《易》言君德之体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备。弟子撰微言,则曰“利与命与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荀氏说:“阴阳相和,各得其宜,然后利矣。”相和,犹言与也。惟利物足以和义,则元亨之德成,而贞固之事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义,而后见万世之性,正万物之情。故欲求性与天道,必求之利与命与仁也。与命者,率性也;与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备五德五行,仁则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则天命之性可以率,可以无终日之间违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无敌无慕,故罕言也。义,性也;利,义之用也,一也。与,比者,与命与仁也,始于以义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谓义,即所谓利也。[7]132-133
《周易》“元亨利贞”即“仁义礼知”。宋翔凤指出,义为体,利为用,义、利统一的关键在于“始于以义治我,乃能以仁治人”,而孔子的“微言”就在于“利与命与仁”之中,欲求“性与天道”也在于“利与命与仁”之中。简言之,义利之辨,当从天命、仁德入手。
再看以《老子》解《论语》,在《论语说义》之中也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如《论语·雍也》“居敬行简”章,引了《老子》第二章与第二十二章来进行互证:
《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者,诚也,诚为敬,故抱一即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即《论语》“军旅之事,未之学也”。[7]112
宋翔凤认为《老子》之中所说的“不言之教”与“为天下式”,其前提“无为”与“抱一”都应当于《论语》所说的“居敬”相通。也即儒家的主敬工夫,其实是与道家的“无”也是相通的。还有宋翔凤在解《论语·宪问》中的“修己以安百姓”章,引了《老子》第四十九章、第五十四章进行互证:
又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即《论语》“修己以安百姓”,非独任清虚者之所及也。[7]113
在他看来,《老子》“以百姓心为心”“修之于身”“修之于家”等,与《论语》“修己以安百姓”是相通的,《老子》所讲的“修”,并非“清虚”,也即不是简单的“无为”。接着他还说:
人君南面之术,则老子与孔子,道同一原。《论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又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言“无为而治”,五千言之文,悉相表里。惟孔子言诗书礼乐,所谓“文章可得而闻”,而道德之意,则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弟子述之,不致有支流之失。老子之失,则有放者之独任清虚,即居简行简,仲弓亦言其弊,非老子之本意也。[7]112
《论语》与《老子》互证,宋翔凤认为关键在于老子与孔子都有着“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同一原”。之所以需要举《老子》之言,则是因为《论语》原书重在《诗》《书》《礼》《乐》之文章,“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故而“无为”之旨需要参之以《老子》。当然《老子》之“无为”,若误读则也会产生“放者之独任清虚”的弊病,狂放自任之人的“居简行简”,冉雍(仲弓)也有批评,然并不是老子的本意。
还有《论语·里仁》中的“吾道一以贯之”章,则《周易》与《老子》这两种玄学之书,共同与《论语》进行互证,从而产生新的发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许慎云:“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故造文字,始一终亥。乾之初爻为一,乾象盈甲而藏于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义,归藏之法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为乾元,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也,于天为北辰,天之中至虚之地,虚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极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数,虚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之以通。
故《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此明虚一之义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7]80-81
《论语》中的“一以贯之”章极为简单,宋翔凤先引用了《说文解字》之释“一”,再从造字而引入《易传》之乾坤、阴阳宇宙生成论,以及《老子》第十一章、三十九章、四十二章说“一”之妙用,则“一以贯之”中的“一”的意思拓展了许多:
《老子》之说通乎《易》,与《论语》“一以贯之”说意相发也。《老子》又曰:“道盅而用之又不盈。”盅为虚,“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为不盈。又曰:“致虚极,守静笃。”致虚者,一也;守静者,不用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言一以贯之也。[7]81
此处宋翔凤点出了三种经典互证的理论依据,因为《老子》之说原本就“通乎《易》”,所以才能与《论语》相互发明。这里引了《老子》第四章、第十六章,再来补充说明“一以贯之”,还应当包括了“致虚”“不盈”“观复”的道理。换言之,“一以贯之”,就是以虚静往复之心理应对千变万化之事物,多种经典的互证对于《论语》之意涵,也就多有新的阐发了。
宋翔凤的《论语说义》以《周易》《老子》与《论语》互证,背后还有一个独特的推论。《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句,宋翔凤从郑玄注“老,老聃;彭,彭祖”,以及《世本》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商之守藏如周柱下,老子继彭祖为此官”与《史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等文献得出结论:
守藏、柱下可互称,殷《易》为《归藏》,文史、卜祝,大史所守,归藏在柱下,故曰“守藏”,彭祖、老聃递守之也。《归藏》,黄帝《易》,《老子》之学出于黄帝,故曰“黄老”。[7]111
黄帝始造文字,始一终亥,皆本《归藏》。……知《老子》所述,皆黄帝之说,《归藏》之说也。[7]114-115
此处的推论可谓大胆,因为彭祖、老子都是“守藏”“柱下”之守官,殷商之《易》为《归藏》,又源出黄帝,故而彭祖、老子之学都出于黄帝,也即出于《归藏》之《易》学。简言之,黄、老之学,即《归藏》之《易》学。宋翔凤还说:“又观十翼之文,则孔子赞《易》,亦多取于《归藏》。《易》《春秋》为微言所存,故皆从窃取之义。”[7]115那么孔子之《易》学和《春秋》学也都与《老子》同源,出于黄帝的《归藏》之《易》学了。黄帝造文字,“始一终亥”即《归藏》之《易》学,老子据以发挥,孔子也据以发挥。对此推论,宋翔凤也觉得太过大胆,故他还有补充说:
老子为黄帝之学何证?考黄帝号曰自然氏,“自然”之字,他书皆作“有熊”,独《白虎通义》曰:“皇帝号曰自然,自然者,独宏大道德也。”按,《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我者,盖黄帝之辞而老子述之也。……故老子自然之说,皆黄帝之说也。[7]113-114
黄帝之号为“自然”,证据来自今文经学的《白虎通义》,这就与《老子》一书“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一句可以对应,那么老子以“自然”为宗,本源于黄帝及其《归藏》。宋翔凤还补充孔子从学于老子:
宋不足征,求于柱下,得之老彭。问礼老聃,《春秋》之礼,皆殷礼也。《小戴》所录七十子之记,皆为殷礼,合乎《春秋》,盖问乎老聃而折其中,不徒《曾子问》所记也。故《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而得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之义,可谓远矣。又《论语》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亲炙之义且尊周史也。[7]115
此即为《述而》章之背景,在宋翔凤的曲折推论之下,孔子的“窃比之义”,也就是孔子问礼于彭祖、老子,并学黄帝的《归藏》之《易》学的证明。最终则还是为了说明,《春秋》之公羊学,与《归藏》与《易》学,以及《老子》都可以与《论语》相互发明。
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宋翔凤系统研究了《论语》全书,并认为各篇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将全书每两章合为一卷来作研讨,也是为了两章之间的联系。比如关于前四章,他说:
上三篇,既详大学、明堂、宗庙之法,此篇明治国,当察邻里风俗之厚薄。故仁、知、礼、义,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于性,而使自择之,则俗无不化,而人无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观于“里仁为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7]67
在宋翔凤看来,《学而》阐述的是大学之道,然后《为政》和《八佾》分别阐述明堂、宗庙之法,到第四篇《里仁》则为如何明察“邻里风俗之厚薄”,故此章所讲都是仁、知、礼、义等“仁性”的问题,说明如何落实化民成俗的道理,从而实现治国之太平。有意思的是,比如上文曾论及的《学而》篇“父在观其志”一节,到了《里仁》篇也有此节,邢昺的《论语注疏》认为有重出,然而宋翔凤也却认为这是有意如此安排,所谓“语虽若一,而义有两施”:
《学而》篇明大学之法,“父在观其志”一节,是言继体之君,以天子、诸侯皆视学,世子亦入学也。《里仁》篇明里邻风俗所系,至此类言孝事,以著为仁之本。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概言人子事亲能三年无改,则可要之没身矣。语虽若一,而义有两施,邢氏以为重出者,非也。[7]84
也就是说,《学而》中此节是从大学之道着眼,说明“继体之君”,即世子如何继承君父之志的问题;而《里仁》中此节,则是为了说明里邻风俗,孝是“为仁之本”,已经转而从培养仁孝治道着眼了。故在宋翔凤看来,《论语》一书为一套完整系统的士大夫之学,篇章次序都是谨严有序,都有其微言大义。
三 结 语
宋翔凤的《论语说义》,就其字词训诂而言,则有着传统汉学的考据工夫,然而他又喜好不失时机地揭示《论语》中孔子微言之所在,并强调其与《春秋》,特别是《公羊传》中的大义都是相通的。宋翔凤的《论语》学还有着清中叶以来群经互证的特点,主要则集中于《春秋》《周易》《老子》这三种经典,因为其中都有包含较多“性与天道”的微言大义。值得注意的是,如易学名家焦循,其《论语通释》与《孟子正义》之中亦有以《周易》互证的,只是以《老子》与《四书》类经典互证,则极为少见,作为今文经学家的宋翔凤,其思想比古文经学家或宋学家更为开放,方才较早和较多地以《老子》与《论语》互证。
关于宋翔凤经学的特色,有学者总结为公羊学的基本取向之外,还杂采古今与汉宋,又以孔老同源说而援道入儒,偶有杂引谶纬牵强附会[9]。其实章太炎早就指出:
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10]156
若就《论语说义》一书之整体而言,则诸如推论黄帝的《归藏》之《易》为孔、老之源等略显无稽,其他牵强附会之说还是不多的。此书能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又通过群经互证,从而将《论语》理解为一套系统的士大夫之学,即便偶有推论过度的尝试,整体而论则既是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又是《论语》学的一大贡献,亦是基于《论语》文本开放性而进行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