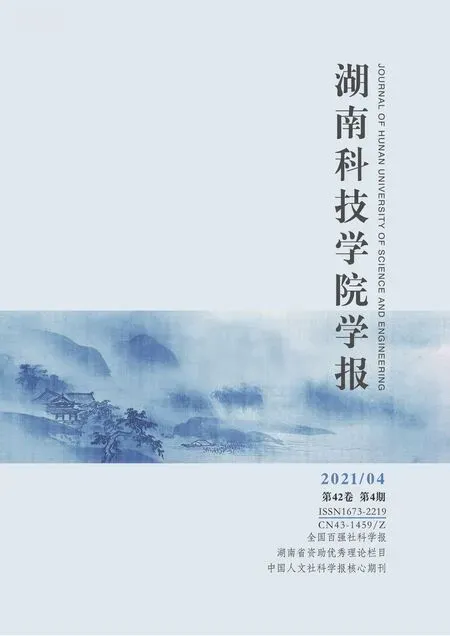论柳宗元天道观
郭新庆
论柳宗元天道观
郭新庆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湖南 永州 425199)
天道观是古人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知,而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借天命论把君权神化了。柳宗元是唐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在继承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天说论。柳宗元的《天说》奠定了他哲学思想的根基,其《非国语》《时令论》《蜡说》公开揭露和批判天命论和封建迷信。柳宗元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突显了历史上少有人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柳宗元;韩愈;《天说》;《非国语》;叛逆者
一 石破天惊话《天说》
《天说》是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的论战,写于永州贬居后期,这是柳宗元哲学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天说》奠定了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根基,其思想高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代。章士钊说∶“子厚《天说》,固近乎今之唯物家言,照耀千年,如日中天。”[1]394以此确立了柳宗元唐代最有影响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无论是儒释道,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忌惮不敢说天。柳宗元《断刑论》说∶“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2]58一针见血,捅破谜底。柳宗元如此直言说天,这在其之前是少有的。柳宗元长年遭贬谪,困居在荒蛮之地,这不但没令他屈服,反而磨砺出如此睿智的思想和胆识。《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那些说天的话,我们在他文集里找不到。吴文治据柳宗元《天说》“子诚有激而为是耶?”[2]386这句话,推测这是韩愈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照常理,韩愈多年后不可能没来由地重提这些不经意的话。刘禹锡《天论》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3]139这段文字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背后的真正起因。韩愈早年官场不顺,因得罪脏官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后因永贞革新时没得到起用,他怨恨柳宗元等人,为此写书信和作诗责斥柳宗元、刘禹锡,借以攻击永贞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诬蔑柳宗元等八司马是“侥倖而速进者”,还说柳宗元和刘禹锡遭贬是天之赏罚[4]332。故此引得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不快,特作《天说》和《天论》回击他。柳宗元《天说》和刘禹锡《天论》,是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的论战,这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韩愈其实是起了宦官和藩镇传声筒的作用。元和八年(813年)六月,韩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他给一个刘秀才写信,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5]202借此为自己曲笔就史,为自己迫于宦官淫威几度改写《永贞实录》辩解。刘禹锡连发《天论》三篇,其首篇愤愤地说:“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夫言天者,斯数穷矣。”[3]139-140刘禹锡说韩愈黑白颠倒,是非易位,赏在奸佞,罚在忠直,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还有何天理可言。韩愈认为天能“赏功而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因而“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论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果蓏、痈痔、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那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2]286。短短数语,字字如雷。震撼千载,照亮了未来路。
刘禹锡《天论》是柳宗元《天说》的解说篇,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人相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与人交相胜耳。”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3]139刘禹锡这一“法制”说得到柳宗元的认同。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2]503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
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亦。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3]143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至于“苒苒之光,浑浑之轮”(指时间),他说:“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謦欬,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邪?”[6]276这是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佛教是唐代社会的时尚,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没能摆脱这些时代的影子,他们都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在仕途失意,常居贬境的痛苦中,他们都向佛教去寻求慰藉。
二 能对《天问》的第一人
《天对》是柳宗元对屈原《天问》的解答。屈原的《天问》是一倒装句,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游国恩说:“《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摄于天象天道之中,所以名曰《天问》。”[7]404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发就能一挥而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它反映了战国时期人的思想认识。屈原与柳宗元一样,常年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屈原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屈原奔走呼号,他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的呼唤写出的《天问》,一直让后人追思和探寻着。《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一直以来,无人能够解答其中的奥秘。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之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天对》是“奇作”,体现了柳宗元的探精神,是柳宗元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作品。宋代黄伯思说:“《天问》之章,词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于千祀后,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弘杰异,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对别附于问,庶几览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为艰深也。”[8]67柳宗元是史上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也是“深得骚学”的第一人。
屈原《天问》涉及天文地理,人事历史。远至开天辟地,人类起始,近及自然山水,封建群争。奇思妙想,问难千古。柳宗元对答精到,辟古开今。我们仅就问答天地的几则来解析,其绝伦之势尽显。以下见《柳河东集》[2]227-240:
1.神话中说盘古氏开辟天地后才有世界,所以古人用开天辟地说宇宙的起源。
屈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柳宗元说,有关天地形成之前的虚妄说法,都是荒诞的人传述的。而巨神开天辟地的传说,混乱不清,没什么好说的。昼夜交替,往来运动变化,蒙昧中生出万物,这都是因为元气的存在,那里是谁创造的。
2.万物由何而生的问题。柳集《天对》篇有注说∶“《谷梁子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淮南子·天文篇》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里的阴、阳、和,是指阴、阳、天或阴、阳、天地(地是附属于天的)。这就是三合之说。柳注“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显然是否定有“人格神”的存在,这与柳宗元《天说》里主张的天人相分思想是一致的。
屈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柳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阴、阳、天参合在一起,由元气统控着。元气变化生出冷暖,而交替作用又促使万物变化。
3.古人有天方地圆之说,并认为天有九重。
屈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柳宗元说,天没人营造而成,阳气积聚形成九重天。天体浑沦,象车轮旋转,被加上“圜”的称号。阳气在高远幽深处凝聚自然形成天,这不是谁的功劳,也没谁创造。
4.天地运行的枢纽。闻一多说∶“古代关于天体的传说,多缘星象而生。”北斗七星,斡为七星之柄,而“制斗之转者为柄”。《汉书·天文志》说,北斗七星转,它后面的维星亦转,天随之。为此把“斡维”说成是运转的枢纽。
屈问∶斡维焉系?无极焉加?
柳对∶乌徯系维,乃麋身位!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柳宗元说,那里用拴绳子来固定天的位置!天无边无际,没有尽头,要能加放在什么上面,又怎会称其之大呢!
5.天地八柱的问题。《淮南子·地形篇》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柱。”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淮南子·天文篇》引《列子·汤问篇》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屈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柳对∶皇熙亹亹,胡栋胡宇!宏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柳宗元说,天广大无际,运动不息,那来的栋梁和房檐!宏大游离不相粘连的天空,要什么八柱来支撑!
6.传说黑水边有仙人,长寿不死。
屈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柳对∶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僭谓不死。
柳宗元说,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谁羡慕。人生命有长短,终都要死的。为何编造的没有边际,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更对迷信妄说不屑一顾。
7.《天问》辞尾屈原提出“天命反恻,何罚何佑?”之说。
柳对∶天邈以蒙,人幺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柳宗元说,天高远迷蒙,人渺小与天相离,为何要把两者扯合在一,责问天赏罚不公呢!
仅仅数段对答,已充分展示了柳宗元“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和反天命、反迷信的思想。《天问》和《天对》象一对姊妹篇,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宋代高似孙说:“柳宗元《天对》,精深环古,成一家之言,《离骚》而后,一人而已。”[8]137-138
三 把《国语》倒过来看
《国语》是儒家推崇的典籍,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文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敢于公开连篇累牍非《国语》的,历史上只有柳宗元。全书六十七篇短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三十篇,书前有一段小序;下卷三十七篇,篇尾附跋文一篇。《非国语》是读书观感式的写法,先引述需要“非”的词句段落,随后加以批驳。《非国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一小段一小段,一小篇一小篇,举凡政治、历史,思想、人伦,无不品之有味,入眼快人。柳宗元写《非国语》的原因,《非国语》序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眈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2]746《国语》披着儒家经典的外衣,内里藏着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它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柳宗元说这是用文采华美的外表罩着陷阱啊!如果不明确地揭示其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就会更多了,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为此柳宗元作《非国语》,在书里标记出《国语》的种种的诬妄之说,以告示天下的读书人。
《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我们翻检《非国语》,这一类篇章占了近一半。柳宗元通过对大量事例的批驳,详尽地阐发和诠释了自己的思想,语言之精彩,论说之透辟,说理之生动,这不仅反映了柳宗元思想和文学的功力,也可看出他写作时付出的艰辛。
1.斥“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幽王二年(前780),泾、渭、洛三条河流域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伯阳父用阴阳二气颠倒解释地震,这说明已具有初始的唯物观认识。可当时人又不可能逃出“天命”的束缚,伯阳父最终还是把地震原因归于人事,认为这是周要灭亡的征兆。他预言说:“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古时一纪为十年。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即位,公元前771年被西方的犬戎部族杀死,西周灭亡了,其间正好十年。左丘明以此宣扬命运天定。这些都是天人感应之说。柳宗元在《三川震》批驳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这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西周灭亡是人事所为,而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柳宗元说他不能赞成这些说法[2]748-749。灵王二十二年(前550)谷水、洛水泛滥,将淹王城,灵王不听儿子太子晋的谏说,堵水避灾。《国语》认为这是违背“天意”,因而导致王室衰亡。柳宗元《谷洛斗》说,“天将毁王宫”而不堵水,这是作王的大罪,不这样做怎么能守得住先王的国家呢?所以他认为“壅之诚是也。王室之乱且卑,在徳”,不能用谷、洛这件事征兆王室的衰败[2]755-7756。
《国语·晋语》记载,晋大夫赵宣子听说宋人杀死宋昭公后,要求出兵伐宋,认为这是反天地违背人伦的事,要受天的惩罚。晋为宋的盟主不去讨伐,也会遭祸的。《伐宋》批驳了这一说法,说天怎么会知道好恶惩罚呢?古时候杀君夺权远过于宋人的多了,照样长寿过着享乐的日子。这显然是直刺天能赏罚的谬说。可柳宗元在这里并不反对伐宋,认为盟主讨罚杀君的人是应该的[2]777。
《国语·周语》记载了宣王料民太原的事。宣王在幽王之前。料民,就是普查户口。大夫仲山父反对说:“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宣王不听,“卒料之”,结果到幽王时,西周灭亡了。前面说三川震,“源塞,国必亡”,这里又说宣王料民“妨于嗣”而致国亡。柳宗元在《料民》篇批驳了这一“天人感应”的说法,其文曰:“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柳宗元责斥这种“愚诬”之说,指出那不是“明其君”,而是“愚其君”。他认为西周的灭亡是幽王“悖乱”造成的,而不是“料民”遭天所恶而受到的惩罚[2]749-750。
2.批神怪迷信。《国语》里有许多谈神说鬼、荒诞迷信的的东西,“甚至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2]506。柳宗元从来不信这些,《非国语》逐个对它们进行了批驳。《神降于莘》揭露了“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谬说的虚弱本质,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鬼怪之说。仅仅几句话,其荒诞不经就被批的彰显无遗了[2]750-751。《曹刿论战》记载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柳宗元《问战》篇首先肯定了曹刿“言狱”取信于民是“知战之本”,但对《国语》祭祀不丰足神灵不会降福的说法,也予以批驳。说对国家存亡和有关百姓命运的事,不求实际而求神道,是很危险的。柳宗元认为,战争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如果但凭曹刿的几句问话去打仗,那是会误国害社稷的[2]759-760。《卜》论辩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的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骗民之术[2]764。《董因》批驳星象预测的迷信。《叔鱼生》批驳据婴儿像貌和哭声断定吉凶祸福。《黄熊》是驳梦卜的。柳宗元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2]782?
3.驳乱政害民。《非国语》还有力的批判了统治者乱政害民。《命官》反对“任人唯亲”的作法,主张任用官吏要按照人的才能,而不应依据姓氏门第。《戮仆》批评公子扬干犯罪却斩杀他无罪的仆人顶替,柳宗元认为这无法严明刑法,还会遗害后人。《大钱》谈论钱币轻重的利害,柳宗元以利民为判断标准,体现以民为本的理政思想。《不藉》批评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柳宗元认为,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求福,“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2]747-748。这简直是对封建礼教扇耳光,是对虚假政治的鞭挞。苏东坡在《答江季恭》里说:“子厚为学,大抵以礼乐为虚器。”[8]43这算是说到点上了。
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2]508-509。柳宗元的为人之道是唐代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长期遭贬,不但位卑职轻,又居于偏远的荒蛮之地,可他的为人品格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思想和文学又像璀璨的启明星一样,照亮了唐代社会,至今还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华。宋、元时,有人作《非非国语》,“泛泛如浮云掠空而过”,今已不得见,可柳宗元的《非国语》岿然不动,还在受到人们的喜爱,仍然在传诵着。
四 批《月令》和蜡祭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写作年代不详。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并批注说:“二论谓天道与人事无关,驳斥汉儒‘五行政治’之谬说。”[9]78《断刑论》与《时令论》是相辅而行之作,名则论断刑,实则是对《时令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章士钊评《断刑论》说:“本文旨言断刑,而不啻为《天说》之铁板注脚,谋之人心以熟吾道一语,是子厚一生经纶最得力处。”[1]110“谋之人心以熟吾道”[2]57,这是柳宗元《断刑论》里说的话,所谓“谋之人心”是说研究谋划人的心理和想法;“以熟吾道”是要引导人了解和遵奉他所主张的思想和道义。柳宗元这里说的“道”是他一生遵守并反复论说的“大中之道”。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儒道不一样,柳宗元处处非议他们,他用自己的“大中之道”溯本清源。从某种意义讲,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礼法”制度的叛逆者。柳宗元为守护自己的“大中之道”,一生孤独痛苦着。
《时令论》是批驳《月令》的,有上下两篇。《月令》篇出自《礼记》和《吕氏春秋》。《礼记》里的《月令》篇是有人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合”编就的,后来被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开元中,大臣张悦以高宗显庆年的《礼记》注解前后不一样,要求重新刊定作为唐礼,这就有了《开元礼》,也称《大唐开元礼》。到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简直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祀事”,行《开元礼》的情形。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他认为其礼其乐,“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教有余也”。他说:“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2]432柳宗元反对鬼神迷信,他主张用祭祀来佐教化,事天地教敬,事宗庙教爱,事有功烈劝善。《时令论》批驳《月令》,反对假借时令行神道这一思想。
《时令论》开篇指出,以《月令》“为大法”不是圣人所为。圣人所做的是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类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的准备。圣人这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柳宗元的结论是:“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柳宗元说:“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2]53《尚书·洪范》里有“敬用五事”之说。所谓五事,指貌、言、视、听、思,这应包括人的所有行为。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古人用这五种物质来解说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物质的多样性。五行说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和《尚书·洪范》。五行说后来被人神秘化了,尤其其是汉代,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柳宗元认为,把节气时令和五事、五行混在一起用来推行政令,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
柳宗元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柳宗元说:“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春季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2]53-55
《时令论》下篇批驳“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月令》”,妄言《月令》为“防昏乱之术”。柳宗元说:“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说,做善事还要规定时间,还得用“五行”等迷信祷告以及怪异的话和事来胁迫人,这是“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又说:“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不除去《月令》这样的“大惑”,不树立“大中”之道,而去讲圣人之道,柳宗元说他是不会相信的。柳宗元最后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2]55-56柳宗元反对《月令》这一类“淫巫瞽史”,所面临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而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刺透纸背,让人每读至此顿生敬意。
《断刑论》仅存下篇,是答辩之文。从内容上看,《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会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柳宗元认为,讲天命而不讲人事,这是糊涂不知事理。“苍苍者”上天怎么会知道和干预人事,又为什么要勉强迁就时令去谄媚它。自然界的雷霆和雪霜,不过是一种物质性的气罢了。春夏雷霆,“破巨石,裂大木”,是木石犯大罪了吗?秋冬雪霜,摧残草木,是草木有大罪吗?难道是雷霆和雪霜惩罚万物吗?柳宗元说,雷霆和雪霜那会什么惩罚,这是效法“天命”人的糊涂之说。柳宗元主张说:“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2]56-58。这种非天,讲人事,重人道的思想太难能可贵了。它如同昏暗的夜空里一束闪电,划过了历史的长河。柳宗元期盼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也即是天时得以顺应,大和能够到来,他追求的“大中之道”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大和,也称太和,指阴阳之气调和,自然界没有灾害,社会没有战乱的升平景象。
古时的神农氏是传说教百姓种五谷的神,他在农历腊月作蜡祭,用染成红色的鞭子鞭打草木,以劝农事。后来蜡祭成了一种愚民的手段,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唐代设一百八十七方神,年末依据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的情况,取消有灾一方神灵的供品,不祭祀它们。柳宗元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任监察御史里行,按唐代礼制监察御史监祭祀。年终蜡祭时,柳宗元“主祀事”,可他却背行自己的身份写《蜡说》,直接批驳蜡祭的虚伪。柳宗元说:“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柳宗元说,神什么样,谁能看到?祭祀的东西神吃没吃,谁又知道?柳宗元认为,古代圣人设蜡的用意,必定有其道理。这就是“非于神也,盖于人也”[2]296。一言蔽之,圣人只为民而不为神。而设蜡祭神是为了警戒人事。柳宗元进而结合社会实际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要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这应该惩罚人。现在古圣人之道不显了,蜡祭只有表面形式流传下来,徒有虚名,原先设教的本意也被隐没了。柳宗元以蜡祭之事分割幽明,是要申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趋重人治。柳宗元反对拿传说牵强附会。他说“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等传说,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这样解答,虽不尽有力,但还是很巧妙,很有说服力的。柳宗元在《蜡说》篇末慨叹道∶“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2]297在唐代迷信猖行的社会,敢说出知道圣人蜡祭的道理,就可以去掉祭祀形式这样的话,这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是历史传统的反叛者。他的所谓“愚痴”和“不识时务”,让他经历了一生的磨难和痛苦,而正是这一经历,磨砺和撞击出如眼的思想火花,照亮了那个时代和后来的社会。
[1]章士钊.柳文指要(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钱仲联,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M].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6]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谭介甫.屈原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404.
[8]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施子愉.柳宗元年谱[M].武汉:武汉大学,1957.
2021-04-12
郭新庆(1949-),男,辽宁大连人,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柳宗元文学。
B241
A
1673-2219(2021)04-0014-06
(责任编校:潘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