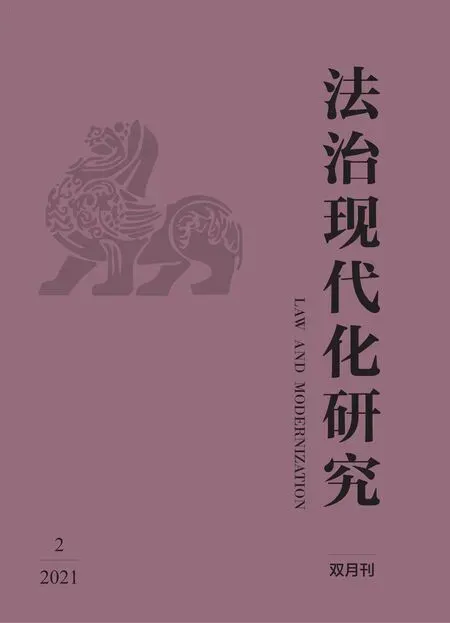解释保险的四种学说(下)
[美]肯尼斯·S.亚伯拉罕 著 严 立 译
四、 产品说
正如合同说那一章所述,合同法上早就有了关于格式合同典型特征的知识积累。(1)凯斯勒讨论过格式合同的萌芽,参见Friedrich Kessler. Contracts of Adhesion: 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 43 Colum. L. Rev. 631-632(1943).拉考夫则描述了格式合同的七种典型特征,参见Todd D. Rakoff. Contracts of Adhesion: An Essay in Reconstruction, 96 Harv. L. Rev. 1177(1983).格式合同令人困扰的是,当事人并未就合同条款进行磋商,而且受约人(即投保人)不清楚,更遑论理解这些条款,所以格式合同条款并不必然具有拘束力。这样总结既有的知识成果,并不算过度精简。(2)“格式合同原则上应推定为有效,一旦把这个规则放到适当的语境中,发现它主要关涉社会权力、自由之序列,这项一般规则便很难维系了。”参见前引①,Rakoff文。由此带来一个困局,如何确定哪些条款有拘束力,哪些没有呢?
依合同说,保险合同条款被推定为有效。欲宣告某一条款无效,或者退一步,对之作出背离文义的创造性解释,被保险人必须证明其有违合同自由,比如该条款模糊不清、显失公平,与被保险人客观上合理的期待龃龉,或者在某个方面违背公共政策。(3)违背惩罚性赔偿的保险即属违背公共政策,参见Hartford Cas. Ins. Co. v. Powell, 19 F. Supp. 2d 678, 693-694 (N.D. Tex. 1998); 保险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其条款是否符合私法立法,比如合同法,应满足的标准。参见W. David Slawson,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d Democratic Control of Lawmaking Power, 84 Harv. L. Rev. 529, 540-544 (1971).唯其如此,被保险人方得主张不应严格依文义适用保险合同,但这种例外并不常见。倘不存在任何一种例外情形,便推定合同条款是当事人逐一同意过的。合同条款的语句是看得见的“面子”,其他决定合同效力的因素则是隐而不彰的“里子”。但正如上文指出的,投保人一般不会阅读保单,也不会对保险的理赔范围条款作出有意识的选择。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投保人并没有同意一系列合同条款;相反,他们是在购买商品——保险——并希望从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许多学者注意到合同说中的紧张关系,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不必然具有拘束力,所以将保险视为合同并不准确。相反,保险更像是一种商品——产品或者物件。(4)保险人向消费者提供“五花八门的基本保险与附加险”,这像极了“琳琅满目的产品”,参见Daniel Schwarcz. A Products Liability Theory for the Judicial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Policies, 48 Wm. & Mary L. Rev. 1389, 1405-1406 (2007);“与其说保险是合同,毋宁说它是某种产品或者商品”,参见Jeffrey W.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44 Tort Trial & Ins. Prac. L.J. 813, 818 (2009) [hereinafter,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若保险人广告宣称的理赔范围与实际情况有差,那么保险就属于缺陷产品,参见Eugene R. Anderson & James J. Fournier. Why Courts Enforce Insurance Policyholders’ Objectively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Insurance Coverage, 5 Conn. Ins. L.J. 335, 419-423 (1998); 订立格式合同的过程就仿佛是一个购买“允诺”的过程,See note ③, Slawson文。另一篇Jeffrey W. Stempel的文章或许也可以归入产品说的范畴,尽管我认为它更像是治理说的主张,参见Jeffrey W.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Social Instrument and Social Institution, 51 Wm. & Mary L. Rev. 1489, 1495 (2010) [hereinafter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Social Instrument].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有一系列强行法规范出卖人的义务。例如,出售一辆汽车,尽管交易是通过买卖合同实现的,出卖人仍然负有侵权法上的义务。因此,持此说者主张正如商品出卖人通常默示担保该商品适合销售,生产者在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时应承担侵权责任,若保险产品有缺陷,保险人就应当承担责任。
产品说不仅试图描述保险的实际特征,还试图阐明保险法的规范含义。在这种理念架构中,事实上决定保险条款法律效力的因素,终于从“里子”变成了“面子”。在支持者眼里,除非保单条款符合一定标准——判断条款是否合理之标准——否则无效。(5)如下文引注⑨,讨论了施瓦茨教授所倡判断保险条款是否有效的标准。保险理赔纠纷的争议焦点因此发生变化。在合同说之下,争议焦点是所适用条款的含义;(6)参见本文上篇“概念核心中的紧张关系”部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但在产品说之下,焦点却变成了这些条款是否有效。
合同说在处理格式合同的问题时遭遇了一些两难困境,产品说则可以有效回避之。正如前述,关于保险的各种学说都必然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产品说则重点关注其中之一:保险人用消极条款限制甚至排除某些赔偿范围,如何确定此类条款哪些可执行,哪些不可以?依余所信,较之合同说,产品说更胜一筹,因其能够更精确地描述保险的本质与功能,尤其是面向广大消费者的个人保险。
但在实践中判断保险条款有效与否时,却发现产品理论存在瑕疵。当然,设计一种产品,要求它绝对安全,还实用又廉价,这无疑是强人所难。因此,即使某些产品设计并非绝顶安全,有时还造成损害,法院也并不课以责任。但倘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并因此造成损害,依侵权法,出卖人即应承担责任。(7)参见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Prods. Liab. § 2(b) (1998).问题在于,不管对于实体的产品还是保险条款,“缺陷”都殊难定义,更不用说实际适用。这一概念很难适应审判实践,原因则不一而足。
(一) 成本— 收益分析法的不足
检验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的主要标准是产品设计产生的风险是否超过其效用。(8)参见Id. § 2, cmt. d.但是评价产品设计的效用却是一个难解的、开放性的问题。产品设计不仅包含安全的要素,尚需考虑造价、外观与功能。而我们并不清楚如何比较产品设计的安全风险与决定其效用的造价、外观与功能。
用“风险—效用”方法——或者“成本—收益”方法,这两种说法别无二致——来评价实体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会有许多困难;而用这种方法判断保险条款有效与否,困难恐怕只多不少。要判定保险条款肇致之风险与其效用孰轻孰重,产品说就必须借助保险条款的“目的”这个分析工具。(9)关于重置成本条款之目的,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入室行窃险与污染致害免责条款之目的,参见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前引④,Schwarcz文。施瓦茨教授或许赞成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是判断某一保险条款是否服务于合法的承保目的;若否,则进入第二步,检验该条款是否符合“成本—收益以及合理替代方案之标准”,若答案仍为否定,则该条款有缺陷。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因为评价保险条款之效用,只能根据该条款是否有效实现了自身目的,此外别无他途。但条款的目的又非不言自明。故必须借由司法推理、事实证据或者此二者的结合,人为地构建一个目的。这种人为构建目的的司法活动并无标准答案,与评价产品设计的效用相比,其开放性不遑多让。
以标准的业主保险(homeowner policy)为例,被保险人必须先行修缮或者重建损毁的财产,完工之后始得要求全额赔偿修缮或者重建费用,即赔付所谓的“置换成本”(replacement cost,指某项财产毁损之后,重新置办一项新的财产所需之费用。比如房子里的电视灭失,则其置换成本就是现在再买一个相似的电视机的价格,无须考虑原有电视的折旧率——译注)。倘若房主未重建,则保险人仅赔付受损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这个数额一般比较低。丹尼尔·施瓦茨教授是产品说的两位主要支持者之一,他把这个条款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认为它未能很好地服务于“承保目的”。(10)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施瓦茨教授论证道,此种理赔限制条款的保险目的是防范道德风险,遏制保险欺诈,因为……被保险人如果想迁居,就可以彻底摧毁房屋,获得保险金,而不是把房子卖掉。显然出卖旧房子所得价款比赔偿的重置成本少,保险人可借此牟利。(11)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
我并不怀疑此类条款的目的之一是防范道德风险,(12)参见Kenneth S. Abraham.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271(5th ed. 2010).也不怀疑保险人可以改写条款以期两全:既能防止被保险人渔利的风险,又能保障那些善意的被保险人。于后者而言,即使保险人先行全额支付置换成本,他们也能够并且愿意重建家园。(13)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但本条款仍可能有另外的目的:阻止损毁财产的无效率重建,从而使保险费保持在一个最优水平。其逻辑在于,如果重建后财产的市场价值与重建成本持平或者更高,一个正常信用市场中的被保险人理应能够获得建设贷款,所以即使被保险人在竣工以前不支付保险金,也无关紧要。相反,倘若重建后的财产价值还不如重置或者再建成本,就很难申请重置的建设贷款。因为此时用作抵押的建筑物价值低于贷款额度。准此而言,规定非经重建不得请求赔偿重置成本,这一要求就既可以将有效率的重建与无效率的重建区别开,又可以使所有其他保险人免于补贴无效率的重建者。
总而言之,要求重建不仅仅能够防范事前的道德风险,还能够阻止无效率的重建(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的道德风险)。因为如果重建是无效率的,被保险人就无法申请到建设贷款,申请不到建设贷款完成重建,保险人就不会支付全额的重置成本。由是观之,这里讨论的理赔限制其实服务于两个保险目的,并非只有一个。所以,它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方法的检验,因而不存在缺陷。
然而法院应该怎样把这种“缺陷检验”应用到重建条款上呢?它到底像我假设的有两个目的,还是如施瓦茨教授所见仅有一个目的?他分析这个问题的口吻就好像这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与合同解释相仿。(14)施瓦茨教授主张法院应追问“保险人不赔偿某种降临到被保险人头上的损失,是否有任何合法的保险目的”。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依施瓦茨教授所信,显然只有保险人的目的是有价值的。而产品说的另一位倡导者杰弗里·斯特姆佩尔(Jeffery Stempel)教授却似乎主张,就保险条款的目的而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的意志均有其价值。(15)参见前引④,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at 847-848.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试图确定条款目的都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比如,将确定目的作为法律问题来处理,将涉及哪些因素就不甚清晰。起草保险单的过程或许可以反映承保的意图。但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全行业共同起草的、格式化的财产保险,所以起草者的意图与特定保险人可能未尽一致,而后者才是出售保险之人。此外,保险人可能要在使用保险条款一段时间以后才意识到,或者开始思考它重要的、额外的功能。如果这些功能确实是保险“目的”的组成部分,法院就必须采取某些方法来发现它们。而一旦更加深入地探究行业共同起草的历史和保险人各自的意图,原本单纯、直接的合同解释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16)施瓦茨也承认上述以及其他潜在的困难,因此并不建议径行采纳产品缺陷的分析方法。他主张产品责任模式“应当是更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而不是一种新保险理论的终点”。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
确定被保险人的意图可能更加困难,这种考验来自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大部分被保险人对承保范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顶多有一个大概的目的——为特定的风险寻求一种保障,比如房子着火、汽车“出事”。这样的意图远远不够具体,无助于解决特定条款的赔偿范围及有关该条款适用的纠纷,毕竟案件事实总是各有不同。
无论如何,风险—效用或者成本—收益方法是不济事的,因此要确定保险的赔偿范围,我们可能需要其他可行的检验标准。施瓦茨也承认,若为规避“裁判”风险排除某些情形下的赔偿请求权,则即使保险条款不满足成本—收益标准,亦非属有缺陷。(17)旨在最小化司法风险的条款“不应被认为是一种保险缺陷,因为它服务于合法且重要的保险功能,往往能够提升保险安排的整体效率”。裁判风险“包含保险人处理理赔申请的交易成本,比如勘定事实的费用、法律服务费等”。前引④,Schwarcz文。举例言之,排除赔偿责任的条款愈依赖于案件事实,其裁判成本就愈高;相反,越独立于事实,排除范围越清晰,成本就越低。(18)保险条款多以“明线规则”(bright-line rules)写就,这种客观而明确的明线规则无法完美地实现保险目的……因为一旦被保险人引发损失,规则就几乎没有疑问地应予适用。参前引④,Schwarcz文。
考虑裁判风险无疑是明智的。但为了降低裁判成本,可能将本来符合保险目的的事项也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这就产生了风险;而承认裁判成本的相关性系属一事,比较所节省的裁判成本与为降低裁判成本带来的风险则属另一事也。(19)显然,对施瓦茨而言,要么判断保险条款是否适用的成本,与特定措辞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成本相关;要么,因为适用免赔范围较小的条款将产生司法成本,故需要其他非特定的标准来检验某个缺陷条款应否保留。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传统上,这种比较属于监管性的判断。但施瓦茨教授坚持法院应采此方法,却不念及法官既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又欠缺“立法资料”,这些资料正是监管者做决定的凭据;法院的这种局限性几乎无可避免。就实际效果而言,施瓦茨希望法院通过仔细审查,重新设计保险条款,以判断该条款是否合理,就好像成本—收益方法要求陪审团通过重新设计产品,确定该产品设计是否存在缺陷。(20)法院依据边际成本收益分析法判断保险条款是否有缺陷,成本收益分析法则建立在“合理替代设计”的基础上。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
(二) Atwater奶油公司与偏好多样性
限制承保范围的权威案例之一是“Atwater奶油公司诉西部国家互助保险公司”一案,(21)参见366 N.W.2d 271 (Minn. 1985)(全席审判)。案涉保险对理赔作了广泛限制,因而有理由认为该条款存在“缺陷”。案涉盗窃险规定,如房屋外部门窗上没有可见的强行进入的痕迹,即不予赔偿。(22)参见366 N.W.2d, at 274.法院认定,以上限制的目的之一在于确保只赔偿真正的第三人入室行窃,而不赔偿所谓的“监守自盗”。(23)参见366 N.W.2d, at 276.施瓦茨显然同意本条款并无缺陷。(24)“本条款服务于合法的保险目的”,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依其所信,这个条款的效用是降低诉讼中的裁判风险,以免需要逐一确认每个保险事故到底是不是监守自盗。诚然它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因为如果确系入室行窃,又未留下可见的闯入痕迹,就会被不恰当地排除在外。(25)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但是此条款效用超过了风险,故无缺陷。斯特姆佩尔却认为前揭条款无法通过缺陷测试。(26)参见前引④,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at 848-849.他承认倘若Atwater一案中,不以可见痕迹为必要条件,固然会造成裁判成本负担,但同时坚持“这样的额外成本其实是微不足道的”。(27)参见前引④, 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Thing, at 848.
由是观之,两位主要的支持者虽然一致认为,这个重要案例可以用产品说妥善处理,但在结果上却背道而驰。从二位的分歧中,足见评价条款之效用是何等难以预期且复杂多变,因为保险条款往往十分宽泛。
1. “合理替代方案”检验?
即使证据表明存在合理的替代方案,在本文情形下,就是更合理的保险条款,也无法规避上述难题:依据特定条款之目的评价其效用。产品责任中,存在合理的替代方案只是风险—效用标准以外的一个附加要求,而不是替代风险—效用方法的标准。(28)“若采纳更合理的替代设计,得降低甚至避免某产品造成损害的预期风险,则该产品为有缺陷……由于舍弃此替代设计,产品并非合理安全。”参见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Prods. Liab. § 2(b) (1998).
将合理替代方案与风险—效用方法当成两项独立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倘使法院仅凭存在合理的替代方案就认定产品有缺陷——即使该产品设计能够通过成本—效用的检验——则意味着只要产品设计还有改进空间,就是缺陷产品。换言之,只要没有采用最好的设计,就会承担责任。依循此逻辑,只要存在“更合理”的替代方案,保险条款就有缺陷。因此纵然某类保险条款令人满意,但保险人并未提供最好的方案,也需要承担责任。产品说的倡导者中,似乎没有谁认为,至少没有明确公开表示,保险条款应当满足合理替代方案的要求。如果判断是否存在缺陷,端视有无合理替代方案而定,就无异于要求保险条款臻于完美,不存在任何更合理的替代方案。
退一步讲,即使以是否存在合理替代方案为准,来判断保险条款是否有缺陷,也还是会产生评价效用时遭遇的困难。因为如果直接分析某个条款的风险与效用,无法避免评价上的困难;而用来替代该条款的方案合理与否,又部分取决于如何评价其效用——这就同样会有“难以预期且复杂多变”的问题。(29)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主张,保险人所同意之合同条款的含义有更清晰的表述,往往可证明此系模糊条款。参见Kenneth S. Abraham. A Theory of Insurance Policy Interpretation, 95 Mich. L. Rev. 531, 540-544 (1996).但此处之同意系一语言的清晰度问题,与评价其效用无涉。
2. 偏好多样性问题
成本—收益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缺陷,即很难适应产品购买者多样的偏好,比如不同的品味或者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即使某种风险—效用的权重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满意的,少数人却可能想要另外一种配置。在复杂的产品中,这一顾虑更显其意义,因为个人购买者绝难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与风险有关的信息——来决定最有利的风险—效用配置。正因为安全市场(market for safety)不完美,法律就必须采纳某种标准,确定大多数人可能的偏好或者预期的最大利益。(30)参见下文“作为组织的保险:多数被保险人与少数被保险人之关系”部分。又因为提供不同品级的替代产品不具可行性,法院就只好采取一种“均码”的法律标准。毫无疑问,此标准试图雨露均沾,却显然无法顾及一部分人的偏好或利益。一旦这么做,消费者想要购买安全性没那么高、价格也没那么贵的产品,也求购无门了。
若用产品说来评价保险条款,情况也没什么两样。成本—收益方法假设所有投保人均有相同的偏好,这往往是不正确的。为解决这个问题,施瓦茨主张保险条款极可能是市场失灵的产物(31)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这就意味着,倘若有且仅有一种保险条款可行,它就不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施瓦茨判断市场是否失灵的方法却是看是否存在不确定性,(32)施瓦茨使用的术语不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是模糊性(ambiguity)。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在此语境下,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不幸的,因为所使用的术语与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密切相关。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列举了法院考虑理赔范围之模糊性的情形)。此时,问题关键就是某一条款是否服务于保险目的,条款模糊与否在所不问。亦即依特定免赔条款之承保目的,系争事项应予赔偿,还是应排除在外并不确定。(33)参见前引④,Schwarcz文。
但是保险市场失灵,并不仅仅在保险人处于“准垄断者”地位时发生;若交易成本过高,保险人无法提供广泛选择以满足投保人的不同偏好,同样属于市场失灵。举例而言,Atwater案中那种盗窃险的承保范围完全可以更宽或者更窄,可以要求可见的入室痕迹,也可以不要求。有些投保人愿意支付更高保费,获得更广的保险范围,有一些却只愿支付较低保费,保险范围小一点也无妨。但如果交易成本过高,提供多种选择不划算,保险人势必只提供一个备选项。那么视保险人提供的选项而定,某些投保人刚好可以获得中意的保险范围,其他人就只能妥协,所得到的要么比自己原本想要的更多,要么更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追问“可见入室痕迹”条款的承保目的何在,意义便十分有限。(34)参见前引-,以及相关阅读材料。因为条款的目的就是提供大多数潜在投保人偏好的保险范围。当然,也有可能——正如在Atwater案一样——大多数被保险人根本不清楚所谓的可见痕迹条款。保险人提供更宽或者更窄的理赔选择不合算,可能正是被保险人的这种不知情所致——因为提供更多选择,增加的保费收入微不足道,所需要的说明成本却大幅提升。
果如此,则产品缺陷标准所能解决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即大多数保险人对保险的承保范围是否满意。即便如此,法院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确知,广大投保人满不满意某种保险的承保范围。只有当大多数被保险人明显要求更大的承保范围,并且愿意为之买单时——这属于法律问题——法院才有底气得出结论,但此类案件并不常见。在其他案件中,多数投保人可能也想要更宽的承保范围并乐于为之付费,但如何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却欠缺可靠的方法。因为多数人之偏好,不仅仅取决于承保范围与价格,还受到潜在投保人对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简单地依靠保险诉讼中的法庭事实调查,是很难查明的。纵如保险监管者,回答与投保人偏好相关的细节问题也诚非易事。
简言之,在传统产品责任领域中,是否存在设计缺陷殊难认定,这个问题在保险的产品说中同样如影随形。理想的情况是,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产品的安全性、成本及其他性能各有不同,从而满足产品购买者不同的偏好。但现实情况却是购买者并不总是充分了解产品的安全风险——也无法以一种经济的方式去了解——既然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产品的风险几何,市场力量又焉能针对其偏好为他提供最优选择呢?
保险产品亦复如是。在实践中,投保人通常不够了解保险条款,市场也不够灵活,因此无法为不同偏好的被保险人提供最优的保险种类与范围。法院或者陪审团也并不能胜任这种“产品最优化”或者“保险最优化”的设计工作。即便他们足堪此任,充其量也只能满足多数产品购买者或者多数投保人的偏好,只得置少数人的偏好于不顾。
举凡安全类监管,皆免不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即使重新设置判断保险条款之效力的标准,亦于事无补。更何况,重新设置标准,只改变了何时监管、如何监管以及由谁来监管的内容,并不能改变监管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监管者得依自己的结论改变市场现状?以及若只能满足某一种偏好,应置少数人的偏好于何地?
五、 治理说
前三种学说均视保险为一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双边交易:传统意义上的合同(只是程度容有差别,合同说),(35)参见本文上篇第二部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需要监管的重要商品买卖(公用事业说),(36)参见本文上篇第三部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以及产品的买卖,故有控制产品质量的责任规则之适用(产品说)。(37)参见本文上篇第四部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另一种不同的视角是将保险理解为一种保险人“治理”被保险人的关系。(38)此学说的代表作当首推Richard V. Ericson et al. Insurance as Governance(2003),作者认为保险在以下九种意义上有治理功能:使风险客观化,成为“概率与损害的程度”;使风险转化为成本与可能性;把人们集中在一起,大家都从损失最小化中获益;通过保险人提供补偿的方式,防范资本流失;“以监控和稽查的方式”管理风险;使风险“受合同与裁判之约束”;为某些观念制造一种文化氛围,比如责任感;提供“一种实现正义的社会机制”;以及“将公共福祉与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然而支持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采取了选择性的态度,即片面地援引与此说契合的保险实践,并且只是部分阐述了其可能的保险法含义。
举例言之,治理说的描述性表达或者解释性表达,揭示了政府与保险人行使的方式,他们的权力颇相类似。(39)例如保险业的监管手段与政府同出一辙,参见Richard V. Ericson et al. Insurance as Governance, at 52-58.其论据是在某些情况下,保险的功能是引导被保险人之行为,并在厄运降临时保护他们,这与政府的职能相近。此观点将保险人视作“替代政府”。问题仅在于将此种相似性贯彻到何种程度而已。
与此不同,这个学说的规范性表达则重点关注被保险人的团结与共同体之建立,保险对此有所助益,这也与政府相似。(40)就促进“个人团结”而言,保险是主要的非政府手段之一,参见François Ewald. The Return of Descartes’s Malicious Demon: An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Precaution(Stephen Utz trans.), in Embracing Risk: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Insurance and Responsibility 273, 277 (Tom Baker & Jonathan Simon eds. 2002) [hereinafter Embracing Risk]; 保险是一种为他人遭受的损害承担“集体责任”的设计,参见Deborah Stone. Beyond Moral Hazard: Insurance as Moral Opportunity, in Embracing Risk, supra, at 52, 54. 许多政界人士也赞同此说,“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坚信,我们应当分担风险,共担责任”,参见155 Cong. Rec. S7941 (daily ed. July 22, 2009) (statement of Sen. Christopher Dodd). 杰弗里·斯特姆佩尔的一篇文章似乎也与治理说相合,“根据我所论述的观点,保险完全可以被视为社会工具,……公共政策工具,甚或是政治工具”。这意味着每个被保险人均有一种持续的责任与权利,且应当反映在保险人的义务之中。此观点蕴含一种组织性的治理理念。然而,被保险人不一定具有同质性,故其利益容有差别——正如一个政府治下的公民,各自利益也不总是一致。就保险而言,多数与少数被保险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仅仅指出这里涉及一个治理的问题,既无法调和彼此冲突的利益,也不意味着选择一种利益而舍弃另外一种。治理却必须完成这项任务。于是,不管是把保险看作替代政府,还是团结不同利益之被保险人的组织,治理说都存在需要攻克的难题。这一观念的某些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 作为替代政府的保险
有学者将保险视为政府,其主要观点之一是,在现代国家保险人常常可以起到控制行为的作用,这是一种准政府职能。(41)无论是强制购买还是自愿购买,保险都是一种管制手段,参见Tom Baker, Jonathan Simon. Embracing Risk, in Embracing Risk, at 1, 13; 对保险的需求把控着人们各种行为的渠道,比如买房、租车等等,参见Carol A. Heimer, Insuring More, Ensuring Les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e Regulation Through Insurance, in Embracing Risk, at 116, 125-128; 人们经商或者从事其他日常活动,往往要求五花八门的保险,参见前引④,Stempel. The Insurance Policy as Social Instrument, at 1498-1501.举例言之,办理机动车登记之前须购买责任保险,所以机动车保险人就有助于管理合法的驾驶人,并决定驾驶机动车需要什么东西。(42)人们买房、驾车,保险都是必要条件,因此它是“管制私人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参见前引, Baker, Simon文。与此相类,医生及其他医务工作者只有在取得医疗事故责任险之后才有资格在医院供职,医疗责任保险人因此可以决定哪些医生能获得任职资格。(43)在医院从事助产工作或者其他医疗专科工作,均须投保职业责任险,参见前引,Heimer文。其实际效果就是,保险人有权决定哪些人能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从事医疗工作,这些医院提供了大多数的医疗服务。相似的情况还有,为防范道德风险,财产保险人和责任保险人往往根据以往的出险情况收取保险费。此种计费方式会影响被保险人之行为,因为它能敦促被保险人一改旧习,更加审慎地行为。(44)关于此种计费方式对投保人行为的影响,参见Kenneth S. Abraham. Distributing Risk: Insurance, Legal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72-74 (1986).
保险还在另一个重要层面上发挥了替代政府的功能,论者有时却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提供某些通常仅能向政府主张的“正当权利”。(46)事实上,倡治理说者强调与过去相比,政府与保险提供的风险保护减少,如何“消化”风险则增加了。因为保险是保护公民免于风险的工具,而提供风险保护正是现代国家的典型特征之一。人寿险、医疗险、残疾险、财产险,无一例外皆有此功用。故自效果言之,保险保障了被保险人的社会福利;有时候他们自愿购买保险,但有时候也别无选择地被强制投保。(47)“保险市场的某些方面依个人选择而定,其他方面则受到监管”,参见前引,Abraham文。
治理说的可能含义之一是保险人应当承担某些政府职责,因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恰恰介于“政府—公民”之公共关系与合同当事人之私人关系之间。政府对公民个人(有时甚至对非本国公民)负有某些义务,但合同当事人对彼此却并无此等义务。与此相对应,公民个人对政府享有一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权利,却不得向其他私主体主张。保险能够控制行为、防护风险,这正是“治理”的题中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希望保险法像对待政府一样对待保险人,而不是把它作为普通的私主体。不管怎样,我们还需要考虑把保险人与政府等而视之,应贯彻到何种程度为宜。两种可能的方案是,保险法要求保险人像政府那样提供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
1. 保险“正当程序”
普通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性地放弃合同权利,不管这么做是否显得任性或者不正规。如果我与你订立合同把汽车卖给你,旋即反悔,那么我需要赔偿你汽车价值的损失。不管我是出于善意违约,比如我想自己留着这辆车,还是出于恶意违约,比如我发现我讨厌你老婆,这个结论都成立。类似地,汽车经销商可以免费送给某个车主一个零部件,尽管他的汽车保修期上个礼拜就已经满了,而他一直是个不错的老主顾;经销商也完全可以因为有顾客以前从别的店买过车,就拒绝给他们这样的优惠。(48)企业可以使用豁免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同时选择性地放弃此种责任豁免,从而“为自己博一个善待消费者的好名声,因为企业在某些案件中放弃责任限制条款,消费者即可行使退货、重作或者变更之权利”。参见前引①,Rakoff文。如此一来,“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了行使或者放弃权利的裁量权。结果在出现纠纷时,如果严格依合同办事,相对人就必须恳求企业给予宽免,问题在于这种优惠本来就是企业免费赠送的”。参见前引①,Rakoff文。确实,根据早期的合同法著作,格式合同有效率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创造了杰森·约翰斯顿(Jason Johnston)教授所称的“选择性的豁免”(tailored forgiveness)。(49)参见Jason Scott Johnston. The Return of Barga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How Standard-Form Contracts Enable Cooperative Negotiation betwee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104 Mich. L. Rev. 857, 879 (2006).详言之,格式合同允许出卖人在合同生效以后,选择性地主张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如果某个顾客可靠又不会偷奸耍滑,就免除其合同义务;但在签订合同之前很难分辨出哪些顾客是靠得住的,也就无法优待他们。(50)签订了格式合同即成为保险消费者,选择性豁免的功能就是令隐藏的消费者类型现出原形。选择性豁免的功能是令作为格式合同当事人的顾客类型暴露无遗。类似地,酒店也可以选择性豁免的手段来适用其退房规则。参见Lucian A. Bebchuk, Richard A. Posner. One-Sided Contracts in Competitive Consumer Markets, 104 Mich. L. Rev. 827, 834 (2006).在保险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在合同成立之后,才甄别出有逆向选择行为的投保人,并冷眼相待,但这属于事后的方法,而不是典型的事前防范道德风险的做法。
与之相反,政府可没有这种“奢侈”的裁量权。例如,政府不得一面给予某些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利益,一面却拒绝其他同样没有资格的申请人。笔者揣测除了违反制定法,许多观察者还会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有悖实质的正当程序(原文系“正当程序的后一部分”,一般认正当程序包含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方面——译注)。
在保险的治理说之下,保险人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像政府一样,依循正当程序对待被保险人呢?在许多州,倘若保险人“恶意”拒绝被保险人本属有效的理赔申请,则保险人需承担责任。(51)参见Zilisch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995 P.2d 276, 279(Ariz. 2000).详言之,一旦保险人恶意拒赔,被保险人不仅有权要求赔偿合同约定的保险金,还有权主张合同以外的损害赔偿,甚至是惩罚性赔偿,这无疑将超出合同约定的金额。而事实上,被保险人甚至无须就保险人的主观恶意承担举证责任。相反,依主流标准,仅当被保险人的理赔请求存在“合理争议”时,拒赔才可能正当。除此之外,拒赔均被推定为恶意。(52)机动车保险公司在处理“存在合理争议”的理赔请求时,必须“善意且尽合理注意”,参见Zilisch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995 P.2d 276, 279 (Ariz. 2000); 有案件运用合理争议标准支持保险人的拒赔处理,本案原告在实施子宫切除术之前即提出了预赔付请求,参见LeRette v. Am. Med. Sec., Inc., 705 N.W.2d 41, 44, 50 (Neb. 2005); 若机动车保险人无足够理由相信理赔请求“存在合理争议”,即不得拒赔,参见Trinity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 Sch.—Freistadt v. Tower Ins. Co., 661 N.W.2d 789, 795 (Wis. 2003).
尽管表面上这一判断标准甚具意义,但保险人一旦拒赔就可能要赔偿数倍于保险金的款项,这种威胁驱使保险人尽量确保不拒绝有效的理赔申请。结果就是保险人会以更加公平的程序考虑被保险人的请求,被保险人由此获得一种“事实上”的程序权利。另外,在许多被保险人恶意要求理赔的案件中,常常有证据表明保险人自身也存在不当行为;而如果政府工作人员从事了相同行为,很可能招致违反正当程序的非难。(53)这样的案件不在少数,参见前引,Abraham文。从这些案例中我总结出,如果保险人处理理赔申请,在错误拒绝一项并无“合理争议”的请求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不当行为,那么即使被保险人要求理赔系恶意行为,成功的概率也很大。也就是说,这里的保险人所采取的“不正当的程序”起了决定作用。(54)参见前引,Abraham文。
除了上揭普通法义务,制定法也有关于保险人义务的诸般规定,这表明保险人提供正当程序的义务与日俱增。举例言之,不少州规定,若拒绝理赔,保险人应当给予受益人寻求行政复议的权利。(55)例如伊利诺伊州规定,寻求复议的申请,必须经过独立的专业医疗复审,参见Rush Prudential HMO, Inc. v. Moran, 536 U.S. 355, 361 (2002).大部分州还颁行了《不当保险行为示范法》,授权保险委员会规制不公平乃至欺诈性的保险行为。(56)参见Unfair Claims Settlement Practices Act, at ST-900-1 to -6 (Nat’l Ass’n of Ins. Comm’rs 2012);关于各州授予保险委员会的权力,参见前引,Abraham文。
根据服务区域内多年来降雨强度、一次降雨历时的发生概率统计,以10年一遇大暴雨事件发生和区域面积因素,雨水调蓄池容积为[10]
然而除了普通法上的恶意责任和有限的制定法义务,保险法为被保险人创设的正当程序权利并不多,可能立法者也发现如此立法实所难能。让我们设想一种典型的场景,普通的合同当事人没有义务为对方提供公平的程序,政府却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人们可能会认为,治理说把保险视为替代政府,所以保险人依保险法所负之义务介乎以上两个端点之间。比如,投保人递交保险申请,保险人依据该申请所陈述的事实承保。随后被保险人遭受损失并提出理赔请求,保险人在调查的过程中却开始怀疑,被保险人可能从事了最严重的逆向选择行为:他在保险申请中,故意对风险作了虚假陈述。但保险人绝难保证获得这种欺诈行为的证据。于是,保险人倾向于基于某些理由拒绝这些人的理赔申请,但却不会基于类似理由拒绝赔偿别人,因为他们没有欺诈行为的嫌疑。(57)参见Heller v. 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y, 833 F.2d 1253, 1257 (7th Cir. 1987).海勒案涉及的伤残险规定,“若被保险人因伤或者因病,完全丧失从事其日常工作的能力”则可要求赔偿误工费。被保险人是一名心脏病学专家,擅长侵入性手术,但是在投保几个月后,他罹患腕道狭窄综合征,手掌及手指的灵活性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接受一项选择性手术有可能使被保险人回到工作岗位,但他拒绝了手术,因此保险人作出拒赔处理。另一项拒赔原因或许是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仍然能够“从事其日常工作”。保险人陈述的拒赔原因很难站得住脚,以至于主张被保险人欺诈反而更有说服力,或许正是因为认为被保险人有欺诈行为,保险人才把案件一路上诉到第七上诉巡回法院,尽管最后以败诉告终。其他可能存在极端道德风险的场合——例如故意纵火——也能作如是观。
没有哪一项保险法规则禁止保险人——尽管其动机可能隐而不彰——使用这样的伎俩,只要被保险人之请求的有效性存在“合理争议”,这是判断保险人是否恶意拒赔的通行标准。(58)参见前引。保险人得视其方便而定,自由选择主张或者放弃拒绝赔付的权利。易言之,对某些被保险人的请求援引抗辩,却对其他人放弃此种抗辩,哪怕此二者之客观情事毫无二致。(59)可以想见,各州“不当保险行为法”能够规制此类行为,若保险人“频繁拒赔,以至于成为一种常规的商业操作”,却在“拒绝赔付时,无法立即从保险合同中找出关于拒赔理由的合理解释”,州法即得制裁之。Cal. Ins. Code § 790.03(h)(13) (West 2005).因此,保险人就拥有了主张或者放弃其合同权利的裁量权,这与上面举的例子同出一辙——汽车经销商也可以自由决定主张还是放弃汽车保修单所规定的权利。
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保险人应当以统一标准对待所有的理赔申请,这是一项有力的证据,证明私人政府说的解释力或许很有限。纵使保险人确实有义务给予被保险人公平的程序权利,此义务却并未要求保险人以相同的实质性标准处理所有的理赔请求。问题在于应不应该令保险人负此种义务呢?
如果支持保险人应当负有此义务,或许可以直接从替代政府理论出发进行论证。对个人及企业的福祉而言,保险是一种重要的——即使不是最核心的——商品。保险与保险人能够促进满足人们的福祉,考虑到其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公正而中立地处理理赔申请,而不得只顾自己的利益”应当可以构建成为一种义务。此外,与其他继续性关系——如工会成员与工会的关系、某些劳动合同——类似,终止保险合同也很困难,或者代价高昂,因此需要一种程序性的措施,保护弱势一方免受强势一方投机行为的损害。如何实现这种保护呢?要求保险人拒赔时必须出示正当理由,并且严格依照该理由行事,不失为一种方法。相反,如果允许保险人运用上述“选择性豁免”的策略,将增加其拒绝赔偿有效理赔申请的风险,因为保险人有可能误认为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出于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某些被保险人可能面临这种无声的指控,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推翻保险人无端的怀疑——毋宁说,根本无从知道自己遭到了怀疑,也不知道这种怀疑正是保险人拒赔的原因。
但是有两种反对正当程序义务——比如公正地告知被保险人拒赔原因——的论证也十分有力,令人质疑上面提到的例子是否真的足以证成保险人的正当程序义务。第一点,正如我在下文将要阐明的,任何把保险视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学说,都必须承认政府系为多数成员的利益行事。如果被保险人以欺诈、纵火等手段不公正地获得保险金,等同于侵夺了本应分配给有效理赔申请的资金。最终,因为无效的申请也得到赔付,这一成本就会摊在现在以及将来的投保人头上,其支付的保费就会增加。大多数正直的投保人都不会同意用他们交纳的保险费去赔付有欺诈行径之人,尽管这有可能会伤及无辜,原本光明磊落却被误认为欺诈的被保险人也会受到牵连。(60)参见前引-以及辅助资料。第二点,即使明确规定正当程序义务,也可能只是一句空话。法律至今三缄其口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被保险人难以有效承担举证责任。为主张其正当程序的权利,被保险人须收集如下证据:① 保险人怀疑被保险人出于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而行为,一旦证明为真,保险人即有正当理由拒赔;② 如果不存在此种怀疑,保险人在与本案相同的情形下不会拒赔,却唯独在本案中拒绝赔付。仅满足条件①是不够的,因为唯此尚不足以证明保险人的怀疑正是拒赔的原因。但是获取条件②的证据,却需要调查、整理保险人文件中海量的数据。依我之见,法院即使在此拥有裁量权,也不会批准此类调查:首先,文件未必能证明保险人确实存有这种假设的怀疑;其次,获取、分析数据的巨额成本也令人望而却步,除非案件涉及大量同类型的当事人,或者保险金数额特别巨大。我研究保险法30余年,未尝见过当事人提出此等请求,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少数法院可能根本不会受理这样的案件。
综上所述,被保险人可能没有机会向保险人寻求所谓的正当程序权利。法院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此种权利,并据此制定法律,进一步贯彻私人政府理念,一切均是未知数。相反,保险人的恶意拒赔责任,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被保险人群体的利益,即要求保险人公正告知真实的拒赔原因。(61)参见前引。质言之,若保险人怀疑被保险人欺诈或者纵火,尽管没有证据,却仍然拒绝赔付,被保险人的请求又并无“合理争议”,则保险人须承担超出合同约定数额的赔偿责任。(62)参见前引以及辅助资料。在少数案件中,被保险人的请求确实相当有争议,却不是保险人拒绝赔付的真实原因,但这样的案件并不多见。果如此,则在保险人运用“选择性豁免”的策略时不加干预,便无伤大雅。
2. 保险“平等保护”
保险法采取某些保护措施防止保险人厚此薄彼。然而大多数保护都来自制定法与行政监管,而非普通法,而且保护程度也很有限。在州层面,立法与行政命令均禁止根据某些分类指标来确定保险费率,哪怕这样得到的保险费层级从保险统计上看其实十分完善。(63)参见Haw. Rev. Stat. § 431:10C-207(2005).各州的保险委员会皆有权禁止“不公正歧视”的保险费率,(64)参见前引,Abraham文。州法有时也在特定的保险种类中禁止实施某些计费标准。举例言之,夏威夷法就禁止机动车保险公司根据“种族、宗教、血统、年龄、性别、驾龄、征信情况、婚姻状况或者身体残疾”来制定标准或者收取保费。(65)参见前引。某些基于遗传信息的分类形式也受到管制。比如在联邦层面,《2008年反遗传信息歧视法》(GINA)即规定保险人在承保或者进行风险分类时不得索取或者使用投保人的个人遗传信息。(66)参见Pub. L. No. 110-233, § 101-104, 122 Stat. 881, 883-903,散见于《美国法典》第26、29及42卷(section)。“过半数的州也立法禁止,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保险人要求投保人做基因检测或者索取投保人自己所做检测的结果。”(67)参见前引,Abraham文。
保险法中有许多促进平等保护的规则,这些规则并不都涉及某个一以贯之的因素。如果说有,那就只能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因素,它不仅仅存在于保险法规则中,也将贯穿于美国宪法或者其他法律渊源提供的平等保护措施中。但是保险法促进平等保护的措施中有一个重要支系,其中存在一种共通的要素:非人力可控的损失原因。因为许多保护性规则禁止考虑某些情况,如精神健康、性别、种族、基因组成等等,因为它们不受被保险人控制。(68)参见前引以及辅助资料。由是观之,保险法似乎认为若风险涉及罗尔斯所称的“天赋博彩”(69)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75 (1971).(即人的禀赋、智力等生而决定的因素,无法由个人控制,因此像一种赌博——译注),则至少一部分此种风险应由所有投保人分担,而不宜使一部分人因此优越于其他人。平等对待非人力可控的风险,这一规范似乎属于保险法的核心,保险法由此具有了平等保护的色彩。
是否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比如对保险人施加更严格的标准,限制其根据被保险人自身的风险计收保费的权力?毕竟,政府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按相同比率收取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费。(70)事实上,政府对所有人征收相同费率的公共保险费,情况远比刚才那个设问句复杂。政府用公共财政支付这种服务费用,而公共财政主要通过累进税制征收,那么人们支付费用的比率其实并不相等。穷人比富人出的钱少,得到的公共服务却相同。为了补偿富人,或许可以提供更多的联邦农业补助、商务部服务,更好的社区治安或者垃圾清运服务,但至少从形式上看,因累进税制的缘故,富人为这些服务支付了更高昂的代价。相反,如果舍弃累进税制的公共财政,在形式上采用平税制,并设置相对较低的征税上限,以此支付社保与医疗保险费,那么实际产生的效果就类似于递减税制(regressive approach)。因为倘若根据个人的风险程度,按相同费率征收,则穷人支付的费用占其总收入之比例无疑将高于富人。果如此,则在其他的公共服务中,穷人与富人能够合理地分担成本,但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服务中,他们对成本的分担却未能令人满意。穷人支付此等公共服务费用的经济压力显然大于富人。遗憾的是,仅仅从保险的合同说转向治理说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因为采纳治理说本身并不能启示我们,应该认同什么样的政府理论。而政府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倾向。总之,指出分类收取保险费涉及平等保护问题,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保险法显然不欲以更加平均主义的姿态规制保险费率分类,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一旦这么做,将引发更严重的逆向选择与交叉补贴问题,人们恐怕难以承受。一般而言,如果分类计收保费的依据是人力可控的风险,就很少受到管制。例如,包括机动车责任险在内,责任保险人有权部分依照被保险人以往的受损失情况计算保费。(71)参见Your Choice Auto Insurance Options, Allstate, http:// www.allstate.com/auto-insurance/auto-insurance-features.aspx (last visited Jan. 11, 2013)(安全驾驶津贴)。诚然,逆向选择的风险在某些时候被过分夸大,但是夸大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72)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参见Peter Siegelman. Adverse Selection in Insurance Markets: An Exaggerated Threat 113 Yale L.J. 1244(2004).若禁止依以往经历收取保费,高风险的驾驶人就倾向于购买更高额度的保险,但他们缴纳的保费仍与获得的保险金赔偿不相称。平均水平风险以及低风险的驾驶人——显然是指多数投保人——自实际效果而言,就需要补贴少数高风险的驾驶人。这实非其所欲。
当然,保险法也可以规定为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但这是一个将资源分配给少数人的问题,能否证成其正当性却未可知。事实上,这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共同体治理的特征。这种冲突在治理说的第二个分支中有所体现。
(二) 作为组织的保险:多数被保险人与少数被保险人之关系
在将保险视为替代政府之余,治理说的另外一个流派把保险当作被保险人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依此观念,保险人更像是代理人或信托受托人,其为投保人—委托人之目的服务,投保人为此种服务付费,保险人遂得从中赚取利润(在允许的情况下)。(73)从法律形式上讲,互助保险公司比股份制的保险公司更符合这一学说,因为互助保险的投保人互为彼此的保险人。虽然互助保险的投保人几乎不会控制或者影响公司的运营管理,但互助型公司与股份制公司的差别主要在于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订立的单个合同仅仅作为一种法律手段,使保险这种制度得以建立并维系。因此可将保险人理解为一种媒介;投保人最初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投保,经由这种媒介成为“团体”的一分子,竟将利己转化成一种利他主义。(74)投保人分类的冲突“反映了个人自治与群体团结对立产生的紧张关系”,参见Regina Austin. The Insurance Classification Controversy, 131 U. Pa. L. Rev. 517, 518 (1983); 保险法之目的包括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合理,以及促进被保险人之间的平等,参见Spencer L. Kimball. The Purpos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 the Theory of Insurance Law, 45 Minn. L. Rev. 491-498(1961).
如果像上文所阐发的把保险视为替代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单个被保险人足以代表整个被保险人群体的情况。然而一俟考虑多数被保险人与少数被保险人之关系,此种假设就难以令人满意。将保险解为一个共同体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果之一是保险人退居次要地位,被治理者,即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则成为关注的重点。某些行为以往可能被认为是保险人投机取巧,此时却可被视为正常的市场反应,其目的在于满足多数被保险人的要求。
让我们假定市场上的出卖人有动机去满足少数消费者的偏好。事实上,与政治手段相比,市场也确实更擅长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75)参见Henry Hansmann.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288 (1996).但还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所有人均无法以理想的价格买到满意的商品。少数消费者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对出卖人而言不划算,因为需求量太少。尽管少量消费者想要1/4码的鞋子,制鞋厂也只生产半码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半码鞋可以接受,他们不愿为制造1/4码的鞋买单,即使那样其实更加合脚。与之类似,在医疗保险中,精神疾病险受到限制,可能也反映了多数人之偏好(此种偏好是否符合多数人自身的长远利益,系另一事),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想要更广泛的身体疾病而非精神疾病保险。另如,在Atwater奶油公司案中,(76)参见Atwater Creamery Co. v. W. Nat’l Mut. Ins. Co., 366 N.W.2d 271, 278 (Minn. 1985); 另参见前引-以及辅助材料。入室盗窃险要求“建筑物外部留有可见的痕迹”方得请求赔付,可能也是多数人偏好的体现,他们希望避免支付额外的保费——因为如果损失究竟确实是入室行窃还是监守自盗所致,需要逐案分析,保险人势必整体提高保险费。准此而言,保险人遭受的许多批判或许恰恰是其对多数人偏好的回应。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一旦把保险理解为一种组织性的治理,这种现象将呈现出另外一种面目。申言之,如果不把少数人看作一群有特殊癖好又没钱满足这些癖好的人,而是视之为共同体的一员,只是其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存在冲突,那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保险法作为一种被保险人自我“治理”的工具,是否应该以及何时应该制定逾越市场规律的规则——市场规律就是满足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之偏好。
讨论保险“平等保护”的时候我提到,现如今的保险法仅在“非人力可控的风险”对少数被保险人不利时方提供保护,比如种族、宗教信仰、性别与遗传等。以此为参照系,治理说的不同流派可能更有平均主义倾向,或者更厌恶平均主义(甚或追求自由主义)。
有一种人力可控的行为,保险法一般选择让被保险人自负其责,而不是让所有被保险人共担风险,那就是被保险人可能从事的投机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会妨害保险之功能,其中尤以逆向选择(77)逆向选择是指遭受损失的风险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更倾向于投保以预防损失。参见前引,Abraham文。保险人试图用多种手段阻却逆向选择。除了例外地禁止依据非人力可控的风险计算保险费率,监管者原则上允许保险人以此种方法阻却逆向选择行为。例如,保险人得向保险申请人询问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反映出来的风险水平计收保费。如果赔偿某种损失很可能滋长逆向选择,保险人即可在保单中设置限制条款,排除对这些损害的赔偿。本于此,房屋保险就珠宝损失的保险金设置上限;人寿保险则限制对自杀损害的赔偿,只要自杀发生在保险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和道德风险(78)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倾向于对避免保险损失尽更少的注意义务,而如果没有保险,他反而会更加谨慎”。保险人力图防范道德风险,方法是部分参照以往的损失情况收取保费,从而激励被保险人在有保险的情况下依然谨慎行事,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后续保险期间的保险费。此外,保险人还在保单中对承保范围设置各种限制,直接或者间接地防范道德风险。例如,没有哪种责任保险赔偿被保险人“期待或计划”的损失,或者他故意造成的损失。又如,美国的大多数商人都购买了“一般商业责任险”(CGL),这种保险就不赔偿因环境污染承担的责任,包括人身损害及其他损害赔偿责任。依余所信,这种安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以下事实:被保险人可以采取谨慎的预防措施,因此“慢性”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力可控的,但保险人却无法观测到污染情况。为典型代表。尽管许多保险范围限制和法律规则的目的都是防范这两种危险,有时却被指责是保险人在咄咄逼人。(79)有论者指出“侵权法的扩张导向了一系列逆向选择的‘死亡漩涡’……最终将使保险市场的某些部分走向崩溃”,参见Tom Baker.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 Hazard, 75 Tex. L. Rev. 249(1996);前引, Siegelman文。无可否认,保险人总是假防范风险之名,行得寸进尺之实。但如果说保险人的许多阻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努力,其实也是在防止少数申请人或被保险人侵害多数人之利益,也并不是无稽之谈。
倘若不考虑高风险申请人带来的风险,直接为其承保,逆向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大量低风险的申请人停止投保或缩减原本计划的投保方案,或者继续投保,这样就不得不交叉补贴高风险的投保人。允许保险人抑制这种趋势,多数人由此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少数逆向选择者之侵害;而保险人无法采取措施阻却逆向选择,就创造出一种“少数人特权”。
同理,若保险条款或保险人不尽力防范道德风险,某些被保险人就会变得更加粗心大意,这显然对时时保持谨慎的被保险人不利。允许保险人制定此等条款、采取此种做法,就保护了多数人免受少数人侵害;而保险人无法采取措施防范道德风险,也会创造出“少数人特权”。
保险人援引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曾有所耳闻。例如他们论证说,如果不对上一个保险年度出过险的驾驶人收取更多保费,对安全驾驶者而言就不公平。又如,保险人过去曾主张,如果不允许在个人自愿购买的医疗保险中加入在先状况条款,无异于鼓励人们病痛缠身以后才去买保险,这对身体无恙就主动投保的人不利。乍一看,少数投保人的行为需要多数人负担成本,就侵犯了多数人的权利,但是这个命题仅在多数人对少数人不负担义务时方成立。换言之,若多数人有义务让少数人从事某种行为,则少数人的此种行为便不算侵犯其权利。果如此,则只要公民有获得医疗保险的权利,在先状况的限制条款就侵害了少数被保险人的权利,而并未损及多数人,少数投保人是否在生病之前就购买保险则非所问。
易言之,治理说有助于理解保险权利与义务——它不仅仅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法律上的”关系,也是被保险人之间“事实上的”关系。唯值注意者,此说本身并不足以揭示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无法告诉我们多数人对少数人应当享有何种权利,或者相反,少数人得对多数人主张何种权利。这是实质性的保险权利义务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某种权利义务理论可以认为,仅应禁止依某些非人力可控的因素确定保险费率之高低。而在人寿保险与终身年金保险中,允许根据性别收取不同保费。因为尽管依性别计收寿险保费对女性不利,但在终身年金的情形中却对女性有利。或者该理论也完全可以主张机动车责任险应严格依照驾驶里程计算保费,以此鼓励人们使用替代性的、节约能源的交通方式。(80)机动车保险法不计后果地鼓励人们驾车,罔顾“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环境恶化以及汽车带来的其他成本”,参见Jennifer B. Wriggins. Automobile Injuries as Injuries with Remedies: Driving, Insurance, Torts, and Changing the “Choice Architecture” of Auto Insurance Pricing, 44 Loy. L.A. L. Rev. 69, 82-84 (2010).要言之,治理说之下,如何确定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倘若法律要改变或推翻市场对这些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徒“保险是治理手段”这种观念不足以成事,尚需借重一种“专门的理论”来回应多数人对少数人应负何种义务的问题。若欠缺一种专门理论,我们就只有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基础。
六、 结 论
本文的主旨在于,用于解释保险的不同学说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把握保险与保险法之全貌,或许还能突出某些应然层面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被某些学说故意隐藏或者未受到其足够重视。揭示保险的不同学说,也为保险法一直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保险单的词句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拘束力,以及公法价值应当在保险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按照这个思路,合同说体现了保险合同条款本身的重要性,并强调承保范围的细微差别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未能充分考虑时不时与合同条款发生冲突的被保险人权利。从保险法对待医疗险与机动车责任险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此二种保险是公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公用事业/受管制行业说恰好抓住了这一点,至于如何解释保险法对待其他类型保险的方式,它却无能为力。产品说则精准地描述了保险在何种意义上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是一种产品,而不是合同,但如何评判“保险产品”设计是否有效,它未能提供一个妥当的标准。就解释保险法的某些特征而言,治理说或许略胜一筹——比如保险人恶意拒赔构成诉讼原因,禁止根据非人力可控的因素划分被保险人的风险等级,以及保险条款为防范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所作的努力——然而仍有大量的保险与保险法问题,治理说未置一词。
此外,当我们从描述性的事实层面转向规范性的应然层面时,并没有哪一种学说仅凭自身就能解决他们所争辩的问题。用一个现在已经显得陈腐的比喻,每一种学说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描摹了大教堂的一种面貌,根据其所观察到的面貌,各种学说提出自己的规范含义。(81)关于这个比喻的起源,参见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85 Harv. L. Rev. 1089, 1089-1090 n.2 (1972).综合事实描述与规范描述所创造的图景,自然比单单一个合同说更加全面完善。但我们也不能指望,仅凭发展一种学说,就知道保险应当如何改变,保险法应该怎么做,但是某些学说的倡导者有时确实这样异想天开。依合同说,某些本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得不退居幕后,而结合事实与规范层面的做法使之得以粉墨登台。但这仍然只是观察保险法的一种特殊的透镜,不足以告诉我们法律应如何规制或者应该做什么样的政策选择。看待保险法的不同方式只能提醒我们注意,尚存在其他的选择可能,只是这些可能性都湮没在了主流的概念体系中。而事实上作出何种选择,仍操之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