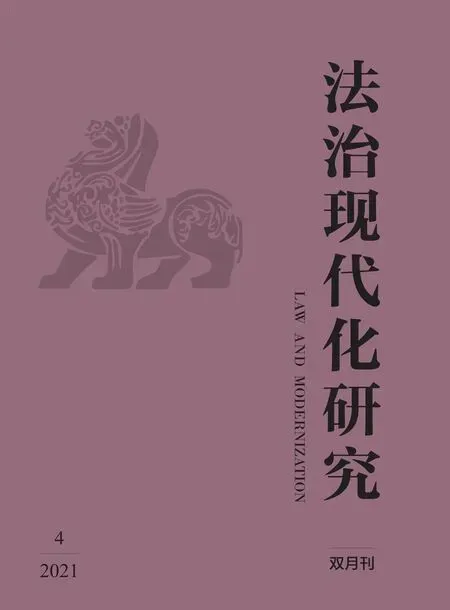论遗弃罪相关问题
[日]桥爪隆 著 王昭武 译
一、 引 言
日本《刑法》第217条(普通遗弃罪)处罚的是“遗弃因年老、年幼、身体障碍或者疾病而需要扶助的人的”行为,第218条(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处罚的是“对年老者、年幼者、身体障碍者或者患病者负有保护责任者,将其遗弃或者对其生存不给予必要保护的”行为,对后者的处罚要重于前者。(1)日本《刑法》第217条〔普通遗弃罪〕:“遗弃因年老、年幼、身体障碍或者疾病而需要扶助的人的,处1年以下惩役。”日本《刑法》第218条〔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对年老者、年幼者、身体障碍者或者患病者负有保护责任者,将其遗弃或者对其生存不给予必要保护的,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惩役。”日本《刑法》第219条〔遗弃致死伤罪〕:“犯前两条(第217条、第218条)之罪,因而致人死伤的,与伤害罪比较,依照较重的刑罚处断。”——译者注这里有三点很重要:(1) “遗弃”与“对其生存不给予必要保护”是分别规定的;(2) 对于“不保护”,处罚对象仅限于保护责任者;(3) 对于“遗弃”,不管行为人是否处于保护责任者的地位均应受处罚,但对保护责任者的“遗弃”,加重了刑罚。基于这几点,如何理解遗弃罪的结构,就属于解释论上的重要课题。本文想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对遗弃罪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2)这样,(广义的)遗弃罪概念就包括遗弃(狭义的遗弃罪)与不保护(不保护罪)这两种行为类型。为此,在使用遗弃罪这种表述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区分广义的遗弃罪与狭义的遗弃罪,但一一标明广义或者狭义过于繁琐,因而,在结合前后文意思明确的场合,就不再一一标明。
二、 基本理解
(一) 罪质
判例将遗弃罪理解为针对生命、身体的危险犯,(3)例如,大判大正4·5·21刑録21輯670頁、大判昭和3·4·6刑集7巻291頁等。通说对此也持支持态度。(4)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第3版〕』(1990年)452頁、大塚仁『刑法概説(各論)〔第3版増補版〕』(2005年)57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42頁、斎藤信治『刑法各論〔第4版〕』(2014年)、曽根威彦「遺棄罪」芝原邦爾ほか編『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各論』(1996年)20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2015年)108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2015年)61頁、佐久間修『刑法各論〔第2版〕』(2012年)57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90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95頁、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2016年)75頁、橋本正博『刑法各論』(2017年)46頁。相反,主张本罪是针对生命的危险犯的观点也属于学界的有力观点。(5)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増補版〕』(2015年)66頁、小暮得雄ほか編『刑法講義各論』(1988年)65頁[町野朔]、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27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31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1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40頁、伊東研祐『刑法講義各論』(2011年)28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33頁。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在于,在虽然能认定存在针对身体的危险,但鲜有针对生命的危险的场合,能否成立遗弃罪?(6)有关两种观点的详细研究,参见和田俊憲「遺棄罪における生命保護の理論的構造」山口厚編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各論』(2007年)45頁以下。
如果原样适用通说观点,存在过度扩大遗弃罪成立范围之虞。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是存在被害人遭受伤害危险的场合也要成立遗弃罪,例如,在寒冷的日子,母亲让幼儿一个人在外面玩耍,对于这种行为,也难免会以幼儿有可能摔倒受伤或者感冒为理由,而认定成立遗弃罪。因此,即便是将本罪理解为针对生命、身体的危险犯,针对身体的危险的内容,也有必要限于存在重大伤害危险的情形。(7)也有学者基于通说立场,主张将针对身体的危险限于针对重大健康伤害的危险,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90頁。并且,如果将针对身体的危险的内容进行上述限制,在存在重大伤害危险的场合,也基本上能认定存在针对生命的危险,因此,其结论与将本罪理解为针对生命的危险犯的观点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非要找出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在虽然存在重大伤害的危险,但还不能说是针对生命的危险的场合(例如,失明的危险,或者因冻伤而可能失去手指的危险),能否认定成立本罪?有学者正是设想到这种情形,而主张应该将重大伤害的危险也包含在本罪的保护法益之内。(8)持这种理解者,参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95頁。不过,对于此类案情,(当然也取决于对危险性内容的理解)认定存在针对生命的危险,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按照这种理解,直接将本罪理解为针对生命的危险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 危险性的判断
遗弃罪没有明文要求引起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只要实施遗弃或者不保护这种实行行为就直接达到既遂。因此,本罪不是具体的危险犯,而是抽象的危险犯。(9)也有观点主张本罪是具体的危险犯,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第3版〕』(1990年)452頁。既然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外,本罪没有明确要求另外发生危险,就很难作出这样的解释。如后所述,毋宁说,作为实行行为的内容,应该要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既然主张本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引起针对生命的危险,那么在缺少针对生命的危险的场合,就不应成立本罪。在对“遗弃”“不保护”这种实行行为进行解释时,就应该考虑行为是否具有针对生命的实质性危险。(10)山口教授将这种中间形态的危险犯称为准抽象的危险犯,参见山口厚『危険犯の研究』(1982年)251頁以下。因此,如果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能够切实地预见被害人会得到保护,就可以以不具有实质的危险性为理由,否定属于“遗弃”或者“不保护”。举一个典型例子,将婴儿放在医院设置的“婴儿邮筒”或者警局门前的行为需要具体探讨的是,是否属于能够切实地预见被害人会得到保护的状况。这样,即便从结果上看婴儿最终得到了保护,但在不具备婴儿会切实地被相关人员发现,并立即得到保护的态势的场合,就不能否定引起了危险,应成立本罪。
对于那些“抛弃小孩”(neglect)的案件,(11)Neglect原意是指疏忽、忽略,这里是指一种虐待儿童、虐待障碍者、虐待老人、虐待患者的行为,针对小孩而言,是指弃婴(放弃养育)、放弃监护、疏于养育等行为。——译者注对危险性的判断尤其重要。例如,抚养幼儿的母亲因为精神疲惫不想做饭,一整天没有管小孩,即便如此,也不会直接成立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这是因为即便一天不吃饭,只要是健康的儿童,(可能)都不会直接发生针对生命的危险。不过,根据被害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即便是短时间的“抛弃小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实质性危险,应认定成立本罪。而且如果长时间“抛弃小孩”,即便是健康的儿童,也应成立本罪。这样,在判断“抛弃小孩”是否属于“不保护”之时,以具体的事实关系为前提,对实质性危险进行判断就是不可或缺的,对其界限的判断也属于微妙的问题。(12)对于保护责任者虽然不足量但还是给予了食品的案件,是否具有“不保护”的该当性也会成为微妙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参见丸山嘉代「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における不作為内容の特定」『捜査研究』593号(2001年)17頁以下。儿童与保护责任者之间出现场所上的隔离的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将小学低年级的小孩放在家中,夫妇二人外出,一晚上喝酒散步,直至第二天早上才回家,即便如此,想必也不构成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但是,根据儿童的年龄、健康状况,有时候也会认定成立本罪。如果长时间离家,当然应该成立本罪。即便是这种情况,基于实质性危险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因为缺少实质性危险而被评价为不符合“遗弃”“不保护”的场合,即便小孩因意想不到的事故等而死伤,当然也不会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伤罪。(13)这种场合存在认定成立过失致死伤罪的余地,但在以不具有针对生命的实质性危险为理由否定具有遗弃、不保护的该当性的状况下,能否肯定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三、 遗弃与不保护的含义
(一) 学说状况
有关第217条(普通遗弃罪)中的“遗弃”与第218条(保护责任遗弃罪)中的“遗弃”“不保护”的含义,学界展开了非常复杂的研究。学说之间的对立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1) 从什么视角来区分“遗弃”与“不保护”?(2) 对于处罚不作为的遗弃所必要的作为义务与第218条的保护责任,能否按照同一意思来理解?
通说(A说)将“遗弃”理解为,通过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场所上的隔离而引起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再将“不保护”理解为,不伴有场所上的隔离,但不实施生存所必要的保护的行为;并且,通说(A说)还认为,造成场所上的隔离的“遗弃”是能够想见作为与不作为的,其中,不作为的遗弃是真正的不作为犯,处罚这种遗弃以存在作为义务为必要,负有解消场所上的隔离这种作为义务的人,就正是那些“对年老者、年幼者、身体障碍者或者患病者负有保护责任者”,即主体限于保护责任者。这样,通过对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按照同一含义来理解,就不能以第217条来处罚不作为的遗弃,而完全是以第218条来处罚。(14)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第3版〕』(1990年)452頁以下、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43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94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2015年)63頁。
如果以通说的这种理解为前提,由于第217条的处罚对象仅限于作为的遗弃,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之间的区别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遗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通过对被害人进行场所上的移动而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移置”;二是将被害人扔在现场不管,通过行为人本人的场所上的移动而形成场所上的隔离的“置之不顾”(即抛弃不管),这样,“移置”与“置之不顾”的区别,就与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的区别相对应。不过,对于这种观点,批判意见指出,例如,默许被害人走向危险场所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移置”,相反,破坏吊桥使得被害人无法接近扶助者的行为则能够被评价为作为的“移置”,因而,“移置”与“置之不顾”的区别,实际上与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的区别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15)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大塚仁『刑法概説(各論)〔第3版増補版〕』(2005年)59頁。既然A说的前提在于作为义务等同于保护责任,那么,按照该说的立场,有关第217条之遗弃与第218条之遗弃的关系,与考虑“移置”与“置之不顾”的区别相比,重视行为方式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这种区别,要更具有理论上的整合性。
按照这种通说观点,尽管第217条与第218条都同样使用了“遗弃”这一表述,但其内容却并不相同。正是以此作为问题,主张应将两罪的“遗弃”的内容均限于“作为的遗弃”的观点(B说)成为近年的有力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遗弃”仅限于作为的形态,不问有无场所上的隔离,不作为形态的参与均相当于第218条的“不保护”。(16)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増補版〕』(2015年)68頁(不过,只有作为的“移置”才该当于“遗弃”)、小暮得雄ほか編『刑法講義各論』(1988年)68頁[町野朔]、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30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41頁、伊東研祐『刑法講義各論』(2011年)31頁、日髙義博「遺棄罪の問題点」中山研一ほか編『現代刑法講座⑷』(1982年)168頁以下。亦即,(1) 不是根据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而是根据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来区分“遗弃”与“不保护”;(2) 既然不作为形态的参与完全该当于“不保护”,那么就应该限于能认定负有保护责任的情形才受到处罚。
B说的长处在于,能够统一地解释第217条的遗弃与第218条的遗弃,(17)不过,对于A说,也完全有可能这样解释:仅限于能认定负有保护责任的情形,才会处罚不作为的遗弃,因此,不过是仅限于第218条,才处罚不作为的遗弃,并没有对“遗弃”概念在第217条、第218条做不同解释。指出这一点者,参见齊藤彰子「遺棄罪」『法学教室』286号(2004年)53頁注40。既然完全是以第218条来处罚不作为形态的遗弃,那么在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按照同一含义来解释这一点上,其与A说并无不同。因此,A说与B说之间不过是,在将不伴有场所上的隔离的不作为形态的参与,究竟是归于“遗弃”还是归于“不保护”这一点上存在对立,在实质性结论上并无大的不同。(18)指出这一点者,参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43頁注59、木村光江「不作為による遺棄」『現代刑事法』53号(2003年)100頁以下。
相反,C说则对A说提出了根本性批判。(19)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平野龍一「単純遺棄と保護責任者遺棄」『警察研究』57巻5号(1986年)9頁以下(不过,平野教授主张,没有必要将“置之不顾”作为普通遗弃罪来处罚)、岡本勝「『不作為による遺棄』に関する覚書」『法学』54巻3号(1990年)9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5頁、曽根威彦「遺棄罪」芝原邦爾ほか編『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各論』(1996年)30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34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98頁以下、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36頁、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2016年)77頁以下。在A说的前提之中,C说虽然维持根据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来区分“遗弃”与“不保护”,但主张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不是同一含义,有些场合,即便不能认定负有保护责任,也应肯定负有作为义务。因此,只要能认定负有作为义务,通过不作为而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行为(不作为的“遗弃”),也完全有可能以第217条予以处罚;在作为义务之外,还具有保护责任者地位的,则以第218条予以加重处罚。不过,即便是以这种观点为前提,对于“不保护”,也仅属于第218条的处罚对象,因此,对于没有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不保护被害人的不作为,就限于能认定负有保护责任的情形,才能以第218条予以处罚。
由于极其缺乏适用第217条的案例,因而判断态度未必明确。(20)有关判例的情况,参见松原和彦「保護責任者遺棄罪における『保護責任』についての一考察(3·完)」『北大法学論集』58巻1号(2007年)132頁以下。对此,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判例认为,因自己的驾驶过失而致行人重伤的汽车驾驶者属于第218条的保护责任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应该理解为,日本《刑法》第218条所谓遗弃也包括单纯的‘置之不顾’,如本案那样,汽车驾驶者因过失使得行人身负达到不能行走程度的重伤……将被害人扶进汽车之后离开事故现场,将车开至正好因下雪而天色昏暗的车道上,谎称喊医生而将被害人扶下车,将该人扔在该地之后继续驾车离开,此时就正属于‘遗弃患者之时’”,从而判定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21)最判昭和34·7·24刑集13巻8号1163頁。本判决不过是在以承认被害人负有保护责任作为前提的基础之上,显示了有关第218条之“遗弃”概念的判断,并非就第217条与第218条的“遗弃”的异同显示了某种判断。不过,对于“日本《刑法》第218条所谓遗弃也包括单纯的‘置之不顾’”这一表述,如果作为其反对解释,认为其旨趣在于,第217条中的遗弃不包括“置之不顾”,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评价为,最高裁判所的这一判例是以A说立场为理论前提的。
(二) 若干探讨
1. 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的关系
这样,对于遗弃罪的结构,学界展开了非常复杂的研究,其中,A说与B说不过是围绕第218条内部的“遗弃”与“不保护”之分配的对立,并不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因此,解释论上的重要对立是,究竟是按照同一含义来理解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完全是以第218条来处罚不作为的遗弃,还是应该分别理解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承认也有以第217条处罚不作为的遗弃的余地?
对于这一点,应该认为后者(C说)的立场是正当的。在能认定具有保护责任者地位的场合,(与普通遗弃罪的情形相比)遗弃行为被加重处罚。并且,按照A说,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是相同含义,那么,基于该说之立场,由于作为义务(也就是保护责任)的存在,与作为的遗弃相比,不作为的遗弃总是被加重处罚。但是,难以在理论上将这种结论予以正当化。(22)关于这一点,参见平野龍一『刑法概説』(1977年)163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各論』(1999年)25頁。这是因为,作为义务能够为不作为与作为的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奠定基础,对于将不作为与作为同等处罚可以予以正当化,但是,作为义务不可能成为与作为相比要加重处罚不作为的根据。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还是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23)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于,是否可以明确区分“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这里的“作为义务”是,对于“遗弃”被当作“不真正不作为犯”而以第217条——行为人是保护责任者之时,则以第218条——予以处罚这一点提供根据的“作为义务”(或者“保障人地位”);“保护责任”是,为针对“遗弃”的加重处罚提供根据,并且,属于处罚“不保护”之根据的特别的“保护责任”。例如,邻居出于好意将幼儿带去郊游,但听任该幼儿自行离开的,将该情形理解为,以“先行行为”或者“对暂时保护他人的事实上的接受”为理由的“遗弃”(第217条)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原因在于,与邻居起初便出于遗弃的意图,而将幼儿从双亲处带离加以遗弃这种属于第217条的情形相比,对于该情形,没有理由予以更加不利益的处分),如果能够明确区别于,亲生父母听任幼儿自行离开这种属于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情形,就能够消除理解上的混乱。也就是,保护责任者限于亲权者、看护义务者,或者接受亲权者、看护义务者的概括性委任,对于需要扶助者有义务予以扶助的“特别义务者”;反之,在基于“先行行为”或者“对暂时保护他人的事实上的接受”的场合,行为人虽属于第217条的保障人,却不属于第218条的保护责任者。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第218条的保护责任属于“特别义务”,是加重了符合第217条之“遗弃”的情形的罪责,是为单纯的不保护的罪责提供追责根据;第217条的作为义务是“普遍义务(普通人的义务)”,不过是为第217条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提供根据(将第217条解释为“制造危险罪”,将第218条解释为“不解消危险状态罪”,就是与本文观点相类似的观点。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违反的是“不得制造危险”这种“普遍义务”,而后者违反的是“无论自己是否制造了危险,都必须予以保护”这种“特别义务”。山口教授也指出,“即便处罚抛弃行为,要求其与需要扶助者在一起,但若不要求其对需要扶助者进行保护,则毫无意义”[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5頁注39],也就是,即便是不负有“保护义务”的人,也可能负有报告警察,或者将需要扶助者带至其保护责任者之处这种程度的作为义务)。问题在于,也有判例对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肯定存在保护责任(最判昭和34·7·24刑集13卷8号1163頁)。但是,无论是通过交通事故而制造出“疾病者”的先行行为,还是日本《道路交通法》赋予事故车辆的所有同乘人员的救护义务,都不足以为超过“作为义务”的“保护责任”提供根据。因此,如果这种程度就可以认定存在“保护责任”的话,就很难将其与“作为义务”区别开来。但是,如果不能区分二者,就不可能消除有关“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的理解上的混乱(参见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王昭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以下)。——译者注因此,应该承认也有以第217条处罚不作为的遗弃的余地。
不过,即便承认也有以第217条处罚不作为的遗弃的余地,但具体来说,究竟何种类型能够成为处罚对象,则未必明确。既往的学说存在抽象地研究第217条与第218条之结构的倾向,但由于两者的主体也并不相同,因而,有必要通过设想具体的行为样态来展开研究。
2. 第217条与第218条的关系
对于第217条与第218条的关系,既往的学说存在这样理解的倾向:第217条与第218条属于相同的犯罪,第218条是基于保护责任的加重类型。然而,遗弃罪的本质在于,保护责任者因怠慢了对需要扶助者的保护而引起了危险,为此,就应该理解为,遗弃罪的犯罪类型原则上应该是第218条,第217条属于对外部人员引起危险的情形补充性地予以处罚的规定。(24)强调第218条属于遗弃罪的基本犯罪类型的观点,参见松原和彦「保護責任者遺棄罪における『保護責任』についての一考察(3·完)」『北大法学論集』58巻1号(2007年)161頁以下、和田俊憲「遺棄罪における生命保護の理論的構造」山口厚編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各論』(2007年)60頁以下。下面想具体阐述这种理解。
遗弃罪的客体(对象)限于因年老、年幼、身体障碍或者疾病而需要扶助的人。这些需要扶助者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妥当应对针对生命的危险,因而需要“扶助者”的保护。对这些需要扶助者而言,“扶助者”的保护正所谓“救命索”,对保证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第218条的旨趣应该是,通过处罚保护责任者怠于保护需要扶助者,从而保护“救命索”的机能。而且,既然“救命索”的机能对保护需要扶助者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应该将以保护责任者为主体的第218条定位于遗弃罪的基本犯罪类型。
相反,第217条处罚的是,外部人员使得需要扶助者之保护状态恶化的行为,就能够被理解为,为了强化对需要扶助者的保护的补充性规定。具体而言,将扶助者与需要扶助者分离开来,使需要扶助者丧失保护的行为,就是第217条的典型行为方式(例如,随意将年幼者从保护者身边带走的行为等)。
这样,在遗弃罪中,第218条是基本犯罪类型,第217条属于补充的处罚类型。两罪在法定刑上的巨大差异,也能从这一角度予以正当化。
3. 对第218条的解释
第218条的行为类型被区分为“遗弃”与“不保护”。不过,如前所述,本罪的处罚根据在于,保护责任者怠于保护需要扶助者,由此引起针对需要扶助者之生命的危险,因此,保护责任者没有实施必要的保护这一事实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就无法否认,将“遗弃”与“不保护”的区别予以相对化,不问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将“遗弃”归为作为的参与类型、“不保护”归为不作为的参与类型的观点(B说)也存在一定的理由。不过,(1) 现行法律特别将“遗弃”与“不保护”作为不同的行为类型加以规定;(2) 发生场所上的隔离本身就可能给需要扶助者的生命带来危险,有鉴于此,最终还是应该遵从通说观点,从保护责任者与需要扶助者之间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来区分两者。
实际上,根据是否出现了场所上的隔离,有时候实质性危险的判断也会不同。就不保护类型而言,如前所述,如果是短时间“抛弃小孩”,就不能被评价为“不保护”,只有在“抛弃小孩”(neglect)的状态持续进行的阶段,才该当于“不保护”。(25)例如,母亲已经下定决心“这是最后一顿饭”,给小孩提供午餐之后,即便其放弃抚养小孩的意思已经确定下来,在此阶段也不能成立不保护罪。只有不提供餐食的事态持续一定程度,才能成立不保护罪。相反,就遗弃类型而言,通过以保护责任者的意图作为危险性的判断材料,完全有可能只要出现了场所上的隔离,就直接肯定该当于“遗弃”。例如,如果母亲决意“抛弃小孩”,只要其将幼儿扔在家中不管而自己外出,在其离开家的时候就可能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场所上的隔离这一事实本身,为危险性奠定基础这一点为理由,与不保护相比,遗弃类型属于处罚时点被提前的行为类型。(26)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和田俊憲「遺棄罪における生命保護の理論的構造」山口厚編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各論』(2007年)65頁。另外,佐伯教授认为,与不保护相比,遗弃属于实行行为更容易认定,心理障碍更高的行为类型,参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99頁注35。另外,在上述案件中,如果母亲的意思是,事情忙完之后马上回家,那么,就不能被谓为因外出行为而创造了实质性危险,因此,不管幼儿而自己外出的行为,就不能被评价为“遗弃”;如果在外出之后,才打算不再回家的,此后,不解消场所上的隔离的行为,就应该被评价为不作为的遗弃。
4. 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
与第218条的构成要件相关,下面还想就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做些探讨。不保护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不给予必要保护的”行为,因而,本罪当然属于不作为犯。问题在于,遗弃罪中如何区别作为与不作为。
既往的学说给人的印象是,原则上是根据是否存在针对需要扶助者的身体的介入来区分作为与不作为。亦即,(1) 移动需要扶助者,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移置”是典型的作为的遗弃;(2) 将需要扶助者留在现场不管,通过保护责任者自己离去而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置之不顾”属于不作为的遗弃。不过,作为与不作为应该根据究竟是身体的“动”还是身体的“静”该当于构成要件来区分;并且,遗弃罪的实行行为,应该作为创造出场所上的隔离的行为来理解。因此,上述(1)的“移置”自不必说,对于上述(2)的“置之不顾”,既然是通过行为人从现场离开这种身体的“动”而创造出场所上的隔离,就应该被评价为是以作为方式实现了构成要件。(27)将“置之不顾”理解为作为的观点,参见酒井安行「遺棄の概念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28号(1983年)86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各論』(1999年)29頁。松原教授也承认,“置之不顾”的行为有相当于遗弃的余地,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38頁。就(2)中的行为人的身体动静而言,从创造出场所上的隔离这一视角来看属于“动”,而从(留在现场)不保护需要扶助者这一视角来看,又属于“静”。认为“置之不顾”属于不作为,这种理解也许重视的是后一视角中的“静”,但这样会混淆遗弃与不保护之间的区别。遗弃类型是通过创造出场所上的隔离而实现构成要件,因此,在是否成立遗弃罪这一点上,考虑的问题应该完全是前一视角中的“动”。(28)松原教授将这种有关“动”与“静”两个侧面的理解更进一步,对于正文中(2)那样的例子,以创造出场所上的隔离(作为的遗弃)与懈怠保护(不保护)这两种行为同时并存为理由,承认有作为第218条前段与后段的包括的一罪予以处罚的余地(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38頁)。尽管松原教授的问题意识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第218条的前段类型是将后段类型予以提前而进行处罚,那么,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前段的处罚就已经完全评价了行为的危险性。
下面想从这一视角,重新考虑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判例的事实关系。本案事实是,被告人造成被害人重伤后,将被害人扶进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将被害人扔在“天色昏暗的车道上”,就此驾车离开了现场。(1) 如果被告人起初就是出于将被害人扔在某处的意思,而将被害人扶进车内,离开事故现场,那么,一系列的移动过程就能够被评价为“移置”。(2) 如果被告人不是出于遗弃被害人的意思而离开事故现场,而是在驾车过程中才产生了遗弃的意思,那么,扔下被害人不管而自己离开的行为,就能被评价为“置之不顾”,(29)本案正属于这样的事实关系,因而,被作为“置之不顾”的类型来处理。关于这一点,参见栗田正「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34年度)285頁。如前所述,这种情形也应该被理解为作为的遗弃。相反,(3) 原本应立即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漫不经心地继续驾驶的,这种行为就有被评价为“不保护”的余地,那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现了构成要件。
另外,如上所述,本文的观点是,应该从究竟是身体的“动”还是身体的“静”创造了场所上的隔离,来区分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如果以这种观点为前提,基本上所有的遗弃都是由作为来实现的。不作为的遗弃就限于那些例外的情形,例如,需要扶助者试图从受到保护的场所离开,却不予制止(例如,对失忆症的高龄患者的徘徊不管不顾);默许需要扶助者离开(例如,不小心与需要扶助者乘坐了不同的车,自己却不下车,而是继续乘车离开)。
5. 对第217条的解释
第217条普通遗弃罪处罚的是,外部人员恶化需要扶助者之保护状态的行为。将扶助者(保护责任者)与需要扶助者从场所上进行隔离,恶化需要扶助者之保护状态的行为,就是其典型行为。这种场合也要求存在场所上的隔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要求的场所上的隔离,不是指行为人与需要辅助者之间,而是指扶助者(保护责任者)与需要扶助者之间。(30)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大塚仁『刑法概説(各論)〔第3版増補版〕』(2005年)59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各論』(1999年)27頁。例如,未经允许随意带走父母保护之下的幼儿的,如果认为,因为行为人与幼儿一起行动,没有产生场所上的隔离,因而此阶段不该当于遗弃罪,这种结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既然已经让幼儿脱离了父母的保护,在此阶段就应该成立遗弃罪(“移置”)。因此,将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幼儿扔在公园不管而自己离去的行为(“置之不顾”),也许属于使得需要扶助者的保护状态更加恶化的行为,但不属于普通遗弃罪的本质性要素。
在需要扶助者之中,也有并未受到扶助者保护的人(例如,没有亲属的高龄老人)。既然也需要保护这些需要扶助者,避免针对生命的危险,那么,第三者将需要扶助者移转至物理上危险的状态的,这种行为也应构成普通遗弃罪。在这种场合,没有讨论需要扶助者与扶助者之间的场所上的隔离的余地,因而,危险环境的创造本身就构成遗弃。(31)与扶助者之间的场所上的隔离,被定位于危险环境的创造的一种类型。关于这一点,参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99頁。
按照通说(A说、B说)的立场,如前所述,第217条的遗弃限于作为的遗弃,但按照主张区分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的立场(C说),也有承认不作为的遗弃的余地。不过,如果将普通遗弃罪中的“遗弃”概念理解为:(1) 创造需要扶助者与扶助者之间的场所上的隔离的行为;(2) 将需要扶助者置于危险状况之下的行为。那么,其适用范围就极其有限,仅仅限于通过不作为实现这些行为,并且是在(并非保护责任者的)行为人被科处作为义务的场合。例如,行为人误以为存在监护人的承诺,将幼儿带走之后,(虽然已经意识到没有承诺)不将幼儿送还给监护人的行为。(32)山口教授举的例子是,“在行为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小孩钻进汽车,行为人却不将小孩送还给其父母”,参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各論』(1999年)28頁。另外,需要扶助者基于自己的意思脱离扶助者的保护,住到行为人这里的,对于不将需要扶助者送还至扶助者的不作为,这种行为是否成立不作为的遗弃,也可能成为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不能认定由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创造出危险的情形,原本能否肯定存在作为义务,也可能成为理论上的问题。除了这种特殊情况之外,再很难想到其他不作为的(普通)遗弃的情形。
6. 小结
遗弃罪的基本犯罪类型是第218条保护责任者遗弃罪。该罪中的“遗弃”与“不保护”,是根据需要扶助者与保护责任者之间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来区分的。对于“遗弃”类型,可以区分为“移置”与“置之不顾”,但这种区分同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并不存在对应关系(“置之不顾”也几乎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实现的)。“不保护”是真正的不作为犯,通过不伴有场所上的隔离而不保护需要扶助者的不作为来实现。
第217条普通遗弃罪的实行行为是由第三者实施的:(1) 在需要扶助者与扶助者(保护责任者)之间产生场所上的隔离的行为,或者(2) 将需要扶助者移转至危险状况的行为。由于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并不等同于第218条的保护责任,因而,也有以第217条处罚不作为的遗弃的余地,但不作为的遗弃实际上仅限于那些特别例外的情形。
四、 保护责任的含义
(一) 研究状况
按照通说(A说、B说)的观点,由于是将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理解为同一含义,因而,是否存在保护责任,就取决于对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的解释。例如,前述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判例援引日本《道路交通法》中有关救护义务的规定(现在的第72条第1款),判定在驾车过程中致使被害人受伤,达到不能行走的程度的“汽车驾驶者依据法令该当于‘应该保护患者之责任者’”,可以说,这是重视法令上的根据,以此来为保护责任(即作为义务)奠定基础。相反,按照从实质性视角来判断是否存在作为义务的观点,被告人因自己的先行行为创造出针对被害人生命的危险,在此基础上,被告人自己又将被害人扶进汽车,之后驾车离开,这些情况(对结果原因的支配)就能为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即保护责任)提供根据。(33)详细的论述,参见橋爪隆「不作為犯の成立要件について」『法学教室』421号(2015年)89頁以下(该文的翻译参见桥爪隆:《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王昭武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译者注)。因此,对于造成被害人受伤的驾驶者将被害人扔在事故现场而自己逃走的情形(单纯的肇事逃逸),就会形成这样的理解:不产生保护责任(即作为义务)。
相反,按照主张区分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的观点(C说),就会从不同于作为义务的其他视角,来判断是否存在保护责任。不过,既然保护责任是赋予行为人保护需要扶助者之义务的东西,就很难否定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之间具有相互重叠的性质。基于这种前提,一般的做法是,进一步限制作为义务的认定范围,进而承认保护责任。(34)相反,对于不保护罪的处罚,松原教授主张应分别要求存在保护责任、作为义务。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41頁。学界的有力观点主张限定性地理解保护责任,例如,“诸如排他性等那样,存在相当强度的支配关系的场合”、(35)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6頁。“以长期的紧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能够强烈期待其具有保护需要扶助者之动机的情形”、(36)参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43頁。“以亲权者、看护义务人为典型的,对需要扶助者负有持续义务的人”。(37)参见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2016年)81頁。持相同旨趣的观点者,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40頁以下。按照这种有力观点的理解,(虽然可能因论者不同,具体结论也可能不同)对于前述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判例的肇事逃逸案件,就存在这样的倾向:以作为汽车驾驶者的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持续性的保护关系为理由,否定存在保护责任。(38)相反,山口教授则是以“被告人将被害人扶进自己的汽车,由此取得了排他性支配”为理由,肯定行为人处于保护责任者的地位。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7頁。
(二) 若干探讨
正如前面反复阐述的那样,并不存在按照同一含义理解保护责任与作为义务的必然性,因而,保护责任者的地位完全应该作为第218条的解释论的问题独立探讨。因此,基于对于哪一范围之内的主体赋予其对需要扶助者的保护责任更为合适这一问题意识进行探讨,就尤为重要。
按照这种理解,存在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等持续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场合,原则上应该肯定存在保护责任。即便只是同居关系,如果设想的是,(某种程度上)持续维持共同生活的关系,也能肯定保护责任。(39)开始同居关系数天之后,男方将女方带来的小孩(3岁)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不管,对此,有判例肯定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参见東京地判昭和48·3·9判タ298号349頁。并且,对于那些受保护责任者之托而保护需要救助者的人(例如医师、护士、保育员等),在实际持续存在对需要扶助者的保护关系的场合,也能肯定其具有保护责任者的地位。(40)指出这一点者,参见佐伯仁志「遺棄罪」『法学教室』359号(2010年)100頁。
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不存在持续性关系,而只是暂时支配着需要扶助者的情形?如上所见,有观点通过要求存在持续性的保护关系而否定这种情形存在保护责任。的确,“对年老者、年幼者、身体障碍者或者患病者负有保护责任者”这一表述,将日常生活中以持续性保护为必要的人作为客体而予以列举,对此就可以理解为,本罪将犯罪主体规定为,那些日常生活中应该保护这些需要扶助者的人,因此,主张将主体限于同居的亲属、医疗机构的相关职员等处于持续性地保护需要扶助者这一地位者,就属于很自然的理解。(41)有关遗弃罪的立法过程,参见松原和彦「保護責任者遺棄罪における『保護責任』についての一考察⑴」『北大法学論集』57巻3号(2006年)314頁以下。实际上,对于高龄老人、幼儿等,保护责任者负有对饮食、抚养、护理等整个生活予以照管的义务,因而,被赋予这种持续性的、全人格的保护的义务的人,就应该限于同居的亲属等具有持续性的、密切的关系的人。
然而,如果彻底贯彻这种理解,例如,(正如后述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决定的案件那样)对于在宾馆房间注射药物之后陷入神智错乱状态的被害人,虽然停留在同一房间内,但没有让被害人接受必要的抢救生命的治疗,这种不作为也只能是归于不可罚。当然,如果能认定行为人存在未必的杀人故意,也是有可能以不作为的杀人罪(未遂)来处罚的。然而,是否存在未必的杀人故意,其认定非常微妙,但如果不能认定存在杀人的故意,被告人的不保护行为就直接归于不可罚,作为对受伤者的生命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在这种场合,即便不能认定存在杀人的故意,难道不能另外认定成立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吗?
尽管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在本文看来,对于是否存在保护责任,就有根据针对需要扶助者的生命的危险性的程度,进行相对性判断的余地。亦即,根据针对需要扶助者的生命的危险性的程度,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1) 存在针对生命的紧迫的危险,应该立即采取抢救生命的措施的情形(如果存在故意,可以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未遂的情形);(2) 止于存在针对生命的抽象的危险的情形。那么,对于后一种情形,可以要求存在持续性的保护关系,但对于前一种情形,即便是暂时性关系,如果存在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奠定基础的情况,也肯定存在保护责任。按照这种理解,对于前述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判例,以及后述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决定的案件,也能认定存在保护责任。在存在针对生命的紧迫的危险的场合,扩大负有避免义务的人的范围,从保护生命的角度来看,尽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可能被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投机取巧。为此,笔者以后还会就此进一步研究。
五、 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的相关问题
(一) 对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决定的探讨
第219条处罚的是,犯普通遗弃罪或者保护责任者遗弃罪,因而致人死伤的结果加重犯。对于遗弃、不保护与死伤结果之间的关系,按照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以存在危险的现实化这种关系为必要。(42)桥爪隆教授就因果关系的详细研究,参见桥爪隆:《刑法总论之困惑(一)》,王昭武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译者注
对于因“移置”行为而引起被害人死伤的情形,很多时候,“移置”行为与死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因而解释论上不会出现特别的问题。例如,第三者未经同意擅自将受到父母保护的幼儿带至危险的地方,结果幼儿受伤的,由于可以说,由作为的“移置”而产生的危险已经被实现于伤害结果,因而应成立遗弃致伤罪。相反,对于“置之不顾”、不保护成为死伤结果之原因的情形,围绕故意、因果关系的判断等问题,就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那些理论上的问题点,下面想以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决定的案件为中心进行探讨。
本案被告人在案发当日的晚上11时左右,将被害女性带至宾馆客房,在当晚11时10分左右,给该女注射了兴奋剂,不久,该女便出现头痛、胸闷、想吐等症状,其身体情况也逐渐恶化,至次日早上零时30分左右,该女出现脱掉衣服、试图跳出窗外等举动,陷入因兴奋剂引起的神智错乱状态,在早上1时40分左右,该女停止了剧烈的身体动作,面部朝下趴在地上,紧闭双眼,发出呻吟声,非常痛苦。被告人因为害怕自己吸食兴奋剂的事实被发现,对该女放任不管,在早上2时15分左右离开了宾馆,该女于早上4点左右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最高裁判所认为,“在被害女性因被告人注射的兴奋剂而陷入神智错乱状态的早上零时30分左右,如果被告人马上要求急救医疗,从该女年纪尚轻(当时13岁)、生命力旺盛、没有特别的疾病等情况来看,可以说该女十有八九是能够得救的。这样的话,能认定该女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能够切实得救,因此,被告人不采取这种措施而是漫不经心地将该女扔在宾馆客房不管的行为,与自早上2时15分左右至早上4时左右这一期间,该女在该房间因兴奋剂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这一结果之间,认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妥当的”,最终判定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43)最決平成元·12·15刑集43巻13号879頁。
1. “不保护”的实行行为与故意
本案作为就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的最高裁判所判例,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其前提,首先有必要确认,被告人的行为符合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构成要件。本案被告人通过对被害女性注射兴奋剂而创造出针对生命的危险,并且,由于发生在宾馆客房之内,其他人难以介入,因而,能认定存在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因此,按照将作为义务与保护责任理解为同一意思的观点,当然能认定存在保护责任。(44)关于这一点,参见原田國男「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元年度)394頁注20。另外,对于被害人自己吸食了兴奋剂的情形,能否认定存在保护责任,就属于非常微妙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参见松藤和博「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における保護義務」池田修=金山薫編『新実例刑法〔各論〕』(2011年)405頁以下。在这种情形下,既然缺乏由先行行为创造出危险,那么,只要不能认定存在可以替代这一点的其他情况,就难以肯定保护责任。按照本文的立场,既然正在发生针对被害女性生命的紧迫危险,就能认定存在保护责任。
不过,从哪一阶段开始能认定“不保护”的实行行为,还有探讨的必要。亦即,在被注射了兴奋剂的被害人出现头痛、胸闷的症状的阶段,事态尚未紧迫到必须马上要求急救医疗的程度。因此,在该时点,即便被告人对被害人置之不顾,既然针对被害人生命的危险尚未显现,此阶段就难以评价为“对其生存不给予必要保护的”行为。这里还存在有关故意的问题。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也是故意犯罪,因而就要求被告人自己处于应该保护被害人的地位,并且,对于怠于“生存所必要的保护”存在认识。因此,如果被告人没有正确认识到被害人的状态,而是认为,过一会被害人会自己康复,就难以认定存在不保护罪的故意。
这样,如果试图谨慎地认定实行行为与故意,就会要求将实行行为的认定延迟至被害人的状态严重恶化的程度。不过,过于推迟实行行为的时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该阶段已经过迟,不能认定存在死亡结果的避免可能性。出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这种问题意识,毋宁说,反而会要求提前实行行为的时点。(45)关于这一点,参见町野朔「判批」『警察研究』62巻9号(1991年)24頁,十河太朗「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法律時報』85巻1号(2013年)38頁。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决定正是试图调和二者,将早上零时30分左右被害人已经陷入神志错乱状态的阶段的不保护认定为实行行为。
2. 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
本决定是因为“该女十有八九是能够得救的”而肯定置之不顾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正如反复强调的那样,“十有八九”不是如同其字面含义那样是指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不过是“切实性达到了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的惯用表述。(46)关于这一点,参见原田國男「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元年度)385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3版〕』(2016年)80頁。作为实体法上的要件,最终要求的是,“是能够得救的”这一事实,作为证明程度,要求达到“切实性达到了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
在本决定中,重要的是,研究的问题是“得救”的可能性,而不是“延续生命”的可能性。这里要求的是,如果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不是单纯地死期被延后这一事实,而是脱离兴奋剂中毒的危机,是“被救活了”。当然,也仅仅是本案认定存在“得救”的可能性,也完全有可能这样理解:即便是“延续生命”的可能性,也有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余地。(47)关于这一点,参见原田國男「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元年度)386頁以下。但是,如果认为,即便是得以延续几天的生命,也能认定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只要不是完全的错过抢救时机,如果尽力实施紧急治疗,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都能够延续一定时间的生命,因而,就会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认定不作为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此一来,对于因果关系,本决定严格要求达到“切实性达到了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这种程度的证明的旨趣,就会被湮没,因而这种做法并不妥当。(48)指出这一点者,参见町野朔「判批」『警察研究』62巻9号(1991年)25頁。因此,在本文看来,对于不作为犯,最终还是应该研究与“得救”之间的因果关系。(49)当然,要严格区分“得救”与“延续生命”是很难做到的,但根据被害人现在能否脱离正在面对的针对生命的危机,大致还是有可能区别二者的。另外,对于医师对因违法堕胎而出生的早产儿置之不管的案件,最高裁判所昭和63年(1988年)决定判定医师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最決昭和63·1·19刑集42巻1号1頁)。在该案中,如果被告人采取保育措施,尽管能够切实延续早产儿的生命,但尚未达到能够切实得救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参见原田國男「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3年度)4頁以下)。如果在本案中不能认定存在切实得救的可能性,按照本文的立场,尽管没有采取保育措施该当于保护责任者不保护罪,但不能认定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山口教授则认为,“只要能够认定短时间内不会死亡即可”,参见山口厚『基本判例に学ぶ刑法各論』(2011年)8頁以下。
的确,作为因果关系的一般论而言,不得不承认,提前死期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死期已经迫近的患者,提前其死期的行为,也属于杀人行为)。这样,不是以“延续生命”而是以“得救”作为问题,就不属于因果关系的一般问题,而应该属于不作为犯特有的问题。本文认为,也有这样理解的余地:在不作为犯中,由于有必要赋予行为人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因而,不仅仅是为了多少延迟一点死期,而是限于以“得救”为目的的场合,对行为人科处一定法律义务,才能够被正当化。
另外,本决定将本案的实行行为表述为,“被告人不采取这种措施而是漫不经心地将该女扔在宾馆客房不管的行为”,这究竟属于“置之不顾”还是属于不保护,判例态度未必明确。勉强从形式上把握的话,在早上2时15分左右之前,没有发生场所上的隔离(不保护),此后,因被告人离去而产生了场所上的隔离(“置之不顾”)。不过,被害人是因为被告人没有要求急救治疗而死亡,而非因为被告人创造了场所上的隔离而死亡。这样考虑的话,被告人死亡的原因就在于被告人的不保护,因此,(严格表述的话)本案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成立保护责任者不保护致死罪。(50)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基本判例に学ぶ刑法総論』(2010年)24頁。如果将正文的这种理解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置之不管,结果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不管是否存在场所上的隔离,原则上也应该是成立保护责任者不保护致死罪,几乎没有成立以“置之不顾”(遗弃)为原因的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的余地。
(二)与不作为的杀人罪的区别
在有关“瞎鼓捣”(51)所谓“瞎鼓捣”,这是音译,是被告人给自己的所谓医术的命名,并无实际意义。该案大致案情为:乙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受乙的亲属丙等人所托,甲答应给乙实施所谓民间疗法“瞎鼓捣”治疗,并叫丙等人让乙出院住进宾馆,但其后并未采取必要医疗措施而是置之不管,乙最终死亡。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因可以归于自己之责的事由而给患者的生命造成了具体的危险,亦即,在患者(乙)被转移至宾馆期间,患者亲属丙等人因信奉甲而将乙的治疗完全交给了甲,因而可认定甲处于全面受托治疗重病患者乙的地位”,进而判定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最决平成17·7·4刑集59卷6号403頁(“瞎鼓捣”治疗案)]。本判决认定存在作为义务的根据在于,存在应归责于甲的先行行为、对患者乙具有排他性支配。——译者注案件的判例中,(52)最决平成17·7·4刑集59卷6号403頁。对于受患者家属之托,不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而是实施所谓“瞎鼓捣”疗法的被告人,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但同时判定,“与不存在杀人犯意的患者亲属之间,在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的限度内成立共同正犯”。(53)另外,在患者家属相信患者会因为被告人的“瞎鼓捣”治疗而恢复健康的场合,原本能否认定存在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的故意,也可能成为问题。但是,即便期待被害人会因“瞎鼓捣”治疗而得以恢复健康,(即便是未必的认识)如果亲属认识到,将被害人带出医院,不让其接受必要的医疗治疗,这种行为伴有的一定的风险,对于患者的亲属也能认定存在该罪的故意(对恢复健康的期待与对风险的认识,是完全有可能两立的心理状态)。
学界的有力观点主张,应该根据作为义务的程度来区分两罪。(54)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小暮得雄ほか編『刑法講義各論』(1988年)65頁[町野朔]、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38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39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46頁。的确,作为义务可以为不作为具有与作为在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奠定基础,因此,杀人罪的作为义务是为了避免发生死亡结果的具体的危险,而遗弃罪的作为义务是为了避免更为抽象的危险,以此来区分两罪,也并非不可能。例如,父母将小学低年级的小孩一个人留在家中,自己出去旅行数日,(当然也与小孩自身的能力有关)这种行为虽然抽象地内含着针对小孩生命的危险,但可以说,不属于具有发生死亡结果之紧迫危险的行为。因此,即便父母已经未必地预见到小孩的死亡,也不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未遂,而且,小孩因意外事故而死亡的,也不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止于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
不过,上述案件中,之所以不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是因为没有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具体的危险。如果处于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性很大的状况之下,当然也能认定存在杀人罪的作为义务,就难以区别于遗弃罪的作为义务。这样考虑的话,与主张杀人罪与遗弃罪的作为义务不同相比,主张区别在于,为认定作为义务而必要的危险程度不同,要更为正确。(55)持这种理解者,参见齊藤彰子「遺棄罪」『法学教室』286号(2004年)54頁。亦即,(1) 在针对生命的危险性并不紧迫的状况下,由于不能认定存在杀人罪的实行的着手,因而完全是是否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问题;(2) 在针对生命的危险性很大的状况下,对于不作为,能同时认定具有两罪的实行行为性,因而就需要根据故意的内容来区分两罪。(56)持这种理解者,参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36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102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43頁、十河太朗「不作為による殺人罪と保護責任者遺棄罪の限界」『同志社法学』57巻6号(2006年)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