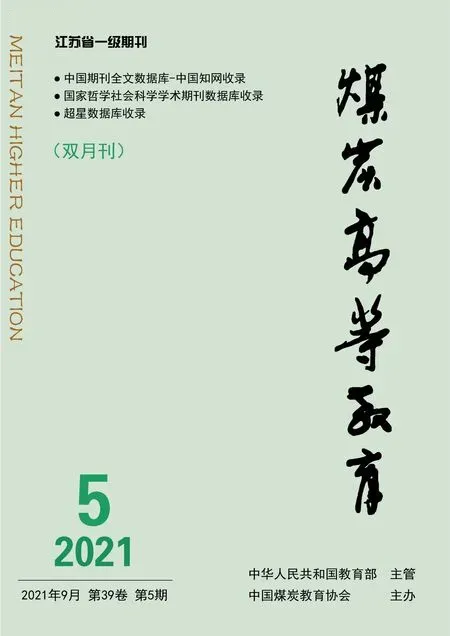在权力和知识之间: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萌芽与制度化发展
张 侃
历史是重要的。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会是在真空之中,而是产生于众多已有制度之中;任何新产生的制度也都不会是全新的,而必然会带有旧有制度的痕迹。中国近现代意义上大学制度的建立,是借鉴移植西方以中世纪大学为起源的大学制度。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也源远流长,虽说没有发展出类似欧洲中世纪大学这样的大学组织形式,可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而历史上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文化无疑也必然会浸入到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中去。中国近代建立的大学制度之中既包含了西方大学制度所具有的理念、精神,也包含了中国自身具有的传统文化和古代高等教育理念、制度影响,并且在大学制度内部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冲突和张力。因此,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从建立之初就是复杂、独特的,是中国古代大学制度和西方大学制度综合作用的产物。要想深入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特质与复杂成因,首先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大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只有先了解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萌芽和制度化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形成的中国传统大学制度的独特气质,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借鉴、学习了西方大学理念和制度之后形成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的独特性之所在。
本文拟先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来大致梳理一下中国大学教育萌芽、发展和制度化的历史,从中归纳出一些中国大学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特点,然后再专门重点论述三个本文认为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制度,即官学中的汉代太学制度、私学中的书院制度和对中国整个古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科举制度。本文以期通过这种纵横结合的深入分析来总结归纳出从中国本土文化中萌芽、生发的大学制度的核心理念、制度特性和精神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理念、制度、精神才是中国大学之根,而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绵延至今,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仍产生着潜移默化而又巨大的影响。
一、权力和知识之间: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萌芽与制度化发展概述
中国的大学教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这时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都是官办的,教育机构与政治行政机构相结合,教育主要是为政治权力服务,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和武士。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教育、军事教育、礼乐教育。到了商代以后书数教育也是基本的内容,大学教育也都是官府举办的,是官学[1]。这一状况延续到西周,就是著名的“学在官府”。官府有学而民间无学术,形成了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官有器而民无器、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现象。西周时候主要的大学教育机构是辟雍,《礼记》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时期的教师还未形成专门单独的职业,都是由政府职官来兼任的,是“官师合一”。
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期被打破。这首先是因为官学的衰败导致的,官吏世袭制度造成贵族不重教育,有贵族甚至宣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2]9。王权的衰落导致了官学的荒废,周天子名存实亡,群雄逐鹿,统一的教育制度更是难以为继。战争的动乱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部都是征战连连,硝烟四起。官守的学术再也守不住了,没落贵族、文化职官流落民间,从而促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出现。私学兴起,引发了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纵横等各家都开始开办私学,聚徒讲学,其中以儒家和墨家的规模较大。春秋时期私学取代了官学,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变革。至此,私学才算是打破了官府办学的垄断而成为了大学教育的举办者。从体制上讲,官学是政教合一的,教育只是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教育无独立的组织机构,无专门的教职,甚至连学生也都只能是贵族;而私学则是政教分设的,教育第一次从政治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有了其独立的组织机构,教育活动也与权力活动相分离,教师成为独立的职业,成为专业化的脑力劳动者。私学的兴起开创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术繁荣和百家争鸣。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的起点决定了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日后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中国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权力和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知识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所以政治(行政)属性而不是学术性,成为了中国大学制度的第一属性,这种制度开创之初就具有的特性产生的影响绵延几千年直到今日也没有消失[3]。
私学的兴起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和知识的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却是因为中央政权的衰弱,官学的“失守”导致的。如果我们纵观历史,还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比如民国战乱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大学的兴盛,这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而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发展和繁荣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例”。稷下学宫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所官家举办私家主持性质的大学教育机构。它创办于齐桓公时期,是“政府”举办,但是其内部运作却完全是由私人,像荀况这样有独立学者身份的学者来负责的。其次,它是一所容纳百家、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机构,曾先后存在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农家等等各个学派的学者,并且允许各家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是同时期执著于一门一派的其它私学所无法做到的。第三,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教育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议作用的高等学府。学宫内部包容百家,讲究“学术自由”,各学派之间地位平等,讲究以理服人,共同为齐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顾问。这些学术活动和类似政治“智库”的功能已经近似于现代大学的活动和功能,不仅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就算是在同时期的西方高等教育领域也是没有的。稷下学宫达到了中国古代大学发展的一个顶峰。不过这种先进的教育和知识文化发展模式似乎并不适合中国的制度、文化、政治环境。战国时期,齐国采取了尊重贤士、尊重学术、大力发展学术文化教育的政策最后却败于采取文化挟制、思想专制的秦国,这其中的意味也值得我们深思。
秦朝是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倒退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秦始皇采取了加强思想控制,烧诗书、坑儒生、禁私学、以吏为师等一系列举措,其对文化的压制和摧残是巨大的,也间接地导致了其快速灭亡。私学到汉朝的时候才得以重新恢复建立。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朝的焚书坑儒,再到汉朝开始的“独尊儒术”,知识的发展在汉朝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即开启了此后千年直到现在的儒家成为中国知识的正宗和文化主流的状况。汉代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在董仲舒的倡导下,开始树立儒学的唯一权威地位。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举措,董仲舒借助政治力量建立了太学来进行宣传教育,将儒家的五经作为唯一的教材[4]。汉朝私学也较为兴盛,主要从事大学教育教学的私学叫经馆,主要是由著名学者进行聚徒讲学,宣讲的内容也主要是儒家经典。魏晋南北朝时基本是承袭汉制。
隋唐时期最大的制度变革就是科举制的兴起,宏观上讲隋唐时期的整体特点是崇儒兴学、兼用佛道、发展科举、鼓励私学。从知识发展上讲,在儒学的一元独尊之下,佛道之学渐盛,对儒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学校教育开始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在唐代,一种新形式的私学——书院,也萌芽产生了。宋朝的大学教育制度基本沿袭唐制。在知识发展上,宋朝产生了新儒学——理学,将道家和佛学与儒学相融会贯通,而这又成为了宋明时期书院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更加重视科举,加强了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在科举考试中将八股文固定为考试文体,禁锢了士人思想,对学风、文风和大学教育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大学也进一步的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清朝沿袭明制,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更加窄化实际上成为了八股文的考试,科举又舞弊丛生,积重难返。可以说清朝的大学教育已经名存实亡,除了应对考试,再无其它教学活动。中国的传统大学制度和科举制一起,走向了末路。与此同时,国门已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已经蓄势待发。
回看中国古代大学制度发展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两条一以贯之的线索:一条是明线,占据了主导作用,那就是政治权力对大学制度变革的影响;还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那就是知识的发展对大学制度和大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基本是一种辅助性的依附于权力的推动。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萌芽与制度化发展都是摇摆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知识和学术的发展占据了较为主要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发展的时期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战国时期了。虽说这个时候的政治力量仍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大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政治权力服务的,但是相对来说地位更加平等一些,知识发展和教学活动的空间更大一些。这自然也就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兴盛的局面,最终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文化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和文化的主体。但是大一统的权力格局中,缺少适宜知识百家争鸣存在的制度环境,春秋战国的知识大发展到了秦朝一下子跌到谷底。到了汉朝,虽说没有秦朝那样极端的控制,但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开始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的知识格局自然带来了新的大学制度,太学的建立就是对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知识发展模式的否定与颠覆。隋唐时期开始兴起的科举制,让儒学一支独尊的地位更进一步加强。当然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历史上其曾受到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最后出现了儒道互补;一次是隋唐佛学对儒学的冲击,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5]。但这些冲击无非是不同的知识流派在统治者面前争夺主流地位的争斗,其最终的融合,也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统治者,比如宋明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与封建宗法相结合,成为了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以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一元化导致了知识发展的窄化和一元化,而知识的窄化和一元化必然会对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科举制实行之后,无论官学和私学都渐渐成为取士制度的附庸,学者和学生都是为了科举、为了考试、为了做官,谋求个人在政治上的发展,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的发展也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末路。
二、权力需要推动下的知识体系变革:汉代太学的建立
汉代太学的建立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是从制度上标志着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大学或者说高等学校不再与政府行政机构混同在一起,在形式上具有了独立性。另一方面就是太学的建立是汉朝“独尊儒术”的制度化体现。太学是“独尊儒术”的产物,其实质就是儒学式的太学。这也是我们要在这里专门分析太学制度的原因之所在。太学的建立,背后实际上就是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当历史上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知识大发展大争鸣和秦朝的大压制大反动之后,汉代的统治者认识到对知识的过于宽容和过于严苛都会危及自身的统治,而找寻一种合适的知识学术体系作为国之根本,然后推行一元化的知识文化发展政策是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而在百家之中,儒学能够成为担当这一大任的学术流派则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儒学自身特点和自我改造的结果。汉初,除了儒学,道家的黄老之学由于符合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需要也一时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但是随着西汉分封制带来的诸侯割据成为威胁国家政权的主要因素的时候,黄老之学却由于自身所限无法提出解决的办法,而儒学的作用却得以发挥,因此逐渐成为了汉代最为强势的显学。汉代幅员辽阔,政权统一稳定,亟需保证皇帝的权威性,让各地都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行动,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能够被广为接受的统一的治国准则和行为规范,以使各级官员和百姓能够安分守己,各安天命。儒学于是就执行了其的职能,发挥出了这种作用。这很类似于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良好、统一并被民众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能够极大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降低统治成本[6]。于是儒学在国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就成为了社会主流的知识范式和价值体系。一种知识体系取代原有的知识体系,关键就在于建立知识替代的制度化场所,以培养信徒,保证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于是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太学建立了。太学的建立可以看成是对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知识制度的颠覆;太学的建立让独尊儒术的政治政策制度化为具有操作性的知识选择制度和知识分配制度。
太学的建立虽说从制度形式上使大学教育制度与权力机构相脱离了,但是其实质上仍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成为了培养儒生、弘扬儒学,巩固儒学独尊地位以维护权力统治的工具。这从太学的制度设计和运作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太学正式建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太学建立后,规模不断扩大,到东汉时期盛极一时[7]。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单一的儒家经典,两汉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有14 家,都是今文经学①。太学学生的出路主要是通过毕业考试,然后依据考试成绩的等级来作为授予官职的依据。参加太学考试而入仕成为当时读书人特别是普通百姓出身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唯一稳妥可行的途径。太学以儒学经典为唯一教学内容,通过太学考试作为主要的选拔官吏的途径,这让儒学迅速成为社会主流的知识形态,形成了独尊的地位。同时,知识分子也逐渐丧失了独立的治学旨趣,只是为了做官而读书。这种体制和稷下学宫实行的“不治而议论”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太学虽说形态上与权力机构相分离,但是在内部联系和实质上却更加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太学的建立和发展也说明了中国的制度环境难以产生类似中世纪大学那样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太学本质上也就是官吏的养成所和现行政治权力制度合法性的辩护人。太学产生的原因根本上也是因为权力统治的需要而推动的“独尊儒术”的知识变革,需要一个制度化场所来实现这样一种一元化的新的知识体系替代先秦产生的多元化的百家争鸣的知识体系。太学无疑为推动儒学的独尊地位颠覆百家并存的知识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儒学知识内部的争议也从没有中断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辩。虽说迎合权力统治需要的今文经学一直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古文经学的发展也始终未断并在私学中的传播有蓬勃之势,这也可以看成是知识发展自身逻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之后,一元化的知识发展被日益加强,知识与权力的捆绑更加紧密,无论官学和私学都成为了取仕制度的附庸,知识发展逻辑那本就微弱的力量,也被强势的政治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体制给渐渐消解掉了。
三、权力的理想与知识的现实:科举制度的兴衰
科举制度始建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再经宋、元、明三朝而定型,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共历时1300 余年[2]152。其实科举制度并不能算是教育制度,更不能将其和古代大学制度相等同,但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大学教育、大学制度紧密相联,对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支配性的作用,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大学制度变迁的时候不可能绕过科举制度。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选官制度,从历史沿革上看,从西周的乡举里选制度、汉代的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再到隋初的察举制度,政治选官制度的目的就是选贤任能,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出任官吏,以更好地维护政权统治。隋朝的科举制就是由察举制度演化而来的,在吸取历史上察举选官制度的经验,经过进一步的改良,终于形成了科举考试制度,中国考试选拔制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考试选官制度之所以一再变迁,从根本上讲也是因为统治者希望通过更加公正、公平的制度来选出真贤选出能吏以更好地管理国家、延续统治,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却往往带来一系列的意外后果。以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为例,以九品中正制取代察举制,就是为了纠正汉代考试中存在的“重文轻行”和察举中的朋党积习,其在实行之初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可是随着实行日久,弊端日显,造成了西晋最大的积弊“门阀政治”的盛行,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科举制的出现,自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追求公平公正和更好地维护统治的理想而建立的。到唐朝,科举逐步发展兴盛,日渐成为古代社会读书之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宋朝的科举在沿袭唐制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展,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常科为常设常规科目;制度科为非常设科目,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设置主持的特殊考试。此外还有文科、武科之分,成人科和童子科之分[8]。宋朝科举还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名额;确定了三年一贡举的制度,从此三年一科举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殿试成为定制;另外为了增加公平公正性,还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以防止科场舞弊,比如锁院制、别头试、誊录制、糊名法等等[2]156。可以说科举制度在宋朝制度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元朝科举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规定考题要从《四书》中出题,要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答题标准,这进一步窄化了考察知识的范围同时也僵化了考试士人的思想,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到了明朝,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朝科举制度在继承前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称为“永制”的科举定式,即确定每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科举考试递次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将八股文作为固定的考试问题;将学校教育纳入到了科举体系之中[9]50-56。明朝的这些制度革新,利弊兼半,比如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一方面将考试内容更加标准化,也彰显了推动公平公正的政治理想,可是另一方面,它也禁锢了士人的思想,败坏了士风学风,对知识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而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从制度上进一步绑定在了一起,虽说有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但是也让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大学的学习不再是知识的学习和探求,而日益被异化为一种考前培训了。清朝科举制度进一步成为国家人才选拔的根本制度,科举制度更加严密,但同时科场舞弊丛生,学校进一步成为科举附庸,不仅科举制度日益走向末路,清朝的大学教育也已经名存实亡。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相对于之前的考试选拔制度更加公平公正了,也在对立僵化的社会阶级之间构筑了一条流动的通道,对于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十分积极地意义的。但科举制的消极影响也随着其的发展而日益明显,具体说来主要有几点:一是进一步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正统知识体系的地位,同时彻底颠覆了春秋战国开创的多元化知识发展、百家争鸣的知识发展格局,将政治权力因素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实科教育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受到极大压制,使其只能在“实用”和技术化的范畴内进行,也让中国逐步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其它国家。二是科举制逐渐成为选拔人才和政府取士的主要途径之后,政府逐渐以功利的观点来看待科举和学校的关系,越来越重视科举的政治作用,而对学校教育的建设和发展逐渐冷落。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清末中国大学教育的名存实亡。
四、权力与知识的博弈:书院制度的盛衰循环
如果说官学由于其官办的性质和与政府联系的紧密而导致其的政治依附性是绝对的,知识的探求与发展往往被压制与忽略的话,那私学的发展,则往往能够更加遵循知识发展的逻辑和蕴含探索知识的好奇与动力。而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学制度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其私学的性质,以学者为办学主体的模式,以及对知识的热情探索,更加平等、民主的教学活动,使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五代,繁荣和完善于宋代,延绵存在一直到清末,延续了一千多年,其中几度盛衰循环。书院与官学的发展此消彼长,官学兴则书院衰,官学衰则书院兴。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学教育逐渐沦为备考应试之地,教学的教育意义丧失,对知识的探求被忽视,书院则成为了对抗官学进行真正知识教学和知识探索的地方。
最初,书院是由私人读书藏书的场所演化为讲学授徒的场所而产生的。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和普通私学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既有藏书又有教学活动,不同于以前以单科学习为主的私学,而形成了知识面较广的新型教学体系和模式。书院产生于唐代,最大的动因还在于官学的衰落,士人失学。唐自安史之乱之后,由盛转衰,藩镇割据,中央政府被严重削弱,战乱不断,官学日趋衰落。于是一些好学之士和有名的学者便各自找寻安静之地建屋藏书,读书求学,同时开始聚徒讲学。这也是和我国长久以来的私人讲学传统的影响有关,中国历史上向来是官学衰则私学兴,循环往复。另外,书院最初的创立也受到了佛教发展的影响,佛教特别是兴盛于唐朝的禅宗一派的修行方法和讲经说法的形式也都对书院的教学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9]73-74。及至宋朝,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逐步完善并兴盛起来。书院大盛于宋朝以及其中的几次盛衰轮转,有知识发展和权力变革两方面的原因。
从知识方面来说,隋唐以后儒学知识开始出现危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内部,科举制的发展对儒学知识产生了异化。儒家知识体系中的某些内容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被行政系统支持成为垄断性具有霸权的知识,它成为了考试的内容、升迁的依据,与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旨趣。这种霸权的知识往往趋向于教条化,与其所在的知识体系相割裂,简化为只是为了应试的一种供认复述与背诵的内容;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考试,成为士人求取功名的工具,而不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学只是成为了备考复习的培训场所,真正的学术被逐出了大学。二是在外部,佛学和道家学说的兴盛,也对独尊的儒学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亟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范式来调和这种冲击,融合不同的知识,以从根本上稳固儒学的地位。于是一种新的儒学应运而生,这就是理学。建立新儒学的最初目的,本意在于中兴儒学,抵制佛道,但是新儒学所讨论的问题,如心性和宇宙论,都是先儒所不谈的,无形中反而蹈袭了佛道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特别是以佛家的禅宗理论对理学的影响最大[10]。由此,中国知识和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三教融合的文化体系开始形成并发展。知识的发展必然会催生新的知识机构的产生,正如百家争鸣、多元化的知识发展催生了稷下学官,独尊儒术的知识发展催生了太学,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引发了书院的繁荣与兴盛。很多理学大家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都积极地在各个书院讲学,同时自己也举办书院。比如周敦颐创办了濂溪书堂,程颐创办了伊川书院等等。周敦颐在其创办的濂溪书堂中讲学,使书院与理学初步结合,也标志着书院制度开始走向成熟。
从权力变革方面说,书院的兴衰还直接取决于官学的发展。比如宋朝初期书院的兴盛,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急功近利,重科举而轻学校,忽视对学校的扶持和人才的教育,以致在立国之后的80 多年间官学一直处于衰败的境地。这就给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使其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民间教育组织,产生了著名的白鹿洞、嵩阳、岳麓和睢阳四大书院。可是之后伴随着北宋的三次政府主导的兴学运动,即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元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和州县官学的日益普及,书院制度很快走向了衰落。北宋的这三次兴学,并在太学推行三舍法改革,都极大地提升了官学的教育教学功能和影响力,也使一批名师硕儒逐渐从隐居收徒讲学转而逐渐进入官学,广大士子也纷纷进入更有利于进入仕途的官学进行学习,官学又兴盛起来,自然书院教育也就被冷落了。之后书院的每一次兴衰也都是与官学的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
从宋朝开始,书院官学化的倾向开始出现。书院的官学化到了元朝被进一步加强,元朝统治者出于邀买汉人士人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出发,推进“汉化”的文教方针,积极倡导兴办书院,但是出于同样的稳固权力的目的,开始进一步加强对书院的实质控制。所以元朝的书院发展,从表面看是一派生机勃勃之势,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可是从本质看,书院官学化倾向日益严重,很多书院完全被纳入官学系统,成为了科举的附庸,书院的精神已经渐渐丧失。明朝初期,由于官学的兴盛和科举必由学校的规定,让更多人趋向官学,书院受到冷落。政府对书院的态度基本是不支持不提倡,但也没有禁止。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正德、嘉靖年间,书院才又开始兴盛起来。这主要也是因为明朝政权内部矛盾激化,宦官专权导致被排挤的士大夫开始设立书院兴学,另外科举腐败,官学衰落和一些知名学者如王守仁、湛若水的倡导也是其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权力的内斗,让一些被压制的官员和士人开始以书院作为宣讲政治抱负、议论时政、影响朝局的场所。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定期讲会制度,主要讲授四书,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同时东林书院还密切关注政治,将讲学活动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东林书院的独特使其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和政治活动中心,这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是比较特殊的,东林书院也因此名震天下。不过明朝书院的兴盛还是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和官学的动荡,书院官学化的进程亦没有停止,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日益密切。白鹿洞书院在万历末年首行洞学科举,开书院考课制度之先河,此后不少书院也开始实行考课制度,书院的官化进一步发展。清朝初期积极创办官学,同时严禁创设书院。及至雍正年间,政府开始积极提倡书院的发展,但同时也更加强了对其的控制。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是清朝后期书院发展的基本特点。所以到清末书院改制之前,大部分书院已经完全官学化了。
总之,书院之兴,根本在于新儒学的产生、发展的推动,同时又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压制而与官学的兴衰呈此消彼长之势,但最终也还是被逐渐官学化了。这也正说明了,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主要受到了两股力量的推动,即政治权力和知识。其中,政治权力是决定性的,但知识的发展也在顽强地展现出自身发展的力量和逻辑。
五、小结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大学制度产生与发展历史的一个简要梳理,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大学精神、大学组织、大学制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从宏观上说,知识的发展和权力的变革是推动大学产生和发展最主要的两大力量。中国古代大学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权力的绝对主导性和知识的相对依附性。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从中国大学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最初的大学教育机构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之后才逐渐分离出来,分离之后也始终受到了政府权力的强力控制。私学的兴起也只能是在政府权力受到削弱或者官学衰落、不被重视的时候。政治权力从一开始就主宰了中国大学的发展和大学制度建立,这种精神也就植根于中国古代大学的灵魂之中,绵延几千年影响至今。
知识的相对依附性,也是因为中国知识发展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知识的发展,重用而轻体,在实践发展之中也是重技术轻理论,重人文轻自然,从而使得中国的知识发展一方面是“偏科”的,对实科不重视对自然科学不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只重实用,特别是注重对治国理政、维护政治统治方面之“用”而轻视对自然、对客观外部世界的探索[11]。这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发展自身的力量相对于政治权力始终是弱小的,主流知识的发展都是人文、伦理方面的,所以都是需要获得权力的认同、被树立为统治阶级的主流理论才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发展自身的“依附性”。学者的思想,其所开创的理论都是修身、治国的,所以是需要向统治者贩售的,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一个典型的贩售自己知识和理论的例子。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也人为地挟制了中国知识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也就切断了中国知识发展的多样化可能。科举制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所有读书人的旨趣,读书不再是为了探求未知、不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被逐渐矮化成为了攀附权力、进入官场做官的敲门砖。大学则也不再是学习和探求知识的场所,而变成了考试培训班、补习班。当知识、教育都成为了权力的附庸,成为了入仕的敲门砖,而与科举制紧紧捆绑在了一起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大学制度的发展,也就只有慢慢衰亡的结局了。这其中,虽说也有私学的勃兴,也有书院的繁盛,但是,一旦官学强大,政治权力开始强势干预,私学、书院马上也就会走向衰败。中国古代社会的强集权化,让中国古代大学深深地被权力所禁锢,没有学术自由的基因;知识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像西方17、18世纪那样确立了自身独立价值和社会需要的知识革命,其主体一直只是需要得到权力认可的人文、伦理形态的知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大学难以有可遵循的知识发展的逻辑,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权力的认可与支持。这些因素共同形塑了中国古代的大学制度,决定了古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而这些因素已经深深地融入在了中国文化之中,外显化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大学制度的变革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为孔子本人所作,治学倾向于依据政治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意志;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学术上重视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倾向于研究《六经》本意,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3.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