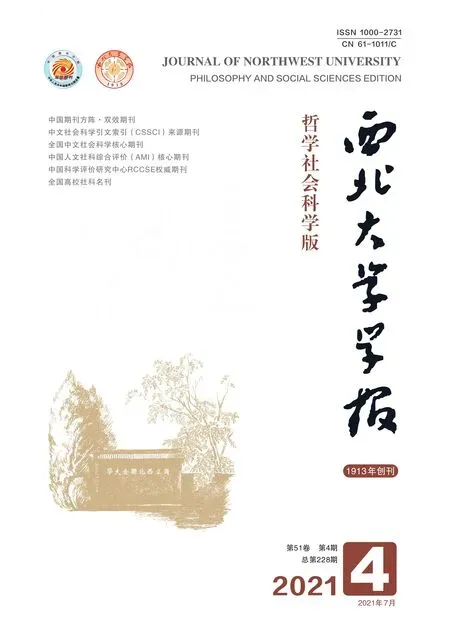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
刘尊举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明清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是近二十年来一个颇受关注但也十分棘手的问题。相关研究成绩显著,但也还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大都侧重于外部研究或观念研究,或是探讨科举制度与八股文写作对明清文人创作心态、思维模式以及整体的文化生态的影响,或是论述明清文人关于古文与八股文关系的讨论、认知以及相应的创作主张,而基于文本分析的文章学或文体学的内部研究明显不足;二是关于“以古文为时文”的研究比较深入,而“以时文为古文”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且同样是以外部研究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为主。诚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有时候外围史料的阐释效力并不比文本自身弱,从科举制度、士人心态、理论批评等角度探讨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当然是必要而且是十分有效的;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对比更不应该被忽略,否则就很难把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实际情形讲清楚。如果能够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辨析两种文体的功能、体制、语体、风格等诸多层面的异同,并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判断其关联与意义,庶几可以将此问题推进一步。唐顺之在古文和八股文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自然是个案研究首先要考虑的研究对象。他与归有光被视为正德、嘉靖时期“以古文为时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而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其研究现状一如整体格局,以外部研究、观念研究为主,落实到文本与文体自身的研究不足;“以古文为时文”探讨深入,“以时文为古文”则较少涉及(1)众多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散文史的通史或断代史或多或少地论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一些流派或作家研究也会涉及相关问题,选本与评点研究往往对古文评点与八股文的关系多有关注,八股文文体研究通常会讨论“以古文为时文”的问题。还有一些专著或论文以古文与时文关系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如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孔庆茂《八股文与中国文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吴承学《简论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6期)、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李光摩《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余来明《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李柯《明代古与时文之关系述评》(《科举学论丛》2011年第2期)对2011年之前的研究状况做了详尽的梳理与总结。其后,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刘尊举《“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形态及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李柯《明前中期古文与时文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师雅惠《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时文改革》(《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陈水云《戴名世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冯小禄、张欢《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体系》(《聊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王苑《论章学诚“以古文为时文”对宋代文章学的接榫与更革》(《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程嫩生《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中州学刊》2018年第12期),将此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研究思路也有新突破,但理论探讨多、文本辨析少的整体格局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2)除上文注释中列举的部分著述涉之外,另有王伟《唐顺之文学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孙彦《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船山学刊》2013年第4期)、蒲彦光《唐顺之四书文研究》(《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2期)等对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问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以唐顺之为典型个案,综合考察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其古文与八股文互相渗透的文体现象,并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审视其文体史意义。
一、 “真精神”:宗旨与命脉
唐顺之并无直接讨论古文与八股文关系的文字,但从他分别的论述和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种文体相同或相近的创作观念。“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作为“本色论”的注脚,是唐顺之论文的宗旨与命脉,也是他会通古文与八股文的理论基础。
唐顺之主张书写“真精神”,似乎主要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强调体会之真切与识见之独特;而从其实际的创作情形来看,其思想实质实则不离乎儒家“文以明道”的文艺观。儒家思想的基本性质和文化品格,与作家个体真切而独特的思想形态,共同构成其“真精神”的完整内涵。
唐顺之的古文创作具有强烈的“明道”意识,与韩、柳以来重视道统、强调社会关怀的古文传统高度契合。唐宋派文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文以明道”“师法唐宋”和“本色论”,其中“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本是互为支撑的,“本色论”与“文以明道”则有着异构而同质的关系。“本色”虽然有鲜明的心学色彩,但并未脱离“道”的范畴。在理论层面及思想领域,“心”与“理”之间或有较大差异。而在文章学领域,尤其是在写作内容的层面,其间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从唐顺之古文创作的实质内容来看,“文以明道”阶段与“本色论”阶段并无明显区别。要之,皆以书写“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为准的。
唐顺之的“明道”意识,首先体现为其明确的儒家文化立场。事关士人之出处行藏,品行之高下优劣,世事之成败得失,一以儒家的忠孝节义观作为判断标准。虽论方外之学,亦必以辨明儒学为鹄的。如《赠张方士序》,虽是赠外方之人,却由其“无为”“坐忘”之学论及儒家“无声无臭之密旨”,曰:“然则为二氏学者,盖未尝无人也。吾圣人无声无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以是赠之以言,使为老氏学者,其无疑于张君之说;而学圣人者,其尚求所谓不传之密旨,而毋徒安于名节、文辞之学也。”[1]500再如《送第上人度海谒观音大士序》,虽然对拜谒观音必至普陀的行为提出质疑,却对其志行之虔诚深表敬意,并由之感慨儒士之不能笃于修身:“以补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绝不见踪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惮惊波之险,飓母蛟鱼之毒,冀一至焉而后为快,盖其信之笃而趋之果如此。今儒者学于孔氏,孔氏之宫岿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与冀一至焉而后为快者,何其少欤!”[1]501
唐顺之文集中虽不乏正面探讨儒家义理的文章,但更多的却是关注国计民瘼,有所为而发,吏治风俗、军情边务、财赋田亩、济难赈灾、兴学养士,无不详论而深究。其有补于世者,虽庶务吏事而必究,街谈巷语而不弃。如《赠竹屿吕通判还郡序》[1]477-479详尽探讨赈灾通例的弊端及解决办法;《裕州均田碑记》[1]541-542细致地记述安如石在裕州推行均田的缘由、实施及成效,并讨论其历史沿革及施行困难的社会原因;《笔畴序》则不嫌其思想驳杂、内容琐细,称:“苟可以诱世而劝俗者,君子不废也。”[1]441至其弊端深重之所在,虽愤世嫉俗而不辞,事关庙堂而不避。如《建陈渡石桥记》,由浮图德山不辞艰辛、率众修桥之事迹,反视官府之庸碌无为,提出严正的批评:“则彼长民者,固众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饱禄以嬉,其于人之疾疹阽苦,则瞀瞀而莫知,盖先王一切所以捍灾备害生人之道,泯然尽矣,其所缺者,宁独一桥也哉!呜呼!此不为而彼或为之,其亦可以观世也已。”[1]544至如《送柯佥事之楚序》一文,则直接将矛头指向朝廷:“显陵之工为费钜矣。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薮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丘墟之间,刳而市其胔,可谓廪廪。夫以杼轴既空之后,而敛之以日溢无限之费,以转徙罢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办之役,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难矣,况于啙窳剽悍之俗乎!”[1]487
唐顺之古文多有独到见解,力避空洞、浮泛,极少有敷衍文字。如《送太平守江君序》[1]472-473详论云南、两广用兵交南之法,措施明确,思路清晰,论述亦颇为周密,倘能施行果能奏效与否固不可知,但观其言论似确有可行者。即使是应酬文字,亦不肯敷衍塞责,务必用心讲出一番道理来。如《送陆训导序》[1]497-498,借陆文祥赴任海盐训导之机,详论《诗》教“独以声传”之特点及其“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之功用。《诗》教久废,陆文祥氏决无振起之力,唐顺之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然其所论却不无意义;况且又退一步,希望陆文祥能辨识“艳词丽曲”,“以雅而易淫”,却不是完全不可完成的任务。再如《陈封君六十寿序》,以与另一篇同题赠序相商榷的方式,深入讨论了老子之学究竟是“长生久枧”[1]510-512,还是“持满守柔”,就赠序的写作而言不免有偷梁换柱之嫌,而就其问题探讨之深刻而言却不无暗渡陈仓之妙。再者,若有不同见解,唐顺之决不肯苟同。如《石屋山志序》[1]468-469,申述“凡情撄于物者,未有不累于中,而丧失其所乐者”之理,虽亦描绘、渲染石屋山图卷之传神,最终却是劝勉彭氏“不待山水而后为乐”。再如《郑君元化正典序》[1]446-447, 更是直接表示“余不能尽解其说也”, 文末乃言“郑君倘得而见之乎? 其归以语我”, 委婉地表达了不肯置信之意。 另有一些文章, 如《重修瓜洲镇龙祠记》《常州新建关侯祠记》, 不免强为之说, 虽算不得好文章, 却也体现了唐顺之“唯陈言之务去”、 戛戛独造的强烈意愿。
以上是唐顺之古文创作所体现的其“真精神”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是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以及贯彻推行其社会理想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是力避陈词滥调、务求真知卓见的构思与写作要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倚重,儒家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理想为文人提供了阔大的情怀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文人的真切体验与独特见解则保证了儒学的实践品格和鲜活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唐顺之的“本色论”并不悖离“文以明道”的文学观,而是进一步的发展,并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
对“真精神”的强调,同样体现于唐顺之八股文的创作观念与创作实践中。他在《与冯午山》一文中论道:
必秀才作文不论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虽拙且滞,必是英俊奇伟之士。不然,虽其文烨然,断非君子。公考试看文,不必论奇论平,论浓论淡,但默默窥其真精神所向,如肯说理、肯用意,必是真实举子。如无理、无意,而但掇取浮华,以眩主司之目,必是作伪小人。[2]166
唐顺之对八股文创作同样要求透露“真精神”,所谓“说理”“用意”是也。整体而言,八股制义原本就是要阐发儒家义理,“说理”“用意”乃是应有之义。唐顺之于此作特别的强调,实则是要求八股文的写作要建立在对儒家义理有深刻的理解与切实的体会的基础之上。此所谓“如有真精神,虽拙且滞,必是英俊奇伟之士”,与其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所论“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之可磨灭之见,……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1]295,思路如出一辙。而他本人在八股文创作中,虽不能背离朱传,却往往能找到独特角度,写出独到见解。比如,其《君子喻于义一节》,即能不拘经传而别有发挥。限于篇幅,我们仅看其破题、承题和起讲部分:
圣人论君子小人之所喻,以示辨志之学也。(破题)
盖义利不容并立, 而其几则微矣。 是君子小人之异其所喻, 而学者所以必辨其志也欤!(承题)
且天下之事无常形,而吾人之心有定向。凡其无所为而为之者皆义也,凡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皆利也。(起讲)[3]正嘉四书文,卷二,97
题目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集注》:“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唐顺之并没有拘泥于传注,将注意力放在“天理”与“人情”的区分上,而是把“辨志”作为论述的重心。承题强调“其几则微”,“微”必“辨”之。何以辨之?需视其“有所为”还是“无所为”,“有所为”即是利,“无所为”则是义。如此立论,既不离经背传,又能别具一格。其他文章,亦多如此。
可知,书写“真精神”,即对儒家思想及相关社会、人生问题的切实体会与独到见解,是唐顺之对文章创作的基本要求,既是创作宗旨,又是决定文章成败的关键。大抵古文功能多样而趣味丰富,故通过具有特定指向性的题材选择昭示其儒家本色。而八股文功能明确、单一,阐释儒家思想不容有异,于是就格外强调透彻领会与独特视角。要之,书写“真精神”,是唐顺之对古文与八股文共同的要求,也如实地贯彻于其创作实践中,这是两种文体得以会通的基本前提。
二、“法寓于无法之中”:由精熟而圆融
唐顺之在法度层面对古文和八股文的写作要求也是高度一致的,概括地讲就是“法寓于无法之中”,拆解而言即“文之必有法”与“神明之变化”。
通常认为,唐顺之的“本色论”对法度构成颠覆性的影响。从其所谓“直摅胸臆,信手写出”“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是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等表述来看,“本色论”似乎的确有颠覆法度的理论指向。然而,颠覆法度显然不是唐顺之的本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中,他对法度都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他在《文编序》中明确地指出:“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1]450他在具体的文章评点中也充分地表现出对文法的重视(3)参见姜云鹏《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文艺评论》2013年第6期;孙彦《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事实上,唐顺之拈出“本色”一说,只是把“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视为文章写作的第一义,而把法度视为相对次要的因素,却绝非否定法度的作用。只不过,在“绳墨布置”“首尾节奏”的基础上,他对法度有更高的要求。或曰“神解”,或曰“神明之变化”,都是强调文法的精熟与高妙。而“法寓于无法之中”的说法,大约最能体现他对法度的完整态度。
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论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1]466汉以前之文“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法“密而不可窥”;唐以来之文“以有法为法”,故其法“严而不可犯”。这“密而不可窥” “寓于无法之中”的“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无法之法”和“有法之法”,究竟哪一个才是理想的法?唐顺之于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却在上文一段譬喻性的文字中做了生动的说明:
喉中以转气,管中以转声;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此皆发于天机之自然,而凡为乐者莫不能然也。最善为乐者则不然,其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潜乎声气之表。气转于气之未湮,是以湮畅百变而常若一气。声转于声之未歇,是以歇宣万殊而常若一声。使喉管声气融而为一而莫可以窥,盖其机微矣。然而其声与气之必有所转,而所谓开阖首尾之节,凡为乐者莫不皆然者,则不容异也。使不转气与声,则何以为乐?使其转气与声而可以窥也,则乐何以为神?[1]465-466
所谓“转气”“转声”“湮而复畅”“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对应的正是“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文法。唐顺之认为声乐之法与文法都是自然法则,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善为乐者”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一法则,就技巧而言是“气转于气之未湮”“声转于声之未歇”,就效果而言则是“湮畅百变而常若一气”“歇宣万殊而常若一声”“喉管声气融而莫可窥”。转而又强调“所谓开阖首尾之节”“则不容异”。可知,唐顺之所谓“寓于无法之中”之法,“密而不可窥”之法,以至“神解”“神明之变化”,并非突破乃至背离基本的创作法则,实则不离乎“开阖首尾”“错综经纬”之法;只是要更加精熟、更加巧妙地运用这些法度,努力追求自然圆融、了无痕迹的运用效果。这一追求同时充分地体现于其古文和八股文的创作中。
唐顺之的文章与唐宋古文在文化精神上高度契合,他对“开阖首尾,错综经纬”之法的精熟运用亦与唐宋古文殊无二致。正如在观念表达上决不肯虚与委蛇,他在行文布局上也从不会敷衍了事。法度的运用,如何算是得其“神解”,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但唐顺之的文章的确多有法度精严而行文高妙者。如《薛翁八十寿序》[1]504-505,章法井然而转换自然。首段论古之人贵义而贱利,皆劝其子弟以趋于仁义道德;今之人贵利而贱义,则望其子弟以趋于富贵利达,故而叹曰:“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于此?”次段讲薛氏图南本亦汲汲乎功名利禄,后得闻仁义道德之说而幡然醒悟,其父亦鼎力支持,父子交相砥,遂“自拔于今之人”;三段论祝寿之旨,称若有闻于仁义道德,则寿命或修或短,礼仪周致与否,都无足重轻。四段论薛氏所居之夫椒山,民风浇薄,乃贵利贱义之尤甚者,进而论薛氏父子能“自拔于今之人”尚不为难,能“自拔于其所居”则难能可贵;继而以转移风气之任寄予于薛氏父子,曰“然则异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称乡先生能风其乡人者,必薛翁矣”,照应开篇“古者乡有耆老父兄,则率其一乡子弟,烝烝然皆劝之于善”。最后以“是谓翁之能自寿,而图南能寿其亲也已”收结,回应主题。此文以祝寿和转移世风二事贯穿全文,二者密切关联又互为支撑,一以仁义道德为旨归,其间以“自拔”为关目,首尾照应,层次井然,夹叙夹议,不急不缓,深得欧、曾古文之致。
《钤山堂诗集序》[1]463-465则别见其为文之用心。《钤山堂诗集》是严嵩的诗集,为严嵩的诗集作序,对唐顺之来说着实是一大难题。称颂不可,贬抑不可,敷衍亦不可。如何能做到既符合序体的规范,不回避诗人与诗作,又能同时避免谄谀与讥刺之嫌呢?唐顺之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一个正面的、严肃的、跟诗歌相关而又不甚紧密的话题。于是,他找到了“知人论世”这样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用其原始义,由诗而知其人、知其世,且只是叙述性的,而非评价性的。曰:“其人之进退隐显,往往自见于诗。”曰:“因其人之进退隐显,而时之休明衰替,变化而蕃,闭塞而隐,亦因可见。”此下论述皆沿此一线索展开。先是历陈严氏由隐居至显贵的生平经历及各时期诗歌之内容,从举进士、入翰林,到隐居钤山,再到任职南都,再到入内阁、任首辅,其诗歌内容也从“多道岩壑幽居之趣”到“多纪留都冠盖之盛”,再到“自为诗以纪其盛”。随后以杜少陵之“诗史”比拟严诗,称其堪称“时政纪”。论杜则称其“偃蹇无所与于世,以其忠义所发为诗”,述严但云“况公诗所纪当世之国家大事,皆身所历而自为之者”,其间幽微,不难领会。其后则以对话的方式,引严氏语以论其诗。首先申明:“公既以全诗授胡梅林总督使刻之,而嘱某为之序。某窃以文词受知于公,公颇谓可与言诗者。”表明其为严嵩作序,乃受其嘱托,非主动为之;其受知于严氏,亦因文词,而非其他。此下论其诗,一一引其自语。如其自谓:“吾少于诗,务锻炼组织,求合古调,今则率吾意而为之耳。”则对曰:“公南都以前之诗,犹烦绳削也,至此则不烦绳削而合矣。”是耶,非耶?逆耶,顺耶?皆据其自谓耳。又如,引其所称:“吾不与后辈谈诗,恐以诗人目我,而敝精于无益语也。”则曰:“夫公之诗雄深古雅,浑密天成,有商、周郊庙之遗,知音者自当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赞于公哉!特举公之诗,系于谈世故之大者,使论世者有考焉,遂书以为‘钤山堂诗集序’。”虽赞其诗“雄深古雅,浑密天成”,却又引其自言一笔抹去,则其诗之意义全在于“使论世者有考焉”。所考者何?是非、成败、善恶、忠奸,其中亦有深意焉。篇末复补入一笔:“公之诸稿,隐显备矣,总而题之曰‘钤山集’,盖处贵显而不忘隐约者,公之志。而读诗者,则以为公之诗,钤山深蓄之力也夫!”扑朔迷离之间,似亦有深味寓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荆川此文,从立意到布局,从结构到语辞,其用心之良苦,虽读者亦可知之。
唐顺之古文大都类此,立意独特,结构工稳,章法精严,层次细密,叙述详备,议论透彻,言辞或雅训含蓄,或平实晓畅,不一而论。我们可以从其古文创作中清晰地体会到其法度的精严与细密,正应了其“文之必有法”的主张。至于“神明之变化”,或曰“神解”,我们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体会,一是精熟高妙,二是灵活变通。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文章明确地感知唐顺之法度运用之精熟及其构思之巧妙。同时,其创作手法又是灵活多变的。通读唐顺之文集,即便是同一文体之中,也很少有重复感,我们很难发现一种写作模式在不同文章中反复出现。不同话题,不同情形,会有不同的叙述策略和篇章布局。无定法而有活法,大概就是其所谓“法寓于无法之中”吧。
八股文有明确的功令要求和相对固定的程式,“文之必有法”自不待言,唐顺之主要在“神明之变化”上下功夫。在正德、嘉靖时期的八股名家中,唐顺之以立意新奇、结构精巧而独树一帜。他往往能在遵守八股文基本体制的基础上,摆脱题文限制,打破板块模式,别出机杼,另立框架结构,致力于寻求独特的立论角度与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从上文例举的《君子喻于义 一节》中,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感知到这一特点。《亚饭干适楚 一节》[4]则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创作特征。该文题目出自《论语微子》:“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朱熹《集注》引张载曰:“周衰乐废,夫子自卫反鲁,一尝治之,其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及鲁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师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乱。圣人俄顷之助,功化如此。”[5]186由于题目仅取其中“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一节,则破题与正文只能紧紧围绕这三句阐述,不得侵上犯下。承题、起讲与结题部分可以稍加拓展或引申,但也要严格遵循朱熹的注释。该文破题“鲁之以乐侑食者,而避乱各异其地焉”,是对“亚饭”三句的概括,前半句讲人物,后半句讲行为。承题点出“可以识圣人正乐之功矣”,是依据朱注“功化如此”揭示“避乱各异其地”所蕴含的义理。起讲依据经文的上下文对题目所涉事件的背景作出说明,并引出正文。题文本三句,若顺题成文,并置三大扇文字,是为正格。此文却揣度题情,别作生发,创制出逐层推进的三段文字。起二股讲三人不避险远去国离乡。以蔡与齐相比,则蔡远于齐,为能自洁其身,缭则不计远近,毅然适蔡;以楚、秦与蔡相比,蔡尚且是华夏之国,楚、秦则是夷、狄之邦,而干、缺二人宁可藏身于夷、狄之地,也不肯与乱臣贼子为伍。中二股论其必有不得已之情。鲁国备六代之乐,得雅、颂之传,而蔡仅具小国之风,楚、秦则只有夷、狄之音。作为乐工,三人岂能因向往异邦音乐而趋向之,则必有其不得已之情也。后二股讲寄居他邦的凄凉处境。昔日于公庭之上,饮食燕乐,各司其职,歌舞之余,欢聚一堂,何其欢愉!如今则纷纷奔走他邦,不惟无暇顾及家人,且忧国君之侧无乐相助;不惟失却官职,且才华技能无从施展。今昔对比,凄怆之情可见。每层文字,变换角度,却都极力烘托去国离乡之艰难,进而反衬出众乐官远离污浊、洁身自好的决心和毅力。最后以感慨收结:“于此可见圣人过化之神,乐官见机之智。而鲁之为国,良可悲欤!”以乐工之卑微,犹且如此,既可见圣人正乐之功,更可知鲁国境况之令人悲叹。则此等寻常题目,一经荆川之手,化平淡成新奇,变枯索为丰腴,不惟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乐工的情绪心态,且通过种种反差极力渲染出一种悲凉气氛。虽是时文体制,却有古文意境,正得益于其对文法的精熟与灵活运用。这只是立意构思和篇章布置方面的体现,我们可借以了解唐顺之八股文写作中“神明之变化”的创作倾向。其具体的写作技法同样是灵活多变的,下文将有详尽论述。
可知,虽然“本色论”具有解构乃至颠覆法度的理论潜能,但在唐顺之本人的文章观念中,尽管法度较之“本色”是次一层级的创作因素,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故曰“文之必有法”。他对理想法度有种种玄秘的表述,如“神明之变化”“神解”等,但终究不离乎“开阖首尾”“错综经纬”之法,只是要求精熟运用,追求圆融无迹、灵活多变的行文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讲“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唐顺之所谓“文之必有法”正是有常之体,“神明之变化”则是无方之数,常体与变数相结合,构成其既严谨又通达的法度观。正是在这种具体的法度观的影响下,唐顺之的古文与八股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会通与互动。
三、“以古文为时文”
唐顺之的古文务求书写“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坚决反对空谈理道、蹈袭旧说。同时,他也不把八股文仅仅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是希望士子能够潜心研阅,独有心得,通过八股文的写作阐述儒家义理,因而同样把“真精神”作为判断八股文优劣的基本标准。在法度上,他主张“法寓于无法之中”,是对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的折中与会通。因此,他并不质疑八股文的价值,也不将其与古文割裂开来,而是在功能、法度、风格等各个方面寻求两者的会通、融合,从而在他的笔下形成古文与八股文双向渗透的趋势。
以古文为时文,本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创作现象和学术话题(4)祝尚书《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将其源头追溯到北宋徽宗时期,并讨论了它在南宋的流传与影响。,但作为明代中期八股文创作的一种独特现象,则具有新的内涵。正德、嘉靖时期,八股文创作兴起一股“以古文为时文”的潮流,而唐顺之正是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所谓“以古文为时文”,是指八股文在趋于成熟与完备之后,有意识地借助古文改进八股文作法、提升八股文境界的文体创新。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特点,大约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八股文语辞的丰富与改造,把经典文本和先秦时期的历史典故融入阐述经文的言辞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调枯燥的宋儒讲义的面貌,方苞称之为“溶液经史”[3]凡例,3。其次是法度的突破与创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破,打破时文成规,突破“体用排偶”的语体限制和刻板、单调的叙述模式,寓骈于散,追求结构布局的新奇多变;二是立,引入古文法度,追求行文的细密、巧妙与灵动。再次是在思想的深刻与情感的厚重或细腻上下功夫,提升八股文的境界与趣味。关于正德、嘉靖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现象,以及唐顺之的表现与作用,学界已有比较充分的探讨(5)参见刘尊举《“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形态及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本文不再展开论述,仅分析一篇典范文字,借以体会唐顺之八股文写作中古文法度的运用与效果,并补充辨析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唐顺之《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 一节》[4]一文,广泛运用古文创作中的各种技法,夹叙夹议,极尽委曲周折之能事,堪称“以古文为时文”之典范。题目出自《孟子·离娄》:“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仅就此节文字而言,纯粹是一段对话体的叙事文。然而,孟子叙述此事,目的在于将其与蒙杀后弈之事作对比,说明君子择友必慎的道理。唐文即依据题文顺序,逐段叙述,并将孟子的意思透露出来。关于此文文法,俞长城引吕晚邨评语论之甚详:
有排场,有事实,有言语,此题中之堆垛也。有真情,有驳辩,有比例,有判断,此题外之堆垛也。先案后断,则叙处呆板。夹案夹断,则忙乱支离。此却将题内题外堆垛,以一炉融铸而出之。或插入叙记中,或提出语句外,或增补闲情,或简省文法,可长可短,忽整忽散,看《左传》《国语》《公羊》《榖梁》及《史记》《汉书》,同叙此事,各见妙笔,此详彼略,东涨西坍,情事不殊,境界顿异。此之谓化工手也。惟荆川得其奥耳![4]
其所谓“题中之堆垛”,是指题文中包含的背景、事件和对话;“题外之堆垛”,是指事件本身又隐含着当事者的心理活动,不同人物、事件之间的对照,以及由此生成的判断,等等。文章内容着实丰富而驳杂。如果先叙述,先描写,最后再作出判断,即所谓“先案后断”,则文章显得呆板;如果叙述、议论交错进行,则容易流于支离、杂乱。此文却将所有这些内容融为一体,事件、对话交错进行,又时有议论穿插其间,却能够做到层次清晰,有条不紊。第一段简要地交代清楚事件背景,忽又插入一语:“两技相角雌雄未可知也。”此即吕晚邨所谓“增补闲情”。经文之中,对话繁多,若一一落实于文章中,必然支离、繁琐。作者便从中挑出关键人物子濯孺子和庾公之斯,仅此二人具有“发言权”。对话过程中仆从的话语,或被简单地概述,或并入子濯孺子的话语中。如其第二段,便将仆从的话一概简省,以子濯孺子自语的方式,讲述出其由“必死”到“必生”的心理变化。“占之于我”“占之于人”则是穿插议论,“幸其得朋之助也”则为下文埋下了伏笔。第三段则将仆从的疑虑化入子濯孺子的回答中,“非谓斯之技不足以杀我也”,其实正是以对答的方式补入仆从的疑问。段末插入“孺子所以能自信其不死也”一语,既是对孺子之语略加小结,又是对此后情节设置悬疑。第四段讲子濯孺子与庾公之斯的对话。“未几而庾公之斯至焉”是叙述事件的进展,“未几”二字犹能增强叙述的故事性。“盖疑其能而示之以弗能也”“盖示以情也”,是判断,是对二人心理活动的揣度。第五段,讲述庾公之斯放过子濯孺子,是对前文子濯孺子“自信其不死”的印证。“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斯固可以必得志于孺子矣”,是作者对当时情形的判断,更能反衬出庾公之斯的仁义。这两段文字,内容最为多样,既有言语,又有叙事,还有议论,却是依次推出,丝毫不乱。第六段纯是议论,将庾公之斯“抱德之厚”和子濯孺子“料人之智”,与蒙杀后弈之事作对比,从而突出题旨。此段处处以二者作比,却总是以庾公之斯或子濯孺子为主,以蒙或后弈为宾,故不为侵上,亦可见荆川文法细密处。结语则跳出题面,另作发挥,却又是从题文中生发出来,故既觉新奇,又无偏离之弊。综观此文,事件与言语、叙述与议论,交错进行,或繁或简,详略得当,深得《左传》《史记》叙事之法。诚如晚邨所论,若能细细比较《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对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则最能体会荆川此文行文之妙,亦可知其创作技巧之所由来。从这一篇例文中,我们几乎能感知唐顺之在各个层面借助古文对八股文的改造。包括语体的骈散相间、寓骈于散,结构的灵动变化,技法的精细、巧妙,刻画之传神,行文之周折,意趣之丰饶,无不体现了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意图与成效。
然而,“以古文为时文”毕竟带有博弈的性质,所以需要格外谨慎地斟酌与拿捏。遵经守传是八股文写作的基本准则,但陈陈相因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如何在不背离经传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就成为八股文构思的首要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唐顺之的八股文写作往往能够别出心裁、立意新奇,似乎是八股文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我们很难断言这一定是受古文的影响。然而,这与其抒写“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诗文创作主张是高度契合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密切关联。在八股文的传统作法中,语用排偶本是毫无争议的规则。然而,随着“以古文为时文”创作风气的形成,骈与散却逐渐成为可供选择、有待权衡的形式因素。有些文章只是将骈句寓于散句之中,主要是为了达到流畅自然的表达效果;有些文章则试图跨越文体之间的界限,有意忽略或淡化八股文的骈偶化特征。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即接近于后者。散体化的创作倾向的确能给八股文创作带来一些崭新的气象,但这显然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好骈与散之间的平衡关系,完全有可能导致八股文体的解散。更重要的是,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创作者科考的失败。于是,他们把目光从语体转向了结构,看看在那里是不是有着更大的转化空间。在文章的结构布局上,唐顺之试图突破八股文机械化的结构方式,寻求更加新奇、富有变化的间架结构。无论是在题文顺序的基础上略作调整,还是彻底变易题文的叙述顺序,都是要打破以往八股文的板块模式,寻求行文的流动感或层次感。细密的起承转合、跌宕顿挫之法,则是实现此一目标的技术性保障。理论上讲,灵活多变的结构方式,精巧高妙的行文法度,并非古文的专有特征,这种变化可以被视为八股文自身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而事实上,面对现成的创作经验,八股文作者不可能熟视无睹,势必从古文中多有借鉴。因此,这些改变均可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重要表现。
四、 “以时文为古文”
在明代的文体价值序列中,古文显然是优先于八股文的。如果说“以古文为时文”尚且能够成为一种风尚,乃至一种标榜,那么“以时文为古文”却往往处于批判性的话语中(6)黄强《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对“以时文为古文”微妙的理论内涵有深刻的剖析。。但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潜移默化,唐顺之的古文中的确有八股文的影子,既表现为结构的,又表现为语体的特征。
八股文的基本结构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大讲、结题五个部分;大讲部分又包括两种基本的体式:一是扇体,一是股体。其中,扇体八股文多为两大扇体或三大扇体,与古文结构较为接近,不易判断其间的相互影响。而股体八股文,最典型的是八股体,与古文结构差异明显,对古文文体的影响较为明显。唐顺之古文受八股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篇立意的形式,颇受八股文破题的影响;二是层层推进,每层文意两两相对的结构模式,明显受到股体八股文的影响;三是对仗散句的大量使用,无疑也是受到八股文独特语体的影响。
古文的开篇方式千变万化、殊无定规。八股文开篇则必须以一句文字点破题旨,同时也是总括文章大意,此之谓破题。古文也可以开篇总括篇章大意,却并不频见。而唐顺之的古文,尤其是序、记体,则多用此法。如《季彭山春秋私考序》开篇云:“《春秋》之难明也,其孰从而求之?曰求之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其孰从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妇之心。”[1]436通篇即围绕此一句展开。再如《笔畴序》“苟可以诱世而劝俗者,君子不废也”[1]441;《石屋山志序》“凡情撄于物者,未有不累于中,而丧失其所乐者也”[1]468;《重修泾县儒学记》“先王本道德、礼乐、经术以造士”[1]523;《零陵县知县题名记》“名者,其起于古之所以励世乎”[1]533,等等皆是。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起句并不能涵盖全文大意,却与主旨密切相关,能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如《明道语略序》开篇云:“道致一而已矣,学者何其多歧也?”[1]434此下即从“道致一而已”说开去,发明“吾心天机自然之妙”。再如《巽峰林侯口义序》以“有逐末之学,而后有反本之论”[1]439开篇,进而引发“即心而经”“即经而心”的讨论。《送陆训导序》开篇云:“六籍之教之废也久矣,而《诗》最为甚,何哉?六籍皆以文传,而诗独以声传也。”[1]497通篇即围绕《诗》教论“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之旨,亦是此例。这一现象,固然与八股文破题的影响密切相关,亦与其好发议论、务求“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古文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股体八股文的正文,即大讲部分,通常由三到六个层次构成,其中以四层最为常见;每一层次包含一组大致对仗的句子,四层则构成八股,三层则构成六股,不一而论。各个层次之间,往往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或并列,或总分,或步步推进,或逐层转换,或是更加复杂的组合关系,总之与唐顺之所谓“开阖首尾,错综经纬”的古文法度有着高度的契合。唐顺之古文的结构与语体,多有受此影响者。以《巽峰林侯口义序》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试尝观之,心之不能离乎经,犹经之不能离乎心也。
自吾心之无所待,而忽然有兴,则《诗》之咏歌,《关雎》《猗那》之篇,已随吾心而森然形矣,是兴固不能离乎《诗》矣。
然自其读《诗》而有得也,未尝不恍然神游乎《关雎》《猗那》之间,相与倡和乎虞庭、周庙,而不知肤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则是学《诗》之时,固已兴矣,非既学《诗》而后反求所以兴也。
自吾心之无所待,而忽然有立,则《礼》之数度,《玉藻》《曲礼》之篇,已随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离乎《礼》矣。
然自其读《礼》而有得也,未尝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礼》之间,相与揖让乎虞庭、周庙,而不知肤理血脉之肃然以敛也,则是学《礼》之时,固已立矣,非既学《礼》而后反求所以立也。
安得以寓于篇者之为经,而随吾心森然形者之不为经耶?故即心而经是已。
安得以无所待者之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与有所待而肃然以敛者之不为吾心耶?故即经而心是已。
然则何末而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而非末,而又何所反耶?[1]439-440
这一段文字单独摘录下来,几乎可以视为一篇独立的八股文。首段和末段分别可以视为破题与结题。二、三两段是第一层,分别从“吾心”与“读《诗》”两端说明“心之不能离乎经,犹经之不能离乎心”,相对成文。四、五两段是第二层,分别从“吾心”与“学《礼》”两端说明“心之不能离乎经,犹经之不能离乎心”,亦相对成文。前两层是并列的关系,分别以《诗》与《礼》为例说明“心之不能离乎经,犹经之能离乎心”。六、七两段是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总结,从中揭示出“即心而经”“即经而心”的结论。显然,无论从结构还是从语体来看,唐顺之这篇序文都深受八股文的影响。
《巽峰林侯口义序》是一篇严肃的论学文字,与八股文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宜乎较多受其影响。而《声承集序》论交友之道,作文态度亦不似上文那般严肃,却同样受到八股文的深刻影响。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渐斋子录其平生交游往复之书及诸赠言,名之曰《声承集》,凡若干卷。
渐斋子始居给舍,侃侃厉名节,故其时所与游,多慷慨奇节之士;已而谢事家居,蝉脱声利,晚乃刊落华叶,潜究精微,故其时所与游多山泽肥遁之流与讲学论道之朋。
且夫人之于世,固未有独立而无与者。缙绅相与以同心而共济,虽山泽与世不相涉,亦必有与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辈,所以不可行于朝,而狷狭枯槁、逃虚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于野也。
渐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节,而使海内高士争慕与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谦虚不自满之量,而使与之游者争献其所长者如注而一无所拒。
故其在朝, 则相与秉公斥奸, 以共忧天下之忧; 在野则相与养志理性, 以共其乐于山林泉石之间。[1]459-46
虽然这段文字结构上不似上文严整,文字的对仗也不如上文工整,其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也更多地保留了古文自然、灵活的文体特征,但其层层推进、每层之内两两成文的结构模式显然也是在八股文的影响下形成的。
《中庸辑略序》一文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创作中古文精神与时文风貌相结合的特点。《中庸辑略》是由《中庸集解》删减而成,《集解》收录二程及其弟子游酢、杨时、谢良佐、侯仲良等人论《中庸》之语。唐顺之对游、杨、谢、侯诸子显然是颇有微辞,认为其学术思想中有佛家思想窜入。因此,他在序中详尽地讨论了六家、九流与佛家思想乱入儒学之危害,以及明辨儒、佛思想的方法与途径。此文鲜明地体现了唐顺之求其“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创作思想,其“开阖首尾,错综经纬”之文法及其所受八股文之影响,同样清晰地呈现出来。首段详叙《辑略》来历及作序缘由,质朴详实,简洁明了,纯是古文笔法。
次段则曰:“盖古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外,而后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中”[1]432,总领下文,犹八股文之破题。三段论六家、九流及佛与儒不相为谋而不相乱。四段论六家、九流及佛窜入儒学而莫之辨,曰:“六家、九流与佛之与吾六经、孔氏并也,是门外之戈也;六家、九流与佛之说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1]433较之三段,是转折,也是推进一层。五段从六家、九流与佛之中单独拈出佛家,曰“六家、九流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其为说也粗,而其为道也小,犹易辨也。佛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则其为道也宏以阔,而其为说也益精以密”[1]433,并指出其与儒学多有相似之说,如“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故最难分辨。六段则详辨儒、佛两家“一原”“无间”之异同,是全文最见工夫处,且具有典型的八股文语体特征。其文如下:
嗟呼!六经、孔氏之旨,与伊、洛之所以讲于六经、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谓“一原”“无间”者,自信乎吾之所谓“一原”“无间”者而后彼之所谓“一原”“无间”者可识矣。儒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顺而达之;其顺而达之也,至于天地万物皆吾喜怒哀乐之所融贯,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佛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逆而销之;其逆而销之也,至于天地万物泊然无一喜怒哀乐之交,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其机常主于逆,故其所谓旋闻反见,与其不住声色香触,乃在于闻见色声香触之外。其机常主于顺,故其所谓不睹不闻,与其无声无臭者,乃即在于睹闻声臭之中。是以虽其求之于内者穷深极微,几与吾圣人不异,而其天机之顺与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1]433-434
末段申明“醇者大矣,其不能浸淫于老与佛”之题旨,照应开端,总结全文。文章观点明确,结构清晰,层次精严,照应严密,堪称古文典范。其立意、结构与语体所受八股文之影响亦昭昭俱在,不必赘言。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八股文大部分的文法本来就源于古文,那么我们从古文中发现八股文的特征,它究竟是八股文的影子还是古文的影子呢?从逻辑上讲,这的确很难判断。然而,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古文和八股文历时性的文本系统中加以辨析,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首先,尽管八股文多受古文影响,但毕竟形成了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我们在此要重点关注的正是其独特之处对古文的影响,比如其散句对偶的语体特征,以及与这种语体相结合的层层推进、两两相对的行文方式等。其次,我们要关注八股文影响下古文与之前古文的同中之异。比如,古文中并非没有开篇立意的行文方式,但唐顺之这样高频率的使用,我们就不能不归结为八股文的影响了。那么,时文法度渗透到古文创作中,其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仅从唐顺之来看,其开篇立意的行文方式,对议论性的文章来说应该还是很有应用价值的;其层层推进、两两呼应的结构方式,如果运用的灵活,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法;至于散句对偶的语体,如果大量使用,不免影响古文质朴自然的文风,但偶一为之也未尝不可。而要想得出全面、稳妥的判断,恐怕还要有更大范围、更大体量的文本分析才行。
五、结 语
唐顺之的古文与八股文创作之间,显然是一种彼此会通、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两种文体会通、互渗的基础则是唐顺之求其“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与“法寓于无法之中”的创作主张。在内容与功能的层面,古文的表现空间要比八股文广阔得多。八股文是应试文体,只能阐发“四书”“五经”中的儒家思想。唐顺之于此强调的“真精神”也主要是指对儒学典籍与思想的切实体会,“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则是在“真精神”的基础上指向立意之新奇。而在古文领域,唐顺之明确的儒家文化立场则保证了“真精神”的内涵与八股文相一致,只是在阐发理道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要求有所为而发,力避空言,务求有补于世。在法度层面,唐顺之倡言“法寓于无法之中”“神明之变化”“神解”,实则是强调“开阖首尾”“错综经纬”的精熟和灵活运用。古文法度本自丰富、灵活,故唐顺之似乎更重视结构之工稳、章法之精严与行文之细密。八股文程式相对固化,则更强调求新求变,注重结构的新奇和独特,务求行文的层次感与流动感。潜移默化之中,唐顺之的古文与八股文又多有文体层面的相互渗透。无论是立意方式、结构布局还是语体色彩,其古文创作时常有八股文的影子。而其八股文更是从古文的创作经验中多方汲取营养,努力实现结构的丰富多变与行文的灵动自然。
通过对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文体之间的确有实质性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互动是建立在作者明确的主观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从散文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借助这一视角,更加准确地把握古文文体的新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与机制。从文章学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八股文创作形态中,感知当时文章家探索文法的现实驱动力及其用力之所在。当然,仅凭对唐顺之一人的研究,尚不足以做出太多的推论。但如果沿此思路,作更多具体的、落到实处的个案研究,或许我们会有更深入的、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