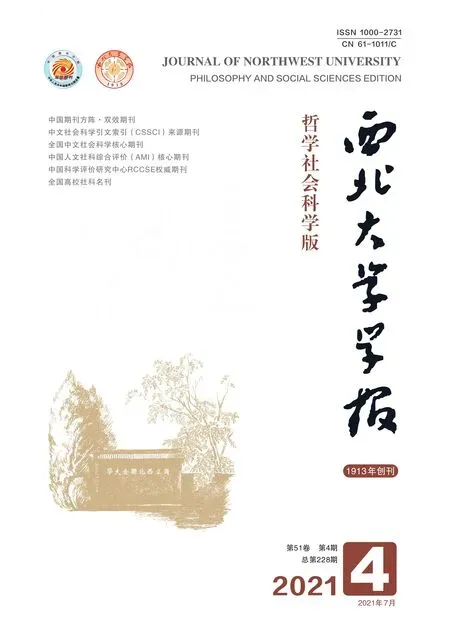《国际卫生条例》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困境与完善
刘雁冰,马 林
(西北大学 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020年1月末,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宣布新冠疫情(COVID-9)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新冠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自WHO成立以来,其主要职责就是领导国际社会共同抗击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WHO依然努力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框架性文件,在新冠疫情应对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一年多来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不论是从防疫建议的有效性,或信息共享的及时性,亦或是防疫资金的充足性来看,WHO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国际社会对其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美国政府甚至于2020年4月14日向国际社会公开表示,将暂停向WHO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WHO在防疫工作中的主动权被大大削弱。WHO作为领导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机构,《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法律规范,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其领导力和作用发挥得似乎不甚理想。面对《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困境,需要在治理机制、治理理念等方面加以完善,进一步增强《国际卫生条例》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使其能更好地应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一、《国际卫生条例》的演进
(一)《国际卫生条例》的形成
《国际卫生条例》最早发源于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为了遏制鼠疫对全世界的侵袭,意大利的威尼斯于1348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检疫法规,施行检疫。19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促进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同时也使得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原有的检疫法规已经无法满足防疫需求。许多国家为防御瘟疫的传播蔓延,相继采取检疫措施,制定检疫法规,并从地区性的协调,逐渐发展到国际间的合作。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于1851年在巴黎召开,制定了《国际卫生公约》。1951年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防止疾病在国际间的传播,同时又尽可能小地干扰世界交通运输。1969年第22届世界卫生大会对《国际公共卫生条例》进行了修改、充实,并改称为《国际卫生条例》,此后又进行了多次局部修订和补充。
《国际卫生条例》生效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疾病族谱不断变化,新的传染病相继出现,世界公共卫生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首先,各国并未履行通报义务,从而导致其他国家过激措施屡禁不止。纵观人类疾病史,我们可以发现,传染病常常高发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缺乏传染病监测和评估能力,不能准确提供受感染的具体地区和人数,更无法对传染病形成全局性的了解。因此,一些国家并未认识到某些传染病事实上只能造成小范围的传播,盲目地采取过激的应对措施。根据当时的国际法惯例,反措施不得在严重性和大小上极为不相当。因而,对于违反通报义务所采取的反措施应严格遵循相称性原则,并以迫使他们履行义务和做出赔偿为限。
其次,适用对象具有局限性。这个时期的《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针对“鼠疫、霍乱、黄热病”三种传染病,各国必须履行通报义务。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传染病早已达几十种之多,《国际卫生条例》在这方面已经严重滞后。
最后,《国际卫生条例》在治理理念上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观念。它只要求成员国在边境上采取措施以抵制传染病的国际扩散,而不要求在国境内完善公共卫生设施,也不要求国家采取措施来改善国内传染病防治的总体状况[1]59。这种被动的治理方式使得各国严重缺乏主动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意识,并缺乏传染病领域的国际合作意识。
(二)《国际卫生条例》的变革
2003年SARS病毒的爆发,成为《国际卫生条例》修改的强大动力。2004年1月和9月,WHO先后两次提出《国际卫生条例》全面修订草稿,广泛征求各成员国意见。2005年5月,第58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新的《国际卫生条例》于2007年6月15日生效。新《国际卫生条例》改变了原有《国际卫生条例》的治理理念,进行了如下变革:
第一,扩大了缔约国的责任与义务,要求缔约国将建设公共卫生核心能力作为目标之一,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传染病信息监测、通报和共享机制;要求各国履行监测和信息通报义务,WHO可对信息进行评估,根据结果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第二,确立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机制,扩大了《国际卫生条例》的适用范围。将原有的三种传染病扩大到既存的、新的和重新出现的疾病,其中还包括非传染疾病所引起的紧急情况[1]61。
第三,引入了人权原则。人权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日渐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卫生治理与人权保护存在着天然不可割裂的联系,新《国际卫生条例》也将人权原则纳入框架当中。
第四,注重国际经济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平衡。新《国际卫生条例》的目的在于,“以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亦即WHO试图通过新《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与国际贸易进行协调。
二、新冠疫情形势下《国际卫生条例》面临的困境
2003年SARS病毒的爆发,促使《国际卫生条例》建立了系统的传染病预警与监测机制。但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最重要的条例,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国际卫生条例》依然陷入了不被遵守的困境。究其制度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缔约国核心能力建设不完善
核心能力建设是保障《国际卫生条例》有效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条件。 只有缔约国具有强大的核心能力, 才能在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与WHO积极正向联动, 确保《国际卫生条例》后续工作的有效开展。
《国际卫生条例》及附件一规定,缔约国应当利用现有的国际机构以及资源,满足《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能力建设要求。该要求包括:一是监测、报告、通报、核实、应对和合作活动;二是指定机场、港口和陆地过境点的活动。各国监测和应对能力建设完成的最终期限为2012年6月15日,未完成建设的国家可申请延期两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2012年6月,193个缔约国中只有42个缔约国向WHO提交报告,表明其在领土范围内完成了核心能力建设。到2014年6月15日,共有64个缔约国宣称达到《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能力建设要求,81个缔约国要求把实施截止日期再延期两年,48个缔约国未向世卫组织传达其意图[2]2。缔约国监测和应对的核心能力是否完善,不仅影响着《国际卫生条例》的有效实施,更直接关系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最终效果。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许多国家并未对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投入过多资金,一些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仅用很少的资金来维持公共事业的运转,资金和技术资源问题仍然是国家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以往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大都发生于核心能力建设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以SARS病毒为例,在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十分薄弱。为了弄清相关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核查清楚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3],疫情评估制度与监测制度的缺失使得SARS疫情在国内迅速蔓延。反观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早在“9·11”事件后炭疽病爆发时,美国就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包括覆盖全国疾病检测报告的预警系统、临床公共卫生沟通系统等,这大大降低了SARS疫情对美国带来的恐慌。SARS疫情使我国清醒地意识到公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此后十年间,中国政府投入了117亿元用于提升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建设,2014年我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已达到《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
除了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外,一些国家在进行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时常常存在其他阻碍,这些阻碍主要包括卫生基础设施在长期的武装冲突或者自然灾害下遭受破坏[4]77;长期对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的意识不足;各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人类发展、教育和卫生方面持续存在重大差距等[2]4。
(二)缺乏强制性“遵约引力”
一个国家是否愿意遵守一项国际制度,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取决于该项国际制度是否符合和反映一国的利益和期待,还取决于该国际制度是否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对缔约国产生规范性、强制性效力,这二者共同作用使得缔约国具有自愿遵约的意愿,形成“遵约引力”[1]61。在酝酿《国际卫生条例》的初期,WHO与各缔约国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间很难平衡。为了使《国际卫生条例》尽快达成,缔约国选择了最佳策略,即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形成公共卫生领域内的集体性力量,从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然而《国际卫生条例》依然存在模糊性,在缔约国因本国利益选择不遵守条例时,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对缔约国的行为进行规制,这使得《国际卫生条例》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依然缺乏“遵约引力”。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疫情发生后各国负有向WHO进行信息通报的义务,但是仍然有许多国家出于对本国利益之考量,并未履行这项义务。信息通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缔约国可能因为向WHO通报本国疫情情况而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过度反应,从而引发负面影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许多国家并未听从WHO的建议,也未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第43条的相关规定,纷纷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构成了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违约。诚实遵约不仅影响着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国际地位,也会使本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上述违约行为,WHO无法作出实质性干预。因为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对额外卫生措施的规制建立在尊重国家自主权和以WHO建议作为制衡的基础之上,设想的是通过透明度和公开性吸引国家主动遵约[5]26。从2011年禽流感到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WHO曾针对《国际卫生条例》第43条的遵守情况做了多次审查,在提高《国际卫生条例》第43条遵约动力方面做了调整。WHO认为,鉴于《国际卫生条例》并未对不履约行为作出惩治规定,因此有必要提高透明度,增强以证据为基础的额外卫生决策[6]140,并且对不必要的破坏性应对措施进行公众披露。然而这种软性的遵约动力并未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发挥效用。在强制性“遵约引力”的缺位下,国家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考量衡量是否遵守《国际卫生条例》。
(三)PHEIC启动机制欠缺规范和透明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机制作为新《国际卫生条例》的一项重大修改,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旦某项公共卫生事件被宣布为PHEIC,就意味着将会对世界经济、政治、医疗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故而作为启动PHEIC机制的唯一决策者WHO,常常承受着来自各缔约国的质疑与责难。这与PHEIC启动机制缺乏规范性和透明性有关。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 申报PHEIC应当按照以下程序: WHO总干事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中挑选专家, 组成紧急委员会, 紧急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受影响国家和专家的意见, 并向总干事提出咨询意见和临时建议; 总干事会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对PHEIC的认定标准, 考虑是否启动PHEIC机制并接受临时建议。 从以上程序我们可以看出, 紧急委员会仅仅起到提供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真正的决策者为WHO总干事, 即总干事在启动PHEIC机制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过去的几次PHEIC机制启动过程中, 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当何时使用、 依照怎样的标准使用, 成为缔约国向WHO发难的主要原因。
在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中,时任WHO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宣布将把甲型H1N1流感疫情警戒级别提高至最高级6级,并第一次宣布其为PHEIC,造成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恐慌。然而,甲型H1N1流感并未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WHO因此饱受质疑,这直接导致了WHO在之后面对埃博拉以及寨卡病毒疫情时的犹豫不决。2014年埃博拉病毒出现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等国于2014年3月就向WHO上报了疫情,但WHO直到同年8月才作出决定,宣布其构成PHEIC。在刚果(金)埃博拉病毒出现后,WHO总干事与紧急委员会就是否应该认定此次疫情构成PHEIC进行了多次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总干事拒绝将此次疫情宣布为PHEIC。理由在于:一是埃博拉疫情不符合条例对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定义中的所有标准,并不满足“国际传播”标准; 二是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会给疫情应对带来更多好处[7]180。然而,在2019年7月,WHO总干事最终接受了紧急委员会的建议,宣布此次疫情构成PHEIC。需要指出的是,WHO总干事与紧急委员会针对PHEIC的认定程序的所有工作都是不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披露的。WHO的“一家之言”以及总干事PHEIC认定过程中态度的反复,都会削弱《国际卫生条例》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使得《国际卫生条例》面临丧失公信力的危险。
三、《国际卫生条例》的完善
(一)提升缔约国核心能力
《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在其基层公共卫生应对方面,一旦发现超过预期水平疫情的信息,应立即向中层或者国家层报告,并采取初步应对措施;在中层的公共卫生应对方面,应当确认报告时间的状况,进行评估后向国家层报告,并采取额外的控制措施;在国家层应对方面,应在48小时之内评估紧急事件的所有报告,并通过归口单位立即通报WHO。可以看出,这种层级分明的评估标准需要缔约国拥有稳定的公共卫生治理环境和强大的财力、技术和人力资源作为保障。笔者认为,WHO对缔约国核心能力建设的要求更接近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因一些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无法完成核心能力的建设。因此,应当以各缔约国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差异化为考量,构建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实际经济负担与社会负担,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时间的公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的建设周期,建立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能力的最低评估标准,并根据国家对该标准的履行能力,制定分时间段的综合性优化计划。除此之外,可以将以国家为单位的核心能力建设转变为以地区为单位的核心能力建设,以保障一些人口基数较小和发展水平较弱的国家得到多方资源的支持。
公共卫生核心能力薄弱的国家应当转变意识,充分认识到发展、加强和维持核心能力建设是一种持续性的过程。为此,应当按WHO的要求,定期进行自我评估,严格审查核心能力建设是否达到《国际卫生条例》的基本要求;在国家内部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资,将国内投资、经常性支出和公共资金专门用于重点环境中的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工作,并将这些项目的支出统一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年度财政预算之中;加大基层医疗工作队伍的建设,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公共卫生的宣传工作,增强广大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意识。已经达到核心能力建设要求的国家应当积极对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帮助各受援国在基层开展公共卫生事业建设。WHO应当对未达到核心能力建设要求的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引导非政府组织、公立和私营部门以及利益攸关方积极提供国际援助,其中包括资金的援助和医疗协作机制的建立等。
(二)以共同利益观为补位
与之前的《国际卫生条例》相比,新《国际卫生条例》加强了缔约国的国际法义务,使WHO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越过缔约国而对一国国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监测和信息收集,其实施仍然受到国家利益的限制。如前所述,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冲突作为《国际卫生条例》实施的先天性障碍,是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进入高速全球化的21世纪,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问题的频繁出现将全人类带入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8]27。“各扫门前雪”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全球化浪潮下的公共卫生治理已经不仅关乎一国国内的国民安全,更是全人类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也是《国际卫生条例》存在之理由。因此,将共同利益观引入《国际卫生条例》的构建中,不仅是完善《国际卫生条例》,也是推动WHO法制的必由之路。细观国际法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已经逐步从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利益导向转变为以人为本、重视人类整体利益发展的利益导向。而此次新冠疫情再次证明,面对危及全人类的全球性灾难,个体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某些国家未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冠疫情中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牺牲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做法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笔者认为,各缔约国应当继续遵循《国际卫生条例》订立之初衷,跳出国家利益之局限,摒弃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利己主义,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要时适度牺牲局部利益换取一个稳定而长效的良性公共卫生环境。同时,《国际卫生条例》应当明确以共同利益观作为立法宗旨,明确缔约国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意义。在全人类共同利益观的补位下,发挥《国际卫生条例》的优势,形成一个诱导性的遵约机制。
(三)强化《国际卫生条例》的“遵约引力”
强制性“遵约引力”的缺失是缔约国不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的重要原因。在国际法领域,一项国际制度能否被遵守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是否具有不可违约的强制力。正是因为《国际卫生条例》缺乏这种强制力,才导致缔约国履行遵约义务时具有随意性。因此,应当对《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使缔约国有行为依据。首先,在监测和信息通报方面,应当制定前置程序,将公共卫生信息的评估标准详细化和具体化。建立事后审查委员会和公共卫生征信机制,审查各缔约国是否将监测和通报义务履行到位,并要求缔约国提交不履约的理由。若缔约国因为缺乏遵约能力而无法遵约,则采取促进性措施帮助缔约国提升遵约能力;若缔约国因其他原因怠于遵约,则可通过征信制度进行惩治。其次,应当提高“额外卫生措施”的使用标准和成本,设置“额外卫生措施”的具体程序性条件,反向促进缔约国遵守WHO的临时建议。
强化《国际卫生条例》的“遵约引力”,还需要以一个有效的外部监督合作机制为依托。具体来说,增设各缔约国对《国际卫生条例》履行情况的监督权利,允许缔约国就其他国家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表达特别关切和“投诉”损害来加强问责。WHO也可以与其他国际组织展开促进《国际卫生条例》实施的国际合作,使公共卫生问题在国际治理的各个领域得到缔约国的重视[5]30。
(四)建立规范和透明的PHEIC启动机制
如前所述,长久以来WHO一直试图将自身定位成一个纯粹中立的权威科学机构,故而PHEIC紧急委员会基本上由各国最具权威的技术专家组成。在宣布PHEIC时,紧急委员会优先选择站在科学角度评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否构成PHEIC。然而事实是当WHO总干事宣布PHEIC时,不仅要考虑该公共卫生事件对卫生安全的威胁,还需要考虑其对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威胁。最明显的证据是,在宣布PHEIC时,WHO总干事和紧急委员会被要求提出有关国际贸易和旅行的相关建议,这本身就是出于国际政治经济的考量。由此可见,宣布PHEIC不仅是一项专业判断,更演变成一项治理决定。因此,WHO总干事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常常受到多方因素的掣肘。笔者认为,首先WHO总干事应当抱着审慎的态度,严格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对PHEIC的界定标准。《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启动PHEIC机制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已经发生大范围的国际间传播;二是传播对国家医疗应对能力造成巨大挑战;三是国际协同努力应对疾病持续传播[9]52。在以往几次PHEIC的决策过程中,造成WHO总干事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共卫生事件到底是否构成“国际传播”这一标准(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bola Outbreak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eclared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17 July 2019), available at
透明度被认为是善治良政的核心,既能捍卫流程及其最终决策的合法有效性,还可以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获得所有可能受到关注或影响国家的理解和支持[10]54。因此,应当建立更加透明的PHEIC启动机制,力求达到审议过程透明化、人员构成透明化、决策依据透明化。具体来说,可以公开紧急委员会的专家名单,并在适当范围内公开紧急委员会审议过程的文字记录,仅对于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进行保留,以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对PHEIC机制进行监督。同时,在WHO的事后审查和问责机制中加入对PHEIC决策的国际问责制度,必要时建立对总干事的问责制度等。通过在事前、事中、事后各个阶段同步提升PHEIC启动机制的规范度和透明度,重塑《国际卫生条例》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可信赖度和权威性。
四、结 语
新冠疫情不仅为中国的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更是对全世界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巨大挑战。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公共卫生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长效的法律治理机制急需被建立,WHO应在这个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建立国际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其完善对WHO今后领导和参与公共卫生法律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次新冠疫情应对来看,《国际卫生条例》虽然在传染病应对方面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防控机制,但仍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陷入实施困境。要突破这种困境,应当继续注重缔约国核心能力的建设,引入共同利益观,强化《国际卫生条例》的“遵约引力”,完善PHEIC启动机制,缓解国家利益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冲突。《国际卫生条例》也应不断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态势相融合,革新治理观念与治理手段,以期在未来能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经过此次新冠疫情的考验,各国及国际组织更应正视《国际卫生条例》的地位与作用,共同保障《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
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WHO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主要的法律框架还略显单薄。 在传染病防控领域,除了《国际卫生条例》《国际疾病分类法》外, 仅以一些建议、 技术指南、 标准等软法作为内容和效力上的补充, 形成了“硬法为主, 软法为辅”的治理模式。 在后疫情时代下, 我们依然需要重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的挑战, 充分认识到国际法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为有效的治理手段之一。 因此, WHO应当积极联合各方力量, 通过完善《国际卫生条例》、 建立规范化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流程为起点, 不断建立完善制度化的国际卫生法律体系, 构筑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法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