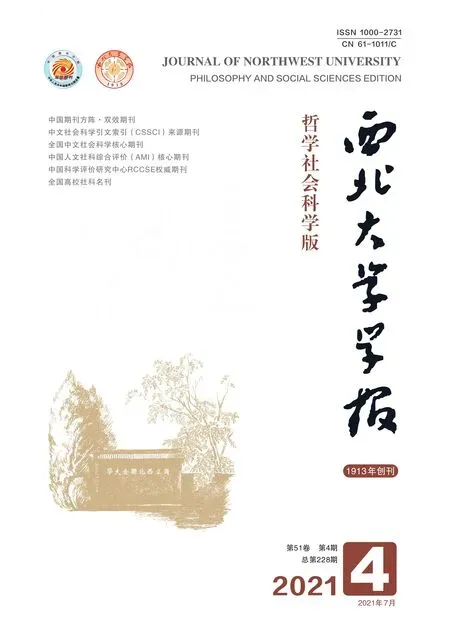中国现代作家的延安道路
——以何其芳延安去留为考察视角
周思辉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1938年8月,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夫妇一起奔赴延安,目的是经过延安到战地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起初三人都没有长期留在延安的计划。初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严重缺乏教员,周扬就邀请何其芳与沙汀在鲁艺文学系任教。何其芳答应得非常爽快,这一点令沙汀都有点惊讶。据沙汀回忆,何其芳到鲁艺任教之后,对人诚恳、爽直,对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在鲁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赞扬,因而不久院部的党组织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按照预定计划,何其芳与沙汀一道向毛泽东请示,说想经过延安到前方去,到华北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得到毛泽东“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的肯定。随后,他和沙汀于1938年11月与鲁艺部分同学一起随贺龙部奔赴前线。1939年7月,何其芳与沙汀返回延安,对于这次前线之行他认为是“失败”的,无论是从写报告文学的角度,还是与广大官兵结合的角度,但是他最终还是留在了延安,后曾写诗《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见《夜歌》1945年初版),多少流露出留在延安的一些苦衷。卞之琳是1939年8月中旬离开延安的,1939年11月中旬,沙汀不顾周扬的一再挽留而决意离开。至此,何其芳、卞之琳、沙汀一起延安之行的三人,只剩下何其芳一人留在延安,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一、“万一情形不好,就还是要回到后方来”
何其芳当初计划奔赴延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决定要留在延安。194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何其芳在重庆曾家岩50号会见熊道光。在交谈中,何其芳告诉熊道光,1938年秋他和沙汀、卞之琳一起去延安,原计划是经过延安到抗战前线去搜集资料,准备写报告文学,“万一情形不好,就还是要回到后方来”[1]20。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给自己是留有后路的,并没有放弃在成都成属联中的教职,以备从延安归来继续在成都任教。何其芳的这个打算并不奇怪,他去延安但对延安的看法是有保留意见的,有两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其芳的这种心态。
(一)追求“批评的自由”
1940年5月8日,何其芳写作《一个平常的故事》一文,文中说他想通过延安去华北战场,并没有想到要接受延安的教育。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夫妇计划经过川陕公路奔赴延安。出发伊始,坐在颠簸的行驶在川陕公路的汽车上,何其芳在对延安向往的憧憬中竟想起倍纳德·萧离开苏联时说过的一句话:
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2]110
何其芳想到倍纳德·萧离开苏联时说的这句话,表明他对延安还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何其芳曾经是京派文人,追求的是独立自由思想。贝纳德·萧之所以在离开苏联时说这句话,是他在苏联看到了一些弊端。延安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苏联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何其芳在到达延安前还在想着这句话,说明在他的预期中,延安或许会有某些自己看不惯的东西。这个细节与他说出“万一情形不好,就还是要回到后方来”这句话,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出现何其芳这句话的《一个平常的故事》这篇散文的写作,已经距他1938年8月中旬辗转赴延安近两年时间了,他的思想已经发生变化。何其芳说他到延安后才发现,这里充满了感动,他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自己而非延安。为表达这种无法掩饰的喜悦,他写下传颂一时的名文《我歌唱延安》,以表示对曾经有想批评延安的想法的悔意。但这些都是何其芳到延安思想转变后,在到延安之前他是要保留自由批评的权利的。
(二)“共产党可敬佩”“很近人情”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的回忆文章《人情》。据他回忆,在1938年秋他刚到延安时,去参加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欢送会。这个小型宴会是为了给一个即将去晋东南前线工作的作家饯行,他的妻子在延安,这次他因公回来。不久还要再去,他的妻子也决定调到那边工作,并和他一道出发。席间谈到此事,相熟的朋友还开这个作家的玩笑。但这时有一个老革命家突然严肃地说,人家都以为我们共产党不近人情,其实我们很近人情。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让夫妇在一个地方工作,不使他们分开。这几句话给何其芳很深的印象,何其芳说:
大概由于受了别人的宣传的影响,我过去刚好就是一个以为共产党虽很可敬佩,却不一定可亲的人。到延安以后,许多事实修正了我这种想法。而这位老革命家的话恰当其时地打动了我。[3]170
这段话有两点信息很重要:一是何其芳在踏上延安土地之前,对党的印象是虽“很可敬佩”,却“不一定可亲”,与共产党在心理上还是有距离的;二是何其芳思想在发生着变化,这位老革命家的话提醒了他,加快了他思想转变的进程,这也成为他留在延安的一个因素。这个细节也可以隐微地表明他为什么当初并没有完全决定一定留在延安。
(三)卞之琳与沙汀的短暂停留
与何其芳一同由成都到延安的卞之琳、沙汀也没有长期留在延安的打算。张曼仪认为卞之琳在国家积弱难返、国民党又消极抗日的情况之下,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大都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出于爱国之心倾向延安,加上好友何其芳向他透露访问延安和前线的心意,卞之琳遂为之所动,也想去看看,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一下,所以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知识性的探求[4]65;另一点是私人因素,当时卞之琳正在追求张充和,为向自己和私心倾慕的人证明他有凌云之志,不是“轻云不解化龙蛇,只贴鬓凝成珠饰”,所以接受了这个精神和体魄上的考验。也因此,何其芳抵达延安后最终留下,卞之琳却在一年后坚持“按原定计划”,以有“后顾之忧”为理由,决意离开延安[4]65。这其实是说卞之琳在启程赴延安之前就计划只是在延安短暂停留。
卞之琳在1988年9月底写的《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中说:“《工作》出了八期就宣告休刊。主要是因为其芳和我,跟沙汀夫妇(留下周文在成都)悄悄前往延安访问,最初其芳和我都主要企图转往前方随军,‘孟夫子’当然知道;他也知道我个人还有私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不过出去转一下接受考验而已。”[5]沙汀也不准备长期待在延安,只是想搜集资料写报告文学。据沙汀回忆:“可以说是出乎意外。我同何其芳、卞之琳两位到延安,原是希望从延安转赴华北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一本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6]78由此可见,二人的原初计划中确实没有留在延安的打算。后沙汀、卞之琳分别于1939年8月中旬和11月中旬相继离开延安,唯独何其芳留在了延安。很明显,何其芳最终留在延安是有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二、延安时期的思想转变
何其芳之所以没有像卞之琳、沙汀那样离开延安返回大西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思想发生了转变。何其芳在1929年至1931年上半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不喜欢嚣张的事物”,要远离“肮脏的政治”,“想做一个渺小的人”。1931年下半年至1935年大学期间信奉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是为个人而艺术)的思想,追求唯美主义,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沉迷于“梦中道路”。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师范教书,在“时代的苦闷”与“个人的苦闷”现实的残酷逼仄下,他开始走出“梦中道路”,关心现实和政治,以致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来干预现实。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何其芳回到成都,他在思想上进一步嬗变,越来越倾向现实主义,并对革命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但何其芳去延安前想保留自由批评的权利,并感觉中国共产党可敬不一定可亲,但与此同时,何其芳的思想已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很多研何人员都忽略了何其芳去延安前对纪德的态度,这一点卞之琳在《何其芳与工作》一文中有披露。卞之琳说,何其芳是他们合办的《工作》半月刊的主力,每期都有文章发表,而且文风已经和《还乡杂记》不同,相比“画梦录”式唯美感伤的散文已经来了一个初步的突变。而卞自己除在开头发表过一篇小文《新的粮食译前话》外,其他每期都在《工作》上发表自己翻译纪德的《新的粮食》。就在这时,何其芳与卞之琳关于纪德的态度产生了差异。
(一)何其芳对纪德态度的转变
纪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思想发生转变一度左倾,此时他发表的《新的粮食》也成为他左倾的标志,但他之后又发表了《苏联归来》,思想又转向右倾。进步人士以此为由攻击纪德,说其左倾之后又发生“转向”。卞之琳对纪德的言行抱基本认同与同情的态度,他说:“纪德发表《新的粮食》是他在30年代中叶举世瞩目的一度思想左倾的标志,虽然他不久又发表了《苏联回来》,引起进步人士群起攻击为再‘转向’,我认为,作为螺旋式发展的向上一个弧线,总是可珍惜的,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教育意义。也就因此,后来在1942年我还在陈占元主持的桂林明日社出版了这个译本的全部,并附我写的较长的序文。”[7]而何其芳并不完全认可纪德的行为。卞之琳认为,何其芳与他不同的文风和作风也就预示了1938年他们一块去延安,目的尽管一致,但何其芳最终留了下来,而自己则按照“原定”计划返回(原定暂回)“西南大后方”[7]。
纪德在思想上左倾后,当时的苏联是走左倾路线的代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红色30年代的背景下,他一度对苏联模式非常着迷,因此他怀着向往去苏联实地考察,但考察的结果与其期待偏差很大。苏联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弊端纪德认为相当严重,他从苏联回到法国后,就写出了《苏联归来》这个并不长但有强烈批判意味的游记文章。对苏联由认同到怀疑也标志着纪德思想的再次转变。卞之琳对纪德的转变持理解态度,这也隐约表明卞之琳对延安还是有保留态度的。何其芳对纪德的这种转向再转向是不理解的,当时与卞之琳讨论时何其芳具体说了什么,《何其芳与工作》一文也没有交代。据方敬回忆,在成都时,何其芳确实与友人就纪德苏联归来等话题进行过讨论,但没有具体说何其芳的看法。方敬说何其芳“同校外知识青年书面或当面谈有关抗战、抗战文学、周作人事件、纪德从苏联归来等等问题,其芳也是很热心的。”[8]77首先,何其芳对纪德的这种转向尽管不理解,但并未完全否定,这可以从他在川陕公路上还引用倍纳德·萧的话看出。倍纳德·萧不也是离开苏联时说要尊重自己批评自由的权利吗?纪德写《苏联归来》观点是可以商榷,这是他的自由。从这一点看,何其芳对纪德转向再转向不理解,但也没有彻底否定。其次,正是有这种不理解作基础,又在延安生活一段时间后,何其芳的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从而彻底否定了纪德。他在延安生活一段时间后写了散文《论快乐》,文中很直接地批评了纪德,他说:
《从苏联回来》的作者纪德却就不理解这点道理。在他那本出名的坏书里面,他很惊讶在今日的苏联,在他所旅行着的苏联,杜斯退益夫斯基已经没有了多少读者。他甚至于怀疑这并不是由于人民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在加以某种禁止和限制。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在还正经历着分娩的痛苦的中国,杜斯退益夫斯基已经和我们隔得相当辽远了。[9]114
何其芳尽管只列举了纪德批判苏联的一个方面,但其反感情绪之强烈已昭然若揭,这恐怕就是卞之琳所说的作风不同。他特意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氏的“阴冷”则是何其芳“京派”时期喜欢的,这里也表明何其芳思想已经发生变化。当然,对延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对延安完全认同呢?
(二)“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
何其芳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接触真正的现实,就感觉现实无比黑暗。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故乡四川万县,继而又来到成都。尽管是国统区的大都市,成都依然看不到希望。他在1938年写作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成都充盈着“享乐”“懒惰的风气”,而且到处充满着“陈腐”“罪恶”“污秽”,总之,一片乌烟瘴气,丑陋不堪。即使行进在川陕公路上,何其芳还能看到很多自己认为极度丑恶的现象。他的《川陕路上杂记》一文就披露了国统区存在吸食鸦片、卖淫及农民因贫苦拉纤而丧命等丑恶现象,使他非常厌恶。
何其芳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在赴延安途中,同行的沙汀就发现他对中国的旧社会了解甚少,思想近乎单纯。沙汀回忆,在路上何其芳看到一些商人在栈房里玩弄女性的丑恶行为竟然使得他那样大惊小怪[10]2。的确,何其芳在《川陕路上杂记》中详细描述了商人同陪烧烟的女子讨价还价的过程,并说这些商人有着“成人的正经的脸”,这种行为令他感到震惊。其实对于国统区的黑暗,何其芳早在抗战前写作于山东莱阳的《还乡杂记》等散文中就有详细的描写,对他来说国统区的黑暗已经恶劣到极点,只是之前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知,而这时却看到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延安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可以从欧阳山到延安后的生活体验先感受一下延安与国统区的不同。欧阳山在《我的文学生活》中说,在延安,旧社会里的那种互相倾轧、互相嘲笑、互相诋毁以及酗酒、赌博、盗窃、纵欲、争吵、咒骂、欺诈、殴打等等现象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尽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诸如像封建、迷信、贫穷、落后、缺乏文化等等,都不会马上消失,但是都在逐步克服之中。农民都是新型的农民,对他来说,延安的社会和人民都是陌生的,看不到他过去熟悉的那些被命运颠弄的不幸者,也听不到人们嘴里发出哀叹和悲伤,也没有发现任何或大或小的悲剧[11]68-69。
这种在延安感受到的惊喜,何其芳表现得更为强烈。到延安两个多月后,何其芳写下《我歌唱延安》。关于这篇文章,何其芳说他是带着一脑子原有的思想与个人愿望来到延安,延安的自由、宽大和快乐,对于他这样一个从旧世界来的受够了压抑的青年来说,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这和欧阳山的感触几乎一致。于是他在激动中写下《我歌唱延安》。何其芳在文中充满喜悦地说,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快活的,这里没有失业、失学的现象,更没有乞丐、妓女。延安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物尽其力,人尽其才”,而且不加限制。抗大等院校即使已经招满,但对络绎不绝前来报名的青年也不加拒绝。尽管延安还有些困难,但对他而言,那都是很微小的缺陷。何其芳大声说:“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12]1938年11月16日夜何其芳在延安创作的《我歌唱延安》,在1945年群益初版的《星火集》中被抽掉了,何其芳在1949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星火集》三版后记二中说:“这个集子的第一版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由群益出版社在重庆印行的。那时出版社震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审查制度的余威,把其中《我歌唱延安》和《论对待文学的态度》两篇自动抽掉了。”[13]178在《星火集》三版中,何其芳将《我歌唱延安》重新收入,而这篇对延安歌颂与赞美的文章,表露了何其芳在延安见到不同景象的喜悦,也透露了留在延安的一些原因。总之,在延安的光明与国统区的黑暗强烈对比中,何其芳对延安由“保留批评的权利”转变为热烈的拥护了。
(三)从孤立到认同
何其芳在抗战前创作的《云》中,就大声说自己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并要以实际工作来介入现实,所以他积极与卞之琳等创办《工作》半月刊,并每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非常热心地与黑暗做着抗争。但是,因为“周作人事件”使自己孤立,在“小圈子”里待不下去了,就有了去延安的想法。何其芳在《星火集》后记中说,《星火集》第一辑里的杂文是他1938年在成都时写的,因那时不懂得深入群众并与社会力量合作,因之在一个小圈子里很快就感到了孤立。成了这样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支苦战了十余年的大军[14]199-200。
这篇后记写于1945年1月7日,此时的何其芳已身在延安。何其芳所说的“小圈子”,主要指的是聚集在《工作》半月刊的创办者和撰稿人。何其芳在“小圈子”里被孤立与他参与“周作人事件”的论争有关。抗战全面爆发后,平津沦陷,文人纷纷南下,朱光潜、沈从文等“京派”文人大都离开北平,而周作人却以种种理由留了下来准备“苦住”。1938年2月9日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周作人出席,会后《每日新闻》发布相关报道及照片,照片上周作人清晰在列,而且刊有周作人的发言。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引发外界对其是否附逆的猜测,称为“周作人事件”。何其芳对周作人的消息十分关心,并且迅速做出反应。1938年5月16日,他在《工作》半月刊第5期发表《论周作人事件》抨击周作人。将周作人直接视为“文化汉奸”“面见颜附逆”,认为周作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并不是怎样可骇异的,因为这不是偶然的失足,也不是奇突的变节,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何其芳的观点立刻遭到他所在“小圈子”核心人物朱光潜的批评。朱光潜发表《再论周作人事件》认为周作人往好说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往坏讲是一个“老于世故怕沾惹是非者”,“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和勇气,明知会被利用,还执意留平是不明智的。尽管留在北平的原因很多,但说其留平是为了准备当汉奸那是近于“捕风捉影”。朱光潜是极力为周作人辩护的,并不讳言对何其芳的不满。对于朱光潜的辩论,何其芳并不认同。他在1938年6月4日写给友人的《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中对朱光潜进行了反驳。何其芳这次在“周作人事件”中过激的表现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除师辈朱光潜外,就连“小圈子”里的同辈也对他不满,如卞之琳。卞之琳与何其芳关系紧密,同为“京派”年轻成员,而且非常理解何其芳。即使这样,卞之琳对“周作人事件”当时也提出要慎重,不要过早地下断语。即使是“小圈子”之外,批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同属“京派”年轻一代的萧乾因他发表《论周作人事件》,特意在外地给他去一信,信中说:“我假若要写抗战对于作者们的影响,一定要举你为例子。你看,《画梦录》的作者也写出这种文章来了。”[15]也是因这篇文章,徐中玉发表了一篇何其芳认为古怪苛刻的书评,意在指责何其芳:“你既然做过梦,就不应该醒来!”[15]何其芳认为在“周作人事件”论争中所遭受的批评,都是片面的,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遭受这种指责他更是不满。但因为参与论争,何其芳被孤立了,也就是他所说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很快就感到了孤立”。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详细讲到了这段经历,他说在成都:
当我的笔碰触到那个在北平参加“更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他老早就劝我不要写杂文,还是写“正经的创作”,而且因为我不接受,他后来便嘲笑我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在这时竟根据我那篇文章断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14]108
与在成都这种孤立相比,何其芳到达延安后,他感受到了延安的热情。且不说受到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一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缺教师,学院负责人就邀请他和沙汀留下教书。沙汀想尽快去前线,但推脱不得,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沙汀都感到惊讶[16]3。这也说明何其芳迫切想参加实际工作。
何其芳由前线返回延安后,接任鲁艺文学系系主任,这是进一步受到重视的表现,何其芳欣然领命。后何其芳向熊道光说,自己刚到边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很需要教员,自己被留在鲁艺教诗歌。他一开始工作就感到环境非常宽松自由,工作学习没有任何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努力工作的人,都会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不问他人事关系如何。他在鲁艺从普通教员到成为系主任,就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而且受到尊重,何其芳感到非常的欣慰[1]20。何其芳曾经多次提到自己的孤独感,说自己遗弃了人群又被人群所遗弃,让他痛苦不堪,感觉几乎与死亡接近。何其芳在延安却找到了集体的温暖,这种孤独感随着融入延安的集体生活而得到缓解。何其芳又说他来到延安并经过前线的阅历,自己不断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15]。曹万生在《孤独·爱情·死亡——郁达夫何其芳早期创作主体意识之比较》一文中认为何其芳在自我探索的痛苦历程中,在延安投身到工农兵去,这种个人与群体协调了,个体当然就不会感到孤独,可以说何其芳创作主体意识在延安实现了对现实自身的认同[17]280。何其芳从前线返回延安之后,即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这是组织上对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何其芳的进一步肯定。再加上,尽管成都的工作没有辞去以备退路,但那个圈子自己已经因为“周作人事件”被孤立。他当初如果返回,迎接他的依然是这个圈子。相比延安自己受尊重,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体现,留在延安的想法自然会占上风。卞之琳之所以想回成都,因为那个由朱光潜、罗念生等组成的“小圈子”与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和融洽的。
综上,何其芳之所以在从前线返回延安后,没有像沙汀、卞之琳一样立刻离开延安,与其思想转变的关联性很强。单纯的何其芳在切实感受到延安的自由与温暖后,觉得与国统区自己看到的黑暗现实及所受的冷遇完全不同,所以决定留下并不为奇。黄药眠曾经对何其芳走向延安参加革命有一个评价很是恰当。黄说何其芳以单纯的心情走向革命,把极端复杂的革命单纯化,还未十分认识革命以前,就已经很天真地向革命掏出了他自己赤子似的心肠了[18],所以当看到解放区另一番纯洁性的景象,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象牙塔”纯洁的生活。留在延安,或许就是何其芳向革命掏出赤子似的心肠的一种有力佐证吧。
三、文艺观与延安爱情
何其芳之所以留在延安,跟他的创作有重要关系。何其芳一行本来就是要经过延安去前线搜集资料写报告文学,但写报告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顺利,在他看来自己写作报告文学的目的是“失败”的。
(一)作为对比的沙汀、卞之琳
沙汀、卞之琳离开的原因上文中尽管说二人都没打算长期留在延安,但真正离开的原因,还是另有隐情。沙汀、卞之琳感觉在延安进行文学创作受到了限制。沙汀是以写作讽刺小说著称的,讽刺是其文学创作熟悉并深爱的写法。讽刺就要暴露黑暗,而延安的环境是不适合大规模暴露黑暗的。尽管当时“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的争论还没有达到白热化,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沙汀已经闻到了某些气息。而且沙汀在随一二○师辗转前线的过程中,看到了老百姓落后的一面,所以执意返回四川国统区老家也主要是出于对自己创作的负责。吴福辉说:“他是以不相信妻子会来为理由的。一直到离开冀中,他还不敢正视自己,不敢把留恋故乡的人物,乡土中存在着他的创作生命,做为一个正当理由提出来。这在当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妻子长期被他,也被别人当作一个理由,来掩盖了潜在的真正的原因。”[18]322沙汀离开延安的原因,吴福辉在《沙汀传》中说:“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没有当场点破。”“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19]505-506其实,沙汀为了写关于贺龙的传记,在随军途中与贺龙有过密切的接触,后鲁艺的学生执意离开前线返回延安,贺龙对此非常反感,当时带队的就是沙汀和何其芳。贺龙也深知沙、何也是想离开前线,其中因缘他自然了解,这时贺龙关于沙汀离开的解释,确实是为了给沙汀解围,而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
卞之琳离开延安,除爱情的原因外,能否保持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是其考量延安去留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卞之琳与何其芳一样,之前与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等京派文人关系密切,他们二人就成为京派文人中的年轻一代。在文学创作风格上有浓重的京派风格,追求文学的唯美性、艺术性,刻意疏远现实政治,强调文学的艺术独立性,以致有强烈的追求“趣味主义”的倾向,当然这一倾向在京派文人中具有普遍性。沈从文说:“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我觉得是可惜的。……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20]148这可以看出沈从文尽管不认同周作人等“趣味的相同”,但也点出了周作人等具有的“趣味主义”创作特征。作为“老京派”的周作人就曾经是“趣味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他的弟子废名。废名对年轻的京派卞之琳与何其芳等影响很大,卞、何二人早期创作风格与周作人、废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何其芳一道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芦焚,与京派文人非常熟悉,他就曾评价卞之琳是“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义者”[21]156。这种“趣味主义者”意指尽管芦焚没有展开,但很清楚意在表明卞之琳有京派追求的“趣味”。延安是革命圣地,有着浓郁的追求现实革命的氛围,对于文学的创作要求与之前卞之琳所处语境是不同的。卞之琳当时就意识到,自己如果按照以前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进行创作是不可行的。卞之琳创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是在行军途中起步的,他说:“想想过去,我忽然想起了也有关这本小书的一点情况。”“同道中不记得谁善意要我警惕过‘趣味主义’。我接受劝告”。[22]380-381从这个细节似乎可以看出,在创作上卞之琳以前熟悉并坚守的“趣味主义”在当时的延安是不适合的。他最终离开延安或许跟他感觉延安的文学创作语境自己不能适应有关。如果从卞之琳离开延安后的整体创作看,追求艺术至上文风的延续,也能看出他对文学性的坚持,执意离开延安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沙汀、卞之琳离开延安最大的原因就是想坚守自己熟悉的文学创作风格,何其芳也并不想完全放弃以前的唯美主义创作方式,但他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现实社会后就开始尝试转变,想关注现实、干预现实,他走向延安就是最好的佐证。他和卞之琳、沙汀同样感到延安的创作环境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自己的创作肯定会受到束缚和影响,他选择留下,是因为期待,延安当时的语境给了他想转变创作介入现实的想象与希望。尽管在之后的延安道路上充满挫折困惑,甚至写出《叹息三章》这种情绪矛盾暗淡的作品,但他对延安文艺主流思想他是认同的,而且在延安受到了文人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程度。作为一名诗人,曾经反复想象咏叹过无数次的爱情,也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萌芽、生发直至结出硕果,这些因素的叠加给何其芳留在延安创造了更多条件。
(二)文艺服务抗战文艺思想的认同
何其芳作为一个唯美主义作家,暴露黑暗、鞭挞丑恶现实的做法本不是其所追求的。但在创作上,何其芳抗战后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论工作》中就表露了将文艺作为抗战武器的想法。他对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在抗战中应该怎么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抗战背景下,务实的抗战与虚幻的文学创作两者之间要作取舍,何其芳选择宁愿放弃后者也要选择前者。而如果相反,何其芳说我们的手里还没有另外的武器来代替之前,仍然不必放弃文学工作,应该更勤苦更热情地负起抗战中的文学工作的责任,要热烈地关心战争,关心着在战争中的人群,而且尽量地为时代尽他个人的力[23]5-6。这里已经暴露出何其芳认同文学服从政治的倾向。何其芳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了毛泽东给路社的回信。何其芳等刚到鲁艺不久,鲁艺文学系成立了一文艺社团,名叫“路社”,因为同学要出板报,就给毛泽东写信请其给以指导,毛泽东热情回信,要求内容要“反映人民称号和写抗日的现实斗争”。在信中毛泽东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24]386-387。据沙汀回忆,周扬还向他和何其芳说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文艺是团结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服务,要到现实斗争中去学习[6]80。将文艺作为武器服务抗战,这种思想和何其芳转变后的文学观刚好吻合。所以何其芳到延安后,面对文学创作中政治性要高于艺术性的要求是有心理准备的。何其芳既然已经放弃了唯美主义创作的方法,出于文学创作的原因而离开在何其芳这里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但有一点应该引起重视,何其芳曾经是极端的唯美主义作家,是逃避现实的,对美是极端渴望的。尽管抗战的大背景使他开始关注现实,但其思想中还是希望能发掘美的东西以给其生活希望。延安的美好的一面刚好契合了他的心理预期,所以后来他执意成为歌颂光明的一派,原因也就在这里。何其芳因为思想转变和创作的原因,最终留在延安,但并不是说其内心是平静的,相反,同行的卞之琳、沙汀的离开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使他更加矛盾、彷徨和忧郁[25]112。即使这样,何其芳直到1944年3月被延安派去重庆宣讲《讲话》才短暂地离开延安,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再没有过离开延安的打算呢?这或许与他的爱情有关。
(三)延安爱情
何其芳留在延安还有一层是出于爱情。沙汀、卞之琳离开延安都有爱情的因素。沙汀说他在延安完成《记贺龙》后,就离开了延安返回四川,原因是“因为黄玉颀病了,又想念留在国统区的老母幼子,我就离开了延安,前去重庆,编辑主要由鲁艺供稿的《文艺战线》”[6]82。黄玉颀并非沙汀原配,而是沙汀与李增峨已婚期间结识并相爱的,对沙汀来说,黄玉颀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这是吴福辉从沙汀《安县县党部之后》中摘录的[19]124。沙汀非常珍惜这份超乎伦理之上的爱情,所以当沙汀要去延安,黄玉颀也要随同,尽管犹豫还是带上了黄玉颀。在《沙汀日记》中,多处记载沙汀在前线120师期间对黄玉颀的想念,黄玉颀想回四川,沙汀出于对黄玉颀的爱,愿意与她一道返回老家也在情理之中。卞之琳说:“在1937年春末,是另一种情况;我与友好中特殊的这一位感情上达到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耍弄禅悟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皆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26]可见,沙、卞离开延安确实与爱情有关。
何其芳就不同了,在赴延安之前除那次与表姐杨应瑞在1931年春前后失败的恋爱外,尽管他一直对爱情充满渴望,但并没有再真正恋爱,所以他在感情这方面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相反,在整风以前的延安自由的环境里,何其芳尝到了爱情的甜蜜。经过几次恋爱后,何其芳最终与鲁艺文学系第3期学员牟决鸣在1942年7月结婚。至此,折磨了何其芳“十年”的爱情算是尘埃落定。从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一刻起,延安给予了何其芳追求爱情的希望,并最终成全了何其芳,恋爱的过程和圆满的结果自然是他不愿意离开延安的原因。
何其芳最终留在延安,与他的思想转变和特殊的经历有关,在“京派”文人与延安的关系中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后,大批的延安文人也包括国统区左翼作家都面临着转变问题。何其芳却转变的更为纯粹,他按照《讲话》和整风运动精神彻底“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不仅从思想上反省自己,而且在创作上作出重大转向,放弃个人抒情性的写作。他的思想与创作的重大改变成为改造的典型,也是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特殊的一位。巴金说他始终认为何其芳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并“始终保持着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27]16。在延安时与何其芳非常熟悉的陈荒煤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每个人的思想当然都有进步和变化,但是,“我感到其芳的变化很大”[28]54。陈荒煤的惊讶也反映了何其芳的转变不同于延安一般的知识分子。鲁艺学生岳瑟对何其芳的转变有一个评价,颇具有代表性,他说:“近些年,有人说何其芳是‘一个人格世界的两面性’,表现出‘时代整体盲目、愚昧的烙印’,似乎另有一个说假话的何其芳。可惜他不能自己出来抗辩了。就我个人的浅见,何其芳始终是一个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谎骗的革命文学家,他的作品,是他个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斗争的历程的真实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个人’,本身就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品格。”[29]237何其芳由一名唯美主义作家转变到革命作家,确实是“当代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斗争的历程的真实反映”,他“这个人”也确实“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品格”。总之,何其芳的延安去留对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延安道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