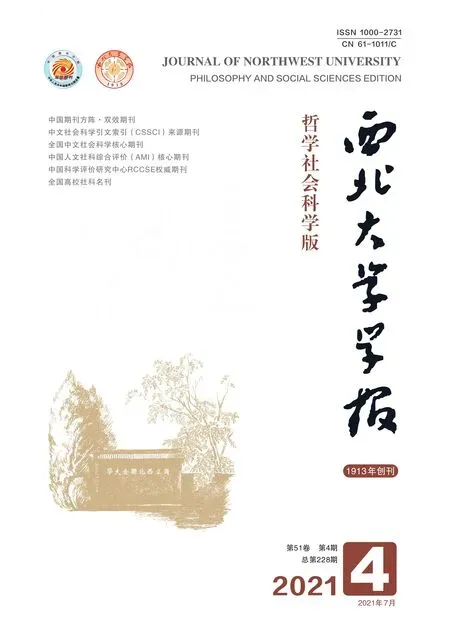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关系的“延异”问题
曹若男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研究永远都是文学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主题,学者们也总是惊讶于发现莎剧人物与真实人物的距离之近:莎士比亚式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活脱脱就是生活当中你我他在文字中的镜像。莎翁悲剧人物特色鲜明,戏剧化手法呈现出的却是感同身受的写实悲情[1];莎翁用自己的创作遐思细致入微地勾勒着最真实的人和人性[2];莎翁笔下的人物早已脱离纯粹的文本空间,他们跃然纸上,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人[3]。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物的书写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思可能,这些人物色彩鲜明、交相辉映,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存在,他们相互验证着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后现代文学评论家们对莎剧人物的研究一直走在多元开放的道路中,其间让我们不断重读莎作,体会着创造性的认知空间和思想智慧。本文将基于解构主义视角,借用德里达的延异观来解读莎翁戏剧对人物关系的不确定性叙写和独特关照,貌似稳固和常态的人际纽带在莎翁笔下饱含异变的危机,时而被改写、时而被颠覆;读者对作品的体味可以在延滞的过程中感知差异,寻访溯源,如此交相往复的互动是我们走入莎翁巨作的一种方式。
一、延异的客体身份和远距生成
“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用以阐述其解构思想的重要突破口。德里达把法文词différence中的第二个e巧妙地改变为a,由此诞生出一个全新的法语单词différance;可是,由于法语本身的发音规则所致,原有字母e和现有字母a的发音却一模一样,如此同音异形的创设彰显了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的彻底解构,而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思维传统由此被颠覆。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倡导一种固定意义的永恒存在,而解构主义概念下的延异则表示延缓的、延宕的差异,代表了意义无休止的消解状态。
(一)“延异”客体身份下的文本消散
在德里达眼中,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审视应当持有“去中心”的态度,文本意义永远是散播的、不确定的,是动态地贯穿于延缓和消解的过程中。对文本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去传送一个个思想讯息,而是包含有多重的冲突,用冲突之间的层次和延宕去输出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视域中可能被无意遗忘,或者被有意克制。“延异”不是简单地去消除二元对立,它表达的是一种对源初状态的不懈追求;由于事物的发展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延异”则指涉产生不同事物之间差异的溯源,也表示构建不同事物之间差异的过程[4]。对于差异的诠释,结构主义者宣称因为事物之间存在差异,故而产生意义;而德里达所创设的“延异”一词则表达出“原则之原则[4]”的存在,它“延缓了我们邂逅事物本身的那一刻[4]”。
德里达主张走入文本深处,找寻文本中的关系冲突和叙事张力的源头,在此过程中,文本意义随之逐步消散,但绝不是不假思索和未经辩证的消亡,是一种意义突变,由此我们可以挖掘文本意义的不连贯性,以及对叙事空间进行仿拟,颠覆原本存在的一系列固定不变的意义符号。用“延异”去细读文本和追寻意义,其价值性体现在“延异”的非静止和非在场的特质;在这个过程中,新意会不断涌动而出,而我们也在享受不停歇地追逐文本意义变化的快乐。德里达给出的“延异”解读使其占据了绝对的客体地位,“延异”具备一种不在场的,应当被推崇的绝对客体身份;同时,他又给“延异”贴上了一个“虚无”(nothingness)的标签,因为“延异”绝不是一个新创造的霸权符号。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明确界定过“能指”和“所指”的内容,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过说明,即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5]”;可在德里达看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亦是临时的,差异不会因为语词作为媒介进行描述而消失,语词对差异的描述甚至会将其无限放大,甚至颠覆。正因为虚无而非符号,“延异”总是拒主体于千里之外,它坚决对抗任何“总体化”(totalization)的企图,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就是对所谓的“绝对真理”的话语权威进行正面攻击,他用自己的学说去批判和颠覆所有的“虚假性”(inauthenticity)。“延异”对主体永远质疑的态度告诉我们应当深省自我认知中的盲目和错误,当“延异”消解了文本的固定意义之后,不断的改写和重构就成为可能,实际上则表达了人们对无穷尽意义的渴求和追寻。
(二)“延异”远距生成中的文本反哺
德里达用“延异”质疑文学批评中的一切可能性,可由于“延异”的特殊存在,一切可能的结论在迷离和消散之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远距生成”(teleopoiesis)概念的提出似乎是德里达给出的一份答案。“远距生成”的思考站位是他性,是拉开距离重新审视一切的不可能,既可以是对主体性的另一种重拾,也可以是一种负责任的道德场域,亦或是一种阅读伦理。与其他后现代哲学家解构思路有所不同,德里达所谓的“延异”先拆解再重构,他对自我的评价则是一位建筑师[6],他眼中的文学批评家就好比工匠——他们具有杰出的工匠精神且独具匠心,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拆分原有结构,而后就地重建,利用拆解下来的原材料构建焕然一新的事物[7]。
“远距生成”被德里达判定为一个通路, 带上对现实的批判, 走向未知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懈探索、 不断质疑、 不停抉择, 这是一种终极的、 无畏无惧的发现精神。 笛卡尔对世界的质疑是其“我思故我在”的表达, 德里达认为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体现在“延异”的缓存与若昧状态中, 无限种可能不会被复制和加工, 人类在不断的颠覆和创造中前行, 这需要一种全情投入的态度和不假思索的献身。 正因为德里达所定义的“远距生成”意指时空的不同所带来的未知力量, 文学的遐思空间由此就变为一个动态发展的、 怀抱一切可能的生命空间。 “延异”对文本的反哺功能让我们深刻感知到, 德里达将人类的主观意志发挥到了极致, 它甚至变为一种永恒的发生状态, 可必须强调的是, 其内在固有的差异性不可能被完全根除, 所以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 就好像潺潺溪水一般流淌, 可是流动的方向却是无尽的循环。
“延异”自身的解构功能使它拉开了认知和感受的距离,斯皮瓦克以调侃的口吻解读德里达的“远距生成”,认为在星球化的时代,自我想象的绝佳状态应当是被他者想象——“这是想象你自身,而其实是让你放弃安全防护,让你自身通过另一种文化,在另一文化中被想象(就是经历那种不可能性)[8]”。德里达为我们架构的是未来的“诗性时空”,他的延异观将我们带向充满着无穷尽可能的遥远世界,这是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更是一种姿态和胸怀,所有事物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解构。“延异”通过“远距生成”的视角,积极对峙一切符号化的意愿,由此它才是最真实的存在(The Real),它透过无尽的虚空(Void)质疑一切符号的中心地位,从旁观者的姿态轻松介入,消解一切意识上的霸权,对“诗性智慧”的追寻成为多种关系博弈的终极诉求,而对文本的反哺在这个假定时空中充满着肆意的挑战和冲动的游戏。
二、莎剧人物关系的延异思考
莎翁一生代表作众多,为前赴后继的学者们着迷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人物才可以被贴上莎士比亚式人物的标签?无可否认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无论何时重读,都不是形单影只,他/她一定身处在一种关系联结中;就某一个主要人物而言,他/她身边的某一具体关系可能时而牢固、时而悬搁、时而断裂。当牢固时,主人公具有清晰的自我关照,他们透过这层关系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剖析,在自我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行为的准确判断和掌控;当悬搁时,他们纠结、彷徨、无措,遭受各种力量的羁绊和巨大的精神困扰;当断裂时,迷惘徘徊的主人公往往迅速坠入未知的深谷,他们在放弃关系对方的同时,实际上也决然放弃了原有的自己。
美国剧作家Dan Decker(1998)在自己建构的戏剧理论中,提出过这么一类戏剧人物形象——窗户人物(window character),意指用于诠释主要人物关怀和界定主要人物身份的他者人物。“窗户人物”用来投射和反映主要人物的变化,建构巧妙的“窗户人物”可以出现在剧本的第一页,也可以在最后一页,他们自始至终地存在于主要人物的发展历程中[9]。在莎士比亚戏剧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William Flesch对“窗户人物”的提法高度褒扬,甚至认为这类人物的存在解读方式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物批评研究具有极度深刻的穿透力。“窗户人物”和传统上定义戏剧中的“心腹或密友”(confidant)式的人物存在功能上的类似。“心腹或密友”往往是戏剧主人公倾诉的对象,他们是主人公最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剧作家利用“心腹或密友”间接传达主人公的心声。可是“窗户人物”却不等同于“心腹或密友”,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呈现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紧紧锁住了主要人物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判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在挑选自己的“窗户人物”时,不仅仅是一种方式的表达,更是主要人物自身主体性的递送[10]。基于“窗户人物”的介入,莎剧人物关系的延异思考才更具讨论意义。
(一)历史剧《亨利四世》中人物关系的往复和抉择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一部历史剧,分为上、下两篇,故事连贯、人物饱满。剧中莎士比亚突破传统思维书写,在整部作品中以两条主线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地描绘着亨利四世(Henry IV)的帝王空间和福斯塔夫(Falstaff)的糜烂世界。亨利四世原本只是王室旁系,并没有合法的继位权力,他推翻昏聩无能的上任君主理查二世,但即位后却也时常为自己弑君篡位的过往而心怀愧疚。更加困心的是自己给予厚望的儿子哈尔(Hal)终日和贵族福斯塔夫厮混在一起,无所事事,恣意妄为。
在《亨利四世》的上篇中,我们透过福斯塔夫这个封建贵族寄生虫形象的“窗户人物”走入哈尔、感受哈尔,就好像福斯塔夫是一扇窗,向我们敞开了对哈尔王子的认知时空;哈尔全然沉溺于和福斯塔夫的交往中,他们一起放荡不羁,一起醉生梦死。而在《亨利四世》的下篇中,哈尔却在逐步摆脱福斯塔夫的干扰,勇气和担当重新回归,他甚至主动反思自己不堪的过去,后悔和福斯塔夫之间的荒唐行为。最初貌似稳固的关系在情节叙事的推移中潜伏着变化的可能,当哈尔决意放弃福斯塔夫这个所谓的朋友时,他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的自我。这种断然的放弃不是简单的关系选择,不是或是或非的二元判定,而是哈尔在认识他者的同时认识自己,透过他者眼中的自己而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在建构人物关系的过程中,哈尔的人物形象由哈尔和福斯塔夫的胶着状态而定义;在解构人物关系的过程中,哈尔的人物形象由哈尔放弃福斯塔夫的友人身份而改变;在重构人物关系的过程中,哈尔的人物形象由自身的道德和责任而转向。
亨利四世、福斯塔夫和哈尔三者之间的关系起伏是整部作品的高潮表现,与亨利四世平定叛乱、统一国家的君王之才相对应的是福斯塔夫庸碌腐朽、不思进取的蛀虫形象,哈尔与国王父亲的关系,与不良朋友的关系,都是我们解读哈尔的重要凭借,他们的关系或近或远,或疏或密,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和消散往复的人物关系中,我们咀嚼着人物的内心,体验着延异的未知。围绕哈尔所发生的人物关系是文本意义的理解要素;一个要素倘使要发挥作用或彰显意义,只有在踪迹中指涉过去的或将来的要素才能实现[11]。没有任何一个要素会先于延异,读者对莎剧人物关系的理解是在延异中进行的对踪迹的开放性探寻。哈尔的过去投射在福斯塔夫的身上,哈尔的未来则书写在对父亲的回应过程中。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主体性即是本我与他者的互生关系,本我的彰显是为了回应他者的存在;在本我与他者关系不断生成、变化、重复、改写的过程中,我们在探索关系差异的本源,在追逐文本意义的游戏空间,在寻访远距生成的视界。
《亨利四世》的创作结构貌似平行,所表达的三角关系却耐人寻味。宫廷的政治斗争和市井的放纵粗俗,上层的权谋算计和下层的插科打诨,都将焦点汇聚在了哈尔一人的身上,何去何从与其说是剧本中哈尔对关系宰制的抉择,不如说是剧本外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诗性思考,人物关系的张力始终建立在延宕的冲突与矛盾中。在戏剧上篇中是哈尔主动选择了福斯塔夫,并通过福斯塔夫去认识其他的福斯塔夫们,“我完全知道你们所有人!”[12](《亨利四世》上篇,第1幕第2场)在下篇中面对福斯塔夫的谄媚言辞,哈尔大声说出:“我不认识你,老头儿!”[12](《亨利四世》下篇,第5幕第5场)作品中此番话述转向带给读者语词延异的无限思考,对于他者的断舍离,哈尔走入了自我的颠覆,他拒绝透过福斯塔夫走进自己,决然割裂了这份关系的存在,转而迎接了父亲对自己的期待。在另一个层面,亨利四世也承载着窗户人物的功能,剧中一个主要人物和两个窗户人物的三角关系一直处于动态的往复回应中,哈尔放弃福斯塔夫这扇窗,走向了父亲的另一扇窗,这另一扇窗既是他者,更是选择,是貌似不确定中的确定,是道德和责任的远距力量。亨利四世的离世使哈尔毅然决然地终结了与福斯塔夫的纠葛,这番抉择是哈尔对自我身份界定的重复性叙写,更是对自我过去的暴力修复,对自我未来的重新诠释。我们在定义他者的同时,恰恰被他者所定义;我们对关系的抉择往往是在自我漂浮中对关系同质或异质的立场表达,而后对他者的准确回应将带离我们做出蜕变,通过重复书写来加深自我的存在。
(二)喜剧《冬天的故事》中人物关系的弥散与重拾
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Leontes)是莎士比亚后期作品《冬天的故事》中勾勒的一个专制君主,他的专制做派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对身边人物关系的肆意挥霍中,这些关系包括儿时朋友、至密爱人、骨肉血亲,以及忠诚部下。由多重关系带来的情感交织在莎翁的剧中时而弥散,时而重拾,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人物关系的延异思考耐人寻味,而这部剧中多个窗户人物的并存铺设则是对主要人物主体性表达的侧面挑衅,亦或是正面挑战。
就因为心血来潮时心生嫉妒而产生的幻想,里昂提斯就决心将儿时伙伴——波西米亚国王波利克塞尼斯(Polixenes)——置之死地,理由是他怀疑波利克塞尼斯和自己的妻子埃尔米奥娜(Hermione)有婚外恋情并孕育了生命。曾经的故友和枕边的爱人,昔日的友情和爱情,在里昂提斯一念之间就被颠覆了。莎翁笔下的里昂提斯多疑善妒、做事果决、不计后果,他与波利克塞尼斯的友谊建立在孩提时代,原本令人垂涎、坚不可摧,可是却瞬间瓦解、荡然无存。里昂提斯的满胸妒火就好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在神灵的驱使下陷入了灭顶疯狂,宛若地震的瞬间爆发或泰坦尼克号的瞬时沉没[13]。他的草率不仅彻底断绝了自己与波利克塞尼斯的兄弟之谊,更透支了拒绝执行其毒杀命令的西西里贵族卡米洛(Camillo)的衷心;善良诚实的卡米洛不愿意遵从对波利克塞尼斯的毒杀指令,毅然决定助其逃离西西里,并决心日后效力于这位波西米亚国王。此时的里昂提斯则一纸令下,派人把自己和皇后所生的女儿珀迪塔(Perdita)遗弃在波西米亚海边,就因为他臆想出的私生子身份,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便无辜受冤、命悬一线。非但如此,这个专制的国王还要眼睁睁地看着皇后接受无端且残忍的审判,他已然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幻念而不能自拔……当他自顾自地驱逐了身边的所有人时,当这些“窗户人物”都消失殆尽时,他还剩下什么呢?他又是谁呢?他扔掉了友情,抛弃了爱情,背离了亲情,无视下属的坦诚和忠心,挣脱了世间所有的情感束缚,撕裂了身边所有的关系联结,可他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张关系联结网正是他诠释这个世界的方式和内容,是他自己最真实的呈现,也是他被诠释的对象。当界定里昂提斯血肉之躯存在的身份之窗被毁于一旦时,绝望的未知凝滞了未来,差异中的变化是延异生成的思考,此时的读者倍感难以承受之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保利娜(Paulina)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西西里贵妇,保利娜为美丽善良的埃尔米奥娜鸣屈不平,为她彻头彻尾的贞洁做辩护。当保利娜强行闯入宫殿,把王后在狱中诞下的小公主——珀迪塔抱来给里昂提斯看时,“我知道她一定会来的[12]”(《冬天的故事》,第2幕第3场),里昂提斯对身边人所指的她就是保利娜。纵然面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里昂提斯也深知保利娜不会顺服于他,因为保利娜的陈情言之凿凿,是里昂提斯拒绝直视的内心恐惧;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保利娜是最有可能定义自己的、那一扇为自己最后开启的明亮之窗……甚至在埃尔米奥娜死后,保利娜仍然坚持谴责里昂提斯,痛斥他的武断、自私,与冷酷,保利娜的声讨果决而无畏,句句肺腑。终于在得知女儿、看到王后死去时,里昂提斯被彻底击倒了,他的意念轰然坍塌,在经历了内心深处如同炽火般的是非胶着和情感纠葛之后,他毅然选择保利娜作为自己最后光亮之所在。在面对保利娜无忌的讽刺时,他彻底放下了自己丑陋不堪的过去,直言道:“墓碑上要刻着她们死去的原因,永远留着我的湔不去的耻辱。”[12](《冬天的故事》,第3幕第2场)从之前笃信保利娜必然前来寻事,到现在直视保利娜放下虚伪的尊严,当场痛恨自己的冷血与无情,前后语词变换的延异播撒带来文本矢量的无限游动,我们终归看到里昂提斯走入了不可能的可能——自我的救赎之路。
作为读者,我们无法把剧本的中心简单地定义为里昂提斯一人,倘若如此,我们必然忽视了这个人物身份在生成、改变、迂回、颠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忽视了与他者关系的不确定性。德里达认为:中心不能以在场者的形式去思考……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个非场所,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相互替换且无止境地游戏着[14]。人物关系的剧烈收缩和倏然扩张是《冬天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表达所在,十六年的忏悔使得里昂提斯终于迎接了女儿的回归和王后的复活,历经重重波折后,故事以喜剧收场。在朋友、爱人、家人和部下这层层鲜活的关系联结网中,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一边定义自己,一边被他人所定义。人物关系的“去中心”创造了巨大的遐思空间,关系的变化延宕带来了人物主体性的虚幻莫测,正如里昂提斯的妥协,这番妥协既是主体身份走向保利娜的明示,亦是颠覆主体过往的激荡宣言。人物关系的延异思考让我们看到一个确定又不确定的循环:我们的所知所想会主宰自我的发展轨迹,自我的发展轨迹会影响他者对我们的认知取舍,他者对我们的认知取舍会定义我们的所知所想……莎翁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始终洞悉着窗户人物,始终也被“窗户人物”所洞悉着,这个过程好似一个反射弧,他者实则是我们自身的镜像,受我们自身作用力的干扰,而我们和他者之间的远距关系,即是延异的张力,是解决自我迷失的答案所在。
(三)悲剧《麦克白》中人物关系的盲从和毁灭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剧中的主人公麦克白(Macbeth)起初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却沦丧为一个极度自我的残忍暴君,最终走向毁灭。当麦克白和战友班柯(Banquo)在战地旁的树林第一次遇见三个女巫时,他听到了自己注定先成为考特爵士(Thane of Cawdor)再跃居苏格兰君王的预言,同时也听到女巫说班柯的后人会主宰未来的王国。此时的麦克白虽有向往之心,却还没有利欲熏心;可随后当他如愿得到国王邓肯(Duncan)的嘉赏摇身变为考特爵士时,他开始犹豫了,但也只是犹豫……回到自己的城堡之后,班柯主动提起女巫们的预言似乎有所灵验,此刻的麦克白还这样答复他:“我可未曾想到过她们[12]”(《麦克白》第2幕第1场),他口中的“她们”指的便是三个女巫,此番表述证明麦克白还没有丧失理智和良知,他在与邪恶斗争……也就是说,他的确最初放弃了使女巫们成为自己另一重身份表达的可能,那么当时可供他选择的其他可能就是: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还是班柯?戏剧的关系冲突随即爆发,当麦克白夫人在丈夫的信中获悉其途中路遇女巫,以及女巫的预言时,她的邪恶与疯狂瞬间吞噬了麦克白,是她蛊惑并煽动丈夫实施残忍毒辣的一系列计划,包括杀死睡梦中善良仁慈的国王邓肯并嫁祸侍卫,接着又伏击了受邀前往赴宴的班柯和他的儿子,班柯遇袭身亡,其子侥幸逃脱。麦克白在夫人的唆使下笃信了女巫的预言,一番倒行逆施使其坠入邪恶的深谷,越坠越深,完全与道德和仁义背向而行。其实,班柯未尝不像麦克白一样,他功勋卓著、渴求权力,但与此同时,他内心深处的理性与道德劝诫着他的选择,虽然在女巫的预言中获得王位的是他的后人,但是班柯却没有盲从,即便当麦克白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愿意助其成功时,他也断然拒绝不为所动。
在麦克白加冕王冠而应验了女巫的预言时,他原本应当沉浸在欢喜陶醉的情绪中,却演变成弑君后的惶恐与不安,以及幻念中看到被自己所刺杀的班柯的冤魂,麦克白坠入疯癫……德里达把疯癫纳入笛卡尔“我思”(cogito)的视域,作为一个具有隐秘性的、深不可测的要素存在,且建构在“疯癫”一词的每一种意义之上,都只是思的一个个案[15]。对于此时的麦克白而言,他的国家在反抗他的统治,他的臣下在图谋对他的颠覆,原本美好的国王宝座在现实中却变了一副模样,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德里达在莎翁作品中坚定不移地找寻着对马克思的幽灵(即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有效解释[16],而麦克白疯癫意念中的幽灵班柯正是他所属意的一种文字游戏方式,借此炸裂文本表层的叙述结构,在意义的不断延异中显现那些不可表征的东西[17]。终于在思考无果之后,麦克白主动寻访女巫,想要获悉自己的未来,女巫的回答饱含戏剧性的条件:没有一个妇人生的孩子会伤害到他,唯有勃南树林(Birnam Wood)移动时他才会被征服。此时,在山洞中被众巫环绕的麦克白自喃道:“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12](《麦克白》,第4幕第1场)。从假意回避女巫预言的话题,到此刻自主而来以求心理庇护,麦克白的语词延异创设了读者与文本的切角关系,其人物建构使故事情节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阅读思考在行进间呈蜘蛛网式肆意舒展,幻化的可能无穷无尽。在莎翁笔下,女巫的两次预言貌似无欺却隐匿着无法预见的可能——预言给予麦克白君上的尊崇和至高的权力,却为他带来无穷尽的痛苦,因为他谋杀邓肯暗杀班柯,他的帝王之路铺洒着无辜者的鲜血,他要为自己的残忍无情付出代价;预言告诉他没有一个妇人生的孩子会伤害到他,可是却回避了向他寻仇的麦克德夫(Macduff)是被剖腹生产的事实;预言告诉他唯有勃南树林移动时他才会被征服,可是当英国军队来袭时,他们恰恰砍下勃南树林的树枝做前进时的掩护……无常的变数彻头彻尾地击垮了自命不凡的麦克白,命运的宠溺既可以让他高高在上,也可以让他深陷泥沼,这所有的不确定性掷地有声地书写着麦克白的跌宕人生,一切终究归于虚无。
麦克白弑君篡位,对赏识自己、信任自己的国王邓肯恩将仇报;继而为了稳固帝位,又出手杀害了自己的亲密战友班柯。邓肯和班柯都是对曾经正直辉煌时的麦克白的见证,铲除了他们,麦克白也扭曲了自己。莎翁笔下的麦克白的悲剧不是宿命论,而是人类自身受欲望驱使所作出的恶意选择,人物关系的延异在这部剧中是扭曲的抉择和毁灭的终结。命运貌似注定,却漂浮未定;女巫们的预言具有先验的因素和迷幻的色彩,她们打开了通向麦克白内心深处的一扇窗,此刻的女巫是戏剧中的窗户人物,可是邓肯也是,班柯也是,麦克白夫人也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克白自己的选择,对他者关系的选择——麦克白选择了女巫,选择了他的夫人,放弃了邓肯和班柯。对预言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考是我们走入麦克白的关键,当麦克白内心深处的恶意如同火山般喷发而出时,一切的后果呼之欲出,莎翁的收尾丝毫不手下留情,悲剧的终结令人窒息:麦克白夫人难逃精神桎梏、发疯而亡,麦克白在战斗中被麦克德夫枭首……疯癫既发生在麦克白身上,也发生在麦克白夫人身上;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疯癫绝不是简单的理性二元对立的那一面,而是彰显理性深层矛盾结构的差异,是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分裂,是在延宕变异中重叙不确定性的存在,更是对远距生成的呼喊。对文本的细读需要远距的力量,这个力量既在批判中形成了希望,又在重读和研读的过程中对他性创造充满了无限的敬畏和期盼。疯癫代表了麦克白对关系差异本源的探寻方式,而延异的虚空则让读者看到麦克白由于关系盲从而带来的终极毁灭。
三、结 语
莎翁笔下的戏剧人物永远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被他人所认识,主要人物始终围绕着他们被窗户人物所定义的方式而绽放色彩。当人物关系被内力或外力改写时,亲情、爱情或友情的联结都会在不经意间断裂,与此同时也宣告了自我发生方式的终结,由此我们在他者眼中消散,既有的主体性被完全颠覆。延异的客体身份为读者走入莎剧,体味莎士比亚式人物关系的生成、发展和变化提供了独特的视域,与他者关系的延异思考会让我们身处文本意义的消散空间而重拾更多的人物关照。莎翁戏剧人物对他者关系的认识,或创造,或倾覆,或毁灭,很大程度上是读者阅读意识的自体性表达,以及对文本审理的创造性情怀。读者对莎士比亚式人物的终极寻访在延异思考中被远距生成的力量所感召,理想的诗性居所既是物质空间的语域,也是精神书写的戏拟。
以延异的视角去揣摩人物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其间或进或退,或明或昧,都让我们体味着无限的可能性。当我们似乎明晰人物关系,对必然的可能怀抱憧憬时,却突然发现已经身处在不可能的可能中,我们的判断被倾覆、被重塑;而当我们后退一步,用远距生成的视角去表达人物关怀时,我们终将看到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相向而行、相视而生。莎翁笔下的主要人物无一不生动地投射在“窗户人物”中,这既是一种镜像,又是一种旁视。任何一个人物,哪怕在一幕剧情中,其在场或不在场的存在即便貌似是孤立的,他/她也绝不是孤独的,因为人物关系的胶着书写早已使得他们共生共亡,主要人物的灵魂在窗户人物的映射中清晰,他们互为彼此、交相托举。德里达告诉我们要拆解一切,要质疑所有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不可能;而在解构莎剧人物关系时,差异间的差异,延缓的差异却让我们感受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是如此义无反顾地为了对方而存在、而消亡,他们无畏无惧,具有他性的光环,体现着他性的创造,将读者带向诗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