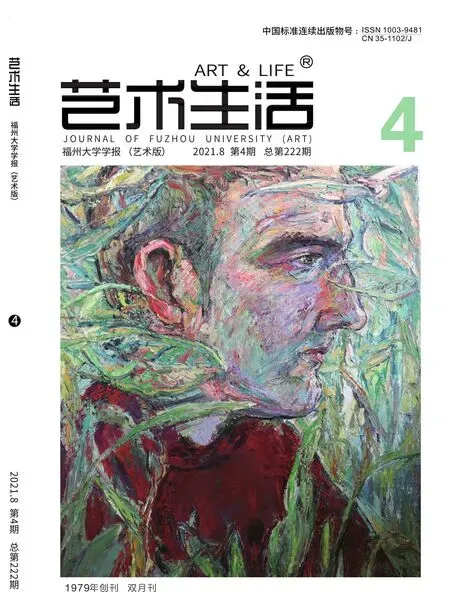绘画神话中的图像、画帧与作品散论
王望峰
(泰州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古人对于图像绘画的种种观念,以神话体裁的文本呈现出来,便构成了绘画神话。绘画神话中那些带有“魔力”的各类作品,或凭借神变推动了神话的情节发展,或借神迹标榜绘画的水准成就。一如石守谦先生在《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中所言:“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会具有与神鬼感通的能力,而产生非人力所能致的灵异事迹。”[1]52虽然经过种种的神异演绎,绘画神话中的“作品”概念与现实世界的作品在构成上还是一致的,它们都包含着“画帧”与“图像”两个层面要素:画帧是基于物质材料的、承载视觉图像的那个媒介平面,图像则是画帧之上诉诸于视觉性的画面形态构成,也即图像内容。神话对作品的叙述重心往往聚焦于其中的图像,而图像离不开画帧媒介的承载,画帧也因此而为神话所关注。可以说,绘画神话中作品的神异就是围绕着对图像与画帧的演绎而展开的。
一、图像的神性塑造:形象与对象
赋予图像以神性的神话细分起来大致有两类:“疑真神话”[2]4-9与“像变神话”[3]140-146,前者侧重于渲染图像对接受者的神效神验,如北宋陆希真画花张挂于壁上而引得蜂来;后者多强调图像超越画帧的神迹神变,如南朝张僧繇画龙点睛能破壁而去。在正统画学的视野中,这些神话所反映的其实就是普通的“逼真”“如生”等评价概念,如白居易在《记画》中说“画无常工,以似为工”[4]4768;韩琦在《稚圭论画》中也说“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5]41,等等。
神话的图像叙事内容光怪陆离、超越现实,但并不仅止于想象的夸张,它们实际上反映出了绘画神话对图像与形象、对象关系的神化处理—神话正是通过采取改变这些关系的策略而完成了神性的塑造。图像是一种基于精神性创造的客观产物;形象则是人们在对事物对象认知、想象或审美等思维活动中形成的主观结果。当人的视觉聚焦于图像时,图像的内容便能转变为形象;对象的形象可通过创作形成图像,但形象并非都来自于图像,如想象亦可生成形象。绘画神话虽然只是对图像概念的演绎,但图像神性的创造过程中无疑还要运用现实中对图像观看的一般经验。
图像与形象、事物对象三者的关系流程可表示为:对象(Object)→形象(Image)→图像(Picture)→新形象(Image’)。我们分别用英文O、I、P、I’字母来替代这几个概念,图像P 所本的事物对象为O,对象的形象为I,图像P 的新形象就是I’。图像所呈现的新形象I’与所本对象的形象I 都是意识的产物,不管它们如何肖似,却并非是一回事,它们的本体各自不同,中间存在着一个模仿或表现过程以及不同视觉特征的区别。O →I、P →I’这两组关系是各自对应的,不可混淆。分析了现实图像的创造与生成关系,概念图像的神化过程就清晰了。神话有意地错置了过程中O、I、P、I’几个概念,将它们进行混淆和神化处理,从而演绎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绘画神话:对I’→I 的神化称为“形象实效化”,创造出疑真神话;对I’→O 的神化名之“对象实体化”,创造出像变神话。
“疑真神话”的塑造注重于对图像的观看效应,故而渲染了图像中新形象(I’)的神异接受。图像(P)是对象形象(O)的描绘,但所绘出的形象(I’)并不是事物本体(O)。神话将图像的新形象(I’)偷换成了对象形象(I),进而在I 产生的接受效应中神化了图像(P)。疑真神话的表现是画家创造出的图像形象被当作为真(I’→I)。如曹不兴在屏风上误点笔而改画的苍蝇被孙权当作真蝇,张僧繇在寺庙画的鹞鹰能够阻吓鸠鸽。为了让图像效用更具有权威神性,神话刻意设定了图像接受对象的身份,或借帝王的身份来渲染图像效用,或以动物的身份将这种神性置于无处置疑的境地,图像的神异效用几乎成为六朝至盛唐一段时期称赞画家成就的“通用之模式”[1]67。
“像变神话”并不强调图像的新形象(I’),而是侧重图像所本对象(O)。神话将图像的形象置换为对象本体(I’→O),这样就必然导致图像发生神性变化,继而创造出各类像变故事来。耳熟能详的“画龙点睛”已不须赘述。李颀在《古今诗话》的“昆山惠聚寺诗”中记述了张僧繇的另一个绘画神话:“苏州昆山县惠聚寺殿基,乃鬼神一夕砌成。殿中有僧繇画龙,每因风雨夜,腾趠波涛,伤田害稼。乡人患之,僧繇再画一锁锁之,仍画一钉钉其锁。至今人扪其钉头尚隐隐。”[6]1890这则神话中,张僧繇所画的图像变为真龙并妨害了画外世界,他只好在图像上再画上“锁钉”—意味着变出的锁将会锁住真龙。
张僧繇的这则像变神话与“顾恺之画邻女”的传说略有些相似之处。《晋书》载顾恺之“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7]2405故事中“邻女”为O,“图其形”为P。但顾张二人神话的内涵是有区别的:顾是通过对图像“以棘针钉其心”的措施而影响对象(P →O),神性成为手段,神话带有明显的厌胜巫术意味(即弗雷泽的“相似巫术”);而张是通过对图像形象“再画一锁锁之”的创造来影响改变对象的神变(I’→O),神性本身即为目的。可见这两则神话虽然都进行了对象置换,但创造神性所用的策略是不同的,一针对图像,一通过形象,这是须区别的细微之处。
图像并非形象,形象也非对象,但从对象到最终形象之间的距离恰恰给图像的神话创造留下了一个发挥的空间—因为不是其物,所以才有可能趋近乃至于成为对象本身。对图像、对象、不同过程形象等概念的有意错置是塑造图像神性的主要但并非唯一方式,这是要注意的。神话按图像的内容将其做“形象实效化”或“对象实体化”的神化虚构,两类不同的神性塑造过程也是图像意义逐步突破画帧的过程,它意味着画家、观者能够通过画帧与作品能够结成更加复杂交错的关系,神话对图像的关注也往往跳出褒赞画艺的意图而转向为复杂的情节叙事服务。
我们讨论神话从对象到形象的关系处理是针对图像神性塑造的策略,并未涉及神性的起因即溯源问题,后者将会牵涉到原始思维方式乃至绘画史中的“传神论”思想等一系列因素,这个问题已有相关探讨[3]140-146,此处不再赘述。
二、画帧的现实意识:表面与平面
作为构成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画帧是能够引起绘画神话关注但又非必要的话题。它在神话中的份量并不显得特别突出,后者对它的叙述也总是呈现出有意或无意的特点,但这些叙述却能反映出神话之于作品更周全的认知。所谓“周全”,即是指神话更为全面地关注到作品构成中图像之外的要素—众所周知,以图像为中心的正统画学对画帧常持以冷落乃至忽略的态度;从这一角度来讲,画帧在神话中的呈现有着别样的价值。
缘于现实的画帧功能和叙事的需要,神话中的画帧概念大致有两个不同的内涵:一是“表面”,即画帧作为媒介载体为图像内容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表面属性;二是“平面”,图像被安排组织进入画帧所包含的空间平面,画帧进而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图像。这两个内涵都有着现实的观念来源,在此基础之上,画帧又被进一步神化成了图像内容与画外世界连接的通道,这无疑是出于神话自身虚造的需要。
在第一个“表面”的属性特征中,现实的画帧对图像来说是物质性的、具体的、被动承载的媒介载体,从岩石、砖木、纸帛到墙壁、屏风、扇面,不同材料、形态和用途的事物都能作为画帧而充当起图像的载体。如杜甫在《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写道:“沱水流中座,岷山到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诗中的建筑构件与画帧俨然已经融为一体。画帧固定的表面为图像准备了一个逻辑与空间上的先决条件。由此转换到神话的概念中,它同样作为图像的存在所必不可少—脱离于画帧表面的图像作品无异于空中之阁,这并不难以理解,作品的神性创造首先须得面临此一前提。
元人伊世珍的《琅嬛记》一书中有两则绘画神话提及了画帧,一是援引《丹青记》中的“王维画石”[8]3490:“王维为岐王画一大石,信笔涂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宝之,时罘罳间独坐注视,作山中想,悠然有余趣。数年之后,益有精彩。一旦大风雨中雷电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坏。不知所以,后见空轴,乃知画石飞去耳。……上始知维画神妙,遍索海内,藏之宫中,地上俱洒鸡狗血压之,恐飞去也。”另一则是辑录《卧游记》中的“李思训画鱼”[8]3417,它与王维的神话很有些相似的地方:“李思训画一鱼,甫完未施藻荇之类,有客叩门,出看寻入,失去画鱼。使童子觅之,乃风吹入池水内,拾视之,惟空纸耳。后思训临池,往往见一鱼如所画者。尝戏画数鱼投池内,经日夜,终不去。”两则唐代画家的神话中出现了“石飞鱼走”的奇迹,特别提到发生神迹的作品只剩下了“空轴”“空纸”的表面。神性虽然体现在图像内容的变化,但还要落实于画帧之上,换言之,这里为神迹的发生提供了前提承载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画帧。图像被“对象实体化”后突破画帧而去,就是神话以“减法”的方式将图像从作品中减除的过程,剩下的空白画帧也就彰显了神话对其媒介载体的特征理解。
第二个“平面”的属性内涵表现为画帧对图像在平面中的组织影响和意义介入,从“表面”到“平面”,画帧的意义也由被动转向主动,功用从具体转向抽象。当图像被组织进画帧时,画帧被隐含地视作一个抽象的、能主动自由包纳的“平面”,这个主动把握的平面与现实在直觉上是相矛盾的:一个画帧可以允许不同情节内容的同时呈现、同一个事物对象的反复出现,甚至被当作屏幕一样的动态窗口—如观赏时边展边收的长卷作品。表面上它们似乎只是布局构图与如何呈现的问题,底层上实际是画帧所具有主动包容性的体现(当然此一主动性亦是来自主体的理解与设定)。画帧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影响介入图像,不熟悉画帧的“平面”特性将不易甚至错误地解读作品①。虽然此一绘画艺术的原理不可能也没必要从神话中得到解释,但当神话在创造演绎作品的神迹时,却可能将画帧对图像施以意义影响的认知蛛丝马迹地流露于文本之中。
唐人刘长卿记述过一篇“张僧繇画僧记”的神话,后被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删节辑引[9]147:“张僧繇……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析为二,后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析多时,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果于其后购得,疾乃愈。刘长卿为记述其事。”陆坚在图像中天竺僧的托梦引导下,让两件半幅作品终于合为一帧,他的疾病也即日而愈。神话叙述的意涵不仅在于那位天竺僧的“托梦求合”与接受者陆坚的“立得病愈”的神迹,更表明这一切皆是缘于画帧分割而导致的因果关联;画帧对图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它的分合与二僧之聚散是一致的,画帧合二为一,图像中的两位天竺僧也才能重逢。正是这种主观的逻辑带来了一系列神迹,也引发了原神话中刘长卿对绘画作品的认知感叹:“信知造思之妙,通于神祇!”[10]3515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画帧概念以其两类源于现实的特性而成为了图像神性塑造中有意义的成分或条件。不过,神话的虚构本能并不满足于对画帧客观特性的简单交代,它还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虚构,使画帧从承载画面、组织平面继而变为不同世界的连接通道,沟通起了现实与期望的彼岸。正是在画帧通道概念的设定基础上,作品才有了下面要探讨的内外世界问题。
三、作品的内外世界:立体与本体
神话中的图像逐步突破画帧,无疑也使得更高层次上的作品意涵发生了改变:由画帧与图像构成的作品的原始概念被打乱,作品从单纯静态的视觉创造物衍生出抽象的“立体”意义来。这种“立体”表现为神话往往围绕着作品的图像内容演绎出内外两个世界来—以画帧为界限的两个对立又融合的空间概念。我们把神化了的图像内容称为“画中世界”,将图像之外包括画帧乃至画家、观者等在内的各种要素组合称为“画外世界”;画中世界与图像内容是同一对象,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作品神性化下的语境。
来看几则虚构了内外世界的绘画神话。唐人杜荀鹤《松窗杂记》中有一篇《赵颜呼画》[11]3433,讲述了一个画中人真真的故事。神话中作为观者的赵颜对图像内容即画中世界的真真一见倾心,画家告其求之要诀,赵颜连续百日呼唤真真其名,终于感动画中美女穿越画帧与之为夫妻。在历经了画外世界的人间生活后,真真因赵颜的背叛而回到画帧中,图像上也多出了一个她所生的孩童。这则神话里的画中世界与画外世界发生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实体化的形象介入画外世界后遭遇了变化并能够体现在图像内容之中。有自画中至画外的顺序,也就有自画外而画中的逆序,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便收录一则“柳生入画”的神话[12]726,讲一位叫柳成的儒生跳进了画家的《竹林会》作品中,并对阮籍的面容图像进行了修改。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画帧平面作为一个通道,在他跳入后,“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从画外到画内的互动,图像的创作就难免匪夷所思了。《丹青记》中有则“天师画龙”便走向了极端:“天师张与材善画龙,变化不测,了无粉本,求者鳞集,海内几遍。晚年修道,懒于举笔,人有绢素,辄呼曰画龙来。顷之忽一龙飞上绢素,即成画矣,故人间往往有言画龙飞去者。”[13]332与“赵颜呼画”“柳生入画”一样,“天师画龙”中也明晰地区分了画中与画外两个世界,不过它直接颠倒了两个世界的关系,将画中世界的内容交由画外世界来“填满”而非创作,这也就偏离了绘画的原始意义。
在画中世界与画外世界的关系中,包括画家等在内各色主体的画外世界创造或影响了画中世界,后者又可以反过来改变作用于前者。内外世界既解决了作品中图像与画帧的矛盾,也打破了绘画与现实的关系秩序,画家或图像中的人物对象可以自由地穿梭于两个世界;甚至出现像“赵颜呼画”那样离奇的关系迭代—画家创作主体创造了图像,图像幻化出新的“创作主体”真真来改变画外世界直至重构了画中世界即图像自身。作品的立体性以“温暖”的态度消弭了现实中面对作品所形成的生硬的主客接受关系,使得绘画活动那种从画家到作品再到观者的单向流程被重构,这种复杂关系的创造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也正是这样虚幻又瑰奇的特点让内外世界成为处理作品的一种套式,特别是更易于被宗教所运用,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宗教图像神话来,即所谓的“瑞像”神话②。
对内外两个世界的的审视还应把作品置入到神话叙述的原境中来进行。对作品的叙述不仅止于作品本身,它在神话中可能仅仅作为其他叙事的一个局部,背后还有着更大的背景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品也就会从目的转变为手段、从对自身的单纯演绎转向为主题叙事做铺垫服务。有不少的绘画神话如《续博物志》中的“画魅”、《广异记》中的“朱敖”、《搜神秘览》中的“道术”,《南村辍耕录》里的“鬼室”、《聊斋志异》里的“画壁”“画马”等,都是以作品为要素来讲述内外世界深度互动的故事。
事实上到了这一步,作品的本体意义已发生了方向改变,作为绘画现象的价值逐渐削弱,它也必然淡出图像文化关注的视野。特别是在传统画学的认知体系中,对作品内外世界的臆造开始持一种排斥贬抑的态度,如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说:“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橱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14]188他将“神妙”与“神异”做了区分,把关涉神话的作品排除在外;而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更是将“野人腾壁”“美女下墙”一类的神异作品归为“术画”,认为是“眩惑以沽名”之作,“皆出方术怪诞,推之画法阙如也”[15]495。绘画神话与传统画学正是在对待作品的态度上逐渐分道扬镳,传统画学向着神、趣、意、韵等范畴主导的视觉形式、风格脉络乃至更深的精神层面进发,而绘画神话随着作品本体的神化和意义偏离,走上了另一条专注于故事情节演绎的文学道路。
结语
绘画神话中的图像、画帧与作品三个概念,图像无疑是神话的焦点与虚构首选,画帧则因图像而为神话认知、论及乃至成为神性演绎的成分或条件,图像的神性向上“传递”到其与画帧构成的作品中,使得作品似乎成为神性的主宰,图像反而成了作品魔力的衍生品。神话对作品的叙述很少是基于对真实画作的演绎,尽管如此,围绕着绘画作品结构与关系的组成仍然体现出对现实作品的观念认知;图像的神性延及至作品整体中来,必然会打破和重构客观的创作及观看关系,从而体现为对作品所划分出的内外世界的策略考量。
神话绘画在对作品所进行的虚构演绎中,图像内容已经完全脱离视觉形式而以文本的形态出现。文本站在作品之外,对图像的视野也有所不同,它更能体现普通民众而非画家群体对待绘画图像的认知理解;图像文化中的某些问题也更容易在神话文本形式的传播中为民众接受并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讲,绘画神话拓宽了传统图像文化的研究视角,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尝试。
注释:
①不同于第一种“表面”属性的客观性,第二种“平面”的内涵是主观性的,来自于创作主体的安排,例如战国宴乐铜壶壶身画、汉画像砖石故事画、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敦煌第9 窟的“降魔变”乃至欧洲巴洛克时期的《舟发西苔岛》等,它可以视作为人类“共时性”意识对画帧平面性的妥协折中。所以有些学者把图像在画帧中的这种安排放在“图像叙事学”的视野中来探讨,称它们为“综合性叙述”和“循环式叙述”,也是有道理的。见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三联书社,2015 年,第442 页。
②“瑞像”神话是宗教中的图像神话,例如佛教中也称为“感通画”神话。一般模式是宗教神祇圣像“显灵”化身介入到像外世界进行互动,甚至互动之后又能在神像中留下印迹等情节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