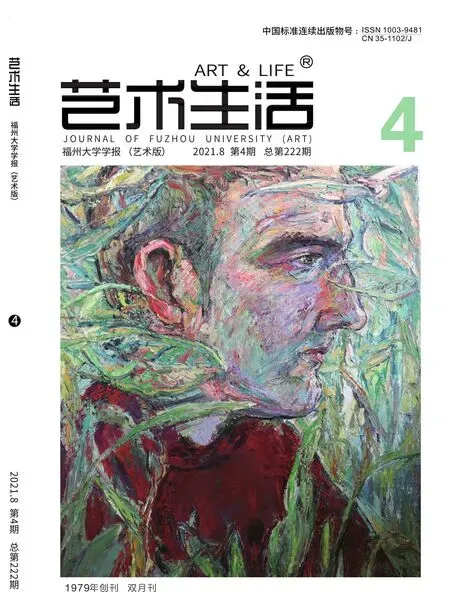莫高窟“白衣佛”的视觉形象与神圣空间建构
孙 超
(中国美术学院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02)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四“观相品”云:“化佛出此光明,此光现时,下方世界有百万金山,于其岩间百亿宝窟,如云踊起,是众窟中纯诸白佛,白妙菩萨及声闻众以为侍者,金精宝光在佛左右,犹如断山众宝映错,有妙宝盖如须弥山无量宝成。”[1]敦煌莫高窟“白衣佛”形象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在流传过程中结合中土传统文化背景,进而呈现出释迦牟尼佛身着白色袈裟禅定或涅槃的形象。贺世哲较早提出“白衣佛”说法,并认为观“白衣佛”是禅观修行方式之一[2]41-52。莫高窟壁画现存五铺身着白色袈裟的“白衣佛”形象,分别位于北魏时期第254、263、431、435 窟和西魏时期第288 窟。它们不同于同时期呈肉色或金色的其他佛像,似乎有着特殊意涵,以其独有的视觉艺术形象,成为建构神圣空间和视觉想象的重要媒介。
一、“白衣佛”的艺术表现形式
莫高窟“白衣佛”画面色彩鲜明,整体基调为深棕色,佛陀背光部分有的施以蓝绿色平涂。青色、蓝色或金色来表现发髻,纯白底色的袈裟上以深棕色线条勾出衣褶轮廓。它们的呈现形式既有单尊也有组合,皆正面而坐。第431、435 窟白衣佛为单尊佛像,第254、263、288 窟“白衣佛”身旁则绘二胁侍菩萨,为典型的一佛二菩萨形式。不论单尊还是组合形式,“白衣佛”形象都以单幅主体画面的构图形式突出呈现。它们呈结跏趺坐像,身着白色通肩袈裟,自然下垂包裹双腿双足。佛像面相圆润,头顶发髻,棕褐色头光与背光交错;鼻翼高挺,耳轮长垂搭肩,双目微睁,低沉而深邃,显得庄重肃穆,似作禅定状。
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0 窟较早出现白描墨线绘制的“白衣佛”形象,佛像眼睛微微睁开,神态安详平和,似作沉思,继承了犍陀罗佛造像风格。莫高窟第254窟开凿年代与阿旃陀石窟相近,“白衣佛”的绘制手法则更进一步,袈裟采用晕染法,层层叠染,下摆和衣袖绘出阶梯状堆叠,显得格外浑厚立体,富有层次感,同样体现出受犍陀罗佛像衣纹的影响。袈裟上部衣纹呈“U”形下垂,遮盖住盘起的双脚。佛像右臂上举,掌心朝前,左手指尖向下伸出,作说法状。“白衣佛”外围绘有圆拱形佛龛,龛楣和龛柱上配有装饰纹样。佛座并非北朝常见的须弥座样式,而是呈土坡状,上面绘有树叶一样的花纹。
第254 窟是北魏时期最早出现“白衣佛”的石窟(图1),其后四座洞窟中的“白衣佛”形象都承袭此窟绘制手法,只是趋于简洁明朗,如第263窟的“白衣佛”(图2)衣纹仅用数根红线一染而过,相较之下略显单薄。第435 窟“白衣佛”袈裟则使用重复的长短线来描绘衣纹的层叠。佛陀头顶无发髻,而是用土红色线条勾勒了一顶宝冠,装饰效果明显。佛陀神情静穆、双目低垂作沉思冥想状,似乎表现了涅槃之态。除受犍陀罗风格影响,莫高窟和阿旃陀石窟“白衣佛”形象应该也吸收了笈多王朝时期马图拉风格(Mathura Style)佛像造型元素。这类佛像往往具有印度人脸型,希腊式鼻子,通肩袈裟,富有韵律感的“U”形衣纹,浑厚的嘴唇,恬静的面容,若有所思的神情,近似冥想的眼神,气度显得雍容庄重。莫高窟“白衣佛”眼、鼻、颧骨等部位均施以白粉作为高光,既能增强佛像的立体感,也让原本昏暗的石窟略显明亮,正如“是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3]。莫高窟和阿旃陀石窟“白衣佛”虽然色彩和服饰存在略微区别,但佛像造型、画面构图、绘制手法等高度相似,表现的都是佛陀的神圣与庄重。它们应该都是源于古印度佛教石窟佛陀的艺术形象。

图1 北魏 莫高窟第254 窟 白衣佛 图片来源: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 册),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第137 页

图2 北魏 莫高窟第263 窟 白衣佛 图片来源: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 册),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第69 页
二、“白衣佛”与石窟图像配置
这五铺“白衣佛”形象分布的洞窟形制基本一致,均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窟源于印度支提窟,具有绕佛礼拜和静修禅观的双重功能。窟内空间多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由窟顶人字披和四壁构成可礼拜的殿堂式空间,是僧侣聚集的前堂;后室开凿中心柱,环塔柱四周则为狭窄的甬道,共同构成一个可供信徒入窟旋绕塔柱进行诵经礼佛的神圣礼拜空间。中心柱在石窟里象征着佛塔之物,是信众礼拜的核心,佛塔又意味着佛陀入灭。
这五窟窟顶均为平綦顶,绘有莲花图案,其中第432 窟、435 窟、288 窟伴有十余身飞天。平綦结构让观者进入窟内随即感受到视野的开阔和无限上升的力量感,自然起到延伸殿堂神圣空间的作用。“白衣佛”处于这五窟中心塔柱窟内后室西壁,即整个石窟的中心位置。东壁绘有千佛形象,北壁和南壁均为与释迦牟尼生平相关的题材。如第254 窟北壁绘难陀出家因缘变、尸毗王本生故事等,南壁绘降魔成道、舍身饲虎本生故事;第263 窟北壁为说法图,南壁为降魔成道;第431 窟北壁为未生怨故事,南壁为禅定佛形象;第435 窟和第288 窟北壁、南壁均为说法图。窟内四壁绘塑题材虽不尽相同,但“白衣佛”四周分布的画面却出奇地一致,满壁都是相互融合的千佛形象,仅第254 窟就有千佛1200 余身。加之各窟绘制的天宫伎乐、飞天形象和佛陀说法图,共同营造出佛国极乐世界的氛围。这显然是开窟者和壁画绘制者有意为之,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石窟图像配置系统。
我们知道,佛陀成道最终以涅槃而永离轮回结束。莫高窟中心柱窟常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在中心柱窟主室表现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入灭这个过程的一系列场景。这五窟的壁画有佛本生故事、佛陀说法、降魔成道等。在这个完整的程序里却唯独缺少直接表现佛陀涅槃的图像,原因是为何呢?佛陀涅槃对于世人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失去庇护而变得黑暗。因此,石窟内光线较暗处,即中心塔柱之后的位置往往会绘制佛陀涅槃场景。涅槃后的佛陀安然卧躺在地,周围是哀伤悲痛的弟子信众。中心柱后自然光线较暗,恰好能够反映佛陀入灭的神秘以及世间的黑暗。
《礼记·郊特牲》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4]“素服”即居丧期间所穿白色丧服。郑玄注《仪礼·丧服》中又载:“三王以来,以唐虞白布冠为丧冠。”[5]白色与中国传统丧葬礼仪联系密切,是最能代表死亡含义的颜色,故丧事又称“白事”。《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曰:“白者,即是菩提之心。”[6]在佛教文化中涅槃即表示死亡,是重生和轮回。因此,“白衣佛”取白色为袈裟颜色,其特殊含义应该就是表现佛陀涅槃。佛塔源于梵语“Stupa”意译,音译为窣堵波,是埋藏佛骨舍利之处,同样代表佛陀涅槃。中心塔柱在石窟中象征佛塔之物,是信徒绕窟礼拜的中心。由此可见,这五铺“白衣佛”均位于中心塔柱窟内,并且与千佛被有目的地安排于同一幅画面中。这绝非巧合,而是开窟者和壁画绘制者有意为之。石窟内的“白衣佛”形象带给虔诚的信徒以令人陶醉的感官体验和充满想象力的视觉效果。从总体的图像程序和石窟形制来看,上述绘有“白衣佛”的石窟,应该是借助“白衣佛”的视觉图像将佛陀的冥想可视化。
三、神圣空间建构的视觉媒介
佛教石窟开凿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了禅观或做功德。“白衣佛”的出现或许也与当时盛行的禅修之风有关。禅观的“禅”指集中注意力坐禅后获得的心性安定,进而产生冥想效果;“观”即“观想”,指在禅的境界里仔细念想,产生特定的存思内容。《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载:“欲观佛像者,先入佛塔,烧香散花,供养佛像,礼佛忏悔。”[1]信众进入中心塔柱窟,即可“观佛像”。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古印度那揭罗曷佛影窟的故事。佛陀尝于此石窟度化瞿波龙王,因龙王至诚劝请留止于此,佛陀遂于窟中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复映现于外。化为佛影,存留影窟。距十余步远望,则如见佛金色相好、光明炳然之真形;近观,则冥然不见,以手触之,唯余四壁。诸天众等闻佛还入窟中,皆来供养佛影,影亦为其说法[1]。经中还介绍了观佛影修行的具体方法:“若欲知佛坐者当观佛影。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1]
法显《佛国记》载:“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馀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转近转微,仿佛如有。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摹写,莫能及。彼国人传云,千佛尽当于此留影。”[7]78玄奘《大唐西域记》记那揭罗曷国小石岭佛影窟时描述,都城向西南行走20多里即小石岭佛影窟,窟中有佛影,容光焕发,犹如佛之真身在场,形态佳妙之极。只有发心祈祷,感动神明后,才能短暂得见佛影。[8]135《洛阳伽蓝记》亦提及这处佛影窟,“那竭城中有佛牙佛发,并作宝函盛之,朝夕供养。至瞿波罗窟,见佛影。入山窟,去十五步,西面向户遥望,则众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见。”[9]393佛教在东晋时期获得空前发展,道安和慧远做出巨大贡献。慧远在庐山结庐,创建东林寺,30 余载迹不入俗,影不出山,使庐山成为江南的佛教中心。义熙八年(412)慧远在庐山营建佛影台,绘制世尊显圣的踪迹“佛影”,吸引了大批朝圣者。慧远及其同时代人主要的冥想指南是《般舟三昧经》,此经介绍了从观想念佛或持名念佛上升到实相念佛的一种特别的修习方式,即般舟三昧。它将大乘般若思想与禅观之术相结合,修持者经由自心作用,了解到诸佛现前皆是内心作用幻化所致。这五铺“白衣佛”如佛影般存在于窟内核心位置,自然也可作为观想对象。
这五铺“白衣佛”均是壁上绘圆拱形龛,佛像绘于龛内。龛楣均绘制半忍冬纹,第254、263、435 窟龛楣外绘有山峦图案。“白衣佛”周围的山峦图案或许是根据《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提到的“百万金山”绘制的,在其周围踊起“诸白佛”[1]。同时,这五窟中心塔柱均四面开龛,龛内塑有禅定佛像和说法佛像,供僧侣禅观所用。
除了禅观的精神层面,佛教石窟更具有强烈的世俗功能。信众从东侧窟门进入洞窟礼拜时,首先到达的是敞亮的长方形前室,这里是能够礼拜佛像的殿堂式空间,信众首先观看到中心柱东面向的佛像并驻足礼拜,此为第一个神圣空间;按照旋绕礼佛传统,信众顺时针右绕中心柱继续礼拜。观者、中心塔柱和南西北三壁佛像共同构成第二个神圣空间。信众通过中心塔柱四周狭窄的甬道时,窟内光线瞬间由亮转暗,行至中心塔柱西面向时,光线变得最暗。继续向北壁前行时,光线又瞬间变亮,然后走出甬道,再次回到主室中心塔柱东面向,最终完成整个绕窟礼佛行为。在此过程中,信众似乎总能感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存在,指引其走向光明。“白衣佛”恰好位于石窟后室西壁,即上述光线最暗的位置。如此设计的意图或许是,“白衣佛”作为信众礼拜的对象,能够给人以光明,佛在光明即在。那么,信众在面临一片黑暗时会怎么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10]他们自然会在这个神圣空间内绕塔礼拜时集中精力冥想,进而获得对佛陀形象的想象。旋绕礼拜的过程也是一次巡礼圣地的经历,这五窟“白衣佛”形象似乎可以理解为信众礼拜观禅时脑中幻想的视觉化呈现。
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心理情境的设定。不论僧侣禅修观佛,还是信众绕窟礼拜,这些绘有“白衣佛”形象的石窟都被视为神圣的殿堂空间,“白衣佛”则是建构这个神圣空间的视觉媒介。在这个神圣空间内,禅修者和礼拜者的身体对于石窟周遭环境的感知,从根本上是其心灵与环境的沟通和联系。此时,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被打破,意识是模糊的,周围是虚空的。随着身体的不断游移,他们感受到的每个瞬间秩序都是短暂的,会在下一个瞬间被新的秩序所取代,正如一瞬间由亮变暗,又由暗变亮那样。如此循环往复,构成无穷无尽的可能,又来构建新的秩序。这是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官体验和视觉想象。禅观和礼拜行为都具有神圣的非人间意义。无需刻意渲染和设计,就能灵活自由地在“幻境”和“现实”之间转换。
结语
佛教石窟中的视觉图像在不同媒介中呈现的形式和变化都不是随意构建的,它们可以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或神圣空间的标志。莫高窟“白衣佛”以其特有的视觉形象,成为建构神圣空间和视觉想象的媒介。它们在石窟中呈现的形式和变化都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遵循着严格的图像配置程序和空间设计逻辑。“白衣佛”的视觉形象与布局方式,再现了一种复杂的观察宇宙的方式,将冥想可视化,成为内心世界外化的视觉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