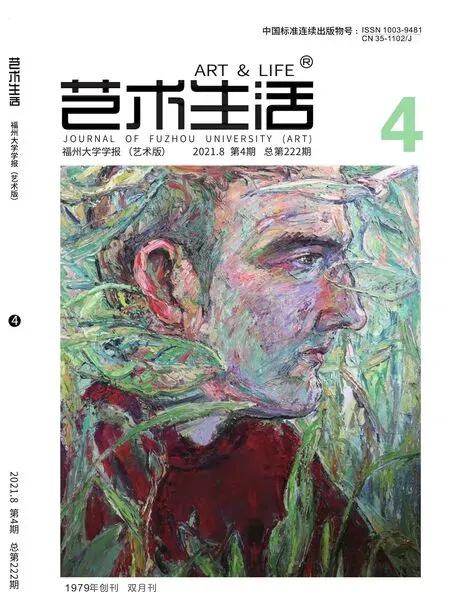奥斯曼帝国16-18 世纪装饰艺术的多元文化分析
杨 静 沈爱凤
(1.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土耳其奥斯曼人(Osman)为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他们初居中亚,在伊朗高原的呼罗珊地区从事游牧活动的过程中逐渐与伊朗各部族相混合。后又迁往小亚细亚,在那里逐渐取代和同化了与他们同血统的塞尔柱克人(Seljuq)。1299 年,奥斯曼自称加齐(Gazi),在其领地范围内建立国家,为奥斯曼人国家的雏形。奥斯曼帝国占据东西方的陆上交通线达几个世纪之久,一直到1922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奥斯曼帝国灭亡。16 世纪是奥斯曼帝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至18 世纪末,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新帝国位处东西文明的交汇处,在其建立与发展壮大过程中继承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土地。因此,奥斯曼的装饰艺术的多样性特点是其帝国形成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文化互鉴交流的结果。
奥斯曼评论家认为以“rumi”和“hatayi” 装饰的艺术品是16 世纪奥斯曼美学的标志性特征[1]22-23。“rumi”(土耳其语Rúmî)字面意义是“罗马”,指一种抽象的花卉装饰,形象为按照几何形态排列的棕榈叶或切开的棕榈叶。它是近东地区晚期流行的装饰词汇,几个世纪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hatayi”(土耳其语Hatâyî)字面意义是“契丹”的意义,暗示着这个图案的东亚来源,它结合其它形态的东亚图案与莲花纹组合成程式化的卷曲状。15 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种新的设计形态出现,它具有东亚的云带纹,三点和条纹图案以及有着团花成分的新图案,这个就是奥斯曼宫廷流行的辛塔曼尼(土语çintamani,英语Chintamani)图案(图1)。

图1 釉底彩陶砖,1550-1600 年,土耳其或叙利亚制作,收藏地: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到了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 年在位)执政时候,他通过皇家设计工作室(Nakkaşhâne)重新确立了一些新的美学词汇。皇家设计工作室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团体。这个工作室最早是为苏丹的图书馆制作带插图的珍本书籍,后来这里的工作内容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新的艺术风格,重新确立了某些艺术形式,并对其它艺术门类产生了重要影响。16 世纪通过皇家设计工作室,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装饰风格:一是传统风格,即早期伊斯兰世界的缠枝花卉设计;二是活泼的Saz 风格,它借鉴了一些东方图案,如中国的莲花、龙元素以及其它富有想象力的生物;三是自然主义风格,即那些写实性的花卉,如16-17 世纪流行的有苏丹们的花押(tuğra,图格拉)、康乃馨、郁金香、罗赛蒂(Rosette)、石榴、马鞭草、爪印、阿拉伯花饰、棕榈、辛塔曼尼等图案。自然主义风格成为奥斯曼时期陶瓷、纺织品及建筑装饰的首选题材。以上图案装饰风格的最终定型图案非一蹴而成的,它是多种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
一、对中国与蒙古装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以奥斯曼宫廷艺术的代表辛塔曼尼图案为例,它常见的构成模式是三个球,并出现在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文化艺术中,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奥斯曼时期辛塔曼尼图案成为宫廷艺术的代表。奥斯曼时期的辛塔曼尼图案包括两个设计元素,分别是“虎纹”(土语pelengî)、“豹纹”(土语benekli)。“虎纹”双线的加入使得原本单纯的造型变得更加多样化,其造型内涵也丰富起来。目前除佛教起源外,还有其它两种合理的解释:一是它的形态是土耳其与伊朗文化艺术之间互动性的结果,也是两种艺术观念的“统一”;二是其艺术造型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动物图腾信仰有关。三个点组合在一起也许是象征拥有斑点纹的动物,如豹子。它的使用或许是为了辟邪、繁殖或保证狩猎的成功。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通常会使用在大衣上,如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博物馆收藏了一件14 世纪的插画,画面描绘了具有突厥牧民风格装扮的斑点纹的披风。除了御寒的实际作用外,其象征性用途更为明显,即伪装成强大的动物,作为萨满巫师与动物进行沟通或唤起动物崇拜的朴素思想。穆罕默德二世曾把辛塔曼尼图案作为个人的象征物[2]48。这无不显示此图案的重要性与其蕴含的象征意义。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辛塔曼尼图案打破了原有的构成模式,展示出了丰富的变体形态,它可以与花卉元素结合在一起;打破常用的偏移图案排列,而以直线排列方式;还可以分开单独使用或者其他形态。它作为奥斯曼时期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图案之一,某种程度上是宫廷审美的体现。16 世纪,奥斯曼各类纺织品上具有丰富多样的纺织图案,但是在一些物品上辛塔曼尼图案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图案,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以辛塔曼尼图案装饰的丝制卡夫坦长袍(Caftan,图2)不仅是权力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帝国内部与外部的权力折射。奥斯曼时期的建筑上喜欢使用釉底瓷砖,有的建筑甚至正面墙都用辛塔曼尼图案的瓷砖装饰。17 世纪,辛塔曼尼设计逐渐变得大众化,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致味道逐渐消失。随着该图案装饰性的加强,其动物象征性势弱,护身功能也消失不见。随着奥斯曼与欧洲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加深,辛塔曼尼图案也出现在了意大利的锡釉陶上。当然,尽管辛塔曼尼图案具有明显的东亚文化影响,但是它在安纳托利亚的流行还是得益于蒙古人的推动作用。除了这个图案外,中国的莲纹、云带纹、龙纹、凤鸟纹(伊朗叫森穆夫(Simurgh/Sēnmurw))等也对奥斯曼的装饰艺术产生了影响。而当奥斯曼与萨法维(safavid)的战争以奥斯曼的胜利告一段落的时候,有大量中国瓷器被带往奥斯曼宫廷,于是当地陶工开始改编了一些东亚图案,从而带动了“中国风”的装饰风格在奥斯曼宫廷的流行。

图2 苏丹塞利姆一世的卡夫坦长袍,1515年,收藏地:土耳其托普卡帕宫
二、与欧洲装饰艺术的互动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特别是苏莱曼大帝当政时期,它的迅速崛起打破了欧洲原本的政治平衡,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兴趣提高。由于政治与商业关系的加强,文化交流随之频繁起来。艺术家、商人、使节、宫廷译员、旅行家与朝圣者之间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双方之间装饰图案与设计的传播与交流。作为研究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文化交流的专家德博拉·霍华德(Deborah Howard)认为:“通过物质商品进行文化迁移的根源在于三个主要方面,即外交、贸易和朝圣。”外交礼仪中,礼物交换与接收仪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威尼斯大使向奥斯曼帝国赠送了丰富的纺织品与服装[3]142。其次,尽管彼此之间也会发生战争,但是却无法阻止彼此之间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再次,朝圣会打破宗教信仰的障碍,是获得对方信息与知识的一个渠道。
16 世纪,那些负责为宫廷和高级官员购买商品的大使们的到来,从侧面说明了双方贸易关系是越来越好。于是,地毯、陶瓷、纺织品、玻璃、书籍等容易携带的物品成为重要的贸易内容。频繁的贸易活动与顺畅的贸易网络不仅影响了贸易内容,也影响了双方新图案与新设计的使用。有些物品上还出现了具有“跨文化”或“混合”图案与设计的特征。
整体来看,奥斯曼与欧洲的装饰艺术联系分为两个阶段:17 世纪之前,奥斯曼艺术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要占上风,当然,这与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密不可分。18 世纪中期开始,奥斯曼的艺术家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西方,并尝试与西方艺术思想接轨。这个转变的主要动力是奥斯曼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增加。中产阶级的崛起促进了财富的重新分配、政治权利中心的调整、受欧洲影响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以上变化的就是艺术思想的变化。于是,奥斯曼的艺术家和纺织工人们开始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灵感。
伊兹尼克(Iznik)的瓷器作坊中开始出现了意大利马约里卡(Majolica)陶器上常有的图案,如那些精心描绘的人物、肖像、风景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一般取自意大利的高层人物或重要的历史事件。反之,伊兹尼克生产的瓷器图案也对意大利马约里卡瓷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奥斯曼典型的Saz 风格、康乃馨、郁金香、鲁米(rumi)等图案(图3)。再者,奥斯曼帝国的那些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在意大利马约里卡的盘子上,反之,意大利同心圆式的构图模式也直接影响了奥斯曼的瓷盘设计。伊兹尼克瓷器的造型也对意大利帕多瓦地区的坎迪亚纳(Candiana)瓷器产生了影响,如两地的长颈瓶在造型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除了瓷器外,还有纺织装饰的互动影响。奥斯曼15-16 世纪的地毯实物幸存下来的很少,但是它们出现在当时的欧洲绘画中,表明了奥斯曼已经与欧洲进行了地毯交易。安纳托利亚最常见的出口地毯因其在意大利和文艺复兴时期北部绘画中的普遍性而被称为“霍尔拜因”地毯(Holbein carpet)和“洛托”地毯(Lotto carpet),二者都是由重复的几何图案构成。前者偏爱八角形和星形图案,而后者则是开放的重复设计,上有尖角的“rumi”图案。地毯像陶瓷一样,成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享有盛誉的贸易商品,尤其是随着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人之间的商业网络的发展[4]81。为了满足当时欧洲对奥斯曼地毯不断增长的需求,16世纪晚期奥斯曼的地毯工人设计出“鸟毯”(图4)来应对。因为传统的地毯图案复杂多变,制作工期长且织工技术有限,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因此,设计师们决定采用简单的图案模式,以便快速简易地完成图案纺织,且可使生产出的地毯满足大众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简约而不失典雅,生机盎然而不失厚重古朴的“小鸟”地毯应运而生了[5]102。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地中海及近东古物博物馆中收藏的“鸟”毯是为当时的大主教Johannes Andreas Próchnicki 定制的。

图3 意大利蒙特鲁朴的马约里卡锡釉盘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装饰图案,1570-1580年,收藏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图4 奥斯曼“鸟”毯,17 世纪,188×160 cm,收藏地: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除此之外,为了满足巴尔干地区、东欧以及莫斯科公国的丝制品需求,奥斯曼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为其制作法衣。有些织锦片段上图案以圆圈为间隔,内有基督像,圆圈之间的间隙点缀十字架。奥斯曼时期为基督教提供的高档丝织品上常见的图案就是十字架与六翼天使(seraphim)。为了满足奥斯曼宫廷的奢华生活,奥斯曼也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进口大量的丝制品。土耳其托普卡帕(Topkapi)皇宫收藏的各类丝织品中,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产的占有一定的比重。奥斯曼帝国的武器,连同丝绸、天鹅绒和马海毛织物在波兰宫廷中非常流行,在波兰的绅士阶层中也很流行。17 世纪波兰绅士的画像通常为葬礼而画,画中他们的穿着让人联想起奥斯曼土耳其的卡夫坦长袍。
三、与萨法维装饰艺术的互动
奥斯曼与萨法维王朝产生于塞尔柱王朝的废墟之上。1473 年,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埃尔津詹(Erzincan)附近击败了波斯白羊王朝的乌宗可汗(Uzun Hasan),夺取了白羊王朝的大片领土[6]105-106。到了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奥斯曼和萨法维之间也一直处于领土的争夺过程。即,奥斯曼帝国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蚕食塞尔柱王朝遗留下的政治遗产,试图完全继承突厥部落的精神遗产[7]93。奥斯曼与萨法维之间的斗争,有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对奥斯曼来说主要是为了维持东部领土的和平,同时还要保护和维持其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商路畅通。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地区从文化和战略上对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不间断的对抗为主。但是,斗争与对抗的常态并没有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在装饰艺术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纺织品和书籍插图上的互动交流。
14-15 世纪奥斯曼对波斯和中亚地区流行的细密画和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而那些文学作品通常配有插图。奥斯曼将波斯的文学题材引入到自己的文化艺术中去。巴耶塞特二世(Bayezid II,1481-1512年在位)统治时期,奥斯曼的书籍中对波斯文学作品的兴趣仍在继续,如插图版的《列王纪》《五卷诗》(Khamsa)以及波斯人的肖像画等,均被奥斯曼宫廷艺术选择性地吸收运用,如将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与服饰细节融入其中,显示出这个时期人们试图创造一种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互相融合的“新装饰风格”。以尼扎米《五卷诗》中的一幅萨珊波斯的统治者巴赫拉姆·古尔(Bahram Gur)与狮子搏斗的场景插图为例,这个主题在萨法维时期的艺术中继续出现。到了奥斯曼的书籍插图中,这个场景的绘制采用了更为宏大的视角,准确的透视关系、饱满的深色色调和具象的画法,使得我们怀疑这些画作可能是出自熟悉波斯装饰语言的意大利画师或他们的实习画师[8]147-161。即,奥斯曼将这个艺术主题纳入自己的视觉语言中,采用了更为科学的方式绘制出来。尽管绘制不一定是奥斯曼的艺术家所为,但却显示了二者之间在某些主题上的共享性。
塞里姆一世(Selim I,1512-1520 年在位)统治时期,那些奢华的手稿产量明显下降。当塞里姆一世于1514年大败萨法维王朝,将其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时候,原本保存于萨法维王室的那些帖木儿时期的赫拉特地区(Herat region)、白羊王朝(Aq Qoyunlu)宫廷以及大不里士等宫廷艺术品被奥斯曼宫廷收为己有。在1525-1526 年的奥斯曼文献记载中列出了29 位艺术家和12 位学徒,其中3 位艺术家来自大不里士,还有4 位学徒来自伊朗高原[9]26。风靡于奥斯曼宫廷艺术的Saz 风格由大不里士的艺术家沙库鲁(英语Shahkulu,土语Şah Kulu )设计。他从萨法维移民奥斯曼之后,1526 年加入由苏莱曼大帝领导的皇家工作室,并于1545 年成为工作室的负责人。他在工作的42 年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沙库鲁设计的Saz 风格,重新诠释了14 世纪流行于伊朗高原的水墨画艺术,给奥斯曼带来了新的装饰艺术风格;此外,这种风格还架起了萨法维大不里士画院与奥斯曼宫廷画院之间的桥梁。Saz 风格风靡于16 世纪中期至17 世纪中期,它几乎出现在各种艺术上,包括墨画(Saz Yolu)、细密画、书籍插图、瓷砖、瓷器以及各类纺织品上。墨画上的Saz 风格大多是通过熟练的想象并使用芦苇笔绘制,所以又称为芦苇风格。
Saz风格设计为程式化、尖锐而弯曲的匕首形叶子,边缘有清晰的锯齿,它可以单独作为装饰主题,也会与具有西亚、中亚和东亚艺术元素的龙、凤凰、狮子等生物(图5)一起使用。极富动态的Saz 风格丰富了土耳其的装饰艺术宝库。龙与凤凰在萨法维的细密画中也常出现。萨法维艺术中,龙作为绘画元素应该是13 世纪末至14 世纪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蒙古西征时期将大量的中国艺术元素带入伊朗高原,而凤凰在伊朗神话与文学作品中是代表仁慈的神鸟森穆夫。波斯艺术中,龙与凤凰组合在一起以争斗、对抗的姿态出现,应是波斯祆教中的善恶两元论和宗教意识形态斗争的艺术化表现。这种具有象征主义的绘画方式也被奥斯曼的艺术所借鉴。此外,沙库鲁在奥斯曼宫廷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奥斯曼宫廷艺术代表Kara Memi 即是其中一位。

图5 墨画龙凤搏斗,16 世纪中叶,Sahkulu 作品收藏
16 世纪20 年代是奥斯曼帝国设计与装饰艺术探索的时期,这在书籍装帧、纺织及建筑装饰中有所体现。塞里姆一世的东方征服活动和苏莱曼大帝的早期军事冒险为奥斯曼宫廷带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品和艺术家。萨法维第一个首都大不里士被誉为“波斯地毯之乡”,它的地毯类型囊括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波斯地毯。萨法维和奥斯曼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1514 年当奥斯曼帝国在击败萨法维王朝的首位沙阿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501-1524 年在位)时,战利品包括1000名呼罗珊(Khurasan)的艺术家和38 名大不里士的艺术家和工匠,其中有3 位就是编织工人。
当大不里士的地毯编织工人和艺术家们到了奥斯曼的宫廷时,势必会给这里的地毯生产打上萨法维文化的影子。奥斯曼一方面继承了塞尔柱克时期对几何形的偏爱,也展示出了其兼容并蓄的大国胸襟。有文献资料记载,在1558 年、1567年和1581 年[10]244-245,萨法维的地毯被当作礼物送到了奥斯曼帝国。同时,萨法维的地毯和生丝也随着亚美尼亚人的陆路贸易网络来到奥斯曼。生丝的到来,为奥斯曼生产奢华的丝质地毯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不过后来经常性的对抗与作战使得贸易路线的安全性出现了问题。于是,奥斯曼地毯逐渐摆脱了萨法维时期复杂多样的地毯装饰影响,继续将几何形态的图案发扬光大。此外,奥斯曼时期地毯上流行的“拱门”形式(即清真寺内的壁龛mihrab)的地毯图案也反过来影响到萨法维和莫卧尔(Mughal)。奥斯曼时期的地毯图案显示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排除掉其自身深远的地毯编织历史影响外,还得益于当时丝路贸易的畅通与繁华。此外,伊朗的工匠将天鹅绒编织技术与提花机在奥斯曼之前的拜占庭与塞尔柱时期就引进到了安纳托利亚。15 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制作了精美的天鹅绒,它们也随贸易来到了大不里士,并对当地的天鹅绒装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结语
在一个瞬息万变且多元的政治环境中,奥斯曼帝国脱颖而出。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在宏大的帝国愿景驱动下,奥斯曼帝国政体接受了与之接触、吸收、并置和综合了来自广阔且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致使现存的文化交流渠道得到扩展与深化,并糅合出新的文化形式。当然,交流方式不乏各类征服、贸易与外交活动。以上共同塑造了15 世纪奥斯曼帝国动态的文化折衷主义。16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对马穆鲁克和萨法维领土的入侵给奥斯曼宫廷带来了大量的艺术家、工匠和艺术品。站在奥斯曼的角度看,伊朗萨法维和中亚、安纳托利亚东部、埃及马穆鲁克(Mamluk)、拜占庭和意大利的艺术文化被开放的奥斯曼接受并糅合,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异质视觉文化系统,这是帝国视野的反映。尽管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新视觉语言与与更宽泛意义上的伊斯兰世纪和地中海世界的视觉语言截然不同,却又处处体现出了联系。这个时期那些稳定中又包含变通的装饰元素成为以后奥斯曼装饰风格继续探索与发展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艺术家们不断诠释并给予新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