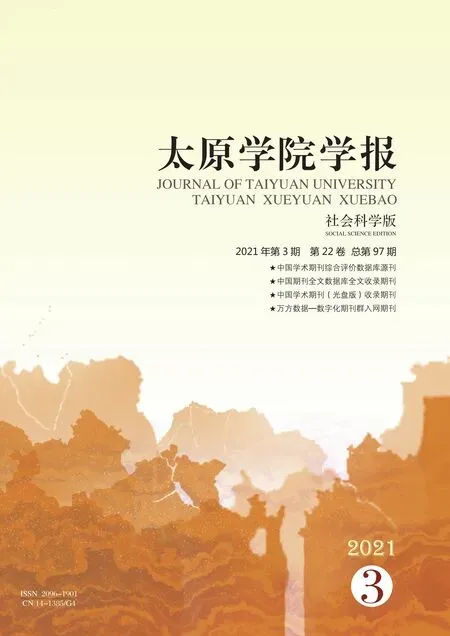论刘勰“通变”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平 雷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中,对文学发展规律、文学创作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作了辩证统一的阐述。在一代代学者的持续研究中,《通变》篇在《文心雕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被逐渐巩固和增强。目前,学者们对《通变》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变”说的主旨、“通变”说的文化渊源、“通变”说在《文心雕龙》一书中的体现等方面。而自从刘勰把“通变”说从哲学领域引入到文学领域,“通变”说就对我国千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专就刘勰“通变”说对唐、宋、元、明、清历代文论的影响进行探究,力图揭示出我国文论领域“会通”与“适变”的分合演变过程。
一、 刘勰“通变”说的涵义辨析
关于刘勰“通变”说的主旨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最早的观点是“复古而名以通变”[1]521,代表学者为纪昀、黄侃和范文澜;第二,认可度最广的观点是继承与革新,代表学者为周振甫、王运熙、樊德三等;第三,认为刘勰“通变”说侧重于“变”,代表学者有石家宜、詹福瑞、蔡钟翔等;第四,从“继承与革新”观发展而来的“会通适变”观,代表学者有蔡钟翔、胡继华、童庆炳等[2]。认为刘勰“通变”说仅侧重于“通”或“变”都是偏颇的,这种片面的观点已经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而“继承与革新”和“会通适变”都体现了“通变”说既重“通”也重“变”的辩证统一性,但一些学者认为“继承与革新”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阐释不符合“通变”说的本义。笔者则认为,“会通适变”所说的实质上还是“继承与革新”的问题,只是“会通适变”更能凸显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即继承是革新的基础、革新是继承的目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接下来,笔者就通过对《通变》篇原文的分析,来阐释刘勰“通变”说的具体涵义——“会通适变”。
《通变》开篇就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内容,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1]519在此,刘勰首先阐明了诗赋书记等各种文体的名称及原理(即《宗经》篇所谓的“体有六义”)是应该继承的,而文辞和文风则既需继承也需革新。多数学者只意识到了“文辞气力”之“变”,却忽视了“文辞气力”之“通”。其实,只要参看《宗经》篇和《风骨》篇的相关论述,便可理解刘勰所谓“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的全面内涵。《宗经》篇曰:“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1]23换言之,经典作品不仅是设立文体的依据,也是丰富文辞的宝库,这就表明了文辞也需要继承。此外,《风骨》篇曰:“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1]514这里指出“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晓变”即“洞晓情变”,而“洞晓情变”的前提就是“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这里虽然偏重于强调“情变”(即文风之变(1)《风骨》篇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也云:“即谓辞精则文骨生,情显则文风生也。”可见文风与情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笔者认为此处的“情变”即是文风之变。)与“辞新”这两个革新的范畴,但仍然没有忽视二者革新的前提是继承。接着,《通变》篇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1]519这里用比喻论证的方法说明了“通变”的重要意义——“通”即可“饮不竭之源”,“变”即可“骋无穷之路”,而只有“通”与“变”都擅长的人才不至于“衔渴”和“辍途”,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刘勰提出“通”“变”并重的观点之后,便举例说明任意忽视一方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刘勰认为,文辞越来越缛丽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这一变化从九代到商周莫不如此,但它们在“序志述时”方面仍然沿袭了一致的原理,这就是刘勰所欣赏的善于“通变”者。而同样是在文辞方面不断新变的楚汉至宋初的文学,却被刘勰批评为“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因为他认为楚汉至宋初的文学只在文辞上“竞今”求变,在文理上却“疏古”忘宗,以致“风末气衰”[1]520。那该如何挽救时弊呢?刘勰曰:“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1]520“还宗经诰”即是《宗经》篇的主旨,有学者由此便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复古主义的、文学发展观是退化的,完全忽视了紧跟其后的“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1]520笔者认为刘勰对“质文”和“雅俗”这两对范畴的态度是中立的,“质”和“文”都需要仔细考虑,“雅”和“俗”也必须恰当矫正,“质”“文”“雅”“俗”既要“会通”又要“适变”,如此理解更符合刘勰在《序志》篇自述的“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727的思想观念。另外,《征圣》篇曰:“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1]16这既是刘勰“折衷”观的另一体现,也是“通变”说意指“会通适变”的另一力证。
随后,刘勰摘取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马融《广成颂》、扬雄《羽猎赋》和张衡《西京赋》中的文字来进一步阐释“参伍因革”的“通变之数”[1]521。五人极写广阔之状的主旨是相循如一的,但由于文体差异、才性各殊等原因,五人文字的沿袭和革新情况却各不相同,刘勰认为这就是“通变”的数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的解读更加清晰,其文曰:“必于古今同异之理,名实分合之原,旁及训故文律,悉能谙练,然后拟古无优孟之讥,自作无刻楮之诮,此制文之要术也。”[1]527“此制文之要术”用刘勰的话来说即是:“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髻,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1]521这一段与第一段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遥相呼应,但此处补充说明了“会通适变”的要领在于“凭情负气”(2)笔者认为“凭情以会通”和“负气以适变”两句是互文,所以将两句合并参看。,即情真气盛才是“会通适变”成功的关键。最后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1]521精辟地概述了文学通过“通变”而不断发展的规律,以及“通变”应把握时机和权衡内容的问题。
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规律决定了“通变”说的产生,《易传》的通变思想也为文论中的“通变”说提供了哲学依据。此外,挚虞、葛洪的通变观念也为刘勰“通变”说奠定了基础(3)参见孙敏强《试述“通变”观的历史发展——兼论刘勰“通变”观》一文。。但《通变》篇首次以“会通”“适变”结合论文而创立了系统完整的“通变”说,这一“通变”说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中国文论内部“会通”与“适变”的矛盾冲突,而正是这一矛盾冲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论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持续发展。
二、千年文论领域“会通”与“适变”的分合演变
“通变”说论定了文学创作中“会通”与“适变”相统一的特性,以及继承与革新共同推动文学发展的规律。然而,由于各个时期文坛风貌与个人思想观念的差异,后代的文论家们却并未沿着刘勰“通变”说的路径行进,以致我国文论领域呈现出“会通”与“适变”不断分合演变的复杂情况。
钟嵘《诗品》专门研究诗歌继承及流派的问题,无疑就是侧重于文学创作中的“会通”特性。钟嵘根据作家风格的相似度,把他们分入小雅、国风、楚辞三大流派中,并依据朝代顺序指出他们的师承关系,比如他说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3]111钟嵘侧重研究诗歌的师承问题,而忽略诗人的创造性,难免显得片面和牵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钟嵘《诗品》也反映了六朝诗坛盛行着学习仿效前代名家之风,这一风气持续萦绕我国文坛两千年都未曾消散。如果说钟嵘《诗品》只是从“会通”的角度梳理了诗坛的继承现象,那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摸拟》中则论述了“会通”的两种方法,即“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4]291。《史通·摸拟》曰:“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4]303可见刘知几所认可的模拟方法为“貌异而心同”,即“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互同,若斯而已。”[4]296这不是胶柱鼓瑟、亦步亦趋的复刻,而是遵循“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4]296之发展逻辑的正确继承方法,与刘勰《通变》篇中“参伍因革”的“通变之数”相同。由此可知,刘知几在《史通·摸拟》中提倡的模拟方法兼具“会通”与“适变”的内涵。
刘知几曰:“述者相效,自古而然”[4]296,这是文人学者受到“宗经”“征圣”思想熏陶之后的普遍观念。自从“宗经”“征圣”之说成为历代正统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文坛的复古之风就愈发热烈,这就不免冲淡了文学创作中的“适变”观念。当仿效前人时忽视“适变”,模仿就容易沦为抄袭。皎然在《诗式》中就严厉批评诗坛中的模拟现象为“偷语”“偷意”“偷势”[5]59。皎然“三偷”之说虽对“三同”的评价有高低之分,但都视三者为卑劣的偷盗行为。那么是否能以此断定皎然是反对模拟的呢?答案是否定的。《诗式》“复古通变体”一条中清楚地阐释了皎然的“复变”观,文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廐,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5]330可见,他虽极力主张诗歌的独创性,但也并未因此而否定复古的合理性。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和柳宗元在文坛上掀起了第一阵复古热潮,但其实他们是打着复古的旗帜而进行革新。韩愈《答刘正夫书》云:“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俱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6]192“师其意,不师其辞”,然后“能自树立不因循”,从这种观点中能清晰地看到刘勰“通变”说的影子。同样地,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传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7]278该段论述了柳宗元通过参考、学习经典作品来作文的方法,这种“旁推交通”的手段并非泥古不化地复古,而是与刘勰的“通变”说相通的。李翱和皇甫湜作为古文运动中的干将,也非常重视文学的革新,比如李翱云“创意造言,皆不相师”[8]41,皇甫湜云“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9]3。然而,刻意追求异常和出众容易走上艰涩怪癖的歧路,这又是偏重“适变”而忽视“会通”的后果,晚唐时的孟郊和贾岛就是一个典例,在此不作赘述。
到了宋代,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中都鲜明地体现出“会通适变”精神的无疑就是黄庭坚。黄庭坚在《与洪甥驹父》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0]401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也说:“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11]15-16“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都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化用前人作品而推陈出新的文学“通变”之法,这在黄庭坚的创作中也有体现。另外,吕本中的“活法”说又进一步补充了黄庭坚的“点夺”说,他在《游远堂诗集序》中云:“顷岁与学者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俱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卒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12]1758掌握“活法”的关键就在于明白什么是可变革的、什么是不可变革的,进而能够遵循规矩而又不囿于规矩,这与刘勰《通变》篇所谓的“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观点也遥相呼应。宋代除了上述与刘勰“通变”说一脉相承的文论外,依然存在偏重于创新或复古的论断,前者代表为姜夔,后者代表为严羽。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说自己本来以黄庭坚为师,但“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俨然高阁矣。”[13]3他在《白石道人诗说》中又云:“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虽鸡林其可欺哉?”[13]89由此可见姜夔反对学习模仿,主张自出机杼,成一家风味。与此相反,严羽论诗十分重视选择学习模仿的对象,他批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和四灵诗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满意这三家的师法对象。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开篇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4]1他认为汉、魏、晋、盛唐之诗是第一义,应该熟参、妙悟,并断言应以盛唐为法,还自诩指出了学诗的“向上一路”。姜夔主张自成一家和严羽主张取法乎上都是有道理的,但不论偏执于哪一方都是片面的,应该把自成一家当做取法乎上的目标,而取法乎上则是自成一家的必要手段。
明代前后七子又一次在文坛掀起了复古热潮,代表人物为李梦阳和何景明。两人虽然都属于复古派,但他们却在学古的观点上发生了争执。何景明在《与空同先生论诗书》中云:“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15]8何景明主张的学古方法是“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所以他批评李梦阳那种“铸形宿模”“独守尺寸”的学古方法。何景明还说:“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15]10何景明反对学古而成为古人的影子,他只是把学古当作学习作文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以传不朽”[15]10。何景明不仅深明“达岸则舍筏”的学古之法,而且明白文学的变化发展之理,他说:“故法同则语不必同矣。仆观尧、舜、周、孔、子思、孟氏之书,皆不相沿袭,而相发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广,此实圣圣传授之心也。”[15]10这种进化发展的文学史观,是何景明学古而不泥古的思想基础。可见,何景明的学古观点包涵着灵活适变的内涵,可与刘勰“通变”说参看。与之相比,李梦阳的学古观点就过于死板和偏狭。李梦阳十分重视学习并遵循古人的法规,他在《驳何氏论文书》中云:“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形,剪裁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悉不可也?”[16]7李梦阳辩解自己主张的复古只是学习古人的法规,看似很有道理。但他把古人的法规当做不可变更的原则,不懂得法规也需要灵活运用和变更进步,就难免自设牢笼而成为古人的奴隶了。由于李梦阳对古人法规的迷信,他甚而反对何景明主张的自立门户一说,《再与何氏书》云:“今人止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宜其谓守法者为影子,而支离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宽也。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16]10这又是极端的拟古理论了。
明代文坛虽流派纷争,但各流派的文学主张其实难出复古与趋新这两大潮流。例如与七子之拟古理论针锋相对的唐宋文派,与七子的差别仅在于前者“文必唐宋”而后者“文必秦汉”,二者本质上都是重摹拟的流派。唐宋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唐顺之,在其文《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谈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17]466唐顺之反对七子“文必秦汉”的主要原因即他认为秦汉之文法“密而不可窥”,无法学习,而他提倡的唐宋文法不仅可学,并且“严而不可犯”。因此,唐宋文派并未修正七子引燃的复古之火,反而为之添薪加油。然而,随着明代文坛复古理论的流弊逐渐暴露,文坛上自然出现了反对者,声势最大的便是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对“凡有一语不肯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18]284的复古风气十分不满,他的学古见解与何景明类似,《论文上》云:“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学耶?余曰: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18]284袁宗道认为古今语言有别,今人学习的古文中的奇字奥句其实只是古人的街谈巷语,所以他认为“学达即所谓学古”,“不必泥其字句”。袁宏道也毫不客气地揭露和批评复古流弊,他在《雪涛阁集序》中云:“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9]709又云:“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19]710他认为文学的演变是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正如他在给江进之的一封尺牍中所云:“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19]515既阐明了文学发展递变的原因,又批评了拟古者厚古薄今的错误心理。为了纠正“剿袭模拟,影响步趋”[19]188的模拟之弊,公安派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9]501,极力倡导自然平易的文风。 但这种主张一经追捧则又造成了俚率僻涩的文病,于是竟陵派应时而出,双管齐下——既矫七子复古之弊,又矫公安趋新之病。钟惺《诗归序》曰:“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肤学古者之心!”[20]289-290前一句批七子之复古,后一句批公安之趋新,其论洞见了两家的症结所在。为纠两家之弊,他主张“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20]290,即求古人之精神。《诗归序》曰:“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20]289换言之,他一面主张学习古人之精神,一面又主张于精神上求变,让人无法忽视此通达之论与刘勰“通变”说的暗合性。但创作实际往往难以像理论主张那样圆满,竟陵派力纠七子和公安之弊,却又纠弊生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论及钟惺时曰:“其所谓幽深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21]571这又是竟陵派标举“幽深孤峭”所滋生的流弊了。
如上所述,明代文坛流派纷争、互相攻讦,这样各执一端便难免矫枉过正,纠弊生弊。这种互争的风气还一直延续到了清初文坛:诗歌领域有学唐与学宋之争,散文领域则有学秦汉与学唐宋之争。直到叶燮基于历史进化观而建设了一套深有洞见且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才有力地矫正了文坛的偏狭之弊,再次回归于“会通”与“适变”的统一。叶燮的文学理论观点主要见于《原诗》内外篇,《原诗》虽是论诗著作,但其中所述观点适用于一切文学。《内篇上》开篇即云:“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22]1首先就揭示了由“理”“势”决定的文学盛衰嬗变的历史进化规律,不仅反驳了明人厚古卑今的退化观,也为文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叶燮对于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都深有见解。从文学的继承性一面来看,叶燮云:“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22]104“取材于古人”之后还要能善用其材,即“夫作诗者,要见古人之自命处、着眼处、作意处、命辞处、出手处,无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如医者之自治结疾,先尽荡其宿垢,以理其清虚,而徐以古人之学识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后匠心而出。我未尝摹拟古人,而古人皆为我役。”[22]107从文学的创新性一面来看,叶燮云:“惟数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终无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谓变化。”[22]113-114他推崇的是像杜甫那样“变化而不失其正”[22]114的创新者,由是便引出叶燮主张的“自然之法”,即“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22]118之法。因为叶燮认为理、事、情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22]150,“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22]125这种“自然之法”属于不可言说的“活法”,出自作者的匠心变化,与吕本中所谓“变化不测,而卒亦不背于规矩”的“活法”有相通之处。《原诗》体大思精,笔者无法一一论说,但在此略举一二论例,便足以窥见叶燮“会通”与“适变”兼明的论文思想。这样一部综贯诗学的作论之书一经问世,就对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林云铭为《原诗》作序时所言,《原诗》“直抉古今来作诗本领,而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娓娓雄辩,靡不高踞绝顶,颠扑不破。”[22]1沈衍也称《原诗》“权衡乎诗之正变与诸家持论之得失,语语如震霆之破睡,可谓精矣神矣。”[22]4《原诗》的论断是否果真颠扑不破暂且不论,但两人盛赞其“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及“权衡乎诗之正变与诸家持论之得失”,则确属持平之论。自此,不仅文坛一洗偏胜的流弊,而且后人论诗也多暗袭叶燮之说。
三、小结
纵观我国千年文论领域“会通”与“适变”的分合演变过程,以“宗经”“征圣”之说为思想渊源的“会通”思想始终活跃于文论领域。在“会通”与“适变”思想的矛盾斗争过程中,我国文论不断发展,文坛风气也随之变更。当“会通”与“适变”的矛盾冲突相对调和时,文学创作可以学古而自成一家,比如韩愈、柳宗元和黄庭坚;当“适变”思想处于斗争上风,文学创作容易走上艰涩奇奥之路,比如贾岛和姚合;反之,一味泥古只会落到模拟抄袭的境地,比如李梦阳。明代各派则偏执一端,复古或趋新彼此纷嚣,导致文坛上一弊刚纠而一病又起,直至叶燮的《原诗》问世,才再次调和文论中的“会通”与“适变”之冲突,终于回归刘勰《通变》篇的“通变”说的轨道,从而解决了文学创作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千年文论领域“会通”与“适变”的分合演变,乃是刘勰“通变”说直接或间接影响后产生的能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