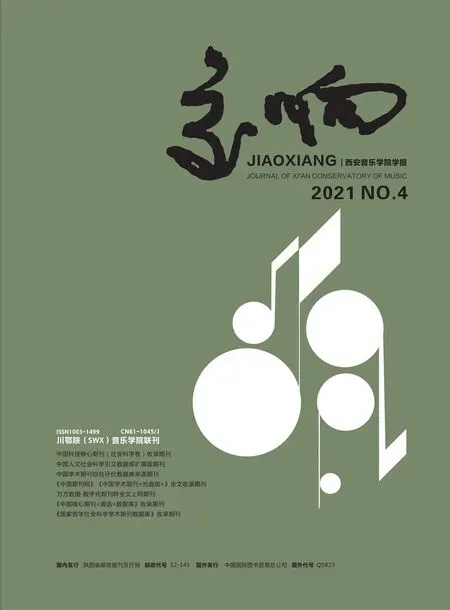古稀乐器筹的传承与“非遗”传承人认定
●高飞胜
(星海音乐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封大相国寺梵乐的代表性传承人释隆江,俗名孙洪德,1926年8月19日生于商丘市民权县白云寺村,早年出家,随寺院师父学习梵乐和管子演奏,1940后多次到大相国寺内“偷学”筹的演奏技艺,解放后还俗、结婚生子,和邻居碰班子(吹唢呐班),演奏管子、筹。1957年3月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用筹演奏了梵乐《报中台》,获二等奖,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返乡后被安排到民权县豫剧团工作。后迫于生计而辞职,继续在民间唢呐班吹打营生,20世纪80年代末,宗教场所陆续得到恢复,他经常被邀请到村内的白云寺表演乐器筹,在当地享有名望,《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南卷》编辑部曾采录他演奏的《报中台》《胡溜》《油葫芦》3首筹曲[1](P1362-1371)。2000年,受开封大相国寺住持之邀来寺教习梵乐及古稀乐器筹,2008年伴随该寺梵乐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隆江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逝世。隆江在大相国寺期间,多次登台演奏,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古稀乐器筹的魅力,还将自己掌握的演奏技巧和制作工艺,传承给徒弟源悟等乐僧,使这一濒危的古稀乐器免于绝迹、后继有人。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质疑其传承人身份,由此也使大相国寺梵乐传承的正统性和本真性受到争议,故而亟需对隆江的从艺经历和师承关系再做探讨。
一、筹在大相国寺的传承及问题的提出
开封大相国寺始创于北齐天宝年间(555年),北宋时作为皇家寺院名扬天下,寺内音乐异常丰富、达到鼎盛。直到民国时期,寺内音乐活动依然形式多样,精彩纷呈。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省,驱僧灭佛,寺内的佛乐队解散,僧人被迫离寺,个别乐僧只能住在寺外的“乐西精社”习乐学艺,偶尔献演于附近剧场和民间丧仪以维持生计。1938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开封后,建敌伪政权,为美化侵略,于1940年将流落民间的释润生等僧人召回①,重新恢复佛事和音乐活动,并剃度了十几位幼僧传习梵乐,王宗葵②便是其中之一。
筹是我国一种吹奏乐器,一管双音,“似笛非笛,似箫非箫”,集边棱音和唇振类发音原理为一体,箫和笛两种音色同在,斜吹和直吹两种吹奏方式并用,且使用两种方式吹奏的音高互补,音域宽广,开笛膜与未开笛膜两种形制并存,未开膜孔的筹同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贾湖骨笛形制基本相同。现存宋时建筑中存有筹的图像,可知筹在北宋时已在开封佛教界流传。但因缺乏文献,尚不清楚筹何时开始在大相国寺传承,只能借助于当代人的回忆和口述。据王宗葵回忆,1940年,大相国寺的乐僧有释润生、释安伦、释安修等人,1944年,他到大相国寺后,便开始跟随师父释安伦学习筹、锡管等乐器。[2](P4)王宗葵还提到,筹的演奏者必须由音乐修养较高的人来担任,凡是乐队要突出才能和水平时,筹就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无形中控制着整个乐队。[3](P15-17)可知,至晚1940年,筹依然在大相国寺流传。1948年,王宗葵离寺还俗,几年后佛乐团再次被解散,乐器筹也随乐僧们散落民间。此次乐队恢复虽然短暂,但在大相国寺梵乐以及筹的传承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大相国寺的申遗材料反映出,隆江于1938年到大相国寺拜释安伦、释安修二位乐僧学习佛乐。③
学者王玉、都本玲以及隆江白云寺村的徒弟张永等人认为释隆江应是白云寺音乐传承人,并非大相国寺梵乐的直系传人,并猜测“造成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为了申报成功,地方政府故意对大相国寺的传承进行夸大。还指出这种地方申报、国家批准的项目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长时间的发展,有关大相国寺梵乐的源流只有伪历史,而历史的真相将不为人知。[4](P14-26)王玉根据其爷爷王宗葵的口述材料及上述观点认定“释隆江法师非大相国寺佛乐直系传人,属于白云寺佛乐传承系统,是于2002年才来到大相国寺传授佛乐的。”[5](P14-26)隆江的徒弟张永在访谈中提到“隆江师父没有在大相国寺学过筹”,并认为大相国寺掩饰真相,是为了给人以传承有序的印象。④
二、释隆江的习筹经历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到隆江的家乡商丘市民权县白云寺村访谈了他的家人、徒弟和邻居,并拟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进行梳理。
(一)关于出家地
最早对隆江研究的学者朱国龙提到“释龙江是河南四大名寺民权白云寺僧人。1927年出生于民权县尹店乡白云寺村。自幼家境贫寒,六岁伤父,母亲将其送往白云寺削发为僧。进寺后师从苍海(号:月波)学习寺庙音乐。练习笙管笛筹等乐器,以练习吹筹为主……后随苍海师父到睢县涧岗天兴寺。”[6](P18)吹筹老艺人文虎在介绍隆江时所说略同。[7](P22-24)商丘籍学者孟庆民说“现白云寺代表性传承僧人是释龙江,1923年8月生,原名孙洪德。1934年,10岁的孙洪德被送到白云寺,皈依月波法师为徒,法号释龙江,1938年开始学习吹筹技艺。”[8](P247-248)这三位学者虽共同认为孙洪德是在白云寺出家,但在法名和出家年龄等具体信息上也有出入。⑤
释隆江同村的同龄人马世兴老先生则提到,“隆江的师父叫月波,姓陈,家是民权县龙塘乡蒋坡楼村的。最初,隆江跟着月波在刘庄的一间小庙里出的家,两三年后才挪到涧岗镇(睢县)上的庙里。隆江在刘庄没有学佛乐,到了涧岗才开始学的。月波的侄子陈二小、睢县榆厢镇的大屯,也是跟着月波学的管子,那时候他们可厉害了,号称“三门管子”,在俺这一片都可响(影响力大)……。”⑥相比学界对隆江的个人信息各执一词的情况来说,马世兴老人的信息更为详细、准确。隆江的出家地并不是白云寺,而是睢县一个不知名的小庙。随师父迁到涧岗镇的小庙后,他才开始学习演奏管子等乐器。
(二)关于习筹地点
青年学者章俊于2002年到隆江家中对其访谈时得知,“12岁时,他(即孙洪德)作为子孙寺庙的僧人去开封大相国寺里看法事时,见到一60多岁的乐僧在吹这个乐器,觉得声音松脆,很好听,就留下来学吹了几天,回去后自己又狠下功夫苦练,这才掌握了一般人难以掌握的吹筹技艺。说起相国寺这个乐僧时,孙老因为当时年幼并不知道更多情况,甚是遗憾。”[9](P6)《民权游览》载曰:“隆江对寺庙里的佛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听得痴迷。一次,他和师父去开封相国寺,见相国寺的僧人在演奏筹乐,美妙的乐曲令他流连忘返,他立志学习筹的演奏技能。隆江苦心学习,……筹的演奏技能日臻成熟,即使嘴唇远离吹孔几公分,仍能照常演奏,令观众惊讶不已。”[10](P55)由此两则资料可以看出,隆江的习筹地应在开封,和大相国寺有密切关系。
(三)关于习筹的经历
据开封市志记载和王宗葵回忆,1927年大相国寺僧人被全部赶出寺院,直到1 9 4 0 年才被敌伪政府召回。由此可知大相国寺非遗申报书的表述确有问题,隆江1938年到大相国寺内拜乐僧释安伦、释安修习筹一说,因而在学界遭到了质疑。青年学者方默涵曾于2007年、2008年三次采访隆江,部分内容如下:
问:您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见到释安伦、释安修的?
答:好像是1939年。
问:您是在大相国寺见到安伦、安修的吗?
答:不是,是在人民剧院,1939年我到开封白衣阁办事,听白衣阁僧人讲,大相国寺乐僧在“人民戏院”⑦吹奏佛乐,叫我去听听,我去了,听了大相国寺乐僧们的演奏,感觉非常好听,特别是那管斜吹的乐器,后来知道叫“筹”。……
问:你是那时拜安伦、安修为师吗?
答:不是,那时小,不敢去说。有机会到相国寺就偷听,回去自己练,再教白云寺的乐僧。[11](P25-26)
隆江对第一次看到大相国寺乐僧演奏筹的时间已不确定。这也合乎常理,让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回忆70年前发生的事情,有些出入也再所难免。正如王建民教授所言:“我们不能把生活史看成是对于过去事实的完全不折不扣的陈述。生活史访谈中研究者不应该简单的指责报道人年代表述错误,更不能因此就说报道人所说的话不足为凭。生活史并非生活本身,都经过了报道人场景性的选择和重新编排。报道人时间上的记忆模糊或混淆、失忆或记忆倒错都有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直接或间接原因。”[12](P36)所以,隆江的回忆是可信的,即1939年左右第一次在开封看到了大相国寺乐僧们演奏筹。他习筹时并未正式拜师,而是以“偷听”“偷学”的方式进行。偷学的地点既然是在大相国寺内,时间也应在乐僧们返回大相国寺之后,即1940年后。也正因是偷听、偷学,难怪王宗葵在回忆中记不得隆江有跟随其师父安伦、安修习筹的经历。
综上,隆江的梵乐和管子是在睢县涧岗的小庙中由师父月波所授,筹的技艺则是在开封大相国寺以“偷学”的形式师承释安伦法师。隆江并非在白云寺出家,而白云寺的筹乐乃隆江所传。可以说,正是这个“偷学”成才的弟子,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他将古稀乐器筹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故而无愧于国家级“非遗”开封大相国寺梵乐的代表性传承人。
三、“非遗”传承人认定工作的思考
通过此个案,我们能感受到“非遗”传承人认定工作的复杂性,也能看到民间技艺传承方式的多样性,而这些反映在传承人的评定方面,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信息来源背后的身份差异
在搜集相关传承人信息的过程中,专家学者、不同传承者、当地群众,甚至政府官员等,由于身份的不同,对于信息客观性、准确性等均有自己的判断,在研究者搜集过程中,可能会提供相互抵牾的情况,或者相同信息出现较大出入的情况等,需引起注意。比如,在对隆江艺术历程的文献整理中,笔者注意到:早期对隆江开展研究的艺人文虎指出,他是受赵沨先生所托对几位吹筹老人进行的调查,此时隆江的身份是还俗僧人和民间艺人。文虎作为吹筹老艺人,调查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各地筹的形制、演奏方式、技巧、持筹姿势和指法等内容。而对吹筹老艺人们的个人信息则有所忽略,从而导致对隆江的年龄等基本信息记载错误,这削弱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为传承人的信息收集和认证工作带来麻烦。
2000年始,隆江已到大相国寺准备组建佛乐团,章俊、方默涵二人于2002年、2007年对其进行了访谈,得出隆江的筹艺是在大相国寺所学的结论,并强调其并未拜相国寺的乐僧为师。方默涵还指出隆江学习的形式为“偷学”,对其传承人的认定提供了有力支撑。2002年大相国寺佛乐团刚成立,寺院还未启动申请国家非遗工作,2007年已启动。两人在不同时间段访谈所得结论基本相同,说明隆江对二人所讲内容变动不大,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当事人的口述史。
2 0 0 8 年隆江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012年,王力指出,隆江的筹是在大相国寺所学,并强调寺内70多岁的吹“筹”僧人曾收其为关门弟子,将运气法、练习步骤全部传授给他,还对隆江在寺内试奏的情景进行了详细描述。[13](P8-9)此说看似详细,但缺少时间节点,字里行间带有较强的修饰色彩,有虚构故事、牵强附会的嫌疑。尼树仁也持同样观点,同大相国寺的申遗材料说法一模一样,连括号内的补充内容都一字不差。[14](P447)时间、地点、人物关键因素具备,但这与隆江本人的说法明显存在出入,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不符。尼树仁先生是业内方家,自1982年起便系统研究大相国寺佛乐,其观点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关注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从艺历史和生活史,做好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是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关键。隆江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众多基本信息都存在错误,一般民间艺人更可想而知。“见戏不见班,见班不见人”正是学术界对民间艺人态度的高度概括。
综上,我们开展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时,要深入开展实地调查,加强审核力度。在审核工作之前,一定要组织专业的调查小组对每一位申报人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调查,充分听取申报人所属社区、行业多数人的意见,形成较为客观的调查报告,为下一步的审核工作提供支撑。审核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最为复杂的一环。相关部门应该抱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加大此环节的执行力度,实事求是,严格审核。只有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评选结果才会更加透明、公平、公正,更有说服力,代表性传承人才能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可,相关部门的工作才会让广大人民更加信服。
(二)资格认定中的利益诉求
国家级“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认定,牵涉地方主管部门及传承者本人的“利益”,难免会引发一些人为的不实信息。隆江的个案可供我们管窥一斑。隆江弟子张永的提醒(见前文)值得引起注意。商丘当地的学者孟庆民也认为隆江应是白云寺音乐的传承人。他在2011年的文章里提到,乐器“筹”早在宋朝时起源于民权白云寺,并强调隆江为白云寺的代表性传承人,但淡化了其师承背景。他从隆江的从艺经历和乐器筹传入白云寺的历史入手来证明这一观点。后来笔者得知,此文是孟老师受民权县非遗传承中心工作人员所托书写而成,部分材料由该中心提供。但文中隆江的年龄和实际竟相差3岁,这难道是笔误?其所提的筹起源于白云寺这一观点明显与商丘当地诸多文化志、县志等存在矛盾。而且,也未提及此观点的出处和参考文献。所以,孟文显然缺乏说服力。
王宗葵作为开封大相国寺梵乐的直系传承人,面对隆江这位外寺僧人被认定为本寺佛乐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家人、徒弟对隆江的传承人身份提出质疑,似在情理之中。另外,开封大相国寺内现在保存的手抄乐谱并非是王宗葵直接提供,而是由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回赠给寺院的。按常理说,乐谱本是寺院历代乐僧所传,王宗葵作为相国寺音乐的传承人,将保存的乐谱交回给寺院应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寺方请他回来寺内传承梵乐也应是最佳人选。但事实并非如此,故也引人遐思。
(三)传承过程的复杂多变
2019年,国家文化与旅游部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3号)第七条明确规定:“认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履行申报、审核、评审、公示、审定、公布等程序。”
民间艺术传承有世传、师传、灵传等方式,在传承过程中不一定延续单一的渠道。如释隆江作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出入于四个寺院,还曾在县豫剧团和民间唢呐班营生,其掌握的不同乐器又师承于不同的寺院和师父,而且师承方式也大有不同,有正式的拜师学艺,也有通过“偷听”“偷学”的方式学习技艺,他演奏的音乐既有原汁原味的佛教音乐《油葫芦》《报中台》,也有唢呐班经常用到的民间传统乐曲《胡溜》。如果不对其师承关系、艺术经历等进行详细实地考察,很容易忽略很多细节,而造成误会和诸多争议。
(四)传承谱系的多脉来源
释隆江作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身份之所以引起一些争议,就在于前述他学艺渠道的复杂性。邓启耀认为,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时候,传承人谱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定,都必须依据可以追溯的历史较为久远的传承谱系。根据传承谱系,我们可以追溯该文化遗产项目的文脉,梳理传承源流。但是,由于实际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传承情况,传承人的传承谱系,也可能是多脉的。在某地传承链环发生断裂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介入的“外缘续传”⑧。追溯释隆江的传承谱系,有来自不同寺院,也有来自专业剧团和民间唢呐班,学艺的师承和渠道不一而足,充分体现了“多脉传承”的情况。他被聘请到大相国寺吹筹,既是“外缘续传”,又是某种程度的“回归”。所以,关于何为他“正宗”传承地的争论,其实意义不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大,我们应该严格按照认定与管理办法审核传承人的申报材料。审核中,要结合传承人的口述史,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检验、补充,多种办法并重,最大限度地弄清楚传承人的从艺历史,理清其师承谱系,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审核认定工作提供有力参考。
注释:
①据尼树仁介绍,他还有幸拜谒过两位大相国寺老乐僧,一位是释云阶,精于吹管、筹、笛等,曾被释润生方丈召回,1950年土地改革时被迫离寺还俗;另外一位是刘心田,开封市尉氏县盆窑村人,善吹管、筹,1927年被驱出寺,后未返回。
②王宗葵,1930年生,原名王松年,开封人,大相国寺曹洞支系第29代僧人、专职乐僧,大相国寺梵乐传承人之一,法名释佛禅、法号明静,1942年在开封大相国寺师从释安伦、释安修学习筹和三弦等乐器,1948年还俗,参军,1952年到中国民族歌舞团任三弦演奏员,现已退休,生活在北京。1977年,王宗葵从其师父释安伦的遗物中发现寺内乐僧代代相传的大相国寺手抄谱本,并于2013年出版发行,使这一宝贵的乐谱资料公布于众。
③大相国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2007年6月18日,内部资料,未出版。
④访谈对象:张永,民权白云寺村人,从小跟随外公学习唢呐,经常和隆江法师一起吹唢呐,小时候曾跟随隆江法师到开封白衣阁给净严法师祝寿,也曾参加净严法师的圆寂法会,并演奏梵乐。1997年拜隆江为师,学习演奏筹和管子,2002年到大相国寺任专职乐僧,2006年返回老家,现自己经营一个唢呐班,在当地名气很大。访谈时间:2019年2月16日下午,访谈地点:张永家。
⑤一是认为其法名应是“龙江”,并非“隆江”;二是出家年龄不同,一说6岁,一说10岁;三是出生日期不同,一说是1923年,一说是1927年,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网站上所公布的日期则为1926年8月15日。
⑥访谈对象:马世兴,92岁,白云寺村人,从小和隆江师父一起长大,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口齿清晰,表述准确。访谈时间:2019年2月16日,访谈地点:民权县白云寺村。
⑦方默涵核对为永乐剧场。笔者认为应为大相国寺西侧的人民广场,此建筑为冯玉祥主政时修建,原名为“国民大剧院”,后改名为“开封人民会场”,此处长期为演出戏剧场所。建国后改为“人民电影院”“人民影剧院”,仍然经常上演戏剧,当地人也仍然习惯称其为“人民会场”。
⑧邓启耀《多重真实、多维整体与多脉传承——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几点思考》,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策、法规与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21年11月13日至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