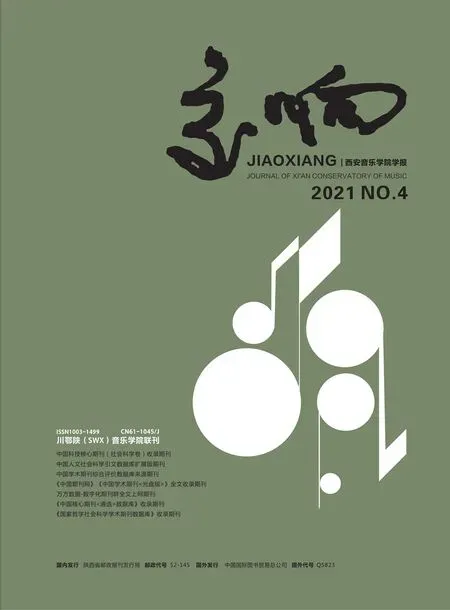丝绸之路弦鸣乐器的跨时空相聚与思考
●李 杨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832002)
一位居住在新疆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老艺人曾说:“汉族的琵琶和维吾尔族的弹布尔、萨塔尔、热瓦普、都塔尔,是父母亲的几个孩子——一家人。”这位精通维吾尔族多种弦鸣乐器老者的话意味深长,言语中似乎道出了古老丝路上多民族乐器同源而异流、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历史形态,让人不禁久久回味。
丝绸之路沿线曾经是众多民族音乐语汇的熔炉,丝绸之路上的弦鸣乐器也是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印证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民族风情。我国当代琵琶大师刘德海曾认为,中国琵琶可分为新疆派和江南派两个派别。[1](P69)这种观点体现了琵琶这件乐器与新疆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经学界前辈的考证与器物比较,认为琵琶与弹布尔、都塔尔、热瓦普等弦鸣乐器同属琉特家族中的成员,与古波斯的乌德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无论此说是否成立,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演变,受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不同传播路径的影响,琵琶也由西域经过丝路走向中原,历经各代艺术家的改造与发展,以其丰富的演奏技法和艺术表现力,在我国民族乐器中被赋予无上美誉。而弹布尔、都塔尔、热瓦普、萨塔尔等则在十四五世纪之后逐渐盛行于西域,成为今天新疆多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十二木卡姆音乐演奏的主要乐器,充满着浓郁的西域风情,展现了丝路弦鸣乐器在多元文化影响下蕴含的独特魅力。单从乐器形态构造的某些细节观察,似乎暗示着琵琶与新疆地区弦鸣乐器间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如果把这些“同源异流”的乐器放在一起切磋、交流,是否也有可以相互借鉴甚或融合之处?
一、图木舒克“斗琴”活动缘起
2018年9月,为了响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南发展”号召,笔者受所供职单位——石河子大学的委托,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所在地喀什地区图木舒克市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北倚天山,南牵叶尔羌河,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城市——图木舒克,坐落在公元前206年所建的唐王城故址以南,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将唐王城称之为“托库孜萨莱”(维吾尔语“托库孜”意为“九”、“萨莱”意为“宫殿”,整句意为“九座宫殿”)。唐王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里遗存有千年的胡杨、沧桑的烽燧、古老的龟兹文、神秘的佛教遗址。[2]站在崇墉百雉的唐王城遗址上,仿佛感受到了几千年前往来于这里的商贾驼队,他们在这里进行贸易交易并传播着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曼妙的西域音乐旋律回荡在山野之间,穿过蜿蜒的叶尔羌河,跨过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连绵的天山山脉,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迈进。
图木舒克也是刀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2012年9月6日,图木舒克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刀郎文化之乡”,并建立了“中国(图木舒克)刀郎文化研究基地”。托库孜萨莱木卡姆是刀郎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一部分,被誉为研究维吾尔族音乐文化的活化石。“我为图木舒克刀郎文化所倾倒。每每听到刀郎音乐中强烈的节奏,都会情不自禁地舞蹈。为了发扬刀郎文化,我和同事努力搜集整理了一些刀郎文化乐曲,参与刀郎文化传承人的遴选活动。”新疆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皖新在提到图木舒克的刀郎文化时总是很兴奋。[3]据刘团长介绍,演奏托库孜萨莱木卡姆的十多名民间演奏者遍布图木舒克辖区内的五个团场的部分连队。已录制完整的托库孜萨莱木卡姆歌曲就有十二首,有三支刀郎歌舞演出队,一年演出刀郎歌舞一百余天。这些珍贵资料的提供为图木舒克地区的音乐文化开拓了更广泛的研究空间。
2019年5月,机缘偶然,在此支教的笔者结识了当地一群维吾尔族民间乐器演奏“高手”。与我一起工作的古再丽努尔·玉素甫得知我是琵琶专业的大学教师,很快介绍起她的家庭——父亲演奏萨塔尔,表哥善弹都塔尔、弹布尔,他们一家经常在劳动之余,邀请亲朋好友在自家院里葡萄架下以鼓乐相伴,欢歌热舞。
在玉素甫一家人盛情邀请之下,也为了亲身感受托库孜萨莱木卡姆的魅力,2019年5月20日的傍晚,我带着自己的琵琶来到玉素甫家里做客,古再丽努尔抱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还有她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全家人早早地就站在院门口迎接我的到来,使我倍感温暖。整洁简朴的农家小院里,葡萄廊、土炕、挂毯、还有几颗挂满青涩果实的杏树,洋溢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维吾尔族人喜欢在院子里种植桑、杏等树木,待树木成材后不但可以遮阴,还可以木材制作乐器。据老艺人介绍,他制作的弹布尔、热瓦普、都塔尔等乐器琴箱主体部分均取材于桑木,因为南疆大部分地区普遍种植该树种,且其耐旱性、稳定性相对较好,原材料的成本低,也能满足乐器本身在音色方面的需求。
当古再丽努尔把我引到她家的“穹纬”(会客室),映入眼帘的是房间墙壁上挂着的都塔尔。古再丽努尔说,这是维吾尔族家中常备的乐器。都塔尔是新疆民间古老的传统乐器,享有“维吾尔族乐器之母”的美誉。都塔尔的乐器名字应来源于波斯语(=dotār),意为“两根弦”[4],长柄半梨形琴身略宽于弹布尔。据在场的制作乐器的维吾尔族师傅吐逊·那买提说,都塔尔琴的面板取材于桃木、杏木,背板则选用干燥后的桑木制作完成。
在享用了古再丽努尔母亲精心准备的手抓肉、抓饭、凉拌米肠等丰盛诱人的维吾尔族传统美食之后,我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斗琴”交流。
二、鸣响于沙漠绿洲的丝弦乐音
此次交流活动之前,古再丽努尔的表哥已经相约了附近的乐手,他们听说玉素甫家里来了一位“琵琶高手”,非常兴奋,都纷纷带着乐器赶来了。十几位民间艺人中,有年近七旬胡子花白拉艾捷克的老人,有英俊潇洒留着小撇胡演奏弹布尔的青壮年,还有当地小有名气的乐器制作师傅等。这些艺人每个人都至少会演奏两种以上的乐器。他们看到我携带的琵琶,十分陌生而新奇地围着这件乐器,在每个人手中传递、观赏,不停地低声交流。
语言不通,就用琴声交流吧。我抱起了自己的琵琶刚弹奏了几个音,艺人们大概听出了熟悉的音调,立刻兴奋起来。我演奏的乐曲正是为维吾尔族音乐人所熟知的曲目《艾介姆》。该曲目原是一首著名的弹布尔独奏曲,根据乌兹别克民歌改编。同一首乐曲经过多位演奏家们演奏通常会形成不同的风格版本,笔者演奏的《艾介姆》是根据努尔买买提·吐尔逊②的演奏版本进行记谱、改编和移植的。使用琵琶演奏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作品,难度在于对大量微分音、波音和逆波音技巧的把握。笔者尽力在保留了该曲原有的风格和韵味的同时,运用了滑音、顿音、润音等琵琶演奏的特殊技法,模仿弹布尔的独特表现力,以尽可能将作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体现出来。
在我独奏过程中,一位老艺人情不自禁拿起了都塔尔进行合奏。虽然是第一次合作,前面几个音试着加入进来还有些许“生硬”之感,但随后就配合非常默契了。全曲完整演奏一遍大约需要9分钟左右,在这短暂的数分钟里,大家或是安静聆听,或是拿起手机录像,又或是低声交流,不时爆发掌声和欢呼。一曲终了,艺人们沉浸在乐曲中意犹未尽。“你演奏得太好了,他们说没想到琵琶还能弹维吾尔族传统乐曲!”古再丽努尔兴奋地告诉我。
“我们来演奏一首”,也许受我的琴声感染,古再丽努尔的表哥与身旁的老艺人低声交流一会,每个人开始调动琴弦进行合奏前的校音。几分钟后,演奏萨塔尔的艺人坐直了身体,将琴箱竖置于左腿上,如一位将军,目视前方,坚定而又自信地拉响了手中的琴弦,随即吼出了一句低沉、苍凉的唱词,独特的琴声与歌声让人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一幅苍茫无际的大漠戈壁画面。经古再丽努尔的解说,得知这首曲目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十一首《木夏唯热克》。萨塔尔老艺人喉咙里迸出的歌声,琴弦中奏出的旋律,像是冲破云层、身披霞光的呐喊,更如酣畅的宣泄。当歌声和琴声融为一体,激昂的旋律似千军万马,冲击着我所有的感官。
老艺人深情的弹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艺人们休息了片刻,喀什民歌《胡嘛里克》便奏响了,帅气的“小撇胡”边唱边奏,弹布尔的领奏成为主调,随后加入了三把都塔尔、一把艾捷克、一把萨塔尔的合奏。音乐的感染力带动我也加入了他们的演奏。此刻,音乐成为两个民族乐手之间共同的语言,跨越了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奏响了每个人心中最和谐的旋律。
维吾尔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样的场合当然也少不了麦西来普。麦西来普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十分喜爱的群众性歌舞形式。“咚哒、咚哒……”,只见古再丽努尔的父亲起身手持达甫(手鼓)敲打着欢快的鼓点,一位头戴礼帽肤色黝黑的老艺人随着鼓点,双手向上,朝空中打了几个响指,迈着轻快又灵活的舞步跳了起来。紧接着,在场所有的观众,包括3、4岁的孩子们都加入到麦西来普的舞蹈中,强烈的氛围感染我也不得不应邀参与到这场“麦西来普”的舞会里。维吾尔族的麦西来普离不开木卡姆乐队的伴奏,艺人们起劲儿地弹奏着昂扬激烈的旋律,大家心应弦、手应鼓,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地舞动着。
一曲麦西来普《玫瑰花》结束了,所有的舞者气喘吁吁地坐回地毯上休息,艺人们放下乐器,欢笑交谈。虽然有点疲乏,但却意犹未尽。古再丽努尔的表哥跟我说:“他们还想听琵琶,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我非常愉快的答应了,随后依次演奏了汉族著名的琵琶传统武曲《十面埋伏》以及文曲代表作《春江花月夜》,还有新疆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这三首具有代表性的琵琶独奏曲,引来在场观众的连连称赞,纷纷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乐曲《艾介姆》在那晚的“斗琴”中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乐曲,我以独奏、重奏、合奏的形式演奏了三遍,老艺人们如醉如痴,也被琵琶这一乐器的声响所震撼。每至演奏间隙,就会有民间艺人抱着琵琶研究一番,或是三两人相互讨论、或是自己尝试弹奏,大家似乎对琵琶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兴趣。对于深居南疆的这些民间艺人来说,他们是第一次接触琵琶这件乐器,在他们手里试着演奏的时候,琵琶的传统风格似乎被脱胎换骨,我们俗称的“皮牙子(洋葱)味”“羊膻味”经维吾尔族老艺人的演奏充分体现了出来。同样的乐器,经不同民族的人演奏所体现出来的效果竟如此的不同,或许这就是他们血液里渗透着的、与生俱来的特有的乐感,或许他们对琵琶这件本就经自西域的乐器并未感到陌生。
此时已是凌晨,安静祥和的村庄里渐渐只剩下玉素甫家的小院依然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不时打破夜的寂静。古再丽努尔母亲给每个人端上了热腾腾的曲曲(馄饨)。连续6个小时的“斗琴”活动结束了。
三、不同历史文化弦音的碰撞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构想的不断推进,丝绸之路所呈现的音乐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音乐学和音乐演奏领域的关注,这种跨越族群的文化生态研究逐渐成为业界研究的新热点。而在对丝路音乐文化的研究中,仅仅针对于石窟壁画或是出土文物等静态主体的研究是不够的,理论研究还须实践的支撑。此次民间状态的“斗琴”活动,通过动态的音乐交流,更生动、直观地呈现了丝绸之路不同历史、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抱弹类弦鸣乐器的迥异形态——乐器的背后往往印证了一个民族或区域的人文环境、生活方式、审美习惯等一系列人文生态特征。
各民族乐器的形制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音乐审美。笔者通过此次“斗琴”活动,发现若从乐器形制来观察,“斗琴”呈现的几样乐器存在着某些共性——大致都有琉特类乐器的外形特征:半梨形音箱,琴颈狭长且有音品,颈部顶端有琴轴,琴箱底端有覆手,按音区域与共鸣琴箱面板平行的一类乐器。琵琶作为曲项则不同于弹布尔和都塔尔等直项乐器,琴颈较为短阔,琴颈部位由六柱组成了相把位的低音区。琵琶与热瓦普均属于有琴头(乐器构造名称)乐器,而弹布尔、都塔尔、萨塔尔则没有琴头。琵琶的琴头呈“如意”形,而如意是我国多民族传统的吉祥物,“如意头”则体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审美观念。热瓦普的琴头大都向后弯曲,琴头造型近似于唐代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现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维吾尔族乐器最具特色的标志,要属乐器上具有民族特色图案的镶嵌。“斗琴”活动中一位制作维吾尔族乐器的师傅吐逊·那买提说:“制作一把乐器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光乐器上镶嵌工艺就得占据大部分的制作时间。”据这位老师傅介绍,萨塔尔、弹布尔、都塔尔等乐器的装饰,大部分材料都是就地取材,采用牛角或牛骨等材料用来逐一镶嵌琴身,制作工程比较复杂,大都采用传统手工的镶嵌方式。
在新疆传统民间弦鸣乐器的形制特点之中,共鸣弦的现象是构成乐器发出特殊音响效果的主要原因,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的音乐魅力。所谓“共鸣弦”,顾名思义是指能够产生共鸣效果的琴弦。经笔者了解,维吾尔族弦鸣乐器普遍存在共鸣弦特征,例如萨塔尔、艾捷克、热瓦普、弹布尔。在这些共鸣类弦鸣乐器中最具代表的当属弓弦乐器萨塔尔,萨塔尔张有十三根琴弦,一弦为主奏弦c音或d音,其余十二根均为共鸣弦,音高因演奏者和演奏曲目而异。演奏时,主奏琴弦承担着旋律音的拉奏,其余共鸣弦起着共振鸣响的作用,因共振而产生了多重发音织体。在听觉效果上,共鸣弦的使用相较单弦拉奏乐器的音色更为饱满,极大丰富了音乐的感染力,凸显乐器本身浓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色彩。
弹布尔定弦中存在着同音共鸣弦的定弦方式,即一弦、二弦为C音(同音),三弦为G音,四弦、五弦为D音(同音),其中二弦、五弦分别作为一弦、四弦的共鸣琴弦。经笔者弹奏,发现双弦同音奏出的旋律相较单弦发音更增强了旋律音的音量和音响的延续性,使旋律音更富立体、饱满、连贯的音色。双弦同音共鸣这一特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弹布尔由于琴杆长、琴弦长而导致其音量较小、共振时间较短的缺陷。弹布尔的同音共鸣弦的装置是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乐器的重要标识,也成为了这件乐器在演奏时产生特殊音响效果的主要原因。外弦的双弦共振的装置,使得弹布尔的发音似乎有嘈杂、“不纯粹”的听觉感受,但是很容易使听者感受到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此引发笔者思考,旋律主音的双弦共振在琵琶这件乐器上是否也可以进行大胆的尝试呢?
在新疆众多热瓦普的分类中,以“斗琴”中笔者所见的也是普及率最高的喀什热瓦普为例。这类乐器无论是五弦或是七弦,除了外弦的主奏旋律用弦,其余的后四根或六根弦均为共鸣弦。其中,五弦喀什热瓦普定弦为c1、e、a、d、g,七弦热瓦普则为c1、#f、b、e、a、d、g或c1、b、e、E、a、d、g。喀什热瓦普与弹布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装有不同音高的共鸣弦,后者具有双弦同音共鸣现象。随着弦鸣类乐器的不断进化和发展,以及各民族演奏者们对音色审美的改变,这种双弦同音共鸣的现象的存在,在现代民族弦鸣类乐器中越来越少见了。
如果说共鸣弦是维吾尔族乐器具有特色的一个象征,那么在“斗琴”活动中民间艺人演奏时微分音的频繁使用则是维吾尔音乐中的重要标志,微分音也使维吾尔音乐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学者的研究曾经提到:“波斯—阿拉伯长颈琉特对古埃及琉特的延续,并不以乐器结构为主要特征,而是品位设置和对微分音的发现。”[5]维吾尔族音乐风格受外来文化影响,微分音被广泛应用在其民族音乐之中。微分音的使用体现了演奏者对音乐的审美需求,琵琶作品中也出现过微分音的使用,在记谱中,演奏者或作曲家通常在主音的斜上方用箭头来标注,箭头的上下方向指示微分音的升降,但大多数演奏者对微分音的演奏都缺少固定的音高位置概念,导致不易正确的奏出微分音。微分音的演奏主要通过左手按音在品位上的滑动结合右手发音来实现,左手手指的滑动是决定音高位置的关键。据笔者观察和模仿演奏后发现,品距的加宽使得音分的构成更加丰富,品的高度越低,左手在上下滑动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越小。因此,笔者认为微分音似乎在品距较宽的绕品长颈琉特类弦鸣乐器的演奏中相对容易体现。
应该说,笔者非常重视此次“斗琴”,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跨越族群和地域的音乐文化交流,作为一名当代中华传统音乐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我更有义务和使命将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前往参与活动之前,我对演奏的曲目、整体布局已做了一些思考,最终选择琵琶传统武曲《十面埋伏》和文曲《春江花月夜》、由新疆民歌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以及我个人根据弹布尔作品移植的《艾介姆》等四首曲目呈现给观众,在展示了传统音乐、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理念基础上,进一步试图探究未来丝绸之路中各民族弦鸣乐器发展空间和互通互鉴的可能性。在我弹奏的琵琶作品《十面埋伏》与《春江花月夜》中,通过大量的左手推、拉、吟、揉及右手扫、拂、轮、滚等技巧的运用,尽可能展现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味儿,彰显虚实相生、和谐、刚柔并济等中华传统美学内涵。观众们尤其是在场的维吾尔族朋友们聆听时专注的神情、激动的掌声,无论是面目表情或是肢体语言都传递着对这样一种音乐的无限感佩与赞赏。经私下交流得知,他们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琵琶音乐,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多元一体的魅力。
如果说舞台化、独奏性是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趋势或学院派追求的目标,那么对于这些民间艺人来说,他们的演奏更趋向一种自由、随意、即兴宣泄心灵的方式,多了份朴实无华,少了些许中规中矩的炫技。我们从小接受的乐器演奏训练模式,导致在表达音乐时习惯于单一按照谱面要求来表现音符或者作品,虽完成了“规范式”的演奏,似乎也少了些音乐本质上的随性与自然。或许如此,“斗琴”活动现场在与艺人们的合奏初始,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参与喀什民歌《胡嘛里克》合奏时“旋律合不上”“音符找不到”的状况让我甚为尴尬、无措。作为音乐演奏专业出身的我,习得了繁杂的演奏技巧和理论知识在这一时刻却派不上用场,面对其他演奏者怡然自得的表演和观众期盼的目光我却只能“干瞪眼儿”。后经思考,隐约察觉到这种“困惑”的出现显然跟技巧的掌握度或理论的储备量关系不大,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不够了解对方的音乐内涵,没有完全跳出“框架”来掌握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演奏规律。
正因为不了解、不熟悉,在接触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相斥现象。“斗琴”中初听民间艺人演奏,总感到音乐中频繁的游移音、微分音的使用给人一种音高不到位或是音律不准的感觉,但是听到后面觉得还蛮有味道,渐渐接受这种音乐表达方式,慢慢体会到了其中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国音乐多元化的呈现造就每个地区和族群在音乐上的审美习惯有所不同,对音准审美和判定标准会产生偏差也属必然现象。民间艺人的演奏虽显右手技法单一,但过多左手的“小动作”却使音乐增添了一些独特的韵味。从琵琶这件乐器的自身性能出发,它同弹布尔、都塔尔、热瓦普这些同源乐器一样,有着相同的律制应用,左手也可利用不同幅度的推、拉、滑、揉等技法来体现游离于标准律制之外的一种表现力,加之右手丰富的技法,是否能充分展现出更立体化、多元化的音响效果?
事实证明有“碰撞”才能擦出“灿烂的火花”,“斗琴”中琵琶演奏《艾介姆》的尝试,使得维吾尔族朋友们也格外喜欢。从民间乐师的反响来看,大家最为激动的情况大多出现在乐曲中频繁运用左手超过八度的大滑音时。在这些长颈琉特类乐器家族中,弹布尔、都塔尔、琵琶、萨塔尔都需坐姿演奏,热瓦普的演奏姿势可坐可站。随着顺应演奏者对演奏和发音的需求,各代演奏家对抱弹类乐器不断进行改造,琵琶的演奏姿势渐渐由“横抱”改为“竖抱”,而弹布尔、热瓦普、都塔尔大致保留着横向抱琴的传统演奏姿势(小部分弹布尔的演奏介于横竖抱姿之间)。越来越丰富的演奏技法,不得不使演奏者逐渐改变持琴姿势来使音乐表现力得到充分发挥。琵琶“竖抱”演奏,一定程度释放了左手,使左手手臂在演奏中跑动更加灵活,相对与民乐中的其他乐器来说更具有空间和优势,在演奏维吾尔族音乐作品时将技巧发挥得更加尽致。
“金属音”的特点也是维吾尔族器乐演奏的一个具有地域性的独有标志,在民间乐师弹布尔的演奏中,右手手腕需紧贴琴面板的边缘,形成支撑点将琴稳固以便于演奏。右手在靠近琴码的地方弹奏发音,音色较琵琶而言相对低沉、音质粗硬。如果说这是形成这种“金属”音色的基础条件,那么造就这种音色关键性的要素应是右手缠绕细钢丝触弦发音这一“钢丝碰钢丝”的发音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民族弹拨乐器演奏中极其罕见。当然,弹布尔的主奏弦为双弦共振的现象也是使其独特音色呈现的决定性因素。仔细聆听后发现,这些“金属音”中还掺杂着一些杂音,我们以往无论在教学或舞台上更趋于追求音的纯净或无杂音演奏,但是这种杂音的出现并未让人感觉不舒服,反而觉得这种伴有杂音的“金属”感就是维吾尔民间音乐的特色,有着较高的音乐辨识度。
从上述罗列的“斗琴”交流中的几种现象,可以总结出现代琵琶与新疆各少数民族弦鸣乐器在演奏技法、创作手法等方面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纵观琉特类弦鸣乐器东传的演变历史,这些具有同源关系的几样乐器已然暗示在未来发展道路上互融的空间和可行性。回顾中国音乐之发展历史,在大一统的汉唐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处于历史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段的音乐最显著的特点当属体现了文化交流的“融”与“容”,在保留了本土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兼容四域音乐,使其相互碰撞、交融,共放光芒。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无论在音乐表演或是创作领域,过于崇尚西洋的现象令人堪忧,现代作品中着重突出“炫技”而往往忽视作品的音乐性。在我们以往的“固化认知”里,认为“有品”乐器对于音腔的变化具有阻力,这次通过与新疆地方少数民族民间艺人的交流,渐渐改变了之前的一些成见。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大多数演奏者或是创作者对民间乐器性能、音乐韵味不够了解。这需要我们真正跳出自己固化的框架,从科学的角度悉心观察事物的本质。
结 语
中国疆域辽阔,各民族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多态的音乐文化,也是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摇篮。“斗琴”活动中,多种琉特类弦鸣乐器的呈现,更加印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包容性,进一步诠释了一体多元和多元一体的精神内涵。在现代国际化的音乐文化发展道路上,无论在音乐作品创作或是音乐表演领域,我们都需要借助自身优势,真正体现中国音乐的特色与内涵。通过这次交流,我理解的中国音乐的“味道”即是民间传统和民族特色。本次“斗琴”交流的动机和初心就是本着以尊重各民族文化、正确看待文化差异为前提,更深刻了解、认识新疆维吾尔族多种弦鸣类抱弹乐器,尝试使文化差异转化为文化互异共存,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探究我国各族音乐在未来发展空间及道路上的互融互鉴,吸取之精华来丰富和壮大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不拘于特定的音乐表达环境和形式,才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鲜活性和生命力,被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承。面对传承中华文化和实现自我文化身份认同这一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中国音乐传承者都有责任思考和为之努力前行的方向。
附言:本文在构思与撰写阶段承蒙中央音乐学院陈荃有教授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①有关这种认识的观点参见: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热瓦普》(一),《乐器研究》,2019年第2期;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及其传来乐器研究》,《音乐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日]林谦三著;钱稻孙译;曾维德,张思睿校注《东亚乐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日]岸边成雄著;王耀华,陈以章译《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
②努尔买买提·吐尔逊(1978-2013),著名的弹布尔演奏家,被誉为新疆的“弹布尔王”。他具有非凡而卓越的演奏技术,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