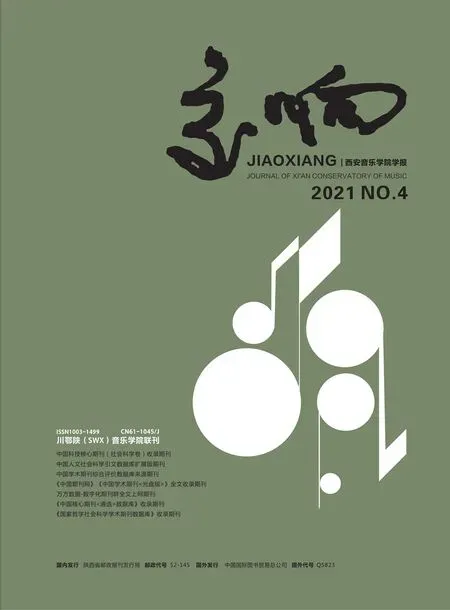先秦时期“音”“乐”对立及儒家音乐理论之肆应
●雷炳锋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99)
先秦时期,音乐领域呈现出既繁荣活跃又矛盾纷纭的发展态势,礼崩乐坏的背景下,雅乐衰微,“新声”蔚起,“郑卫之音”成为关注的焦点,又有“女乐”“新乐”“世俗之乐”绽放乐坛。儒家学者对此局面痛心疾首,斥之为“淫声”“奸声”“溺音”“邪音”“淫乐”,必欲除之而后快,以维护与恢复“正声”“古乐”“先王之乐”为代表的礼乐制度。但诸侯国君却普遍“好音”,喜好“郑卫之音”成为一时风尚。因而,“郑声”与“雅乐”、“音”与“乐”、“新乐”与“先王之乐”构成了一组组的矛盾。传统认为这些矛盾仅仅是“新乐”与“先王之乐”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其实,中国古代音乐学史中“声”“音”“乐”是一组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和术语,虽然所指可能相同,但在概念的使用时却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与意义指向。“郑声”与“雅乐”的矛盾强调的是“雅乐”内部的混乱情形,“音”与“乐”、“新乐”与“先王之乐”的矛盾强调的是地域文化、音乐对礼乐制度的冲击。那么,“音”“乐”之对立因何而起?“郑卫之音”的实质是什么?儒家在音乐理论方面有何肆应?诸多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国君“好音”与“音”“乐”之对立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君都“好音”,如卫灵公、晋平公、赵烈侯、魏文侯、赵惠文王、齐宣王等,此外,晋国的世卿中行文子(荀寅)、西戎的戎王等也都留下了“好音”的记载。《韩非子·十过》总结国君“十过”,其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并比较具体地记载了晋平公的“好音”作为例证,通过记载可知:1.晋平公所好之音又被称为“新声”,产生于濮水之上,来源于师延为商纣王所为之“靡靡之乐”,所以是“亡国之声”;2.“新声”最突出的特征是“悲”,从“清商”到“清徵”“清角”,“悲”的程度递增;3.“新声”属“亡国之声”,能产生“国必削”的后果,国君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德行、一味沉溺其中则会妨碍治国,“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1](P66)卫灵公“闻鼓新声者而说之”、师涓“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旷演奏“清徵”“清角”,则表明“新声”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流传,因而能够为乐师所熟悉与演奏、为诸侯所喜爱。
《史记·赵世家》载“烈侯好音”,又曰“郑歌者枪、石二人”,司马贞《索隐》曰:“枪与石二人名”[2](P1797),可知赵烈侯的“好音”实际指的是“郑歌”。《礼记·乐记》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巳而自沈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孔颖达疏曰:“郑国之音,好滥淫志,卫国之乐,促速烦志,并是乱世之音也。”[3](P1528)可以说,“新声”“郑歌”“郑卫之音”所指皆同。
“音”作为一个音乐学概念起源甚早,据《吕氏春秋·音初》,“东音”始于夏后氏孔甲的“破斧之歌”,“南音”始于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西音”始于殷整甲,秦穆公又在“西音”的基础上“作为秦音”,“北音”则始于有娀氏之二佚女。“音”往往与方位、侯国、族群连用,表明“音”由个体情感的凝聚、积淀而蕴含着特定的方域音乐、文化、习俗、心理等意义,李方元即指出:“‘音’之重要性在于其地域意义,并内化为‘音’的最根本特性。”[4](P51)周初制礼作乐,以“六代乐舞”为核心,将乐舞广泛用于祭祀、燕飨、射礼等场合,形成了“周道四达,礼乐交通”的礼乐制度。“乐”成为标识周人历史统系、权力来源、等级区分、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因而在礼乐制度下,消解“音”的方域特色,把“音”纳入礼乐体系之内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吕氏春秋·音初》载,以“南音”为基础,“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5](P338)据《仪礼》,《周南》《召南》属“乡乐”,一般用于燕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之正歌的合乐环节。另,《周礼·春官·宗伯》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6](P801)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自有舞。夷乐,四夷之乐,亦皆有声歌及舞。”[6](P801)可见,将方域与四夷之音(“声歌”)改造成散乐,作为燕乐的乐舞用于祭祀、宾客等礼仪之中。此外,韎师掌教的东夷之舞(韎乐)、鞮鞻氏掌的四夷之乐与其声歌,也都用于祭祀、大飨。“音”成为了礼乐的组成部分。
以四方之音为内核的散乐、夷乐虽用于礼乐活动,但因其内蕴了方域文化与群体意识、习俗,且亦由“四方舞士”和“野人为乐之善者”演奏,如孔颖达疏曰:“野人能舞者,属旄人,选舞人当于中取之故也。”故而依然能够保持其自身的音乐特征,清李光地《古乐经传》云:“散乐,列国之乐也。夷乐,杂居中国夷狄之乐也。”[7](P32)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引郑锷曰:“作四夷之乐,当从其国不变其俗”[8](P664),又曰:“散乐,野人之乐,节奏疏散而非六代之舞;夷乐,四夷之乐而非中国之法舞。”[8](P665)清方苞曰:“散乐,方隅土风所成之乐,王朝亦备之,以知民风也。四方以舞仕,即能舞是乐者以属旄人,选舞人或于中取之。”[9](P192)散乐与夷乐性质相似、施用场合相同,在乐事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一是因为舞者乃“野人为乐之善者”“不在官之员内”,二是因为“凡舞夷乐,皆门外为之”,可见散乐、夷乐并非施于礼乐的正歌环节。所以,散乐、夷乐在本质上并没有被周人礼乐所同化,而依然保持与礼乐异质的自身音乐、文化方面的特性,不过因为其在整个乐事活动中被边缘化的地位,在礼乐制度下并没有出现“音”与“乐”的矛盾与对立现象。换言之,在礼乐制度下,周王朝以其绝对威权能够对各诸侯国形成有效控制与羁縻,象征王朝威权的礼乐也能够对方域之音进行极力压制,进而使“音”完全从属于“乐”。
春秋以降,由于礼乐废坏、新声兴起以及“郑卫之音”风靡等原因,“新乐”也随之产生并流行,“新乐”又称“今乐”“世俗之乐”,与“古乐”“先王之乐”相对。其实,所谓“新乐”,其本质则是“郑声”“郑卫之音”,如赵岐注齐宣王所好的“世俗之乐”曰“谓郑声也”[10](P2673),魏文侯称“郑卫之音”为“新乐”。“郑卫之音”衍为“新乐”,对“古乐”产生强烈冲击,体现出了“音”“乐”之对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郑卫之音”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迎合了人们的音乐审美趣味,所以很快风靡开来,得到了上至诸侯国君、下到世俗之人的普遍喜爱。《盐铁论》载大夫曰:“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11](P254),因此,先秦诸侯“好音”成为风尚,齐宣王“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10](P2673),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12](P1583),这表明“郑卫之音”的风行进一步促成了“古乐”的衰微。其次,在礼乐制度崩溃的背景下,未能进入仪式正歌的散乐也在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演化为“新乐”。《乐府诗集》卷五十六释“散乐”曰:“《周礼》曰:‘旄人教舞散乐。’郑康成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即《汉书》所谓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是也。汉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群臣。然则雅乐之外,又有宴私之乐焉。《唐书·乐志》曰:‘散乐者,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13](P819)一般将郑玄“若今黄门倡”之语理解为“不在官之员内”,如孔颖达疏曰:“云‘若今黄门倡矣’者,汉倡优之人,亦非官乐之内,故举以为说也。”[6](P801)郭茂倩则指出散乐的演奏者野人从身份上来说,与汉代的名倡丙强、景武一样同属于倡优,认同《旧唐书·乐志》关于散乐是指由倡优演奏的歌舞杂奏的说法。郭茂倩的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野人兼俱倡优与“不在官之员内”的双重特征,《乐府诗集》卷五十六“俳歌辞”解题云:
一曰《侏儒导》,自古有之,盖倡优戏也。《说文》曰:“俳,戏也。”《谷梁》曰:“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范宁云:“优,俳。施,其名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问曰:‘新乐进俯退俯,俳优侏儒獶杂子女’。”王肃云:“俳优,短人也。”则其所从来亦远矣。[13](P819)
由此可见,魏文侯所好的“新乐”即“倡优戏”,是由散乐演化而来的。
第三,礼崩乐坏也导致了礼乐的制作权发生转移,《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朱熹注:“先王之制,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伐。”[14](P171)何宴注:“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於隐公。”邢昺疏:“王者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立司马之官,掌九伐之法,诸侯不得制作礼乐,赐弓矢然后专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者,谓天子微弱,诸侯上僭,自作礼乐,专行征伐也。”[15](P2521)于是诸侯根据自身喜好,以“好音”为契机,推动“郑卫之音”成为“新乐”。《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梁丘据扃入歌人虞,变齐音”,被晏子斥为“以新乐淫君”,而齐桓公却坚称“夫乐何必故哉?”[16](P23-24)《列女传》曰:“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17](P676),《论衡》曰:“秦缪公好淫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18](P639),“淫乐”可以视为“郑卫之音”的代名词,是诸侯自制之乐。从这个角度说,“音”“乐”之矛盾其实也是音乐制作权的矛盾。
二、从“郑声”到“郑卫之音”
先秦时期,“乐”“音”“声”三分,构成一组内涵不同的音乐学术语。但在先秦典籍中,涉及使用“郑声”“郑卫之音”“新乐”等名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呈现出三者既含杂不清,又各有侧重的复杂情形。“郑声”与“郑卫之音”是中国古代音乐批评领域内的两个重要概念,二者在所指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可以用来指称产生于郑、卫一带最终风靡于世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当时又被称为“新声”“溺音”“邪音”“新乐”“淫乐”“今乐”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似乎表明先秦时期“声”“音”“乐”三个概念在使用的时候是随意的、混乱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先秦时期,乐是合诗、乐、舞一体的综合形态,《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9](P131)既有八音乐器之音,也有人声的歌唱,用律吕来调和声音,用乐舞来加以展现,“声”与“音”是构成“乐”的两个要素。从相区分的角度来说,“声”强调的是音乐的节奏、声调的调配等音乐层面的特征,而“音”则强调内蕴的文化习俗、族群心理等社会层面的特征。
中国古代音乐学史上,首先出现的一对矛盾是“郑声”与“雅乐”的矛盾,孔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又曰“放郑声”“郑声淫”(《论语·卫灵公》),孔子将“郑声”与“雅乐”对举,指出“郑声”“淫”的特征,主张因“乱雅乐”而“放郑声”,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郑声”渗入“雅乐”而致使“雅乐”产生了混乱,“雅郑”的矛盾更多是“雅乐”内部不同音乐特征的冲突。雅乐崇尚喜乐,即“乐者,乐也”,“郑声”则以“悲”为美;雅乐中正和平,为“中声之所止”,“郑声”则“烦手淫声”,“无中正和平之致”;雅乐“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3](P1528),乐音清、淡、无味,“郑声”则音调婉凄,能惑溺人心。总之,“中正则雅,多哇则郑”[20](P53),“郑声”作为新声以其悦耳、曼妙、艳丽迅速风靡于世。
“郑声之乱雅乐”首先体现为“郑声”的某些音乐特征开始向“雅乐”渗透,《礼记·乐记》载孔子与宾牟贾谈论《武》乐,孔子问“声淫及商何也?”宾牟贾对曰:“非《武》音也”,“商”即商音、商调,来源于商纣王的“靡靡之乐”,师涓所奏“桑间、濮上之音”即谓“清商”,也就是“郑声”,这表明了因“有司失其传”致使“郑声”向雅乐渗透的具体情形。其次,“郑声”开始进入“雅乐”序列,孙奭《孟子注疏》曰:“《论语》云‘郑声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传》云:‘郑声惑人心,其与雅乐同也。’”[10](P2674)所谓“与雅乐同”指“郑声”与“雅乐”混同,混用于同样的场合。针对“郑声”泛滥的局面,为了解决“雅郑”对立、冲突的矛盾,孔子提出“放郑声”,一方面强调与重申雅乐与“郑声”不同的使用场合,将“郑声”从正乐环节排除出去,使得“雅颂各得其所”。同时排除雅乐中的“郑声”成分,对雅乐进行净化、提纯等工作。《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21](P1936),这段记载既表明对“三百五篇”中的雅颂之乐作了修订,也说明孔子对“三百五篇”中的“郑声”进行了改造。孔子改造“郑声”的方式是通过“弦歌”将“郑声”雅化,使“郑声”成为合于“合《韶》《武》《雅》《颂》之音”的雅乐,从而进入礼乐的体系之内。至此,“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得以最终解决,其结果是《诗经》文本正式集结,“雅乐”得以恢复,“郑声”在转化为“雅乐”的同时也随着“雅乐”以及礼乐制度一起走向衰微。
“郑卫之音”的强势兴起与诸侯国君的“好音”,体现的是“乐”与“音”的冲突,是“音”对礼乐制度以及“新乐”对“先王之乐”的最后一击,其本质则在于周天子式微、诸侯强大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乐”“音”冲突的过程中,“音”的方域、群体特征愈发凸显。“郑卫之音”这一术语就凸显了积淀于其中的郑、卫诸国的民风习俗,《礼记·乐记》载子夏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22]认为四者都是“淫於色而害於德”的“溺音”,此处的“淫”显然指的男女淫乱,孔颖达疏则指出“淫佚”是郑音、宋音、卫音、齐音共有的总体特征,但郑音的“非已俦匹,别相淫窃”与宋音的“己之妻妾燕安”又有所不同,而卫音与齐音除“淫佚”之外还分别有“促速”与“敖辟”之特征。这些特征是由各国的民俗所决定的,《汉书·地理志》曰:“(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23](P1652),又曰“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23](P1665)《白虎通·礼乐》:“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24](P97)《乐记》疏引许慎《五经异义》云:“《今论语》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3](P1528)这几条材料虽试图论证“郑声”或“郑诗”之“淫”,但也表明从风俗的角度考察、阐释各国乐音的做法已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
“郑卫之音”的风行还凸显了郑国等地方音乐的艺术特色。春秋诸国中郑国的音乐最为发达,其显著特色是女乐,据《左传》,郑国于襄公十一年以女乐赂晋,襄公十五年又以女乐赂宋,“郑音”与女乐结合起来更显淫辟,方苞《礼记析疑》曰:“自周以前,虽桀纣之乱,未闻有女乐。以昭徳象功,无缘使女妇参其间也。自郑卫之风作,则所歌者本男女淫辟之事,此女乐所由兴也。自是见于经传者:齐人归女乐,郑赂晋以女乐二八,屈原九歌‘姱女娼兮容与’,娼女獶杂则必有父子聚麀而不自知者矣。”[25](P167)吕祖谦《左氏传说》云:“郑音首坏先王之乐,其奸声尤甚,……郑所有之乐皆非先王所有之乐”[26](P61)。女乐在郑国、宋国、晋国、齐国、鲁国、楚国、秦国乃至西戎广泛流行,对“先王之乐”造成了严重破坏。
三、儒家音乐理论之肆应
先秦时期,诸侯国君“好音”与“音”“乐”对立的现象,体现出的本质问题有两点:诸侯基于“好音”而自制新乐,使礼乐制度与“先王之乐”濒于崩溃;“音”从乐、舞中分离出来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使儒家诗、乐、舞一体的音乐体系与音乐理论趋于解体。为了维护礼乐制度,解决“音”“乐”之间的矛盾,儒家也在音乐理论方面作了回应与重构。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乐”,把“音”纳入“乐”的体系之内。《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3](P1527)心-声-音-乐的音乐生成序列,是儒家关于音乐本质的理论创新,其意义在于承认音乐是自下而上渐次生成的,承认构成乐的声、音属于人声,是人的歌唱。传统的儒家音乐理论认为,乐的制作权专属于先王,是先王功成治定的体现,先王制定礼乐颁行天下,体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乐的生成序列。又认为乐是对天地自然的效法,《礼记·乐记》云: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3](P1531)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12](P1536)
无论是模仿天地自然之音,还是遵循天地自然之道,都与人声无涉。可见,在新的乐本理论之下,承载个体情感、体现地域特质的“音”是由“声”到“乐”的关键环节,因而先从“音”说起,强调了“音”的地位与重要性。
其次,结合人心、人性来论述音乐,批判“郑卫之音”,维护先王之乐。在心-声-音-乐的序列中,从心感外物而形于声到声变为音可视为一个较为独立的阶段,因为“音”是人声的最终形态,其后方为乐器对“音”的摹写以及配合乐舞而形成“乐”的阶段。而“音”与何种乐舞结合则并非必然,如前所述,由于“音”的地域特性,“音”与方域之舞有着更为紧密的天然联系,“郑卫之音”多配以女乐即是明显的例证。所以,按照心-声-音-乐这一生成序列,最终生成的是女乐而非“先王之乐”,这是“音”与“乐”相冲突的深层原因。如此一来,心-声-音-乐的自下而上的音乐生成的乐本理论与儒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音乐生成理论自相矛盾,乐本论从一开始就带有内在的理论缺陷。
为了弥补这种理论缺陷,儒家将心性论引入乐论,对“音”进行伦理分级,强调只有“德音”方能入乐,“郑卫之音”等“德音”之外的“音”则在批判、排斥之列。由于“音”生于心感外物,而人心充满了喜怒哀乐等情感,在外物的诱惑之下容易产生各种欲望,进而形于各种“不为道”的“声”与“音”,《荀子·乐论》曰:“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27](P379)《礼记·乐记》则详细列举了“噍以杀”“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等“声”,以及“志微噍杀之音”“繁文简节之音”“奋末广贲之音”“廉直劲正庄诚之音”“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等“音”。儒家又强调这些“声”与“音”并不是人的本性,而只是惑于外物所激发出的各种欲望的显现,因而可以从源头处进行截断,方法是用先王的礼乐政刑制度与先王之乐来合同人心,《礼记·乐记》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12](P1535),“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3](P1527)为了突出“正声”的感人效果,还作了一组对比:“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12](P1536)“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無《韶》歌《武》,使人之心庄。”[27](P381)个中体现出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肯定“正声”“和乐”,反对“奸声”“淫乐”。概括来说,儒家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将人心所感的外物替换成了“正声”与“奸声”(“先王之乐”与“郑卫之音”),实质上所持的是先王之乐-心-声-音-乐的音乐生成理论,依然强调自上而下的教化功能,这相当于否了外物-心-声-音-乐的乐本理论。
所以,儒家对“奸声”“郑卫之音”极力批判,如“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郑卫之曲动而心淫”,把郑音、宋音、卫音、齐音等统称为“溺音”,强调只有“德音之谓乐”。所谓“德音”,即“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从子夏所引《大雅·皇矣》之“莫其德音”等句来看,“德音”乃指帝王之功业与德行①。“德音之谓乐”的理论实质,依然是王者功成治定之后制定礼乐以教化天下,这在理论上不仅把“音”排除于“乐”之外,还把心-声-音-乐的乐本论彻底推翻。
第三,立足于国君“好音”与“音”地域特征,将音乐批评转换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把“音”与诸国政治状况联系在一起,“音”的形态成为考察治乱兴衰的表征。《礼记·乐记》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3](P1527-1528)现实政治既呈现于“音”中,“音”的宫、商、角、徵、羽分别象征君、臣、民、事、物,如果“五者皆乱,迭相陵”,则“亡国无日矣”,把作为源于已亡之国的“郑卫之音”重新阐释为能使人亡国之“音”。治乱兴衰有赖于国君的德行,所以音乐批评又可用于道德批评,如认为国君痴迷“溺音”就会“淫於色而害於德”,“好音”与国君的纵欲、荒淫、奢靡、违礼等种种败德行为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此外,能否由“知音”而达于“知乐”成为君子与众庶的分野,《礼记·乐记》云:“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3](P1528)君子应该“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自觉地以先王之乐自我约束,“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以道制欲”从而提升道德修养。
四、余论
先秦时期,诸侯国君“好音”的风尚,助长了“郑卫之音”的风靡,进一步凸显了“音”与“乐”、“新乐”与“先王之乐”的矛盾与冲突。为了维护礼乐制度,儒家通过重构音乐理论的方式作为对这种局面积极肆应。
儒家学者构建了外物-人心-声-音-乐的自下而上的音乐生成的乐本论,把“音”作为“乐”的一个重要环节纳入“乐”的序列之中,肯定了人心、人声、人歌(音)是“乐”的基础,强调了“音”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儒家又不自觉地偷换了概念,以“先王之乐”(“正声”)代替人心所感的外物,使乐本论又回复到先王之乐-人心-正声-德音-正乐的自上而下的音乐生成理论。同时,基于人心、人性来论述声、音、乐,一再强调“德音之谓乐”,批判与排斥“音”(“郑卫之音”),而所谓“德音”依然只是先王德行、功德的代名词。儒家又分别以冲突的双方“音”与“乐”为基础,通过对比的方式,肯定“乐”而否定“音”,将音乐批评转化为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乐本论。这既表明儒家音乐理论存在致命缺陷,也体现了“音”“乐”之矛盾在当时是无法调和的。
另一方面,儒家乐论也某种程度地受到了“音”的影响,首先,基于“音”的个体情感特征,肯定“乐”亦是先王情感的承载,“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斧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齐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乱畏之。”[27](P380)其次,儒家否定“郑卫之音”-“新乐”体系,如子夏关于“新乐之发”的描述,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言论,荀子关于“乐中平”“乐肃庄”“乐姚冶以险”的分类,但批判、排斥其实也是不自觉、有限度地承认了“新乐”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形。第三,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承认“音”的独立性,认为“音”可离开“乐”而发挥作用。《礼记·乐记》载子夏对魏文侯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22](P1540)师乙告子贡曰:“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22](P1545)所“歌”者即为“音”,“音”能与人的气质性格互相涵养、相得益彰,如郑玄所言:“声歌各有宜,气顺性也”。
注释:
①《大雅·皇矣》毛传:“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郑玄笺曰:“德正应和曰貊,照临四方曰明。类,善也。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王季之德,比于文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圣人为匹。”详参[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519-5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