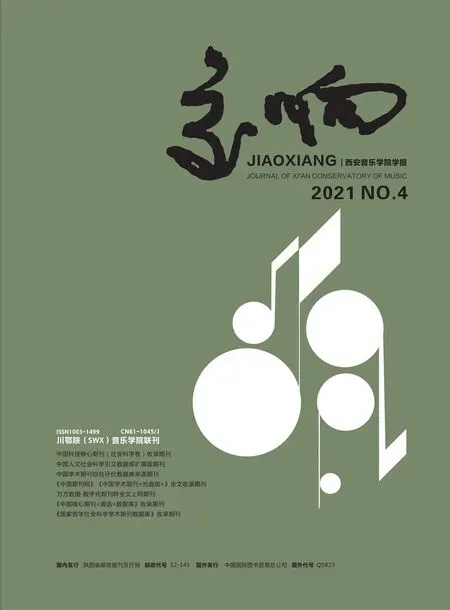许如辉流行歌曲研究
●王露晗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200031)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上海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中心。如泉水般涌进的西方元素与中华固有文化,在不断地碰撞中擦出了新的火花。音乐领域里,流行歌曲的出现,就像是时代历程里的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在诸如通俗歌曲、爵士乐等各种外来音乐的启发下,为了满足普通市民对音乐大众化的需求,一批音乐家开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黎锦晖首当其冲,于1926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①。黎锦光、陈歌辛等音乐家紧随其后,将西方的爵士节奏与中国的传统风格结合,创作的流行歌曲以亲民的歌词及易于上口的旋律在普通群众之间广为流传。这其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音乐家,写作了大量流行歌曲作品,却逐渐被历史所淡忘。本文所要论述的许如辉便是其中之一。②
一、许如辉生平事略
1910年,许如辉出生于浙江嵊县,乳名常喜,自小在外打工,13岁随舅父来到上海,改名许如辉。15岁时,偶遇大同乐会,为琴瑟之声所吸引,遂跟随郑觐文学习民族乐器,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在此期间,他学习了古筝、古琴、琵琶、箫等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还参与了《月儿高》《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等古谱的整理工作。大量的学习与实践,培养出了其较高的音乐素养,也为今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歌舞厅、唱片业的迅速崛起,流行歌曲很快便传遍了上海各个角落。新兴而起的音乐文化激发了许如辉强烈的创作欲望,《四时吟》便是许如辉创作的第一首流行歌曲。[1](P1)
1929年,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得到有效地推广,许如辉创办了子夜乐会。其下包含子夜社、子夜歌会、子夜乐团等分支,全方面地为流行歌曲的宣传而服务。《搁楼上的小姐》作为他自费印成的第一本歌集,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30年,在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音部主任任光的支持下,大量流行歌曲被陆续灌成唱片发行。同时,随着电台广播的不断发展,“子夜社”陆续邀请到了当时著名的歌星为许如辉所创作的歌曲进行录制、广播(记录中有江曼莉、包庸珍、余静、夏佩珍等)[2](P68)。自此,许如辉的流行歌曲开始全面地在上海流行起来。
20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快速发展为不少流行歌曲作曲家提供了新的创作平台。1931年,许如辉被明星影片公司正式聘为音乐专家(翌年转为“基本作曲”即固定作曲家)为电影创作主题曲及配乐作品。受益于子夜乐团曾为默片进行配乐的经历,许如辉很快便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之后的7年里,许如辉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上,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流行歌曲作品,诸如《月夜小曲》、《村姑乐》(电影《生龙活虎》插曲)、《打碎玉栏杆》(电影《桃李争艳》片名曲)、《女权》(电影《女权》主题歌)、《兄弟行》(电影《兄弟行》主题歌)等。
抗战爆发后,许如辉随舅父钱智修撤至大后方重庆,暂时放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在这期间,他再次遇到了曾经的好友——上海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之子郑玉荪,二人经过详谈,决定重振大同乐会(自郑觐文去世之后,大同乐会便失去了核心凝聚力,又“恐被敌伪利用”,无奈之下,郑玉荪摘下了大同乐会在上海的牌匾,赶往重庆。③)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王晓籁等理事的支持下,重庆大同乐会最终建立成为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乐器制造、集体演出为一体的音乐社团组织,其下难童国乐教养院、乐器工厂、中国国乐团等组织参与了大量社会音乐活动,由许如辉创作的诸如乐剧《木兰从军》、话剧《董小宛》插曲等作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重庆大同乐会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绚丽的色彩,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许如辉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抗战胜利后,成员各奔东西,社团也失去了主要的资金赞助。人员溃散下,支撑了6年的重庆大同乐会最终宣告落幕。
回到上海的许如辉,最初还是回到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之中,先后完成了电影《吕四娘》《凤头钗》等音乐作曲的工作。1951年,随着政务部提出戏曲改革,其音乐创作正式走向了戏曲音乐领域,并先后任职于上海沪剧团与勤艺沪剧团。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戏曲音乐作品,代表作沪剧《白毛女》的音乐部分获得了1952年10月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戏曲“红花奖”[3](P44)。经典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母女泪》《陈化成》《黄河颂》等更是深受民众的喜爱。曾经丰富的活动经验与深厚的知识积累,让许如辉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的创作,也包括了基础理论和演奏技巧的传授。同时,于戏曲音乐领域里日积月累的学习,也让他在参与作品的排演与演员的定腔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最终,其接连不断、广受好评的戏曲音乐作品确立了勤艺沪剧团经典的音乐风格,成就了被誉为“江南四大悲旦”之一的杨飞飞,这也奠定了许如辉在上海沪剧界的牢固地位。
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许如辉在重庆时期与国民党的密切接触,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的特殊身份,使得其不得不停下所有的创作,接受调查。他创作的许多戏曲作品,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撤销署名。临近权杖之年的许如辉在长时间的审问下郁结成疾,于1987年在上海逝世,享年78岁。④
回顾其一生,许如辉无疑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作品遍及流行歌曲、民族器乐曲、话剧插曲、电影配乐、戏曲等各种体裁,本人更是善于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他对音乐事业的付出与贡献,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一隅,具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二、许如辉前期流行歌曲创作
依据作曲家创作流行歌曲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传播方式,笔者认为,可以将许如辉的流行歌曲创作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音乐作品主要集中于20年代至30年代初,这些作品除了电台广播与唱片的传播外,主要依附于歌集的形式进行宣传。《搁楼上的小姐》、《子夜周歌》以及诸如《电影新歌曲》这样的歌本、杂志记录下了许如辉在离开上海之前创作的流行歌曲,也是许如辉在这一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作品。
(一)《搁楼上的小姐》
这本歌集由许如辉自费出版,既是其出版的第一本歌集,也是唯一一本。曲集以《搁楼上的小姐》为封面。全集共12首歌曲,分别是《月夜之歌》《永远亲爱》《摩登女郎》《村姑姑》《这回事情太稀奇》《田家乐》《永别了我的弟弟》《卖笑者》《放在心上》《月下女郎》《搁楼上的小姐》《重返故乡》。其中,《永别了我的弟弟》和《搁楼上的小姐》是传唱度最高的作品。
《永别了我的弟弟》创作于1929年,取材于现实生活,表达了许如辉对其弟弟常林的缅怀与思念之情。该曲在当时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已发掘的歌手名册中,有260余位歌手唱过《永别了我的弟弟》,包括周璇、姚莉、汪淡淡、余静等。[5]笔者有幸听到的是由江曼丽演唱,任光担任钢琴伴奏的版本,曲调婉转动人、绵延细腻,[6]除钢琴外还可以听到始终伴随歌唱的弦乐以及灵动的打击乐器之声。作曲家采用了五声调式进行写作,旋律贴合歌词声调,起伏自然,乐句间几次跳进将情绪逐步推进直至曲末达到高潮,以三次不同的曲调,重复演唱“永别了,我的弟弟”,表达出内心的不舍与思念。
谱例1:《永别了我的弟弟》选段⑤

《搁楼上的小姐》曾被批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但其实,这是一首警喻之作。据许文霞介绍:《搁楼上的小姐》其实是描绘了上海一些社会底层青年,住在阁楼上,虚度青春年华、不求奋发上进的生活习俗。[2](P67)题中使用动词“搁”而不是名词“阁”也是有原因的,许文霞解释,此处应将其理解为把她搁在楼上。由此我们推断,“搁楼上的小姐”其实具有暗讽之意:楼上的青年迫于现实,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日日虚度光阴。以此为视角表达了当时生活在底层百姓生活的无奈与不易。这首歌曲一经传播,很快在百姓间流传开来,由此可见,其现实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轻快流畅的旋律奠定了此曲易于传唱的基调;乐句中部分一字一音的演唱体现了传统说唱音乐的特点;充满爵士风格的附点节奏赋予了作品愉悦动人的情绪特征。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使得作品听起来韵味十足、精致巧妙。
(二)《子夜周歌》
《子夜周歌》是以子夜社为名义而创办的刊物,一周一歌。“文革”时,许如辉的许多资料尽数烧毁,目前已不能找到完整的《子夜周歌》。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的是目前幸存的三期,分别是:第三期《路柳墙花》、第四期《四时吟》和第五期《我当初认识你》。这些谱例都使用了五线谱、简谱、工尺谱三种记谱方式同时记录,这不仅体现了作曲家优良的中西音乐素养,也有利地促进了作品的广泛传播。整体来看,这三首小曲都是抒情之作,表现了对四季景致的热爱以及少年情窦初开的懵懂之情。旋律起伏平稳,具有较好的歌唱性,但部分乐句过于追求词曲的结合而忽略了音乐的断句,稍显冗长。由于这三首作品都创作于许如辉少年之时,为创作初期,难免生涩,出现些许不足之处也可以理解。
其中《四时吟》是许如辉创作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创作于约1926年,[1](P1)在《子夜周歌》出版,1934年被灌成唱片发行。这首歌描写了四季迷人的景象:
春季里春花香,红桃艳李柳叶长,佳景宜人多欢畅,蝴蝶儿双双飞舞在粉墙,山青天秀美尽天壤,及时行乐快把春来赏……[6]
言辞中充满了少年之朝气。作品采用民族调式创作,旋律柔美间不失民间小调的性格特征。对于初出茅庐的许如辉来说,这首作品展现出了其深厚的传统音乐功底与过人的音乐创作天赋。
(三)其他刊物与杂志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许如辉创作了大量的流行歌曲,除了通过上述《搁楼上的小姐》《子夜周歌》这些其自身出版的歌本传播以外,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录于诸如《电影新歌集》[7]、《电影新歌曲》[8]、《歌星画报》[9]等杂志刊物之中。这些作品选材于生活,展现出了自然动人的日常视角,唱起来亲切倍增,因而深得百姓喜爱,比如《卖油条》《缝穷婆》《回忆慈母曲》等。其中,《卖油条》与上文所述的《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是许如辉所有作品中被电台听众点播最多的3首作品。与前文所述抒情性风格不同,《卖油条》以活泼欢快的曲风,表现了独特的音乐张力,用幽默诙谐的方式,道出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表达了乐观向上的生活观念。曲中多次重复“卖油条”,并在曲尾通过模拟上海方言的语气来表现叫卖的场景,借鉴了民歌中叫卖调的元素,也使得音乐充满了强大的亲和力。
三、许如辉后期流行歌曲创作
从1931年开始,随着有声电影的发展,流行歌曲开始作为主题歌或插曲,依靠电影的形式进行传播,打破了原本仅依靠舞厅和电台传播流行歌曲的局面。同时,一些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开始招聘作曲家,这极大地拓展了流行歌曲作曲家的创作空间。许如辉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创作了大量的电影主题曲与插曲作品。有赖于影视作品的加持,这些流行歌曲有了更加广阔的传播途径。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许如辉共参与了约15部电影作品的音乐创作。如今可查音频与谱例资料涉及其中10部,共计13首流行歌曲(见表格)。

电影名称(上映时间) 作品名称《香草美人》(1933) 《香草美人》[10](P32)《费翠马》(1935) 《下琼楼》[11](P32)《劫后桃花》(1935) 《劫后桃花》《生龙活虎》(1936) 《月夜小曲》[7](P27)《村姑乐》[7](P27-28)《桃李争艳》(1936) 《打碎玉栏杆》[7](P46)《青春误》[7](P47-48)《金刚钻》(1936) 《桃花之歌》《女权》(1936) 《女权》[7](P36)《兄弟行》(1936) 《兄弟行》[7](P40-41)《年年明月夜》(1936) 《采茶歌》[7](P57-58)《茶山情歌》[7](P56-57)《梦里乾坤》(1937) 《凯旋歌》
这些流行歌曲,从题材上可以分成四类:表现生活、唤醒斗志、抒发情感以及寄托希望。这四种类型紧扣当时的时代背景,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表现生活
作曲家通过巧妙模仿与适度创新的方式,在呈现当下生活现状的同时,传递积极的时代精神,以《村姑乐》《茶山情歌》以及《香草美人》为代表。
接近生活的音乐语言和大量象声词的运用是《村姑乐》的最大亮点,如“喳喳喳”“咯咯哒”等象声词使作品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日常气质。这首歌曲以温饱都难以满足的农村人民为主体,道出了因“母鸡下了蛋,明天能吃个饱”的乐观心态,让人心疼不已。《茶山情歌》以江南小调“无锡景”的旋律骨干音展开叙述,结合山歌中情歌对唱的演绎方式,使民歌融入流行歌曲,让传统元素在时代交替之时继续流传。与前二者表现农村生活场景不同的是,《香草美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香草美人”生活贫寒、家人分离、前程无望的悲惨现实,“找营生,找营生,快找营生”“快救命,快救命,快快救命”[10](P32)等词展现出了底层劳动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心声与愿望。
谱例2:《村姑乐》选段

谱例3:《茶山情歌》

(二)唤醒斗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原本闭锁的国门,大量异国元素鱼贯而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让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启蒙与救亡的呼声由此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许多警世、斗争之作,《下琼楼》《打碎玉栏杆》《青春误》《兄弟行》《女权》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以《下琼楼》与《女权》最具代表性。
《下琼楼》为电影《翡翠马》的插曲,旨在呼吁有志青年走出闭锁,寻找自我,为社会而奋斗。作品整体为单三部结构,旋律行进舒展而歌唱。唱词最后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声音:“我为苦海人群们呼救,我为社会永远地永远地奋斗!”[10](P32)
电影同名曲《女权》采用了五声调式写作,旋律中展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味,而2/4拍的节拍框架之下坚定有力的节奏韵律赋予了作品强烈的斗争性格。全曲表达的思想是为女权斗争,为此许如辉使用了很多附点八分音符加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增加音乐的韵律感。而曲中多次使用的同音反复,铿锵有力,表现出了歌曲激昂的斗争精神。
(三)抒发情感
除了体现百姓生活,展现现实斗争以外,许如辉还创作了不少抒情之作,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作品类型。在笔者看来,《月夜小曲》与《桃花之歌》是这一时期许如辉创作的最优秀的两首流行歌曲。
《月夜小曲》是一首3/4拍的歌曲,缓慢、抒情地以舞曲的韵律节奏,唱着孤独而痛心的独白,由顾兰君演唱。从结构上看,这首歌曲的唱词可以明确地分成3句,情感走向非常自然,一开始以诉说的口吻表达对月夜的热爱,后来发现,这皎洁的月光“只能照着我的身,却照不了我的心”[7](P27),到最后触景生情,望着这明月“无限悲伤,分外痛心”[7](P27)。歌曲以附点节奏贯彻首尾,乐句伴随着情感的递进由疏至密,押韵而走心的唱词与细腻婉转的旋律配以干净而简单的钢琴、弦乐织体,让这首浅浅吟唱的月夜小曲塑造出了一个忧郁悲伤又让人心疼的音乐形象,深入人心、难以忘怀。
《桃花之歌》由顾兰君和顾梅君姐妹演唱,笔者并未找到这首歌曲的谱例资料,所以仅通过音频将其记谱如下。
谱例4:《桃花之歌》旋律谱⑥

全曲使用五声调式写作,虽然由于年代悠久,唱片中的伴奏音质和演员的歌唱听起来有些瑕疵,但其朗朗上口、积极向上的唱词和优美流动的旋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把弦乐乐器作为伴奏,配合自然:一把小提琴跟随着演员演奏主题,另一把小提琴配合对位,两条旋律线互相交织、共同发展。在这首歌曲中,许如辉结合了西方流行歌曲的节奏韵律,以三度音程下的切分节奏统领全曲,使音乐充满了舞动之感。
(四)寄托希望
愈是社会动荡之时,愈需要勇于面对的坚毅之心,方才能迎来希望中的未来。音乐便在此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易于独有的情感特质,能够散发出鼓舞人心的积极意义。许如辉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电影《梦里乾坤》中创作了插曲《凯旋歌》。这是笔者找到的所有歌曲资料中唯一一首进行曲风格的作品,音乐风格突出,词曲结合间具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全曲共分成三部分,结构规整。前两部分在音乐上完全重复,七字为一句的唱词音韵自然,配合音乐中大量的附点与切分节奏,使得作品在律动之余,充满力量之感。最后一部分在持续高音的二分音符中走向结尾,将音乐中的坚毅、果敢发挥到了极致,铿锵有力间希冀无限,给予了人们强大的心灵支撑。
谱例5:《凯旋歌》选段⑦

四、许如辉流行歌曲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正值中国娱乐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电影、唱片、广播电台等艺术媒介以及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流行歌曲的诞生与传播。然而这一时期也恰逢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且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量的流行歌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淹没消失,许如辉创作的流行歌曲便是如此。历史纵使被深埋,也总会重见阳光。许如辉所创作的流行歌曲,在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艺术价值
许如辉的流行歌曲作品,从内容上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曲调亲民、情感真挚,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1.贴切现实的题材
许如辉的创作在题材上有着很强的大众性与现实性。比如《卖油条》《村姑乐》等作品,以底层劳动人民的艰难生活为中心,表达积极向上、活泼愉悦的乐观情感。用欢快的曲调歌唱苦楚的生活,一方面激励在困难中的人们乐观面对生活的不易,另一方面也让生活相对富足的听众为之动容。又如《青春误》《打碎玉栏杆》《女权》《搁楼上的小姐》等作品,以警世或反讽的方式,激励年轻人珍惜光阴,勇于斗争。从现实出发,使得许如辉的大部分歌曲作品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共鸣,遂广而流传。这对于今天的音乐创作,特别是流行歌曲的创作依然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2.易于传唱的曲调
许如辉很擅长创作抒情动人的主题旋律,且进行自然、节奏统一。比如其传唱最多的《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永别了我的弟弟》以及《月夜小曲》与《桃花之歌》,婉转动人的主题音调在多次重复之下唱出了深入人心的音乐形象。
此外,由于受到其舅父在文学上的影响,许如辉的歌词写作大都韵律规整、朗朗上口。更难得的是,他在旋律与唱词的结合上有着独到的思考。比如他在《村姑乐》中运用了很多象声词来使音乐更贴近生活,但这些象声词并没有影响音乐的表达,而是赋予了音乐日常化的生机之意与亲切之感。正是这样细腻的处理方式,让歌曲唱出了生活之乐,也唱进了百姓的心里。
3.民族化的音乐风格
民族化的表达可以说是许如辉音乐创作中的一大特点所在。很多作品中都使用了五声调式,有些还结合运用了民歌的元素,比如《茶山情歌》中对江南小调的运用。而从少量的音频资料中可以发现,许如辉一部分流行歌曲中的伴奏会使用民族乐器进行配器。比如在《搁楼上的小姐》中以单旋律的弦乐伴奏为主,用民间弹拨乐器与打击乐器围绕主旋律进行节奏的对位和补充。相对简洁的伴奏织体,营造出了清新雅致的音乐氛围。
民族调式及传统乐器的使用自然地迎合了平民阶层老百姓的听觉习惯,也促进了流行歌曲的传播。与此同时,他在部分歌曲中还加入了少量西方的音乐元素,比如《永别了我的弟弟》中使用钢琴进行简单的和声性伴奏、《桃花之歌》中运用带有爵士风格的切分节奏等。这样的创作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不仅推动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对于中西方音乐的融合与交流也具有着重要的探索意义。
(二)历史意义
许如辉的流行歌曲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创作作出了贡献,也是这段历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目前可见的各类歌集、杂志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创作存在着一个颇为壮观的作曲家群,许如辉便是其中的一员。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等作曲家和一些有影响的歌星上,忽略了其他在当时同样广受传播的流行歌曲。在笔者看来,许如辉的流行歌曲作品,不仅丰富了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歌曲创作,且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着亲民、向上的淳朴精神,也蕴含着深刻的警世意义。他本人所提出的“音乐到民间去”⑧的理念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与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流行歌曲作曲家黎锦晖的平民音乐思想不谋而合。
此外,纵观许如辉的流行歌曲创作,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融合、交织,这一方面源于其深厚的民族音乐功底与扎实的基础素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因此,他创作的这些流行歌曲,不仅反应了其本人的艺术思想,也可以认为是其视角下的时代缩影。通过对其作品的研究,侧面展现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音乐样貌及社会形态,借此,也为当今的人们打开了重读历史的一扇窗。
诚然,受限于创作经验,许如辉的流行歌曲作品确实存在着少许不足之处,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探索过程。伴随着各种题材的尝试、摸索、进步,这些作品才展现出了许如辉独树一帜的个人特色——其古朴雅致的音乐气质,正是历史动荡时期最难能可贵的艺术品质。因而,许如辉的流行歌曲创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虽然“文革”的历史原因让许如辉的流行歌曲长久地埋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更不能将其遗忘。从时代特征看,那时的每一首流行歌曲都是作曲家随着时代的发展摸索、探寻出来的,挖掘与研究这些音乐家与其创作的流行歌曲对于探寻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史为鉴,这些音乐作品,无论是其个性或是特性,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中国音乐持续不断的发展历程中,它们始终熠熠闪光。
注释:
①周琳《<申报>黎锦晖音乐史料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第31页。文中列举了《申报》中1926年的两则信息,证明《毛毛雨》的创作时间应为1926年。
②目前除许如辉的女儿许文霞女士在《中国民族乐派音乐家许如辉传略》《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等文中对许如辉的艺术人生作过简要的介绍外,未见有学者对许如辉做出专门研究,关于许如辉的生平事略已不为世人所知。本文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文中所提到的许多乐谱和史料都是在许如辉先生的女儿许文霞女士的帮助之下搜集整理完成的,对此笔者深表谢忱。
③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未发表),第3页。
④部分生平总结自2017年笔者与许文霞女士的电话访谈记录。
⑤许如辉《搁楼上的小姐》,上海子夜乐会出版,1934年。谱例由许文霞女士提供,原谱由五线谱与简谱共同呈现,笔者选取其中段落,重新制谱完成。
⑥该谱例由笔者听记完成。
⑦此处谱例由许文霞女士提供,笔者根据原谱重新记录完成。
⑧许如辉手稿,来自于2017年5月13日,笔者与许文霞女士的电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