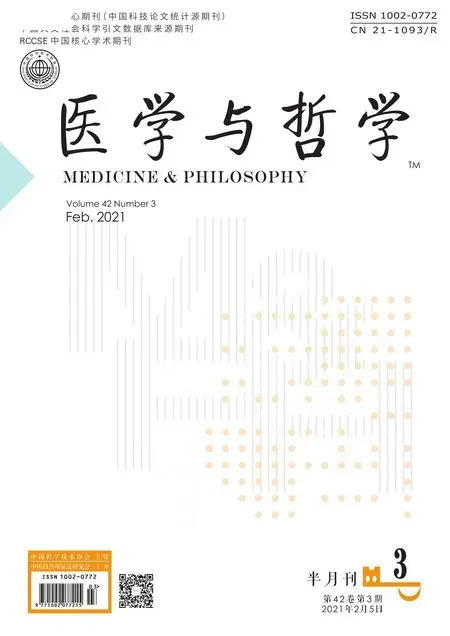从淳于意与华佗医案比较观汉代医事*
于 凌
汉代是中医理论体系构建成形的关键时期,尽管其年代久远,可资利用的医案文献少之又少,史籍中关于名医医案的文献研究价值及中医学术贡献值得关注。淳于意与华佗分别是西汉初期与东汉末年的名医,他们没有明确留下自己的医学著作,但他们的临证思维与实践经历已保留在部分史料中。笔者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淳于意的诊籍[1]和散落在《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的华佗医案[2]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二人在正史中行医记录的比较,梳理两批医案的特色,在医案概况、病因认识、病种分科、诊断技术、治法运用、医学伦理等方面比较两批医案的异同,以冀能从中找寻到中医理论形成初期的某些学术认知规律,并力图从局部管窥汉代医学及医术的发展概貌(《后汉书·方技列传》的华佗医案与《三国志》中华佗医案基本雷同;《中藏经》等相传为华佗之作的书籍,一则成书年代及其真伪尚存疑惑,二则行文风格与上述正史书籍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暂不纳入讨论)。
1 简况梳理
《史记》载有25例内容翔实的医案(谓之“诊籍”),每案均对患者的姓名、职业、性别、病名、症状、脉象脉理、发病原因、诊疗过程详细记录。诊籍草创了中医传统病案的基本范式,是中医医案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典文献。《史记》中关于医学理论及术语等方面的记载非常专业,很有可能是参考了当时格式已基本定型的医疗档案后,进行文学化的加工而形成。因此诊籍不仅是一个个可读性很强的生动医学故事,更有可能是专业性很强的病历记录。相较而言,在《三国志》与《后汉书》中记载华佗行医生涯中的17例(剔除重复)生动医案,尽管年代更晚,但和诊籍医案相比则粗陋得多,没有相对固定的行文格式或医案要素罗列,内容侧重在歌颂或神化华佗的高超医术,而医学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而专业的内容则相对简略,整体内容更加艺术化和生活化,学术色彩并不浓厚,也有一些让人难以信服或中医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上述差异或许与两位医生的生活经历(淳于意多在庙堂行医而华佗常游历于民间)有关,或许与西汉鼎盛时期文档管理有效及东汉末年兵连祸结造成文献缺失有关,或许与司马迁、陈寿及班固等不同作者写史的风格不同、目的不同有关。
从患者性别及年龄分布看,诊籍有18例男性,7例女性。除“齐王中子”有可能是幼儿,其余均集中于成年阶段。而华佗医案中14例为男性,3例为女性。患者年龄除1例是2岁患儿,其余皆为成年。因此,在对患者一般信息的收集上,两批医案大同小异,都未对个案中的性别或年龄因素作特殊强调或分析,说明汉代在年龄对疾病的影响方面尚未过多关注。至于现代医案比较关注的职业因素,两批医案多从姓名中带出职业称谓,但也很难看出是医者基于职业对疾病影响的考虑。关于患者的身份或地位,诊籍中有3例是明确的奴、侍者类阶层,20例明确是政府官员或贵族阶级,另有2例身份不明。而华佗医案则更倾向于对普通百姓的诊治,与疾病相关的社会信息缺失较多。
关于预后,25例诊籍医案中,治愈15例,死亡10例,且患者死亡之前,淳于意均对不良后果做出了准确预判。华佗医案治愈12例,死亡5例(均准确预判)。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医疗水平,这已属于难能可贵,我们无法以现代的眼光对其苛求太多。
2 两批医案的主要内容
2.1 病因认识
淳于意医案的病因类别,外感病因9例(风、寒、湿、热等邪气),各种不良生活习惯7例(如汗出伏地、过劳、卧开口及食而不漱、好持重、饱食而疾走、服石等),房劳因素7例(反映当时社会对房劳与健康关系的重视),嗜酒因素5例(与患者多为贵族阶级,有奢侈的生活条件有关),情志因素3例(忧、怒、郁等),外伤1例(堕马僵石上)。华佗医案在病因方面的交代多阙如,仅部分医案涉及外感(府吏兄寻、李延并案)、外伤(督邮徐毅针刺误伤案)或虫毒(彭城夫人案)、嗜酒(盐渎严昕案)、房劳(督邮顿子献案)、饮食(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案)等因素,其余病案则对病因语焉不详。可见,汉代医学已可初见中医病因理论早期大体分类的端倪。后世较为成熟的中医病因分类始于宋代陈无择的三因分类,而上述医案对于病因的大体分类与之相比,在外感病因方面大体相似,但在内伤病因方面尚有较大分歧,如没有比较确切地从情志、饮食或劳逸等方面进行梳理,对于生活方式不良的病因也比较分散,但同时却非常重视房劳和嗜酒因素(并未像后世一样把房劳归入劳逸一类,把饮酒归为饮食内伤一类)。另外对于后世较为重视的病理产物性致病因素(如痰饮、瘀血等)则没有提及,而是作为了整个病理过程的中间环节。从现在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框架看,病理产物性致病因素不列入病因而是作为病机概念,更加符合临床实际,也更加能理顺理论体系上的逻辑关系。对这个问题重新界定有助于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完善。另外,把诱因当作病因的习惯也在汉代医案中基本形成。
2.2 病种分科
若依后世中医分科的标准,诊籍医案除妇产科2例(难产、闭经),外科1例(肺伤),儿科1例(齐王中子病气鬲案)、寄生虫1例,齿科1例(龋齿),其他均属于内科病证,分别是(内)疽、涌疝、热气病、风瘅、肺消瘅、遗积瘕、迥风、风厥、气疝、热厥、内关之病等,多数从原文病名无法推断相当于现代何病,但主症多集中于发热类、晕厥类、虚损类、疼痛类及饮食、二便、出汗、四肢运动等方面的异常。说明诊籍致病涉猎广泛,也提示当时社会没有明确的疾病分科诊疗意识。
华佗医案涉及内科11例(除部分头痛等症状外,其余病证表述不明确者居多);外科3例(外伤、虫兽伤、手术各1例);妇科2例(均为胎死腹中);儿科1例(下利)。华佗医案的语言没有太过晦涩的医学术语,也基本不提病名,只是偶尔简要叙述主要症状,甚至很多医案连主症都没有。
两批医案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数疾苦和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此外,淳于意长于内科,而华佗擅于外科的传说凭据也若隐若现。
2.3 诊断技术
诊籍中有大量的扁鹊脉法的传承记载,包括很多更早时期脉学著作的引文,诊病当时脉法的运用及淳于意本人对诊脉技法及临床意义的理解。以齐侍御史成案为例,“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从文中可知以下几点:首先,虽然多数关于脉学、脉法的论述和后世历代通行的脉学理论及实践有较大出入,但可以看出在汉代中期,学院派的脉学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且自成体系,为何未能传承下来可能与过于复杂、操作空间较小,不利于流传等因素有关;其次,淳于意的脉学技能并非凭空出现,也是得益于更早的脉学文献在当时社会的流行,更早的脉学文献我们已经无法见到,因此诊籍就成为了珍贵的二次文献;第三,汉代的脉学理论我们现在无法完全破解其医学含义或操作规范,但从文中可知当时的脉学理论中已经有了脉的形、势、度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脉象变化已经与体内的脏腑、经络、形体、气血等状态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各种病理改变、病证分类等内容有了大致的对应关系;第四,脉诊方面在当时已经是判断病因、分析病机、标定病位、推测病势的重要手段。目前我们尚无法通过诊籍中这些碎片化的脉法内容构筑一个完整而实用的脉学理论,但诊籍中的脉学文献的价值可略见一斑。
除脉诊外,淳于意的色诊方法也很有特点,如在齐丞相舍人奴案中,提到“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在齐王黄姬兄黄长卿案中提到“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干,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在齐中郎破石案中提到“色又乘之”[1]的色诊脉诊互参法。
反观华佗医案,如李将军妻病案,甘陵相夫人有妊案等都叙述了华佗诊脉技能几乎出神入化,但由于具体方法及医学解释上没有记载,使得华佗医案中的脉法蒙上了传说的色彩而失去了医学价值上的研究意义。
2.4 治法运用
诊籍中的内治法涉及到了火齐汤(6例医案均有涉及,综合分析可知火齐汤或为当时运用较为广泛的治疗下焦实热病变的类方)、下气汤(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案中用于清热泻火)、柔汤(齐王黄姬兄黄长卿案中用于治疗肾痹,即肾系外感湿邪所致的腰胁痛不可俯仰)、药酒(济北王病案中治疗寒湿内侵所致的风厥胸满、菑川王美人案中治疗难产)等汤剂及芫花(临菑氾里女子薄吾案中治疗寄生虫)等药物。外治法主要涉及刺法(济北王阿母案、菑川王两案中均用于泄热)、灸法(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案中用于治疗寒客膀胱、齐中大夫病龋齿中使用)、苦参漱口(齐中大夫病龋齿)、寒水拊头(菑川王案)等。
华佗医案中,内治法有汤剂有丸散,治法提到过汗法、下法,具体方药提及四物女苑丸(东阳陈叔山小男案中治疗虚寒),蒜(治疗某病咽塞)等,其中四物女苑丸可视为四物汤的前身,对后世方剂学产生重要影响[3];外治法有针刺(曹操苦头风眩案、李将军妻病难产案),手术(某腹疾案),温汤渍手(彭城夫人虿螫其手案)。另有1例情志疗法(某郡守笃病久案),通过激怒病人达到治疗目的的另类疗法。
两批医案的治法各有千秋,淳于意的医案中常有两到三种治法综合运用,如内外治并用,针药融合等,而华佗医案的治法较为简略且单一。从病证与治法的对应性来看,淳于意的医案中的治法更加贴合后世通行的主流医学理论与实践方法,如清热法、活血法、温中法、散寒法等,尽管具体方药不得而知,但治疗理念与后世临床一脉相承。反观华佗医案中的治法,不可解释或没有解释的地方更多,如用活血法治疗虚寒证。另辟蹊径的治法也更多,如情志疗法,手术或外治法等。这些或许是淳于意代表了当时学院派的做法,而华佗更像是民间医生做派的又一例证。
此外,治法的细节(如何选药,如何取穴,如何手术等)我们无法得知,但两批医案中表露出来的治则治法理念非常值得后世传承与发扬。
2.5 医学伦理
医学伦理的问题古今中外皆有,从不会因为年代古远便显得浅薄。越缺少技术支撑的年代,对人心、人情的关怀越发显得重要。汉代的医学伦理内容虽然远未达到后世的理论高度,但医案中处处流露出临床中医患双方不得不面对的伦理问题和汉代医生的处理方式。
关于知情同意:淳于意在诊断齐国侍御史成的头痛时感到了疾病的凶险,便“即出,独告成弟昌”,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医者就早早在隐瞒与知情的伦理争论上选择了前者,或许对患者本人的某种权益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尊重,但是对患者的疾病进展或生命质量都力争最大限度的维护,说明在古代名医心里,当生命与法理相悖时,医者多选择更加重视生命的价值。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医学伦理特点,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医学伦理范式,也无法做到重视病人知情权大于重视生命本身。
关于临床决策:华佗医案中曾记载:“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无论是多么高明的医生,治不治和如何治的选择权始终是掌握在患者手里的。同出于汉代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确立患者为本的治病理念,率先提出了“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的英明论断,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仍然有其现实价值[4]。这种理念在华佗本案中得以充分体现。
关于临终关怀:诊籍在齐章武里曹山跗病案中提出 “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此种决定体现了淳于意朴素的临终关怀思想。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忌讳谈论死亡,但诊籍中已有如此明确的处理方式,似乎与普遍的民众习俗或文化特征不符。这恰恰是诊籍这个传统医案范式之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所在。承认死亡,才能在治疗无效的前提下实施临终关怀。承认医治对某些濒死患者来说是无效的客观现实, 通过对他们提供舒适的照料来替代卫生资源的无谓消耗, 它实质上体现了对患者及大多数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5]。
3 讨论
3.1 两批医案的异同
异中之同:“诊籍”出现于西汉,华佗医案散见与东汉末年。前者更周详,也更贴近于真实的医疗状况,后者多少带有了一些传说或传奇的意味。两批医案在对医生的评价,医生的职责,病证谱系的呈现,诊断技术及治法种类的记述等内容大体一致。两批医案在成书年代、行文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勾勒了西汉到三国时期医学发展的风貌。
同中之异:两批医案展现了官方与民间两个不同类型医学的双重形式。前者对于医学内容本身及医学相关内容的记述反映了官方规范(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要素、立论依据、操作说明、结果呈现等内容),呈现出医学学术工作或政府档案管理的双重需求;而后者则凸显了民间医学的一种随意性(形式不拘一格,内容略于实证而感情色彩浓厚),折射出民众对名医垂问人间疾苦,不计功名利禄的美好形象的渴望。
3.2 两批医案的医学启示
合而观之,我们可从两批医案感知汉代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成熟度。首先,在医疗技术水平低下的年代,对疾病预后的判断是医生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评价医生水平的重要指征,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对于技术高超的名医一律怀有尊崇敬畏之心与渴求之意。其次,对于病因的认识和后世病因理论相比,更加简化而欠于逻辑内涵,但同时也没有后世那种病因病机相混淆而导致的无谓复杂化的倾向。再次,虽然两批医案所处的年代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比较粗浅,但对症状本身、症状与病因的对应关系,症状的产生发展机理等方面的医学解释已经作了大量尝试,并且部分病证的解释和分类对今天的中医学术内涵乃至临床应对也具有启示。最后,汉代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与后世中医临床的种种诊疗技术大相径庭,在后世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规范与简化(便于操作与评价)是发展主线,由此也牺牲了很多有效但另类的诊疗技术,两批医案在诊断与治疗方法上的特殊内容是今天中医理论与临床技术提升的重要内容。
3.3 两批医案的人文价值
在史书中记载的医案不同于医案专著里的医案。后者非常注重医学本身的客观性,而史书中的医案,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与创作目的都有特殊性,因此选案未必完备或客观,而且记录过程也非常容易忽视医学的问题而专注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两批医案较后世医案专著而言,具备了更多更广泛的人文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对上述文中提到的知情同意或临终关怀等人文理念,似与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某些观点异曲同工,但同时又蕴含了中国传统医案中“以人为本”的文化特征,值得当今社会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