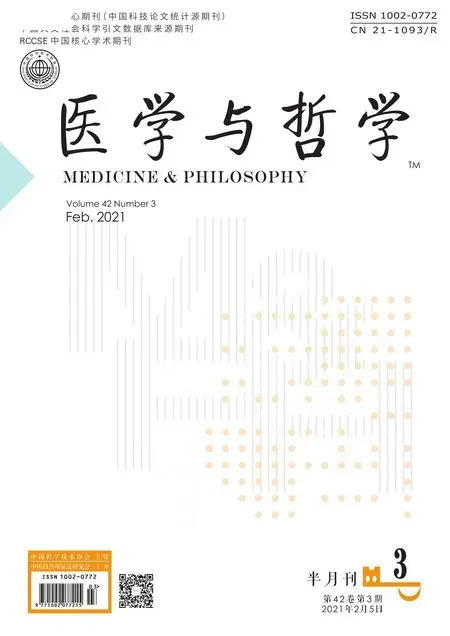文化情境主义下的心理创伤与心理弹性研究进展
吴佳佳 赵旭东②③
当前局势下,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群体心理创伤(socio-psychological trauma)和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成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主题。最新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民众普遍存在抑郁、焦虑、恐惧、无助等创伤应激反应[1-2]。同时,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面临高强度的身心负荷,其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3-5]。鉴于此次疫情诊疗和防控具有不可分离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复杂特点[6],这对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心理专家和学者们对此一致认为,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长远来看更是一个关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谐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议题[7]。其中,提高整体社会系统的支持水平,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强调文化软实力因素,对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至关重要[8-9]。这一共识与西方心理创伤学领域中的文化情境主义转向不谋而合。
心理创伤和心理弹性是个体在面对心理危机时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方向的应对路径。面对此次疫情对心理危机工作提出的艰巨任务,传统基于个人视角和症状导向的心理创伤医学诊断模式无法单独回应这一挑战。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心理创伤学领域中发展出的基于文化情境主义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弹性理论,可以平衡传统心理创伤视角的局限性,为当前心理危机干预的临床实践拓展新的理论视角和工作思路。本文首先阐述西方心理创伤学的文化情境主义转向,包括群体心理创伤概念的发展。之后,概要介绍近年来西方文化神经科学领域关于文化对创伤认知和心理弹性影响的相关研究结果。最后,分别介绍Ungar提出的心理弹性的家庭-社会-生态模型,以及Maercker和Horn提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PTSD)的社会-人际整合模型, 以期为我国的心理创伤和干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
1 西方心理创伤学的文化情境主义转向
西方的心理创伤学(psychotraumatology)在二战后得到持续的发展,尤其体现在对PTSD的症状诊断和干预治疗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其特征之一是以情境主义(contexualism)作为认识论基础来批判传统的客观主义认识论[10]。情境主义认识论持有多元主义的知识信念,强调社会文化和背景信息在创造知识过程中的建构作用[11]。20世纪70年代,情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如发展心理学对个人心理发展的认识,其研究范式从对人类发展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转向对过程和解释的关注[12]。
在心理创伤学领域,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出现从个人主义范式向文化情境主义范式的转变。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13]。创伤学家批判PTSD概念仅关注症状而剥离了创伤的情境,把创伤看作是对过去事件的反应和结果,而忽视了创伤情境可能具有长期慢性的特点。因此,文化情境主义取向的创伤学家倡导一种突出社会性和过程性的创伤定义。例如,Volkan[14]最先采用情境主义视角,提出了“集体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的概念,并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理解集体选择性创伤形成的动力机制。Alexander[15]提出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概念,强调创伤对文化认同产生的消极影响。Denham[16]重新定义了“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的概念,侧重创伤代际传递的动力机制,以及集体叙事作为心理弹性的资源。另外,德国创伤学家Becker[17]和Hamburger[18]分别提出了“社会政治创伤”(socio-political trauma)和“社会创伤”(social trauma)的概念,把非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纳入创伤概念的内涵中。虽然这些群体心理创伤概念各有侧重,拓展了创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也带来概念界定不清和相互混淆的问题。Brunner[19]提出需要谨慎使用过于简化的群体心理创伤概念,把创伤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够的,有必要将文化敏感性纳入对创伤的考虑。文化心理学家Kirmayer等[20]也认识到诸如历史创伤这样的群体创伤概念的定义不够操作化,难以获得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而文化神经科学与心理创伤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推进群体心理创伤概念发展的新方向。
2 文化要素对心理创伤认知和心理弹性的影响
随着文化情境主义视角的普遍流行,文化心理学研究成为当代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新浪潮,为多样化理论范式的统一以及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联合提供了可能[21]。其中,文化神经科学就是认知心理学以文化论为基础的第二次革命的典型代表。它结合了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化、心理过程、大脑和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神经科学的最大优势是在文化和生物学之间搭建桥梁,借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理解文化对大脑的影响。同时,文化神经科学不满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研究范式,致力于丰富多元的文化视角。文化神经科学假定,社会文化环境极大地塑造了个体的思维、行为和情绪体验[22]。
近年来,文化神经科学与心理创伤学结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2016年,Liddell等[23]在《欧洲心理创伤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在影响PTSD的神经基质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显示,文化会对PTSD的神经基质(neural substrates)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与创伤相关的恐惧调节异常(fear dysregulation)、对威胁的注意偏差(attentional biases to threat)、情绪和自传体记忆(emotion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受损、自我参照过程(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不足、依恋和人际过程改变等方面。文化通过影响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进而影响这些策略在生理层面产生的结果,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文化价值表征的变化可能会增强特定的神经过程,这些过程因文化而异,从而巩固了特定的行为反应模式、认知和情感倾向。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通过对情绪采取压抑反应,来减少对创伤的再体验和回避症状。换言之,情绪压抑不但与心理健康水平不呈负相关,反而有利于心理功能的发挥。这是由于集体主义价值观鼓励压抑强烈的情绪表达,从而对他人带来最小的不利影响,以实现社会和谐。另外,文化变量在PTSD的创伤记忆的巩固和提取中扮演重要作用,如创伤记忆越具有文化适应性,就越少出现回忆侵入现象。
2019年,Bernardi等[24]进一步聚焦文化对创伤认知评估的影响。创伤的认知评估在PTSD的治疗中起到核心作用。而自我理解的文化差异则通过影响个体对自主、控制、心理挫败、自我的消极评估等方面,进而影响到PTSD的症状和治疗。跨文化研究显示,相比美国人,中国人在面对挫败时更倾向于坚持,并对挫败有更高的容忍度,更少认为挫败会对他们的目标和自尊产生影响。在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方面,亚洲人的感知控制低于美国人,而较低的感知控制对心理痛苦的影响也较少。这意味着,与一般认为的较低的感知控制带来较高的心理痛苦不同,亚洲人虽然有较低的感知控制,但这并不带来较高的心理痛苦。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互相依赖、团体的内聚力,而较少看重个人控制的价值。鉴于个人控制不是受文化鼓励的特质,缺乏个人控制可能较少带来心理痛苦。在亚洲群体中,创伤幸存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感受和认知对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而言越是恰当的,他们就越少出现PTSD症状。另外,亚洲被试者对自我和世界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显著地预测PTSD症状。
在心理弹性研究领域,Meili等[25]于2019年发表了关于文化影响心理弹性的跨文化研究。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个体寻求社会支持的策略,以及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的叙事来体现。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一是影响个体寻求社会支持的决定;另一个是寻求社会支持对健康的作用。在决定是否寻求社会支持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多留意他们的决定是否对亲近他人产生影响,他们对关系约束更为敏感,于是更容易认为寻求帮助会对团体和谐带来消极作用。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寻求支持时更多偏向于问题解决的方式。在寻求社会支持的效果评估方面,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在接受间接的支持时,痛苦减轻的效果更明显。在创伤后成长叙事方面,不同社会文化情境对灾难后的心理弹性和PTG的叙事有所不同。北美文化过度强调生活的积极面,对从负面事件中产生积极变化的评价过高。有学者把这种过度强调积极面的态度称之为“积极态度的暴政”。相对而言,亚洲文化的叙事中更多体现了“接受、平衡、隐忍”的态度。这些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文化作用的理解,也为进一步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思路。
3 心理弹性的家庭-社会-生态模型
文化情境主义的范式转向,不仅引导心理创伤理论朝向整合个人和社会水平的方向发展,而且也推进心理创伤干预转向以资源取向为主导的系统观路径。20世纪70年代,西方心理创伤学领域出现从创伤的病理取向转向对积极适应的研究,心理弹性(或称心理韧性、复原力)成为研究热点。心理弹性研究经历了1970年~1990年侧重个人特质与保护因子研究,1990年~2000年关注心理弹性形成过程研究,以及2000年之后强调心理弹性作为积极成长的心理潜能[26]。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视角依然围绕个人主义为核心。
近10年来,随着发展系统理论的出现,以Masten[27]为代表的学者们努力将心理弹性视角与家庭理论和实践进行融合,出现了家庭心理弹性的概念,以家庭为核心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日渐成熟。系统理论的核心原则认为:(1)互动系统在多个水平塑造了系统的功能和发展;(2)系统的适应能力及其发展是动力性的,持续处于变化中;(3)由于系统内部的互相联结和彼此互动,在各领域和功能水平都会出现改变;(4)系统是彼此依赖关联的。这些适应系统的复杂特点同样适用于个体和家庭的心理弹性。从系统的观点看,个体的心理弹性有赖于家庭的心理弹性,而家庭的心理弹性又有赖于社区、文化环境等更大系统的心理弹性。
除了家庭心理弹性概念之外,以Ungar[28]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开启了心理弹性的第四个浪潮,进一步提出了心理弹性的社会-生态模式(social ecological model)。该模式认为,应把对心理弹性的定义扩展为:一个人以具有文化意义的方式与控制资源的人进行协商,并成功地获得了维持其福祉所需资源的能力。这个定义强调心理弹性不仅指个体渡过危险环境的能力,同时也强调环境为个体需求提供资源的能力。这意味着,心理弹性既有赖于家庭、学校、社区、政府为个体需求提供资源;同时,心理弹性也体现为在文化、社区、关系和个人方面的资源[29]。这一社会-生态模型区别于传统心理弹性理论的特点在于:其一,创伤症状与心理弹性两者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二元关系。个体在出现创伤症状的同时也可以具备积极的心理功能,如社会联结、共情能力等。其二,强调心理弹性本身具有情境性和动态性。个体在某一方面具有心理功能优势,而在另一方面则可能不具备同样的优势。其三,强调心理弹性不仅是个人的建构,也是环境提供个体成长所需资源的能力,即后天环境大于先天优势。其四,强调心理弹性受文化变量的影响。只有受到重视的资源才有可能成为优势资源。也只有在文化态度环境的积极促进中,个体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心理弹性的潜能。而积极应对能力的培养也是文化因素的结果,若个体所处的信念系统一致认为痛苦对个人成长而言是必要的,那么个体对痛苦就有更高的承受力。
总而言之,文化情境主义视角认为心理弹性是一个涉及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动态的、系统性的概念。根据系统理论,如果我们只聚焦个体的心理弹性培养,以便促进个体更好地应对挫折,这属于第一序的改变。而如果我们关注于提供一个促进性的有利环境,为心理弹性的培养提供资源,这属于第二序的改变。往往第二序的改变比第一序的改变更能够调节创伤的负面作用,促进性的环境能够改变发展性的路径,如个人动机、自主感、气质类型、人格,以及针对特定行为的基因表达。
4 PTSD的社会-人际整合模型
传统的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框架仅从个人视角来看待PTSD,侧重对患者的创伤后症状进行描述、解释和治疗,而较少考虑患者所处的社会情境要素。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聚焦个体的心理创伤视角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发展[30]。基于个人视角的创伤治疗以调整个体的记忆、认知、情感方面的功能失调为目标。近年来,基于以下理由,文化情境主义取向的创伤学家对个人视角的PTSD理论提出批判和质疑:其一,将个体作为社会生物的哲学观不可忽视。其二,社会视角的创伤理论认为受到创伤的不仅仅是个人,更是整个社会。 其三,当前创伤压力已扩展到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之间无法彼此孤立地应对创伤,使用基于西方文化的创伤理论时需要考虑本土文化的敏感性。
2012年,Maercker等[31]提出了PTSD的“社会-人际模型”, 将文化情境主义视角整合进PTSD理论。该整合模型将个人嵌入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层面,认为对PTSD的考虑应涉及个人、人际关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首先,个人层面既包涵传统PTSD模型强调的个体内部心理特点和症状,又将社会性情感反应涵盖其中。社会性情感反应(social-affective response)指的是与自我和他人相关的心理状态,如羞耻、内疚、愤怒、复仇心理等。如“幸存者内疚”就是与PTSD相关的一种常见的社会性情感反应。个体表现出自我责怪的陈述,如“为什么幸存下来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如果我当时那样做/不那样做,对方就可能幸存下来”。此外,羞耻和愤怒也是常见的创伤后社会性情感反应。Maercker和Horn指出,与内疚、羞耻和愤怒相比,报复心理较少受到研究关注。而很多社会影响恶劣的个人危害社会事件可能与创伤后的报复心理有关。第二,人际层面由亲近的社会关系(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情境构成。亲近关系指的是高水平的心理亲密关系,如伴侣、重要家庭成员、亲密朋友等。具体而言,人际关系层面与创伤的暴露表达、社会支持、创伤的负面影响、共情能力等有关。这些方面都涉及到与亲近关系的互动,因此关系满意度和心理亲密感是反映个体的关系现实的重要结果变量。这意味着较高的关系满意度可以成为创伤的保护因素。其三,社会层面(social contexts)反映了文化和社会要素对个体创伤过程的影响,包括个体所属的文化价值系统对创伤的社会性态度、对创伤的集体叙事以及体验等。这意味着在评估创伤影响时,要将社会凝聚力和价值系统纳入考虑要素中。同时,该模型强调三个层面的不同要素之间彼此作为中介影响PTSD。
2016年,Maercker等[32]进一步扩展了PTSD的社会-人际整合模型在心理创伤干预中的应用。他们认为心理创伤干预的目的除了缓解和消除PTSD的症状之外,还应包括提升关系质量和社区功能。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可以采取聚焦创伤的叙事暴露治疗(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特别关注在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在关系层面,促进家庭互动的心理宣教、聚焦特定障碍的伴侣治疗等干预都是不错的治疗方法。在社会文化层面,鼓励个体表达、防止社会支持氛围的恶化,处理怨恨和挫败的社会性情感,支持团体认同、意义重建等都是可行的干预措施。简言之,基于PTSD的社会-人际模型的心理干预,将个体的PTSD治疗、家庭伴侣治疗以及社区的团体干预都纳入到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心理干预“大概念”中,同时强调将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心理弹性作为干预目标,展开相关的心理弹性工作坊、引导公众对创伤受害者持有更为公正和共情的态度。
5 文化情境主义视角与国内群体创伤研究
相对于西方心理创伤领域文化情境主义转向的热潮,国内心理创伤的研究仍然以PTSD的医学诊断模式为主导。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群体心理创伤有所关注。例如,林瑶等[33]于201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创伤代价传递的综述。张静秋等[34]提出了社会性创伤的概念,指的是一系列直接作用于个体心理的社会事件所产生的创伤性影响,并研究了其与PTSD和心理控制感的关系。事实上,诸如创伤的代际传递和社会性创伤的现象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中屡见不鲜。早在1991年,赵旭东等[35]已提出在我国开展文化与心理卫生、发展与健康的研究具有十分必要的意义。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契合性是近几十年来国内临床心理工作者一直倡导的重要主题。例如,罗鸣春等[36]提出心理问题躯体化、心理问题道德化、心理问题生活化是儒家文化与中国人社会心理和行为相互建构的典型表现。余霞等[37]提出心理健康服务本身作为文化与心理交互建构的产物,其理论建构具有明显的文化和历史根植性。
在心理干预的临床实践方面,文化情境主义视角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实践思路。首先,PTSD的社会-人际整合模型符合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政府决策,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心理支持,是我们的文化“支持”优势[8]。社会-人际整合模型为我们充分挖掘家庭、社区、社会文化对个体心理弹性的资源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例如,借鉴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治疗思路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提供心理支持[38]就体现了这一方向的临床实践。最新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对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创伤后成长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39]。这与创伤社会认同模型[40]的观点一致,团结、社会支持、稳定的意识形态等社会认同可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源。杨平等[9]也提出,中国文化特有的群体态度、国民性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对于心理工作者而言,文化敏感性视角要求我们提升对创伤心理的文化差异的理解,进而采用适合个体文化背景的治疗方法。具体而言,心理工作者需要意识到,个体关于心理疾病性质的文化信念会影响治疗的过程,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会展现出不同的心理疾病症状,不同文化对心理疾病的诊断也应有所不同。从自我反思的层面而言,心理工作者还需要不断意识到文化在个人身上的印记和影响[41]。采取阴阳辩证的哲学态度来看待积极和消极心理之间的动态平衡[42],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尊重本土文化传统对创伤的理解和态度,避免落入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积极态度的暴政”。
在心理创伤的科学研究方面,文化情境主义视角可以为我国推进群体心理创伤的本体化研究提供认识论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扩展社会文化认识论视角,建构本土化的理论框架。群体心理创伤相关的社会认同建构、PTG的集体叙事等主题都可以成为未来展开本土化研究的方向。同时,借鉴西方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以为进一步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合作提供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