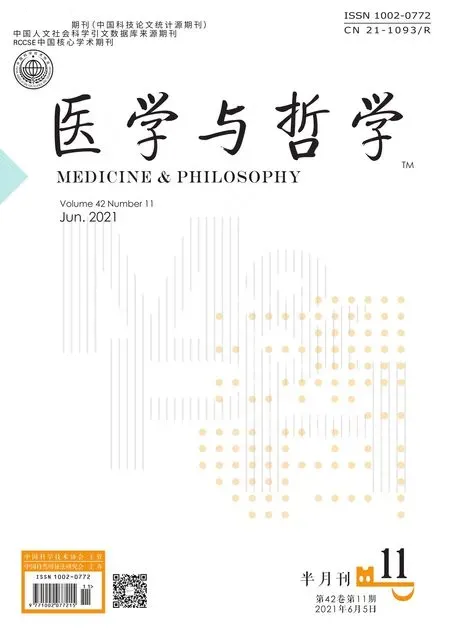“性别不一致”去精神病化的思考
贺 莹 彭会清 崔夕龙 陈晓岗
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2019年5月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 eleventh revision,ICD-11)中所使用的概念,指个体所体验到的性别和被指派的性别之间存在显著且持续的不一致的情况。ICD-11摒弃了“性身份障碍”这一原本隶属于“人格与行为障碍”下的诊断名称,将“性别不一致”纳入“性健康相关情况”,意味着“性别不一致”彻底“去精神病化”,同时还保证了去精神病化后的个体仍能得到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
1 “性别不一致”诊断变更历程
早在1979年,ICD-9中就开始出现易性症(trans-sexualism)的诊断名称,隶属于“精神障碍”下“性与性别认同障碍”条目。几乎同时期(1980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The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third edition,DSM-Ⅲ)[1]也开始将“性身份识别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纳入疾病诊断分类中,并在之后的DSM-Ⅳ中沿用[2]。后来我国在2001年编制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TheChineseClassificationofMentalDisorders,third version,CCMD-3)[3]则同时借鉴了ICD和DSM系统的诊断结构,将“易性症”归于“性身份障碍”,直到如今,在我国实施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是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症”诊断证明。直到2013年DSM-5问世后才有所改变,不再将性别认同差异视为障碍,而是更关注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并因此将其命名为性别烦躁/性别苦恼(gender dysphoria)[4],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性别不一致“去精神病化”的重要里程碑。
2 性别的多维和非二元特征
性别不一致主要涉及的心理学领域是个体的性别认同,发展心理学认为儿童对自身的性别认同开始于2岁左右,其形成主要与对性别角色的模仿以及行为强化有关,并通过这种认同来获得性别角色群体归属感[5]。但是我们以往对性别的角色分类完全是基于生物学性别,在这种有限的认知下,与生物学性别不符的性别表达就被归类于“性别角色异化”,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角色适应障碍[6]。
由于性学研究、性与性别少数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性别并不是指单一的生物学性别,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维度,即生物学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7]。不同维度之间不一定是完全统一的,各个维度之内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更多的是以“连续谱”的形式存在的。因此,“性别角色异化”“性别角色适应不良”此类说法不仅没有考虑到性别在各个维度上的个体化差异,而且还充斥着大量的对性别认识的刻板印象,即对性别角色特征的固定看法。
在性别的四个维度中,性别表达和性倾向这两个方面,已有大量的性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对其进行探讨,或涉及自由意志和自我价值,或涉及社会构建和人权,本文将不再进行赘述,本文主要从医学视角对生物学性别和性别认同进行介绍。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以往认为固定的生物学性别,其实也有着大量的医学上的非二元发现。生物学性别的非二元发现,对“性别不一致”的去精神病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被指派的性别”往往是二元分类的,而若连指派的依据——生物学性别本身都是具有非二元特征的,那么个体有不同的性别体验也不一定非得用精神病来解释。
生物学性别首先和性染色体相关,但是性染色体本身除了最常见的XX、XY组合外,可能的性染色体组合变异还有XYY、XXY、XXX等,而XXY组型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间性人”,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生物学非二元性别。
除了性染色体之外,生物学性别还主要和性激素相关,性激素又分为男性激素和女性激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男性只拥有男性激素,而女性只拥有女性激素,但近年来在神经内分泌方面的研究逐渐否定了这一观点:第一,性激素本身不具有二态性,并非对应性别所独有。神经内分泌研究显示激素在男、女及非二元性别者中都存在[8],雌激素能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合成,睾酮甚至可在芳香化酶的催化下转化成雌二醇,而这些产生途径在所有性别中都存在[9]。第二,性激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水平会受年龄、环境和行为等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纵向研究表明:青春期前儿童和胎儿的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差异,因此在胎儿期和青春期前不能根据激素来区分个体生物学性别[9]。而在青春期,不论男女,其睾酮水平均会上升,只是男性增长幅度高于女性[9],但最终睾酮水平在两性的分布也是连续且存在重叠的[10]。另外,研究发现养成相关行为(如育儿行为)会降低睾酮水平[11]、社交亲密关系可升高女性的孕激素水平[12],而竞争相关行为则会增加女性的睾酮水平[13-15]。
也就是说,以性染色体和性激素为典型指标的生物学性别本身也是非二元的,尤其是性激素,甚至是会不断变化的。因此,根据生物学性别对性的其他维度(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进行二元限定、规定其对应“正常”表现形式的做法是存在逻辑问题的。
3 “性别不一致”与精神障碍的差别
除此之外,另一个对“性别不一致”的去病化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就是对“疾病”认知的改变。自20世纪末期精神病学界对“性别不一致”现象有所觉察后,先是DSM将其纳入“性及性身份识别障碍”,并定义为“性身份识别障碍(性别认同障碍)”,然后是ICD-10中将“性身份障碍”归类于“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这两种归类将性别认同的不一致划归为一种认知或者人格障碍,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与生物学性别不同的性别认同,是因为“患者”的“妄想”。
但实际上,这种“不一致”的认同和精神病性的“妄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妄想”是一种病态、歪曲的信念,其内容涉及自身、与患者经历相关且有个体独特性,但与现实不符[16];但是“性别不一致”或“性别认同与生物学性别不符”并非独一无二的个体现象,而是存在于一部分人当中的(约占总人口的0.5%)[17],且并非只有“生物学性别”是现实,“性别认同”也是一种可以操作、可实现的认知事实而非单纯的臆想。同样,“性别不一致”也与“人格障碍”截然不同:首先,人格是指全部心理特征的整合,患“人格障碍”的人会有明显偏离正常的行为方式,自身适应不良的同时还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18],但“性别认同”仅仅是性别相关的一个心理维度,代表不了整体的心理特征;并且,与其说“性别不一致”是因人格问题而导致自身适应不良,不如说是社会对性别的理解和包容还不够,给“性别不一致”个体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另外,“性别不一致”常会伴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精神问题,这也是DSM-5所谓“性别烦躁”的重点,但这种共存的内化疾患不应与“性别认同”本身混为一谈,这就好比留守儿童和失独老人常会出现焦虑、抑郁,但是“留守”和“失独”本身并不是精神障碍一般,这也是ICD-11将“性别不一致”剔除出精神疾病诊断条目的理念的先进之处。至于20世纪末最主流的观点——将“性别不一致”归为一种“认知障碍”,然而,这种观点也没能很好地把握住定义“相关障碍”的界限。“性别认同”的确是一种“认知”,但是这种认知的变异本身并不能构成“障碍”,即便是因此产生了功能损伤和适应不良,也是由于个体在与某种事物以及某种固定看法对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压力、情绪反应乃至不良应对,而非“认知”本身存在障碍。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同样表明,这种认为某些“性别认知”属于“精神障碍”范畴,并对“性别不一致”个体进行扭转治疗的诊疗不仅无效且令人痛苦[19]。希望随着学界以及大众对“性别”认识不断加深、对“疾病”概念愈加审慎、对多元认同及表达持续尊重和包容态度。
4 性别选择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然而,在性别选择和变性手术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20],“性别不一致”去精神病化也带来了一些伦理上的挑战和相关法律问题。如美国2021年2月通过的《平等法》规定了个人可以根据自身性别认同来使用包括洗手间、更衣室等公共设施。这一法案的通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论,法案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性少数免于歧视,但是也让性别暴力有了更多可乘之机,如果大众将这些暴力违法犯罪事件归罪于性少数身份的掩护甚至是性少数本身,无疑会加重对性少数的污名甚至是仇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性别不一致”去精神病化后,失去了严格专业的精神科鉴别,让性别认同有了相对较大的主观自由度,但是他人和法律应当以何为依据,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对个人的性别认同予以尊重和接受,这类课题还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探讨和探索。
5 “性别不一致”的逻辑悖论
尽管“性别不一致”的诊断在目前看来已属先进,但是这一概念的本身仍有逻辑悖论的嫌疑。因为,“性别不一致”去精神病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性别连续谱学说,其本质上是反二元分类的,也就是说绝对的“性别不一致”和“性别一致”都是极少数。但是“性别不一致”作为一个诊断条目,仅是“去精神病化”而非彻底“去病化”,这其中有出于争取医疗保健服务的考虑,但却再次人为地将人群二分为“性别不一致”和“性别认同在健康范围”两类。对此,笔者认为较为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将不必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进行定义,每个人出生都带有生物学性别,在接下来的成长和社会生活阶段,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等维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每个人都有管理自己性别的自由和权利,最终从性别的繁衍属性、性别相关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
6 结语
综上所述,性别是多维度、非二元、并非一成不变的,“性别不一致”也并不是精神疾病。然而,长期以来,“性别不一致”个体却背负着类似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所幸的是,教育界正在积极推动性教育的知识更新和普及,同样,医学界也在积极响应ICD-11所倡导的性别健康服务内容,开始逐渐重视对“性别”的多维度管理,从社会、心理和生理三个方面践行医学伦理学“有利”“尊重”的基本原则。医学的本质从来也不是区分正常与异常、区别少数与多数,更不是为学派、假说和观点服务,而是为了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