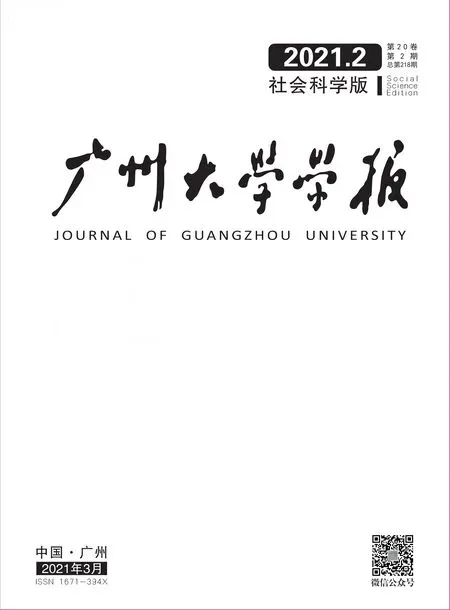审美的可规定性与人性塑造
张玉能,张 弓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东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审美教育在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不仅在党的教育方针中已经明确地写入了“审美教育”,而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提到要加强审美教育。那么,审美教育究竟如何塑造人性呢?只有揭开其中的奥妙,我们才能够按照审美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来更好地进行审美教育。
一、审美教育让人进入“可规定性”的审美自由状态
审美教育无论在中外历史、教育史和美学史上,都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中外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左右,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审美教育。但是,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教育学或者美学学科性质的范畴概念,“审美教育”却是德国伟大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在1795年出版的《论人的审美教育的书简》(以下简称“《审美教育书简》”)中正式命名的。席勒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晚期和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历史现实出发,洞察了私有制和分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及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揭露了当时社会人性分裂的状况,要求运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来使人类回归到古希腊黄金时代的人性完整。他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综合感性与理性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在私有制和分工的条件下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是造成人性分裂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找到了能够把感性与理性综合起来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像古希腊人那样人性完整的人。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不仅揭示了审美教育的游戏冲动综合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特点,而且揭开了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处于一种“可规定性”的自由状态,从而可以重新塑造人性,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和人性完整的人,也就是揭开了审美教育塑造人的秘密。
从审美教育手段的角度来看,席勒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结合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游戏冲动的对象,因此,它们就可以在人类身上把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人性的分裂,从而形成人性完整的人。在《审美教育书简》第15封信中,席勒说:“感性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最广义的生活;这个概念指一切物质存在和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既有本义又有引伸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力的一切关系。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种普通的概括来表示,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总而言之,用以表示在最广的意义上称为美的那种东西。”“美是两种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语言的用法完全证明这个名称是正确的,语言通常用‘游戏’这个词来表示一切在主体和客体方面都不是偶然的,而无论从外在方面还是从内在方面都不受强制的东西。因为心灵在直观美的东西时正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个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所以,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它也就不仅摆脱了法则的强制,而且还摆脱了需要的强制。质料冲动和形式冲动都认为它们自己的要求是严肃的,因为在认识时,前者与事物的现实性有关,后者与事物的必然性有关;因为在行动时,前者以维持生命为目标,后者以维护尊严为目标,因而二者都以真实和完善为目标。但是,一旦尊严介入了,生命就变得无关紧要,而只要爱好在吸引,义务就不再强制;同样,一旦事物的现实性即质料的真实性,同形式的真实性即必然性的法则相会合,心灵就会比较自由地、平静地接受事物的现实性即质料的真实性,而只要直接的直观能够伴随着抽象,心灵就不会再由于抽象而感到紧张。总而言之,当心灵与观念相结合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小了;当心灵与感觉相会合时,必然的东西就抛弃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轻了。”因此,他认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1]256-257,259也就是说,正因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和产物,所以,它们就能够把感性与理性综合起来,从而使人性完整。这就是席勒的改造世界的良方。这一良方是他在法国大革命的血与火的震撼之下思考出来的。席勒不希望人类经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与火的灾难,而希望经过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游戏”来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性分裂、人类异化的状况。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席勒的这种设想和救世良方当然是乌托邦式的,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改变社会制度是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但是,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而基本上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席勒的理想倒是可以有希望变成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综合感性与理性的性质和特点,那种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功利目的的,统一了感性和理性、个体和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与人类目的性的“自由的游戏”,也就是美和艺术的审美活动或审美教育活动,可以实现使人性完整的崇高目标。
席勒把这种运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使人类达到审美自由的状态叫做“可规定性”状态。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0封信中,席勒说:“心灵从感觉过渡到思维要经过一个中间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感性与理性同时活动,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起规定作用的力量相互抵消,并通过对立引起了否定。在这种中间心境中,心灵既不受自然的强制,也不受道德的强制,却以这两种方式活动,因而这种中间心境理应特别地称为自由的心境。如果我们把感性规定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把理性规定的状态称为逻辑的状态和道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实在的和主动的可规定性的状态称为审美状态。”[1]270接着在第21封信中席勒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人的心灵,与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规定的,它要么被感性的感觉所规定,就是自然的人(个体),要么被理性的思维所规定,就是理性的人(人格),二者在现实中必居其一。但是,人的心灵也可能处于一种“纯粹无规定性”状态或者“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他说:“感觉和思维只在唯一的一点上互相接触,那就是在两种状态中心灵都被限定着,人只能是某一个——不是个体,就是人格——在一切其它情况下,感觉和思维却是相互分离,走向无限;同这种情况完全一样,审美的可规定性与纯粹的无规定性也只在唯一的一点上相一致,就是两者都排除任何被规定的存在,而在其他一切点上,就像‘无’与‘一切’那样,它们则是无限地相区分的。所以,如果后者即由于缺乏形成的无规定性被设想为一种空虚的无限性,那么,那种无规定性的现实对立物,即审美规定的自由就必须被看作一种充实的无限性;这种设想与前面那些探讨所说明的东西(第十四和第十五封信)完全吻合。”[1]271“纯粹的无规定性”和“审美的可规定性”都排除了一切规定性,但是,“纯粹的无规定性”是一种“空虚的无限性”,而“审美的可规定性”却是“充实的无限性”,也就是说,“纯粹的无规定性”状态是“无”,即什么也不是;而“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却是“一切”,也就是具有了成为其他任何规定性的自由,也就是说具有“无限可能性”,也就是无限潜在的可能性。席勒说:“只要人们仅仅注意一个个别的结果,而不注意全部能力,并且只看到在人身上缺乏任何特殊规定,那么人在审美状态中就是零。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那样一些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声明,美以及美使我们的心灵所处的那种心境,对于认识和信念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和毫无结果的。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美不论对于知性还是对于意志都绝对不会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美既不实现智力上的个别目的,也不实现道德上的个别目的;美发现不了任何一种真理,美无助于我们完成任何一项义务。总而言之,美既不善于确立性格,也不善于启蒙头脑。因此,倘若一个人的个人价值或他的尊严只能依赖于他本身而存在,那么通过审美文化,他的这种价值或尊严仍然还是完全不确定的;美现在除了使人能够按照本性,从自己本身出发来创造他所愿望的东西——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人能够成为他所应该是的东西,此外,美无论什么也达不到了。”[1]271正是这种审美的自由状态,给予人的心灵“充实的无限性”,使人能够具有了人性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席勒说:“也正因为如此才达到了某种无限的东西。因为只要我们想到,在感觉时由于自然的片面强制和在思维时由于理性的排它性立法,在人那里这种自由就恰恰被剥夺了,所以,我们必须把在审美心境中归还给人的能力看作是一切馈赠中的最高礼物,即人性的馈赠。当然,人在进入任何一种被规定状态之前,就已经具有了这种天赋的人性,但是就事实而言,人随着他进入任何一种被规定状态也就丧失了这种人性;如果人能够过渡到一种相反的状态,那么,他就能每一次都通过审美生活重新得到这种人性。”[1]271-272正因为如此,席勒才“把美称为我们的第二创造者”[1]272,“因为,尽管美只是使我们可能具有人性,而把其余问题,即我们想使人性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现实,交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所以在这一点上美与我们原来的创造者——大自然依然是有相通之处的,大自然同样也只是赐给我们达到人性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的运用就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决定了”[1]271-272。这样一来,席勒就在第22封信中指出,审美心境具有两面性:“如果心灵的审美心境,从一个方面来考虑,即只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和确定的作用上,就必须被视为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倘若人们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限制,注意到在同一个心灵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就必须认为审美心境是一种最高实在性的状态。”[1]272也正因为审美状态包蕴着人性的整体,给心灵的塑造蕴涵着一切可规定性,而不是某一种规定性,因此,“审美状态对于认识和道德是最有效果的”[1]272。“正是因为心灵的心境没有把人性的个别功能单独地保护起来,所以它对每一种功能都毫无区别地有益,而且它之所以并不特别优待个别功能,的确只是因为它是一切功能的可能性的基础。一切其他的训练都会给心灵任何一种特殊的本领,但也因此给心灵设立了一种特殊的界限;唯独审美的训练把心灵引向无限制境界。我们可能进入的任何一种其他状态,都使我们返回到前一种状态,而要消除这种状态就需要下一种状态;只有审美状态是一个在自身中的整体,因为它把它的起源的一切条件和它的延续的一切条件都在自身之中结合起来了。唯有在审美状态中,我们才感到我们好像挣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才纯洁而完整地表现出来,仿佛它还没有由于外在力量的影响而受到任何损害。”[1]272-273由此可见,席勒所说的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就是一种审美的自由状态,它具有不受物质限制的自由性,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类心意功能的完整性(整体性),超脱时间和空间等现实条件的超越性,不受质料限制的形式性。正因为如此,席勒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才可能在这种审美自由状态中实现人性的复归和完整,因而,美是人类的第二创造者。
席勒所说的“审美自由状态”“审美心境”就是一种最为有利于人性的重塑和回归完整的“可规定性状态”,同样也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使人们超越现实而所处的心境状态。正是这种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所带来的“纯粹的审美作用”,使得人从自然的人可能转化为“审美的人”,再从审美的人转化为“自由的人”。在第23封信中,席勒指出:“从感觉的受动状态过渡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实现。尽管这种状态本身不论对我们的理解还是信念都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因而也不会使我们的智力的和道德的价值出任何问题,然而这种状态仍然是我们能够达到理解和信念的唯一必要条件。总而言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1]275席勒把造就审美的人的任务赋予了审美文化,也就是赋予了审美教育。他说:“文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使人就是在他纯粹的自然生命中也一定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却不能从自然状态中发展而来。如果人要想在任何一种个别的情况下都能具有使自己的判断和意志成为族类的判断的能力,人要想从任何一种有限的存在中都能找到通向无限存在的道路,从任何一种依附状态中都能向自主性和自由展翅飞翔,那么,他就必须设法使他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仅仅是个体,都不仅仅受自然法则驱遣。如果人要想能够并且完成从自然目的的狭窄圈子里把自己提高到理性目的,那么,他就必须在自然目的的范围之内早就为适应理性目的而进行训练,必须以一定的精神自由,即按照美的法则,来实现他的自然规定。”[1]277
席勒就是这样分析了审美教育、审美文化如何重塑人性的机制。尽管席勒的这些分析并非无懈可击,也不是完全正确,比如,他把感性与理性、感觉与思维、自然的人与自由的人看作是完全对立的,而把人性的改造、重塑完全寄托在人类的心灵的自由心境,而且过分强调审美的纯粹形式性,而排除美与真以及善在内在质料上的联系,就使得他的论述带有某些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因此也就使得他的论述最终成为了一种无法付诸现实的乌托邦幻想。但是,他所分析的“审美自由状态”“审美心境”的“可规定性”,确实揭示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在审美文化和审美教育中的一些心理机制和创造性规律:(1)审美可规定性的不受物质限制的自由性,使得人类能够超越功利性;(2)审美可规定性的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使得人类回归人性完整成为可能;(3)可规定性的人类心意功能的完整性(整体性),使得人类不至于片面发展;(4)可规定性的超脱时间和空间等现实条件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充分发挥;(5)可规定性的不受质料限制的形式性,使得人类的人性可能摆脱实在的质料的限制达到自由境界。但是,席勒的“审美可规定性”由于从根本上脱离了人类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活动包括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因而成为了纯粹的精神游戏,他所说的审美可规定性的自由性、无限可能性、超越性、整体性、形式性都是意识领域内的性质特点,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
二、审美“可规定性”与“虚静”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所论述的这个审美教育的“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过程以及审美“可规定性”状态,虽然是18世纪末提出来的,然而,早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的轴心时代和魏晋南北朝中华审美意识觉醒时期就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探讨和表述。实际上,席勒所说的这种审美“可规定性”状态,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中被描述为一种通过“心斋”“坐忘”“凝神观照”达到的“虚静”的审美自由状态,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中的一种审美教育和文艺创作的最佳境界。
虚静原本是道家所倡导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主要是指:人们要追寻万物的本质和生命的佳境,必须达到“无知、无欲、无为、无事、无我”的状态,回到最原始的“虚静”状态。虚静又称“静思”“滤心”“空静”。老子《道德经》最早提出这个问题:“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十六章)也就是:尽力使心灵的虚空达到极点,坚守生活的清静不变;万物一齐蓬勃生长,我才能从中观察到循环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繁茂盛,最终各自又返回到它的根本。老子告诫人们:只有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或者心境,才能把握万物及其本质。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虚静思想,非常强调“心斋”“坐忘”,要求人从生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摆脱利害得失,做到内心的澄彻空明。《庄子·天道》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意思是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的本性。不仅道家如此,管子和荀子也非常看重虚静的修身养性的作用。管子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荀子《解蔽篇》也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2]124-128也就是说,心灵只有虚心、专一、安静,才能懂得道,才能达到认识上的极其透彻、没有遮蔽的境界。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审美精神达到了觉醒的状态,老庄道家的“虚静”说传播和引入到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领域,尤其是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一时间“虚静”成为了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必备心理状态,许多论述文学艺术创作的论著都涉及到“虚静”的思想。据考证,西晋文学理论批评家陆机最早把“虚静”说引入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他在《文赋》中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要求创作文学作品前,应该久立天地之间,深入观察万物;博览三坟五典,以此陶冶性灵。也就是要求作家不受外物干扰、思虑清明、心神专一,进入“虚静”的心境,进行全面审美观照。尽管陆机没有明确使用“虚静”这个概念,但是“虚静”的意思是比较明显的。接着,南朝梁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129-130正式把“虚静”概念引入了文学理论范畴,深刻阐发了“虚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虚静”是诗人作家进入创造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最佳审美状态,他们酝酿文思,贵在内心虚空宁静,摆脱杂念欲求,疏通内心的阻碍,洗涤净化精神。从此,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虚静说就成为了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成熟的理论观点,并且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领域。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澄怀味象”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3]“澄怀”也就是要求审美主体澄清胸怀,涤除杂念;“味象”就是品味、体验客体物象、审美对象。“澄怀味象”就是要求审美主体的胸襟情怀达到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境界,才能够品味、体验到审美对象的深层意蕴、内在精神。
由此可见,虚静说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在审美的创作和欣赏活动中,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审美主体应该具有虚空宁静的胸襟情怀,排除私欲杂念,净化升华精神,超越尘凡俗界,凝神观照,这样才能够把握万事万物的本质特性,感悟到审美形象世界的真善美统一的蕴涵和精粹。实际上,虚静说在审美教育理论中也就与席勒的审美“可规定性”状态和审美自由境界是息息相通、交相辉映的美学理论观点。特别是到了儒道佛融汇合流的唐宋时代,这种“虚静”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达到,就与道家的“坐忘”“心斋”和佛家的“禅悟”等修炼方法相融合,把悟道与体美相结合,成为一种养成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君子”的手段和途径。苏轼的《送参寥师》一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2]140这里虽然说的是写诗,但是作为审美教育也应该是相通的:在审美教育中,同样需要受教育者有一种虚静的胸襟情怀,因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因此,在审美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具体引导受教育者“虚壹而静”“澄怀味象”,在虚空、专一、宁静的胸襟情怀中,在澄清胸怀、涤除杂念的自由境界中,他们才能够“凝神观照”,感受到审美形象世界的深层蕴涵和内在精神,从而在情感的感染中,不受强制地、不知不觉地接受审美对象的形象教化和楷模导引,净化心灵,升华精神,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君子,即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由此可见,“虚静”可以看作是“审美的可规定性”的一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
三、审美“可规定性”与“面向事实本身”
借鉴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现象学观点来看,这种审美“可规定性”和“虚静”的审美自由状态,也就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它悬置了一切现实的利害冲突,在审美直觉之中“面向事实本身”,从而达到“本质直观”,使得世界和人性都回到本真状态,从而能够塑造出本真的人性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也可以说,“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还原也就是“审美可规定性”的现代现象学的表述。
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的创立者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对艺术作品要采取纯粹的审美态度。这是一种非自然主义的态度,或者超越自然主义态度对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是现象学的对待世界的方式。“纯粹审美态度”,实际上就是对世界及其事物的一种非存在的、非现实性的、非客观主义的、先验的主观主义的纯粹自我我思活动,它是关系到人的认识的绝对真理性和有效性、关系到人的生活目的的意义的“认识批判”或反思。具体来说,就是对一个纯粹美学的艺术作品的直观是在严格排除任何智慧的存在性表态和任何感情、意愿的表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后一种表态是以前一种表态为前提的。或者说,艺术作品将我们置身于一种纯粹美学的、排除了任何表态的直观之中。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排除所有存在性的执态,也就是要把文学艺术及其作品的存在问题存而不论,“悬搁”起来,放在括号里面不予考虑。这个思想实质上与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性(无功利性)是一脉相承的。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过程之中,从对存在和对存在的信念的“悬搁”到还原到“纯粹意识现象”,再到“本质直观还原”,最终达到“先验还原”,“直观”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也是现象学还原以“面向实事本身”的根本途径。胡塞尔在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说:“一旦认识的斯芬克斯提出它的问题,一旦我们看到了认识可能性的深邃问题,这些认识仅仅在主观体验中得以进行并且可以说是把握了自在存在的客观性,我们对所有已有的认识以及对已有的存在——对所有的科学和所有被宣称的现实——的态度便会彻底改变。这一切都是可疑的,都是难以理解的,都是莫名其妙的!要解这个谜,就只有站在这个谜的基地上,把一切认识都看作是可疑的并且不接受任何已有的存在。这样,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现实(也包括本身自我的现实)都成了‘现象’。剩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纯粹的直观中(在纯粹直观的分析和抽象中)阐明内在于现象之中的意义;即阐明认识本身以及对象本身根据其内在本质所指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超越出纯粹现象一步,就是说,不把任何在现象中被误认为是超越的存在设定为是被给予的并且不去利用这些超越的存在。‘认识’的所有类型、形式都要受到这样的探讨。如果所有的认识都可疑,那么‘认识’这个现象便是惟一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我承认某物有效之前,我只是直观并纯粹直观地(也可说是纯粹美学地)研究:有效性究竟是指什么,就是说,认识本身以及随同它在它之中‘被认识的对象’所指的是什么。当然为了‘直观地’研究认识,我不能仅仅依据那种动词的拟—认识(符号性思维),而是依据真正‘明证的’‘明察的’认识,尽管对那种符号性的认识也需要在与明证性认识的关系中受到现象学的分析。”[4]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纯粹审美直观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可以达到绝对真理性和有效性。胡塞尔的这种现象学还原的过程,特别是“本质直观”,在哲学上无疑是唯我论和先验论的唯心主义,但是,这种过程倒是非常类似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过程和观赏者的欣赏过程。作家艺术家和观赏者在创造和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时,确实是并不把文学艺术及其作品当作一个现实的实在,而是在纯粹意识现象世界之中来建构文学艺术及其作品的意向性世界,并且通过对这个形象性的意向性世界的直观来显现人生世界的本质(真谛),回到人生世界本身,也要回溯到那个构成这个形象性的意向性世界的先验主体性——作家艺术家或观赏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意识行为的可能性。[5]
我们看到,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的“纯粹审美态度”的“悬搁”“本质直观”“面向事实本身”实际上也就与席勒所谓的审美“可规定性”状态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虚静”状态具有审美意义上的相通之处。那就是,首先把对象从现实的存在中“悬搁”起来,让它成为非自然的、非现实的、非实用功利性的“意向性”现象,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对待它;然后,以直观和审美直观的方式,建构起直观形象世界(审美直观形象世界),从而从根本上、本真的意义上揭示对象的意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从而最终达到“面向事实本身”(面向实事本身),也就是把握了对象的本原性的真理,得到了关于对象世界的本真的真理认识,而不是像传统的符合论的真理观所要求的那样,让人的认识与对象的存在相符合。那么,从审美教育的角度来看,在这种“纯粹审美态度”“本质直观”的现象学还原的过程中,人类主体的“先验主体性”就得到了实现,也就是相当于席勒所说的,经过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审美教育,当今异化的人类的人性分裂状态得到了克服,回归到了古希腊黄金时代的人性完整的状态。我们如果剔除了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从美学和审美教育的角度来借鉴现象学哲学和美学,事实上“现象学还原”的过程倒是一种审美过程和审美教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的揭示。
如果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看,那么,主要就是这样的三个步骤:首先,引导受教育者以审美态度对待审美对象和艺术对象,也就是超功利、超时空地对待审美对象和艺术对象;其次,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审美形象和艺术形象的世界,做到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上”,与审美形象世界和艺术形象世界“物我相忘”;再次,在审美形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之中非强制地受到教育,以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塑造受教育者的人性、人格,塑造全面发展的人。
席勒好像在《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论作为一种道德机构的剧院》中,以戏剧为例阐述了这种具体的审美教育的操作过程。他指出:“剧院促使娱乐与功课、平静与紧张、乐趣与教育结合起来,不让一种心灵力量损害另一种心灵力量,不让娱乐占用全部精力。如果悲哀在折磨心灵,如果忧郁的心境毒化了我们平静的时日,如果世界和职业令我们厌恶,如果千万种负担压迫着我们的心灵,而我们的敏感性在职业工作中面临窒息的危险,那么剧院就接纳我们——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我们离开现实的东西去梦想,我们复归于自己本身,我们感觉在苏醒。有益健康的激情刺激着我们昏睡的自然本性,使之热血沸腾起来。在这里,不幸的人借别人的忧伤来宣泄他自己胸中块垒——幸福的人会变得冷静,平和的人也会变得审慎。在这里,多愁善感的柔弱者锻炼成大丈夫,不开化的野蛮人在这里开始第一次生出属人的精神感受。而且,如果人们从一切范围、区域和状态中摆脱了矫饰和时髦的任何羁绊,摆脱了命运的任何逼迫,通过一种包罗万象的同情结为兄弟,把他们自己重新融合在一个族类之中,并且忘掉世界而接近他们美好的发源地,在这种情况下,被踩到地上的自然本性就随时又重新复活——这对于你,自然本性,是多么值得欢庆的一个胜利啊!每一个人都享受着众人的愉悦,这种愉悦从千百双眼睛中反映到他心中并得到强化和美化,于是他的心中就只可能有一种感受:必须成为一个人。”[1]15-16在这篇文章中,席勒还有一段以反面的例子来论述,似乎说得更加具体。他说:“在人间的法律领域终止的地方,剧院的裁判权就开始了。当正义为了金钱而迷惑而尽情享受罪恶的俸禄时,当强权的罪行嘲笑它的无能,而人们的畏惧捆住了官府的手脚时,剧院就接过宝剑和天平,并在一个极大的法官席前撕碎罪恶。整个想象领域和历史,过去和未来都供它用来表现。在尘世中早就腐烂很久的大胆罪犯们现在被诗歌艺术威力无比的呼声传唤出庭,并且重新把一种可耻的生活变成令后代人惊恐不已的教程。他们时代的惊恐立即不知不觉地把一面凹面镜中的影像在我们眼前演示一番,而我们就满怀惊愕诅咒他们的回忆。如果道德不再得到教导,宗教不再得到信仰,如果法律不再存在,那么,当(欧里庇德斯戏剧中的)美狄亚踉踉跄跄地走下宫殿的阶梯,而且当即杀了孩子时,她就会使我们惊恐;当马克白斯夫人,一个惊恐的梦游者在洗她的手,用尽一切阿拉伯的香料帮助消除恶腐的谋杀血腥气时,有益健康的惊恐将打动人类,并且会在平静时褒奖他的任何善心。当弗兰茨·封·莫尔从永恒的梦中惊起,被临近法庭的惊恐所包围,从微睡中跳起来的时侯,当他被雷鸣震木了觉醒的良心,从天地万物中否定上帝,并在做完最后祷告后,以无耻的咒骂发泄他压抑的情怀时,我们之中有谁能冷静地旁观,谁不充满对美德的热烈渴望和对罪恶的强烈仇恨呢?如果有人断言,在剧院中表现的这些生动图景最终与普通人的道德融为一体,并且在各种单独情况下决定着他的感情,那并不是夸张。过去和现在我都不止一次地目睹,有人把他对恶劣行径的憎恨凝聚在一句谴责的话中:‘这个人是一个弗兰茨·莫尔。’这些印象是不可磨灭的,而在轻微触动时,在人的心灵中完全淡忘的艺术图景就像突然从坟墓中出现一样。所以,具体的表演肯定比僵死的文字和冷淡的讲述更有力地起作用,剧院肯定比道德和法律更深刻和更持久地起作用。”[1]10-11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体悟到审美教育的超越性、直觉性、主体性,正是这些所组成的审美“可规定性”自由状态,使得审美教育能够发挥出重塑人性和回归人性的伟大作用。
总而言之,通过席勒的审美“可规定性”、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虚静”、胡塞尔现象学的“审美直观”的“面向事实本身”的内涵的发掘,我们就可以窥见审美教育塑造人的奥秘了。那就是要在审美教育中,让受教育者具有一种超越物质功利的态度,进入一种审美自由状态,形成重新塑造人性的可能性,再以美和艺术的理想形象来重新塑造人的人性和人格,从而达到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明白了这个基本原理,我们在实施审美教育时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方向明确、措施得当,也才能够达到审美教育塑造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根本目的。
[本文写作受到华东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17HZK03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