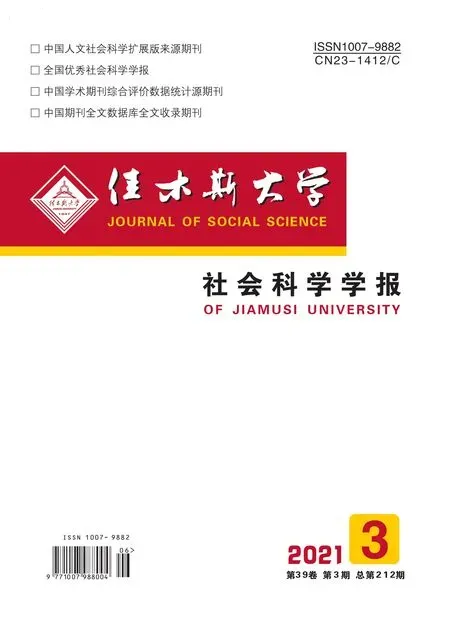记忆诗学视域下《祝福》再阐释*
李枭银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
从记忆诗学角度对《祝福》的考察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基于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主人公祥林嫂的精神记忆展开分析。其次,是基于祥林嫂的记忆现象的分析基础上,对《祝福》文本所建构起的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文化意义进行考察。这一分析策略是基于对《祝福》文本本体的尊重:它首先是文学文本,其次才是作为具有社会性的文学文本,换言之,这里所预设的大前提是:《祝福》文本的社会影响生成是建基于它高超的文学成就。此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对《祝福》的阐释增添新视角和具有说服力的话语,进而使这一经典性文本的当代影响能够可持续进行。
一、祥林嫂人格结构分析
从记忆诗学的角度进行《祝福》文本展开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首选方法,因为《祝福》是关于祥林嫂悲剧的故事,因而考察祥林嫂悲剧的生成不能不对祥林嫂本人进行分析,特别是关乎其心理的精神分析。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祥林嫂内心深处一个病态的循环怪圈。
“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1]77-78——“本我”意义上的祥林嫂。弗洛伊德认为“本我”(ID,有直译为“伊德”)是人格结构的第一层,他这样论到:“伊德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什么是道德。与快乐原 则如此紧密相连的效益因素,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叫数量因素,支配着伊德所有的活动。本能发泄总是在寻找出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伊德的全部内容。”[2]129从中可以发现,“本我”的本质属性有三:其一,是无外在的价值判断,即“本我”的运行是在潜意识的催动下自发产生的;其二,是追求“快乐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理解为“本我”是趋利避害的;其三,“本我”是需要发泄的,它不安于隐秘的状态,总是试图进入“自我”状态或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那么,祥林嫂的“本我”是怎样的呢?从单纯的文本内容中,我们很难从“性”或“力比多”的角度发掘祥林嫂的“本我”,但是从祥林嫂一些“出格”或者“冲动”行为中,可以归纳出隐含于文本中的关于祥林嫂“本我”的部分特征。文中最明显的一处就是当祥林嫂的婆婆准备将她嫁到贺家墺时,祥林嫂的表现是“一路只是嚎,骂”,她是被“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轿”,最后是“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出祥林嫂对于再婚的抗拒,这不是基于现实原则下的行动,却恰恰是在“快乐原则”驱动下的冲动,尽管她的行为造成了她身体的伤害,但从心理的角度上说这是祥林嫂趋利避害的选择。文中还有一处“非白”值得注意,即第一次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当女工是背着婆婆逃出来的。叙述者没有交代她为什么逃出来,只是说她有一个“严厉的婆婆”。综合上述两件事,不难发现反抗是祥林嫂最重要的“本我”逻辑:她反抗婆家因而选择逃离,她反抗婚姻因而大哭大闹,所有的反抗所追求的仅仅祥林嫂想象意义上的快乐,尽管她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并且给自己增添了更大的创伤。
“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自我”意义上的祥林嫂。“自我”(Ego)是人格结构的中间部分,“通过知觉意识的中介而为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本我的一部分”[3]173。与“本我”的无意识催动不同,“自我”是意识活动的产物,它的形成与社会教育、制度、法则等多重规定密切相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在此基础上,人格结构的第一个矛盾便出现了:社会性的外力在相关程度上必然与“本我”的天性发生抵牾,此时也就出现了意识的“压抑”,那些与“力比多”有关的或羞耻或乱伦或与社会法则不符的意识便内化为潜意识。由此观照文本,可以发现祥林嫂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压抑状态,一个表征便是祥林嫂是趋于沉默的,当她第一次来鲁四老爷家,便表现出“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后文直接描述到,“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然而,此时祥林嫂的“本我”是处于“自我”的有效管理下的,二者的关系还是平衡的,这表现在祥林嫂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能干,在忙碌的劳动中她却感到一丝满足,不仅仅是在鲁四老爷家,之后嫁到贺家墺后,文本中还是用一个“胖”描述她,“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不难推断出,祥林嫂“自我”遵循的现实原极为简单,她所需要的仅仅是劳动的空间与劳动的条件,在劳动中她便处于一种满足、健康状态。
“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超我”意义上的祥林嫂。“超我”(Super—ego)是人格结构的最高一层,是具有理想意义的“我”的存在形态,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然而,尽管“超我”是“自我”意义上的升华,但是这样一种典范形态却是基于社会文化认同,换而言之“超我”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是一定文化语境的产物。“超我”一方面勉励着“自我”,一方面又严格约束着“自我”。在祥林嫂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她的“超我”呈现怎样的形态呢?在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鲁四老爷曾这样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里的“不干不净”极具深意,通过它可以去理解祥林嫂的“超我”:作一个“干净”的人。这样一个“超我”的形成,将其归纳为封建文化中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规约,是耳濡目染的贞操观念使然,是符合逻辑的阐释。因此,当婆婆将她再嫁时,她竭力反抗。当听到柳妈关于“阴司”“阎罗大王”的描绘时,她便急着去捐门槛。“干净”就是祥林嫂理想的祈求,但是在婆婆的逼迫、鲁四老爷的“祖宗文化”中,她的“超我”的规定性打破。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结合上文论述,祥林嫂“本我”意识中的反抗、求生原则,竟是趋向“超我”的方向,由此形成了病态的人格怪圈:追求的目标迫使她反抗,而她所反抗的方向却是追求的目标。她的反抗不是向着生命本真的自由方向,而是趋向于迫害的方向。道德化的“超我”与本能化的“自我”趋同,这是祥林嫂真正麻木的体现,她的行为看似自主,实则是背后文化大手的推动,她无能为力,在有限的行动中,不断加重自己的病态。
二、祥林嫂的创伤经历与记忆扭曲
人格结构的病态对祥林嫂而言是隐性的,若是没有突发事件,这病态或许将永远潜伏在祥林嫂的无意识中。然而,祥林嫂之所以是“祥林嫂”,并不仅仅是人格结构中的病态,她的不幸在于她的遭遇,李长之说《祝福》“主要的故事,只有两点,一是再嫁,一是丧子”[4]88。他的归纳颇为精准,围绕“再嫁”和“丧子”,系列创伤袭向祥林嫂,它直接导致了祥林嫂记忆扭曲。正如创伤研究学者凯如斯指出:“在突然的,或灾难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5]11。因此,对祥林嫂的精神分析另一个重要切口,是对她的创伤经历展开解读,由此分析其精神记忆扭曲的诸种不同形态,进而归纳出它们所生成的文本效果。
就祥林嫂的创伤经历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物质性创伤和精神性创伤。她的物质性创伤集中体现在“再嫁”情节中。因祥林嫂对再嫁的反抗,“她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最明显的物质性创伤,尽管文中没有交代后文中祥林嫂的“傻”、“疯”与这次伤害的直接联系,但是,这必然对祥林嫂日后精神的失常产生潜在的影响。然而,这样一次物质性创伤对于祥林嫂而言只是一次“意外”吗?如果她在再嫁的过程中没有极力反抗,或许可以避免?这样的假设是不符合人物真实性的:祥林嫂“超我”结构就是当时特定文化熏陶下的道德化“自我”,强烈的女子贞操意识驱动她必须全力反抗。尽管物质性创伤对于祥林嫂的伤害是严重的,但是伴随着身体的康复,它并没有显性、直接地对祥林嫂的生活造成影响,文本中卫老婆子的言语可以佐证:“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出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哎哎,她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可以说,祥林嫂最大的创伤是精神性的,在文本中至少可以发现四处:1.被婆家抓走时的恐惧;2.不准祥林嫂参与祭祀;3.鲁镇民众对祥林嫂的冷漠;4.“我”回答祥林嫂有鬼魂、地狱的存在。
这里只是从论证角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出文本中祥林嫂所经历的创伤,严格地说,祥林嫂的记忆扭曲与创伤经历形成不是线性发生的,毋宁说这是一个“创伤的循环”:经受创伤,导致记忆失常;记忆失常,回应着新的创伤,在系列的循环中一步步逼向精神的极限。祥林嫂记忆扭曲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反复回忆与日常健忘,并且二者具有深刻的文本意义,记忆扭曲不是简单的“迹象”或“情报”,而是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反复回忆,“我真傻,真的”成为祥林嫂的口头禅,并且逢人就诉说她丧子的经历,这样一种独白,“侵犯了别人的生活秩序……是一种跟一般人的生活秩序的断裂,威胁别人的约定俗成的秩序”[6]30-36,由此祥林嫂被排除在鲁镇群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鲁镇民众这样一种取乐或拒绝的态度,使得祥林嫂移情的宣泄方式失败,“……自己再也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瞥他们一眼,并不回答一句话”,她彻底陷入压抑之中。另一方面,因为日常健忘,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的帮工越来越差,“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正因为如此,祥林嫂终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成为鲁镇上无家可归的乞丐,渐渐走向死亡。
三、祥林嫂的死因及其文化意义
学者殷鼎曾采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方法研究《祝福》,认为该文本“作为一个以不完全的形式进行的句子的文本,其结构如下:她的死(主语)乃由……造成。”[7]26-33因此,文本中每一次关于祥林嫂的创伤事件,都可以作为谓语之一,补充着谓语部分,使得这一句型完整化。但是,作者鲁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个谓语不是单一的,毋宁说谓语是以复数形式呈现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回答。
首先,是“祥林嫂自己”杀死祥林嫂的。我们可以假设,若她是一个乐天派,是一个无所知的人,一切得过且过,不去考虑“阴间”的遭际,祥林嫂是不会死去的。她的死,在于精神的“未完全麻木”,但这“未完全麻木”却是浸透在精神的“绝对麻木”之中,这便是“本我”与“超我”之间深刻的矛盾。弗洛伊德论到,“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8]86。上文分析到,祥林嫂的“自我”只是希望能够安稳地劳动,道德化的“超我”驱动她能够参加如祭祀这样“重要”的庆典,然而在“自我”求生的原则、快乐原则下,所要反抗的就是“超我”的道德预设。然而,事实却是外界的创伤使得祥林嫂的“自我”已经伤痕累累,她是一个寡妇、没了儿子、“不干净”的人,她是一个自我呓语的“疯子”。这种情况下显示出扭曲的“自我”,导致祥林嫂自己人格的严重分裂,“超我”与“本我”的背到而驰。终于,在经历着系列的创伤,在“内伤”与“外伤”的双重打击下,祥林嫂的精神与身体走向忍耐的极限而死亡。从这个角度而言,祥林嫂首先是被自己杀死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发问:促使“本我”与“超我”扭曲的推动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没有可以让祥林嫂宣泄的途径?
其次,杀死祥林嫂的是鲁镇上所有人的合谋。这样的“合谋”,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从客观效果上而言的确是如此。老监生鲁四老爷一开始就嫌弃作为寡妇的祥林嫂,并且定下“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的规矩;作为鲁四老爷命令忠实的执行者,四婶在祥林嫂捐门槛前后都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不论是前一次“祥林嫂,你放着罢!”还是“你放着罢,祥林嫂!”,内容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情绪更加激动。至于鲁镇其他民众呢?他们先是对祥林嫂进行“情感消费”,当对祥林嫂的倾诉感到厌倦后,便是挖苦、嘲讽。鲁镇的民众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看客”,他们“看”中透露出的取乐、嫌弃、冷漠,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边缘。
最后,还有一位直接的“杀手”,那就是“我”了。钱理群通过分析认为,“我”对于“鲁镇社会”而言是“格格不入”的,“《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9]10-12。然而,正是作为鲁镇社会“异己者”的我,在祥林嫂命悬一线之际,给予她一个大大的推力,使其精神一溃千里。这个推力就是我在吞吞吐吐中对祥林嫂的回答,以猜测的语气告诉她“人死之后是有魂灵的”“地狱也是有的”。我的一番对话,使得祥林嫂对于死的看法也极为矛盾:在饥寒交迫中无法生存,但是出于对阴间的恐惧,她却又不敢死,于是乎——她必须死,她又不敢死,祥林嫂一定是在惶恐、孤单中闭上眼睛。这是鲁迅最为深刻的地方,他的批判不是外在性的,他将“我”也纳入了批判的视野,他在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可以说,《祝福》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凶手,鲁四老爷、四婶、卫老婆子、至于鲁镇上的所有人、“我”、祥林嫂的婆婆、丈夫。“在这篇文字中,愤恨是掩藏了,伤感也是隐忍着,可是抒情的气息,却弥散于每一个似乎不带情感的字面上”[4]90。鲁迅的批判是深刻的,从“我”至全方位的鲁镇社会,从人间到地狱。然而,正如李长之所论,这种批判是具有抒情性的,《祝福》之所以是文学文本,是基于鲁迅强烈的同情感。如果说,《祝福》书写的是关于祥林嫂的创伤,那么,鲁迅文字中的克制与隐忍,甚至一种虚无感、无力感的建构,凸显出创伤叙事的深度与广度,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苦难的宣泄、一种“苦难情怀”的贩卖,而是一种关于政治、文化乃至“人”生存问题的叩问与反思。例如,有学者认为《祝福》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它体现出“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编织成的严密的网”[10]71;也有学者认为,“鲁迅其实是以祥林嫂的遭遇为结构中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以儒释道三教构成的‘鲁镇社会’将她逐渐吞噬的清晰过程和思想图景,并通过祥林嫂的‘被吃’,宣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11]18-24。
四、作为集体记忆的祥林嫂
《祝福》一文写于1924年2月7日,同年3月25日刊登于《东方杂志》。伴随着1926年9月30日《世界日报副刊》中《痛读<彷徨>》中首次涉及关于《祝福》的评论,围绕《祝福》或祥林嫂的“接受/阐释”系统渐渐形成。在这其中,对《祝福》接受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个事件:其一,是1950年《祝福》首次编入语文教材,此后一直保留;其二,是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由夏衍改编的电影《祝福》正式上映,《祝福》的图像化传播时代开启。诚然,《祝福》的接受与阐释因具体社会语境的变迁而显示出差异性,其中渗透着诸多话语权力的博弈,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文学现实是:《祝福》的经典性已得到社会认同,“祥林嫂”已经成为所指丰富的意义符号,从这个角度而言,祥林嫂形塑着独特的“中国记忆”,这样一种记忆是具有集体性质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对于特定社会的认同感、凝聚力建构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12]94。基于此,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的是,在当代语境中,祥林嫂作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或者这个问题,还关系到《祝福》文本经典性的持续问题。笔者以为,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第一,是文化反思的督促。反思是一个有别于记忆与回忆的思维过程,如果说记忆是对过去的客观化再现,要求是精准的还原,那么记忆是不具有感情色彩的,它具有一定的工具性质;回忆则是主观性地思维过去的切身经历过的人或事,因而回忆对于现实而言有可能是失真的,它是“主观真实”、“主观满足”。对于反思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折返性思考”,返回 “过去”,这里的“过去”,不仅仅是“记忆”与“回忆”中的某一类型,宁毋说是二者兼有之,返回事件本身,返回阐释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下语境进行“思”。《祝福》的悲剧性是公认的,鲁迅在进行关于祥林嫂的创伤叙事时,其实无意中为民族的文化增添了一道创伤。这道关于文化的创伤是明显的,它让接受者看到了在曾经的一个文化悲剧的时代:对妇女的压迫,对小人物的摧残,其中的人物都在无意识地“杀人”,并且一个个都是基于对文化正统认同的合法性想象。因而,反思应当是对待《祝福》文本一个永恒的姿态:是什么造就了祥林嫂的悲剧?祥林嫂式的悲剧及其变形在当代社会还会发生吗?唯有如此,在反思性立场下民族文化才有可能保证活力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是底层关怀的表征。这是基于鲁迅的写作立场而言的,他笔下的小人物:阿Q、祥林嫂、闰土等总是具有鲜明的典型性,而这与作家本人强烈的关怀意识密切相关。正如上文分析到,《祝福》之中鲁迅饱含着同情、也饱含着愤与怨,但是他却隐忍着,没有强烈表现在文本中,显示出一种言外之味。有学者认为,《祝福》文本中的“我”隐约象征着1924年初鲁迅自我生命危急与反省,他“承载的正是鲁迅审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审视自我生存危机的苛毒眼光”[13]185-198,这在《祝福》文本中体现在“我”的思想中:一方面,“我”急迫地想要离开鲁镇;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无聊,想象着鱼翅、想象着醉饮。那么,结合鲁迅当时的生命状态:一个人在苦闷与彷徨之中写下的文字,一定是最真实的,它是一种无力的发泄,是灵魂深处的流露。因此,此时的鲁迅以“祥林嫂”为中心,通过一个女人的创伤与生死,进行全方位的鲁镇批判,凸显心系底层人物的深刻情感。“《祝福》这样的作品,是他精神的注脚。那立场,就完全是民间的。……这种从弱小者的爱欲里思考问题的姿态,是本然的反应,可是没有几个读书人意识到了这些。”[14]8这应当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又一个启示,在城市化、“加速”社会的语境下,是否有一些被遗忘的小人物?他们或在农村,或在城市的最底层。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的确还活着,《祝福》折射出的底层关怀,是每个时代文学精神不可或缺的维度。
——以《祝福》中三处细节描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