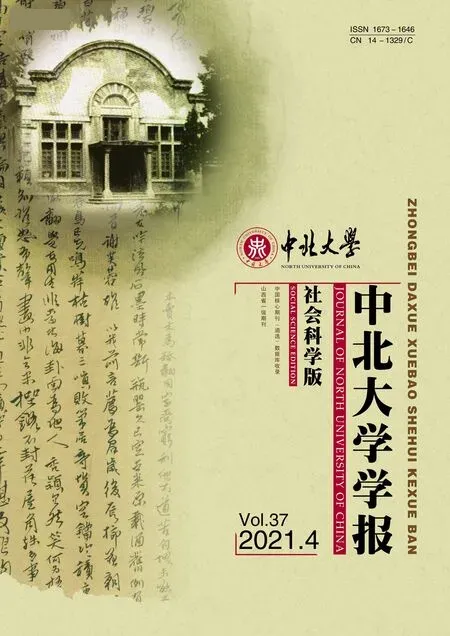电影《大赢家》的后现代狂欢
乔 慧
(山东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福柯、 利奥塔、 鲍德里亚等人对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 资本主义整体“新社会运动”的到来进行深刻反思,要求以开放的态度对待随全新的社会秩序而来的历史断裂和话语失序。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席卷哲学、 文学、 艺术的潮流中,以消解崇高、 打破传统权威和价值规范为特征的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或者批判方式,成为日常生活体验的一种标准和处理社会与文化变迁问题的一种视野。
巴赫金,以其对杂合性、 颠覆、 延展、 去中心的自我等概念的先见性描述,被伊格尔顿称为“后现代西方的学术明星”[1],与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赫金以其狂欢理论为主要贡献,在解构主义语境下, 狂欢作为“社会的倒置”[2]342,是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颠覆,是社会下层大众文化对上层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等级制度的否定消解。后现代性在上世纪末的发展与巴赫金狂欢理论一脉相承。
疫情期间继《囧妈》 《肥龙过江》之后第3部选择网络播出的院线电影,是于淼导演的《大赢家》。该片上映后口碑参差不齐,质疑与差评大部分源自与韩国电影《率性而活》的比较,认为于淼作品在喜剧性上画蛇添足而在逻辑严密性上舍本逐末。但从对文化意蕴的解析趋向来说,《大赢家》在对其所购买版权的都井邦彦小说《游戏世界不会结束》的影视化改编上,所选取的闹剧式荒诞化喜剧路线与《率性而活》将个人悲剧与社会批判隐于黑色幽默风格的区分,事实上体现出了在本土化表达需要上对本国社会生活以及当下社会文化的考察与反映,影片将故事放置于我国典型的、 以人事关系为脉络的社会框架中,以中国逻辑重新建构故事逻辑与人物关系,调整故事节奏与走向,呈现出合理改编的商业意识与文化意识,具有不同于韩国版本的在地性的后现代特质与狂欢化色彩。在《十二公民》 《误杀》 《“大”人物》等翻拍片纷纷涌现的当下,探讨《大赢家》在地化改编的后现代狂欢,可以为外国小说、 外国电影的本土化翻拍找到适合中国文化传统、 塑造中国现代人物、 讲述中国故事、 传扬中国道德精神和社会价值的有益借鉴。
1 戏仿、 解构与“认知图绘”
后现代不是虚无缥缈的时代与思潮,其根本是产生于现代并作为现代的后延; 电影艺术也不是完全虚幻的艺术,而是植根与生长于当前的社会环境。于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结合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认知图绘”[3]52的概念,认为后现代电影也是对社会环境风貌的反映。《大赢家》在原作基础上做出不小的改动,内里包含着多层面多维度的后现代戏仿与解构,在更改了的节奏与结局里,我们都能找到“跟本地的、 本国的以及在国际上的阶级现实之间的社会关系”[4]123。
1.1 戏仿:作为后现代语法的双重编码
琳达·哈钦在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基础上,打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壁垒,形成与詹姆逊的敌视截然不同的对“戏仿”的重视观念。哈钦论戏仿:“它使得源文本与新文本之间有了差异性,而差异性中又蕴含了讽刺意味。”[5]25并由此给出她对于“戏仿”的定义:“戏仿是指带有差异的重复。一个通常以反讽为信号的批评性距离隐含在被戏仿的背景文本和新合成的作品中。”[5]32。戏仿在电影中意味着对现代主义以及现实社会或者其他文本中的已有因素的创造性重组和重构性利用,当既成的范式与戏谑后的新品同时出现在后现代艺术作品中,必然发出巴赫金所说的“若即若离的不同指向的双声语”[2]110。《大赢家》的戏仿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在现实意义上,其故事主体中的演习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戏仿; 而对前作《率性而活》经典成分的吸纳,包括皮卡丘头套与其他电影碎片的荒诞化引入,则形成电影对其他艺术文本的互文性戏仿。
1.1.1 敷衍的演习本身作为一种戏仿
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戏仿令人耳熟能详的是以周星驰为代表的香港无厘头电影,后来,在国内喜剧电影中也频频出现,逐渐成为后现代作者惯用表达方式和审美接受习惯,甚至成了电影作品彰显其后现代性的标配风格。但是,以往的电影或者以先前的影视或文学作品为戏仿蓝本,或者对网络视频笑话段子进行移植借鉴,无一例外是艺术作品之间的戏仿。在《大赢家》的文本故事中,想要被新闻报道推上“热搜”的行长所主导的一场敷衍的演习,本身就是对银行对抗抢劫犯和警察抓捕抢劫犯这种严肃的社会事件的戏仿。行长在路上眉开眼笑联系的专访、 民警老姚说的“演习嘛,能有多大事儿啊”和副队长“这个点儿出警,半个小时解决战斗”的笑言,自演习一开始就奠定了这场演习的基调。演习是对预想事件的仿,闹剧一般的敷衍演习自然就成为对预想事件的“戏仿”。在商业社会以成效定输赢的时代,连形式主义都无力做到完满,而对这种日常现实的反思批判并不能成为影视作品的爆点,现实生活中的繁琐问题因其无法独立于社会大背景中,在作为娱乐消费产品的电影中真实再现难免带有将日常生活沉重化的意指,而当“敷衍的演习”作为对日常所见的现实的开拓性“戏仿”后,又用凭空插入的见义勇为老大爷将真实与演习、 认真与游戏的分野置换,内蕴的故事形成一种拜厄特所说的“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6]11。
1.1.2 戏仿被戏仿了的皮卡丘及其他碎片
《大侦探皮卡丘》曾以成年男性的粗犷嗓音戏仿并消解了《精灵宝可梦》二维动画时代的萌宠形象,《大赢家》再次以劫匪头套的造型对前者中皮卡丘的侦探身份做了戏仿,细瘦狰狞又“烈焰红唇”,戏仿原型后又完全更改了其表象。波林·罗斯诺认为后现代对表象的批判的一个共同点是“表象蕴含着将某事、 某人、 某地点或某时间再现为另一物、 另一人、 另一地点或另一时间”[7]138,因而,在认识论、 方法论和实质性上都是欺诈性的,戏仿使人开始重新思考文化起源,并对过去形成的墨守成规的对表象的认识发起挑战,戏仿的再创造,使戏仿对象在原有样态之外延伸出更宽广的文化视野,运用反讽、 滑稽、 嘲讽等看似不正统的表达方式去实现更多的文化艺术意蕴,这种功能是现代主义的封闭自指无法实现的。哈钦延续赛义德的理论观念,认为后现代主义戏仿能够让艺术家们通过重新编码埋葬过去也能够开启新生。《大赢家》线上放映以来,以前占据皮卡丘淘宝搜索前列的暖萌少女帽子和抱枕排名跌落,“大鹏同款恶搞劫匪头套”占据前几页,作为一种戏仿文化的衍生品的意义已经成立。当然,戏仿除了反讽之外也含有严肃致敬的倾向,也能让受众感受到契合戏仿互文性的多元化之维:抢劫开始时主人公严谨一人、 一箱、 一头套,场景与镜头调度都是《黑暗骑士》丑爷的复刻; 众人质挤作一团登上大巴车,是同题材电影《热天午后》的套路; 之外,诸如《火车大劫案》与《荒野大镖客2:救赎》等熟悉的灯光站位与布景,甚至Route 66头盔的梦想象征,都是符合哈钦列举戏仿的第四层意义的接近之意的。
1.2 解构:作为对本质主义的一场反叛
尼采、 海德格尔、 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福柯、 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罗蒂等人的新实用主义等多源共汇,形成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潮流。后现代“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 没有根据的、 多样的、 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 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8]前言7。“解构” 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原意为分解、 拆解、 消解、 揭示等,后现代主义之父哈桑在他给“不确定性”所下的定义中揭示了不确定性和解构性的重合性。《大赢家》对本质主义的反叛解构也是多层次的,既以对原作的颠覆实现了“作者之死”,又以对自身的反转实现了叙事意义的不确定性。被解构的符号与被解构的生死以喜剧形式贯穿其中,实现了后现代批判维度。
1.2.1 被解构的影片与“作者之死”
这里提到的作者有两个层面,其一是都井邦彦作为故事原文本的作者,其二是《大赢家》电影本身自开始到结束之前七分钟所树立起来的底层观念与批判意识。影片首先改写了都井邦彦所设置的警察内部演习的人际范围,增补了“朝阳群众”一般的举报现场,从而制造了一场貌似出师未捷的假性破灭,添加了带有后现代女性主义意识的云珠对男性的调戏与“凝视”段落,从而形成与原作完全不同的不以批判执法者失效为目的、 合国情的喜剧走向; 然后,在开头设定的被行长赶出、 在第1小时18分录制视频时候所说的“被家人冷落、 被领导误会、 被同事排挤”等“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边缘人物悲情基调,也在第1小时30分影片将要结束时全面反转为家人送蛋糕、 领导给奖状、 同事送祝福等“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普通人的小确幸。人设之转换带来主题之转换,批判意识再次轰然倒塌。两个层面的解构体现了罗斯诺所研究的“抛弃作者,转换文本和重置读者”的过程。[7]48原著“作者之死”的同时,《大赢家》主创人员作为读者的身份转换为第二次“作者”。然后,在作品行将完成时又亲手颠覆了自己的作者权威形成二次“作者之死”,以此“后现代主义者戏剧性地变更了作者、 文本和读者的传统角色。”[7]34
1.2.2 被解构的生与死
当“合理合法抢银行”在反向叙事中获得道德提前合法化的处理,生与死的意义就在这种反向里随之颠倒成就了生之煎熬与死之快感。胖子为求先“死”在戏谑无厘头的荒诞场景中认认真真轰然一跪,将对“死”的追求猛然推上超脱出“戏仿”与“游戏”之外的意义,又与“领导先死”形成含有双重世俗意味的复调。而在“咱们也配合一下吧”之前,“生”则在敷衍的闹剧里限定于封闭孤立的人质框架之内,演习的戏仿将本该在死之威胁前孱弱的生命解构为毫无重量的在无限拖延中找不到意义的所指,以“歹徒现在就要杀人质了”的死亡狂喜和慢动作倒地的死亡仪式作为新意义的开启。鲍德里亚认为当前社会中处理死亡的方式可以被视为处理其他许多失误的典型方式,恰如此意。
1.2.3 被解构的能指过剩的符号
鲍德里亚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概念[9]26,认为在现代消费社会“所指的价值”已经消失,符号形式所指向的“真实”内容已经荡然无存,所以,符号不会与真实互动。影片中出现了数次银行门口的狮子雕像的头,或是孤零零兀自矗立或是被严家小妹当做吸烟时候倚靠的背景,但全影片观看下来,我们并不能找到这个复沓出现的意象所蕴含的确定能指。而对于枪支来说,不同于《率性而活》警察扮作劫匪的预设,使水枪与纸枪的出现顺理成章且充满闹剧色彩,儿戏的且换着样貌的枪与想象出的动作血腥场景——“都打烂了,特别的血腥”叠加出后现代仿真序列的意味,在特定语境下的仿制品“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10]10,名称与图像与其所指意义在断裂后被重组,不再指向其使用价值而是指向人们的欲望,狮子头与枪可以被操控的符号的表意链条分崩离析,膨胀出增殖的无意义的形式外观。
1.3 “认知图绘”:读图景观与视频欺骗
詹姆逊认为,在陌生的生存当下人们迫切需要由他者而及个人找到关于自身生存的图像,在此意义上,《大赢家》以“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使电影故事具备普罗大众生活缩影的功能,投射了当下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图像,喻指出我们以何种态度在社会系统中工作与生存。此外,“认知绘图”的主导符码是“空间”,当局长以经过剪辑的不实影像确定了严谨的位置,这一误认就产生了类似詹姆逊所分析过的“鸿运饭店玻璃幕墙”的意义内涵,扩而散之,整个银行大堂也如詹姆逊理论中的饭店大厅。由此,片中的“读视频”与后现代的“读图”文化景观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认为人迷恋并且追求确定性是一种规避生活变化的不真实的幻想,他们无力也不可能认识真正的自己,也更加不能明确地认识别人。这种“空间”的无法掌握,发生在严谨身上,就表现为他陈述之中所感受到的与他现实生活相反的“边缘处境”,正如詹姆逊所说“是一个偌大的空间,人处其中,无法在脑海里把他们在都是整体中的位置绘制出来,无法为自己定位,找到自我”[11]302。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就如同银行外的人看不清大堂内的真实,“增加了自己判断和行动的难度,给人一种完全失去距离感的感受,使得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感受体积、 透视景物的能力,整个人无助的置身于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3]495,银幕外的我们也同样看不清严谨的真实人生境遇直至最后反转。后现代的“景观”文化之下真实与真相被悬置,虚假的、 被“景观”所设定好的一切引领认知,然后,又一次一次颠覆。“认知图绘有着力于重建个人集体性经验的政治文化承担,使个体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中掌握再现,表达出难以言表的整体的都市结构”[12]89,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功能是在自身属性基础上对社会环境产生作用能力,它与社会语境和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大赢家》也是通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声东击西的影射转换,以局部领域间接投射出社会总体的运作规律,并在对空间与社会“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筑建起空间与社会的第二关联——狂欢。
2 “狂欢广场”、 起义与加冕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用世俗与神圣为标准可以将社会划分为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其间有“过渡仪式”存焉。埃德蒙·利奇则运用范热内普的三重阶段理论来分析狂欢节的前后过程,随后这种“阈限阶段”的论断被劳拉·穆尔维引申入对狂欢仪式的研究。(1)“阈限”概念“来自拉丁文‘极限’,意指所有间隙性的或模棱两可的状态”,范热内普研究“仪式”时认为过渡仪式都有三个阶段标志出来:分离、 边缘(或阈限)、 聚合,特纳这种三分基础上,将仪式细分为阈限前、 阈限、 阈限后三个阶段,并指出阈限中存在的“地位逆转仪式(少数的年度性仪式和群体危机仪式)”。穆尔维认为阈限阶段如狂欢仪式充满了冲突和不稳定,是一个开放的过渡阶段,它冲击了资本主义历史叙事趋于稳定的结局,从而用“阈限阶段”以分析“狂欢”叙事的变革性力量。在《大赢家》这部电影中,以日常上班跑业务、 下班吃饭休息的生活为开端,进入阈限阶段的演习喜剧为中心重点,最后回归日常生活为结束,三段式的划分里有狂欢体验的无序与颠覆,也有叙事结构与剧中人物生活节奏的闭合与稳定,在其阈限阶段充满典型的狂欢化色彩。
2.1 “狂欢广场”:三个广场空间的形式
巴赫金在论述拉伯雷小说的狂欢化时,是从广场话语的角度切入的,“广场因素”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广场”的范围并不是受到局限的指定地点,而是认为“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如大街、 小酒馆、 道路、 澡堂、 船上甲板等,都会增加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13]169。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大赢家》的银行大堂显然具备“狂欢广场”的特质。防盗门落下,工作人员、 顾客与“劫匪”密闭一堂,而不营业的大堂因其“无用”性脱离了现代派的实用主义,成为“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2]166。银行大堂作为《大赢家》中的第一个狂欢广场,不仅承载了爷孙两代人的代沟与亲密、 经理与职员两个群体的斗争与互助、 被俘虏的特警与人质两个集团的对立与统一,还是一度代表权威阶层的行长被第二世界“造反”的发生地,众人从开始消极对抗演习到后期认真参与,和自称“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现在很残暴”的“劫匪”提供出抢来的钱供大家打牌游戏作筹码所用,都典型地体现了在这一文化意义上的广场内所发生事件的全民狂欢色彩。
集聚了警察、 群众、 媒体等各色人群的银行之外,自然形成第二个狂欢广场。尽管电影大部分外景段落将群众处理为虚化了的背景,但透过选择人质替换时的摇镜头、 张弛被点名送火锅时欢悦呼喊的全景镜头和严家父母喊话的场景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小的“广场”的存在,主持人对不符合“通稿”的事件的质疑、 行长与队长的想法差异与严家父母在警察追随下绕圈喊话的各种插曲,都显示了数量虽少但拥有各种行业差异与立场差异的“群众”,在银行之外形成了所谓的“狂欢广场”。
狂欢广场之三,在媒介社会与网络社会,虚构的时空因其包容性也具备成为“广场”的可能。严母一边看直播一边打电话,电话中的众人因严母所问的“你看了” “不是那个胖子”“拿枪的那个”种种交流证实了另一个群众集群的“在场”性。受警察委派劝说时兴高采烈地介绍各色相亲对象,则证实了该集群的“参与”性,因为这些在广场话语中存在的人物群体的“在场”与“参与”,我们完全可以判定第三个狂欢广场,即直播与电话所搭建起来的狂欢广场的实在性。
2.2 起义:第二世界对“伪第一世界”的倾覆
巴赫金在狂欢理论中划定了两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官方的,特征是压抑、 等级森严,令平民过着常规谨小慎微的日子并对强权与教条屈从与恐惧。第二世界是狂欢的广场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另一面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普通民众在这一世界中打破阶级、 血缘、 年龄、 身份等诸多等级的界限,众声喧哗通过狂欢、 戏谑等方式,实现自由与友爱的乌托邦。《大赢家》中以严谨为代表的第二世界中的人物,通过对以行长为首的第一世界人物的漠视与反击,完成了第二世界的起义狂欢。
影片中的银行行长是以第一世界的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存在的。吴行长一开场就以并不符合手续规定的任务给严谨下达指令并斥责其未完成,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 然后,以“打比方”的形式交代第一世界的所谓“惯例”。在故事发展的进程中,行长数次以“造反哪你” “我是行长我说了算” 和“一个个都得开除了”强调第一世界的权威性。在演习的过程中,严谨作为第二世界的代表,初期是以不完成行长布置的任务,如不让客户签约与不草草结束演习行动与第一世界孤军作战的,在行长进入作为狂欢广场的内部之后,冒充“劫匪”中弹死亡意图结束演习; 而受到开除逼迫与童言激励的银行全体员工,作为第二世界整体参与了颠覆第一世界权威的一场起义:“行长你差不多得了”,然后认认真真给行长挂上写有“死亡”的牌子,暗示第二世界倾覆第一世界的胜利。基于在地化改编的要求,影片高明之处是将警察局长设置为第一世界的真正代言人,他的身份与他对行动规范的掌控,使吴行长所遵循的信条沦为“伪第一世界”,从而保证了狂欢阈限阶段结束后回归世俗状态的平稳,并以此树立起在我国社会框架内,去除“伪第一世界”后,真正的全民狂欢的文化图景。
2.3 加冕与脱冕:人物设定的反转与再建构
在狂欢节里,最主要的狂欢活动是狂欢节丑角国王的加冕和随后的脱冕废黜。加冕—脱冕是两位一体的双重仪式,二者的相互转化才能彰显以交替和更新为特征的狂欢的世界感受。《大赢家》以主人公认真近乎死板的性格,为其在敷衍成风、 得过且过的工作作风通病下的别具风格树碑立传,并镌刻以“严谨”之名,又以其自述的边缘化处境成就其悲剧英雄和可以为普罗大众代言的代表意义; 然而,当他跟家人说“我要抢银行了”,家人认真倾听的态度与父母的鼓励、 妹妹的共犯,已经为不久后的“脱冕”做好第一步铺垫。充满喜感的皮卡丘头套从何而来,可以在严母打电话时织毛线的伴生动作里找到根源; 妹妹抢过喇叭孤注一掷、 严母絮絮叨叨夸他认真、 严父一再嘱咐儿子受到领导信任就要珍惜机会、 行长报上去的优秀员工表格里他的名字,这种种对初期人设的解构和颠覆,在事实上是完成了对严谨作为一个悲情代表英雄的脱冕仪式。随着严谨吃起母亲送来的饺子和妹妹抢过扩音器惊天一喊接踵出现,之前设定的家人冷落被推翻,大堂内众人决定好好配合,与视频中严谨的感人自述产生强烈对撞,其实影片于此构建了一次鲍德里亚式的虚拟内爆:第二世界整体社会的改变和之前构筑的边缘人意义的消失。
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率性而活》里“劫匪”之父母以埋怨曾将他作为户主和在劝说现场追问钥匙的行为,确立了郑度满作为真正“悲情边缘人”的人物画像,至影片结束也没有扭转,家人的冷落和被劫女职员斯德哥尔摩式的伪情动,人质特点模糊不清只突出主角的塑造方式,使他的“起义”以孤零零一个人代表第二世界而告终,算不上狂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自嗨。《大赢家》的导演于淼之前在专访中说过:“我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不对的?我们眼中的怪咖,有没有可能反倒掌握了真理?这是做这部片子的内核。”[14]电影给严谨脱冕的同时是父母家人、 老人与孙、 行长局长、 同事顾客所有人全民参与的一场狂欢。众多“人质”参与的“举报”与“起义”,形成整体的第二世界对自我心性和生存价值的自我肯定,并由此而产生内在优越感,群体的胜利与群体的喜剧精神盖过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此外,这种变异的脱冕背后,我们可以预见阈限阶段结束后,主人公告别狂欢重回生活的温暖延续,也就是后现代解构之后的再建构。改编后的狂欢在阈限阶段结束后并未戛然而止,而是以中国电影的伦理精神指向新生,用一种温情脉脉的余韵回归现实,美好从“狂欢”隐匿为日常生活中的温和,从而营造出具有抚慰性的乌托邦童话寓言世界,它引发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 偏见与事实之间、 态度与结果之间、 行为与信仰等终极命题的一系列再思考。
3 结 语
《大赢家》是合当前社会文化与社会语境下对都井邦彦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在地化电影改编,改编作品呈现出后现代特质的风格,对现实与先有文本的戏仿、 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以及在电影叙事阈限阶段呈现出来的狂欢化色彩都堪称地道; 在内容与立意上,改编中注意到了作为中国喜剧电影的社会与伦理承担。影片对执法权威的正面描绘、 对人情人际关系的温暖处理、 对未来现实的信任倾向、 与对人生态度的批判反思,虽然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但从普通生活和抚慰现代焦虑的角度,为以后的翻拍电影和改编电影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改编思路,本身也别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