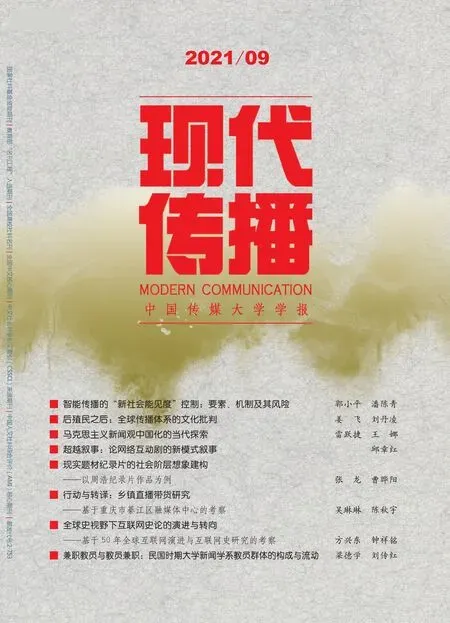福柯的“主体化”及其传播学认识论意义*
■ 朱振明 陈卫星
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以及主体身份”的时代,逢“主体身份”建构必谈“话语”(discours),而谈“话语”又必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尤其是在有关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话语”与“主体身份”成了时代学术的流行语。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是与“话语”“知识”和“权力”关系分不开的,主体化在话语的形成和权力关系技术的运作中得以形成,话语和权力(pouvoir)成了“主体”的塑造者,主体是知识和权力关系程序的结果。因此理解福柯的“主体化”,就要从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来把握社会实践中“主体”的形成。本文将借助文献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福柯有关“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思想文献的分析,来揭示福柯的主体与其他三个元素间不可分离的关系,“知识、话语与权力”的互动是理解“主体化”形式的关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当下哲学”观;第二是福柯的“人”的观念;第三是福柯的话语、知识和权力;第四是福柯的“主体化”形式;最后是福柯“主体化”理论的传播学认识论意义。
一、福柯的“当下哲学”观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观的重要依据。福柯认为:“康德建立了现代哲学的两个传统……在他的批判作品中,康德建立了涉及探讨使真实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哲学传统,这就是自19世纪发展起来的真理分析哲学;另一种是拥有批判探讨形式的当下本体论,即有关我们自己的本体论。”①福柯把自己归属于康德的批判传统,并把自己的工作方案称作“思维的批判史”。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主张走出人类的幼稚状态,并因此涉及到当下哲学的问题,即“我们是什么”的问题。福柯认为,康德的质询“把主体和实践、思维和行为联系在一起。人的存在不必是超验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需要借助话语和技术、法典和制度来回答下列问题的历史解释:我们怎么成为我们?质询人的存在意味着探究他得以建构的历史条件,其决定了今天的我们的所做、所说、所思”②。
福柯在坚持“当下哲学”观时又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影响,认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过的事情”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来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④。“我们被过程、运动和力量所贯穿;我们不知道这些过程和这些力量,哲学的作用无疑就是分析这些力量,分析它的现状。”⑤在福柯看来,今天要面对的政治的、种族的、社会的、哲学的问题不是去尝试把个体从国家及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把我们从国家及与其相关联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通过拒绝以往几个世纪强加的个体性类型来促生新的主体性形式。
在这种认识论的背景下,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被结构在生产关系、意义关系和权力关系之中,但福柯要做的是在复杂权力关系中来探讨社会活动者的“主体化”以及新“主体”的可能性。福柯处理“主体”及其“主体性”形成的具体方法在于“问题化”。福柯的“问题化”不是去再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话语来创造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是“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这些实践让某物进入真实—虚假的游戏中,把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不管是以道德反思的形式还是以科学认识与政治分析的形式”⑥。如自古典时期开始,通过理性话语,即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分,借助管理与纪律程序,人被赋予一定的秩序,在此实践中出现了作为研究问题的“疯癫”(理性/非理性)、“性欲”(道德/非道德)、“疾病”(科学/非科学)等话语。福柯所指的“游戏”不是去模仿或生产喜剧,而是一套生产真理的规则,一套导向某种结果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规则和原则该结果可被认为真实与否。因此,福柯的工作更多被描述为对于某个既定时期相对应的“问题化”形式的研究,对“问题化”方式的研究也就成了福柯在(问题的)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分析方法——毋宁说,“主体化”的分析方法。
二、福柯的“人”的观念
在福柯那里,人既不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它是思维考古学展示的一个新的发明(或现代性的发明),是我们知识中的一个“褶子”,其可能随着新的认识型的出现又很快会消失。⑦具体地,在古典时期(17世纪中期),人是由话语的“表征”秩序框架来界定的,不是一个拥有自己具体生活、工作与语言的存在;随着古典时期的结束,在作为“话语”的语言的解体中,出现了“人”的形象,诞生了人文科学。不过随着语言在文学、语言学、心理分析和民族学(ethnology)中的再现,人的形象又面临着解体。
福柯的“人”一词存在于现代认识型(自19世纪初)的两种配置中:对有限性分析和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在有限性分析中,人是一个“经验—超验的双重存在,因为其能够认识自己的所做”⑧,人的外在的经验形式需要通过人本身的有限性来把握。人文科学考古学没有把有关人的知识分析指向任何一种建立它的超验机构,而是指向现实中以人为经验和超验存在的社会历史实践。二者随着从无限性出发来思考有限性以及无限性形而上学的消失而得以形成。不过,并不是说必须到了19世纪才发现有限性,时至当时有限性已经被思考,不过是通过其与形而上学无限性的关联来进行,即在无限性的内部来思考有限性,而有限性分析则是从有限性出发来思考有限性。即,从人的有限性(如身体、欲望和说话的能力)出发来思考外在经验性(如生活、工作和语言)的有限性,是以“表征”(représentation,如语言只是再现自然的工具)为特征的古典认识型式微的结果。
在人文科学考古学层面上,人的形象随着古典话语的消失在话语碎片的缝隙中得以形成,但语言在文化、语言学、心理分析、民族学中的重新出现又宣告了人的形象的解体。福柯认为,随着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出现以及古典话语的消失,出现了“人”的形象,不过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换句话说,人不仅是有限的认识对象而且也是有限的认识主体。哲学进入到“人类学沉睡”当中。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体现在知识的实证性当中,人由生活、工作和语言来支配——后者先于前者;另一方面,这些标识人的有限性的每一种外在形式只能通过人自身的有限性来把握。“我能接触到生活的存在形式,从根本上是通过我自身的身体来进行的;生产的决定性是借助我自己的欲望来进行的;借助语言的历史性是根据说出语言的时刻来进行的。”⑨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经验(生活、工作和语言的有限性)有限性追溯到更为根本的人的有限性(即身体、欲望和讲话能力的有限性),借助这种人的根本有限性,经验性的有限性才能界定。有限性分析意味着从一种有限性走向另一种有限性。
在系谱学层面上,沿循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之死”,福柯提出了“人之死”,哲学从“人类学沉睡”中被唤醒,“人”成了形式主体。与这种“人之死”(或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主体”或“建构主体”)相伴随的则是“人的诞生”,即“人被构建为主体”。福柯的“人之死”表示:“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我们可以说,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⑩“人”不再是“主体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和永恒的,而是一个经验的存在,成了历史与社会实践的产物。
不过在福柯那里,“人”的形象并不等同于“主体”。前者属于现代认识型安排中的形象,是我们开始从“有限性”出发来思考“有限性”时出现的,后者则形成于福柯对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或一种非历史的、绝对自由的“唯我主义意识”的批判,试图把哲学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即知识与主体性并不来自“超验的先验”,而是来自“历史的先验”。福柯对作为“唯我主义意识”的主体的批判,以“主体化”的形式追溯到古希腊和“那些使我们成为自己历史囚犯的机制”。
三、福柯的话语、知识与权力
在福柯那里,话语、知识和权力是主体的形塑元素。福柯的话语不是语言学话语,更多涉及的是科学话语,如疯癫话语、诊所话语、性话语、人文科学话语等。不过福柯说,虽然考古学分析对象主要是科学话语,但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因为“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具体结构中的科学,而是不同的知识领域”。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套陈述,这套陈述不是被随意生产的,而是被一定数量的程序控制、组织和再分配的。“(话语)隶属于或来自同一构成系统的一套陈述。”“陈述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作为语言学单位的词语、句子与命题是其物质性载体,或话语“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些规则不仅是语言的或形式的,而且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背景决定性的区分,如理性/非理性、科学/非科学、正常/非正常”。实施话语分析就要去关注话语的“外在性”或话语的生成条件,探讨话语的构成,描述“陈述的功能、它的存在、它的条件以及调节它的规则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这些规则不仅规定了“客体”出现的历史条件,而且也规定了“谁”根据何种条件在相关领域内必须做出怎样的陈述。如某个人说“这座桥承受不了卡车的重量”,这不是一个陈述,只是一种语言学行为,如果是“国家道路管理局的工程师”说出来,那就是一个陈述,因为前者是一种用意义表达的日常生活话语行为,没有合法性过程的支撑,后者则是一种技术话语行为,其根据一定的技术规则建立起来。所有这些客体、规则、陈述、概念等成了“考古学”知识的组成元素。
在福柯处,“知识”表现为一套元素,是人们在某个话语实践中可以谈及的东西,包含某个话语根据自己的构成规则而生产的对象资料库、陈述方式、概念以及理论选择。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如此描述“知识”(savoir):“这是一套通过话语实践有规律地形成的、一门科学形成所必需的元素,尽管并不必然导致一门科学的产生,但我们能称之为知识。知识,就是我们在被详细说明的话语实践中谈及的东西:这是一个由将可能与否获得科学地位的不同对象所构成的领域……知识,也是主体能够为谈论在话语中与自己有关的对象而表明立场的空间……知识,也是陈述协调和隶属的场域:在此,概念经历着出现、界定、应用、变化等过程……最后,知识由话语提供的应用和挪用的可能性来界定……是一系列与其他话语或其他非话语实践的构合点。存在着独立于科学的知识,但不存在没有明确话语实践的知识。所有的话语实践由它形成的知识来界定。”总体而言,“知识的秩序不仅被理解为科学、哲学所说的东西,而且也被理解为文学、法律和规则、未被书写的知识、宗教、道德,即所有在一个文化中被知道的东西。”
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知识和权力是分不开的,他指出“我想标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不同权力机制在我们之间、我们身体中或外的运作方法。我想知道我们的身体、日常行为、性行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科学和理论话语与多种彼此相联系的权力系统结合起来的方法”。福柯并不否定传统的权力观,但在他那里,“权力不是强加或命令,是力量关系和影响”,不是法律、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权力,不是“某些人”向其他人直接施加影响,而是“一种影响行为的行为,一种影响可能或现实、未来或当下行为的行为”,权力的行使在于“引导行为”与调整可能性,结构他者可能行为的场域。权力是借助战略与战术抵抗通过“不断被发明、被完善与发展的‘程序’(或技术)”来实现的。抵抗在能建立新的权力关系的同时,新的权力关系又能发明新的抵抗形式,权力(或权力关系)因自由个体的无处不在而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
话语、知识和权力彼此构合在一起,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发挥作用的,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手段。话语的世界不能被分解为统治话语与被统治话语,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权力话语”。话语被看成“力量关系”场域中的一些元素或战术组,是诸多能在不同策略中发挥作用的话语元素,策略中的话语战术是一种知识—权力装置。不存在与某个“知识场域”构成无关的权力关系,同时也不存在与权力关系构成无关的知识。“如果不与一套具有特定时期科学话语类型特征的规则和束缚相一致,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理性的、共同接受的、有效性的约束或激励效果,任何东西都不能表现为知识的元素。相反,如果不根据结构严密的知识体系中有效的程序、工具、手段、目标来展开运作,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权力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福柯以“性”话语为例对此进行了总结说明:“如果性形成了要认识的领域,这是权力关系把它构建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如果权力把其作为目标,这是因为知识技术、话语程序能够对其进行关照。”
主体是权力—知识关系的结果。权力—知识关系不是从自由的认识主体开始或参照权力体系去分析的,而是相反,认识主体、要认识的对象以及认识的模式是这些权力—知识的基本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的结果。就是在话语、知识和权力的构合中,主体成了被加工对象。法国的福柯研究专家朱迪斯·雷菲在《福柯的字典》中借助“纪律”对权力/知识的关系做了如下说明:“如果没有知识的形成、组织与循环,毋宁说,知识机器(即积累知识、技术、档案、保存、记录、方法、调查、研究、验证机器等有效工具)的循环,纪律权力就不能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生产一种使主体客体化并预示着一切主体化体验的知识话语,权力就不能使个体遵守纪律。权力/知识的构合是双重的:权力从个体处提取一种知识,并且是有关这些被控制主体的知识。因此,这不仅涉及分析个体成为被治理主体的方法,而且最终主体被要求生产一种有关自己的话语——他们的存在、工作、情感、性等——以便使生活本身成为生命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生活本身成了诸多知识的对象。”也就是,知识与权力构合于主体的“被规训”的过程中,不但构建了主体而且生产有关主体自身的话语:知识是有关“被规训主体”的知识,权力运作是借助知识主体被规训的“发明程序”,它们一起生产了有关能思、说、做和欲主体的话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身体政治技术”(technologie politique du corps)中就明确地表述了以身体为对象的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构合特征,被驯服的身体不只是通过暴力或意识形态工具所获得,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种有关身体的、不完全是其功能科学的“知识”和一种对其力量的操控,这种操控不仅仅表现为克服其力量的能力(capacité),二者构成我们所谓的身体政治工艺学。简而言之,福柯的技术(technologie)是一个包含知识与权力的生产机制,就是在这种机制中人变成了被规训的存在。
四、福柯的“主体化”形式
福柯从一开始就对西方主体哲学中的笛卡尔的“我思主体”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唯我主义的、自由建构的主体,自己关注的则是位于历史脉络中被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起来的主体。福柯的研究主要从“思维的批判史”出发来研究西方社会主体的主体化—客体化体验形式,例如疯癫体验、性体验、罪犯体验等等。在每个“体验”中,有些元素彼此构合在一起(一种可能的知识形式、个体的行为模式以及可能主体的存在方式)形成了福柯所研究的“体验焦点”。例如,把疯癫当作西方文化中的体验来研究,首先把它看作出发点,从此出发来构建一系列或多或少异质的知识:疯癫作为认识模式,其可能是医学的、精神病分析的,也可能是心理学、社会学等;其次,疯癫既是知识形式,也是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使我们把它视作某个社会中的“失范”现象,同时其也是个体在疯癫方面的行为规范:它们既是正常个体的规范,也是医生的规范,也是精神病分析人员的规范;最后,在这种疯癫体验相对疯子来界定正常个体存在方式的构成层面上来研究疯癫。可能的知识形式、个体的行为模式与主体构成之间的构合基本上成了福柯的主要研究工作,其涵盖了考古学、系谱学和伦理分析。
虽然福柯的研究涉及了话语、知识和权力,但福柯说自己研究的基本主题“是主体而非权力”,自己的著作在于“创造有关不同形式的历史,通过我们文化中的这些形式,人类被转变成了主体”。即福柯的研究在于探究作为话语、知识和权力的“褶子”的主体及其主体性,如《词与物》从“认识型”的视角来处理主体问题,关注作为主体和客体的“人”的构成和解体;《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知识的意志》从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出发把主体构建为权力和知识形式发挥作用的产物。因此又可说,福柯所从事的理论工作聚焦于主体问题向主体化问题的转变,其借助“思维”行为来构建主客体间的可能关系。福柯的“思维的批判史”是对主客体间关系形成和改变(以形成某种知识形式)的条件的分析。“这些条件必须规定主体应当服从于什么、主体应当拥有怎样的地位、主体占据怎样的位置以便成为合法认识的主体、在何种条件下能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以何种问题化出现、服从怎样的界定。”从主体建构出发,“主体的构建要通过权力、认识以及自我技术的实践来进行。主体性的历史生产问题既属于一些有关主体知识构成的考古学描述,也属于对个体服从的统治实践与管理策略的系谱学描述,又属于对人们自我生产与自我变迁的技术分析”。在福柯看来,作为主体和客体的“人”不仅是认识领域中的一种确定的安排(disposition),而且也是权力形式和知识形式发挥作用的结果。
福柯认为,“主体化”指一种过程,借助该过程主体得以构建,或者更确切地,一种主体性的构建。总体上,人的“主体化”有两种形式:一方面,把人变为主体的观察方式,该方式意味着人只有通过客体化才能成为主体(如作为权力关系与知识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主体化形式是客体化实践;另一方面,是人与自己关系的方式,借助一系列的生活技术和自我技术,人被构建成自我存在的主体。“生活技术”是古希腊人的伦理工具,“自我技术”则是禁欲主义者和基督教所采用的自我关照的伦理手段。换句话说,“主体化的方式”一方面在广义上指主体的客体化方式,即主体表现为某种确定的认识和权力关系的对象;另一方面在狭义上指“施加于自身的活动形式”,隶属伦理范畴。人的主体化是和客体化相联系的,通过对人的客体化,实现了人的主体化过程,构建了人的主体性。即,主体被引导来观察自我、分析自我、解读自我并把自己当作可能的知识领域。
具体地,福柯的这种研究涉及三种把人变成主体的客体化方式。首先是被赋予科学地位的研究方式,事关言说、工作和生活的主体问题在某个具有科学地位的认识领域和形式中出现和融入,例如,普遍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的讲话主体的客体化,生产主体(参与了工作、财富与经济分析)的客体化,自然历史或生物学中对生命事实的客体化,这涉及某些“人文科学”的形成,这些“人文科学”通过参照经验科学实践与17、18世纪的话语来进行研究(如《词与物》);其次是位于“区分实践”中主体的客体化,该主体或自我分离或与他者区分,在此过程把主体看成了对象,如疯癫和理智、生病和健康、罪犯和“好的小伙子”,这是通过精神病学、诊所医学和犯罪实践来实现的(如《疯癫史》《诊所的诞生》《规训与惩罚》);最后是人通过与自身的关系转变为主体的方法,如在《性史》中,人们用何种方法把自己看成“性”的主体,即通过基督教及其之外的东西,“个体被召唤把自己理解为愉悦的主体、欲望的主体、淫欲的主体、诱惑的主体,被要求通过不同的方法(自我检查、精神训练、供认、忏悔)就他们自身与构成他们主体性最隐蔽的和个人的部分来展现真实/错误规则”。这就是福柯在晚年对自己的总结:“首先,我实现了一种与真理有关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借助真理我们把自己构建为‘认识的主体’;其次,实现了一种与权力场域有关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借助权力场域我们把自己构建为影响他人的主体;最后,实现了一种与伦理有关的历史本体论,借助伦理把我们构建为‘道德的活动者’。”
在主体化的具体建构操作中,福柯的“精神病治疗装置”颇具代表性,其构合了以上三种路径。“精神病治疗装置”的分析围绕三个轴心来展开:权力轴心、真理轴心和主体化轴心。首先,围绕权力轴心,精神病医生把自己构建为影响他者或病人的主体。在“精神病治疗装置”的“权力轴心”安排中,一方面,权力着力于身体,如身体在庇护所空间中的分布、身体的表现方法、其需求和欲望,权力实现了一种身体微观物理学安排;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家和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或力量关系是不稳定的,充满斗争和抵抗,如病人借助作为“反操作”的抵抗,对医生的权力产生了影响或损伤了医生的权力,病人逃避了医生为他们规定的范畴,于是出现了“反制度”建构的可能性。其次,借助真理轴心,精神错乱者被构建为知识的客体对象。收容所不仅是一个纪律系统,而且也是某种真理话语形成的场所,在此,权力装置和真理游戏构合在一起。最后,通过主体化轴心,主体必须把强加给他的规范变成自己的东西。治疗医生一方面不仅从外部来接触病人,而且借助程序(如询问、催眠)从后者来获取病人的主体私事,让病人接受和内化从外部施加的规范和说明。籍此,主体成了不同真理体制和话语实践中复杂与可变的“函数”。
五、福柯的“主体化”理论的传播学认识论意义
福柯对“主体化”的思考本身就体现出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福柯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的局部理性化过程,这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对西方社会宏大理性化过程的反思,也有别于(尤其)借助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的“主体性”建构。在福柯那里,认识主体不是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超验主体,不存在先验的认识,主体是形式主体,不同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构建了人的主体性。因此,福柯说:“在人的历史中,人不停地构建自己,不停地把自己构建成一系列不同的主体性,我们因此从来没有面对一个‘人’的东西。”
福柯借助《自我技术》(Lestechniquesdesoi)一文对自己研究的技术思路进行了描述:“我的目标是勾勒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发展有关自己知识的不同方法历史:经济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医学、刑法学。关键点……是来分析这种被称作‘科学’的具体‘真理游戏’,这些‘真理游戏’与人们用以了解自己的具体的技术相关……我们必须理解存在四种主要的‘技术’(techniques)类型,每种类型都代表了一种实践理性模式:(1)生产技术,其使我们得以生产、改变或操纵事务;(2)符号系统技术,其使我们得以使用符号、意义或含义;(3)权力技术,其使我们能够决定个体的行为,使他们服从某种目的或支配(domination),存在于主体的客体化;(4)自我的技术,其使个体在自己或他人的帮助下能够对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思维、行为或任何一种存在形式产生影响,由此获得自身的改变,达到某种愉悦、纯净、智慧或长生的状态。”虽然这四种技术方式从来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不过每种技术是与某种特殊的支配类型联系在一起。在此,福柯明确指出,就是要借助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真理游戏”来了解不同技术类型改变个体的方式,即个体的主体(性)构建方式。其中,福柯所说的“生产技术”和“符号系统技术”属于科学和语言学研究领域,是其他研究者早已从事的工作,“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则事关支配技术和主体技术,是他自己所专注的领域。这样,借助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来揭示主体化成了福柯研究的考古—系谱学进路——考古学偏重去考察“主体存在的形式”;系谱学则更多关注“主体化”的实践过程。
福柯的“主体性”建构特征在于,借助不同知识领域中的“真理游戏”(或“真理化”veridiction)通过个体的“客体化”方式来实现主体建构,主体不仅是权力控制过程的结果,而且也是权力运作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偏移、变化与更新的中继站和强度节点。个体被构建为疯子、罪犯、病人等,其中作为“技术”的被发明的、被完善的、且不断发展的权力关系程序和知识发挥着最根本的作用。
福柯有关“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化”的观点使我们看到,在考虑人类自身的建构时,不能把主体的建构与话语、权力和知识分裂开来。在考古学—系谱学层面上,主体及主体性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话语和权力互动关系的结果,但在微观层面上则表现为对知识(或历史先验)的把握和对作为权力战术的程序的掌控。要理解这种“建构”就要从了解社会实践入手,具体地,了解实践领域中知识和话语形成的规则,同时思考权力技术(更多体现为非话语实践的设置、安排以及程序)的配置,不能依赖超验的主体想象,脱离现实社会实践。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福柯有关“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这种认识对于“主体与主体性建构”传播学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福柯的“主体化”理论摆脱了本质主义的永恒“主体”,认为处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是形式功能主体,是个变量,身份因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处于权力关系场域中的主体不是“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而是自由地存在于权力关系场域中,自由是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主体性的改变取决于对知识和权力技术(或战术)的把握,这为新主体和新制度现实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可借鉴路径。另一方面,“主体化”理论为传播学的“主体与主体性建构”命题提供了新的思考选择路径。在这里,主体不再是本质主义的存在,而是一种与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紧密相联系的主体,或者说,主体是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中介化的结果。主体性的建构不再仅靠“超验的意识先验”(胡塞尔)、“语言学符号的意义”(伊丽莎白·特劳戈特)、“意识形态的灌输”(阿尔都塞)、“社会心理学主客我的互动”(米德)、“心理学的异化”(拉康)等过程来完成,而是借助知识—权力装置来实现自由主体的生产。尤其是“主体化”操作摆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关系的抽象性描述,尤其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的权力施加,主体性成了被动的建构结果。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话语、知识、权力与主体”观念在“符号学意义建构主体”观念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过程观”之外提供了新的主体可能性,使我们看到主体身份建构的微观动态机制,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个变迁的结果或一个宏大的信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流程及其所产生的中观与宏观效应。福柯的这种“主体观”不但有助于世界上广大地区走出后殖民主义身份观,而且丰富和重构了后现代视角下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建构与传播框架。
注释:
② Gabriel Terol Rojo.LecturasDelacríticaFoucaultianaalaSubjetivacion.Thémata.Revista de Filosofía,no.47,2013.p.279.
③⑩ Michel Foucault.Ditsetécrits,I,1954—1975.Paris:Gallimard.1994.p.612,pp.788-789.
⑤ Michel Foucault.Estética,éticayherméneutica,Obrasesenciales,VolumenIII.Barcelona:Paidos.1999.p.152.
⑦⑧ Michel Foucault.LesMotsetlesChoses.Paris:Gallimard.1966.p.15,p.329.
⑨ Edgardo Castro.DiccionarioFoucault.Temas,ConceptosYautores.Buenos Aires:Siglo XXI Argentina.2011.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