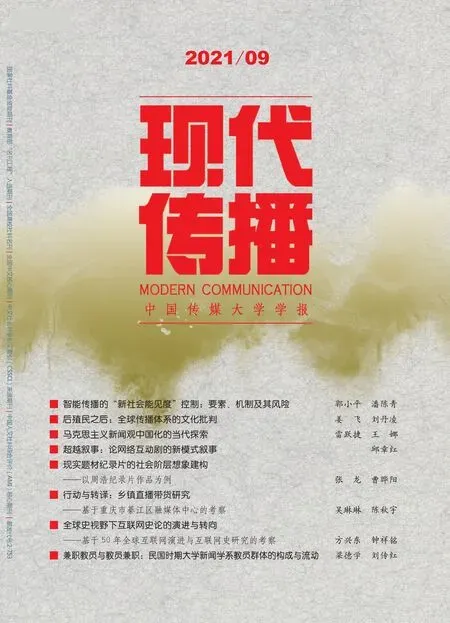民心相通析论*
■ 张勇锋
一、引言:民心相通——概念还是命题?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内涵深度的理论问题。作为“五通”机制中唯一直接指向人际关系的顶层设计,民心相通的理论研究却明显存在滞后,尤其是对民心相通的语义内涵至今没有取得广泛且规范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民心相通是指“人民群众在心理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方面的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等,具体包含心理层面的情感认同、观念层面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层面的实践认同”①;另有学者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在目标、理念、情感和文明方面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认同”②;还有学者试图从文化传播视角对民心相通作出界定:“文化作为传播过程中的意义,通过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载体得到传播,最终在无形中拉近不同文化区域人民的距离,实现民心相通。”③诸多概念化解读各有侧重地含括了民心相通的“人民”“心理”“情感”“沟通”“传播”“理解”“认同”等基本因素,但这些阐释多流于政策解读和经验描述,难以在学理层面形成对民心相通的本体性概括和抽象性表达;更重要的是,对于民心相通语义系统中的“民”“心”“相”“通”各构成要素失之笼统甚至未能触及。民心相通作为中国政府参与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倡议机制,其语义内涵的不确定性常常导致语用实践上的模糊、粗放乃至混乱,“一带一路”建设在深入推进的同时,遇到的掣肘乃至冲突也时有发生。
要对民心相通的语义进行准确厘定,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一项完整的理论研究议程,首先应当回到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起点进行探究,明确民心相通究竟是一个概念还是一项命题。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④,是知识组成的元单位。人们必须具有关于某事物的概念,才能作出关于某事物的判断、推理与论证。在逻辑学和语言学中,民心相通显然并不具备概念本身不可拆分的基础属性,而是一个具有判断性语义的命题。命题“即通过肯定或否定对事物作出某种陈述的语句”⑤,是由多个概念组成的复合语义系统。一般而言,一个简单命题可以拆分为不同的词项,即主项、谓项、联项和量项。民心相通虽然是一个极简命题,仍然可以拆分为若干关键要素,其中“民”是量项,“心”是主项,“相”是联项,“通”是谓项。对各要素项进行准确厘定,是理解命题并判断其真伪的必要前提,正如英国分析哲学大师罗素(B.Russell)指出:“要发现一个命题所处理的是什么,有一个方法就是自我询问;即我们必须都了解些什么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哪些客体,——然后才能明了命题的意义。”⑥罗素所谓的“词”和“客体”,也就是命题的构成概念及其所指。目前学界对民心相通的理解和阐释莫衷一是,原因就在于直接将作为命题的民心相通视为一个完整自足的概念予以说明,忽视了对其内部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联的进一步探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指出:“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命题与概念上的模糊与错位,不仅给民心相通的实践带来一定困扰和障碍,更限制了民心相通作为一项重要理论命题的深入发展。本文以中国哲学思想为理论分析工具,从民心相通语义系统中的“民”“心”“相”“通”四个基础概念要素出发,尝试剖析其各自含义及其内在关联,以此探析民心相通在命题语义上的规范意涵。
二、民
目前学界对民心相通之“民”的解释,基本没有涉及,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直接使用,并未考虑“在使用一个概念前如何先去探究其来龙去脉和前后左右关系”⑧。一般研究者多把“民”理解为“人民”“群众”或者“公众”。前二者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色彩;而“公众”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依法享有政治权利并参与国家事务的社会成员群体。上述对“民”的诸种政治化的理解,并不符合民心相通的生成语境及其目标意图。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是与“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全新理念相一致的,是以不同国家国民为主体的人际交往范式而非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家间外交“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一种官方活动”⑨,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而民心相通的跨国民间交往性质规约了其基本诉求,即交往主体间政治关系的弱化、淡化乃至归零,以及主体间作为“人”的关系的交互、提升和强化。质言之,民心相通在根本上是“人”的相通。
“人”的概念可以分别从生物、精神和文化角度得到最基本的界定,而生物性则是各种界定的逻辑基础,由此为民心相通找到了在最大程度上求同存异的客观依据,即民心相通的主体,是超越种族、国界、制度和文化藩篱的无差别的生物性的人。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Peter·F.Strawson)认为,“人”的概念具有“逻辑上的原始性”。斯氏在讨论心灵哲学时指出:“我们按照人类的共同本性而行动,那么就更好理解:我们怎么可能相互把对方(以及我们自己)当作人看待。”斯特劳森意在强调,相互把对方当作具有“共同本性”的“人”来看待,是人与人之间有效交往的前提。换言之,唯有不附加任何外在条件而在最本质的“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心灵的互通。
民心相通之“民”之所以要“去政治化”再回到斯特劳森所说的“人类的共同本性”上来,究其实质,是因为政治的“对抗”属性往往会成为国际社会交往的直接障碍。墨菲(Chantal Mouffe)和拉克劳(Ernesto Laclau)从本体论上将“对抗”(antagonism)视为政治的“本性”,施米特(Carl Schmitt)更是不无极言地宣称:政治就是“最剧烈、最极端地对抗,而且每一次具体对抗的程度越接近极点,即形成敌—友阵营,其政治性也就越强”。政治对抗的核心是基于利益盘算的权力争夺,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观点,政治的产生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人自己的经济之中,在每一个都是全然的他者的领土上,计算属于自己的朋友,计算他人”。放眼世界,古往今来一切的国族纷争,无一不是“利益计算”的政治问题,而更多的则是强权政治将经济、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非政治问题政治化,以便将权力和利益争夺的触手伸向更远的边界。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交往,本质上是资本在全球的所向披靡和资本挤压之下人性的遁迹潜形。在此功利逻辑的驭驶下,人的交往被置换为资本的交往和政治的角力,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此意义上,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利益的全球化。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此指出:“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看来,这种基于政治利益争夺的交往,是企图以“我心”征服和控制“他心”的“权力欲”,也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无数灾难和痛苦的罪魁祸首。因此,在政治的框架下讨论民心相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客观而言,处于各国政治体制中的人,天然地会带有各自政治文化的烙印与基因,故而彻底的“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所谓“去”,是将国际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对抗因素暂时搁置而求同存异,回归到“人”的本体和本性上来,寻求“人”在最根本意义上的共通性与一致性,通过民心相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自乃至共同的愿景目标。
三、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是最能表达中国人性情和气质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比中国人更在乎人心了。”通过“心”来认知和把握外在世界,是中国人传统的认知和交往方式,也是华夏传播独具的“人文气质”和实现“心传天下”的独特取径。
那么,民心相通之“心”究竟何谓?与前述之“人”相关联,所谓“心”即人之为人的最一般、最普遍的人性,亦即上文斯特劳森所描述的“人类的共同本性”。相比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对“心”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阐释。宋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心之体性也”“至善者性也”。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性”,即是“至善”。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人性善思想,认为心是道德的本源和最高境界,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由此出发,阳明心学建构出一种以“心”为媒介的认知与交往伦理,即“良知”以及进一步的“致良知”:“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比如看见小孩落井自然会生出同情之心,此即谓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在社会交往中将这种人皆本然的同情之心付诸以行,便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下落人心的凝聚之处,而致良知正是求得天下大治与大同的必然取径:“良知之在人心,无关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由上可以看出,以“至善”“天理”“良知”为本体的“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感受性。感受性是经验主体内部呈现出来的一种主观意识活动。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心”之所指,不论是指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作用功能,还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及情感意识,都具有鲜明的感受性特征。也因此,“心”之交互必须通过“同情”和“共感”的非物理方式方能达到相互经验,进而达到共通地理解彼此和天下之事,这正是中国哲学的“感通”之谓。二是道德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主张“人是道德的动物”。阳明心学所谓“至善”即是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亦即“良知”或俗话所说的“道德心”。这是一种人人生而具之的作为“心之本体”的纯善本然。三是本真性。“心”的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辩证逻辑思维,后者的立足点在于思维过程与外界目的的一致性上,这种思维直接导致了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以此为渊薮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扩张主义等西方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而以“心”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并不预设某种功利关系,体现的是人际交往基于“至善”的本真性。四是归一性。宋明心学之祖陆九渊将心归结为“理”:“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王阳明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天理”存于人心而人人皆有,故“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这种万物归心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为“一带一路”乃至国际社会交往的民心相通提供了创生共通意义空间的哲学基础。五是无限性。不论是中国的心学,还是西方的心灵哲学,都认为人的心灵具有“无限性”。这种无限性既指陆九渊所谓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亦指人的心灵具有破除各种限制的能力,它体现为一种针对客观实在的主观意念的解放和自由。在关山阻隔、壁垒重重、地缘政治极为复杂的“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球范围,民心相通所以可能,正源自于人心的无限性特征。
四、相
民心相通语义系统中的“相”,并非毫无意义、可有可无的虚字空词。汉语中作为副词的“相”,首先表达的是双方对等的交互动作与关系,如形影相吊、相敬如宾等。具体到民心相通的命题语境,作为联项的“相”表达的是“民心”与“通”之间的互为关系,彰显的是一种国际社会交往中“从人心到人心”的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性质,它超越了“主体—客体”的关系模式而进入到“主体—主体”的关系模式。“其实,‘主体间性’早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致思取向。”由此生发出民心相通与西方功能主义传播学直线单向、一味追求控制效果的交往范式完全不同的诸多关系特质。
其一,交往主体的平等性。民心相通之“相”意涵着一种双方对等的平等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ichael Blau)用“不平等”(inequal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两个基本参数来描述一般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而这两个参数在丝路沿线庞大的国际社会系统结构中表现十分突出。“一带一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制度、种族、宗教、民族、文化、经济状况、生活惯习等方面的多元分化、发展不均与悬殊差异,但另一方面,民心相通旨在不同主体间“我心”与“他心”的交往与沟通,是对人性的求同存异,在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上又具有异构同质性,由此也在规范意义上决定了民心相通交往主体的平等性特征。
其二,交往关系的互动性。如果对“交往”所对应的英文“communication”进行追溯,双向、互动是其固有的始源含义。只是随着美国社会学经验功能主义的日益坐大,“communication”所表达的主体间积极往来互动的关系意涵,最终被简化缩窄为直线单向的控制模式。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由个别西方大国所主导的霸权思想正是这种控制模式的产物。而基于中国哲学的民心相通中“相”所蕴含的主体间性,恰是对交往之“双向”“互动”始源意义的回归与重申。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这种“注重关系的立场必然不是个人本位的立场,它主张在个人与其他对象结成的关系中,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互以对方为重”。
回到民心相通的现实语境,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这些论述中的“友好往来”“区域合作”“对话”“有来有往”等话语,清晰地表征出民心相通交往实践中双向、交互的关系特征。作为民心相通的高位原则,“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基本方针,也内在地包含着共建主体双向互动、彼此看重的交往理念。
其三,交往手段的中介性。在传播学看来,民心相通之“相”意味着必须通过居于主体间的一定媒介来进行。毋庸置疑,当今全球交往的主要媒介手段依然是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传递工具。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在其《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深刻揭示出,以资本与文化征服为目标的大众传媒非但没有促进国家及其民众间的理想沟通,反而造就了充满霸权色彩的文化帝国主义。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见倾心”“聊表寸心”“一片冰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等,都是一种将“心”作为媒介的话语表达和交往实践。中西方的交往实践反差说明,在世界信息传播秩序长期失衡、全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情势下,唯有通过以“至善”“天理”“良知”为本体的“心”之中介、桥梁与纽带,方能实现国际社会在交往境界上的互利共赢与自由和谐。
五、通
在一般意义上,“通”指的是一种彼此通达而没有阻碍的理想状态。陈崇山先生力主将“传播”(communication,也译为“交往”)译为“传通”,指出“传”是沟通行为,而“通”才是最终目的,如果沟通行为因故未能引起对方共鸣,则是“传”而未“通”。在“一带一路”的交往语境中,通过人与人之间“心”的交互而达致彼此“传通”,正是民心相通的传播归旨。
如前所述,民心相通之“心”指的是生而为人的“至善”“天理”与“良知”。民心相“通”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人人生而有之、人人皆可共之的“道德心”,每个人在其道德良知的本性上是相知、相感、相通的,民心相通之“通”,指的就是交往主体之间以“心”为媒介的同情共感和互融互通。通过这种基于“良知”的道德交往,可以获得人类共同确认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乃至世界观背景,从而达成共通的意义空间。陆九渊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这样一种交往的“心通”境界。
作为归旨“性善”的人类交往行为,民心相通之“心通”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1797年,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第一次使用了“交往德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德性“不仅是对自己的任务,而且是对他人的任务”。民心相通的交往德性既不同于康德基于“绝对命令”的义务伦理,也不同于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伦理,更不同于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反伦理,而是基于感应机制的情感伦理。在唐君毅先生看来,这种情感伦理正是“心通”的关键:“心灵在意义空间中最根本的贯通方式,就是‘我心’与‘他心’之间的交相辉映、互为融摄,以获得意境的超拔提升和无限生命的现实化体现。”
与此相反,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悲观地认为,“人与人的心灵之间不可能相互接触”,因为“互动永远不可能是思想的交融”。事实上,民心相通之“心通”并非彼得斯所无法企及的“思通”,而是如前所述的“感通”,亦即交往主体能够对他者的情感体验“感同身受”,并且能“换位思考”,能够基于人类共通的道德情感从他者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这与现代心理学上所谓的“共情”(empathy)颇多类似。正如吴飞教授所言:“有共情能力的人能够将心比心,能够让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想、去体验、去表达,进而在感情上得以共振,在共情的体悟之中达到理解。”
进一步看,民心相通之“心通”并非交往主体间简单的“共情”便可达致心灵的融通之境,更在于通过“共情”唤起主体“本心”的彼此呼应,在人之为人的道德良知层面获得共鸣。人类交往固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的阻隔,而普遍的人性却是人类共通的一种生理与心理状态,一旦这些最基本的知觉情感激发起生而为人的“至善”“天理”与“良知”,则可因其“心”之无限性而跨越国界、制度、种族和文化的藩篱,在交往主体间引起王阳明所谓“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心灵共鸣。如果以阳明心学观之,这恰是一个交往主体间“致良知”的过程:“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民心相通之“心通”,在其本质上正是交往主体积极践行“致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善果。
六、结语
随着当前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历史“从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历史向普遍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转变”已然成为现实,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伴随这一必然趋势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这些问题在以资本逻辑与零和思维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不但没有减少和减弱,反而日趋严重。2020年暴发并肆虐至今的全球新冠疫情,将国际社会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发并累积的各种深刻矛盾暴露无遗。“面对这些问题,使我们相信,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市场、个人主义去解决,是不可能的。”在此背景下,由中国政府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出的民心相通倡议机制,无疑为国际社会的新型全球化治理提供了一种“中国方案”。作为一项由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重要倡议命题,民心相通的概念要素包蕴着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民”所内含的人的去政治化,“心”的“至善”“天理”与“良知”,“相”的主体间性和以“心”为媒,直至“通”的我心与他心的同情共感和相知相融,这些紧密勾连的概念要素有机组合成一个具有高度意义的语义系统,进而型构出一种人类共通的国际社会交往新范式。这一充满中国哲学智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交往范式,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铺就了民意与社会基础的理念框架,更在终极意义上给当前国际社会严峻的全球化困境提供了迈向天下大同的思想启迪与治理路径。
注释:
① 徐绍华、蔡春玲、李海樱:《从心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对策思路》,《创新》,2017年第2期,第98页。
② 郭宪纲、姜志达:《“民心相通”:认知误区与推进思路——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之思想认识》,《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期,第2页。
③ 甄巍然、刘洪亮:《“民心相通”:基于文化交往的共同体图景——“一带一路”中文化的认同的困境与破解》,《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8页。
④⑤ 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298页。
⑥ [英]伯特兰·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4页。
⑦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⑧ [美]里奇:《传播概念译丛》,伍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⑨ 金正昆:《外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