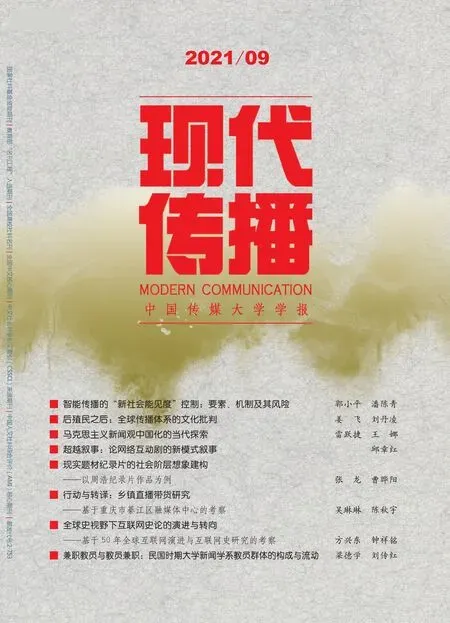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
■ 姜 飞 刘丹凌
一、导言与问题意识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提出和践行过程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信息传播媒介(medium)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中将发挥重大作用,朝向我国两大社科理论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实现历史传承的有机性、发展的和谐性;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建构和传播,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实现彼此尊重、合作共处。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复兴中华文化、重申民族自信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也不止是重塑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软实力的经济学问题,更是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与文化格局中深刻反思和战略应对文化霸权、提出中国传播观、更新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球文化传播秩序的努力,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传播意义上的同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良性变革的传播支撑和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综合性问题。
正如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Bernard Voyenne)所说,“新闻业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是一对孪生姐妹”①,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的背后是全球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更后面是近300年的殖民主义体系作为这些霸权的滥觞。“后殖民”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中,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国家的尴尬处境②,并似乎开启了后殖民之后全球健康发展导向下的反思性重建进程。在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格瑞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1989年出版的合著《逆写帝国》(TheEmpireWritesBack)中,“后殖民”涵盖了“自殖民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③,指向一种“话语群组”④。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梳理了“后殖民”的三种用法:一是描述曾经是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包括第三世界以及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与第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移居者的殖民地;二是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全球状况;三是描述论及上述状况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通过这些状况产生的认识论和精神的方向来传达的。⑤
从“后殖民”术语的使用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最初的历史分期演化为一种“理论与批判的场域”⑥,包含着视点的拓展——从空间视点(领土、民族)、时间视点(殖民与后殖民时期)、主体视点(殖民者、被殖民者)到话语视点(话语表达、传播机制,知识与意义生产方式)⑦,以及基于这些视点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之反思与批判的深入。因而,“后殖民”常常被冠以“主义”和“批评”之类的后缀,用以观察、审视和叩问种族、帝国、移民和族性与文化成果的相互关联⑧,该概念自1978年提出至传播到全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鞭挞,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
但是,迄今作为极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后殖民研究大多沉淀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当下资本收益带来的诱惑已模糊了现代人的理智边界,新殖民(文化)以及西方经济的“全球化”以不可抵御的力量阻挡了人们回顾的眼神,从形式上努力破解历史经济锁链的努力不断在认识上自我局限的墙壁前碰撞,不断在传播话语权设置的陷阱中跌倒。后殖民批评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传播维度的价值日益凸显,全球文化现状和后果与资本主义的传播体系、传播机制之间的重要关系亟需得到充分地挖掘和阐释,正如Raka shome、Radha S.Hegde、Shanti Kuma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研究中的传播维度一直比较缺失,传播研究中的后殖民议题也同样缺失⑨。这推动着更多研究者深入思考,后殖民理论如何深刻揭示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是如何在殖民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建立和演化的,而这种传播体系和格局又是如何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滋长、蔓延和肆虐提供温床和通道的。
纵观历史,传统和现代传播体系的演进从萌芽到发展,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史以及理念、格局的变迁有着广泛深入的互动性、互构性特征,这体现在殖民时期和新殖民⑩时期两个历史阶段:
二、从殖民到新殖民:早期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的历史性建构
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扩张基调下,随着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和平台的发展,界定了全球传播的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实现了早期殖民主义和国际传播体系的互构。
15世纪到“二战”结束是殖民传播体系的形成时期,它确立了以政治功能为核心的基本架构,伴随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占领、侵略和宰治。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体系,它紧跟殖民扩张的步伐和技术变迁的节奏,逐步拓展传播范围、传播内容和传播形态,从而建构和完善起来。而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也伴随着帝国霸权的确立,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征服美洲》(ConquestofAmerica)中所分析的,对交流手段的掌控,是任何殖民视野获得权力的要素。因为,自由交换原则必须支配信息和传输工具,信息的自由流动仅仅是商品和劳务自由流动的必然结果。
交通、商品和语言的传播属性被深度开发,奠定了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的早期殖民传播结构。帝国势力的扩张和较量更多取决于交通技术的发展,运输条件的改善为殖民者的地理空间开拓奠定了基础,保障了物资与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同时也奠定了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的早期殖民传播结构。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所言,在担负全球使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理性建构的过程中,正是铁路公司带来了管理资本主义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两种“基础性的材料”。铁路延伸到哪里,人和语言就延伸到哪里,在对非洲的殖民过程中,葡萄牙人不仅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向黑人译员教授葡萄牙语;法国的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在北美远征多次,施展才能与土著人民进行人际接触;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作坊,资本家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学校,教育、培训现代产业工人以及服膺于殖民管理和统治的“本土精英”。这些早期的殖民传播活动契合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将理性主义、商品经济、自由市场连同“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殖民征服逻辑一起打包倾销到被侵略和占领的属地,为直接的殖民贸易和殖民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即,印刷术将交通、商品和语言的传播属性予以整合,开启了殖民大众传播的新时代。1455年,德国人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zur Laden zum Gutenberg)在美因茨(Mainz)发明活字印刷术,将人类载入书面出版时代。尽管印刷术更大的威力显现于两个世纪之后,但它开启的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承新格局却逐渐明朗起来。正因为如此,殖民者也将书面出版纳入传播的重要范畴,以巩固殖民统治。葡萄牙王国是最早意识到利用媒介巩固殖民地统治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它在出口货物的轮船上同时装载大量书籍运往各地,还在所属殖民地上自办印刷媒体,最早的实践是1557年在印度的果阿和1588年在中国的澳门创办的印刷媒体。其他欧洲强国也利用新技术和印刷书籍加强亚洲的殖民统治。1638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引入印刷厂和出版社,用于印刷殖民地的法律法规和宗教书籍等,其目的主要是加强殖民地自上而下严格管控的信息发布模式,服务于殖民统治。印刷术在殖民地属于稀有的、昂贵的奢侈品,仅限于为殖民地统治者、宗教人士和社会精英服务,藉由信息传播不对称的张力制造实质上的控制与被控制,成为殖民控制体系的龙骨支撑。
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直接介入战争宣传甚至成为殖民战争发动机。印刷业的演进促进了近代报刊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殖民传播的路径和范围,亚非拉广阔的殖民土壤孕育了数目繁多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西班牙文报刊和葡萄牙文报刊,其中既有传教士报刊,亦有宗主国主导的殖民地本土报刊。以中国为例,随侵略者一起闯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纪德(Samuel Kidd)等人快速引入西方印刷技术,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等第一批近代华文报刊,宣传基督教教义、评论时事、散播域外知识。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突破了封建新闻传播在内容上的限制,将科技知识、民主模式和新闻自由等信息强力输入中国。这些明显带有侵略色彩的活动客观上将封建统治撕开了裂口……”在科技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广大殖民地也很快孕育了一批“本土”报刊。其中,被欧洲中心国家主导的殖民地本土报刊在维系移民与宗主国联系、实施语言和文化控制、重构殖民地社会和黏合多元族群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欧洲的征服种族们预计……那些在学校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成长过程中读他们的图书和报纸,吸收了他们观点的本地孩子,会从他们的角度看待生活,这将会使他们政府的问题大大简化”。例如,西属美洲从1737年起,除再版《马德里公报》和墨西哥城与利马的公报外,还增加了《利马文学经济商务日报》(后成为《秘鲁信使报》)、《信使导报》、《文化入门》等报刊,使得来自欧洲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得以在殖民地广泛散播、接受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负责提供图片,我负责提供战争”的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式“传奇”将这种传播与政治利益深度媾和的神话呈现得更加充分;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对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战时宣传技巧的研究,则从理性上阐释清楚了报刊等传播手段对于殖民国家塑造正义形象、争取盟友和舆论支持、实施文化控制、妖魔化敌对势力、美化战争,继而为殖民利益争夺、殖民成果保驾护航的重要价值。
在没有电波的时代,基于印刷术革命的文艺书籍也曾“无远弗届”地延长强大的殖民传播体系。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海上远征的拓展,欧洲列强的魔爪伸向更遥远的疆域,以旅行游记为基础的文艺创作成为殖民传播的重要内容。葡萄牙诗人卡蒙斯(LuísVaz de Cam es)1572年写就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将欧洲文化与东方经验熔为一炉;英国人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1697年写就的游记《环球旅行》是笛福(DanielDefoe)著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原型,这部小说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旅行文学也成为17世纪意大利的时尚,维也纳成立了自然奇观学院,出版了众多旅行书籍和博物学家的著作。1771年,法国人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将航海家的经验和科学结合,出版了趣味盎然的《环球航行》。这些以旅行见闻为基础的游记、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既没有杀戮的血腥,亦没有强取豪夺的野蛮,更没有受虐者的抗拒和挣扎;殖民主义被客观化为有关探险、科考和开拓的英雄传奇,而荒蛮的东方被塑造为静待发现的蒙昧之地,神秘的东方经验则被展演为凝视的对象和景观。这些作品暗合了启蒙主义对“自然”和“理性”的尊崇,就像发现来自遥远国度的“善良的野人”一样,鲁滨逊、星期五等满足了西方人对发现世界的期待。围绕帝国的创造亦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文学主潮——“英法文化的几乎每个角落里,我们都可以见到帝国事实的种种暗示”。
全球邮政体系本质上延伸了殖民传播体系的触角。1840年英国实施邮政改革,统一全国邮资;1874年,世界邮政大会召开,统一世界邮资标准,并对尊重通信秘密的原则给予确认;1875年,世界邮政协会在伯尔尼(瑞士首都)成立。邮政系统随着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变革成为信息交换的重要纽带,方便了殖民帝国对内对外的信息交流和贸易往来,巩固了殖民帝国的地位。因此,英、法、美等国家都对国际邮政业务实施津贴制度,促进其在殖民贸易中的作用。
海底电缆是全球传播格局中基础设施革命的典型代表,电报一出现就融入殖民工具序列,并成为殖民传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节点。海底电缆将以殖民宗主国为中心的传播体系乃至世界格局首次具象化地链接成体系,建构并呈现在世人面前。1838年,第一条商业电报线路在英国铺设完毕;1851年,公共电报业务在英国开通,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邮政汇票体系,同年,连接英国与法国的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正式开通;从1851年到1868年的十余年间,海底电报网络的铺设遍及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到了1870年代,电报线路在亚洲各主要国家开通,一个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网络开始形成,并且不断蔓延,这也成为维多利亚霸权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由于铺设电缆的投入巨大,广大殖民地的电报电缆所有权掌握在宗主国手中。对于英国等殖民国家而言,电报电缆的架通大大缩短了殖民地官府和宗主国之间联系和交流的时间,不仅为殖民贸易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而且对强化殖民控制和管理大有裨益。连接战场、参谋部与宗主国的“直通电报”更是展露了它在军事行动和新闻传递等方面的应用。1898年,法崤达危机爆发,这是英、法两大殖民列强在非洲大陆的争夺焦点,法国皇帝以布拉柴维尔为起点的扩张计划与英国在非洲东南部的扩张计划相冲突。巴黎不得不依赖它对手的传播网络,即向伦敦请示批准使用英国基奇纳将军的船和海底电缆来和刚刚占领法崤达的法国马尔尚船长联系。
现代通讯社的出现实质是信息全流域的争夺,从信息流动的上游根本性瓜分、垄断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播。殖民活动对于商业信息和国际新闻的需求也刺激了通讯社的发展。1835年,法国的哈瓦斯(Havas)通讯社成立;1849年,德国的沃尔夫(Wolff)通讯社成立;1851年,英国路透社(Reuters)成立。三大通讯社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服务资本扩张和殖民争夺的国际新闻竞争,并于1870年签署协议,促生“联环同盟”(Ring Combination),将世界信息市场一分为三,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新闻信息秩序开始形成。1848年成立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随后也卷入这场激烈的国际新闻争战,并于一战后迅速崛起为世界性的通讯社。可以说,通讯社奠定了世界信息秩序的上中下游格局,自通讯社诞生开始至20世纪开启之前,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全球传播的第一次浪潮,是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基于殖民掠夺和殖民控制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初步成形;彼时,美国正努力跻身于这样的位列,小心翼翼但坚定有力地学习和融入殖民传播体系。
电影技术通过虚拟现实/超现实的建构和魅力呈现,成为殖民传播体系的最好文化“帮办”。以“好莱坞”电影生产体系为代表,刷新、规制、强化了以往书、报、刊所建构的文化想象,并与书报刊、广播、通讯社以及后来的电视等知识、信息生产体系互为表里,编织“现代社会”的总体想象、话语体系和牢固的认知生产体系。截至一战前夕,1907年成立的法国电影公司百代影业(Pathe)一直垄断欧洲电影市场,并将发行网络延展至土耳其、美国和巴西等地。1909年至1913年间,独立制片人推动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高速发展,好莱坞从此成为世界的“梦工场”,不仅主导了全球的形象生产,盘踞了家用影碟、电视和有线市场,而且凭借娱乐、音乐、时尚、广告等的强势输出,将“美国主义”传播至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传播至新崛起的第二世界以及逐渐没落的欧洲国家。正如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所揭示的那样,“在旧的政治边界内,欧洲是在语言及其保存的记忆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被组织起来的”,这个涵盖传教、教育、书报刊、通讯社、电报、广播、电话、电影等在内的多维殖民传播体系为殖民主义提供了语言、信息和文化组织的基础。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广播和电视成为殖民传播的新阵地,“信息传播”获得史无前例的投入和关注,开启了全球传播的第二次浪潮,奠定了现代传播学的基础。从诞生伊始,广播就将宣传作为自身发展的一部分,利用其威力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因此,无线电技术的制度化开发和国际化利用也成为大英帝国乃至德国等其他欧洲殖民国家争夺的新焦点。1906年,国际无线电报联盟在英德的倡导下建立;1912年,各国于伦敦签署的协议确定了“先到者先得”的频率分配办法,使资本和技术雄厚的殖民国家在有限的频谱争夺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信息逆差,表明传播领域的“不平等交换”这种生产体制间的差距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而扩大。荷兰是世界上最早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它从1927年开始启用荷兰语向海外殖民地东印度等进行广播,不久又增加了英语和印尼语进行广播。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殖民国家也不甘落后,相继开办国际广播,一方面加强对殖民地的同化和思想钳制,另一方面开展与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舆论战。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纳粹”团体更是积极利用国际广播资源进行法西斯宣传和种族优劣论的宣传,博取国内外公众认同。
对“宣传战”“心理战”的青睐从“一战”一直延续到“二战”,因此,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和资源争夺,也是传媒角力、传播竞争。两次战争期间,参战国广泛调用传单、报刊、广播、电影等传播资源鼓舞士气、美化战争、妖魔化敌方,并通过新闻审查制度、新闻法规规范、情报系统操控等机制实施传播控制,维护国家利益。法西斯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信条揭示了这场“媒体大战”的实质——“新闻是战争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列强在传播网络的助力下,从根本上确立了殖民话语的霸权地位,生产了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正是这种认知暴力巩固了帝国主义的“君上的自我”(sovereign self)观念,诱导本土居民在自我主体建构中与之共谋,将“属下”变成沉默和喑哑的“他者”,尽管从客观上说,它也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知识、理性精神和民主意识广为散播,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广大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觉醒。但其根本仍然是在为资本扩张保驾护航:首先,通过经济及相关信息的传播,保证殖民贸易的顺利进行和拓展;其次,通过科技及知识的传播,提升劳动力文化素养,保障殖民生产(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殖民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最后,通过资本主义价值谱系和殖民理念的传播开展文化政治动员,规训被殖民者和被统治阶层,改造殖民地社会以适应全球市场经济需求。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殖民传播体系为16世纪到19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信息和文化环境;同时,更不可小觑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广播资源的掠夺、交战国的信息传播体系布局,实现了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国际传播格局的最大转型——正是藉由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国际传播影响力从英法德等传统殖民强国向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接力:这是全球传播的第二次浪潮,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视这些今天被称为“传统媒体”的平台和介质成就了美国文化的全球成功传播(“美国梦”)、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格局的转型、美国主导的话语权/话语霸权的顺利交接。尤其是从诸多领域和视角考察“马歇尔计划”的时候,经常被遮蔽但绝难被忽略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精心设计的国际传播布局的支撑,该计划的实施将是举步维艰的,甚至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本身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支撑之下获得成功的,同时,其最大的成功也是美国对国际传播格局的重组,奠定了其之后半个世纪的强大话语权。正是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支撑下,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接受甚至拥抱了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和传媒体系,美国的媒体得以在全球设立分支,美国内容得以在全球畅通传播,无论是从国际舆论还是社会心理上,都有效地护航了马歇尔的经济和政治计划,这是尤其值得当今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的。
两次全球传播浪潮,见证了殖民传播体系的建制以及变迁。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直接奴役、强取豪夺,对殖民国家除领土、资源和人力的奴役之外,对信息、知识等深层权力的垄断和共谋控制,全球传播体制既是第一次殖民时期的结果,其巨大成就更是为第二次文化殖民打开了通道。传播体制与殖民野心的文化共谋,随着广播和电视等强大影响力媒介的诞生,逐渐机制化,甚而从后台或者平行路线,走到前台,演变为国家传播战略——这是我们当今看待和处置任何有关媒介、传播问题的认识出发点。
三、从新殖民到后殖民:晚期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的现代性建构
殖民和传播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历史性合流,建构了美国为主导的新殖民主义传播体系,并在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支撑下实现传播体制的更新升级,在2001年“9·11”事件触发下开启了第三次的全球传播格局重组浪潮。
“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相继获得民族革命的胜利,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领土殖民的历史终结。然而,直接殖民的终结并不代表以“殖民”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土崩瓦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后期,是不同于以前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意思;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k Jameson)进一步将“晚期资本主义”从文化上进行阐释,认为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践行着新的殖民政策,文化成为这副殖民面孔最曼妙的矫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以文化全球化为基本战略的新殖民路径,经济与社会的普遍联系是这种全球化运动的联接点,传播机器通过不断地扩大人员、物质与象征财富的流动来加速逐渐扩大的整体对社会的融合,并且不停地移动物质、知识和精神的边界,文化渗透、价值同化和思想同步成为该殖民路径的新内核。
殖民和传播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历史性合流,建构了新的殖民主义传播体系。美国从他的欧洲老师那里出师,不仅全盘继承了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一脉相承的机制,而且建构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文明—文化话语世界阐释体制。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也从赤裸的物质层面转向隐匿的精神层面,消费意识形态承担起全球“启蒙”的新角色,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所谓“进步、发展”带来的好处,彷佛两三百年前坚船利炮式的侵略和屠戮从未发生过。当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附魂于文化产品,并借助消费侵入日常生活和社会机理,服膺于资本逐利本性的“消费”也就摇身变为最高意识形态,殖民地、第三世界或者所谓新兴国家、后发国家从发展被外力束缚、资源被强制开发、人民被奴役转到发展被纳入西方全球化的轨道,资源和人民的精神也被纳入西方的某个生产线,进入了自虐的然而看起来却是自慰的循环中,以至“被殖民者永远不知道殖民者什么时候把他们看作什么东西,是完全拥有自我的人,或仅仅是物体”。这种新殖民主义亦被称为后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它是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延伸,即葛兰西所谓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合法化的过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传播资本的崛起是新殖民传播体系建构成功,并与老牌殖民主义跨越时空实现精神对接,进而建构新的全球传播主导的资本主义本性的显赫标志。尽管不是起点,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全面商业化仍然是“二战”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项举世瞩目的变化,“大企业已经大规模接管了国内的传播机构”,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出版、唱片、动漫、游戏、通信等产业共同构筑了资本主义信息文化工业帝国。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终端设备等领域,连同以新闻、娱乐、时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场域、经济增值的生长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了全球主要的媒体资源和信息文化服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影像和信息产品通常是美国生产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新闻和流行文化产品”。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早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曾阐明,文化工业不仅是操控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逻辑,服务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传播不再是单纯依附于资本殖民扩张的手段,其自身发展逻辑也逐渐呈现“去工具论”色彩,也即是说,传播资本成为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资本殖民扩张之组织架构,甚至殖民扩张本身,建构了强大的主体性。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是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逻辑起点,维持殖民扩张的既得利益、开拓全球资本市场是其旨归。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传播体系随之彰显出强烈的“后(殖民)”系特征,以信息文化工业为主体(新媒体、融媒体)、以国家战略传播为辅助、以重大事件和人物为抓手,以新闻信息传播为主干,以旅游、教育及科研交流为延长线的新殖民传播体系日臻完善。从传统的殖民方式转换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以生产为内核的经济扩张过渡到以消费为内核的经济扩张,从直接性的掠夺转向间接性的需求创造,从文化强制转向文化认同——藉由传播实现广袤地域的全球治理目标。
资本主义信息文化工业(主要是美国)延续着意识形态征战和制造认同的神圣使命。其创造的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不仅以全球化之名将“美国主义”推行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以瓦解欧洲生活并使之美国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殖民”。叶维廉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中说:“从弱化原住民历史、文化意识到原住民对殖民者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同化,人性工具化的文化工业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西方人性工具化的文化工业之输入第三世界的底线,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重新布置,利用合作的说词,做市场全球性的扩张……”政治学家凯瑟琳·萨利卡克斯(Catherine Sally Cox)认为,多种(地区的、国家的、全球的)文化地域范围的存在并不表明它们的力量平等,因为受美国支配的全球文化和传媒产业已经培养全世界的观众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传媒认知模式:“认可音乐剧的规范,盼望看到情景喜剧的结局,将新闻理解为精英阶层提供的信息,接受与那些熟悉的形式有关的新的娱乐和信息形式。”而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绝不仅是一种认识模式的培养,更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运作,经由霸权想象、霸权认定、霸权实施三个步骤,它完成了对弱势文化的非线性重组。在霸权想象阶段,强势文化中介媒介,把资本主义的各种象征符码植入弱势群体,促发弱势文化群体的想象力,使他们以这些符码为源泉构筑想象中的西方帝国(特别是美国);当文化产品由渠道输入,当部分弱势群体由渠道直接接触、感受所谓的强势文化时,原先的想象与现实即进行简单的置换,巨大的反差促使他们不仅认定且拥抱这种强势文化,把“自我”边缘化甚至抛弃;所谓的霸权实施就是由这些人,回到弱势群体之中,即以“舆论领袖”的地位激发新一轮的霸权想象……当所有这一切都已构筑完毕时,则是西方媒体和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之时,即是霸权文化的实施之时。这种文化霸权运作的实质是将资本的逻辑、自由市场的逻辑、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连同美国梦的愿景包装成一种普世价值,一种世界大同的基础,传播至全球各个角落,内化为其他民族国家人民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和道德意识。用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Herman)的话说:“至少受到部分遏制的商业化全球浪潮到底体现着‘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文化依赖’?——主要的入侵是模式的灌输。其次重要的是商业网的发展、巩固和集中以及和全球体系的日益融合,再加上这些进程逐渐对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主要的入侵决定了要走的道路,并且把有关国家带入了主要大国的利益轨道。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形式,它已经取代了旧的、粗野的和过时的殖民方式。”
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开启了信息资本主义和电子殖民时代。丹·席勒(Dan Schiller)在《信息拜物教》中深刻地研究了以信息商品化为最新前沿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剖析了“计算机革命”的动因、机制、媒体整合的历史渊源,商品化过程在电信、广告、卫星电视、移动电话等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加速、深化和全球延伸等重要问题,揭开了“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化衰退”的神秘面纱。在他看来,数字信息技术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资本主义核心的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网络化的政治经济中不断发展和加速。按照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观点:“在数字时代,主要的传播组织形式由全球化的多媒体商业网络占据,它们使用不同的传播媒介但又整合在同一家大集团内,在一个越来越由寡头垄断的商业环境中,竞争力得以提升。不仅如此,横向传播网络与单向的传统传播形式(如电视、广播、出版社)日益融合,由此形成一个使用数字技术的混合型传播体系,从而由统一的普通超文本演变为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我的文本’(mytext)。”这显然不仅是资本化传播权力日渐集中、商品化传播产品愈加丰富、殖民化传播体系日臻完善的问题,其中还隐藏着资本固有的剥削和拓展逻辑在个体层面的有效延伸——新兴信息传播技术藉由日新月异的传播终端,实现了大众传播最后一公里的突破:既有传播技术升级推动的传播终端将信息推送到手机和指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动态个性化传播机制、零散时间的充分填补、兴趣和眼球经济的传播效应助推下实现的信息入耳、入脑的最后一公里。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新兴的传播技术体系下,不断拓展的殖民传播体系将资本家用于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资金和时间都节省下来,绝对性地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传播体系以海量信息供应激发和满足了劳动力信息欲望和消除部分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大的信息不确定性和欲望空间,推动着劳动力在法定的工作时间之外的任何空隙和碎片时间去消费信息、消费文化、消费教育,从而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在这样的总体形势背景下,工业资本家将信息产业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榨取,并强化了控制。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将人群吸引到“文化石舫”,像地铁里手机消费的低头一族将自我完全交托窗外的呼啸。主体在信息时代走向彻底异化——并且是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这是“殖民”的另外一种状态,一条主体性溃败的不归路。
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随着传播新技术和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度调整,也为新殖民传播体系图景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支点。美国的国家宣传体系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型于“二战”结束到“冷战”之前,成熟于千禧年之后,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即确保并进一步伸张其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部署和制度安排。1917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权主导的“制度化的宣传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先后成立“新闻协调署”(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精确资料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美国之音(VOA)、“战时新闻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战略事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ec)、“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署”(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等机构,并设立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传播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全面开展对内对外的宣传。1947年至1953年,美国政府依照《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The U.S.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等,先后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新闻署(USIA),为美国的战略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2001年“9.11”事件爆发之后,以美国国防部为主的势力推动由战略传播概念统摄的美国宣传机制重构;2003年11月,小布什总统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从机制上再次恢复了国际传播布局,抑或说是外宣职能;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提出包含“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国际广播”(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和信息/心理运作(IO/PSYOP)为基本构架,以认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为目标,以国内外受众(Domestic & Foreign audience)为对象的国家战略传播系统;2010年3月和2012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两次向国会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架构》(NationalFrameworkforStrategicCommunications),系统阐述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性质、目的和实施体系,标志着美国传播体系的战略构想日渐清晰、国家战略传播运作日渐成熟,内外传播活动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形成了全面整合各方信息和舆论资源的机制。“全球传播”“战略传播”等概念对“国际传播”的覆庇和替代,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家传播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不过是在传播生态环境变迁情境下所做的调整和适应,即从以民间机构和个体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向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主体、主导的国际传播转变,是被西方妖魔化的“宣传”策略借着新生术语上演的一出修辞还魂戏法。从“冷战”“越战”到两次海湾战争,再到新近的“反恐”大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展示着利用“信息战”宣传“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和征战的野心和能力。
传播教育及科研交流是新殖民传播体系的重要延长线。无论是以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为标杆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及其东方之旅,还是以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等为代表的东方学教育、研究和交流,都传承、浸染着不同程度的“东方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传播学理论及假设有三个重要的现实源头:其一是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诉求,“信息自由流动”被视为商品交换和自由市场的基础,这决定了其经济导向;其二是战时宣传经验和以大选为代表的政治实践,新闻传播及文化产品被视为树立良好形象、操控舆论阵地的重要手段,这决定了其行政导向;其三是在传播格局已经确立上中下游地位的前提下,“信息自由流动”成为话语权实施的护航,换句话说,话语权成为有权力掌控传播媒介、传播平台内容的主导者的话语权。美国传播学也因而确定了以效果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而施拉姆的《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罗杰斯(E.M.Rogers)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等看似系统和客观的历史书写不过是基于价值观的选择和建构,目的正是论证和维护他们所开创的这种实证主义范式。在勒纳(Daniel Lerner)、施拉姆所倡导的“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现代化理论的传播学变体推动下,美国传播学走过了一个迅速“世界化”的过程,一方面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传播教育和研究的“主流范式”,另一方面也被寄予拉动经济社会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热望。这无疑再次印证了东方学当中关于“西方”优越性的论断。而始于19世纪初叶的东方学研究持续生产着关于“东方”的想象,甚至生产着关于“东方”想象的再想象,“与所有那些被赋予诸如落后、堕落、不开化和迟缓这些名称的民族一样,东方是在一个生物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谕结构框架中被加以审视的。因此,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犯罪、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当它在新殖民时期逐渐成为人文研究的显学并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学科建制之后,这种“想象的文化地理学”亦成为更多西方学者、西方民众,以及以教育、交流之名被纳入其中的东方学者、东方民众笃信的“事实”,体现了西方知识以权力意志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努力。
总体来说,新殖民传播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助推了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经济扩张和政治影响,也猝不及防地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抑或被理论家们更中性地称为“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 Country)的这些新生但贫弱的国家拽入全球化的利益轨道;“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将有关西方的文明神话、现代化想象和发展愿景散播得更远、更广、更光芒四射,并在殖民主体和殖民客体的“双向互动”和“密切配合”中,完成了政治同化、经济控制和文化收编,以全球化、“文化化”之名打乱了广大亚、非、中南美洲文明的自我演进历程,使西方与东方的中心—边缘关系更加固化,西方的支配和霸权地位更加稳固。
四、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格局批判
对传播以及传播过程的认识上升到人类知识生产及其影响的理论层面,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实质就是信息殖民。“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62)的“后工业社会”、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93)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从不同维度说明了“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物质劳动、生产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政治形态被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谓的信息方式所重新结构。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对传播与帝国事业的关系进行了直接论述,通过对美国大众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全面剖析,他批判性地揭示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信息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卡斯特则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秘密: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相比,网络社会形成了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形态,其核心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力及对获利能力的强调,摆脱了工业社会单一的生产力增长方式,其结果是金融、贸易、科技、生产、消费在全球范围的重新结构和广泛拓展,这是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相契合的。丹·席勒继承了赫伯特·席勒的衣钵,关注媒介—文化与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的双向建构作用,并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下对这种作用进行了具象化阐释。他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从至关重要且内在关联的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首先,无法抵御的新自由主义或曰市场驱动型政策影响和决定了电子传播体系及它们对跨国公司的赋权,其结果是现存社会差距的扩大;其次,赛博空间为全球范围内消费主义的培养和深化提供了独特有效的工具,尤其服膺于既得利益集团;最后,数字传播资本主义已经接管了教育,使其成为所有权市场逻辑的宠儿。这恰好回应了利奥塔(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中的预见:“有一天,民族—国家将会致力于信息的控制,正如他们曾经致力于控制领土,及至后来为了获取和利用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展开争夺一样。”
作为新殖民传播体系主体的信息文化工业不仅自身践行着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逻辑,同时也助推其他资本形态的增殖和扩张,以一种商业动员和组织的面貌重新着陆:一方面,信息文化工业使得信息商品化,自由流通的信息商品既是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润滑剂,更是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信息来源,而在一个信息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之中,信息与知识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本和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信息文化工业不仅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营销的前沿阵地,通过商品、服务和形象广告增益企业的“文化资本”;并且在“文化的循环”和“符号的幻象”中不断生产、刺激新的消费欲望,为夸耀性的消费提供象征价值、想象性经验和一种理当如此的氛围,构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并将之演绎为世界性愿景。资本与文化的合谋,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力量,而安东尼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断言,跨国公司势力的扩张传播共同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
从殖民传播体系到新殖民传播体系的演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了全球传播格局的形成和调适,在此过程中,传播与殖民的耦合关系也充分彰显于经由传播网络达成的信息/文化流通和经由市场网络达成的商品流通的耦合关系当中。
该传播格局并非总是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那样平等、自由和普适,而是体现出下述特征:第一,从理念指引来看,它以美国传播学为主导,注重传播的“效果”和“功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第二,从基础构架来看,它依赖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平台的更新,而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先进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不仅牢牢地掌控在微软、苹果、高通、Alphabet(谷歌母公司)、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全球性媒体、文化或通信公司/平台手中,而且其设计逻辑本身就是扩张的、快速迭代的,体现了资本的内在逻辑和全球野心;第三,从范围和布局来看,它跨越了国界、消弭了时空阻隔,将全球的信息和文化领导权集中于实力雄厚的跨国媒体集团,将信息、文化和服务源源不断地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占据甚至超越国家的话语权;第四,从权力关系来看,它构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后者陷于对传播制度、传播技术、传播内容、传播资本、广告,以及传播评判标准等的多重依赖之中,因而丧失了内生的发展动力;第五,从经济和文化后果来看,在对劳动分工和世界工厂的组织中,它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并将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兜售到世界各地;第六,从社会生产角色系列来看,传播体系实现了华丽的转型,从依附变成主导。从早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奔跑着传递信息的奴隶、威尼斯码头上出售航期信息的二道贩子、美西战争期间的黄色新闻散播者和战争“制造”者以及便士报时代以来信息和娱乐的传递者等角色,转化为社会权力的“无冕之王”、政治权力的“第四等级”;由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空气,转变成了空气本身——还是空气,但是,却是须臾不可少的空气,是家庭的“第五壁”、政治的操盘手、经济发展所需资源中最上游的信息资源;当学生毕业从墙头跳向社会海洋之后,就被传播体系所接管,甚至,在新兴融媒体技术条件下,大众传播早已跨越教育围墙,消弭了知识传播和大众信息传播的边界,在主体性的培育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宰制作用。
可以说,“殖民—殖民主义”与“传播—传播体系”两大概念群的关系再现,实质性地反映了广义人类发展思想史与传播思想史的汇流乃至重构,他们同属广义“文化”概念群且都在推动文化变迁上发力,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化变迁”的动态视野介入,来再现或重构这个断面。全面、恰切地把握殖民传播体系,首先需要从思想史的视野了解“殖民”和“传播”的耦合与体系化的过程;其次,同时兼顾殖民视野下的传播与传播视野下的殖民两条思考路径;最后,认真审视殖民体系和传播体系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历史性的合流以及变异。这也是理解全球传播格局,把握殖民传播的文化逻辑及其后果的密匙。
注释:
① [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丁雪英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② 转引自[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④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⑤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⑥ 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⑧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⑨ Raka shome and Radha S.Hegde.PostcolonialApproachestoCommunication:ChartingtheTerrain,EngagingtheIntersections.Communication Theory,vol.12,no.3,2002.p.249;Shanti Kumar.Media,Communication,andPostcolonialTheory.in Robert S.Fortner & P.Mark Fackler,ed.,TheHandbookofMediaandMassCommunicationTheory.West Sussex:Wiley Blackwell.2014.p.380.
⑩ 有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为后殖民时期,本文从广义上将后殖民视为一种“理论与批判的场域”,为避免混淆,我们将历史分期中的后殖民阶段称为“新殖民时期”。
——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