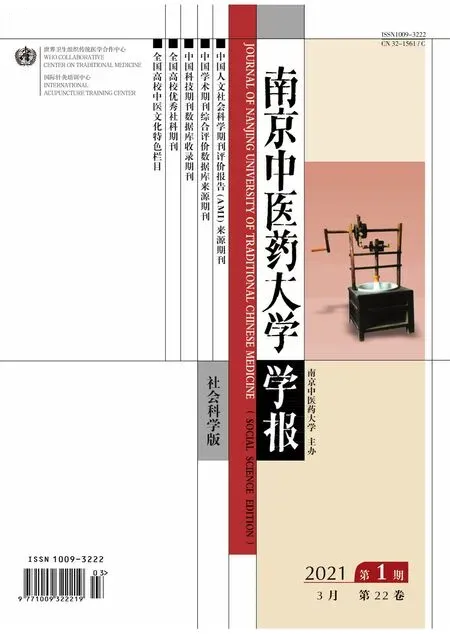北宋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李艳杰,刘宏岩
(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经学是儒学的学术主体,是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随着儒家影响的扩大,经学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学术的核心部分。经历了中唐的社会变革,经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变化,涌现了批判怀疑的思潮,在治学方法上出现了抛弃章句训诂,回归经典、溯本求源的倾向。北宋时期的经学上承隋唐,下启南宋元明清,是汉唐经学的终结与宋明理学开启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段时期也是古代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受经学变化的影响,医学研究在经典认识、古医籍校勘及注释研究等方面相较于前代都有所改变。一部分儒士也在此影响下积极从事医学研究,进一步促进了经学与医理研究的融合。
1 北宋经学的发展与变化
唐末宋初的儒者认为,藩镇割据、朝政腐败、皇权旁落等唐朝灭亡原因源自于唐人“抛弃夫子之道”。宋代统治者效仿前汉,以儒礼治国,因此儒学重获思想正统,经学再次成为当时的官学与显学。
针对前朝儒学发展的状况,宋儒认为,唐代经学偏囿于注疏与训诂[1],长期纠结于学术门户之争,无益于经世济用。他们认同啖助、孙复的研究方法,即抛开汉唐注疏,采纳各家论述,发挥己见阐述儒经之“微言大义”。宋代经学研究的变化,刺激与培养了宋儒的批判怀疑思维,逐渐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作代述”的治学特点。宋儒研究重点向古代经典的回归促进了儒学经典学术地位的提升,“崇尚经典”“典籍中心主义”成为宋代经学的核心思想[2]。
2 经学影响下对经典医籍的重视
在北宋经学地位变化的影响下,《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著作受到了宋人前所未有的重视。宋人视秦汉以前出现的医学著作为经典,若是作者涉及神农、黄帝等人文始祖,更是被视为理论的本源[3],并将修正与保留古代医籍内容作为医著编纂的核心工作。北宋校正医书局的儒臣认为,《内经》是上古圣人的著作,讲论的不仅仅是医学,也暗含着和谐天地国运的“圣王之道”。于是,从仁宗天圣四年(1026)至徽宗政和八年(1118),北宋政府先后5次[4]对《内经》等进行校勘整理,以恢复这部经典的全貌;《神农本草经》同样受到了北宋政府的关注。在修订《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大观本草》等国家药典时,编撰者通过各种方式(如阴阳文)将《神农本草经》的原文予以保留并清晰地展示给读者。对《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医籍的整理校勘活动,体现了宋廷对这些经典医籍的重视与推崇。
北宋官办医学教育的创立也是经典医籍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籍一经注释刊行,很快就成为官办医学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且宋代官办医学教育比唐代更重视经典理论的教育[5]。在经学的影响下,官办医学教育仿照太学模式,更注重对医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在教育考核方面,北宋官办医学教育更是照搬了科举考试的相关办法,重在考核医学生对于经典医理的记忆、理解及应用。
经学治学方法一方面给宋人指明了经典是理论知识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告知人们怎样的著作才能称作“经典”。《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得到了宋廷的认可和推广,逐渐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
3 经学治学方法在《伤寒杂病论》校勘注释中的应用
经学治学方法不仅影响了宋人对医经的评价,也影响了他们对方书的选择。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宋人认为,仲景理论宗于《内经》《难经》,方药源于伊尹,是继承黄帝、神农医理的典范,符合宋儒正统学术传承的认识;仲景习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契合了宋儒的研习模式。伤寒在宋以前尤为难治,由于仲景创立了较为完整的辨证体系,记载积累了组方严谨、行之有效的临证经验,被宋代医家广为接受与重视,并逐渐获得了与《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相等的学术地位。
北宋年间崇尚经典的思想深入人心,宋人不断地追求古代经典的完整与无误,因此宋廷积极收集古代医籍,召集儒臣与医家,成立专门的医书校勘机构,保存并整理了大批几近亡佚的古代医籍。不仅使《素问》《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等医籍获得良好校勘并流行于世,更使《伤寒论》在宋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单行本,为后来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人瞩目的是,通过校正医书局的校勘整理,《金匮要略》脱离蠹简重现于世,仲景学说终于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得以相对完整地传承下来。
3.1 《金匮要略》校勘中经学治学方法的应用
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成书后即遭亡佚,后王叔和将部分内容整理成《伤寒论》流传于世,而杂病部分至北宋前未见流传。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于蠹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为《伤寒杂病论》节略本。至宋英宗时期,《金匮玉函要略方》中的杂病部分经医书局林亿、孙奇等人整理,单独成书,是为《金匮要略方》(以下简称《金匮要略》)。相较于其他医籍,《金匮要略》的校勘在一定程度上存留了更多经学的痕迹。
首先,《金匮要略》的校勘不同于前代“录而不改、述而不作”,林亿等校定此书时,改变了旧本 “前论后方”的内容结构,采用了“论下为方、方证同条”的格式重新整合;并且为了突出“杂病”内容特点,删除了《金匮玉函要略方》有关论述伤寒的条文。其次,林亿等为了恢复仲景著作原貌,依宋儒注释《春秋》之法,不拘门户,综合《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古今录验》《肘后方》各家著作中保存的仲景方补入残缺的原文,力求呈现原书面貌。再次,宋臣对于疑惑难解之处则根据医理做出了推理性校注与评论,如针对《五脏风寒积聚证并治第十一》原文残缺,林亿等注:“去古既远,无文可以补缀也”;针对“紫参汤方”“诃梨勒散方”“红蓝花酒方”“小儿疳蚀齿方” “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长服诃梨勒丸方”等,林亿等认为,其遣方用药思路异于仲景其他著述,故评论其“疑非仲景方”。
从以上细节可以看出,《金匮要略》的校勘活动深受经学治学方法的影响。《金匮要略》的校勘缘于宋人对经典的重视,而部分原文的校勘亦是参考经学研究方法而完成。校正医书局对《金匮要略》的校勘不仅使仲景方术较为完整地重现于世,其运用经学思维、经学方法开展古籍校勘整理,更是为后来的医籍研究开启了思路。
3.2 《伤寒论》注释中经学治学方法的应用
经过校正医书局十余年的校勘整理,一大批著名医籍刊行于世,极大地拓宽了当时医家的理论视野。如《伤寒论》刊行后,众多医家纷纷对其展开研究和阐释,开创了我国古代研究仲景医理的新阶段。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打乱原文顺序,借助《伤寒论》原文,阐发医家的各自见解;二是维持宋版《伤寒论》原貌,注释中注重追根溯源,以《内经》《难经》原文阐释发挥仲景医理。
《伤寒论》两种研究方法的兴盛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北宋徽宗之前,宋儒推崇的“明经致用”之实学一度成为社会风尚[6],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一系列北宋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无不是以此为核心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医家对于经典的研究也倾向于临证的实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的出现也契合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徽宗以后,在北宋政局保守势力的阻挠下,熙宁变法失败,后经历了靖康之难,宋儒在这一系列的变故中对“明经致用”的理解出现了重大转变,探索经典的“心性义理”成为“明经”的核心,引经据典阐释儒经“微言大义”成为北宋之后经学的主流。中医学发展受此影响,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尊崇宋本原貌,引用《内经》《难经》理论、《金匮要略》相关条文注释《伤寒论》原文,以经解经,以论注论,以古释今。这既是北宋以来《伤寒论》注释方法的发展,也是经学影响下医学典籍研究方法的转变。在《伤寒论》研究领域,宋以后一部分医家推崇王叔和编次、成无己注释本,主张“维护旧论”者渐成一派,与元末之后兴起的“错简重订派”发生了学术争鸣。
4 经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医的出现
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重视医药学,颁布医学诏令、校勘医学典籍、推广医学教育,数十年间医学骎骎日盛。宋朝以儒礼治国,推崇仁孝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医学可上疗君亲、下救贫厄,符合儒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此时的医学界提倡回归经典,与回归先秦古文、探求微言大义的经学治学方法相通,相似的理想信念与研习方法拉近了医士与儒士间的距离。在此影响下,宋人知儒通医,促进了儒医的出现。
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设立“医学”,并在中央州县召集生源,如政和三年闰四月九日敕:“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窃见诸州有在学内外舍生,素通医术,令诸州教授知通保明……”
可见在政和三年前,已经存在一批“素通医术”的“(诸州有在学)内外舍生”。这些儒生,或许未经政府官办医学教育的培养,凭借喜好而自学成才。此后,“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7]
此“医学”与太学并立,为宋徽宗设立的官方医学教育机构。“医学”的设立,为当时读书人提供了另一求仕途径。此时的儒医是指经国家医学教育培养后掌握一定医学知识与技能的儒士。
从政和年间的这些敕令中可以获取以下历史信息:
第一,北宋后期,儒而知医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儒士习医或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第二,素通医术的儒士,有的接受过官办医学教育机构的培训(宋徽宗设立“医学”之前由太医局负责完成),有的则自学成才。第三,宋廷对儒医现象默许之中包含鼓励,儒医甚至成为后世良医的标准。
在北宋经学影响及朝廷具体措施的鼓励下,众多儒士涉猎岐黄之术,促进了北宋年间儒医的出现。这些儒士钻研经典,应用经学治学方法研究与阐释医学理论。在儒医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推动了崇奉经典、以作代述的治学方法与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使之在医学研究中蔚然成风,逐渐成为后世医学研习的主要思路。
综上所述,北宋年间经学治学方法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北宋年间医学的发展。推崇儒学思想的北宋政府重视医学,颁布各种医学诏令,完善医学教育,推动古医籍的整理与校勘。这些措施与办法一方面推动了以《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推动了 崇尚经典、溯本求源的医学研究风尚。同时,北宋年间儒学的发展、经学治学方法的改变吸引了更多的儒士留心医药,出现了一批儒医,促进了儒学与医学的融合,影响了后世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