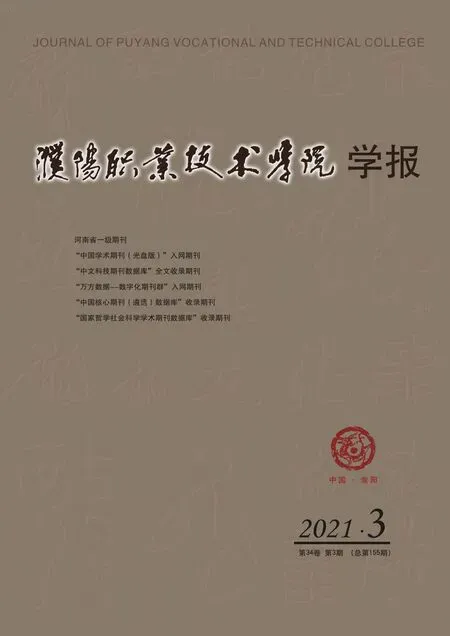儒家道德的历史境遇
孙旭鹏,赵文丹
(西安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当前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议, 尤其是儒家道德更是为我们所重视, 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我们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尽管当前学界大部分学者均对儒家道德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儒家道德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资源,坚信儒家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且与时俱进地实现自身的发展。无疑,当前儒家道德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有益的思想资源,然而,审视儒家道德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道德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道德所遭遇的批判是前所未有的, 在其时儒家道德是以一副消极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由此,我们不禁要问, 对于儒家道德的认知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究竟是儒家道德自身的问题,还是时代发生转变所产生的问题?
一、“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德
近代以来,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之冲击,然而,儒家道德所引发的争议却绝不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事情,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讲:“儒学将再一次面临往昔的窘境;它在古代遭遇的麻烦将会在前面等着它。”[1](125)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时期,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道德就面临着当时诸多学派的质疑与挑战,尤其是墨家、 道家以及法家都对儒家的道德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儒家道德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由时代转变所造成的, 在儒家道德自身内部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我们有必要从先秦儒学开始,通过梳理“百家争鸣”过程中不同思想学派对于儒家道德的批判,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来加深对儒家道德之理解。
首先对儒家思想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当属墨家学派,儒家与墨家在当时均为“显学”,产生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作为墨家代表人物的墨翟原为儒门弟子,然而其对儒家道德的很多方面却并不满意,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其中尤其是对儒家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差等之爱”提出了尖锐批判。 墨子主张应该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就是他的“兼爱”思想,墨子认为儒家的“差等之爱”必然导向“私爱”,而“兼爱”则是一种平等之爱。
墨家的眼光无疑是犀利的, 实质上我们也能看到,儒家道德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公”与“私”的紧张,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其实已经存在着以“私”坏“公”的倾向,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作为儿子应不应该检举父亲呢?如果从“差等之爱”出发,儿子爱自己的父亲肯定胜于爱其他人, 就应该为父亲隐瞒罪行,孔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主张“子为父隐”的。 墨子显然是不满意孔子这一主张的, 其提出的“兼爱”思想主张平等地爱一切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消解了儒家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私爱”,“要求人们兼相爱,反对当时社会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兼并战争”[2](89), 这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然而墨家的“兼爱”缺乏加以实施的社会基础,其后来的发展由于缺少现实生活的滋养而日益萎缩。尽管墨家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及儒家,然而其却以独特的视角指出了“兼爱”与“差等之爱”的区别,我们在后来经常提到的“私德”与“公德”的冲突问题,本质上正是儒家“差等之爱”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继墨家之后, 道家更是对儒家道德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道家的批判主要指向儒家的“仁义”思想,主张以“自然”来取代“仁义”。 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第十八章》)老子认为“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是顺应“自然”,儒家的“仁义”思想是有悖于“自然”的。无疑,较之于墨家,道家对儒家的批判是更深层次的, 是从理论层面的彻底批判。 道家从形而上的层面为道德树立了“自然”标准,“自然”与“人为”相对立,具有一种不为人力所改变的客观规律性,道家认为人类原本是素朴无争的,正是“仁义”思想改变了人类素朴的本性,在追逐“仁义”的背后隐藏着个人利益的打算,人类之间的争斗也就随之展开。那么,儒家的“仁义”思想是如何成为争斗的开端的呢?庄子尖锐地指出,“仁义”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那里已经成为了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此之为“盗亦有道”:“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 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庄子·胠箧》)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道德绑架”也属于此类情况,一部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以道德之名义迫使他人满足自己的要求,此时的“道德”已经名不副实,徒有“道德”之名,而无“道德”之实。
道家对儒家道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如何才能做到道德的名实相副呢?道家认为只有回归“自然”杜绝“人为”才有可能实现。 道家认为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都是背离“自然”的,不需要刻意地去追逐“仁义”,只要顺应人类原本素朴的本性,自然就可以实现一种“至德之世”。 无疑,道家的道德世界具有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其发觉儒家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存在儒家“仁义”之名被歪曲被盗用的情况,然而抛弃了儒家“仁义”的道德标准之后,道家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至德之世”呢? 这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道家固然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标准,然而这种“自然”的标准依然带有极强的主观性。道家的“自然”最终落实于人的内心,庄子所言“心斋”即是如此,爱莲心称之为“赤子心灵”:“当心灵的分析功能静止时,另一种心灵出现了,那是赤子心灵。 ”[3](28)道家这种沾染上了主观色彩的“自然”无疑也很难给现实道德的重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应该说,道家看到了儒家道德在现实应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尤其是对于道德标准的滥用, 然而道家采取了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那就是取消现实标准,而代之以充满主观理想色彩的“自然”。 尽管道家的“自然”包含着公平的意蕴, 然而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加以有效实施的路径, 从而使得这种公平的理论依然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无法为现实道德的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继之而起的是法家对于儒家道德的激烈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家是对道家的继承发展,由于道家的“道”与“自然”缺乏现实标准,法家就将“道”落实到现实层面的“法”,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 如果说道家的“道”是寄希望通过落实于内心来寻找标准的话,那么法家则将“法”的标准完全客观化,法家完全从生理层面的“趋利避害”来看待人性,“求利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4](13),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态度。在法家看来,只有现实层面的“法”才能体现真正的“道”。依法家的眼光,不论是儒家的“仁义”还是道家的“自然”,其本质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无法为现实社会治理提供依据。 于是,法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人性,摒弃了儒家的“性善”以及道家人性素朴的理论,完全从生理层面来看待人性, 不再给人性添加任何一丝的理想色彩。 法家的道德思想不再有任何理想的色彩,完全沦为了一种功利算计,这在当时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的时代,也确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秦朝完成统一,正是得益于法家思想的指导。法家也正是从效用这一层面来批判儒家仁义道德,法家认为儒家以“仁义”为代表的道德思想并不能够为当时社会带来任何改变, 反而运用赏罚措施却可以在诸侯国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然而, 依靠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在短时期内便分崩离析, 这同时反映出法家道德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越来越在社会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法家道德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其看待人性的方式, 人类固然在生理层面有与其他生物相通的一面,即本能的“趋利避害”性,然而人类却不仅仅追求生理层面的满足,更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法家恰恰忽略了人类追求精神满足这一层面,从而片面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看作完全依赖于冷冰冰的生理满足,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看待人性的方式,法家道德看似“客观”实质上却很不“客观”。 究其实质,儒家道德并不是“无用”的,问题在于应用过程中的失效, 正如墨家与道家所批判的那样,道德成为个人谋利的一种工具,这是应该加以避免和化解的。
尽管儒家道德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的批判,然而最终历史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 儒家道德思想不管在社会政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并被采纳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思想,儒家道德在平稳发展演进的过程中, 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道统”,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儒家道德对于现实生活的调节就是完美无缺的,应该说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中,儒家道德基本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保持着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但是儒家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先秦墨家、道家以及法家的批判当中寻出端倪,比如“公德”与“私德”的冲突,比如“道德绑架”的难题,比如儒家道德对于“法治”的忽略等等,这些问题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二、现代境遇中的儒家道德
儒家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问题并不代表不存在了,自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儒家道德存在的问题又被重新加以认识,并被进行了无限的放大, 此时儒家道德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之困局, 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道德的现代困境。 现代境遇中的儒家道德面临着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挑战,这是一次与西方文化的正面交锋,也是儒家道德自身进行一种现代转化的良好机遇。
首先,儒家道德面临着“民主”思想的挑战。 “民主”是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概念表述,以张扬个体权利为基本特征,“‘民主’这一术语,就其本源来讲, 反映的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的特征,即由多数公民按其意愿进行直接统治”[5](16)。很显然, 儒家道德与西方民主精神是存在文化上的差异的,儒家道德所培育出来的“民本”思想在着眼于社会治理的时候,凸现的是整体优先,而非个体优先。例如,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就主张以“礼”来教化民众,将民众视为治理的对象,用整体的视角来看待民众,而“礼”又是由“君师”制定出来的,“君师为政治教化之本源,社会的安宁,人民安居乐业,要靠君师之教育感化”[6](21)。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批的有志之士将儒家思想归结为中国落后的根源, 这诚然有点言过其实了, 然而也从侧面指出了儒家道德存在的内在问题,尤其是儒家道德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礼教”思想,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之批判。其实,儒家道德是“民本”与“礼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本”需要依靠“礼教”才能实现,这在不自觉中将民众视为教化治理的对象。 儒家道德中的“礼教”思想之所以成为批判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源于“礼教”与现代民主思想相悖,在当时“礼教”几乎成为了“专制”的同义词,当然也就视“民本”与“民主”根本对立,由此将儒家道德视为现代民主发展的障碍, 并对儒家道德加以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近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儒家“礼教”思想压制了个人的自由,成为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帮凶,儒家道德在他们眼中就完全成为了负面的东西,而希望全部加以根除, 以此在文化层面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诚然,儒家道德确实在现代化的转型时期陷入了一种困境, 然而这也并不代表儒家道德一无是处, 并且儒家道德面临的困境也是完全可以得到化解的。 以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努力实现儒家道德的现代转型,从儒家“德治”传统中开出现代民主。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儒家道德并不能同“专制”划等号,相反,儒家道德恰恰是开出现代民主思想必不可少的文化土壤,儒家的“仁政”学说恰恰彰显了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性。
其次,儒家道德面临着“科学”思维的挑战。近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认为, 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出像西方那样的科学思维,根源正在于儒家道德的束缚。不可否认的是, 儒家确实将精力放在伦理道德上的建构,相对忽略科学技术层面的发展。其实不仅仅是儒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都在人生哲学方面,而对科学思维关注较少, 在整个先秦时期也只有墨家在关注逻辑思维层面的内容。 儒家道德只是对科学思维关注较少,但绝非与科学思维截然对立,孔子就明确提出对民众既“富之”又“教之”的思想,当然孔子从事的是“教之”的事业,而“富之”的事业则需要科学技术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尽管没有提出如何“富之”的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并不反对科学思想。 孔子就曾讲自己在如何种植庄稼方面不如老农, 可见儒家思想只是将重心放在道德伦理方面,但是并不代表其反对科学技术,我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思维的过程中,儒家道德并不构成一种障碍。而且, 儒家道德在另一方面可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舒适与便捷的同时, 也带来一系列道德伦理的风险,而如何化解这一系列风险,则正是儒家道德的长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儒家道德完全可以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并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总之,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儒家道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儒家道德如何回应“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就变得至关重要,是彻底否定儒家道德还是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发展“民主”与“科学”,就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儒家的态度。事实也证明,我们一方面无法彻底清除儒家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完全清除儒家道德的影响,现代的“民主”与“科学”只有通过对接儒家道德的传统,才有可能获得健康发展,“欲融通中西文化, 首先必须从中国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7](260)。
三、儒家道德的现代转化
我们简要梳理儒家道德的历史境遇, 并不是要对儒家道德做出一种优劣评判,因为究其实质,文化自身并没有所谓优劣之分, 而只有是否适应时代的问题。 儒家道德思想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这一历史事实, 恰恰说明了其自身的生命力以及与时代相适应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实现儒家道德的创造性转化,更好地促进当今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其道德思想已经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之中, 儒家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的精神之根, 想要从根本上摆脱儒家道德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透过先秦时期各个学派对儒家道德的批判, 以及近代以来儒家道德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道德之所以面临不同的历史境遇, 既与儒家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关,同时也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因而,我们要想实现儒家道德的现代转化, 既要关注儒家道德自身的问题,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来化解儒家道德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客观正视儒家道德所存在的问题,儒家道德的历史境遇显现出其自身的问题。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其他学派对儒家道德的批判正反映出儒家道德的薄弱之处,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关于“私德”与“公德”对立的问题,这在墨家对于儒家“亲亲相隐”的批判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依然需要在当前的社会道德建设中加以化解,努力提升公德意识。关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名实不副的道德现象, 正如道家所指出的那样,也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道德不能徒有虚名,而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中。关于法家对于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认为儒家道德是“无用”的,则需要我们在当前加强“法治”建设来为道德保驾护航,自觉进行“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以补救单纯依靠“德治”的不足。想要实现儒家道德的现代转化,就必须首先认识到儒家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儒家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出发, 结合时代的要求来对其进行一种现代转化。
其次,对儒家道德进行现代转化必须与时俱进,使儒家道德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转变。 近代以来儒家道德面临的困境也充分说明,面对“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儒家道德自身也应该积极回应,只有通过积极回应时代,儒家道德自身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而不是固步自封与时代相隔绝。 事实也证明,儒家道德不仅与“民主”“科学”不相冲突,而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能够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融入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促进自身发展。 例如,传统儒家道德的“家国天下” 观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传统封建意义上的‘国’转换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天下’转换为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8](40)。
纵观儒家道德的历史境遇,使我们意识到:一方面, 进行社会道德建设依然需要建立在对儒家道德进行深刻认知的基础之上, 不能忽略儒家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在现实层面加以化解,在促进儒家道德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儒家道德的发展需要与时代相结合,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儒家道德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正说明了儒家道德的可塑性与生命力。由此, 儒家道德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反思,没有经过不断反思的文化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儒家道德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境遇本质上即为文化省察的过程,并在这种不断省察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 儒家道德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克服自身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儒家道德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 我们有理由相信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而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这其中当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文化研究者的努力, 不断对儒家道德进行自觉地省察,以促进儒家道德“日日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