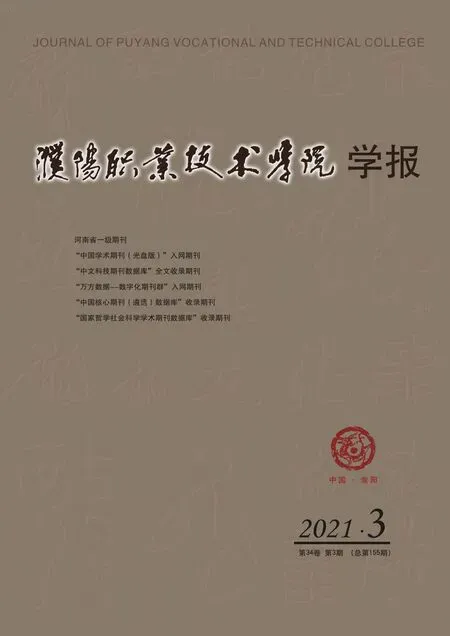美国电影《分歧者》的反乌托邦思想
陈琦瑶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分歧者》 是2014 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反乌托邦题材的电影。这部电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是美国青年女作家维罗尼卡·罗斯。该片塑造了一个异化的未来社会体系, 以博学派为首的五大派系牢牢掌控着人类最后的城市——芝加哥, 实行灭绝人性的高压统治。不属于五大派系的人被称为“分歧者”,被社会所排斥。 女主角翠丝坚持与这个异化的社会抗争,最终成为分歧者的领军人物,不仅收获了个人的自由与爱情,更是转变了芝加哥人的固有观点,最终建立起自由美好的崭新芝加哥。 《分歧者》自上映以来, 就以其深刻的反乌托邦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片的反乌托邦思想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反面的乌托邦”,即一个与美好理想背道而驰的问题社会;另一方面是指“反抗乌托邦”,这里反抗的是已经被扭曲异化的反面乌托邦。 主角在反抗被异化的乌托邦的过程中, 也暴露出近年来美国过度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一、反乌托邦概念在电影中的体现
公元前4 世纪,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哲学巨著《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完全符合他的政治理想的完美国度,可以说是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思想源头。而“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中,寄托了莫尔所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在电影《分歧者》中,芝加哥市是末世里人类幸存者最后的乐土,整个城市被高墙围绕,城内科技发达,居民劳有所得。整个城市由友好派、诚实派、博学派、无私派和无畏派这五个派系组成。每位公民在16 岁时要进行一次测试选择自己的派系,只要通过了测试,一生就衣食无忧,没有疾病与战争的困扰。且五个派系的名字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芝加哥人对五类美德的憧憬与追求, 而这份对美好品质的追求也确实对人有潜移默化的约束作用, 使芝加哥以自己独特的社会体制运转了多年。可以说,表面上欣欣向荣的芝加哥市显然是乌托邦的化身, 是自古希腊至今人人崇尚的完美社会。
然而过分的完美使乌托邦这个名词仿佛镜中花水中月,是让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由于各类乌托邦作品描绘的愿景过于美好, 对于乌托邦思想的怀疑也纷至沓来, 当下美国流行的反乌托邦作品也正来源于此,在众多美国学者看来,完美的社会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反乌托邦”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 反乌托邦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是“反面的乌托邦”, 即一个与美好理想背道而驰的问题社会,具体体现为社会制度专制、人性扭曲异化。另一方面是“反抗乌托邦”,这里反抗的是已经被扭曲异化的反面乌托邦。美国科幻作家约翰·坎贝尔曾说:“科幻作家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怀有真挚而深切的期待。 ”[1](396)在他们看来,社会永远都存在进步的可能性,因此表面完美的社会必然也存在漏洞,而要修补这种漏洞,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必经之路, 就是对当前的社会体制进行反抗。在美国科幻作品中,“反乌托邦”社会一般并不直接表现出贫困落后的形态,而是表面繁荣,内里腐坏。电影中,芝加哥便是这类表面欣欣向荣的反乌托邦社会的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的追求五种美德反而逐渐扭曲了人性。由于崇尚美德的“纯粹性”,不同派系的人不允许生活在一起, 即使是家人也被迫分开。 而测试出多重美德的年轻人被称为“分歧者”,不仅不能得到赞扬,还面临着被驱逐毁灭的危险,不被社会接受。博学派的领导者以严酷的专制统治压迫人民,以洗脑式的教育迫使人们保持对“五种美德”的忠诚。 “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恰怡导致了对这些原则普遍的颠倒——科学变成了野蛮,理性蜕变为非理性,自由变成了桎梏,民主成了新的专制”[2](12)。本应该作为人类最后乐土的芝加哥市看起来光鲜亮丽, 事实上早已千疮百孔。 芝加哥繁荣的假象可以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但只要揭去表面虚伪的面纱,就能看到底下漏洞百出的制度体系,完美只是幻影,人性扭曲的反面乌托邦才是芝加哥丑陋的真容。
无论是乌托邦作品还是反乌托邦作品, 作者对于真正的完美社会都是持向往支持态度的。以《分歧者》为代表的反乌托邦科幻电影,并不是单纯地塑造一个黑暗社会,而是通过揭露问题来促使公民反思,从而向真正的乌托邦迈进。
二、《分歧者》所体现的反乌托邦政治理念
“乌托邦”这一名词最初的提出,就与政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乌托邦一向是个政治问题, 是文学形式的不寻常命运。 ”[3](6)《分歧者》作为与乌托邦作品紧密相连的反乌托邦作品,也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是与美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
在反乌托邦作品中, 无论是明确提出还是通过暗示,“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政治设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作者所塑造的秩序混乱、人性扭曲的乌托邦,与作品中初代统治者的领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分歧者》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体现的, 一方面是塑造连续两届芝加哥政府乃至墙外世界政府的负面形象; 另一方面是女主角翠丝在反抗专制政府统治的同时, 拒绝自己成为执政者。 其实,“作为政治术语的无政府主义并非表征着无秩序的价值,毋宁说意味着没有人统治着他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是‘为每个人的权力’,权力不加诸任何人”[4](254)。 在电影中,芝加哥的执政者珍妮专制、冷酷,任何怀疑五大派系的人都被她直接清除,是剧情里的第一位“暴君”。 女主角翠丝就因为具备所有美德被追杀, 但却阴差阳错地通过了芝加哥建立者的最终测试,揭开了“分歧者才是维持人性的关键”这一惊人的真相。翠丝满心欢喜,对珍妮解释“我们不是麻烦,而是钥匙”,并天真地以为珍妮可以改变针对分歧者的政策。然而珍妮却试图掩埋真相,杀死翠丝。 可以看出以珍妮为首的第一任芝加哥政府是自私堕落、无可救药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任何一位无辜的芝加哥市民, 是完全负面的政府形象。 在女主角翠丝与男主角老四一同推翻了珍妮的统治后,分歧者队伍曾经的带头人、男主角的母亲伊芙琳接替了珍妮的领导地位, 然而翠丝发现,伊芙琳的所作所为与珍妮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她们都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 伊芙琳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死珍妮的拥护者, 最后甚至试图通过清除人们的记忆来维护自己地位, 为此女主角再次走上了反抗之路。 如果说女主角第一次推翻当局的统治是大部分科幻小说创造“更美好世界” 的必经之路, 那么第二次推翻芝加哥的领导者——曾和自己同为分歧者的伊芙琳时, 明显表达了作者对政府的不信任。 在作者看来,政府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会走上专制的歧途,这与无政府主义中“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否认一切权威”的主张不谋而合。 电影第三部开始时, 本应加入芝加哥领导集团的女主角面对朋友的询问时,直接表示“我可不愿上去制定规则”,也是作者借女主角之口表现了个人对政府的排斥,是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的体现。
《分歧者》三部曲塑造了连续两届芝加哥政府的负面形象, 且详细描绘了两届政府被人民推翻的情景, 而极富领导才能的主角翠丝拒绝接任芝加哥的管理职位,都体现了反乌托邦作品提倡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自由社会,反对集权统治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 反乌托邦作品的这一政治理念与美国现存的社会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贫富悬殊、次贷危机以及长期存在的人种、 宗教矛盾都造成了美国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加深了美国公民对政府的怀疑,进而使无政府主义这一政治理念再度成为作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但文学乃至衍生的影视作品表现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们等同于政治。 因此在分析电影的反乌托邦政治理念时,其中的审美因素更不容忽视。
三、暴力与战争:美国反乌托邦作品无法逃避的悖论
“反战”一直是反乌托邦作品的主题之一。 反乌托邦世界与秩序井然的乌托邦世界截然相反, 它一直饱受战乱与暴力冲突的困扰, 是作者幻想出来的人间炼狱。近年来大受观众欢迎的《饥饿游戏》《移动迷宫》以及《分歧者》等反乌托邦电影都表达了反战的思想。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往往都借主角的行动,直言不讳地诉说自己渴望和平的心愿。 在《分歧者》中,翠丝一直对暴力冲突持厌恶与反对的态度,在第三部开头伊芙琳以暴力手段处决曾经的敌人时,翠丝拒绝继续待在所谓的“庆功宴”中,转而选择逃离芝加哥去探索新世界。由此可见,翠丝的反乌托邦思想最初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 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处理矛盾。 反乌托邦电影中的反战思想之所以尤为鲜明,是与美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美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参与战争,战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但也给民众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因此,有学者指出:“现代战争是反乌托邦小说生成的现实契机, 反乌托邦作家经历了世界大战的阴影,利用文学来探讨战争,试图证明战争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并为人类的发展敲响警钟。”[5](15)因此美国当代流行的反乌托邦作品, 作者都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反战思想以及对和平、和谐社会的向往。
然而矛盾的是, 每部反乌托邦电影的主角往往也是战争的挑起者和领导者, 也许主角一开始并不承认这点,但他们依然被作为战争的精神支柱,并一步步自愿承担起先锋的任务。 《分歧者》的主角翠丝虽然表现出了对暴力反抗的厌恶, 但在行动上常常出现矛盾的地方。在电影的第二部中,主角翠丝一行人登上无派别者的火车想要逃离搜捕, 此时他们与无派别者发生了口角,男主角试图让两方人马都“冷静下来”,但翠丝直接选择了大打出手。 而到了第三部的后半部分, 当翠丝看到自己的爱人面临失去记忆的威胁时,毅然选择了发动攻击,与自己的同伴一起参与了推翻伊芙琳的军事行动。在伊芙琳被擒后,翠丝更是向为伊芙琳提供清除记忆的药物的“墙外世界”发表了类似宣战的讲话。主角由战争的逃避者转化为战争的发动者, 这与美国长期以来宣扬的反战思想是相矛盾的, 但并没有引起美国观众的任何负面反响。 且在同类型的《饥饿游戏》以及《移动迷宫》中,主角也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这与美国观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审美价值观是分不开的。
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审美观是在多种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无论是古希腊文化中《荷马史诗》塑造的英雄奥德修斯,还是基督教文化中“万能的主”耶稣,都有着非凡的能力以及独一无二的使命,这些极富魅力的英雄形象都为美国对个人英雄的崇拜奠定了文化基础。 以《分歧者》为代表的反乌托邦电影的主角, 往往都继承了古希腊英雄以及基督耶稣的特点,有拯救世人的任务,且表现得无所不能。电影常常夸张地宣扬个人的能力, 第二部中翠丝与另外二人离开友好派时,男女主角分别以一己之力压制住了整个追捕队的火力, 不仅没有受伤还反身击毙了数名敌人,这类情节本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为了塑造出无所不能的英雄人物形象, 电影放弃了对真实细节的刻画。而为了使翠丝救世主的地位不可替代,导演将翠丝塑造成了唯一一个能通过四项美德考验的分歧者。在超凡能力与救世使命双重光环的加持下,主角甚至可以抛开道德与理性的约束转为施暴者,美国观众在不知不觉间包容了翠丝的暴力行为, 忽略了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无形中成为暴力的推崇者。
虽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也可以表现反战思想,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反战电影的佳作, 但在这些电影中导演都细致地刻画了战争所带给人类的灾难,使观众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以此反思、制止暴力与战争的重临。 但是在《分歧者》中,导演并没有表现出主角暴力行为产生的负面作用,主角以自身的恐怖行动阻止了新的恐怖行动的产生,而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美好的新世界。 然而由主角领导的暴力冲突乃至发动的战争所造成的流血与牺牲、所带给人民的精神创伤、财产损失在电影中都被一略而过了, 而这些才是反战电影真正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不仅是好莱坞影片迎合美国观众的审美需要所提供的“暴力美学”,也是美国近年来过度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影响的结果。因此,尽管反乌托邦题材电影中往往充斥着与作者试图表达的反战思想背道而驰的暴力场景,但依然受到美国观众的欢迎。
四、结语
作为一部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分歧者》除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效果以外, 更重要的是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文学及影视作品不应回避政治问题,将审美与政治因素割裂为对立的两部分。 《分歧者》充分体现了反乌托邦的两方面概念,即“反面”与“反抗”,引起观众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思考与对人性的反思, 且以电影的形式展现了反乌托邦中蕴含的多方面政治理念, 这是当下许多只追求娱乐性的好莱坞商业电影所做不到的。 但影片也暴露了美国影视乃至文学作品展现的暴力行为与反战思想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美国过度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造成的,是植根于美国文化中的。 总体来说,虽然《分歧者》暴露出美国大片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但电影中对人类美德的诚挚追寻还是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成为美国反乌托邦电影的代表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