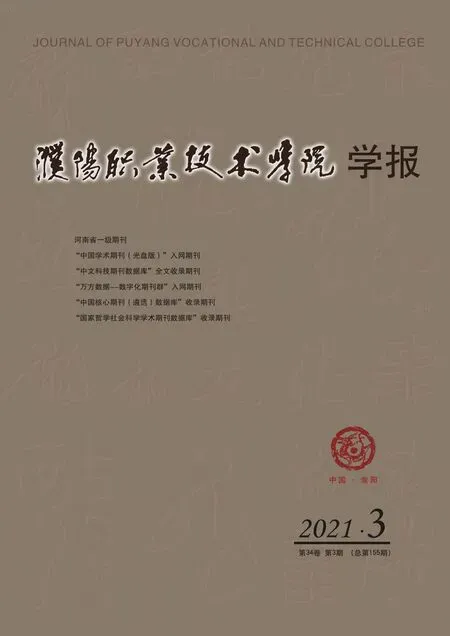“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论杜甫的社会历史主体观
刘倩倩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1](25)他认为,主体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是现实中活的独特的个人,是具有思维能力,并且能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人(或集体),社会历史主体理论就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2](84)人在实践中把智力和体力注入客体, 使原来纯自然的客体变成人化的客体。 因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人的主体性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举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等一切活动,都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结果。社会历史规律则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中并通过人的活动去实现。
由此,社会主体研究的对象也是人,在对人的活动、本质以及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中,来展示社会的本质与发展的规律。 可将马克思对社会主体的研究分为三点:一是人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二是人是现实存在人,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相应的社会属性和特点;三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杜甫时代与马克思时代虽相隔千年, 但同作为所属时代的伟人, 却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社会历史主体观。
一、杜甫及其思想渊源
杜甫,唐中后期伟大诗人,他的诗歌极具现实主义风格,后世称其为“诗圣”,并将他的诗誉为“诗史”。杜甫一生充满坎坷,然而他却时刻心怀天下,以其精湛的诗艺、 超凡的人格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 在他现存的1400 多首诗歌中,忧民气息随处可见。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析。
(一)“中间人”——特殊的阶级出身
杜甫出生于“一个有着小官僚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小地主家庭”[3](17), 其十三世祖杜预曾经是西晋的名将,战功累累;祖父杜审言官居修文馆直学士,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杜闲曾官居兖州司马。 由此可见,杜甫生于一个小宦官世家,虽不是钟鸣鼎食之贵族,但绝对算得上世代书香,家学渊远。所以他既有着“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鵰赋表》)的自豪,又有“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之叹。 他所说的“贫穷”,是与那些大官僚、大地主相比。在当时,杜甫只能算作中间阶层——算不上贵族阶级,但也不是农民阶级,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更接近人民,同时他也承担部分赋税,难免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压迫, 因此并不是一个与人民疏远的阶级层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人民,对贫苦人民抱有同情。所以,杜甫便成为这一中间阶层的典型代表。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以一句垂世经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展现了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关心。
(二)“儒家者流”——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
杜甫思想的滥觞,一方面与家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他自幼接受了儒家所主张的“入世”和“有为”思想,即使在困居长安时期,经历了应试落第的打击,又辗转于权贵之间,投赠干谒,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但始终不坠入世之志,奔走献赋,希图出世。
杜甫对于儒家积极思想虚心接纳, 同时对其消极落后的一面也直言不讳地进行批判。 尽管儒家奉行“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但杜甫却直言“临危莫爱身”(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劝诫友人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以大局为重,为社稷奋不顾身,不可只顾爱惜自己的生命。
而他本人, 以实际行动和具有鲜明人民性的作品笃行了这一点: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相对安定的巴蜀之地成了北方士人奔赴的避难所, 杜甫也在成都度过了一生中相对适逸的生活。 然而他的一颗忧民之心却不甘落闲——他在写于这一时期(宝应元年)的江头四咏之《鸂鶒》中,开篇便写到“故使笼宽织”,浦起龙《读杜心解》中说:“通首都从‘笼’作意”。[4](430)此时杜甫虽入川已有时日,内心深处却对这种偷安一隅的生活并不满意,仿佛身处牢笼之中,他在诗的下一句发出了“失水任呼号”的悲叹。 人民身处危难之中,心系百姓的杜甫,内心是无论如何难以平复的! 这也是对儒家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反叛。对于儒家思想的扬弃,使他能够走出本阶级的狭隘立场,以一种唯物论的思维看待一切问题。
(三)“吾道属艰难”——忠君与爱民的抉择
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 往往只片面强调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的言论,认为其一力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这当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全面分析杜甫的忠君思想。
同样是出于拥护君主的目的, 杜甫却不能与一般所谓“愚忠”混为一谈,有人说杜甫是“一饭未尝忘君”,但其实是“一饭未尝忘致君”[3](48),“致君”即直言上谏,让君主能够做出为国为民的圣断。杜甫厌恶战争,反对宦官干政,对于朝廷无节制的征税进行严厉的批判等等都体现了“致君”。 杜甫的忠义之心不容质疑,但并不是一味地唯王命是听,而是有所反抗,敢于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
然而,拥戴皇帝和热爱人民很难做到和谐统一,当人君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产生矛盾时, 杜甫毅然决然选择了忠于人民、 以人民利益为上, 这就意味着,他走上了一条犯颜进谏的道路,这自然会引起君王的厌恶,最终落得个“朝廷记忆疏”(《酬韦韶州见寄》)的惨境。杜甫自知惨淡难逃,发出“吾道属艰难”(《空囊》)的吁叹,然而这种“艰难”,对于诗人来说,未尝不是因祸得福, 使他更有可能突破官僚阶级思想的局限性,而成为一个贴近底层人民的诗人。
二、时代的共性——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创造这一切,……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5](118-119)历史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历史的一切都是由现实的人所创造的。可见,马克思对人的主体地位作出了高度评价, 甚至将人的地位上升到了凌驾于社会历史本身的高度,为之仰叹。
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 杜甫也真正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达到了当时诗人所不曾达到的历史高度。杜甫用实际行动践行——哪怕回顾半生已是龙钟潦倒,哪怕自己时常衣不蔽体、食难果腹,也从未忘却体恤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充分表明了其忧国忧民之心。 他的出身使他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诗人并未以此自矜,反而一想到百姓比自己更加难以维生,就连连发出叹息,心如刀绞。 人民的位置,已经牢牢占据在杜甫心头,热爱人民也仿佛内化为他与生俱来的本能。
公元769 年,这是杜甫生前的最后一个年头。由长沙前往衡州的路上,途经花石城,本已是风烛残年之躯,非拄杖不能行,但想到这里是唐的戎兵之所,他还是抱着一丝幻想系舟上岸, 却目睹了眼前一派荒凉:“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由于遭受战乱,人们早就四散逃离, 只有用来灌溉的泉水还在独自流着,一副荒凉景象跃入眼帘。当他看到那些曾经浸透过汗水的劳动工具,却弃置不被使用,看到“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他发自灵魂地质问:“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可见,杜甫的热爱人民之情,真是达到了忘却自我的境界。
此外,服务于百姓,更是成为杜甫的终极政治目标。 他的从政理念,与儒家“仁政”主张一脉亲承。 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对于一切有害人民的现象,无论剥削讹榨、奢侈糜费、奸淫掳掠,还是神怪迷信等,他都一律加以反对, 毫不吝惜地攻击与民为敌的贪官污吏,甚至大胆地对昏君庸帝口诛笔伐。他对皇帝不作为十分痛心:“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 ”(《奉赠卢万丈参谋》),他对贪污官吏恨之入骨,发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书谏》)的呼喊,他批判统治阶级的丑态,“惜哉俗态好蒙蔽, 亦如小臣媚至尊”(《石笋行》)。 这些诗歌表明,杜甫心怀人民,始终致力于为人民争取切实的利益。
三、 时代的鲜明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是“社会的人”[6](27),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 其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上文虽谈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此处强调前提是人存在于社会中, 其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因而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谓“一切社会关系”,既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 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
同样, 任何一个作家, 都不可能超然于时代之外。 杜甫及杜诗的成就,并非偶然,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时代环境就是其首要客观条件。社会环境影响着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创作道路,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罪恶昭著、人民苦不堪言之时, 这种影响就更为显著。 杜甫身处安史之乱,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他与人民同处艰难环境之中,有着贴近人民生活的丰富实践经历,加之本身的忧国忧民思想, 就自然在作品中形成了丰富而鲜明的特征。 一部杜诗,便是一个时代。
他的诗歌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惨状,如《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悲陈陶》《悲青坂》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安史之乱后, 统治者实行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 《羌村》:“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新安吏》:“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垂老別》:“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可见当吋,壮丁抓尽后,连不盈岁的“中男”和“儿童”,甚至年迈的老人都被逼上战场。 而留守在家的妇女,也不能幸免,时时担心受到官兵的侮辱,“闻道杀人汉水上, 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 人民衣食无着自不消说,甚至只有通过卖子女才有钱交税,“况闻处处鬻男女, 割慈忍爱还租庸! ”(《岁晏行》)不仅如此,连“丈夫死百役”(《遣遇》)的鳏寡遗孀也逃不过恶爪,于是便有了“征伐诛求寡妇哭”(《虎牙行》)。此外,杜甫还在作品中展现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在名篇《丽人行》中,诗人通过描写三月三杨家兄妹曲江春游的场景——携一行侍眷雕车宝马, 个个着绫罗细软, 戴翠羽明珰,宴饮上更是象箸玉杯、一食万钱,深刻讨伐了杨氏家族骄纵荒淫的丑恶生活;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记一次在骊山脚下、华清宫外,听到丝竹管弦的靡靡之音, 嗅到驼蹄羹汤的酒食之气更露骨地鞭笞了当时君臣上下奢靡无度、欲仙欲死的生活状态。
所有的战乱、昏庸、奢靡、剥削与压迫,都被诗人一一纪录在案,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四、 时代的主体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要重视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主体作用。 这在杜甫的思想或作品中亦皆有所体现: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物质生产资料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 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这间接地生产出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劳动者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当然,远在杜甫那样的封建时代,他可能还无法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社会的起源, 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伟大意义。但由于他的底层生活经验,尤其是晚年躬耕劳作的经历, 使他深深意识到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对人生的首要意义,以及劳动者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感叹:“谷者命之本! ”(《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又说:“浮生难去食! ”(《赠王侍御》)
杜甫热爱劳动,他的一双手不仅执笔,也“学稼”“学圃”,他不以文人自居,而自称为“老农”;他丝毫不认为劳动是低贱之事, 反而以因病不能参加劳动而深感遗憾:“恨无抱瓮力,庶减临江费。 ”(《甘林》)他只要身体尚存遗力,只要还能拿得动一锄一犁,就乐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如:“独绕虑斋径,常持小斧柯”(《思树》),“白锄稀菜甲, 小摘为情亲”(《有客》),“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秋野》)。 劳动活动,在杜翁笔下充满美和诗意:“细雨荷锄立,江猿吟翠屏”(《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 可见,他已体悟到劳动的乐趣,生发出对劳动由衷的热爱,否则不会费意将躬耕生活绘入诗中。
对于农民,杜甫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坦言:“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 ”(《暇日小园散病》)将他对“州府”的不爱与对“旁舍”的爱,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所谓“旁舍”,指的是劳动人民。而农民对杜甫的态度,也是视若乡邻。在《遭田父泥饮》诗中,杜甫被一位农民老伯盛情邀请去品尝新酿的春酒。“泥”在这里是缠着不放之意,可见杜甫与老伯亲密无间,情谊深厚。 对待劳动者,杜甫总是一种平等、谦和的态度,在《信行远修水筒》诗中,雇工信行上山修理水筒,直到天黑才回到家。杜甫悯其辛劳, 心怀愧疚, 写道:“日曛惊未餐, 貌赤愧相对。”可见,杜甫全然没有主仆尊卑之心,只有一颗体恤、热爱劳动者的初心。
(二)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不仅具有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 其他精神文化产品也无一不是他们实践活动的产物。 历史上,数不尽的科学发明、艺术创作都是由人民群众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正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中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又从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创造出宝贵的精神财富。
杜甫自觉从民间吸收俗语入诗, 一些俗语由于粗俗不雅, 被许多诗人弃如敝履, 但杜甫却不以为然,他尝试把民间的一些俚俗口语,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不仅使其语言通俗易懂,也使诗意中增添几分生活的真实性。如《新婚别》:“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便与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表达很是相近。
此外,杜甫常与乡间邻里往来,诗中广泛使用方言俗语,如家常话“爷娘”“寡妇”“鹅儿”“鸡儿”“噢饭”等,在他的笔下都信手拈来:“爷娘妻子走相送”(《兵车行》),“但使残年饱噢饭”(《病后遇王倚饮赠歌》);又如“呀吭瞥眼过”,用“呀吭”二字,拟写纤夫的劳动号子。 在他看来, 这些人民口中随性所说的“当时语”,便是诗歌创作最好的素材。
再具体以《兵车行》为例,“爷娘妻子走相送”一句,若是觉得在诗句中直呼“爷娘”太过俗气,那么换上书面语“父母”则更为不妥,反而是方言俗语的运用给诗歌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若是觉得太过粗俗,那么换成委婉些的“牵襟扯袂泪阑干” 则失去了那亲人互相撕扯着衣衫、捶胸顿足、奔走呼号的画面感,反而削弱了这一悲剧的形象性。据影印朱刻本《分门集注杜工部集》,杜甫在“爷娘妻子走相送”这句诗后自注,说明引用的是北朝民歌《木兰辞》中的“不闻爷娘唤女声”一句。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性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同时,也得以想见诗人杜甫是怎样虚心吸收民间艺术成果的。
(三)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这样的表述,没有了生产者阶级,社会也将不在。人民群众也就是生产者阶级,扮演着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历史上的奴隶、农民、工人代表着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他们依靠着历史赋予的社会主体力量,赢得了光辉的革命成就。无论历史如何更替, 都必须经由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斗争。
杜甫正因为早就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历史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所以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群众的一边,广泛而又细致地反映人民的各种愿望,并且他也懂得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战争的态度,便是如此。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他便强烈反对发动战争,并且劝诫君主“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战乱爆发后,他为了保卫祖国,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战,一方面也期盼战争能早日结束,怜悯饱受战乱的无辜百姓。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由自身的遭遇联想到天下文人的艰难处境。 他不仅呻吟“吾庐独破”,更多是为“天下寒士”的痛苦处境而哀叹,一颗广忧黎民的拳拳之心昭然若揭。 并且,杜甫清楚地意识到,连年征战只会带来生产破坏、剥削加剧等一系列民不聊生的结果, 所以他希望将武器变作农具,希望农民能尽快恢复生产,屡屡喊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以及“土著还力农”(《往在》)。
杜甫亲眼目睹过人民被剥削的艰难生活, 他反对对人民乱征赋税,呼吁统治者“下令减征赋”;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进行痛批;“难拒供给费, 幸哀渔夺私”(《送杨监赴蜀见相公》),处处体恤民情,发出民怨。
(四)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
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7](220)的情况,这些杰出人物参与决定性的重大事件。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杜甫既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忽略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做到了“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统一。
他入蜀以后,写了一系列赞扬诸葛亮功绩的诗,例如《八阵图》《古柏行》《诸葛庙》《咏怀古迹其五》等,其中《蜀相》最为著名。 全诗可见诗人对诸葛亮溢于言表的敬佩之情。 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中,用“寻”传达出杜甫对诸葛亮的无尽追思。“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讲述了诸葛亮充满传奇的一生。从最初的“三顾茅庐”,刘备礼贤下士,不厌其烦的前后三次拜访诸葛亮,希望卧龙先生出山助他一臂之力,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诸葛亮的经天纬地之才,不禁让人对其心生钦佩之情。在最后的两句诗中, 杜甫对诸葛亮最终未能复兴汉室痛感同情与惋惜。但是,虽然诸葛亮没有完成他兴复汉室的承诺,然而他一生为了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不负其信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杜甫常常思及此,便不由得“泪满襟”。而“长使”二字,更是让人不禁将惋惜之情蔓延到了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 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包含了对英雄的无限叹惋和崇敬。
此外,在其他四首《咏怀古迹》中,杜甫又分别对历史上的四位人物进行歌颂。其一咏庾信,杜甫对他的诗歌极为喜爱,也为庾信的平生萧瑟而感同身受;其二咏宋玉,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才华的倾心,并为其身后鸣不平; 其三咏昭君, 惋惜昭君的悲剧命运,肯定了巾帼英雄的身世家国之情,代为抒发了美人的去国之怨;其四咏刘备,歌颂了一代君王的丰功伟绩,感叹其壮志未竟而身先不存,对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同心,充满了无限向往。这组诗赞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学识、品性、功德,并对其身世浮沉、壮志未酬的人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饱含对历史伟人的敬重与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