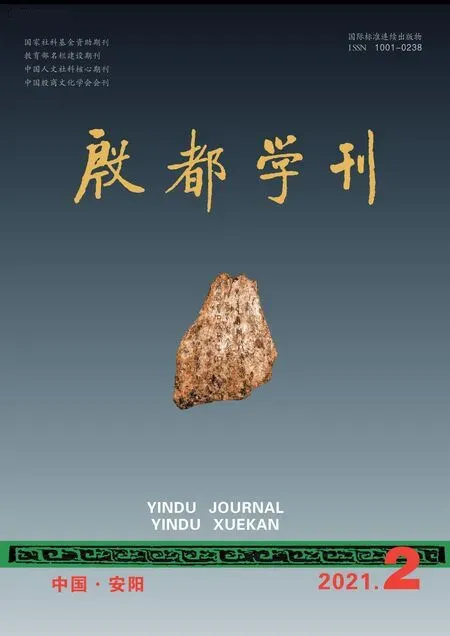论《西厢记》的情礼妥协与人伦重建
杜瑶瑶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西厢记》常被冠以反传统礼教、女性解放等意义,如:“《西厢记》的主题可用一句话概括:‘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和反抗,控诉与批判。”(1)田同旭:《元杂剧通论》(上),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48页。此类表述随处可见,似乎已成为定论。归纳前人的反礼教说,大致有三个理由:张生跳墙赴约、莺莺夜会西厢、“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2)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52页。。其实,崔、张二人的越轨行为皆发生在老夫人许婚又赖婚之后,他们的叛逆仅限于与自身相关的爱情,从未真正突破传统礼教,而最终张生考取功名与莺莺喜结连理的结局,亦是对礼教挑战的失败。情与礼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查洪德先生曾指出:“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就一定不依照礼法成婚;依照礼法成婚的男女,一定是没有感情的?没有这样的逻辑。”(3)查洪德:《元杂剧的淑世精神与社会重建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44页。也从没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唐玄宗李隆基有词《好时光》:“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4)林音等注析:《婉约词》,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页。李白有《相逢行二首》(其一):“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5)《全唐诗》,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页。皆表达了与有情人结为眷属之意,但不能说李隆基与李白是反封建礼教的。王实甫从头到尾都没有以激烈的方式抨击传统礼教,而是在“礼崩乐坏”、纲常紊乱的时代背景下,既肯定了情之可贵,更强调了礼之重要,创造了情与礼的完美结合。他不仅没有以情反礼,还在为传统的婚姻观念礼赞,并极力呼吁重建伦理秩序、回归传统礼教。
一、社会失序与对“礼”的调和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特别强调了《西厢记》的“主脑”:“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6)李渔:《李渔全集》卷3《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页。何为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意也。”(7)李渔:《李渔全集》卷3《闲情偶寄》,第8页。李渔认为,《西厢记》的主脑是白马解围,作者的立意也是白马解围,并不是反礼教和女性解放。
何为白马解围?《西厢记》开篇即上演了官军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事件,他在独白中交代了天下大乱的背景:“方今上德宗即位,天下扰攘。”(8)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6页。他围寺逼婚的理由是:“因主将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9)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6页。此处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方今……天下扰攘”说明当时世道已乱;其次,孙飞虎的身份是官军,却在河桥一带劫掳良民,说明乱世之中官军与贼寇无异。此情节的设置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现实的写照。官府的职责本是保一方平安。然而,元代很多地方官府公然侵夺百姓、苦害良民,“专以掊克聚敛为能,官吏相与为贪私以病民。”(10)宋濂等撰:《元史》卷159《宋子贞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736页。成为百姓灾难的直接根源。
官府与官军搜刮民脂民膏的办法很多,除了剧中孙飞虎的直接劫掠,还通过捕盗之名,为己谋私,并将此作为便捷而广泛的生财之道。据姚燧《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记载,相邻的官府彼此勾结,“吾得盗,必使诬汝县富室”(11)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29《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45页。。此地抓获盗贼后,讹诈彼地的富室之家,使对方感恩戴德,获得钱粮补偿;另一地官府抓获盗贼后,亦可讹诈此地之富人,“易地为之,胥相益也。”(12)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29《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第445页。捕盗为假、谋财为实。对此,姚燧悲叹道:“尉乎,御盗欤?师盗欤?”(13)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29《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第446页。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凡是数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14)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29《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第446页。并且有很多县尉都采用这种方法发家致富。
甚至,官府为了更加便利地抢劫、盗窃,还明目张胆地与盗贼勾结,反将无辜的告发者诬陷为盗贼。《元史》记载,至正年间,丰润县(河北省唐山市)一个被判死刑的少年在临死前说出了自己入狱的全过程:“昏暮三人投宿,将诣集场,约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间,见数人如有宿约者,疑之,众以为盗告,不从,胁以白刃,驱之前,至一民家,众皆入,独留户外,遂潜奔赴县,未及报而被收。”(15)宋濂等:《元史》卷183《王思诚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212—4213页。无辜的少年成了群盗的替罪者。在这样的社会中,百姓的正常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可见,地方官府与官员为了个人利益,丝毫不考虑百姓的死活,这种以执行公务为名掳掠财物的行为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比真正的盗贼更加可恶,成为百姓灾难的直接根源。
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的情节正是当时社会乱象的缩影,官军迫害良民,直接导致了百姓的灾难,“这厮每于家为国无忠信,恣情的掳掠人民。更将那天宫般盖造焚烧尽……”(16)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8页。作者借此情节提出一个问题:在社会混乱、正常秩序被颠覆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原有的婚约?是保全性命,还是僵化地遵守教条?崔莺莺考虑再三,自愿献身以救一家老小与寺庙众僧:“孩儿有一计,想来只是我与贼汉为妻,庶可免一家儿性命。”(17)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8页。老夫人则站在礼法的角度怜惜莺莺之贞洁:“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18)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8—69页。莺莺与老夫人的较量,实则是作者的纠结、盲目、不知所措,天下太平、秩序井然之时,固然应当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天下已乱、社会失序之时,是否还应当坚持维护虚礼?最终,夫人想出一计:“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19)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9页。理由是小姐的贞洁比门户之见更为重要,“强如陷于贼中”(20)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9页。。作者借老夫人之口给出了答案,乱世之中,“礼”可适当予以调和,生命高于一切。
同时,白马解围事件为崔张二人的结合提供了合理性条件:官军围寺逼婚,已定婚约的郑恒显然不如一个素昧平生但可搬得神兵的张生。老夫人的诺言与张生对崔府上下的救命之恩,给了崔莺莺夜会西厢一个合理合情的理由。这让莺莺对礼教的反抗成为泡影和意外,更无法说明崔莺莺所代表的贵族阶级女性的个人意识觉醒,以及对传统礼教的反抗。
而崔张感情的每一次推进,都与白马解围事件下老夫人的诺言与报恩之义紧紧绑定。崔莺莺第一次主动联系张生,是因老夫人悔婚导致张生病重,故让红娘送简,探望其病情,“谢张生伸志,一封书到便兴师……若不是剪草除根半万贼,险些儿灭绝户了俺一家儿。”(21)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28页。莺莺第二次主动联系张生,仍是出于报恩之心,因跳墙私会的失败,使张生病情越发加重,红娘一针见血道:“莺莺呵,你送了他人。”于情于理,崔莺莺都不能于无动于衷,于是才发生了夜会西厢事件。若没有老夫人的许婚悔婚与莺莺的报恩之义,则不会有崔张二人的越轨行为。
于张生而言,虽然崔莺莺与郑恒已有婚约,但他当时并不知情,老夫人的许诺虽不符旧礼,但为他在“义”的层面上进行了支撑。因孙飞虎抢亲一事本已破坏正常的礼教秩序,在无“礼”可循的非常规情况下,崔莺莺与郑恒的婚约自然也暂时失去了礼的约束。作者通过此情节用强化的“义”盖过了“礼”。
二、崔张心中的礼教烙印与发乎情止乎礼
前人对《西厢记》表现的“情”已有很多论述,郭沫若先生早提出过:“《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22)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387页。细品剧本,作者从未将“情”提升到冲破传统礼教的高度,也自始至终都没有与“礼”决裂。相反,王实甫对崔张故事的叙述既突出了情的可贵,又写出了其思想深处的礼教烙印,发乎情而止乎礼。
张生在内心深处并未真正突破与反抗传统礼教,他的所有举动只是情之使然,而终止于礼。张生一出场,便面对滔滔黄河发出一番感慨,“小生……学成满腹文章……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23)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7页。气势不亚于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一个饱读诗书、满怀抱负的传统儒士形象跃然纸上。心中只有功名与前程的张生在遇到莺莺后,春心萌动,神魂颠倒,于是见到红娘便忍不住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中州洛阳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先父曾官拜礼部尚书,一生清廉,故此小生家境清寒,尚未娶妻。”(24)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30页。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张生,竟跨越了男女隔离的界限,主动自报家门,这种行为显然与他的儒士身份不相符,所以才会引来红娘发笑,并被骂是个“书呆子”。剧中多处展现了张生引人发笑的一面,这在常人看来,的确是一个“傻角”。张生的言行之所以能产生喜剧效果,是因为其行为与身份产生了背离,背离性的根源在于作者与剧中的其他角色有一个共同立场,即推崇传统礼教、维护先王之礼。而最具挑战性的跳墙私会与夜会莺莺的情节,却是因误会和红娘撮合而致,这也不得不说是作者刻意为之。王实甫之所以将崔张二人的越轨行为写成外力推进的结果,是因为张生丝毫没有反礼教的想法,作者也是认同传统礼教的。
谈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前人的研究将崔莺莺作为榜样,认为她在与整个封建礼教制度作抗争。其实不然,从小生活在深宅大院的千金小姐,已然将礼教刻进骨髓,在与张生的交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的性格特点,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言行。崔莺莺见到张生后,心生好感:“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25)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67—68页。但这种好感仅存于内心,没有丝毫表露。直至老夫人悔亲,张生相思成疾,莺莺对张生充满了担心与忧虑,但面对张生的书信却摆出闺中大小姐的样子愤怒道:“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26)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38页。然而她读完信后又修书一封,同时遮遮掩掩,假意撇清关系,让红娘转达兄妹之情。张生因误会莺莺诗意而跳墙赴约,莺莺的内心也渴望与张生互诉衷肠,但她深知礼法不允许如此,更无法真正卸下传统礼教对她的束缚,故对张生当场翻脸:“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27)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55页。崔张二人的这次赴约表面看似乎是对礼教的有力冲击, 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失败的。
崔莺莺前后矛盾的言行正说明了她无论从行为表现还是内心深处,都深受当时礼教的束缚,她深知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相国小姐的身份和社会要求,所以才会言行不一、前后反复。在追求爱情上的一点叛逆是崔莺莺的起点也是终点。
崔莺莺依旧是被传统礼教束缚的女性,即使她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进步,也是在个人情感无法克制下的自然流露,她在“情”与“礼”发生冲突时仍旧选择了“礼”,没有背弃自己的小姐身份和儒学传统。正如金圣叹所言,崔莺莺是遵循礼制的:“夫才子之爱佳人则爱,而才子之爱先王则又爱者,是乃才子之所以为才子。佳人之爱才子则爱,佳人之畏礼又畏者,是乃佳人之所以为佳人也。”(28)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69页。她对礼制的遵循在送张生赶考之时可见一斑:“【幺篇】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29)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95页。“【朝天子】眼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头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30)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95页。“此一行,得官不得官,急早回来者!”(31)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96页。不仅表现出她对功名利禄的唾弃与对来之不易的爱情的珍重,更流露出她对母亲让自己和爱人分别的满腹委屈、怨恨,但她没有任何反抗的行动,对母亲的安排持屈从态度。崔莺莺的内心十分复杂,若张生如愿考取了功名,则有“停妻再娶妻”(32)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97页。的风险;若没有高中状元,则她可能在母亲的逼迫下嫁给郑恒,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她思想深处的礼教烙印,才有了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冲突,并由此构成了《西厢记》的曲折情节。
所以,按照人物对待爱情的态度,来寻找反抗封建礼教的证据并不可靠。我们不仅要看到主人公对待爱情的态度,更应探讨其藏于内心深处的思想。崔张二人终究未从根本上冲破封建伦理的阻挠,也没有像元代社会的很多男女一样私奔外逃,而是变相地回归传统礼教——张生考取功名,方可迎娶莺莺。可见,作者并没想通过他们抨击传统婚姻,二人最终完成了传统的父母之命、门当户对、明媒正娶、喜结连理。
再谈红娘,她是《西厢记》中最出彩的角色,也是崔张二人感情的重要推动者。前人的研究也将其作为冲破封建礼教的典范,如郭英德先生所言:“元杂剧作家热情赞扬那些无私地帮助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的婢女。《西厢记》里的红娘最为光彩夺目,她始终站在封建叛逆者的一边……”(33)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其实不然,她与崔张二人一样,亦是处处谨遵并维护礼教的楷模。红娘的身份是崔莺莺的婢女,她在崔张之间起到了传话、送简的重要作用,但在与张生的初期接触中却处处申之以礼。张生因爱慕莺莺,见到红娘便自报家门,红娘却答道:“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4)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30—31页。又告之崔家是严守礼教之家:“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35)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31页。这是红娘第一次向张生展示了“礼”的威力。第二次是崔莺莺与红娘在花园烧香之时,张生与莺莺隔墙相和、互诉衷肠,待崔莺莺情不自禁,“我拽起罗衫欲行”(36)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47页。时,红娘再次申之以礼防,“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著。”(37)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47页。显然,红娘有明确的男女之防的礼教观念。
经过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的事件,张生一纸书信退去官兵,目不识丁的红娘也不免增生好感:“衣冠济楚庞儿整……据相貌,凭才情,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38)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93页。但也仅限于好感,她深知自己的丫鬟身份与书生的身份相隔甚远,所以没有任何逾越的想法。直至崔母赖婚之后,红娘开始为二人穿针引线、来回奔波,对此,学界评价红娘充满了侠义精神,以及对崔张二人爱情的同情。其实不然,在传统社会中,婢女随主子一同出嫁,是“媵妾”文化的内涵之一, 媵是正妻的姐妹,而妾则是陪嫁奴婢,地位比普通的妾高很多,已算得上是很好的出路了。在莺莺第一次到花园烧香许愿时,红娘便帮其道出了难以言说的第三桩愿望:“姐姐不祝这一柱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39)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46页。对红娘而言,“媵妾”是最佳出路。因此红娘对张生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对自己未来的筹谋,她虽言语犀利,但从根本上无从反抗这种礼教制度。
三、伦理失范与对“礼”的强化
崔张二人的越轨行为,曾被认为是反封建礼教的有力证据。并非如此,首先,二人夜会西厢之举并非毫无伦理的野合,而是有老夫人的许诺在先,并加入了报恩之义。前已论述,此不赘言。其次,元代由于受到胡风国俗的影响,男女之间的交往也更加自由、开放,甚至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案件。崔张二人的结合也并非作者为表达反礼教意图而有意为之,只是对当时伦理状况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反映。对此,王实甫在大的情节与小的细节处理上,处处强调“礼”之可贵,鲜明表达了乱世中的情需要以礼约束的观点。
从元代的实际环境来看,婚嫁观念的确较为松动,女性的社会活动增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比以往更加自由。尤其在北方地区,本已受到女真族一百多年的影响,加上元代蒙古族习俗的再次浸染,律法长期处于紊乱状态,所以男女之间的隔离并不像其他朝代那么严密,社会上呈现出礼防松动、甚至道德失范的状况。维护封建伦理的文人发出喟叹:“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40)宋濂等:《元史·列女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793页。这是对元代女子放任越礼之世风的笼统概括。
在儒家文化系统中,夫妻关系被认为是世间一切秩序与礼义的源头,“夫妇乃人伦之首”,将夫妻直接与人伦联系起来,婚姻是十分慎重而庄严的事情。草原游牧民族对待两性关系则较为随意,以成吉思汗为例,其年轻时,妻子为敌人所夺,待其势力发展壮大之后,又将妻子夺回,对此,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后,成吉思汗还将这位爱妻赐予了一位军功卓著的将领,并且声明她是贞节而美丽的。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大众的两性观念便可想而知了。在日常生活中,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准则不复存在,孛术鲁翀在《知许州刘侯民爱碑》中记载了“惮严其舅姑而私窜外”者与“嫁而奔人”者,陈基在《离伦妇》诗自注中记载了“见夫久贫辞去”的情况,更有丈夫典雇妻子的现象。这些行为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导致家庭极度不稳固,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其实,《西厢记》所上演的崔莺莺与张生、郑恒之间的婚约纠葛在元代并非个例,女子违背原定婚约而另嫁他人的现象十分普遍。江浙行省晋宁路总管曾说:“今百姓之家,始于结亲,家道丰足,两相敦睦……女家不放婚娶,遂生侥幸,违负元约,转行别嫁,亦有因取唤归家等事,遂聘它人者。”(41)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18《户部四·嫁娶》“订婚不许悔亲”条,第631页。可见,两家定亲之后,女方违背约定而另嫁他人的现象不在少数。相关记载在元代史料中也有很多,如至元六年(1269)的一则案例:“(李仲和)凭媒将女丑哥聘与郭伯成[男]驴儿为妇,受讫财钱三十五两、红花等物定婚,未娶过门。又于至元七年,受讫石驴儿财钱一十五两,召入舍为婿。”(42)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18《户部四·嫁娶》“订婚不许悔亲”条,第619页。案件中的李仲和原本接受了郭伯成家的财礼,将女儿许配于郭伯成之子,但未曾迎娶过门,又接受了石驴儿的财钱,并将其招为女婿,由此而引发了经济纠纷与社会矛盾。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这种行为“启侥幸之路,成贪鄙之风,不惟紊烦官府,实为有伤风化。”(43)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18《户部四·嫁娶》“订婚不许悔亲”条,第631页。并建议官府严禁此类现象的发生,但是,民众的整体道德水平已然下滑,悔亲别嫁的行为禁而不止。
不少男性也同样失去了基本的道德观念,近乎于买卖妻子的典雇婚现象在元代的江浙地区盛行起来。所谓典雇,即丈夫将妻子典于其他男子,在约定期限内生子后返回。《通制条格》记载:“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如同夫妇。”(44)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4《户令·典雇妻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0页。由于官方缺乏教化,典雇妻子的现象在百姓中流行起来,据胡长孺《陈孝子传》记载,陈泽民在钱塘典雇了一位王姓的女子,为他生得一子,名为陈斗龙;王氏按照合同在期限满后离开,又嫁给了一个姓施的人。很多年后,陈斗民“访求母亲”(45)苏天爵:《元文类》卷69《陈孝子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00页。,并在施家留住三日而返回,说明百姓是认可此事的,无需再遮遮掩掩。典雇妻子的现象不仅在民众中盛行,还实现了合法化,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雇人之妻为妾,年满而归,雇主复与通,即以奸论。”(46)宋濂等:《元史》卷104《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654页。法律禁止合同期满后男女双方继续交往的行为,而并不禁止典雇行为,说明典雇妻子的做法是被法律认可的。对此,孔齐哀叹道:“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47)孔齐:《至正直记》卷2“浙西风俗”,中华书局,1991年,第48页。被典雇的女子在张家住两年,又在李家住三年,自然无所谓有无丈夫、有无子女。可见当时的风俗之薄。
面对元代伦理失范的现实状况,王实甫没有摒弃延续千年的儒学伦理传统,而是强调了礼的重要性。所谓的反封建礼教与女性解放观点只是今人从一些片面表象按图索骥。
崔张二人的爱情之路虽十分艰难,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流露出与传统礼教相决裂的态度,相反,儒家伦理观念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老夫人悔亲之后,张生夜下抚琴,崔莺莺不觉泪下,“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48)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17页。她也同样难过、悲痛,她的真实想法是“紧摩弄,索将他拦纵”(49)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18页。,而实际上却默默离开了花园,因为她清醒地知道何为妇德。之后,二人情感的推进离不开红娘的巧妙周旋,但崔莺莺一直没有在红娘面前表露心声,是相国千金的小姐身份约束着她,也是与丫鬟的阶级差距压制着她,而这一切都折射出了传统礼教在崔莺莺心中的地位。
夜会西厢一事因崔母许诺在先,二人的结合既合“情”也合“义”,但是否合“礼”呢?从二人共赴云雨后的对话可窥探其真实想法:“(末跪云)谢小姐不弃, 张珙今夕得就枕席, 异日犬马之报。(旦云)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末云)小生焉敢如此?”(50)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76页。
白头之叹是一个典故,意为被弃的感叹。《西京杂记》卷三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51)刘歆:《西京杂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不难看出,崔张的结合虽有“义”做支撑,但他们都清楚,这样的婚姻尚不能算作真正的合“礼”。翻云覆雨后,莺莺的惶惶不安与张生的心有余悸都在表达:儒家传统的婚姻观念从来没有从主人公的内心消失。尽管老夫人的许婚又悔亲为崔莺莺的主动献身提供了一丝理所当然的勇气,但她知道这是极不合“礼”又有很大风险的下下策,这种行为的受害者恐怕终将是自己。这种认识与所谓的女性解放意识相差甚远。
事情败露后,红娘劝老夫人:“目下老夫人若不息此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52)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86页。红娘之意正是作者之意:恕其小罪而完其大事,既可遮盖二人婚前私会的无“礼”之举,又能报答张生的救命之恩,还可维护老夫人“治家之严”的名声。这在大众看来,仍是“父母之命”下的传统婚姻,只是在进入婚姻前产生了爱情这一催化剂,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婚姻才是符合人性的进步婚姻。
男女结婚需门当户对,这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传统婚姻观念,也是作者所认同的儒家文化。所以当崔母提出“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53)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187页。的要求时,张生欣然拜谢。因为功名对张生而言,不是强加于他的不合理要求,而是他所认定的人生价值,是他毕生的追求,作品在他一出场时便交代了“往京师求进”(54)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第7页。而途径普救寺的背景。故事以张生考中状元,与莺莺顺利结婚结尾。这一结局的设置正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婚姻观的回归。这一婚姻果实来之不易,既有崔莺莺的以身相许,更有张生对功名的不弃,张生以自身的努力改变了身份,使二人门当户对。努力的结果不是反抗礼教,而是回归礼教,使他们的爱情符合礼教的规范。
总体来看,他们“不合规矩”的行为只是在试探传统婚姻观的边界,是在其束缚下的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是与老夫人的互相妥协与无奈。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正名,更没有为婚姻前的自由恋爱正名,相反,是在老夫人的督促下考取功名,走上符合传统礼教的道路。所以二人的结合不能算是反封建的典范,相反是对传统礼教的变通继承与回归。同时,作者也是在伦理失范的元代社会向人们展示了传统婚姻秩序的可行性与可贵性。
四、结语
孟子在《滕文公下》中早提出过:“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5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第107页。孟子明确讲到,钻穴隙与逾墙行为是“国人皆贱之”之举。《西厢记》最引人非议的情节——跳墙赴约与夜会西厢显然非无意之举,但王实甫的用意与孟子不尽相同。孟子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理想,他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理念,而王实甫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提出了此愿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面对元代“礼崩乐坏”、纲常紊乱的现实状况,王实甫肯定情之可贵,也赞扬礼的重要,他在认同传统礼教的前提下,合乎时宜地对礼教进行了调和,以情释礼,融情于礼,并强调对传统礼教的回归。
——从曲中的副词分析崔莺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