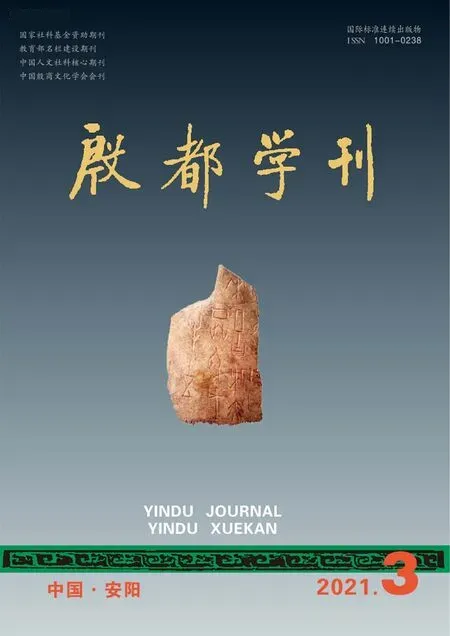重审经史关系:经学视阈下的汉代史书编撰
黄海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人事教育处,云南 昆明 650034)
范文澜先生曾说过:“‘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5页。因此,历代学者不可能不研究经学,而研究经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同出一源的史学、涉及到经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主要讨论的是二者的尊卑,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2)黄海涛:《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先秦两汉经史关系的转变及原因》,《理论月刊》2020年第6期。。此后关于经史关系的研究虽有拓展,但主要侧重于讨论经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对史书编撰过程中的经学影响关注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如许凌云先生认为:“孔子、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的则在思想方面。”(3)许凌云:《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吴怀祺先生强调:“不研究经学就不可能理解史学,特别是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的史学思想。”(4)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故此,本文以汉代为例,从史料的来源与取舍、史书体例的形成、治史方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专门探讨经学对史书编撰过程的影响。
一、“考信于六艺”:经学与史料的来源与取舍
汉代经学的繁盛推动了儒家经传的复出、诸子百家著述的再现,为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著《史记》,虽搜求广泛、采录宏博,但最重要的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六经不仅是汉代史家著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也是其选择史料及判断史料价值的主要标准。
(一)六经与史料来源
六经作为先秦重要文献资料,是汉代史家撰写先秦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时的主要史料来源。《史记》作为通史,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司马迁本人也在《史记·殷本纪赞》中指出:“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6)《史记》卷3《殷本纪》,第109页。
首先是对《诗》的采用。白寿彝先生指出:“《殷本纪》《周本纪》里面很多材料来自《诗经》。《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儒林列传》里也提到了韩诗,但没有采用。”(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云:“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8)《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第1519页。
其次是对《书》的采用。如《史记·五帝本纪》云:“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9)《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6页。取自《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10)《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18-119页。又如《史记·夏本纪》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11)《史记》卷2《夏本纪》,第77页。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2)《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53页。
再次是对《礼》的采用。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13)《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页。《正义》注云:“聪明,闻见明辨也。此以上至‘轩辕’,皆《大戴礼》文。”(14)《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页。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5)《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1-12页。取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16)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页。
最后是对《春秋》的采用。由于《春秋》经传本身就是史书,司马迁著《史记》,春秋时期的史实多抄录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左传》。顾炎武指出:“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1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31页。举《左传》与《史记》对照,知此言不诬。如《左传·襄公五年》记载:“季文子卒。大夫入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18)《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37页。《史记·鲁周公世家》基本抄录《左传》原文,只是略微改动语言文字:“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19)《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第1538页。
以儒家经传为基础史料的并非只有《史记》。刘向亦“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20)《汉书》卷36《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7页。。张涛先生指出:《列女传》“卷一《母仪传》今存的十四篇传记中,有九篇主要采自经传”(21)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先秦至西汉文献,撰成《别录》《七略》,其中儒家经传占了很大部分。班固所撰《汉书》,虽断汉为史,但其十志所记典章制度关系到先秦到西汉的发展沿革,也有很多地方采用儒家经传,在《汉书》纪传的赞、表、志的序中,多次采引经义进行分析与评价。
(二)六经与史料取舍
汉代史家不仅把六经作为史料,还把六经作为选择史料及判断史料价值的标准。按司马迁之言,他所采用的史料除了“六经异传”,还有“百家杂语”。六经异传属周代王官之学,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可靠的,但诸子百家学说中夹杂着传说甚至神话,真实性就不能保证了。因此,必须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辨别,并树立一个取舍的标准,司马迁取舍史料的标准就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
如汉代流传的有关黄帝的传说非常多,《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黄帝书》一百篇,神仙家《黄帝书》六十一卷,多是人神杂糅。《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有请风伯、雨师、天女助战的描写。关于黄帝的死,也有升天成仙的神话。古代有关鲧、禹的神话传说也很多。如《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2页。《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23)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译注:《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1页。《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24)《汉书》卷6《武帝纪》颜师古注,第190页。
司马迁没有采用这些神话传说,而是按照六经来进行论载。有关黄帝的记载,主要是采用《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对于涿鹿之战,他摒弃神话传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仅作如下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25)《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页。至于黄帝的死,他不采用乘龙升天的传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仅记载:“黄帝崩,葬桥山。”(26)《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0页。关于鲧禹治水,则主要采用《尚书》中《尧典》《大禹谟》《禹贡》等篇章记载,鲧窃息壤、鲧死化为黄熊、禹化熊通山、涂山氏化石生启等神话一律不予记载。
不仅仅是司马迁在史料上“考信于六艺”,汉代其他史家也以六经作为判断史料价值的标准。譬如刘向曾评价《晏子》八篇中有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27)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2页。。班彪更是树立了“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28)《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的治史准则。班固继父业,著《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29)《汉书》卷100下《叙传》下,第4235页。。可见班氏父子分析取舍史料的标准亦是“依五经”“同圣人”。
二、“为春秋考纪表志传”:经学与史书体例的形成
经学对汉代史书编撰的影响也表现在史家对史书结构的安排上。追根溯源,纪传体的产生是儒家经传及经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在史书编撰过程中,无论是立名定目,还是内容编排,汉代史家都会选择经学作为最终依据。
(一)纪传体形成的经学根源
唐代刘知几最早论及纪传体与儒家经传的源流关系。《史通·列传》云:“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30)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史通·书志》云:“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31)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第42页。清人王鸣盛亦认为,《史记》的体例是“司马取法《尚书》及《春秋》内外传”(32)王鸣盛著,黄曙晖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页。而创立的,其“八书”深受《礼》的影响,“《史记》八书,采《礼记》《大戴礼》《荀子》、贾谊《新书》等书而成”(33)王鸣盛著,黄曙晖点校:《十七史商榷》,第25页。。白寿彝先生发挥刘知几的观点,指出:“纪与传的关系,可以比作‘经’与‘传’的关系。世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世家的内容有时起本纪的‘传’的作用,有时起列传的‘经’的作用。”(3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第352页。
司马迁首创纪传体,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班固对其进行了改革和补充,把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改为四体(纪、表、志、传)。班固的改革同样以经传形式为指导,将“本纪”改为“纪”,把项羽从“纪”中剔除,使“纪”规范为帝王的编年大事记,又将“列传”改为“传”,把“世家”并入“传”中,以“传”释“纪”,如同《春秋》各传解经一样。经过改进,《汉书》的纪传体例布局严整、井然有序,后世史家纷纷效法,奉为史书之楷模。
纪传体的产生和完善不仅受到经传体例的影响,也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譬如朱政惠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对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他指出,“天人合一”思想从《诗经》的“天生蒸民”和《易传》的“与天地合德”发展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直接导致了纪传体史书《史记》的问世(35)朱政惠:《“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庞天佑先生认为,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循环思想与对纪传体断代史的创立有着密切关系(36)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
(二)立名定目的经学背景
先秦各国史书,秦曰“记”,晋曰“乘”,楚曰“梼杌”,鲁曰“春秋”。而“春秋”则为当时史书的通称。如《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37)《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728页。《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38)《史通·六家》引《墨子》佚文。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第8页。孔子修《春秋》以后,又有史书《左氏春秋》《楚汉春秋》等。因此,无论是从以往惯例还是从司马迁对《春秋》的推崇来看,《史记》更应该以“春秋”为名。
司马迁著史,与孔子作《春秋》相比,效法孔子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他本人却对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39)《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9-3300页。而序目中“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作《殷本纪》第三”等一百三十个“作”字又赫然在列。司马迁著史效法于《春秋》,而又不敢言明,是因为随着经学的确立,“五经”已成权威,不能随意模仿了,书名自然更不能僭称“春秋”了。
除书名受到经学的影响外,《史记》内目亦多依托经典。五体之中,“表”之名源于《礼》,司马贞注“三代世表”曰:“《礼》有《表记》(40)《史记》卷13《三代世表》索引,第487页。;“书”之名源于《尚书》,范文澜先生认为“八书之名,本于《尚书》”(41)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页。;“传”之名源于解经之传,如《谷梁传》《公羊传》之类。“八书”之中,《礼书》之名源于《礼》;《乐书》之名源于《乐》;《律书》之名引经“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42)《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27页。;《历书》之名引经“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尓躬”(43)《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
《汉书》名目的确立同样受到经学典籍的影响。《汉书》之名的由来,班固并未明说,刘知几认为:“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44)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第18页。《尚书》中有《虞书》《商书》《周书》之目,依照此例,断汉为史当然应称《汉书》。瞿林东先生也认为:“班固又以‘书’名汉史,意在仿效《尚书》之义。”(45)瞿林东:《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汉书》以“书”为名,便改《史记》五体之一的“书”为“志”。《汉书》“十志”之名皆依经典,最能彰显经学影响。作者多在各“志”开头,罗列所依经典,指明立名缘由。譬如改《史记》之《平准书》为《食货志》,开篇即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46)《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17页。改《史记》之《封禅书》为《郊祀志》,开篇即为:“《洪范》八政,三曰祀。”(47)《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189页。改《史记》之《天官书》为《天文志》,又新立《地理志》,正合《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48)《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77页。
(三)结构编排的经学依据
《史记》五体创立多根源于经典,前面已有介绍。此外,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之数目也各有依据,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49)《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之类。范文澜先生认为:“本纪十二,实效法《春秋》十二公而作。”(50)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二卷),第16页。张大可先生同意范先生的观点,指出:“‘本纪’效《春秋》十二公,故为十二篇。”(51)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同时,不仅仅是篇章数目,篇章次序的排列也深受经学的影响。“八书”之中,以《礼书》为首,《乐书》为继,毫无疑问是受《礼》《乐》次序的影响。
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妇女通史和独立的传记体著作,其结构体制也反映出经传的影响。清人章学诚指其“引《风》缀《雅》,托兴六义,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于诗经部次,庶几相合”(52)章学诚撰,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5页。,还是很有道理的。
《汉书》不但书名影射《尚书》,在篇数上也暗合。《汉书·叙传》云:“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53)《汉书》卷100下《叙传》下,第4235页。《尚书》在秦火以前,原有百篇,是汉儒之通说。如《法言·问神》云:“昔之说《书》者,序以百。”(54)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50页。《汉书·艺文志》云:“至孔子撰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55)《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6页。此外,《汉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这些数字都见于《史记》结构,寓意也应相似。
同《史记》一样,《汉书》篇章排列也各有经典为依据。如十志之中,以《律历志》为首,《礼乐志》为继,盖因《律历志》据《虞书》,《礼乐志》据《礼》《乐》,而“六经”之中,《书》在《礼》《乐》前。又《食货志》在《郊祀志》前,盖因《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56)《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9页。。《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以六艺为首,以诸子为继,这样排列是因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于道最为高”(57)《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8页。,其余九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58)《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6页。。
汉代史书在内容安排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详今略古。譬如《史记》共一百三十篇,记录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其中专记汉代人和事的就有六十二篇,另有十一篇兼记汉事,汉初一百年所占篇幅竟然比过去两千多年要多。这种详今略古的做法同样是经学影响的结果,如《诗经》《尚书》等经典在内容上都明显贯彻这一原则。而班固更是将这种传统发扬到极致,断代为史,干脆只写今、不书古了。
三、“以一字为褒贬”:经学与治史方法的选择
孔子整理历史文献、删定六经,有一定的方法,蕴含在六经之中,如《春秋》的史法和史义,便深为后世所称道。汉代去古未远,史家治史之法多源于经学,包括记事的方法、议论的方法、注释的方法和引用的方法等等。
(一)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指孔子修《春秋》时“以一字为褒贬”(59)《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07页。的一种褒贬用讳手法。后世儒者均认为其中蕴含“微言大义”,具有政治目的。《左传》以史事解经,归纳出了《春秋》褒贬用讳的各种义例,往往用“凡”字引领,晋代杜预统计有“五十凡”。司马迁对《春秋》的褒贬笔法极为推崇,《史记》中的褒贬手法就深受春秋笔法的影响。如《春秋》据鲁宗周、内诸夏而外夷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以此为依据为诸侯排序为: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春秋》对人物的称谓有严格义例,以正名分,如称吴、楚国君为“子”,齐国君为“侯”,宋国君为“公”。《史记》中人物称谓也各不相同,如孔子、老子、孙子、孟子称子,郦生、贾生、伏生、董生称生,荀卿、虞卿称卿。《史记》中破例为体之处,实则寓褒贬于其中。
《春秋》记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60)《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13页。。司马迁发展了这种历史记述方法,创立了“寓论断于序事”和“互见法”。纪实直书也是《春秋》基本书法之一。孔子非常推崇先秦史官的纪实精神,曾称赞晋国董狐的秉笔直书,其作《春秋》,便遵循古代良史的纪实书法,晋代杜预评价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61)《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06页。《史记》因此以实录著称,《汉书·司马迁传》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2)《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738页。既然在《汉书》中赞赏《史记》的实录精神,说明班固也是推崇纪实直书的。
但相较之下,《史记》主要发扬了《春秋》的褒贬之体和纪实精神,《汉书》则更重《春秋》的“正名”和“讳书”。《春秋》强调正名,要理顺君、臣、父、子的关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3)《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503-2504页。。《汉书》把项羽从“纪”中剔除,把“世家”并入“传”,改了《史记》中许多称呼,譬如改“项王”为“羽”,“陈王”为“胜”,“刘季”为“高祖”,“吕太后本纪”为“高后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正名分”。《汉书》中很多篇章有为尊者讳的书法。如《汉书·高后纪》删除《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毒害戚夫人、杀害赵王如意、封诸吕为王、暗害少帝等事。又如汉成帝本为酒色之徒,荒淫无耻,但《汉书·成帝纪》却全然不载。
《汉书》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代表,其重视正名和讳书也代表了后来史家应用春秋笔法的走向。如《东观汉记》对东汉光武帝至灵帝十一位君主,无一例外加以美化,吹捧他们“幼而聪明睿智,容貌庄丽”(64)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54页。,“幼而聪达才敏,多识世事,动容静止,圣表有异”(65)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76页。等等;又另创载记一体,用来记载虽曾称霸一方,但最终未能位居正统的人物,如刘盆子、隗嚣、公孙述等,放在列传之后,以凸显君臣名分。
(二)史论与史注
史论是史家对史事或人物发表的评论,如《左传》在叙述史事之后,常用“君子曰”的形式发表议论,有时也用“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以知”等,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议论方法。司马迁著《史记》,也沿用此例,以“太史公曰”发论,有篇前论、篇末论和篇中论三种形式,后人把篇前论称“序”、篇后论称“赞”、篇中论称“论”。当然司马迁本人并没有作此命名,《史通》之《论赞》《序例》篇正式称“太史公曰”为“赞”为“序”以后,论、赞才成通称。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虽继承自《左传》,但其使用比《左传》的“君子曰”更加系统,内容也更为广泛。《史记》全书,有序论二十三篇,赞论一百零六篇,论传五篇,共计一百三十四篇,“乃《史记》一书之血气”(66)张大可:《史记研究》,第252页。。《左传》和《史记》开辟的史论新形式,影响深远,为后世史家所效仿。刘知几总结道:“继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67)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第59页。此外,刘向的《列女传》各卷末尾亦用“君子曰”“君子谓”,《后汉书》“论”“赞”并用,《晋书》因唐太宗做评而称“制曰”,欧阳修《新五代史》用“呜呼”。总之,自司马迁根据《左传》“君子曰”创立系统的史论以后,论、赞便成了史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史家著史发表议论的主要方式。
史注是对史书正文的一种补充,有自注和他注。这种方法同样来源于经学,因为通过注释经典来阐发经义是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两汉经学繁盛,涌现出大量注经之作,这种风气很快影响到了史学领域。自注的开创,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瞿林东先生指出:“《史记》纪传部分时有‘语在某纪’、‘语见某传’,也都属于自注的性质。”(68)瞿林东:《中国简明史学史》,第163页。《汉书》也有自注,譬如《地理志》每述一个郡、县,就在名称下注明建置、沿革等,《艺文志》书名下注明作者姓氏、起讫时间等。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努力搜集材料注史,于是出现了一批他注,如延笃的《史记音义》、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等。这些史注不仅为阅读相关的史著提供了方便,而且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三)载言与载文
载言与载文是指在史书中记载人物的言论、编入已写成的文章。这种写作手法在《春秋》经传中便已大量使用,如《左传》虽以记事见长,但大量载言及载文,涉及《诗经》《尚书》《易经》《周礼》等典籍,以及各类古语、歌谣、谚语、俗语等。载言多孔子语,载文则多为儒家经典,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诗经》,有学者统计称:“《左传》18万余言,言《诗》之处凡277条,涉及《诗》152篇。”(69)张林川、周春健:《<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两汉史书的编纂之法深受经学的影响,载言载文之法也不例外。《史记》全载有用之文,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怀沙赋》《吊屈原赋》《鹏鸟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子虚赋》《大人赋》,《太史公自序》载《论六家要指》等。与《史记》相比,《汉书》载文更多,如《陆贾传》增载《治安策》《晁错传》增载《教太子》《言兵事》《募民徙塞下》等疏,《董仲舒传》增载《天人三策》等等。两汉史书亦多载孔子之言和经典之语。如《史记》在“太史公曰”中对经典就多有引用,至于班固的《汉书》之中,引用孔子和五经之言更多,甚至在文章开头,便罗列所依经典。前文已述,不再赘言。
在史书中引用他人言论和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譬如赵翼就认为,《史记》和《汉书》中所载的文章都是“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7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页。。白云先生指出:“在编纂史书时,适当地引用历史人物的语言或选录当时人的作品,不仅有利于表现人物,也有利于反映某些时代风尚。”(71)白云:《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2页。总之,经学著作引用之风的盛行,影响了两汉史著编纂引用之法。同时,两汉史著引用多孔子之言和经典之语,则更见经学影响的深度。
四、结语
周予同先生在《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经、史关系问题”(7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2页。列在首位,充分凸显了经史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经学和史学的关系,在两汉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张涛先生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以后,儒家经学跃居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的地位,并全面兴盛。”(73)张涛:《经学与汉赋的发展》,《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汉代是经学的繁盛时期,又是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经学因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而兴起,史学也因司马迁撰成《史记》、成一家之言而独立。在政权的支持下,经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对这一时期各家学术及学术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史学作为与经学有着同源关系的学术,自然更不例外。
经学对汉代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为汉代史学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但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史家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论、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还为史书编撰准备了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促进了史书体例的创新、提供了治史的方法。从史料来源来看,六经既是汉代史家著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其选择史料及判断史料价值的主要标准;从史书体例来看,纪传体的产生是儒家经传及经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在史书编撰过程中,无论是立名定目,还是内容编排,汉代史家都会选择经学作为最终依据;从治史方法来看,汉代史家记事的方法、议论的方法、注释的方法和引用的方法等,均源于经学。进一步考察汉代史书编撰过程中的经学影响,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经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