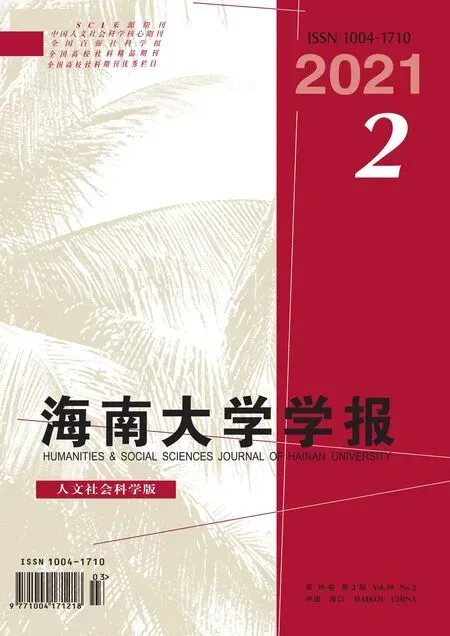婚姻关系与女性身份重构
——斯坦顿的女性主义婚姻思想阐释
常艳娇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她曾经在给另一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的信中表示:“只要女性在婚姻中仍然处于被降格被贬低的地位,那么争取女性地位的提高就是徒劳的……正确的婚姻观念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我认为整个女权问题都是围绕着婚姻关系这个中心展开的。”①Tracy A. Thomas,“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the Feminist Foundations of Family Law”,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6,p.73.对斯坦顿来说,要改变婚姻中女性的境遇,就需要对整个婚姻机制进行改革,而婚姻关系本身则是进行婚姻改革的核心,如果不了解婚姻的本质,那么对有关婚姻法律等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
一、对传统婚姻契约的超越
婚姻制度发展至今,有关其本质的理论有很多,在西方国家中主要以契约论为主,其契约属性得到了法律和宗教文化的认可与维护。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明确表示:“我们的法律认为婚姻就是一个民事契约……法律对待婚姻就如它对待所有其他的契约。”②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1: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79.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詹姆斯·威尔逊也认同婚姻的契约属性,认为婚姻作为政治主体的一个基本单位,是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共同构建的社会契约,而双方当事人同意是每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的核心。《圣经》中的先知则将上帝与以色列的盟约关系比喻成婚姻关系,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盟约,更是与上帝之间的盟约,如果不守约,即在背弃了夫妻间契约的同时,亦背弃了与上帝的盟约。
婚姻契约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生而平等、崇尚自由理念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建立平等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契约刚好提供了这一方式。然而事实上,婚姻契约并未真正实现婚姻关系中两性之间的平等。首先,在婚姻契约的签订上,女性处于静默和被忽视的状态。婚姻契约虽然强调双方同意,但是女性却被认为不具备签订契约的能力,“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③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此外,婚姻契约中的各项条款并非由婚姻中的当事人制定,反而受到联邦法律、社会文化、基督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制约。社会文化和基督宗教文化又以男性特权为特征,法律和政府体系则由男性主导,因此婚姻契约的制定可以说是以男性意识为出发点,优先考虑男性利益,女性并无任何发言权和参与权。其次,进入婚姻契约之后,女性自然而然地被囿于“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和文化,女性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份被终结,在婚姻契约中被降格和从属化。威廉·布莱克斯通在对普通法的阐释中指出:“通过婚姻,在法律上丈夫和妻子即变成一个人,也就是说在婚姻中女性的个体存在或者法律存在被终止,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或合并到丈夫的个体存在或法律身份中;妻子在丈夫的限制、保护和庇荫下,行使一切权力。”①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Book 1:Of the Rights of Persons)”,pp.284-285.“有夫之妇”的身份从法律上剥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公民身份、社会地位、个人自由和各项权利,并相应地转移到丈夫名下,保障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人和保护者身份,与此同时,妻子为了获得丈夫的保护和经济支持,需要尽到相应的服从的义务。此外,立法者用法律契约约束婚姻关系的同时又指出,婚姻制度不受法律契约的约束,而是受到“比契约和惯例更为强大的力量”的控制②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Matilda Joslyn Gage eds.,“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Volume I)”, New York:Fowler and Wells,1881,p.617.,并且以上帝的口吻教导婚姻中的女性要顺服男性。
因此,斯坦顿认为这种婚姻契约空有契约之表,实则是由男性创造和主导的婚姻契约。基于自由主义思想,她重构了婚姻关系和婚姻契约,以实现婚姻中两性之间的平等,使婚姻真正成为法律上的契约,而非仅仅借鉴契约的形式。自由主义的概念最早由约翰·洛克提出,发展到18 世纪晚期,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强调自然权利和平等。然而这种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又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提供了支撑,它所指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包括女性在内,而是特指人类中的男性。斯坦顿表示,天赋人权的理念法则应同样适用于女性,适用于婚姻,因此她在《感伤宣言》中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更正为“男人与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她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③Elizabeth Cady Stanton,“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1848),Joy Ritchie,Kate Ronald eds,“Available Means:An Anthology of Women’s Rhetoric”,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1,p.139.,反对一切阻碍女性发展和主张男尊女卑的法律。斯坦顿在《感伤宣言》中对一切主张男尊女卑法律的否定即是对妇女“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和文化传统的否定和拒绝,强调女性在婚姻中的自然权利和个人平等。
此外,在西方的传统中,婚姻契约被认为具有神圣性和不可破坏性,婚姻契约的缔结有上帝的见证和参与,上帝和宗教条文对婚姻契约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圣经》中对于婚姻契约有“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④《圣经——中英对照》(新标点和合本),香港:香港圣经公会2008年版,第1719页。的教导,且离婚被认为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影响社会文明的进程,因此婚姻契约不同于其他契约;同时它还受到联邦政府、民事法律和宗教的管控。但是斯坦顿认为,婚姻契约的缔结、维持、解体应该是私人化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婚姻契约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民事法律和宗教无权加以规范,且婚姻契约中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女性的权益也应考虑在内。因此婚姻应该如其他契约一样,“如果不能产生或促进人的幸福,理应不具备任何力量或权威;且废除它不仅是一项权利,更应该是一项义务”⑤Tracy A.Thomas,“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the Feminist Foundations of Family Law”,2016,p.131.。
总而言之,虽然国家、教会、普通法等认可婚姻的契约性,但是这一契约对女性来说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正如斯坦顿所言,是男性创造和主导的婚姻。斯坦顿在其女性主义实践中超越了传统的婚姻契约思想,主张“由平等的双方签订,过着平等的生活,且双方有平等的约束和特权”⑥Elisabeth Griffith,“In Her Own Right:The Life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04.的婚姻契约,这更符合契约对双方平等、权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婚姻契约的复杂性,它不仅受到民事法律的规范和限制,而且受到社会文化、教会和国家联邦政府的影响。斯坦顿对婚姻契约的改革不仅仅只是针对以男性特权为主的婚姻法律,同时还对社会文化、宗教等进行改革,削弱社会文化、教会、国家在婚姻的缔结、维持和解体中的作用。她对婚姻契约的重构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中一些问题的关注也不够深刻,但却促进了后来的婚姻契约的完善和发展。
二、对婚姻场域中不平等关系的批判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①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②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第155页.。由此可见,场域并不是客观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关系性的社会空间。这样,婚姻场域可以理解为,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后,以婚姻中的男女两性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遵循婚姻法律和社会文化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定的社会文化空间。
在传统的婚姻场域中,男性为了巩固其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和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这一私人领域中。美国的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与此同时,家庭的经济功能逐渐丧失,家庭结构缩小,男性走出家门寻找工作,主导了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职业,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法律等成为男性有绝对发言权的公共领域;相应地,女性被困于家庭领域中,成为家庭主妇,并承担养育儿女的义务。同时,在以金钱和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并不能产生表现为劳动报酬形式的经济效益,在家庭中的工作因此贬值,婚姻沦为女性用自己的服务和顺从换取丈夫的经济支持和保护的交易。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对共和母亲的推崇,强调女性可以通过对儿子的教育承担社会责任。共和母亲发展到19 世纪成为对真正的女性气质和居家主妇的崇拜,将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母亲的作用最大化,强调女性对于家庭幸福的重大影响,进而通过家庭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美德。这看似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给予女性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权利,实则通过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道德价值导向作用,更严格地界定了女性的活动区域,将女性禁锢在私人领域这一范围之内。
斯坦顿通过为婚姻中的女性争取财产权、无过错离婚等方面的权利,试图改变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中的从属地位。普通法规定,已婚妇女在法律上的一切权利都属于丈夫,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有绝对的所有权,并且有绝对的使用和处置权力,甚至包括她在婚姻中通过劳动获得的报酬。为了使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在婚姻中获得独立和自由,拥有财产权就是关键。在以斯坦顿为首的女性主义者的不断努力下,美国各州相继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保证妇女在婚姻中有独立的财产权、平等的继承权、订立契约的权利和子女的监护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保障了婚姻中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为女性争取子女的监护权提供了可能。在为女性争取财产权的同时,斯坦顿还为女性争取了离婚的权利。她对离婚的支持是建立在婚姻是平等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且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有不同意义的认识之上。她表示:“婚姻并不是男性生命的全部,他有无限的娱乐和消遣方式,可以以世界为家。他的生意、政治、俱乐部、与任何性别的友谊,都可以帮助他填补不幸的结合或分离造成的空虚。但是对女性来说,婚姻就是一切,是她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她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是她寤寐求之的东西。”③Elizabeth Cady Stanton,“Address to the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Ann D. Gordon, ed.,“The Selected Papers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Susan B.Anthony:In the School of Anti-Slavery,1840—1866”,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p.425.父权制社会以保护柔弱女性远离社会丑恶的名义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却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男性的暴行和伤害。女性作为通过诉诸离婚手段改变悲惨命运的主要群体,却在离婚问题上毫无发言权,相反,离婚是男性的特权,“男人制定离婚法,规定允许离婚的正当理由;规定双方分离后孩子的监护权;法律完全不考虑妇女的幸福”④Elizabeth Cady Stanton,“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1848),Joy Ritchie,Kate Ronald eds,“Available Means:An Anthology of Women’s Rhetoric”,p.140.。斯坦顿认为,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男性而非女性,且因丈夫对妻子绝对的法律和经济权利而加剧,如果逼迫女性与刻薄、专制、有酗酒和暴力等行为的丈夫在一起,则与公认的自然法则“人类必须追求真正的、实质的幸福”相违背。因此她认为,应该充分考虑妇女的个人利益和自身幸福,扩大离婚正当理由的范围,争取女性离婚后的赡养费和孩子的监护权,扩大离婚妇女的合法权利。
同时,对于斯坦顿来说,帮助婚姻中的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为女性争取投票的权利。投票权是公民的首要权利,对女性投票权的剥夺,使得女性在立法机构没有发声渠道,而只能由男性来代理,这封锁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政治生活的途径,使男性得以从各个方面压迫妇女。事实上,由男性代理妇女投票并没有经过妇女的默许与同意,只是从男性的视角和利益出发,自作主张地替女性做了决定,对女性来说是一种非自愿的代表。斯坦顿的女性主义思想以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为基础,自由主义提倡人人生而平等,那么女性跟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参政权;共和主义则重视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公民应该超越自身利益参与公共事务,因此女性也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此外,由于社会对女性相较于男性的道德优越性的认可,那么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特质更有助于她们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因此更有必要赋予她们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为女性争取投票权挑战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有助于改变目前以男性为主导的法律体系,保障女性其他权利的获得,“描绘了女性自治的前景,这是主张其他平等权利所无法达到的”①Ellen Carol DuBois,“Feminism and Suffrage: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46.。
斯坦顿对婚姻中女性从属地位的提高和女性境遇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单方面权利的争取,而是试图促进法律、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扩大女性从婚姻场域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路径。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权保证了妇女在婚姻中经济上的自立,同时也为妇女争取离婚自由权提供了必要条件;离婚法的改革,为婚姻生活不幸福的妇女提供了补救措施和其他可能;对投票权的争取则有助于妇女在政治、法律、教育、职业等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斯坦顿在婚姻方面的观点略显激进,受到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与抨击,因而未能在当时实现,但是,她的女性主义实践使当时的女性认识到了自己在婚姻场域中不平等的事实,提高了女性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方面的认识并努力追求之。
三、寻求婚姻场域中女性身份的建构
女性常常被视为第二性的存在,其身份通常通过男性来定义,而在婚姻关系中尤甚。婚姻中的女性身份完全由其丈夫决定,女性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存在,并根据丈夫和社会的需要来刻画完美的妻子、母亲的形象,从而规范了女性的身份建构,使得女性身份在婚姻场域中被迫消隐,甚至受到这种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自身也参与到了女性身份消隐的过程中。在女性主义实践中,斯坦顿着重于打破这种父权制社会构建的婚姻中的女性形象,谴责婚姻对女性身份的剥夺,意在使女性从自身出发,重新构建婚姻关系中的自我身份。
首先,整个社会文化塑造了女性是第二性的公共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特别是无处不在的基督宗教条文和教理使女性相信并接受她们应该被男性压迫和统治的事实,这使得当时的女性对女权运动持冷漠和反抗的态度,不利于女性重新构建其女性身份。斯坦顿在为婚姻中的女性争取权利的同时,抨击了以基督宗教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在妇女个体身份的消隐方面产生的影响。她曾经这样反诘:“在每个安息日,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讲坛上聆听着圣经中的这些教导,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和压迫是神圣启示的想法呢?”②Elizabeth Cady Stanton,“The Woman’s Bible”,New York:Europe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p.7.《圣经》以“上帝的话语”之形式建立权威,使得妇女接受其观念,并以其中观念理解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公民身份,从而导致女性自我身份的降格和消隐。她批判性地指出,男性为保障自己的权威性和维护父权制社会规范,对《圣经》进行了篡改和误解,两个版本的人类起源故事的矛盾,反倒证明了上帝并未明确说过让男性统治女性。斯坦顿还认为,《圣经》和《圣经》阐释对女性形象有意边缘化和丑恶化,因此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构了《圣经》和宗教教义,以改变女性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的盲从盲信,为女性重建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新福音。在传统的基督宗教文化中,男性以《圣经》中顺从虔诚的积极的女性形象和道德缺失、自私邪恶的消极的女性形象为例子,要求女性温顺柔弱、自我克制、勤俭持家。斯坦顿认为,《圣经》的这一教导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了。她通过挖掘那些被弱化的女性人物,发现被歪曲和否定的女性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为女性重建个体身份提供了模仿对象。斯坦顿指出,被视为原罪之源的夏娃有其反叛的一面,且夏娃偷吃禁果乃是因为被知识所吸引,这与斯坦顿提倡的完善对女性的教育和新一代女性应追求自我发展的形象不谋而合。应该说,要解放女性,首先应该让她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宗教等方面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和法律体系对她们生活的制约,相信男女两性可以享有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斯坦顿对宗教体系和《圣经》的批判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西方传统中,女性身份丧失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女性一旦进入婚姻,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名,被冠以夫姓。当妇女进入婚姻契约时,她的公民身份和法律关系即被纳入丈夫的法律框架,被认为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自己的姓名了。对男性的称呼通常证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对婚姻中的女性附属于丈夫的称呼则显示了她从属于男性的社会身份。女性的个体身份被隐匿在丈夫的权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霸权意识和对妻子绝对的所有权,证明了妇女低等地位的性别阶级体系。姓名象征着一个人的个体身份和尊严,因此斯坦顿在嫁给亨利·斯坦顿时,拒绝放弃自己的姓——凯迪,坚持使用自己的全名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而不是社交称呼亨利·斯坦顿夫人,这象征着她在婚姻关系中对自我身份的坚持和保留。与此同时,斯坦顿在婚礼仪式上也拒绝做出“服从丈夫”的承诺,在婚姻关系中她与丈夫是平等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服从的义务。对她来说,重建婚姻中女性个体身份的第一步可能就是使用自己的本名并在婚姻仪式中拒绝做出“服从丈夫”的承诺。这意味着女性不需要通过与丈夫的关系来定义她的身份,而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丈夫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而存在。
同时,为了维护男权制的社会体系和男性优越性,加强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和依赖,将女性纳入到基于男性权力明确划分的公私领域,男性从自身利益出发构建了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当时,斯坦顿所处的社会以所谓“真正女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崇尚“虔诚、贞洁、温顺、持家”的美德,认为女性的最大价值在于自我牺牲,为丈夫提供一个稳定、平和的庇护所①Bar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American Quarterly,Vol.18,1966,pp.151-174.。但是,对斯坦顿来说,女性注重自我发展比自我牺牲更重要,女性在婚姻契约中与男性是平等的,具有平等地享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她认为,在崇尚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感的时代,婚姻中的女性应该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承担妻子、母亲角色之外的个人身份,母亲、妻子、女儿、姐妹只是生活中偶然存在的附带关系,不能根据这种偶然存在的角色决定其作为个人、公民、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因此具有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的权利②Elizabeth Cady Stanton,“The Solitude of Self:Speech by ECS to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Ann D.Gordon ed.,“The Selected Papers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Susan B.Anthony:Their Place Inside the Body-Politic,1887—1895”,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pp.424-425.。
此外,斯坦顿还致力于改变女性纤弱的刻板印象,重建对美的认识。由于男性与女性性别上的天然差异,女性被认为天生软弱、敏感,斯坦顿承认两性的这种天然差异,但指出,男性不能因此认为女性身体上的柔弱是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应该处于劣势的理由。斯坦顿批判了女性通过束身衣、化妆品等方式改变自己的自然外表以迎合男性审美的社会现象,因为这种男性审美给女性传达了错误的观念,即以脆弱和虚假为美,以取悦男性为目的,其后果,给女性带来的除了生活的不便利和身体的伤害外,还有对女性定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特别是未来的年轻一代应该追求身体健康,摒弃女性天生软弱的观念,因此她建议在对女性的教育上应注重培养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另外,斯坦顿认为,真正的美不在于外表形象,而“更多地取决于智力、品味、情感和心灵,取决于使这个世界比你发现的更好的真诚无私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头发、眼睛的颜色或肤色”③Lisa S.Strange,“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the‘Coming Girl’”,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Vol.68,No.1,2002,p.9.。因此她注重对女性理性的教育,培养其理智和独立的精神,以更好地承担家庭之外的义务和责任。
总之,斯坦顿对婚姻场域、政治体制、宗教传统和社会文化的抨击和批判,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广泛觉醒,使她们相信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并没有必然地处于服从位置,相反,女性和男性享有天然的平等和自由。她自身对其本名的保留和对传统婚姻仪式的反叛,为女性重构个体身份提供了可资想象的路径和方法。此外,她对新一代女性气质和女性美的重建,打破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对女性进行了重新定位,强调女性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存在,而非取悦男性的附属品。
四、结语
与同时代的女权运动者相比,斯坦顿对婚姻关系的重构超出了婚姻制度改革的范围。她不仅着眼于为婚姻场域中的女性争取权利,而且主张从政治、法律、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女性独立身份的建构,以期改变婚姻关系中女性的降格与从属地位。斯坦顿从自然权利出发对婚姻的契约本质进行了重新阐释,主张婚姻契约应该由平等的男女双方签订,不应该受到宗教文化的干涉。与此同时,她谴责了基于男性的优越性和女性的劣等性假设来进行的对婚姻场域的公私划分,她对婚姻关系中妇女财产权的争取保证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经济独立,对女性投票权的争取则为女性从婚姻场域进入公共空间提供了途径。斯坦顿批判了宗教文化对女权运动发展和女性意识觉醒的消极影响,主张从社会文化改革、女性气质重塑和重新建构对女性美的认识等几个方面,来重新建构独立自主、崇尚自我发展的女性个体身份。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