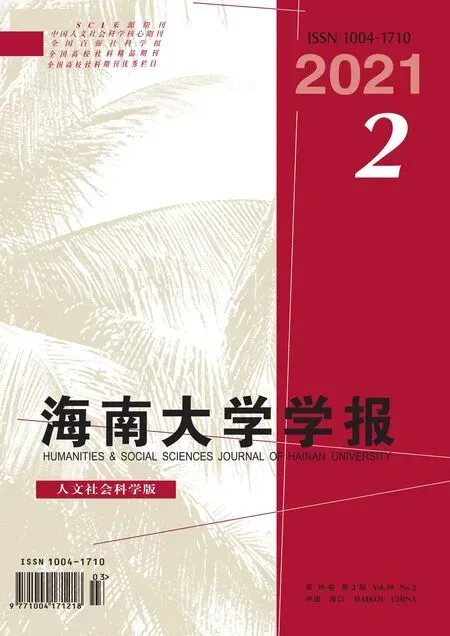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汉学路径
——兼论汉学家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及其价值
陈思思,梁 燕
(1.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361024;2.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9)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更是民族的。”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与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等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超越时空为世界各民族所传颂,就是因为他们“映照现实、启迪人心”“回归臻善、觉醒世人”,不仅为近代欧洲带来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曙光,也为世界增添了理性主义的思想光芒。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世界级瑰宝,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传世之作,成为当时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意大利民族的文化之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又多姿多彩,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与精神展现,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要完成文化复兴的伟大使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互通与互融,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我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已日益凸显。2019年,以文学、戏曲、文物、影视剧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交流,已向世人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有文化根脉、有现代追求的中国,一个敬畏历史、关爱生命、有智慧、有力量、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一个拥有多彩文明而又愿向世界共享的中国①梁燕:《2019: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交出漂亮答卷》,《光明日报》2019年12月31日第16版。。当今中国,文化盛宴异彩纷呈,我们将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方式阐释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艺术成为世界的艺术,让中国文化成为中西交流的纽带。
在中华文化走上世界舞台的进程中,以京剧、昆剧等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裒集中华民族之艺术精华,扮演着特殊角色。中国戏曲是一项伟大的艺术,据考证,第一位将中国戏曲传播到海外的是我国京剧武生演员张桂轩。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应当时华侨之邀,张桂轩赴日本长崎、东京、神户等地演出,而后又赴朝、俄等国演出,成为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先驱。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的欧美京剧演出更是在海外掀起了一股中国戏曲热。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京剧院为代表的各国内戏剧团纷纷到世界各地演出,使中国戏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中国戏曲的百年海外传播历程,也成了中国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文化的复写”①陈世华:《“古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76页。,而是一个双向度的互动过程。中国戏曲走上世界,不仅需要我国戏曲艺术家们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讲故事”,还需要海外戏曲研究者们从其自身国家文化语境出发展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用他们的研究范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海外汉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她用跨文化的、独立的学科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跨文化就是海外研究者用其本国研究范式研究中国文化;独立性就是汉学研究既不受西方学术框架束缚,又较少受到来自中国学界的影响。因此,开展对民族文化海外传播汉学路径的研究,既有助于突破我国国内已有的研究框架,又有助于拓宽当前的学术视野。在中国戏曲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施高德无疑是一位卓有贡献的研究学者,正如著名剧场导演菲力普·萨睿立(Phillip Zarrilli,1947-)所言:施高德“是第一位把京剧译成英语的人”②菲力普·萨睿立:《演员的“另类”戏剧艺术能力的培养——精神物理训练》,http://www.sohu.com/a/148930457_757705,2018年7月30日访问。,他在汉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是西方世界亚洲戏剧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一、汉学家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述略
施高德(Adolph Clarence Scott,1909—1985),美国现当代中国戏剧研究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翻译家。他致力于中国戏曲研究四十余载,完成多部著述,包括介绍戏曲艺术本体的《中国古典戏曲》(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讲解二十部传统剧目情节的《中国戏曲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介绍梅兰芳生平的《梨园领袖梅兰芳》(Mei Lanfang.Leader of the Pear Garden)、译介《四郎探母》等六部经典剧目的《中国传统戏曲》(共三卷本)(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 Volume I.II.III)、介绍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与艺术发展概况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in China)、讨论中国戏曲服装变迁的《演变中的中国服饰》(Chinese Costume in Transition)与回顾其二次来华期间工作与生活状况的《唱戏的是疯子——一名中国戏迷的随笔》(Actors are Madmen-Notebook of a Theatregoer in China)等。施高德不仅专门著书研究中国戏曲,而且在介绍其他国家戏剧的著作中,也将中国戏曲视为重要参照读物,如在《日本能剧》与《亚洲戏剧》等的阐释方面就大量引征了中国戏曲。纵观施高德戏曲研究著述,可以发现,他的戏剧研究立场,是以中国戏曲为核心的。在对中国戏曲的具体研究过程中,他不仅立足于包括诸如戏曲简史、舞台表演、戏曲音乐、舞台美术、剧本翻译、演出点评等戏曲本体的探析,还关注到戏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对社会状况的考察。
事实上,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不仅限于案头考察,他还做了大量努力来推动中国戏曲的社会化。施高德让中国戏曲走进美国社会的实践方式主要有三:其一,邀请中国戏曲艺术家走进课堂为西方学生亲身示范戏曲表演。受施高德之邀,著名昆曲艺术家张充和曾为威斯康星大学戏剧系学生表演《思凡》。一位学生在观赏《思凡》演出后写道:“中国戏曲用姿态和动作来加强语言和音乐,而不是将其取代……观众们陶醉于斯,并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艺术上的真实,是台词与音乐的有机结合。”③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2”,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p.vi.可见,中国戏曲艺术家的亲临演绎与现场互动在帮助西方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戏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二,亲自导演中国戏曲,并根据中西文化及语言差异做适当调试。1961年11月,由施高德导演的中国传统剧目《蝴蝶梦》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礼堂演出。考虑到中西文化与语言的差异,施高德大胆尝试“演员无需唱出咏叹调,慢条斯理地说出与伴乐搭配的台词”的演出方法④Liu Siyuan,“A.C.Scott”,Asian Theatre Journal,Vol.28,No.2,2011,p.419.,为《蝴蝶梦》的最终上演准备了条件,演出收获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大获好评。其三,在西方戏剧日常教育与训练中,掺入中国戏曲表演元素。20 世纪70年代后期,施高德将中国戏曲表演方法运用于演员的日常训练中,希冀借此解决他们在表演过程中存在的乐感、情感与舞感等问题。通过与中国戏曲表演的融合,这些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节奏,控制面部表情,在自我控制与角色保持中展现出一种较强的凝聚力”①A.C.Scott,“Reflection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rforming and Martial Arts of Fast Asia”,Philip B.Zarrilli ed.,“Asian Martial Arts in Actor Training”,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3,p.56.。借中国戏曲改善西方学生表演的做法,也使施高德赢得了业界的好评与尊重。
可见,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主要指向三个维度:其一,从理论上解释何为中国戏曲,对象为戏曲研究学界,为此,施高德从艺术本体出发着重阐释中国戏曲的基本构成与艺术特征;其二,从实践上演绎何为中国戏曲,对象为西方广大受众,为此,施高德立足于经典剧目的翻译与文化内涵的解读,试图再现戏曲舞台表演全貌,以求达到最佳的演出效果;其三,从跨文化交流上阐发何为中国戏曲,对象为西方戏曲学生,为此,施高德身体力行导演中国戏曲,指导学生的日常训练,以拓宽西方学生的世界视野。施高德的这种追求东西文化交融的艺术理念,不仅深深感染着他的学生,更直接提升了美国社会对于中国戏曲的热爱程度,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的认识与理解,促进了中国戏曲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有效传播。
二、施高德的戏曲观:让戏曲研究摈弃文学读本先念而回归戏曲本源
施高德深入学习与研究中国戏曲四十余载,他的研究过程展示出了一条独特的轨迹: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对中国戏曲做普及性的介绍,寄望读者从宏观层面认识中国戏曲;六十年代,他专注于戏曲剧本的翻译,期望读者从演出层面了解中国戏曲;七十年代至去世,他重点关注特定的脚色行当——丑角,产生了将中国戏曲的表演元素运用到西方戏剧中去的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引导读者认可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的价值。虽然施高德的戏曲研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具体形态,但当中也存在一些稳定的特质,例如施高德对中国戏曲本质的看法。
(一)戏曲观:一个研究视角
研究施高德的戏曲观,首先要弄清楚“戏曲观”概念。戏曲观源于戏剧,“戏曲”与“戏剧”在定义域与范畴域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戏剧”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戏剧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中国又称之为‘话剧’;广义戏剧除了狭义的舞台演出外,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诸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等。”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戏剧”定义为:“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的艺术,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综合。分为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按作品类型又可分为悲剧、喜剧、正剧等。”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 版,第1398页。从上述定义可知,(,(广义的)“戏剧”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是“戏曲”的上位词,而“戏曲”通常与传统的民族表演形式相关联,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④叶长海:《戏曲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因此,本文所涉及讨论的施高德笔下的“中国戏曲”主要是指我国的传统戏剧,尤以京剧、昆曲为代表。
“戏剧是大概念,戏曲是小概念,大可包小”,参鉴“戏剧观”概念来讨论“戏曲观”蕴涵是合适的⑤任中敏:《对王国维戏曲理论的简评》,《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第34页。。事实上,“戏剧观”并非一个新名称。1962年,《人民日报》刊登了黄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首提“戏剧观”概念。他指出:“‘戏剧观’是对整个戏剧艺术的总的看法。”丁扬忠(1983年)也表述了类似观点,他指出:“戏剧观是戏剧家对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总体看法,包括戏剧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包括戏剧家对戏剧社会功能的认识,戏剧研究所恪守的艺术方法、原则等许多复杂内容。”⑥丁扬忠:《谈戏剧观的突破》,见雷达主编:《中国新时期戏剧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5页。童道明则认为“戏剧观”就是戏剧家对舞台和舞台真实的看法⑦童道明:《也谈戏剧观》,见杜清源编:《戏剧观争鸣集(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63-71页。。基于上述有关“戏剧观”的观点,考虑到戏剧概念的外延性,我们认为:“戏曲观”是指戏曲家或戏曲研究者在特定时期内对戏曲艺术的总的看法,它既包括对戏曲本身的定性,如戏曲是什么,戏曲的舞台表现性如何等;也包括对戏曲之于外部环境关系的态度,如戏曲具有何种社会功能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戏曲观既反映戏曲家或戏曲研究者对于戏曲的整体看法,又影响戏曲家或戏曲研究者对于具体戏曲活动的演绎行为。施高德在华期间的戏曲田野调查及其与梅兰芳、张君秋、马连良、俞振飞等中国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们的交流与友谊,使得他对中国戏曲有着独特的认识与理解。也正是有了这些认识,才使得施高德戏曲观有着独特之处,它不仅反映了施高德对中国戏曲的本质把握,也透视出这位汉学家对于中国戏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全面、客观地理解施高德戏曲观,有助于把握施高德之于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贡献。
(二)施高德的戏曲观:演员“演”故事
任何作品都不能是对客观现实单纯的、机械的复制,它必须掺入创作者或著述者的创作思想,反映其对艺术的观点与态度。施高德的戏曲观也在其戏曲著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戏曲》是施高德向西方社会阐释中国戏曲的首部论著。书名虽以“中国古典戏曲”泛称,但其论述的对象主要是京剧。这部作品系统、全面、翔实地阐释了京剧,具体包括京剧发展史、京剧音乐、演员表演技法、角色行当、演出剧场等,堪称“中国戏曲的实用手册”①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57,preface.。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第五章“演员的表演技法”②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92.对演员舞台表演的身段与方法展开了细致的分说,内容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在具体行文过程中,施高德采用了西方常见的解剖式治学方法。首先将戏曲美学元素分成四大类,分别是“话白与演唱、动作与姿态、服饰与妆容、武器与砌末”③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92.。紧接着逐一阐说“生旦净丑”四大脚色的表演要领及其动作的象征意义。以旦角的抖袖为例,施高德写道,“旦角登台时,站立了片刻,似乎在整理服装。头部微朝下,右手掌心朝内,从胸前向右边膝盖方向甩去……动作是给予乐师的信号,当右胳膊摆起时,表明演员说或唱的开始”④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97.。再看一例:关于曲牌[点绛唇],施高德描述道,“这类动作通常由扮演武士的人物来完成,例如将军。演员站在舞台的前方,将袖子举起放置脸前。这个动作象征着他身处战场或指挥部”⑤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94.。此类关于“如何演”的文字在《中国古典戏曲》中俯拾皆是。可见,施高德十分重视演员表演的顺序与动作细节,试图以文字为载体还原稍纵即逝的舞台演出;他还重视读者对演员具体演出过程的理解,即程式化动作的意义。据此,他试图既让读者明白这些动作是如何完成的,又让他们知晓这些动作在表达何种意思或传递何种情感。往更深处讲,透过这些著述或作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领略到施高德戏曲观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施高德试图在摈弃戏曲文学读本先念下,让戏曲回归到它作为“舞台表演”的艺术本源上来。重视“演员‘演’故事”贯穿于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施高德对剧目的选取依据凸显其“演员‘演’故事”的戏曲本源追求。《中国传统戏曲》是施高德戏曲翻译的代表作,共分三卷,分别于1967年、1969年以及1975年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收入了《四郎探母》《蝴蝶梦》《思凡》《十五贯》《女起解》与《拾玉镯》等六部作品。译著甄选与出版有个惯例,那就是他国作品在被译入到本国之前,首先须经译者的系统筛选。从施高德《中国传统戏曲》的剧目选择看,笔者认为,上述六部作品能够入选《中国传统戏曲》(三卷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均能集中展现戏曲“演”的特质,这也是施高德对剧目的选取依据。《蝴蝶梦》是施高德搬上美国舞台的唯一中国戏曲作品,谈及其选择原因,他指出“该剧演唱部分少,但舞台动作偏多,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而开展研究”⑥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1”,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7,p.96.;《;《思凡》的魅力主要源自“优美舞蹈与抒情姿态的完美融合”⑦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2”,1969,p.vi.;而《女起解》《十五贯》《拾玉镯》中的丑角“一个个充满艺术感的瞥眼,在没有任何言语的暗示下,便将人物本性暴露无遗”⑧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3”,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5,p.v.。如果说上述五部作品中演员的表演技法赢得了施高德的青睐,那么在他看来,《四郎探母》确是向西方全面展示戏曲演出元素的绝佳代表,不仅脚色行当齐全,而且演出手段多样,还兼具动作表演与演员说唱。当然,除剧目本身的特色外,我们以为,上述六部作品的现时价值亦是施高德剧目考量的重要维度。《四郎探母》等六部作品是深受国人喜爱的传统剧目,建国后它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如《十五贯》(1956年)在北京上演;有的还被选中作为赴外演出的代表,如《拾玉镯》(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施高德从传统戏曲作品中挑选出活态剧目进行翻译与研究的举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它正反映了施高德选择剧目重“演”的艺术倾向。因为文学读本仅为艺术载体,只有演员登台“演”故事,把故事“演”活,才能让戏曲回归其艺术本源,让戏曲安身立命而实现传承式发展。
其次,施高德对剧本的翻译手法让“演员‘演’故事”变得活灵活现。他对中国戏曲作品的翻译不单是对中文剧本本身做出语言转换,还试图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大量源语剧本之外的注解。如在《中国传统戏曲》三卷本的译介过程中,他增添了诸如剧目的人物关系、演出史、演员装扮、演出环境等注解内容;在正文翻译中,除演员台词与简单舞台指令外,还加入了对专有名词的阐释、文字游戏的解说、文化知识的说明、舞台表演过程的记录等内容。对某一特定剧目作解说时,他甚至会将整场演出过程从主角到龙套、从乐师到观众等详情,以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这类描述传递给读者的信息量早已远超源语剧本内容。再以《拾玉镯》第一幕中孙玉娇登台时的译介为例,施高德注解道:“孙玉娇迈着花旦特有的小碎步从右边登台,即观众的左边。右手持着一张大丝帕,双手在身前左右摆动,向舞台前方走去……她站立片刻,娇羞地左右瞥视,整理了发饰,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化表演动作,接着朝向舞台前方的中部走去……最终她来到舞台的中央,不急不慢地说出开场白,也就是引子,数量上通常有两到四句”①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2”,pp.45-46.。这些文字仅仅是施高德译本中有关戏曲表演记录的一个缩影,诚如卞赵如兰所说,“早期京剧翻译只注重大纲,施高德比较着重一个完整的戏剧,尽量把舞台上一切动作、声音效果都表示出来”②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除演出的记录外,施高德在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动词,借此凸显戏曲“演”的本质。我们将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1859—1943)与艾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合译的《思凡》标题,与施高德所译的《思凡》标题进行比较,可以更明显地领悟到施高德“演员‘演’故事”的戏曲研究本质。阿灵敦等人将《思凡》译作“A Nun Craves Worldly Vanities”③L.C.Arlington and Harold Acton,“Famous Chinese Plays”,Peiping:Henri Vetch,1937,p.319.,施高德则译为“Longing for Worldly Pleasures”④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2”,p.13.。《思凡》这部戏讲述了女尼不耐佛门寂寞,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后,私自逃出尼庵的故事。施高德选择的动词组“long for”,将女尼的纠结与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阿灵敦等人的译文更偏向于对故事内容的平直交代。在剧本翻译中,施高德通过大量使用动词、记录戏曲演出过程等手法,让戏曲“故事”通过演员真切的表演而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次,施高德对戏艺的时空比对为其“演员‘演’故事”的研究立场写下了生动注脚。对比研究是研究者的天生本能,当西方人接触东方戏曲的时候,“比较就随时发生了”⑤A.C.Scott,“Actors are Madmen-Notebook of a Theatregoer in China”,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p.38.。比较研究的意识在施高德戏曲研究作品中随处可见,且其内容也丰富多样:有中西戏剧的空间对比,有中西观众的审美对比,有中国曲艺的时间维对比,还有中日戏剧艺术对比等。事实上,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读者之于中国戏曲文化的排斥,缩短了中西异质文化间的距离。从研究者意图看,对比研究过程中,比较对象的选取、比较内容的确定等都将反映研究者的内心世界。施高德的戏曲研究时常挑选西方歌剧,并将其作为中国戏曲研究的比较对象。对此,他解释道,将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相比较是因为“中国戏曲的演唱部分与西方歌剧类似”⑥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Singapore:Donald Moore,1958.p.7.,西方歌剧的本质是“聆听演员的演唱与乐器伴奏,因此观众可以忽略演员的外形”⑦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 p.8.。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戏曲。虽然演员的演唱不可忽略,但舞台的视觉表演更为重要”⑧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p.8.。这些述说反映了施高德将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相比较的真正意图:在他看来,舞台音乐是二者间的共性,此二者相比较可以缩短中西戏剧间的文化距离;舞台表演是中国戏曲独特魅力之所在,这也正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对比的关键。由于差异性往往是他者文化身份之重要特质,因此,将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进行比较,正反映出施高德重“演”的戏艺视角与研究立场。当然,中国戏曲艺术的跨时段比较也是施高德戏曲对比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两次来华,经历民国末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这两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戏曲的艺术律动。但不论是中西戏剧间对比抑或中国戏剧时间维比较,在施高德那里,“演员‘演’故事”的研究立场始终为其戏曲研究之核心内容。
最后,施高德对“戏曲经验”的有力把握增强了“演员‘演’故事”的艺术效果。由上观之,重视舞台表演是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的本质特征。事实上,为更好诠释舞台表演,在著述或现场指导时,施高德还掺入了大量如戏曲音乐、舞台美术等有关舞台表演之外的其他内容。在他看来,这些内容是帮助读者和戏曲受众理解与欣赏戏曲舞台演出的必要前提。20 世纪6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理论的问世,读者的重要位置逐渐受到关注。施高德曾总结过西方人欣赏戏曲时产生的种种困惑,如“乐器刺耳的声响、检场、演员甩袖子动作等”都是西方人所不理解的①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pp.1-2.。他提到,西方人之所以难以收获戏曲美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缺乏一套合适的欣赏标准,以对这种完全不同于本国歌舞的艺术形式实施有效判断”②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p.2.。因此,“只有累积了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够欣赏中国戏曲”③A.C.Scott,“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heatre”,p.1.。施高德将这些背景知识称之为“戏曲经验”④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20.,具体指“表演方法、动作意义以及相关的戏曲资料”⑤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20.。基于此,施高德在中国戏曲研究过程中,还特意对其艺术本体进行分类解构,除戏剧技法外,还加注了大量的戏曲评论、戏曲历史、戏曲舞台美术等“戏曲经验”。此外,在舞台演出或现场指导时,他还会向受众重点交代剧本的故事情节,阐释剧本中的服装、扮相及道具背后的文化意义,甚至点评舞台演出特色等。由此可见,虽然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忠实于源语戏曲文本,但表演技法与具体演出详情等相关内容并非一家独大,他并未漠视甚至忽略表演以外的其他内容。相反,在他看来,“戏曲经验”不容忽视,它能更好地服务于西方观众对于中国戏曲的欣赏与理解,增强“演员‘演’故事”的艺术效果。
“演员‘演’故事”是施高德进行中国戏曲研究的总的立场和基本观点,这种戏曲观的实质就是让戏曲研究摈弃文学读本先念而回归戏曲本源。施高德戏曲观的形成不仅源于他的“中国经历”,更得益于他对中国戏曲自身属性的中肯把握与深刻理解。施高德是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使者,他的中国戏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不被曲解。
三、施高德戏曲研究对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重要贡献与价值
中国戏曲走出国门,通常有国内学者主动输出与海外汉学家异域植入两种方式。汉学家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就是中国戏曲异域植入的典范。加强对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的研究,可窥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为中国戏曲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借鉴。从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维度看,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具有以下价值与意义。
(一)拓展海外戏曲研究风格,开启西方解读中国戏曲新境界
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735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译者省略唱词与韵白,保留宾白的做法,并未完整呈现原剧文本;而后,根据《赵氏孤儿》,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创作出《中国孤儿》,借以阐发自己的政见;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也翻译过多部元曲,主要代表作有《老生儿》,遗憾的是,译者也删除了剧中些许细节,未能忠实地呈现源语剧本。19 世纪,对中国戏曲热情最高、贡献最大的当属法国学者巴赞(Antonie Pierre Louis Bazin,1799—1863),他译介了二十余部元明戏曲,虽多以剧本选译、内容简介为主,但在当时也颇具文学价值。可以看出,20 世纪前,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多以西方学者对中国戏曲的剧情述评、剧本选译、编译、改编为主,且多以文字材料呈现。20 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戏剧由写实戏剧向写意戏剧发展。30年代梅兰芳的美苏之行对这一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时,西方学者更多地从自身的学术立场理解中国戏曲,以戏曲表演为参照物阐释自身的艺术追求。如布莱希特借中国戏曲表演点燃了“陌生化效果”理论的火花。20 世纪中叶,作为国家文化外交的方式,京剧频频在海外上演,演出地点遍及欧洲、南美洲、亚洲,这使得京剧的国际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1955年,法国戏剧家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观看京剧后评论道,“主题、结构以及表现方法令我对京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⑥Leonard C.Pronko,“Theatre East and West:Perspectives Toward a Total Theat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65.。1957年,伦敦艺术评论家布兰德(Brad.W.D,1904—1984)在欣赏完京剧剧目后表示,“京剧团到访演出,令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感受到中国古典戏曲不同寻常的美妙”①A.C.Scott,“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New York:Doubleday&Company,1963,p.163.。
相比之下,当时美国接触地道中国戏曲演出的机会却屈指可数,20 世纪30年代梅兰芳的访美演出算得上是最早的“中国戏曲美国行”②A.C.Scott,“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Vol.1”,p.v.。另外,由于美国华人社区分布零散,具有水准的戏曲演出在华人内部更是参差不齐。于是,在美国观众那里,最终草率地得出了“中国戏曲不太可取”的结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施高德开始着手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与此前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戏曲的研究相比较,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与延伸:其一,在剧本翻译过程中,对源语剧本的内容不做任意改编与删减,演员台词、舞台指令等内容,即便是语义重复的部分都完整译出,这使得译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著剧本的本来面貌;其二,在研究过程中,施高德对中国戏曲艺术做出了本体性、系统性的阐释,对演员演出全貌等细节性内容也都做了细致记录,戏曲艺术魅力在施高德那里得到了完美展现;其三,强化了对“演”的阐释。“合歌舞以演一事”③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有声必歌,无动不舞”④齐如山:《齐如山文集》(第三卷),中国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64页。,这是对我国戏曲本质的凝炼式总结。没有唱、念、做、打等表演,也就没有了戏曲。“演”乃戏曲之生命,脱离了表演,戏曲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华期间,施高德“几乎每晚都在戏院看戏”⑤A.C.Scott,“Actors are Madmen-Notebook of a Theatregoer in China”, p.51.,这让他领悟到了中国戏曲的真谛。为此,在进行中国戏曲研究时,再现戏曲的表演形式与舞台魅力便成了施高德的孜孜追求。
可见,一改西方之前纯文本译介的研究风格,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更加注重对中国戏曲本质的研究,使得中国戏曲的艺术表征与美学内涵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忠实传递与完整展现。施高德提出要重新考量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的价值所在,指出“中国卓越的艺术值得学习”⑥A.C.Scott,“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p.187.,他认为西方的戏曲研究要重视对中国戏曲艺术特质的理解,努力实现中国戏曲在西方世界的“可读、可看、可演”。对比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的纯文本性“可读”研究,施高德“可读、可看、可演”的中国戏曲研究无疑开启了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戏曲的新境界。
(二)消解海外戏曲认知偏见,奏响中西戏剧平等交流新序曲
20 世纪中叶之前,西方对中国戏曲的看法多半充满了误解与偏见。《。《赵氏孤儿》是传入欧洲较早的一部中国戏曲作品,于1735年由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47—1743)收录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杜赫德对这部中国戏曲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它不遵守“三一律”,也不遵守当时欧洲戏剧的其他惯例。对《赵氏孤儿》进行批评的还有阿尔更斯侯爵(Marquis.D Argens,1704—1771),理由是它违背了“从前使希腊人那么高明而不久以前又使法兰西人跟希腊人媲美的种种规律”⑦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19 世纪,德庇时在谈到选择《汉宫秋》进行翻译时指出“译者被当下批评的标准所影响”⑧J.F.Davis,“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A Chinese Tragedy”,London:A.J.Valpy,1829,preface.。20 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戏曲获得了更多西方学者的关注,但对其评价多戴以“有色眼镜”,如曼特乌斯(Karl Mantzius,1860—1921)1903年在《戏剧艺术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atrical Ar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中写道:“中国文学里并不包括那种带有可达到我们这种真正艺术标准特征的戏剧”⑨Karl Mantzius,“A History of Theatrical Ar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New York:Peter Smith,1937,p.2.;汉学家庄士敦(R.F.Johnston,1874—1938)1921年在《中国戏曲》(The Chinese Drama)中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历史及特征,特别指出从西方角度看来“中国戏曲中并不存在悲剧”⑩R.F.Johnston,“The Chinese Drama”,Shanghai:Kelley and Walsh,1921,p.29.;切尼(Sheldon Cheney,1886—1980)认为中国戏剧文学永远无法达到苏格拉底或莎士比亚所赋予西方戏剧的那般重要性⑪Sheldon Cheney,“The Theatre:Three Thousand Years of Drama, Acting and Stagecraft”, New York:Longmans, Green and Co., 1972,pp.122-124.;阿灵敦在著作中感慨道:“中文字典里没有一个词,不论从庄严还是范围上能够与西方世界‘drama’相媲美”⑫L.C.Arlington,“The Chinese Dra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Beijing: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2015,p.4.。由此可见,20 世纪中叶前,西方世界倾向于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戏曲,他们试图以西方审美标准来评判中国戏曲,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这种忘却中国传统文化而以他者文化对中国戏曲所做的评价,注定是一种非完备性的曲解甚至错误。
与之相比较的是,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注重对中国戏曲文化的阐释,着重戏曲表演过程的完整呈现。他对中国戏曲的这一研究范式,打破了一直以来西方学者一味迁就西方观众而以西方标准研判中国戏曲的倾向。20 世纪50年代,施高德甚至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用西方戏剧的欣赏标准来判断中国戏曲”①A.C.Scott,“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p.16.,这一倡议明确阐明了施高德在中西戏剧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态度与立场。在研究实践中,他一方面从中国文化等“戏曲经验”视角对中国戏曲进行本体性的理论解说,另一方面以舞台表演为载体积极向海外观众推介中国戏曲。在谈论中西戏剧文化相互影响时,他并没有一味地赞颂西方戏剧。比如在中国戏曲表演引进西式舞台布景这一事件上,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违背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传统做法。”②A.C.Scott,“Actors are Madmen-Notebook of a Theatregoer in China”,p.179.可见,一改以往西方的傲慢态度,施高德的戏曲研究坚持了中国戏曲的本位思想,这既是对当时西方社会文化“沙文主义”的抗议,又为学界树立了中国戏曲研究的应有立场。从此意义上讲,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消解了海外之于中国戏曲的认知偏见,奏响了中西戏剧平等交流的新序曲。
(三)树立戏曲海外传播新标杆,开创中西戏剧文化交流新局面
20 世纪中叶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多半是出于对异国风情的好奇。1755年,伏尔泰版的《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为迎合观众,伏尔泰对原剧本《赵氏孤儿》进行了大幅修改;1759年,谋飞(Arthur Murphy,1727—1805)改编的《中国孤儿》在伦敦上演,先后共演出九次,从演出效果看是成功的,但据熟悉剧院情况的詹姆斯·波顿(James Boaden,1762—1839)回忆,当时舞台上出现了一大堆光彩夺目的外国服装③James Boaden,“Memoirs of Mrs.Siddons,Vol 1”,Philadelphia:H.C.Carey,1827,p.138.;1912年,美国剧作家哈利·本里默(J.Harry Benrimo,1874—1942)自编自导的中国剧《黄马褂》在百老汇上演,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这并不算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剧,德国戏剧分析家莱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1943-)将《黄马褂》的成功归因于“似乎利用殖民主义的话语,展现那种愚蠢的表达方式以及中国戏曲中奇怪的风俗习惯”④Erika Fischer-Lichte,“What are the Rules of the Game?Some Remarks on The Yellow Jacket”,Theatre Survey,Vol.36,No.1,1995,p.25.;1934年伦敦剧院上演了熊式一创作的《王宝钏》,演出时间长达三年,征服了伦敦⑤郭英德:《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王宝钏》的故事源自中国古典名剧《红鬃烈马》,但施高德认为,无论从原著内容的忠实性还是从传统舞台的表现性来看,这都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可以看出,早前中国戏曲的海外演出都持一套固有模式:都是西方学者按照自身创作意图对中国剧本的改编而非中国戏曲原剧本;演出过程采用的是一套西方观众熟悉的表现手法,只是在背景色彩等环境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异国风情。所以,这一类型的演出,不论从主题、结构、艺术形态还是从表现手法上看,均迥异于中国戏曲的真实面貌,不能呈现中国戏曲的精髓。
1961年,施高德导演的中国戏曲《蝴蝶梦》在美国上演。与《中国孤儿》《黄马褂》《王宝钏》等中国戏曲的海外演出情况相比,施高德的《蝴蝶梦》做出了以下探索与创新:其一,演出过程忠实于《蝴蝶梦》源语剧本,对内容未擅做删除与改动,场景环境等都遵照中国文化布置,抛弃了此前西方上演中国戏曲时的那种“旧瓶装新酒”的全盘移植的处理方法;其二,完全采用中国戏曲自身的表演方法进行演绎,引导西方观众加深对中国戏曲的认识,引导他们去关注中国戏曲自身的美学原理,为获得更好的演出效果,施高德还专程从香港邀请了两位中国戏曲演员赴美为演员进行现场示范与当面指导;其三,促成了西方受众从对单纯异国情调的追捧向对中国戏曲神韵认知的转变。艺术无国界,但艺术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作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是中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沉淀,更具民族文化蕴意。脱离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就谈不上对中国戏曲的理解。施高德深知这一艺术原理,为此,在《蝴蝶梦》表演过程中,他着重对剧本“戏曲经验”的解说。另外,他还在艺术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中西戏剧交流的方式,并尝试将中国戏曲表演的深层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在威斯康星大学戏剧系学生的日常训练中,并强调在中西文化互碰与互撞的交流中加强异质文化互包与互融。可见,施高德不仅是中国戏曲文化的海外传播者,更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忠实践行者,他为当代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树立了新的标杆,开创了中西戏曲文化交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局面。
四、结语
尊重中国戏曲文化,回归中国戏曲本源是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总的研究立场与态度。这种重本体研究的戏曲观,不仅体现在如作品译介、文化阐释、剧本解读等施高德戏曲理论“案头”研究过程中,还体现在如戏曲演出、现场指导、艺术临摹等戏曲实践过程中。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是民族艺术登上世界舞台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互包互融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施高德中国戏曲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在研究过程中,他着重“演员‘演’故事”,试图摈弃戏曲文学读本先念而回归戏曲本源,但事实上,基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戏曲音乐处理方面,他又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让受众身临其境去感受中国戏曲本身带给他们的那种“美的律动”与“美的至真感受”。施高德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也尝试地做了一些补救性工作,如在《中国传统戏曲》(第一卷)附录中他特意增补《四郎探母》的一段唱词曲谱并制成音频材料,以供读者领悟、揣摩中国古典戏曲的乐律与文化氛围。随着中国古典戏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与窗口,中国戏曲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瑕不掩瑜,汉学家施高德的中国戏曲研究在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奏响了中西戏剧平等交流的新序曲,开创了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是民族文化海外传播汉学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