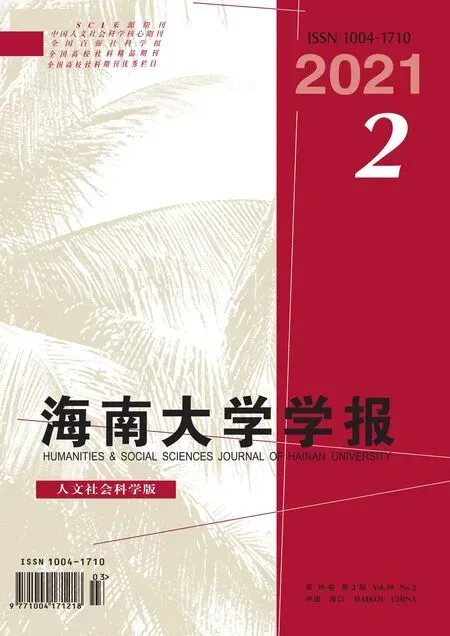人的觉醒
——魏晋天人视域下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及其嬗变
曾 嘉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23)
与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哲学侧重于辨说神人关系不同,中国哲学始终关注自然与人,恒论天人关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道法自然”,中国哲学从孕育之初开始,作为主宰的“神”即是缺位的。这种“神”的缺位,其积极面是“人”的觉醒,消极面则是人的“越位”。这种觉醒与越位之间的折冲与转换,在魏晋时期尤为凸显。先秦哲学的无神论倾向是作为“类”的人的觉醒,而魏晋玄学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觉醒。这种觉醒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如果没有超越层面的赋命、提升与制衡,那么“觉醒”极易导致“失格”,乃至沦丧。这个超越的层面,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中即是“天”。在中国哲学叙事中,天与人是一贯的、合一的。天人合一背景下的“人的觉醒”,在魏晋时期就表现为名教与自然之关系及其嬗变。
一、天人视域及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兴起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在儒道二家有着本体论的意味。二家皆欲贯通天道与性命,故都本天道以明人事,将“天人合一”悬为人生与政治之鹄的。然而,儒家是人文主义的,道家是自然主义的,其对天人关系的辨析旨近而趣异。这种趣异在汉魏时就表现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所以要研探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在天人视域内对二家别异做一番厘清。
(一)天与人
中国古民以农为业,农业紧关天时,所以古民信天最笃,合天道以行人事。何者为“天”?在儒家看来,天是造物的主宰。《诗经·大雅》:“天生烝民。”①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4页。《易传·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②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79页。《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③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487页。更可言之,天是一种宇宙秩序。在道家那里,天却是纯真的自然。老、庄或称天为“朴”,或称天为“真”,正是此理,如《庄子·秋水》:“无以人灭天,……是谓反其真。”④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1页。汉初黄老之学的文本《淮南子》继承了此种观点:“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①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这里的“天”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它自然而然,没有人为干预,没有人类行为的痕迹。
何者为“人”?人是天地之心,人是天地之灵。《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②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083页。“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③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081页。《孝经·圣治章》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④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551页。在儒家的经典中,一以贯之地论述人之地位的崇高。儒家贵人,道家则贵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⑤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470页。老子却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在道家看来,人的最高境界是“真人”“至人”,而“至人无己”“真人……与道合真,同于自然”⑦《道藏》(第25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高妙的境界都是摆脱人的束缚,臻至与道相合的自然而然。
所以在天人关系上,道家把天人看作相反对待的事物,主张去人而从天,甚至灭人以全天,如庄子所说“畸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⑧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150页。。道家把“损”“忘”作为修养功夫。反过来,儒家把天人看作是相辅相成的事物,主张尽人以合天,“参天地,赞化育”,故其以“名教”“礼法”为治平纲要。
儒道在天人关系上的此种歧异,在相同的救世情怀的驱动下,入汉以后,便表现为名教与自然的纷争与融合。
(二)自然与名教
这里所谓“自然”约有二义:其一,天道,运生万物。何晏《无名论》:“自然者,道也。”⑨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页。自然就是道;其二,天然,纯真无为。《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⑩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321页。牛马的四足是天生的,天然如此。为了控制牛马而拴马绳和穿牛鼻却是后天的,是人为添加的表现。因此郭象在注《庄子》时就认为:“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⑪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26页。自然正是在此意义上与名教相对,自然是天真无为,自然而然,与之对立者是“为”或“伪”。故自然是一种去礼法,非名教的状态。
所谓“名教”,就是“以名为教”。春秋末期,孔子欲“正名”以救时弊。汉代将纲常立为名分,号称名节,用它来论德才、定功名,这就是“以名为教”。而名爵及其相关的道德伦理又为礼仪所规范,所以名教又是礼教。
在汉代初年,治用黄老,与民休息。武帝之后,推任董仲舒,儒术重新焕发出光彩,朝廷用名教纲常约束政治与社会生活。举孝廉,选茂才,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升进人才,整饬政治,但经术不醇,人心未正,朝廷用儒术来文饰政治,士人们则藉经术谋取俸禄。孝廉方正,也往往名不副实,行不副名。谭嗣同总结这种现象说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⑫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于是高明之人、激愤之士乃有所反动,不再标榜道德而转求于解放人性。
此外,王莽新政多据儒家经典而行,但矫情虚饰,不切实际,徒然惑乱天下,而以败亡终。魏武霸业,唯才是举,其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⑬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页。这在实际上选拔了那些不仁不孝之人,形成了对名教的冲击。
(三)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背景
从汉初学术的发展理路上看,儒道二家对名教与自然皆有两个侧面的解说。儒家一方面大讲“天人感应”“人副天数”“唯人独能偶天地。……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14-316页。。这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形态,按其内在逻辑,则名教就是自然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伴随着经学的兴起,谶纬之说也开始盛行“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②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页。,相应地,非谶之论随之而起。天人感应说是从内在理路中正面引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命题,并提供了资粮;符命谶纬则是从外在风潮上反面刺激了该命题,并为玄风所终结。
道家方面,汉初尊崇黄老学说,用清净之说来应对民生凋敝,汇通“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意,弱化刑罚之治,所以《新语》上说:“是以君子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③王利器:《新语校注》,第118页。这说明,治国者应该作出教化的准则,专心一致建设儒教式的道德社会,但究其实质,却是对刘汉政治合法性的否定。“无为”的政治意涵中有一个面向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可与遵守。景帝时,儒道两家针对汤武革命的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黄老一方的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④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2页。辕固因此反问说:“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⑤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93页。从此一争论可以看出,黄老思想的“无为”作为汉初社会的治理原则,其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时虽成效显著,但“无为”作为政治哲学的概念却牵涉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君臣上下是否可以流转更替?这种流转更替如何实现?其实现方式是什么?道家对现有社会的遵从仅是“无为”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无为”在时间维度上指向《老子》文本中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才是接近于“道”的真正的无为。而仁义道德、礼乐制度等都是“道”不能维持之后产生的,所以道家“无为”是对现有社会规范的消极否定,潜藏着对名教的批判和回到本初状态的要求。东汉以降,名教式微,道家学说勃兴,士大夫开始追求自我,魏晋玄风中掀起了名教与自然之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则促成了此一辨说的发生与演进。
二、早期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视域,将名教与自然置于其中,是一种横向的共时性考察,可以在广域中窥见二者范畴之间的统一与不同,既识其广,还探其深。共时性的考察之后,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通过历时性的检视,对于范畴的认识,几乎可称完备。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名教与自然之辨做纵贯全史的梳理,只能从某一个历史节点上略做剖辨,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回溯名教与自然的分衍史,先秦时期萌芽,汉世发展枝叶,到魏晋则开花结果,之后花果飘零,已不足观。因此这里仅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中,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嬗变。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援道入儒”。玄学穷究本体,而远离人事轻忽名教,因此自然与名教之辨成了玄学的重要议题。人们对“玄”的阐释,自东汉至魏晋,已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之后,儒学就深陷谶纬神学的漩涡,以至于到了东汉末年,经学所构建的神学世界与价值体系轰然崩溃,魏晋玄学随即登场,对汉代以来的名教观念全力反对,并渴求回复到本初的自然之中。汤用彤指出,汉人论玄“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而魏晋玄学则“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⑥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39页。。前者崇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推重“进于纯玄学之讨论”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40页。。所以在对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解释上,汉与魏晋便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冯友兰认为玄学是“新道家”,但正始玄学又未尝不可说是“新儒学”。何晏汇集注释《论语》,王弼注释《易》,都是援道入儒,藉老庄以通儒学,所以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名教本于自然”。详辨之,所谓“本于”又包含着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的三层义蕴。
(一)名教与自然是体与用的关系
老子说:“道法自然”,而道就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10页。,因此何、王皆“贵无”。在何晏的理论中,“无”是“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他说:“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②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6页。“无”“有”之间的关系是“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③杨伯峻:《列子集释》,第10-11页。。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把“有”的生成追溯到了“无”,体现了以无为本的核心意涵。推而广之,宇宙的运行和圣人的作为都依“自然”而行,也就是所谓:“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④杨伯峻:《列子集释》,第121页。。这里的“自然”是天地、圣人都需依从的事物。王弼继承了何晏的观点,认为“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⑤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页。“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⑥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27页。。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以“无”为根据,“皆赖无以为用”,名教是“有”,是“事”,也就是“用”,名教作为“用”须以“无”为本体才能发挥作用。
(二)自然与名教是道与器的关系
自然是最本初的状态,可以说是“无”,也可以说是“真”,是形而上的道。名教是形而下的器,是形上之道的体现。自然与名教之间就是“真”(“朴”)与“名”的生成关系,如老子说:“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⑦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75页。“真”生成“名”,换言之就是名教本于自然。具体的生成过程王弼曾这样描述:“始制,谓朴散为官长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⑧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82页。也就是说,器生于道,名教生于自然。
(三)自然与名教是本与末的关系
王弼用母子关系来解释这种本末关系,《老子注》:“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⑨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95页。这里“母”喻指自然,“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⑩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95页。,王弼以朴素自然之性为伦理道德之本,认为道德若失其本,“任名以号物”,就会导致“名虽美焉,伪亦必生”——丧失了真,“失治之母也”,就产生了种种“伪”,完全是自然与名教关系的本末倒置。本末倒置会导致“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弥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愈竞”⑪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9页。。“自然”被认为是“敦朴之德”,是清净无欲,是人的应然状态。“名教”被认为是“名行之美”,是仁义礼法等道德行为规范,是人的实然状态。人在实然状态中,受制于名教,忸怩作态,以至于整个社会最终都将“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⑫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9页。。这便是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王弼厌恶此种社会现象,而以自然为政治的至高境界:“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⑬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40页。诚信缺失的统治者,不会得到百姓的信任,社会道德的失范也会被归诸名教。不过,名教又有其“不可不立”的必要性。早在何、王之前,蔡邕就已经这样认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⑭袁宏:《袁宏〈后汉纪〉集校》,李兴和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天地之性”及“自然之理”表明了君臣父子之间上下级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蔡邕用“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解说名教,已经具有了某种玄学的气息。由此可以看出,“名教本于自然”之说的确是当时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观念。总之,“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出于自然”,何、王崇本而不绝末,自然固要标举,但名教也不可摒弃。
然而,援道入儒并由之产生的“名教本于自然”的理念却导致了对名教的消解。名教是保证社会秩序得以稳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将名教的价值根源归因于“自然”,把“自然”视为先天,“名教”视为后天,以“散朴为器”作为解释依据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结果却是名教的后天性相对于自然的先天性在价值序列中不具备优先级。王弼说:“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①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49页。他认为,效法道的自然就是在以道治国,安定天下。在与自然的比照中名教被视为末流,是奇而不是正。名教既然存在于“自然”的意义之下,是在“无”中产生的,那么名教的存在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玄学在下一阶段的变化中转而生成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对此的调和——“名教即自然”,中后期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论述正由此展开。
三、中后期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
前汉儒学复兴,以阴阳杂于其中。魏晋玄学发展初期,何晏、王弼以老、庄申说儒义。世道陵替,风气变化,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逆转,阮籍、嵇康推崇老、庄而贬抑儒教。正始玄学时期,自然与名教是本与末、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虽然主张“抱朴以全笃实”,但还是认为“兴仁义”可以“敦薄俗”。然而,何晏以曹氏驸马之贵、尚书列侯之尊,却被夷灭三族;王弼以旷世天纵之才,却受政治牵连,暴病而亡,赍志以殁,人们由此对所谓可以安身立命的名教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老子所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②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第93页。,随之被玄学家奉为圭臬。于是玄学转向了更加激进的层面,玄学家们将名教看作赘疣、寇仇,认为只有彻底地抛弃名教,才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嵇康认为,六经违性,名教矫饰,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六经纷错,百家繁炽,……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③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08页。他直接指责名教的核心经典“六经”贬低人性,导致人追求荣利而忘却了本性。这里所说的自然,是人的自然之性,“违其愿”是反自然的,顺应人性欲望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嵇康的理论更好地把自愿与自然联系在了一起。
阮籍则直接将恪守礼法的君子比作虱子,称世之所谓君子“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④阮籍:《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166页。。阮籍的言下之意是,代表着人伦纲常的礼法就如同裈裆一般,是没有恒久价值的。将礼法君子和人伦纲常都否定之后,阮籍又进一步否定君臣之义。他认为,名教既然如此不堪,那么君臣之义也不必再守了,他针对君主、君臣存在的依据及其应有责任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他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⑤阮籍:《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第170页。要知道,君君臣臣正是名教之本啊!鲍敬言也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⑥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杨明照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93页。两者都直接否定了君主存在的必要性。
“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一种人生观或政治理念,其人性论的基础是“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⑦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第408页。。可以看出,“不逼”是“愿得”和“志从”的大前提。社会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就要对个性理解与尊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⑧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第408页。?这是“任自然”的历史依据。可以清晰地看出,嵇康主张大人君子需要超越凡俗的规矩制度而顺应自然之道,所谓“越名教”,是要越凌假名教;所谓“任自然”,却并非是要纵意恣肆,而是要“不违乎道”。嵇康指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①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第368页。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如果心中能不在乎、不关心凡俗世间的是非观念,就可以遵循自然之大道,如果内心超越,就可以不被欲望所束缚。所以,竹林玄学与正始玄学在理路上不是抵牾的,而是衔接相承的,都是融合了儒道以救时弊。阮、嵇二人的“越名教”,正是《论语·子路》所记载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简言之,“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名教,无措是非。竹林七贤正是在此理念下才不堕下流,不媚权贵,不亏大节,进退不失其据的。
随着放达风气的兴盛,玄学末流任情而背理,其恣纵之行甚至有下于俗常之人。《晋书》:“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②房玄龄:《晋书》,第2458页。于是就有了裴頠的“崇有”、王坦之的“废庄”、郭象的“独化”,都想拨乱反正,倡导“自然即是名教”的思想。
裴頠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济有者皆有也。”③房玄龄:《晋书》,第1046-1047页。在这里,“有”已经成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崇尚“有”就是不废名教,名教是本体在社会人生中的必然体现,也就是说名教即是自然。因为“贵无”思想的后果会导致士大夫们“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④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9页。,亦即轻视社会规范,贬低功业,将虚浮视为高尚,低估实干,所以裴頠抨击“贵无”,推崇“实有”。他指出“贵无”论者“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⑤严可均:《全晋文》,第329页。。结合史实来看,这种抨击并不过分,“贵无”确实造成了社会失衡现象,导致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及价值观念的无序和混乱。当然,裴頠也没有完全否定无为之说:“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⑥严可均:《全晋文》,第326页。也就是说,尧舜统治的时期就属于所谓“无为”,但实际上这个“无为”并不是真的没有作为,而是有所“劳”,有所“为”,选贤举善就是其表现之一。
裴頠从“贵无”到“崇有”的视角转换,混同了本质与现象,使人生失去了超越层面的向度。东晋孙盛认为:“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⑦严可均:《全晋文》,第653页。《贵无论》已轶,我们无法确知其“非有非无”的理路,但孙盛为东晋人,应当看过裴頠的作品,他认为裴頠尚无既失,崇有也未得,没有能达到虚胜之道。裴頠之后,郭象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玄冥”“独化”等理论。
独化在郭象的理论中具有多重意涵:其一,万物是“自然”——“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⑧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406页。,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受外力作用的;其二,万物是“自尔”——“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⑨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268页。,万物的根本在于自身;其三,万物是“自生”——“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⑩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208页。,万物的源起不是他物引起的,而是万物自生;其四,万物是“自造”——“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⑪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60页。,万物的形成没有一个造物主,万物自身成为自身。郭象“独化论”的四重意涵意在说明自生与独化为一,万物生生化化,不生他物,也不为他物所生。万物生化的原动力不在事物的外部,乃是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
独化论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从郭象注文可以清晰地看出,郭象的自生、独化说是一种否定本原的思想。郭象重新解释了“无”,他认为,“无”只是“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⑫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137页。,这就是“玄冥”。如何理解“玄冥”呢?“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⑬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141页。“玄冥”不是空无,它是这个或那个样子,都有所然,却又不知其所以然,也不问其所以然。“玄冥”就是“玄冥之境”,就是“有”,其中蕴涵了有形(物)与无形(气)之物,这种不得不然的情况就是“玄冥”①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注。,而万有“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②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60页。。所以辩证地说,独化论不仅反对“贵无”也反对“崇有”:“若游有,则不能周遍咸也”③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400页。。这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逍遥,在社会政治上则表现为不废名教,“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④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281页。。郭象认为,人性有变化,人的性情在具体内容上也应该因时而变,若执着于仁义旧教条,就会变成为仁义而仁义,产生伪仁义,不仅违背人的本性,也忘却了人的“自性”。仁义礼乐是人之性情所固有的,所以“名教即自然”,遵循名教是人之性情的内在需要。人事本乎天命,郭象所提倡的名教,乃以现实人性为标准,与庄子的人性标准自有不同。《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⑤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321页。天与人被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又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郭象却认为:“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⑥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321页。牛马能够被驾驭是因为天性如此,那么人类社会的名教礼法也是符合天性的,因此“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岂礼之大意哉”⑦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147页。!在郭象看来,“游外以经内”意味着礼法世界与超越礼法束缚的不同准则,对外在的礼法主张要以超越的眼光来对待,以人的内在情性为前提;“守母以存子”意味着允许“迹”的存在,“迹”是现象,表现为名教,“所以迹”是原因和本质,是性与自然。“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⑧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288页。“迹”是末,“所以迹”是本,“所以迹”必然要表现为“迹”,任物之真性的政治必然转化为名教。“称情而直往”则是强调要顺着真实人性去领悟礼的大意,不受外在礼制的牵绊,礼的内在实质乃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以看出,郭象的名教就是本于人性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名教非但不违人性,反而是适于人性的。适性就是物得其所,人得其位,最终都各遂其生。总之,独化论反对无中生有,主张自生无待,讲究足性逍遥,把冥内遊外、名教与自然合一作为哲学至境。
自何晏、王弼而至向秀、郭象,从诠释学上看,何、王是援道入儒,阮、嵇是越儒崇道,向、郭是融儒正道,而经过向、郭的修正,庄学越趋圆融。如《庄子·逍遥游》所论蜩鸠与鲲鹏、朝菌与冥灵,尚有小大之辨,高下之分,而郭象却说:“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⑨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页。从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看,此刻在玄学中恰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演进周期。至此,自然与名教之辨已基本完结。
四、名教与自然的嬗变
魏晋玄学是士人的哲学,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是士人对时代困境的回应。西汉以降,政治上,名教纲常悬为国宪,桎梏人性;学术上,一方面谶纬的兴盛违背理性,另一方面古、今文经学之争没有停止;人生遭际上,篡乱相乘,兵戎迭起,操守已不足恃,性命已无所寄:这些都激发了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觉醒。刘师培说:“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⑩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见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2页。名教与自然之辨,正是这种人性解放与自我觉醒的体现,社会秩序需要名教,人性解放向往自然。人性既有对秩序的呼唤,又有对秩序冲决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就构成了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递进与嬗变。
就玄学本身来说,名教与自然的讨论已达到了援道入儒的理论顶点。从“名教本于自然”到“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归于“名教即自然”,这是一条清晰的玄学发展脉络。东汉末年以降儒家的伦理纲常,不足以合理解释社会现实的变化,因此士人们援引道家的思想阐释儒学,试图以此找到隐藏于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在这之中无论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如何,始终都需要面对名教是社会秩序之唯一来源的理论困境。因此,在理论思考中无论将名教置于何处,都必须对它给予说明,即便是将名教作为先天性的东西,也是如此,因为名教的先天性却面对着社会中的政治乱象,与名教的秩序性是不相匹配的。
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纯思想性的思考,是在概念的精神王国中遨游,此种抽象玄思讨论的是最根本的问题。玄思是由社会现实引起的,但一旦上升到概念的领域,就必然与现实无关了。儒学作为魏晋士人最为根本的思想来源,始终摆脱不了儒学的实践面向,很显然,王弼、阮籍、嵇康、裴頠等人虽然努力地想要在思想上有所建构,却终究有所欠缺。王弼需要回应理想政治,阮籍、嵇康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体认超越名教的自然,裴頠则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弥补现实与理想的鸿沟。
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将人的自然本性与名教的社会秩序相结合,以“各适其性”的理路,构建出可以应对社会动荡的理解方式,蜩、学鸠、鲲鹏三者之间“各适其性”就暗含了这种理解方式。人可以各适其性,社会政治也是如此。郭象说:“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①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30页。可以看出,名教的君臣孝悌都是符合人的天性的,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自然。他的这一套理论逻辑不仅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切中了文化价值取向之所在,“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②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第15页。。这种糅杂儒道的和谐,此后便成了后世所称颂的典范。
因此,当玄学家们在“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中构建出一个鲜明的儒道融合的圣人模式时,名教与自然的命题就已在中国文化中完成了时代任务,既超脱于俗世,又存在于俗世之中。俗世并不是人生抵达圣人境界的阻碍,而是一个人修成圣人的必备条件,这种理念自郭象提出后,自然而然就成了后世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它既包含了儒学强烈的实践要求,又表现出一种“无碍于物”的通达。
从“名教本于自然”到“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名教即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回归到了“天人合一”。名教与自然之辨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中重要的一环。能将名教与自然绾合为一,就是圣人,这便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中庸》中“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的圣王境界。但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内圣外王,在名教与自然的这种表达中,都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天人合一中的“天”,内圣外王中的“圣”,如果仅仅停留于“自然”的层面,那么人的发展就失去了超越的向度。也就是说,人如果仅仅是自然的,人终究也只能是世俗的。天人合一的高阶发展必然指向“超自然”的维度,亦即宗教的维度,于是就出现了玄学与佛学的合流。
玄学贵无,般若谈空;玄学讲无名、无为,般若讲无相、无生,因此玄学与佛学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佛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夫论以及思辨性上都远超儒、道二家,所以佛学一经传入,就势陵儒、道之上,直欲夺其席,易其帜,如支道林以僧人身份却成了清谈领袖。《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逍遥”是当时玄学清谈的重要主题,向、郭二人对“逍遥”的阐释流行一时,可支道林却能别开新意,“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③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4页。。因此,“后遂用支理”④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第184页。。汤用彤在总结东晋学术发展时更是指出:“因是学术大柄,为此外来之教(佛教)所篡夺。”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名教与自然之辨,由于儒、道的融合,在“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中得以完结。当佛学兴起以后,名教与自然之辨,又在性理层面上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与融合,而这已是宋代理学的范畴了。
五、结语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范畴。魏晋以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不再直接为学人所关注,但唐宋以后,关于人与天、理与性的深究严辩,仍可看作为名教和自然之辨的延伸。而这种意义上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对当今社会与学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当今世界的最大困境就是西方传统哲学中高度抽象和机械的自然观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巨大撕裂,而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特有的圆融与合一,正可以正其邪、补其弊。如果说名教与自然之辨在魏晋时期是士人对彼时时代困境的回应,那么,在现代的语境中,名教与自然之辨已经具有了后现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