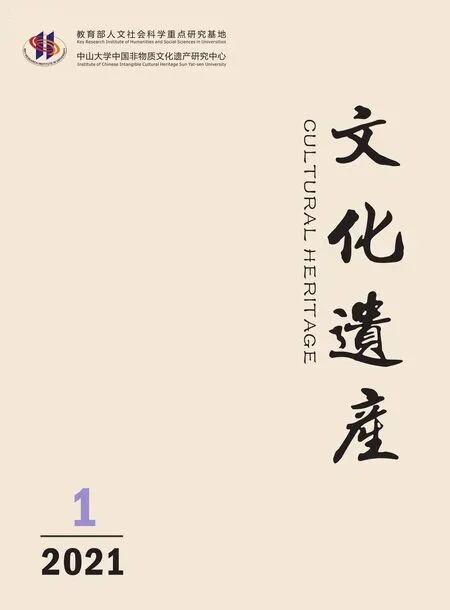乐部西来与乐部东传*
黎国韬 黄竞娴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交流史上,乐部西来与乐部东传是非常著名的两件事情。所谓“乐部西来”,主要指汉唐时期经由西域传入的各种外来乐舞、乐人、乐谱和乐律知识,它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影响。虽则学界对此关注已多,并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至于“乐部东传”,主要指唐宋时期中国乐制、乐人、乐舞、乐书等向日本和朝鲜的输出,这对于东方两国的音乐发展影响甚巨。虽则学界对此已有关注,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须进一步探讨。为此,下文试作考述,祈能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戏曲史有所补阙焉。
一
从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记载来看,西域胡乐之输入中国至迟从西汉武帝(前140-前87)时就开始了。如晋人崔豹《古今注》有云: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1)崔豹:《古今注》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所谓“张博望”,即凿通西域的张骞;据此可知,胡乐西来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横吹乐传入西京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后,胡乐西来的数量逐渐增多;(2)比如南阳市出土东汉墓纯乐器演奏图中,可看到较为罕见的“竖箜篌”,竖箜篌即西来乐器的一种。其它外域传入的乐器,在各地出土汉画像中也时有发现。参见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178-179页。至东汉,则有大秦“幻术人”通过西南一路将胡乐输入中国。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3)范晔撰、李贤等注,司马彪撰志、刘昭注补《后汉书》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1页。“永宁”是东汉安帝(107-125在位)年号,“掸国”即今缅甸,“海西”一般认为即大秦,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据台静农先生的观点,大秦乐舞及幻人乃由海路传入缅甸,其后由于缅甸国王向汉朝进贡,这批胡乐因而传入中原。(4)台静农:《两汉乐舞考》,收入《台静农论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约而言之,两汉是乐部西来开始频繁的时期。
但从较新的考古成果来看,丝绸之路的初步开辟,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远早于张骞通西域的时间。(5)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第45页。因此,在张博望“凿空”之前恐怕已有胡乐的输入,古籍的记载为此留下了史影,先看几条相关材料:
《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一作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6)吕不韦:《吕氏春秋》,收入《诸子集成》六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51-52页。
《世本·作篇》:伶伦造律吕。(7)佚名:《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8页。
《说苑·修文》: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8)刘向:《说苑》卷十九,收入《百子全书》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汉书·古今人表》:泠沦氏,服虔曰:“沦音鳏,始造十二律者。”(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69页。
不难看出,以上几条材料讲述了远古一位名叫“伶伦”的乐官创造“律吕”之事,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但神话传说的产生一般都有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伶伦用以制作律管的竹子,乃采自“大夏之西”;他所效仿的“凤皇之鸣”,亦在大夏之西的阮隃之阴;这就曲折反映出,中国古代律吕的产生,可能与大夏之西的音乐传入有关。那么“大夏之西”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王国维先生《西胡考下》一文曾指出:“大夏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1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30页。显见属于古西域之地。而神话学研究者丁山先生在《由鲧陻洪水论舜放四凶(下)》一文则认为:“所谓‘夏海之穷’,当即苏武所居‘北海上无人处’,《庄子》谓之北冥矣。是沙漠也,而名曰‘夏海’,曰‘大夏’,正同于古之有夏。”又认为:“鲧为夏郊,而其化名为鲲,为夸父,为共工。流共工于幽都,余已说明为驱旱神回朔漠之寓言;而相传鲲与夸父神话,又莫不以夏海(即北海)为中心;是饕餮、穷奇、夸父之地,犬戎、昆夷、大夏之国,皆得谓即夏后子孙。”(11)丁山:《由鲧陻洪水论舜放四凶》(下),载《文史》第4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依照此说,“大夏”就是“北海”,即苏武牧羊之处,也属于古西域的范围。此外,音乐史家王光祈先生《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一文亦有相近见解:“古代的中国人比较诚实,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的音乐是从西域的大夏人民中学来的,据说,大夏可能就是巴克特里亚或吐火罗。”(12)四川音乐学院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85页。所谓“从西域的大夏人民中学来”,正是指“伶伦截竹造律”一事;而王氏认为“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或吐火罗,与王国维、丁山二先生的说法相差并不远。因此,大夏的具体地点虽存在不同看法,但大致位于古西域范围内则没有问题。换言之,伶伦的神话传说有上古史影在焉,反映出两汉之前已有零星的胡乐西来中国。
二
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胡乐的输入变得更加频繁。对此,《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作了比较恰当之概括:“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胡乐’,包括西域乐和外国乐,陆续东来,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乐舞的一大变革。前凉时天竺乐传入凉州。前秦末年,吕光灭龟兹,得龟兹乐,龟兹乐后来散入中原,进入北魏乐府。吕光、沮渠蒙逊等又在凉州以旧乐杂入龟兹乐,成为西凉乐(又称秦汉乐),太武帝灭凉获之。在此前后,北魏灭北燕,得高丽乐;通西域,又得疏勒乐、安国乐。西魏、北周时,高昌乐、康国乐也传入内地。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传入七调的乐律。北齐胡乐更盛,……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胡人,都以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北朝的太常雅乐,大量参用胡声,胡乐的乐章、乐器、乐舞,在民间也颇流行。”(1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约而言之,这一时期已经不是单支乐曲、某种伎艺的传入,而是乐章、乐器、乐舞、乐人等全面而大量地西来。上述情况不但在古代典籍中屡见记载,在众多石窟壁画中也屡有表现。如郑汝中先生就曾指出,敦煌石窟早期的乐舞壁画,具有浓重的西域风。(14)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第37页。所谓“早期”,在郑氏书中指的就是北凉、北魏、西魏时期。
而在六朝时期众多西来乐部中,龟兹乐人、乐舞、乐律的成就和影响可谓最为突出,在新疆龟兹石窟中出现的大量伎乐图像,足以作为佐证。(15)韩翔、朱荣英撰:《龟兹石窟》,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以下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予以说明,据《魏书·乐志》记载:
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16)魏收:《魏书》卷一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43页。
上引材料说的是北魏后期史事,其中提到崔九龙以“声折”记录乐曲。对此,乐学研究者何昌林先生认为,这种“声折”就是从龟兹传入的“筚篥谱”,“与唐代的管色谱,宋代迄今的俗字谱当有一脉相承的关系”。(17)何昌林:《中国俗字谱与拜占廷乐谱》,《交响》1985年3期。吴晓萍先生更进一步认为,这种筚篥谱就是后来工尺谱的起源。(18)吴晓萍:《有关工尺谱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文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第267-298页。均有一定道理。另据《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19)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2页。由此可见,唐人仍广泛地使用“龟兹乐谱”以记录乐曲。对此,美国学者谢弗认为:“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过这种龟兹乐谱的实物,但是在敦煌发现了用弦线标谱法写成的古琵琶曲,而且在日本也保存着唐朝五弦琵琶使用的曲谱。这些记谱法强烈地受到了龟兹乐的影响,宁王所阅读的龟兹乐谱必定与它们极为相近。”(20)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02页。这种猜测也有一定道理。
六朝时期,龟兹乐部西来的另一著名例子是“琵琶七调”理论的传入,其事见于《隋书·音乐志》:“开皇二年(590),……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郑)译云:‘先是周武帝(561-578)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因作书二十余篇,以明其指。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众从译议。”(21)魏徵等:《隋书》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5-347页。从郑译的话中不难看出,北周武帝时曾有一位名叫苏祗婆的龟兹乐人来到中国,(22)杨宪益先生《关于苏祗婆身世的一个假设》一文曾推测,苏祗婆可能即北齐著名乐官曹妙达;参见杨宪益《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8页。不过,曹氏为粟特九姓之一,与《隋书》所说苏祗婆为龟兹人存在较大出入,在未有确据的情况下,兹从古籍。并带来了“琵琶七调”理论。这一理论为郑译习得,继而在“开皇乐议”中被议乐众人所接受。后来,龟兹七调还成为唐代燕乐调的理论基础,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龟兹乐部西来对《西凉》乐的产生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凉》乐是六朝至隋唐时期极为流行的乐舞,兴起于十六国的前秦,《隋书·音乐志》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23)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78页。由此可见,《西凉乐》的出现时间约在前秦世祖苻坚在位(357-385)末年。及至北魏太武帝“平河西”,吞并北凉(439),得到了这种“秦汉伎”,遂改称“西凉乐”,“西凉”在北魏人眼里即“西方凉州”的意思。更为重要的是,《西凉》乐乃“变龟兹声为之”,所以其产生乃直接渊源于西来的龟兹乐部。到了魏、周之际,此乐已有“国伎”之称;它在北齐也极为流行,当时中书省内就曾专门设立“伶官西凉部直长”以管此乐之进御。(24)魏徵等:《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第754页。由此足见六朝龟兹乐部的西来对中国古乐影响之大。
三
到了隋唐时期,胡乐之全面输入不但没有中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前人考证,隋唐宫廷胡人乐官中有几个姓氏最为著名,比如于阗的尉迟氏,疏勒的裴氏,龟兹的白氏;此外还有西域粟特九姓中的石氏、曹氏、米氏、史氏、何氏、康氏、安氏、穆氏等,(2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二《流寓长安之西域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5页;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35页。以下介绍数例:
《隋书·音乐志》: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26)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78-379页。
《乐府杂录·觱篥》: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不数月到京,访尉迟青所居在常乐坊。……乃求谒见,阍者不纳,厚赂之方得见通。青即席地令坐,因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曲终,汗浃其背。尉迟颔颐而已,谓曰:“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调吹之,麻奴涕泣愧谢。(27)段安节撰、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14页。
《乐府杂录·琵琶》: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皆袭所艺。次有裴兴奴,与纲同时。曹纲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捻,不[下]拨稍软。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师于曹纲,尽纲之能。(28)段安节撰、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第10页。
《听安万善吹觱栗歌》(李颀诗):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29)清官修《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54页。
据上引第一条史料,白明达乃龟兹白氏,他在隋朝炀帝时为乐正,创制了大量“新声”。据第二条史料,尉迟青居于唐代长安的常乐坊(即长乐坊),由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置左右教坊,左教坊所在的延政坊原名长乐坊,可知尉迟青实为教坊乐官,(30)有关唐代教坊的问题,参见黎国韬《历代教坊制度沿革考——兼论其对戏剧之影响》,《文学遗产》2015年1期。他最擅长的乐器则是胡乐筚篥。据第三条史料,中唐最善于弹琵琶的乐官有曹氏、王氏、裴氏等,其中曹氏父子为西域粟特九姓的后裔。至于李颀诗中提到的安万善,亦出于粟特九姓中的安国。如果说,六朝时期的西来乐部以龟兹乐最为著名的话;那么,隋唐时期最著名的西来乐部则要数粟特九姓胡人所传了。(31)在中古西域地区,居住着“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等“粟特九姓胡人”,它们以善于经商、信奉祆教而著称;有关情况,参见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粟特九姓胡人特别擅长歌舞,极负盛名的“胡腾舞、胡旋舞”等,就是从粟特九姓国传入的。另外,隋《九部乐》中的《安国乐》《康国乐》,分别从安国和康国传入,唐燕乐部伎中尚见保留。(32)据《唐戏弄》第七章所录,唐代优伶九十八人中,至少有十六人皆为此粟特九姓一系,并可作为粟特乐盛行的例证。参见任半塘《唐戏弄》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66页。
以下不妨举粟特九姓中的“何氏”乐官为例,看看这种西来胡乐传入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艺术史家常任侠先生曾指出:“不仅米、何、康、石、曹、史诸姓可以断定为九姓胡族,尉迟青是南疆于田贵族,即李姓、贺姓,也可能是胡族的乐人。据冯承钧的研究,则《何满子》不仅是舞曲名,而且是以歌人得名,何满子也是西域何国人。”(33)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75页。李姓、贺姓是否胡人,尚须细加甄别,但何满子是粟特九姓中何国人的可能性却很大。据《碧鸡漫志》记载:
《何满子》。白乐天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云:“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34)王灼撰、罗济平校点:《碧鸡漫志》卷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由此可见,乐曲《何满子》为乐工何满子临刑前所作。但为什么说这个“何”就是粟特九姓中何国之“何”呢?“满子”一词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据《新唐书·武平一传》记载:“胡人袜(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3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95页。引文提到的“袜(襪)子”一词,未见古书提及,故不可直解;但从它与“胡人”并称来看,此词当是译语。另据学者研究指出:“祆教或火祆教就是西语的波斯magi古教,正因为此教以幻术闻名,所以magi在西语中的解释就是:古波斯僧、祆教僧、魔术家、弄幻术者。”(36)罗绍文:《西域幻术东传及其影响》,原载《新疆艺术》1988年5期,引自李强《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对此说法,笔者十分赞同;反观“magi”,其读音与中古时期“袜子”的读音极为相近,由此推断,袜子一词所对译的应就是magi一词。换言之,唱《合生》的何懿其实是一位信奉火祆教的胡人;如所周知,粟特九姓主要信奉火祆教,所以何懿显然来自粟特何国,故不妨称之为“何袜(襪)子”。如果将“何袜(襪)子”和“何满子”放在一起比较,满子与袜(襪)子的读音也极为相近,两人又都姓何,所以何满子极有可能是来自粟特何国且信奉火祆教的乐工。前引《碧鸡漫志》提到白居易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细勘诗意,白氏似乎早已知道满子既是人名也是译名。
四
汉唐是胡人乐部西来中国最频繁的时期,唐宋则是中国乐部东传日本和朝鲜最频繁的时期。其中唐朝传入日本的音乐艺人、乐舞器具、戏剧表演和音乐书籍等,实不在少数。比如武则天朝的《乐书要录》,就是由日本僧人吉备真备带回日本而得以幸存于世的珍本,在中国却久已亡佚;又如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传乐器,达到十五种、五十九件之多,都是世上珍品,中国国内难得一见;再如唐代的歌舞戏《兰陵王》和《拔头》,在日本尚有同名乐舞流传;(37)关于日舞与唐舞之关系,参见任半塘先生《唐声诗》下编《弁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此外,唐朝乐人中出现了东赴日本并在日本充任乐官者,皇甫东朝父女就是著名的例子。(38)据冯文慈先生称:“在奈良时代末期,唐朝也有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为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叫做皇甫东朝。据《续日本记》的记载,他和他的女儿皇甫升女于女帝孝谦天皇天平神护二年(766)十月在日本法华寺演奏了唐乐。转年,皇甫东朝被任命为雅乐员外助,成为日本的乐官。由于被风浪所阻,父女二人未能回国,终身居留日本。”参见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以上这些情况,学界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但对中国唐朝音乐制度影响日本乐制建置的问题,则尚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早在西汉时期日本与中国已有交往;到了隋朝,又曾数次派“遣隋使”来中国学习文化;及至唐代,“遣唐使”更不下十余次之多。而在遣唐使者的成员当中,有所谓“音声长”与“音声生”,(39)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其任务是专门学取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据《日本国志·礼俗志三》载:“由唐时传授乐曲有《万岁乐》《回波乐》《鸟歌承和乐》《河水乐》《菩萨破》《武德乐》《兰陵王》《安乐盐》《三台盐》《甘州》《胡渭州》《庆云乐》《想夫怜》《夜半乐》《扶南小娘子》《越天乐》《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杨柳》《春庭乐》《柳花苑》《赤白桃李花》《喜春莺》《平蛮乐》《千秋乐》《苏合香》《轮台倾杯乐》《太平乐》《打球乐》《还京乐》《苏芳菲》《长庆子》《一团娇》《采桑》《秋风乐》《贺皇恩》《玉树后庭花》《泛龙舟》《破阵乐》《拔头》诸乐,然传其谱不传其辞。”(40)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上举的一大批乐曲,显然是通过“音声长、音声生”等东传到日本的。而“音声长”与“音声生”这些称谓,却是出自中国。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乐]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4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二,第477页。不难看出,日本的“音声长、音声生”乃源出于唐代太常寺所辖“音声人”,他们是太乐署、鼓吹署管辖的乐工,中国音乐制度对日本乐制建置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日本乐制受唐朝乐制之影响还可以举出不少例证,比如说“内教坊”这一乐官机构,在日本史书中初见于《续日本纪》卷二十二“天平宝字三年”(759),赵维平先生指出:“虽然日本内教坊的成立不知其明确的时期,但是在初唐高宗设立了内教坊制度后,玄宗二年(714)在禁中又设内教坊和左右教坊,此时正直元正天皇时期,也就是说在八世纪上半叶日本已经开始接纳了中国的音乐制度,并形成了内教坊的组织机构了。”(42)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将日本内教坊的渊源追溯到唐朝内教坊,是没有问题的,但赵氏的表述却有不少错误:其一,初唐内教坊建于高祖武德(618-626)年间,不是“初唐高宗”时期;其二,左右教坊的设立是在玄宗开元二年(714),不是“玄宗二年”。尽管有误,说“日本内教坊制度受唐朝教坊乐官制度影响而设”乃不争之事实。
又比如说“雅乐寮”,是根据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制定的大宝令而建立的乐官机构,(43)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第40页。《日本国志·礼俗志》对其设置和职能有较详细记载:
伶官:古有雅乐寮,隶于治部省。设歌师四人,歌生三十人,歌女百人,舞师四人,舞生八人,笛师二人,笛生六人,笛工八人。唐乐师十二人,内横笛师一人,合笙师一人,箫师一人,筚篥师一人,尺八师一人,箜篌师一人,筝师一人,琵琶师一人,方磬师一人,鼓师一人,歌师一人,舞师一人,乐生六十人。又高丽、百济、新罗乐师各四人,乐生各二十人,又伎乐师一人,腰鼓师二人。伶官皆世禄,世守其业,至今尚有存者。(44)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六,第375页。
由此可见,雅乐寮为日本治部省辖下的伶官,下设乐官、乐工多种,世袭其业,并兼管高丽、百济、新罗等乐。张前先生曾指出:“雅乐寮……是类似于唐朝大[太]乐署那样的管理宫廷音乐活动的机构。成立当时,它不仅是管理唐乐以及其它外来音乐,例如三韩乐、伎乐等,同时也管理日本的国风歌舞。”(45)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第40页。将雅乐寮和唐朝太乐署联系在一起,颇有道理。我们从“雅乐寮”的名称不难看出,它主要职掌日本“雅乐”,与唐代太常寺辖下的“太乐署”之主要职掌基本相同。而在中国,“太乐”始置于秦汉时期,历代沿置,都以“掌管雅乐”为主要职能,所以很明显是日本雅乐寮的渊源所在。另外,从东晋以至隋唐,太乐署职能有所扩大,逐渐兼管各种外来乐舞,(46)参见黎国韬《太乐职能演变考》一文所述,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与日本雅乐寮同时掌管高丽、百济、新罗等异国乐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除内教坊和雅乐寮外,当时日本还有一个乐官机构叫“鼓吹司”,或称“吹部”,见于《日本后纪》恒武天皇延历十五年(796)十月所载。张前先生指出:“鼓吹司是日本学习唐朝鼓吹署的制度,主要为在宫廷仪式中演奏鼓吹音乐而设立的机构。”(47)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第43-44页。这一说法也颇有道理。在中国,鼓吹署始置于西晋时期,历代大多沿置,唐朝亦有之,属太常寺辖下乐官,(48)参见黎国韬《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音乐研究》2009年5期。前引《新唐书·礼乐志》即提到音声人隶于鼓吹署“番上”的情况。总之,八世纪日本国的乐官制度是雅乐寮、鼓吹司、内教坊三署(司)分立,这与唐代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四署(司)分立的制度非常近似,仅少了梨园乐官这一系统。可以说,日本乐制的建置实深受唐代音乐制度的影响。
五
中国乐部东传的另一个主要流向是朝鲜,但其输入时间则与日本有所区别。陈万鼐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歌舞形象,一般人都认同日本雅乐近于唐代音乐,韩国雅乐近于宋代音乐,这是从两国雅乐演奏的审美观而判断的。”(49)陈万鼐:《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更主要原因是:中国乐之输入日本多数发生在唐朝,而输入朝鲜多数发生在宋朝。正如席臻贯先生所云:“如果说对日本音乐曾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唐朝音乐的话,那么对朝鲜音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宋朝音乐。在高丽时期,宋朝雅乐的传入被认为是朝鲜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50)席臻贯:《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兰州: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以下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谈谈乐部东传朝鲜的情况。
据说,商纣无道,箕子逃入朝鲜,所以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可能已对朝鲜一带产生影响。另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51)范晔撰、李贤等注,司马彪撰志、刘昭注补《后汉书》卷八十五,第2813页。由此可见,朝鲜音乐受汉人音乐影响的时间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时期。不过上述影响毕竟是零星的,到了北宋,中国乐才开始大规模输入朝鲜,据《宋史·乐志》载:
(政和六年)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
(七年二月)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52)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9页。
据此可知,北宋徽宗置大晟府、制大晟乐后不久,大晟雅乐即已传入朝鲜,由此对朝鲜的音乐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宋史·外国三·高丽》就记载:“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晟燕乐》、笾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53)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七,第14049页。又载:“乐声甚下,无金石之音,即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曰‘乡乐’,其故习也。”(54)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七,第14054-14055页。据此可知,朝鲜乐部之所以分为左右两部,正是受宋乐东传影响所致;其中“唐乐”之“唐”,是唐人的意思,并不是指唐朝。对此,冯文慈先生曾经指出:“高丽是唯一从中国吸收宫廷雅乐即北宋大晟乐的国家。”(55)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第138页。笔者以为,这句话在表述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中国宫廷雅乐并非只有大晟乐,吸收中国宫廷雅乐的也未必只有高丽国。当然,朝鲜乐制主要受宋乐影响一事则无庸置疑。
除大晟乐外,北宋的教坊乐也曾大量输入朝鲜。比如朝鲜郑麟趾等人撰有《高丽史》一书,(56)郑氏《高丽史》原刊于明景泰二年(1451),近人姜亚沙等编入《朝鲜史料汇编》一书中,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其卷七十一《乐志二》的“唐乐”部分就记载了北宋徽宗时传入朝鲜的中国乐曲,内有大曲七套:《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莲花台》《惜奴娇》(曲破)《万年欢》(慢)。兹录《寿延长》一曲为例:
舞队、乐官及妓衣冠、行次如前仪。
乐官奏《宴大清》引子,妓二人,奉竹竿子足蹈而进,立于前,乐止。口号致语曰:“红流绕殿布祯祥,瑞气云霞映圣光。万方归顺来拱手,梨园乐部奏中腔。”讫,左右分立。
乐官又奏《宴大清》引子。妓十六人分四队,队四人,齐行舞蹈而进,立定,唱《中腔令》“彤云映彩色”词曰:“彤云映彩色相映,御座中天簇簪缨。万花铺锦满高亭,庆敞需宴欢声。千龄启统乐官[功]成,同意贺元珪丰擎。宝觞频举侠群英,万万载乐昇平。”
乐官奏《中腔令》,各队回旋而舞,三匝,讫,各队头一人,队队分立为四人,或面或背而舞,讫;退坐低头,以手控地。各队第二人如前仪,讫。各队第三人亦如之;各队第四人亦如之。循环而毕,如前仪,向北立。
乐官奏《破字令》,各队四人不出队,一面一背而舞。奉袂唱《破字令》“青春玉殿”词曰:“青春玉殿和风细,奏箫韶络绎。瑞绕行云飘飘曳,泛金尊流霞艳溢。瑞日晖晖临丹扆,广布慈德宸遐迩。愿听歌声舞缀,万万年,仰瞻宴启。”
乐官奏《中腔令》。竹竿子二人少进于前,口号致语曰:“太平时节好风光,玉殿深深日正长。花杂寿香薰绮席,天将美禄泛金尊。三边奠枕投戈戟,南极明星献瑞祥。欲识圣明多乐事,梨园新曲奏中腔。”讫。
乐官又奏《中腔令》。如前仪足蹈而[退],各队四人亦从舞蹈而退。(57)据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一《乐志二》,收入姜亚沙等编《朝鲜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98-200页。
如所周知,北宋教坊中有所谓“队舞之制”,内分“小儿队”和“女弟子队”两种,主要就是进行“大曲”表演(参见《宋史·乐志十七》所述)。因此,《高丽史·乐志二》所载的这批大曲乃北宋教坊队舞传入朝鲜的重要见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所能看到的宋代大曲“曲本”(参考“剧本”一词,本文将记录大曲队舞具体表演情况的文献称为“曲本”),基本上是南宋或以后的材料,北宋的资料极为罕有。保存在《高丽史·乐志》中的这批“曲本”实属珍贵,其中关于大曲表演形态的记录值得古代音乐史、戏剧史、诗歌史研究者深入探讨。约而言之,宋代是中国乐部东传朝鲜的重要时期,其中以大晟乐和教坊大曲的东传最具研究价值。
小 结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在先秦时期,已经有零星的“乐部西来”,“伶伦于大夏之西截竹制律”的神话传说为此保存了史影。两汉时期,随着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乐部西来始见频繁。到了魏晋南北朝,胡人乐章、乐器、乐舞、乐工更加大量地涌入,其中尤以龟兹乐部的影响为大。到了隋唐时期,宫廷出现不少声名显赫的胡人乐官,粟特九姓胡乐则在诸部胡乐中最负盛名。另一方面,唐代又是中国乐部东传日本最频繁的时期,音乐制度的影响尤为巨大,日本的雅乐寮、鼓吹司、内教坊就是在唐朝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的影响下建立的。而宋代则是中国乐部东传朝鲜最频繁的时期,其中大晟乐的传入,改变了朝鲜乐部的构成;北宋教坊大曲的传入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保存于朝鲜古代典籍中的大曲“曲本”在中国多已失传,这些曲本为后人研究唐宋大曲和唐宋戏剧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材料。总之,乐部西来和乐部东传都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交流史上的著名事件,它们为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致而言,龟兹乐部和粟特胡乐是乐部西来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而日本唐乐、朝鲜宋乐则是乐部东传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也可以说,“兹龟、粟特、日本、朝鲜”是这方面研究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