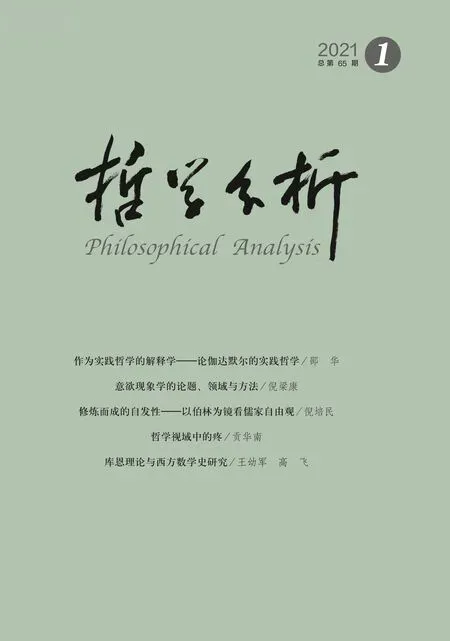主体、言语与情境的诠释学思考
——从理性与德性作为概念的处境出发
吴 雁
意识行为视理解为必需。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意味着诠释的不断发展与构建。这样看来,理解促生发展与提升,即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论与价值实践的等同。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所经验、所理解的东西,究竟是“意识及其对象性还是在无蔽和去蔽之中的存在者的存在”?①只是引用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参见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7, S. 91),但本文中问题所面对的语境与理论前置是与此不同的。在诠释学中恐怕更应该考虑的是后者,这也是“文化摆设”②海德格尔提到了文化的“摆放”(参见冈特·绍伊博尔:《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指:有存在者,无其存在——这种情况的文化则成为“摆设”。与“能指链”③“能指链”,也称“能指连环”,本是拉康的概念(参见拉康:《拉康文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这里用它来表达私有语言能指的被动“连绵”,既在主体间性中消减主体,又制造大量的误解与病态意识。的言语情境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技时代,弥漫着理性掌控与强力意志,不仅仅文化成为“摆设”,人类自身也日益成为“摆设”,这时候存在者的存在似乎在消解,消解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技术式文化工业的“第三持留”。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意见,艺术与各种意指情境原本是可以反斥和唯一表达存在意义的,但事实是,当存在者处于一个形态中,它依然在以特定的方式在消解其存在。①冈特·绍伊博尔:《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目录页。那么,如何保有存在者的存在②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并不意味着其存在,而存在并不总是表现为存在者。所以才有这里“保有存在者的存在”一说。,即如何更好、更有意义地诠释,也即如何使人类及其实践更有意义,达成无遮蔽的本真,从而成就美德——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上述问题更多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陷入诠释的泥潭中,陷入作为语言运用通病的“能指链”现象之中。“能指链”概念来自拉康,但这里主要用来表达人们对于能指的能指式解释,它已经造成了部门语言的误用,后果相当严重——部门语言成了能指不再具有知识确定性的能指本能。此外,人们相互间的私有语言交流中,作为言语行为的能指“连绵”造成主体间性对于主体保有的消减。③即后文所说的,人们以喻体为实指,从而以想象的情境替代元情境,以虚假的主体替代元主体,在异化主体间性的基础上造成事实上的主体消减,即主体存在性的丧失。所以,这些反映在意识领域就是,语言似乎处处充满着隐喻、暗喻,而人们却以喻体为实指,继而深深陷入意识的大泥潭中不可自拔。这看上去是语言的堕落,其实是意识的堕落。这些都对诠释学构成了挑战。
人们开始深刻反省:这类情境的产生与发展何以可能?言语行为构建情境时,主体的理性与德性何以自处?理性与德性在私有语言和公有语言不同的言语行为构境中各自发生着何种作用?它们与主体的关系如何?私有语言有没有可能发生公有语言的转向?在以上问题中,主体和主体性又有何种作用?人们浸润于语言之中,生活于言语行为之中,存在于情境之中。主体的理性还是德性概念,虽然并非必然要思考的,但的确是会出现的问题或可能发生矛盾的问题。这些最重要的话题,比较适合从其理性作为概念的处境开始,即从诠释的言语和情境出发来进行探讨。
一、主体、言语与情境的诠释
(一) 理性在私有言语情境中的合法性与历史化困窘
理性与主体相互存有,这是主体作为合法主体的存有。④主体具有意识,在更社会化的范畴中会以主体具有理性这种说法来表达,即理性的持有与理性本身的存在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表征着主体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是所谓“理性与主体相互存有,这是主体作为合法主体的存有”状态——这更多的是对于社会意识特征的表述。但在现代文化背景下,或者说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各种意识持留①非主体性的、超越了时空间性的意识持留,由现代科技支持与保障的“第三持留”(斯蒂格勒的用词)。例如:电影工业以电影的形式对于意识的持留,使得人的意识与主体在某种意义上相剥离,即所谓主体异化,即意识的相互非存有,或单一非存有但增长(如电影意识的工业增值),后者更加强了异化的程度。出现的现时代,主体会发生不知不觉的异化。对于主体性不再与理性相互自然存有,甚至相互为非存有,或单一方面的非存有和增长所意谓的异化而言,理性与主体间不再是相生相存的关系。②当可以作为截留、持有与再造意识的由现代科技所支持的“第三持留”更进一步发展时,主体作为意识的生产者不再是必然的了,作为意识的重要成分的理性首当其冲。这意谓着原本作为现代科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意识——理性,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反而成为自身的否定者。另一方面,在“第三持留”中存在且衍生出的“意识”与其表达,呈现出一种与主体存在者和存在不直接关联的特性(这也是“第三持留”对于意识持留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异化出现了,主要是主体与意识最直接的关系的异化出现了。这种非自然状态下的二者关系急需探讨。
由此出发,作为主体认知、理解与诠释意识自身的私人语言,不是缺乏存在和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延展的第一步,私人语言阶段是必然的。当然私人语言也会转化,即终究会成为私有语言——随语言外化为言语行为要表达的主要内容的变化而终究变化。
1. 私有语言与私人语言的必然性及普遍存在
语言对于认知的作用至关重要。认知总是要从具象开始,即有样本的实指。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语言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在于如何用语言的语词、语句等更贴切地表达具象。这种对于认知的表达需要主体的理解,也会表现为尽可能客观地期待想象的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理解。故而依照主体的理解,总有可能建构出来一个适合自身规定性的意义系统。或者说,这个意义系统并不是被建构起来的,而是既定存在着的,只不过是通过语言的指称,使之以符号化的形式完成具象凝定、固化呈现,如果没有语言式的呈现,世界将只是一种关于隐性事实的世界,只是关于可能性的世界。这就是主体认知本身的意义,也是语言在其中的决定性意义。
可见,基于主体的语言是合理的,它本身在争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发生着演变,即始于语言、终于诠释。这不仅仅是语言作为现象的演变过程,更是主体由认识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到其存在本身的过程。所谓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维特根斯坦)时, 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它并不会表现为从语言到语言的单一与直接性,而是首先会被理解并演绎为私有语言,这种私有语言的出现并不突兀,是在语言发出意向性的同时才出现的。所以,私有语言的特殊性在于其能展示自身于言语行为之中,后者建构了私有语言的言语情境,即在场之“场”——虽然主体发动言语行为之原初并不欲其成为这样的私有语言。如此一来,无论是言语行为于私有语言的展现,还是言语行为展现并蕴含其中的主体情境,都意味着理性的可疑与困窘。这不必定是理性的丧失,某种程度上还表达着理性格外的合法性——个体理性的合法性凸显,但理性在建制的同时也感受着被建制,这使它蕴含着冲破囿限的巨大张力。理性从而尤其追求意蕴,求其于解构的同时再建情境——宏大而深远,真实且圆满。虽然看上去这种追求并非如此尽得心意,道阻且长(这一困窘在言语行为作为主体自身救赎的理性转变中尤其具有多层次性与丰富 性)。
事实上,私有语言包含着私人语言,或者说,私人语言是私有语言不同形式中的一种特殊表达。由于对于语言(包括文本语言,但不限于此)的理解,认知主体会试图在其中找到与自身语言体系相类的匹配,在发现有异的时候,可能会放弃自身,迎合认知对象语言体系,一步步达成领会和内化。在此过程中一般有两个选择:其一,完整地接受其语言体系;其二,以主体既有的语言体系再诠释——说明对象语言原本就是对象语言主体的某种诠释。当然还有第三种诠释,就是既有主体加上对象主体体系整合为第三种体系,这在诠释者看来是最优的,是对对象和诠释本体的超越。这三种诠释看上去是不同的,但对于诠释的形而上学来说意义相同,即以一种认知主体能接受的语言进行诠释,这时所谓的私人语言产生。
这里的私有语言和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个不具存在可能性的私有语言是有区别的,当然在他看来,那种不可能的私有语言应当是这样的:“这种语言的语词指称是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称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明显可见,维特根斯坦是基于语言的社会文化性来分析并得出结论的。所以,这种私有语言的特征是:只存在于个体的内情境之中;其言语行为不为他人所理解,可名之为私人语言——如上所述,作为私有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事实上,在诠释学要面对的意识结构中,存在着大量的包含私人语言形式在内的不同形式的私有语言。在某些人身上,这种私有语言的使用甚至远远超过了公有语言,他们还使它的使用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最有趣的是,在维特根斯坦否定的私有语言的基础上,人们可以描摹出两类“私有语言”:一类是基于其作为指称本身,另一类基于其作为语言的意义。如果并非侧重以上两类的任何一种,私有语言一般都不会产生,或者说,在公有语言的领域中,私有语言形成和出现是具有一定存在条件的。①但现在看到的是,从维特根斯坦开始的研究者们对于此类私有语言的混淆与误读。
第一类是基于作为指称本身的私有语言,一般会首先出现于具有共性环境、共性经历、共属秘密、共同敌人、共同友人等小范围的人身上,因为个体以为这个小范围有可能更私密、更特别。当语言以私有语言(指称与公有语言具特定差异性)作为交流实践的行为时,私有语言就真正出现了。但私有语言的缺憾是,交流互动者之间并不如语言发起者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很好地理解,因为私有语言只具有其本身的指称联系。交流者会假定对方与自己是有共同指称意识的,但实践的事实往往是,人们(语言的主体)相互的误读、误指、误认、标准频频变化,语言在此成了一种真正的私有语言。
第二类是基于作为语言的意义的私有语言。这种私有语言的出现是因为主体间使用的语言意义不具同构性,即语言发动者处于不同的语言区域,如处于公共域和自以为的公共域,因而对话或语言行为不畅,由此产生私有语言。可见,私有语言并不是稳定的且如公有语言般固化的语言状态,它是会时而出现、也会倏忽飞逝的特殊的语言系统,它的指称和意义标准随时可能变化,其行为范围可能极狭窄和私密,但它是广泛存在着的语言状态,是一个除公共语言域之外人类意识的同样重要的状态,而且在技术时代,它的重要性远超公共语言域的公有语言。
那么,了解了这样的私有语言,在对其理解和读取时,又该秉持何种理念?事实上,在最早触及私有语言的时候,人们最有可能将之置于公共语言区域去理解,即人们即便不了解私有语言系统的规定性,至少也可以理性地去看待它们,但这往往令私有语言丧失了旨趣。在这个层面上,理性使人们失去了语言的意义,而对私有语言的回归,则使理性完全附属于私人言语情境,无法自主,成为工具性存在,时日久长,丧失了的则是人作为存在者本身的存在。
此外,除了如上两种私有语言(不包括私人语言),还有更广阔意义上的一种私有语言,正是这种语言,现在给人们造成了巨大困扰。这种私有语言就是部门语言,简言之,它不是以主体的个体为私,而是以技术的个体为私,从而是专门化的、一种部门内的私有语言。以前科技不发达,人们或许还对之无甚感觉,但随着科技理性越来越强大,部门语言作为私有语言,对于其范畴以外的人群更加具有类型与知识的排斥性,并显示为非公有性。后两个特征是自然发生的,例如,量子计算领域的部门语言已经是相当私有的,因为即便将语言的内容展示于大众,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与诠释它,这样的私有语言已经处于无法让人(私有语言圈之外)解构、诠释或理解的程度了。这只是其中之一,在现代科技社会,这类私有语言数量之多,已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私有语言发展到这样强大莫争的程度,对于社会来说,诠释已经不能改变私有语言前进的步伐。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文化摆设”的由来,人们也将成为此类文化的重要元素。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至少需有一个可行性的思路。
所以,实际上有三种私有语言,这里的私有是以语言系统的个体性与部门性而言的。故当其言语行为的强力意志成为消解主体的武器时,主体无力还击。事实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他者的主体自我,都免不了以他者形象塑造及再塑造自身。当言语行为的强力对其主体产生冲击时,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如此的改变呢?因为这里还牵扯到另一个重要元素——质料。事实上,认知构成的最初摹本来自物理世界。这个摹画过程可参照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摹画形式”。有摹本的意识经过经验规定性的改造,意识结构中的物理意象才能够建立起来。这样的物理意象会包括自我的形象、他人的形象等。当然,关于自我或他人形象固化意象的观念则是物理规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与其说是主体间的,不如说是主客体互置间的,所以是一种建构模式。如果人们足够重视技术带来的副作用,诠释学就不能忽视“质料”与物理构成。
总体来说,私人语言的认知主体是具有既有知识系统的人的实体个体。私有语言的认知主体可以是部门主体,即一种知识系统主体,此主体表现为符号性的(集体性作为个体符号)主体,但同样以拥有私有语言为特征,此私有在某种程度上是纯粹客观的、不具有普遍解构性的,更具意义的是其作为意识必然要表现出意向性来,而当后者有所表现时,言语行为也就此产生。
2. 不同理性持有的言语行为作为情境与诠释的阈限
语言和言语活动不应混为一谈。言语活动或许会以语言为内容,但更多地以一种社会行为的姿态出现——当社会意识已经内化到主体中时,社会行为本身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公众的,但首先是私人的,并非必然处于外情境之中。一般来说,如果是言语活动,那么至少会有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交流(当然也可以是自言自语),这时候的语言是被使用的状态,那么语言的意义就不是单纯地由其自身作为系统的规则所决定的,而是由说话者与听话者所在的情境、二者对于公共语言的默契程度,以及私人语言的范畴、确定性等因素所决定。此时,语言作为被施行出的行为,被称为言语活动,在其活动中伴有音声、文字、手势、表情等,这些现象都是意识中的意象的外化表达,是心理现象的外化表现。与此同时,言语行为(活动)会对参与者产生共同影响——从音、字、义、意各方面,这些影响通过生理再次产生心理变化,这就是言语行为不同于单纯语言的综合反应。言语行为必须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言语行为在自我表达的时候也必然是以个体化的形式进行的,它需要通过言语者本人的具体方式加以呈现,即首先表现为意识内语言。言语行为在意识域中一般表现为两种:其一,言语本身成为一种行为,侧重语言的内容力量,而且是处于某种情境中才能表达出的力量。这种行为可以是符号化的语言,如乐曲、画作、建筑,或多种能指的综合,等等;其二,言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形式的表达,无所谓情境和力量。
可以这么说,无论私人语言或私有语言有多么重大,不表现为言语行为,它们基本就等于无。作为一种思之实践,言语行为不仅表达语言本身的意向,更在其达成情境之际产生更丰富的新的语言和系统,后者足够充实之时,则对于主体产生重新建构或加固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强力意志对于主体的反噬。无论何种情况,它们都是主体与理性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要么平衡,要么不平衡,而后者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异化现象,前者更多时候则会被后者迅速取代。这种现象是由言语行为作为主体认知的私有语言表达的有限性所决定的。
(1) 私有语言言语行为是主体认知与诠释的有限阶段
说到言语行为,一般有两种意谓。其一,谈论言语行为就是谈论一种情境。虽然我们不与心理主义为伍,但不得不表述一下行为主义心理哲学:一种意向性对于意识的精神性刺激,表现为言语行为的即是其神经反射,即反应。这样的机制并不脱离哲学本体——意识的建构。这样的机制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它改变逻辑的先后(当然也许只存在着时间的先后)而产出言语行为,具象为情境。这看起来是心理学的,但也可以是诠释学的工作。其二,言语行为可以是私有语言的,也可以是公有语言的。在私有语言的意向性中,它有着朝向部门主体的自体化,理性在其中主导着分辨、选择、接受的过程。虽然理性在这里是合法的,它似乎弥漫着智慧之光,但它受到语言系统的最大限制——终归摆脱不了部门的限制且无法突破,甚至越突破越受限。理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应用,同时也损害了主体自身,而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私有语言,它从根本上冲击了本真,所以只会远离而不会更接近本真。甚至,言语行为的强力意志凌驾于主体的固有结构之上,而对全体在场的存在者形同“摆设”加以摆放,只看到存在者而看不到存在。
还有必要简要提到其他语言现象。不仅仅语言文本是人们的诠释对象,还有更日常化的其他语言现象,它们虽不以文本为形式但同样表达着语言的所指。应该注意到这类表达,它们或者是在文本前,或者是在文本后,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直接从语言开始的,如果是后者,则可理解为言语行为。所以,这里统一概括为言语行为。
语言离不开言语行为,因为后者才是前者的意义——“理解即意义”。对于所谓的言语行为的基本单位或语言的基本单位,在其语言哲学研究的层面都不具有很大意义,因为言语行为是表达为情境的,这个时候表现的不是语言,语言只是情境借以表达和实现自身及其发展的工具。此时的言语行为很可能是行为上虽然完成了,但其影响和作用刚刚产生,甚至在后续阶段才产生——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言语行为产生特定情境,作为私有语言的言语行为从而成为情境能指,或者说,情境能指的意义就在于能指——能指是诠释的最应有之义。拉康认为,不存在意指,只存在不间断的能指链和这个层面的表达。这个观点值得思考,如果言语行为只是表达为不间断的能指,那么何时可以去蔽?看上去只会是蔽上加蔽。海德格尔在表述艺术之作为技术“座架”的救赎功能时认为,面对一幅关于耕犁的画作,人们不是去探究耕犁及其效用,而是领会其所表达的本真情境,那就是一种对于存在者存在的感悟,是一种对于遮蔽的去蔽。但是,人们如果不熟悉耕犁这种用具,就既不会着意于它的基本农作功能,也不能领会它的存在之意;如果知道和熟悉耕犁,也并没有聚焦于其表象思维,而是关注到它表现为存在。这种存在依然是一种关于某种存在者存在的领悟,并不会映射到主体(阅读者)关于自身的领悟,即使有,也是对象性的、局部的、二分的,没有达到主体自性化的程度。这也是拉康提出“能指链”概念的意谓。综上,主体认知与诠释被限制在似乎无限的能指迁移中,而无法实现其作为无蔽“本真”的无限存在,表象无限遮蔽了人们能够发现真实无限的视角。
私有语言以言语行为的方式编织着生活之网,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能指性。主体在能指的断裂、链接与消解中发生着异化、丧失和升华,其中理性以工具理性、情志理性和直观理性的形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手作用。从逻辑上来讲,私有语言必然要转向公有语言,诠释学事实上的表现也的确如此。
(2) 私有语言的转向与必然性
在私有语言阶段最普遍存在的异化,一直是造成社会与人类巨大困扰的重要原因,这表达的不但是诠释的困窘,也是理性的困窘。
异化首先是主体的异化。这已经被广泛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还有一种由基本社会关系生发开来的异化,类似卡夫卡讲到的亲戚伦理作为基本社会关系伦理的变异。但它并不是一种“真”问题、“真”异化,其根本仍在于另外一种异化——理性与主体关系变异,前者是后者及两者关系变异的“投射”,归根结底还是主体的异化。从言语行为所表达的私有语言整体来看,首先,其主体性的言语建构出自主体的自主选择,其次,这种自主选择有三种自然走向。
第一种情况,工具理性的主体认知与诠释发生能指断裂,产生能指困窘。但这也只是表象,其深层伤害是对于主体具可能性的根本伤害。能指总是具有危险性的,不仅因为其作为认知与诠释的不确定性,而且因为此不确定性有可能造成的主体性变异,即表现为异化而终成险情。如果主体由工具理性出发作出选择,则可加大这种不确定性的概率,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使用可能造成主体性的变异——甚至未必是过度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作为部门语言的私有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对于主体的必然作用,其效果是主体消减或主体丧失,主体性异化为非主体性。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主体错乱,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非同质化的必然结果。但对于认知来说,这种异质却是认知知识累积中的常态,因此存在着一个悖论,即主体认知本身的悖论:主体越多认知,主体越加离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如果非要寻求其原因,那么应该是因为从认知的最开端就孕含着这种矛盾的萌芽——工具理性的目标与使用。工具理性也带来了认知领域能指迁移可能给予主体的有限性生机,因为工具理性既不能消解能指,弃绝对于知识的固着,彻底升华主体,也不能在能指间迁移而形成类主体性的“连绵”,使主体苟延残喘。工具理性只能固着于其认知对象的既有系统,达到对其原生主体的最大程度的覆盖。由此,主体性已成为非主体性,主体已经被消减或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者不断产出、不断对于知识“变现”。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固着性取代主体对于自身的关照的过程。看上去像是“摆设”的主体情境,事实上意谓着主体的更换——对彼主体而言的“摆设”情境,对此主体则意味着“主体性”言语情境。或者说,工具理性对于部门系统的固着,使得部门语言主体成了现主体,从而取代了原初的认知主体,也即诠释取代了认知。这对于认知主体来说确实是一种丧失,而对于诠释本身来说也许恰恰相反。
总体而言,主体对于工具理性全然投注而以寻求认知的部门语言主体及其存在为目标,也就意味着,原主体自愿放弃自身主体性,使工具理性发生固着,不再符合主体自身秩序,从而产生能指断裂、理性困窘、情境作为“摆设”等后果,甚至表现为德性缺失或产生作为恶德的一系列言语行为。
第二种情况,情志理性的主体形成能指链的能指,表现为类主体性“连绵”,主体间性日益减弱主体性。
言语行为对于私有语言的传达是以情境的方式表现的,所以在其中可以同时表达多种形式的理性。情志理性往往表现于主体在人际交往或社会关系联络的认知中。情志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它是以感情、信念等为基础的理性原则与表现。认知能指往往产生能指改造性迁移,使新能指对认知主体的情境知觉而言更合情理。在不同主体的认知进程中,此过程会无限延长,表现为现象主体的“连绵”。初能指在一定的情志理性基础上无限链接新能指,这也就意味着主体的不断迁移与变化,以及认知与诠释的无限转换与歧义的永不消止。这也是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私有语言的局限性与非科学性之缘由。在此意义上,诠释理解中的主体与主体性被削减——主体间性对于主体性的削弱与消减。这种认知情境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其效果与工具理性及其主体的相互作用恰恰相反,但都会表现为德性概念上的负效应。
第三种情况是能指消解。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直观理性主导的言语行为中,即主体充分理解主要是部门语言的私有语言作为能指的知识性,从而直达公有语言言语行为(情境)。除非能指以此种方式消解,不然私有语言是很难突破有限进入更广泛意义的公有语言范畴。
直观理性是私有语言——特别是以部门语言为主的私有语言——转向公有语言的契机。主体充分理解部门语言作为知识性的能指,从而在形式上消解了能指,达到了更深层次的存在,与此同时,也达到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公有语言的存在。
这种以公有语言作为诠释的言语行为的情境中的无蔽,是人类新生活的情境,虽然可以达成“德性”,但仍不是本真无蔽。
(二) 公有语言的言语行为情境达成德性
1. 主体诠释从私有言语行为到达公有语言
语言作为意识结构所造成的复杂现象促使人们试图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消除私有语言的纷乱。这样一来,日常生活的自然语言就成了被诟病的对象,但其在诠释学上的意义更加重要,因为自然语言表达的是存在者存在的常态,反映的是真正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的世界。相对于私有语言,自然语言可被视为公有语言。
如前文所述,私有语言向公有语言的转向是具有可能性的,毋宁说二者实为一体——私有语言阶段是公有语言阶段建构的基础,未经历基础建构,则不具有公共诠释确立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理性只有认识到囿于主体(私有)情境中自身的困窘和存在危机,才可能敞开于公有情境之中,拥抱意指、达成德性。
2. 公有语言作为诠释的诠释
公有语言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非部门化特性。如果说各种部门语言作为私有语言强力控制了现代意识,则其救赎或许来自公有语言。当然,海德格尔的救赎是一种思路,但他所说的“文化摆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坦言其绝望。当文化作为私有语言也已经遭到荼毒,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救赎呢?似乎只有日常化的公有语言了——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情境中映照存在者之存在的质料,以凸显存在意义。
公有语言中的言语行为排除了部门性,似乎更宏大、更普遍、更不设限,基本上也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大多方面,容易在日常情境和根本情境的在场中,实现存在者的去蔽与根本存在,即归向根本美德——本真。
与私有语言的言语行为相同,公有语言的言语行为起初作为能指,必然有其能指主体;不同的是,后者作为能指主体的在场之场,其情境往往是日常生活的叙事,基本的关于“质料”之存在的映照与实践、熟悉的情境与无意识的方式,消解的是阅读者与阅读对象的分离感,同时也消解了在场者的遮蔽,于是在场的存在者感受到的是似乎“不在场”,正是不在场的在场,最终达到了能指的意指,或者说亦消解了能指作为能指本身。事实上,能指与意指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成为了一种滑动——从能指链端到能指消解,能指的终结即意指(元意指),即存在本身。在场者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的存在;完全的无蔽状态,超越了去蔽的无蔽。
当私有语言不再囿于某些哲学家的语言之隙时,其作为概念则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与诠释性。对于诠释概念的解构与再建构是必需的,也正是概念的重新理解与建构,让人们看到理性之困窘与德性之难得,而这都是在场之场的决定。主体能指的言语行为决定了其在场之场的能指情境,这已非单纯的能指链,而应为能指链簇。这种结构在作为公有语言的言语行为时最为日常且简洁,不易觉察到其在场之场,即更易被消解。拉康之所以说能指链,是就其不能达到意指而言,如果能指一旦被消解,则意味着意指的呈现。
不在场的在场,是海德格尔的追求,但在他提出的方案中,这是不易达成的,反而在言语情境诠释的公有语言域内具有达成的可能性。由主体言语行为的理性走向去主体性的情境本真(德性),其关键在于诠释是否为其本身的诠释。只有当公有语言的言语行为不再以阅读日常的方式来消解诠释对象之时,即不再以理解与诠释能指为目标时,无蔽本真才可达成,哲学性的最高“德性”才可达成,存在者不在场的在场(存在)达成。这看上去是二分法的取消,其实是语言对于主体的取消,即言语行为去主体化的自我情境——诠释作为诠释本身。这既是自然之度,又是情境之易。
(三) 概念的理性、德性与主体之不可不提的问题
事实上,作为概念的纯粹理性或德性并不与价值判断相关。这涉及一个纯粹理性的行为法规以及与实践理性之辨离的问题。
首先,关于纯粹理性的行为法规问题。我们在言语行为中看到的往往是理性基于欲望基础的自我放纵,所以有必要了解此中的理性及其行为法规。
对于纯粹理性及其在于人类实践中的法规问题, 康德很早之前讨论 过:
人类理性在自己的纯粹应用中一事无成,甚至还需要一种训练来约束自己的放纵,并防止由此给它带来的幻象,这对它来说是耻辱的。但另一方面,使它重新振奋并给它以自信的是,它能够并且必须自己实施这种训练,不允许对自己进行一种别的审查……也许,它可以希望在还给它剩下的唯一道路上,也就是说在实践应用的道路上,会有对它来说更好的运气。……所以,这种法规将不涉及思辨的理性应用,而是涉及实践的理性应用……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纯粹理性批判》 (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509页。
事实上,理性除了在自身的应用(实践的理性应用——理解性诠释、言语行为等)中本身具有的防止其他审查的自我保护外,它还需要对于其基于欲望的超出经验范畴之“放纵”加以自我训练。按照康德的意思,由于理性“只能提供自由行为的实用法则”,而后者即“道德的法则”,所以理性的自我训练实应“着眼于道德的东西”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纯粹理性批判》 (第三卷),第511页。。
然而,作为概念的纯粹理性本身并不会先天地囿于所谓的经验式“道德”,它只会表现为“道德”或非“道德”,也即表现为概念的合理或否。所以需要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互辨离,这也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戴维森看来,实践理性是一个整体模式,缺少其整体的任一部分,都会产生不节制的情形,不但是对主体的损害,也是理性本身的丧失。
一旦我们能够把一个生物的活动看作一种理性模式的一部分,这种理性模式同时也包括思想、欲望、情感和意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生物视为有理性的。(在这方面我们极大地受惠于我们构想为言语表述的行动。)由于错误推理、证据不足、缺乏勤奋或者同情心衰退,我们常常不能够察觉一个模式的存在。不过,在不节制的情形中,试图把理性解读到行为里头去必然招致某种程度上的挫折……不节制的特殊之处在于行动者不能够理解自己:他认识到,在他自己的意向性行为里,存在某种在本质上是无理的东西。②牟博选编:《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491—492页。
可见,作为人类这种生物的那些活动,如果在其过程中丧失了思想、欲望、情感和意志中的任何一种,甚至只是消减,都会是对主体的伤害。这里包含着几点:(1)工具理性、情志理性和直观理性都是概念理性在实践中的元素,它们的合理存在状态是共时性的。其不合理的存在状态则表现为无“德”。(2)实践理性如不具备完整性,会直接影响到主体本身,甚至产生严重异化,表现为非道德的、无“德性”的。(3)作为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情境的非完整性,既有可能来自主体,也有可能对主体产生负面作用。这种情境也被视为非节制的,即无理的、非道德的。
二、主体、言语与情境的诠释学
如何诠释就会如何解释诠释学。如果排除了对于私有语言的先在认知,那么诠释从一开始就发生在私有语言域,而且几乎从未走出。当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后,就可以得到更多启发,可以投入到诠释学研究中来。
(一) 诠释不会因主体与理性发生改变,是其应有之义
诠释意味着诠释对象的发生、诠释主体的活动、有语言规范的系统、由言语行为构建的情境。诠释更多存在于私有语言范畴中,因为原则上来说公有语言域的理解与解释并不比人们想象的有更多障碍,还因为诠释作为部门语言本身就属于私有语言域。由公有语言域出发的诠释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出现在公有语言域之中的诠释,也更多是具有全部意向性而不能从言语行为的特殊性被观察到。
对于私有语言的诠释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知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这些诠释的情境能指就是其最真实的存在,但是诠释者往往并不甘于此,而试图寻求其背后或许可能存在的意指,这就构成了能指链。人们之间的误解就此产生,无休无止的能指,意指似乎越来越远,歧义也便越来越多。单一的能指是消除诠释歧义的最根本元素,在这个环节上,“意义即使用”(维特根斯坦)是可以成立的。能指链其实还表达着一种意向,即理性的意向。在能指之中,理性处于私有语言之中,这并不能满足理性冲破藩篱的本能,它感觉到了遮蔽,感受到了接近存在、找到真实自身的欲望。但也是在能指中,理性发挥到了主体内的最大程度,这同时对它产生压抑,此中发生着主体的消耗。这是一个悖论。
虽然主体与理性的变易是一直存在着的,但这个诠释的阶段不可或缺,当然也无法摆脱。试想,一旦不能认识能指之为能指,人们又如何冲破它的遮蔽而抵达意指 呢?
(二) 诠释会因情境与理性敞开发生改变,这是其必然之途
如前所述,能指还是意指,这取决于在场的主体,而在场之场更为重要。在私有语言域内,主体终究面临着自我的不断更新,面临着理性的不断拷问与将要冲破羁绊的张力。这是一种不具有发生不在场的在场可能性的主体与情境。那个时候的言语行为始终表现为根本遮蔽。
而在公有语言域内,情境的能指基本不会引起主体的诠释性障碍——唯一引起遮蔽的就是阅读与其对象的二分关系。人们会说诠释终归消解于情境之中,言下之意是指主体的忘我或参与。这可以解释为“意义即符合”。当然只有这个阶段具有符合(无蔽)的可能性。
三、终结“文化摆设”
言语行为只能是对主体的情境诠释,而主体性表现的不足或过度实际都如上所述,是主体发生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情境与其表达元素是不和谐统一的,看上去就像是“摆设”,而对于文化能指来说,这就是一种“文化摆设”。情境应该是主体的情境,而主体的情境也可以是变化和发展的,因为言语行为对于语言产生反作用,最终指向语言的主体。
总体来说,在私有语言域内,强力意志已经最大限度地改造了主体自身,使得主体固有的理性不再能正常发挥作用,此时,一切都成为了摆设——包括主体在内。而在此阶段的言语行为并不能表达终极性的诠释,这既是私有语言的局限,也是质料(物理构成)的局限。这时候,有意地发展公有语言,以其言语行为的叙事来完成情境再构,从文化的外围修复和改善其主体的消减。如前所述,只有在公有语言域内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符合”意指(随着能指情境的能指消解而达到),如此一来,情境不再是摆设的情境,文化和人的主体也不再是摆设。
理解语言的言语行为、认知情境的能指与转化、着力于主体与情境的“符合”,通过如此种种方式,以情境的诠释学来弥补理解上的盲点,可为技术社会的论争以及理性与德性作为概念的处境问题找到一条可能性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