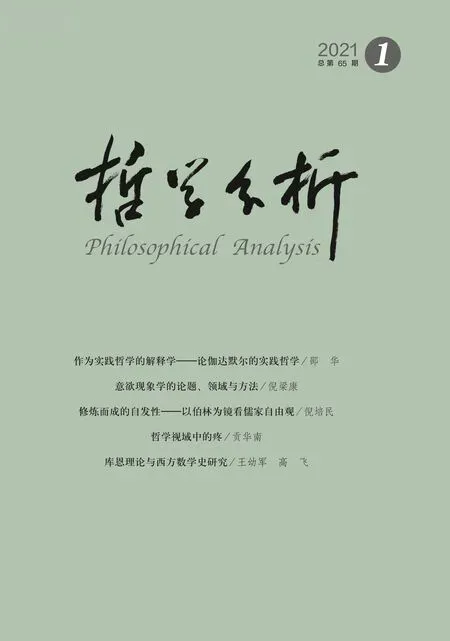行动、叙事与认同:从阿伦特到利科
陈高华
认同(identity,身份、同一性)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处境,也是一个论域极广的话题,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在何种领域,涉及哪种认同,从哲学上来讲,都无一例外地关涉“自我”(self)。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认同都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即都关涉自我的自身意识和同一性,是对“我是谁”的追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认同问题几乎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它彰显在苏格拉底的座右铭“认识你自己”之中,同时也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无论是奥古斯丁的“我对我自己成了问题”的慨叹,还是胡塞尔关于“主体这一世界之谜”的追溯,都是这一判断的证据。与此同时,人还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并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人的认同不可避免地有共同体的维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正是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易言之,认同问题涉及个人与共同体两个方面,正是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构成,才产生了认同问题。
然而,无论是发端于笛卡尔的精神实体的非还原论,还是奠基于洛克的记忆经验的还原论,关于认同问题的种种论说基本上都忽视了认同的公共维度,而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窠臼。实际上,如果没有他者,没有人一出生就进入的世界或共同体,根本上就不会有认同问题。因此,现代社会中的认同问题之所以成为话题,乃是因为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在存在论上,则是因为他者或共同体使得认同成为真正的、政治性的问题,而这正是全球化的推进引发认同危机的原因。本文以20世纪极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的行动思想作为视域,论述一种别具一格的认同观,以彰显认同的公共维度,进而阐述利科的叙事认同观;并为现代社会中因技术化的切割而陷入碎片化生存的现代人寻找一种完整的“认同”,确立一个在时间中持久的公共形象。
一、行动与“谁”之彰显
众所周知,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发端于她对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经历的反思。而实际上,她的整个思想都是对极权主义现象的理论回应。但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并没有如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囿于现成的极权政府,而是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把极权主义阐释为“让人之为人变得多余”的境况,因为“它的胜利无异于人之为人(humanity)的毁灭;它在哪里统治,哪里就开始摧毁人的本质”①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73, p. viii.。更为重要的是,阿伦特进而指出这种境况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而极权主义不过是它最残酷的形式而已。易言之,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是为在现代社会中陷入危机的人重申人之为人的地位,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她的理论巨著《人的境况》之中。她对积极生活的区分和分析,呈现了她对“人之为人的说明”②海登编:《阿伦特:关键概念》,陈高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她对现代社会中劳动地位上升的解释,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危机。
面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起,阿伦特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基础上,重申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境况,即构成人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三个要素:劳动、制作和行动。然而,尽管劳动、制作和行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境况,并对应着人在世界上生活的三种基本处境,但是,阿伦特强调,真正让人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过一种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生活的,则是行动。正如贝纳尔所言:“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生活的首要事业是战胜我们的有死性”①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贝纳尔编,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即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受制于必然性的生死循环,这就要求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们能够在劳动之外有所行动,展现令人铭记的行迹,从而能够在一个持久稳定的世界中塑造一个稳固的公共形象,达到“不 朽”。
根据阿伦特的区分,劳动(labor)是人作为自然界的物种与自然进行的新陈代谢的活动,为的是劳动者自己的生存以及种类的繁衍,实际上呈现的是自然物种与自然物种之间的关系,对应的是“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life itself)”②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7.。严格来说,尽管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此时作为劳动者的人还不可以被称作人,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称进行劳动的人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因此,劳动虽然是人的一种基本活动,对应着人的一种基本境况,但它不足以彰显一个“谁”、塑造一种认同。因为,此时作为劳动动物的人,尚未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仍处在必然性束缚的循环之中,遑论对自身的认同了。让人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的是制作(work)活动。它打破了自然界施加于人的循环过程,通过在自然万物之外生产人造物而构造了一个有别于自然界的世界。因此,进行制作活动的人被阿伦特称作技艺人(homo faber)。技艺人通过人造物而构成的世界,通常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持续得更长,从而为居于其间的人们留存于世提供了可能性。为此,我把人通过制作活动所展示的关系称作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凸显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差别,展现了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性,对应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worldliness)”③Ibid.,p. 7.。尽管人通过制作活动使得自身从自然界中脱离了出来,展现了人作为一个类别的非自然存在,但是它并没有在个性的意义上彰显人的那个“谁”,因而也没有在完整的意义上塑造一种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制造活动囿于“手段—目的”范畴,始终无法摆脱有用性、功利性和工具性,从而陷于一种无尽的“手段”链之中,无法确立事物和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即“无法获得一种‘有意义的’人类生存”④海登编:《阿伦特:关键概念》,第49页。。就此而言,制作活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作为类的“主体性”,但因其本质上将“人类经验主体化/主观化……致使人类被剥夺了它们最深层次的需要”,①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第9页。即每一个人自身在公共世界之中显现的需要。因此,人借由制作活动也无法完满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至多可以给出的是“什么”(职业者、专家),因而也就无法呈现一种本真意义上的认同。要让人摆脱“有用性”之手段链的遮蔽,彰显自我,呈现个人的独一无二性,即回答“我是谁”这个自我认同问题,就要恢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主体间性的经验。阿伦特认为,这种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就是行动。它对应的“人之境况是复多性(plurality)”,即“生活在这个地球并居于世界的并不是人(Man),而是人们(men)。”②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7.易言之,人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维系自我认同,就必须与他人一起展开行动,成为行动者(actor)。唯有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中,个性才会呈现,人才能获得自由,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才得以可能,从而实现真正的认同。
总而言之,尽管劳动、制作和行动作为积极生活的三种要素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完整形态,都在某种意义上维系着人的自我认同,但行动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我认同的充分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人是否真正地实现自我认同,在于他/她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行动者。那么,行动何以彰显一个人的“谁”、塑造一个人的认同 呢?
要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到阿伦特的一个重要区分,即“人是谁”与“人是什么”的区分。根据阿伦特的理解,哲学史上第一个区分“我是谁”与“我是什么”的哲学家是奥古斯丁。他认为“我是谁”是人的自我发问,然而对此的回答只能是“一个人”;而“我是什么”则是人向上帝的求解,对此,作为人之创造者的上帝或许知道,但对于人而言,能够获得的依然是启示性的答案。阿伦特根据奥古斯丁的这一区分,认为人无法像说出“人是什么”那样说出一个人的“谁”,因为人不是上帝,无法用认识自然万物的认知模式去认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是“谁”。那些围绕某个人而得到的认识,无论是生理特征、天才禀赋还是社会角色、职务身份,其实只能是“什么”,它们无论多么独特,都是可替代的,即无法揭示一个人的“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的”③Ibid., p. 97.。正因为此,在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中,惟有行动在生存论上能够彰显一个人的“谁”。毕竟,无论是劳动还是制作,其实完全可以被替代,不只是被他人所替代,而且可以为非人的其他机械或智能所替代。如今,这种替代被一些人认为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危机之一。然而行动则不同,它不仅让人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也使得自身个体化,成为有着可辨识身份的独特人格。阿伦特说:“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自己是谁,积极地揭示他们独一无二的人格身份,使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之中。”①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79.
如前所述,行动对应的人之境况是复多性。所谓复多性,就是指人们之间既相互平等又彼此差异。因为平等,所以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又因为差异,所以有必要相互交流和理解。特别是人的这种差异性(distinctness),有别于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它性(otherness),后者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不同于他物的性质,可以保持物的同一性,却无法具有差异性带来的自身意识。正因为人具有这样的自身意识,“人才能表达这种差异,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②Ibid., p. 176.,形成自己的独一无二性,从而获得认同。阿伦特认为,这种独一无二性通过行动得以展现。借此,人不仅从他物中脱颖而出,打破了自然界施加于人的必然性,也弃绝了制作活动内在的目的性,而且与他人区别开来,凸显自己。因此,这种凸显不是体现在身体上,而是体现在人之为人的那个“谁”上。这个“谁”完全建立在“主动性”之上。它是人之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人可以无需劳动而生活,无需制作而使用物的世界中的一切,但没有人能够无需“主动性”的行动而仍能称之为人。正如阿伦特援引罗马人的话所言:没有行动的生活,实际上无异于世间的死亡,因为所谓死亡,就是“不再生活于人们之间”③Ibid., p. 8.。
正因如此,行动对于“谁”的彰显,需要一个他者的维度。行动作为自我揭示活动,需要一个作见证的“他者”,需要这个他者来感知、了解和判断,由此确保这个彰显出来的“谁”的实在性。更确切地说,尽管行动者的自我认同出自行动者自身的行动和判断,但若没有他人的感知和判断,就无法确保这种“自我认同”的实在性而陷入“自我幻想”。易言之,行动一方面必定是与他人一起展开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的活动,即行动就是互动(interaction);另一方面,行动必定是公开的活动,而不是隐藏着的私下活动,即行动是公共领域进行的活动。也恰恰是在与他人一起展开的公开行动中,行动者个人的自我才得以彰显。因此,与劳动动物那种淹没个性的集体劳动和技艺人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处境不同,“行动者的存在处境乃是,在言行彼此互动交往的过程中,每一个行动者展现他的独特个体性”④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由此,行动既彰显了行动者的那个“谁”,又保障了人们的多元性。进一步来说,这种他者的维度其实就是公共维度,即行动者的那个“谁”的彰显实际上发生在一个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通过行动者与他者的互动,构成了“谁”之彰显的公共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让人们得以显现的公共领域,堪称人所特有的产物。而且,“若没有这样一个显现空间,没有对言说和行动作为一种共同生活方式的信任,就不能毫无疑问地确立自我以及认同的实在性”。①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08.总而言之,行动作为行动者之为“谁”的彰显,是在公共领域与他人一起进行互动的结果,是在人们通过互动而构成的关系网中的呈现。然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犹如劳动活动,在其停止的那一刻就消失不见。因此,要使得那种在公共领域里切实可见的“谁”之彰显得以持久,就需要另一种较为模糊的活动,即叙事。因为“某人是或曾经是谁,我们只能通过了解以其作为主人公的故事得知”②Ibid., p. 186.,而且任何行动其实都具有一种叙事性格。
二、叙事与“谁”之持存
正如利科所言:“回答‘谁’的问题,就得讲述某个生命的故事。”③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Kathleen Blamey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 146.更何况行动自身所具有的脆弱性,使得一个人经由行动所彰显的“谁”始终处于未定之中。若没有稳定的叙事,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某个行动者之为“谁”的确定形象;若没有不断的叙事,行动者的那个“谁”就会渐行渐远而逝。
如前所述,行动者通过行动所彰显自己的“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加以叙述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再现的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之中与他人一起展开的行动。反过来,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他/她恰恰是通过叙事使得自身或共同体与展开的行动(发生的事件)达成和解、实现认同。然而,在阿伦特看来,行动者虽然是故事的主角,却不是自己故事的作者,因为故事之形成,必定是行动者在人际关系网中与他人彼此互动的结果。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换言之,故事表示出一位行动者,但这行动者不是故事的作者和制造者”。④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84.
人作为行动者,本质上是一段生命故事,因此,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物,在生灭循环中踏着自然的节奏,也不同于人的造物那样具有一定的“持久性”,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论述的那样,人是一种朝向死亡的存在者。人之所以需要叙事,以展现自身之为“谁”,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性。更确切地说,若没有叙事,没有行动者展开的行动,就不会有具体而真实的意义,也就无法实现认同。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行动本身的脆弱性来进行阐述。
根据阿伦特的论述,积极生活的三种基本活动各有其特征。行动既不同于劳动那种循环的徒劳性;也不同于制作因其产品而具有的抵御时间之侵蚀的持久性;而就算是行动本身,它也只在展开的时候存在,有其脆弱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与劳动具有某种相似性,若没有叙事者把它们讲述为一个故事,或化为某个作品,它就会像劳动一样在其停止时消失。因此,行动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显现性。所谓显现性,就是说行动即其当下的展开、演示。阿伦特常常用表演艺术来类比行动,以表明它有别于“手段—目的”范畴的制作。比如,跳舞就是跳舞活动的展开,当其停止时,就不再存在。为此,我们若想以某种方式来保持这些行动的展现,留住行动的存在意义,就需要叙事。易言之,行动具有的彰显性和脆弱性,使得它需要叙事才能呈现那种彰显的连贯性和意义。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行动的意义完成于故事的叙述,也就是显示于历史家的回顾。”①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01.
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行动的脆弱性唯有通过叙事或历史书写才可能得到克服,人的那个“谁”的这种认同才能达成。为此,阿伦特特地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认为古希腊的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所以进行历史书写,正是为了把人的伟大行迹从时间的侵蚀中拯救出来,使那些伟大的行迹所彰显的行动者的那个“谁”得以不朽,以战胜人的“有死性”(mortality)。因此,阿伦特说:“根据古希腊人的理解,诗人和史家的工作(亚里士多德视这两种活动为同一个范畴,其共同的主题是人的行动),在于通过记忆创造出持久之物。”②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 p. 48.毫无疑问,阿伦特这里所说的记忆,就是发生的事件即展开的行动的重演或重组,把它们转化为可以叙述的文字作品或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可以流传的持久之物。在《历史的概念:古代与现代》一文中,阿伦特认为历史是最原初的叙 事:
历史作为人存在的一个范畴,当然是比文字的写作,较之希罗多德甚或比荷马的诗作更早。不以历史而以诗的吟唱之角度来看,它的开始在于:当尤利西斯在腓尼基宫廷倾听其言行与遭遇——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时,他的言行、遭遇变成了身外之物,变成所有人皆可见闻的客体。曾经是纯粹发生的事情变成了历史。把独特的事件和事情转化成历史,基本上,跟后来应用于古希腊悲剧之概念:“行动之模仿”,是同样意思。尤利西斯倾听自己生命故事之场景是历史和诗歌的滥觞和典范。“与现实和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悲剧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则是历史的终极目标。①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 p. 45.
在这段话中,阿伦特不仅表明历史是原初意义的叙事,而且认为,正是通过历史这种叙事,倾听者达到了与现实的和解,从而获得认同。对此,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详细阐述。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历史性之呈现,必须经由叙事,或者如前所述,历史即叙事。所谓叙事,“就是把一件历史事件的原始本末,以及牵涉其中的人、事、环境的变化形塑出一具完整结构的、可理解的整体”。②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第148页。因此,叙事是一项塑形活动,它把各种不同的要素塑造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关系复合体。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历史事件的处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一个范例。她并不是在确立某种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链,而是通过揭示种种要素而塑造某种关系整体。通过这样的叙事,种种发生的事件、展开的行动显示了自身的连贯性,也获得了明确的意义。这种通过叙事展示行动之意义的做法,阿伦特称之为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易言之,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共同体)的认同必须经由叙事得到塑造,因而认同表现为在人际事务关系中的动态过程,即行动者(个体以及共同体)通过叙事在与所发生的事件的不断重新和解中实现认同。
如前所述,叙事对于认同之所以重要,首先一点就在于彰显“谁”的行动的脆弱性。唯有通过叙事,这种当下即逝的行动才能获得其实在性和具体意义,否则的话,一切行动以及行动者都会成为历史中的“过眼烟云”。其次,行动皆是互动,发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行动者不仅要与其他行动者互动,还得面对不同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因此,尽管行动者通过行动彰显了自己的那个“谁”,但这个“谁”对于身处世事变化、人事纠葛的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者而言,其实并非一目了然。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人希望通过其行动的践履彰显自己的形象,然而这形象在行动的历程中对行动者本人往往显得陌生。”③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 24.这样一来,行动者需要通过叙事来澄清自己的形象,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彰显自己的那个“谁”。最后,行动总是具体的行动,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因而行动者常常受制于处境而无法进行全盘考虑,在整体上作出判断。此外,具体处境下展开行动的行动者,也难免遭受挫折、陷入情绪之中。凡此种种,若无叙事的事后重建,不仅无法看清行动所展现的整体形象,还可能会让行动者沉溺于情绪之中,无法进一步展开行动、彰显自身。总之,无论是行动的脆弱性,还是行动的复杂性及其造成的负面效应,都需要叙事加以克服。正如阿伦特所言:“人的本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也不是人的性格之优长和缺短,而是‘谁’的认同,它只有在生命结束之际留下一段故事后,才显得明白。”①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92.很显然,“我是谁”这种人的认同,唯有通过历史的回顾即叙事才能得到清晰的表露,然而,这种叙事的认同由于始终需要通过不断的叙事才能得到维持,必定是动态的认同。它既非行动者个人之主观意愿所能控制,也不是某个外在力量的强加足以支配,而是在不断的历史叙事中大白于天下。
实际上,这种叙事认同也同样作用于共同体,也就是说,任何共同体必须通过叙事使其公民对它有一个稳定的认识,否则,最初通过出生(或移民)而来的公民作为“新来者”,就始终是共同体的陌生者,从而对共同体产生一种疏离感。唯有通过不断的恰当叙事,才能让公民对身处其中的共同体获得集体的认同,而不恰当的叙事则让这样的认同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叙事中,作为教育主要内容的历史至为重要,它实际上担负着塑造公民的共同体认同(国家认同)的重任。总而言之,若没有叙事的认同对发生之事的重组,无论是个人的认同,还是共同体的认同,都无法得到实现。因此,人在世界上的归属感,首先要归功于叙事。
三、行动与叙事认同
认同,是行动者与其行动所造成的现实达成和解,从而彰显自己的那个“谁”。因此,它需要叙事把在具体情境下展开的行动编织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故事。在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文章中,阿伦特援引她的话说:“所有的悲伤皆可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进或叙述为一个故事。”②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p. 104.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叙事使得行动者与发生之事达成和解,重新寻回了自己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即实现认同,从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种家园感。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也被阿伦特放在《人的境况》论述“行动”那一章的开头,实际上表明了行动本身的叙事品格。阿伦特在其作品中触及的叙事认同,后来得到现象学诠释学家利科的进一步阐明。
行动彰显了行动者的“谁”,而叙事则使得行动者所展开的事件成为一个讲述的“故事”,从而确立行动者的“谁”。在1983年的一篇论阿伦特的《人的境况》的文章中,利科凸显了行动与故事的紧密关联,并且强调“在阿伦特那里,行动的主要标准就是谁的揭示”①Paul Ricoeur, “Action, Story and History: On Re-reading The Human Condition”, Salmagundi, No. 60, 1983,p. 65.,由此表明了故事与谁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进一步指出,这个“谁”作为负责任的主体,并不是主观主义意义上的主体,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体,即处在人们之间的主体。因此,这里的“揭示”意味着,为他人所见闻,它有一个显现空间,是在人类关系网中彰显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指出,“谁的揭示”与“公共领域、显现空间和人类关系网”②Ibid., p. 66.是相互构成或重叠的术语。由此可见,在阿伦特那里,行动者之为“谁”的认同,是一个政治问题,有着显然的公共维度,有别于劳动动物和技艺人。
然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谁”之彰显的空间性,而没有说明这个“谁”如何在时间中流转。换句话说,若“谁”不是在时间中持久地彰显,就不会有“谁”的彰显。因此,在利科看来,他人的在场或人类关系网不仅为“谁”的彰显提供了一个显现空间,而且为这个“谁”的生命故事提供了一个持续过程,即时间性。这就是说,生命故事以行动者的行动作为基础,却需要人们互动的人类关系网才得以成全。结果,在这个人们互动的人类关系网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却没有哪一个人是自己故事的“作者”。因此,故事和历史虽然围绕行动而展开,但行动者自身却不是这个故事和这一历史的创作者,它们的创作者乃是叙事者。易言之,叙事使“谁”的认同得以达成。此外,叙事不仅使通过行动得以彰显的“谁”获得认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使行动者朝向了不朽。而这一朝向,恰恰又是行动者之所以展开行动的根据所在,即克服自身与生俱来的“有死性”,也正是人的“有死性”的这种时间性,使得叙事成了行动者构建自身认同的关键环节。恰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叙事是为了使那个在行动中彰显的“谁”从遗忘中被拯救出来。概而言之,叙事使得行动者通过行动彰显的“谁”获得认同,因此,它在行动者主体构建自身的过程中至为关键。
随后,认同的叙事化在利科那里被确立为一个主题,得到进一步的阐述。1985年,利科在其代表作《时间与叙事》第三卷的结尾,正式提出“叙事认同”概念。1988年,利科在《精神》杂志上发表了《叙事认同》一文,导论性地介绍了叙事认同的基本内容。1990年,利科又在其著作《作为他者的自身》中用两章讨论叙事认同问题,具体而微地阐述了阿伦特所触及的叙事认同观念。
所谓叙事认同,是指“人通过叙事功能的中介获得的那种认同”①Paul Ricoeur, “Narrative Identity,” i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88.。利科指出,他之所以认为叙事在认同上至为关键,无论是个人认同还是共同体认同,乃是基于如下一种直观性的前理解:讲述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的故事,可以使得他们自身更容易得到理解。这是因为,从行动的角度来看,寻找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的认同,就是“通过在时间中铺展各种观点之间的联系,说出谁做了某事、怎么做的”。②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p. 146.在这样的铺展过程中所讲述的故事,建构了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就是人物的叙事认同,即呈现了人物的“谁”。因此,叙事认同首要在于情节的一致性,因为人物的认同正是在与之相关的情节的一致性中凸显出来。情节的一致性,无论是基于发生之事件的叙事重组(历史),还是基于行动之模仿的叙事虚构(小说),都是旨在追求一种和谐,从而使得人物的“谁”得到呈现。因此,情节的运作就是和谐之追求与对种种不和谐因素的承认之间的辩证实践。作为叙事塑型的情节化,则是通过情节运作在这种辩证实践中达到一种不断生成着的形象构成,由此显示叙事的构成功能。在情节化的过程中,叙事所涉及的人物,其形象必然得到呈现,并且与所发生之事或模仿的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即使是行动之模仿,也预设了行动者的存在,他/她“就是在叙事中作出行动的人”③Ibid., p. 143.。由此可见,在叙事中,情节、行动与人物之间彼此构成、相互推动。人物的形象正是在所叙述的故事本身的统一性中获得认同。可以说,没有得到叙述的故事,就不会有某个人物的认同,以至于利科断言:“人物之塑造,就是更多的叙事。”④Ibid., p. 144.这种叙事,无论是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共同体而言,都具有构建作用。实际上,主体正是通过讲述关于自身的故事而构建自身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叙事即认同。
四、结语
认同既是一个恒久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主题。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随着个人主体性的觉醒和多元价值观的传播,无论是个人认同还是共同体认同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毫无疑问,种族、宗教、性别等在今天依然是个人认同和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也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因此,阿伦特绕过通常人们用以确认个人认同以及共同体认同的那些特征而聚焦于行动和叙事,在我们的时代具有显然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陷入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注于消费和生产而忘了行动的结果。由于行动的没落,人们失去了彰显自己之为“谁”的可能性,叙事也缺乏得以展开的资源。相应地,在现代社会中,那些冲击认同、使认同陷入危机的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同因素,而恰恰是叙事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无论是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对于当前的国家认同建构而言,都是需要特别注重的关键维度。如果我们的教科书不能反复叙说、解释那些创建历史的故事,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借由行动之模仿体现、传播所推崇的价值观,那我们就无法促进国家认同的建构,也将使个人认同陷于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