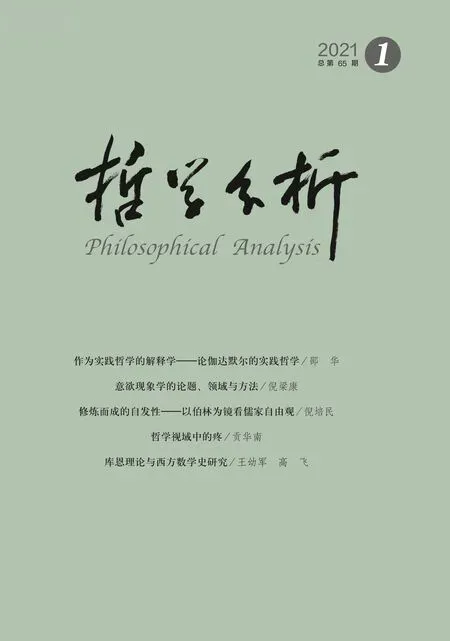修炼而成的自发性
——以伯林为镜看儒家自由观
倪培民
“自由”是启蒙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然而,儒家思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饱受诟病。自由的观念似乎在儒家学说中无一席之地;相反,20世纪以来,儒家学说常常被批评为极端专制和限制个人自由的礼教。儒家提倡维护的传统礼仪不仅要求人们有外在行为的遵从,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12.1),更要求人们“思无邪”,非礼勿思(《论语·为政》2.2)。儒家学说给中国社会制定了一整套等级秩序规范,从个人、家庭、社团到国家层面,无所不包,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曲阜孔庙中有众多历代皇帝所立的碑,其中明宪宗朱见深(1464—1487年在位)所立的“成化碑”最为醒目。碑文 曰: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一日不可无孔子焉。
在这种社会秩序里,“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被看得与天尊地卑一样理所当然,亘古不变。传统本身成了“正确”的代名词。一旦搬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就是天经地义,其他的理由都不需要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偶尔也有个性解放的呼声,但多属于远离庙堂、逍遥方外的山林隐士,属于饮酒邀月、赋诗弹琴的浪漫文人。它们与道家文化有天然的亲近,和儒家传统则似乎鲜有关联。即便从儒家内部出现变革的声音,它们通常也很快就被保守势力压倒。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指出,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浪潮中,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新旧之交的转折点,儒家被视为旧中国一切愚昧和落后的根源,包括政治上的腐败和专制、对妇女的歧视压迫,乃至纳妾、溺婴、文盲等,“自由女神(一个法国的产物)……绝不代表任何中国的或儒家的传统”①参见Wm. Theodore de Bary, 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p. 103—108。。孟德斯鸠说:“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不见任何其他东西。”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3页。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魏特曼(Christina B. Whitman)更尖锐地批评说:“儒家抵制法家,恰恰是因为法家为人们留下了某些自由的空间。以说服教育取代法规的强制不是为了给老百姓背离社会规范留下更多的余地,而是为了取得更普遍的一统天下。”③Christina B. Whitman, “Privacy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Thought”,in Donald J.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5,p. 93.鲁迅先生以讽刺的口吻说,中国的历史是两个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的“一治一 乱”。
但如果我们不是把先秦儒家的思想与后世所有以儒家的名义所行之实混为一谈,即可发现儒家思想与自由的观念并不像上述那么简单。在“自由”被看作现代性之重要标志的今天,如何对待自由这一当代核心价值成了儒学复兴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少人依然坚持儒学与自由价值对立的观念。持自由主义立场者认为,要确立现代性就必须批判和否弃儒家传统,而“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则拒斥西方自由主义,全面否定西方价值,认为儒学的价值正在于它与西方自由观念的对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的主流价值互不相容。今天,持这两个极端的还是大有人在,但更多的学者都认为事实并非那么极端,儒家思想与自由观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张君劢、徐复观,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狄百瑞等,都曾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发掘自由思想的因素。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不同而可兼容。如吴根友指出,许多有关论述的“一个隐性前提大体上都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为标准,然后在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与此标准相近似的思想内容,从而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找到合理性的证明。”①吴根友:《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儒家仁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可能性》,载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8页。吴根友将这种把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当作“取舍儒家仁学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唯一尺度”的取向称作“文化比较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他提出,应当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可通约性”放在两者都共同认可的“人道主义”层次,把儒家的仁学和自由主义看作“具有不同精神气质的人道主义”②同上书,第363页。。这个观点拒绝把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当作现代性的唯一标志,虽然它并不否认个性自由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陈少明也提出,儒家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但它们不必相互排斥。“自由无须借助儒学伸张,反过来,儒学也不必依靠自由拯救。儒学有自己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仁爱。”③陈少明:《儒学与自由—— 一个仍然有待商讨的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当然,既然两者可以兼容,则原则上双方可以互相借鉴和吸收。以“自由儒学”为口号的青年学者郭萍明确地提出,要将现代自由观念接纳到儒学系统中来,“以民族性的话语来表达现代自由的价值诉求”④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版,后记。。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明确儒学对自由本身的态度。儒学的复兴要求我们对“自由”的含义作出深入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儒家思想当中有没有自由观念,儒家思想能够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自由观念,以及儒家思想能否为自由观念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作为消极自由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自由”这个概念似乎十分简单,它无非是指不受约束的状态。其实不然。我们说一个关在牢房里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他受牢房的约束而无法逃脱。但是我们不会说一个弃之荒野的物件是自由的,即便它不受任何外来的约束。这里的区别在于关在牢房里的囚犯是能作出决断和自主行为的人,而物件则没有掌控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借用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和“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这个概念框架来解释上述例子。①其实在伯林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如T. H. Green, “Lectures on Liberal Legisla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in Paul Harris and John Morrow (eds.),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4—212。“消极自由” 也被称为“无约束的自由” (freedom from),指的是没有外来的限制和强制。 “积极自由” 也称为“能动式自由”(freedom to),指的是掌控自己行动的能力。根据这个区别,一个关在牢房里的囚犯虽然不具备消极自由(他无法逃脱),但他仍具有积极自由(他至少可以掌控自己是不是试图去逃脱)。而且他的积极自由正是构成其消极不自由的条件——正因为他可以有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是不是按照其意愿来行动,才决定了他在消极的意义上是不自由的,即他的行为客观上受到了外在的限制而无法成功。而一个物件缺乏的是积极自由,虽然它可以有消极的自由。
尽管伯林对这两种自由的区分本身并不是十分清楚,因为它们相互交集,有时似乎可以说就是同一个自由的正反两面,②如邓晓芒说:“就连伯林自己也觉察到”他对“积极自由”的阐述“怎么看都像是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的阐述”,所以伯林说:“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而已”。(《伯林自由观批判》,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五期,第21页。)麦卡勒姆(Gerald MacCallum)说,自由总是牵涉到一个由于能够免于某种约束(free from something)而能够能动地去做某件事情(free to do something)的能力。(Gerald MacCallum,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in Liberty, David Miller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0—122.)而且如有些学者所怀疑的,它似乎并未涵括自由的所有内容,③参见Quentin Skinner,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in Liberty, pp. 183—205;Philip Pettit, 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17—27;“Republican Political Theory”,in Political Theory, Andrew Vincen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2—131。这个概念框架还是受到了非常广泛的接受,被看作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面旗帜。而且毕竟有无自控能力和有无外在限制至少是看待自由的两个不同角度。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概念框架来理清儒家自由观及其与伯林所代表的那种当代自由主义的异同。
伯林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其目的是要强调消极自由,即个人不受干扰和强制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儒家其实也有非常相似的说法。比如《论语》中记载,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回答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5.12)这里子贡的话就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观念。历代注家多将子贡的话看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表述。其实它们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比“己所欲施于人”显示了更多的对他人的尊重,因为它包含了“不加诸人”的含义,但它还没有完整地体现消极自由的观念。“己所不欲”还是具体的个人之所不欲,尚未脱离个体的特殊性,而子贡的话是总体的“不欲人之加诸我”,不管加诸我的东西是我所欲的还是我所不欲的。这就更具普遍性了,因而与消极自由的观念更加接近。
有意思的是,孔子对子贡的回应,“非尔所及也”,显示出他不是将这种消极自由看作个人的权利,而是看作一种需要获取的成就。康有为解释说:“子贡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①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页。这里的“自立”,实际上是“不欲人立我”的含义。康有为认为:“子贡尝闻天道自立自由之学,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欲推行于天下。孔子以生当据乱,世尚幼稚,道虽极美,而行之太早,则如幼童无保傅,易滋流弊,须待进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今去此时世甚远,非子贡所及见也。盖极赞美子贡所创之学派,而惜未至其时也。”②同上。无论孔子的“非尔所及”指的是子贡本人尚做不到无需别人“保傅”,还是指整个“天下”尚达不到人人都能自立而无需保傅,作为一种理想,都是指人之达到自立或成熟的成就。③康有为甚至认为,子贡此说经田子方而传给庄子,是庄子思想的来源。
康有为的这个解读并非简单地把近代西方的消极自由观加诸孔子,而是揭示了孔子的功夫视角,即把人和社会都看作具有发展过程,需要经过修炼而走向成熟完美的。他把“不欲人之加诸我”看作一种成熟状态。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中的广大民众,都只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以后,才可以无需别人的干预而能够自立。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不一样,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把消极自由看作超越于个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或者说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个人和社会的绝对价值,是一种人人皆应享受的权利,而不是经过修炼而获得的成就。
程颐和朱熹对这段话的解释虽然与康有为有别,但他们的解读也还是功夫解读。他们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勿”是“禁止之谓”,换句话说是规范性的原则,而子贡所欲达到的“无加诸人”中的“无”是“自然而然”的境界,是“仁”。孔子认为子贡还没有达到能够“无加诸人”的高度,还需要从“恕”开始做起。①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8—79页。与康有为的解读不同,程朱把“无加诸人”看作是一个高功夫的境界,而康有为是把“无需人加诸己”看作是高功夫的境界。但是两者都是功夫修炼的成就,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
与子贡的话相比,《论语》里那句著名的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更能表现儒家自由观“为仁由己”(《论语·颜渊》 12.1)的特点。此语虽短,其中的含意却非常丰富,而且与自由这一主题直接相关。
首先,“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被看作表达了“消极自由”的状态。显然,此语不是说到了七十岁,所有的人都对孔子开绿灯、不加限制,让他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三个字显示了“矩”的存在,因此不是伯林所说的无外在限制的消极自由。但是,经过长年的修养,孔子的心已经不会有不恰当的欲望,因此那些曾经对孔子来说是限制的矩已不再是限制了,因而也是没有外来强制的状态。对于一个不想抢银行的人来说,银行里的监控摄像不是约束。对于一个没有想超速的驾驶员来说,公路上的时速限制不是约束。对于一个不抽烟的人而言,公共场合“禁止抽烟”的标示也不是约束。只有当人们有逾越它们的意愿,而外在的规范限制其意愿的实现时,它们才有约束的意义。
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享受着许多消极自由,只是我们把那些自由都看作理所当然,因此也就完全不当回事。比如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允许以虐待儿童取乐,而一个正常的人也不会有这样的欲望,因此,所有正常的人都享受着不受到“不准虐待儿童”这一道德原则(矩)约束的自由,因为这样的原则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约束的意义。一个人欲望越多,外在的限制也就越多。只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欲望其实相当有限,许多限制对一般人而言也就无所谓是限制了。
当代自由主义也并不主张无条件地取消对个人的所有限制。一个对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社会对人的限制的“底线”也是随历史发展而进化的。越是文明的社会,各种规则规范也就越多。在医院、电梯之类的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在影院剧场禁止大声喧哗,在各种大小公路上禁止超速超载,都是过去千百年里所从未有过的对自由的限制。这个底线随社会的进步逐渐提高。因此可以说,社会越发展,人也越受限制。但同时这些也都是自由的升华——因为它们给予人们呼吸清洁空气的自由、安静地欣赏演出的自由、安全行车的自由。但是随着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那些新的限制也就相应地不成其为限制了。一个文明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不能随地吐痰,不能随意闯红灯,或者不能在影院剧场里大声说话而感到不自由。自由不只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除了多一点或少一点自由,还有高级与低级自由的区分。限制随地吐痰的低级自由,同时是提供干净卫生的活动场所的高级自由。一个对不文明行为毫无限制的国度可以在许多地方比文明发达的国家更“自由”,但那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政府对商品质量的监管,对最低工资、劳工福利的规定等对自由的限制,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这种进步其实也意味着更广泛和更高级的自由的落实。
上述获得自由的途径,体现了功夫自由观的核心,即通往自由的途径常常是由接受一些“矩”的限制开始,通过修炼而使“矩”不但不再成为限制,而且成为自由发挥的条件。儒家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1.15)“克己复礼”(《论语·颜渊》 12.1)就是如此,其目的是使人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佛教里的“戒”也是如此,其最终目的是让修行者获得脱离苦海的自由。教育体制中的课程要求和考核体制也是如此,其目的最终是为了学生在相应的领域获得自由发挥的能力。如果从一开始就让人完全没有约束地自由发展,他在当下是享受了自由,却会因此而丧失今后长久的、更为广阔的自由。
有人可能质疑,通过修炼而使自己不再有“逾矩”的意愿,或者使“矩”内化成为自己的意愿,是不是指向了一个逻辑的结论,即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他也就完全自由了?伯林就认为,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基督教禁欲主义、康德的“自律”以及“东方圣者的寂静主义”,是通过减损自己的感性需求,通过摆脱欲望,来达到不为外界所限制和强制的自由的。“这不折不扣是一种酸葡萄学说: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由此所获得的抽象的自由“绝非政治自由,而是其反面”。①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酸葡萄”学说指的是虽然葡萄本是甜的,自己也想要吃葡萄,只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以此自我安慰。鲁迅笔下的阿Q,也用“酸葡萄”式的精神胜利法来获得他的“自由”。阿Q这个形象揭示了一种难以救治的深层的自我否定。鲁迅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南腔北调集·漫与》)当代的一些心灵鸡汤式的说教也起着同样的麻痹作用。它们在使人解脱欲望束缚的同时,也消解了有欲望的主体和生活本身。欧洲文艺复兴的积极意义就是人性的解放,摆脱宗教禁锢。当人的合理需求受到外来人为限制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鼓励人们压抑或者减损自己的需求,相反,应该打破和去除那些限制。这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的本意。孔子和孟子都从来没有否定过合理的欲望。儒家对财富的欲望从来都是“取之有道”的态度。“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12);“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6.11),颜回所乐,乐在求道,而不是乐于其贫困。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以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6A:10)这里完全没有说自己得不到的鱼是“酸葡 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确实有吃不得的酸葡萄。这就需要我们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区分何种“欲”与什么“矩”。对于合理的需求和欲望,不但不应该否弃,而且应该予以保护,但是对于非分的欲望,则不能说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合理的“矩”当然应该遵守。对所谓“恋童癖”,即以儿童作为性欲对象的性倾向,即便是天生的,也必须予以禁止。满足这种欲望是对儿童健康的摧残和对其自由发展的侵犯,会对儿童的一生造成不可抹去的负面影响。笼统地把经过修炼,转化欲望而得到的自由称作“酸葡萄学说”,表面上是维护了自由的纯洁性,即自由与欲望的对错无关,但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狭义的自由而牺牲了广义的自由,维护了低级自由而牺牲了高级自由。
儒家的基本经典清楚地反映了儒家获取自由的方式主要是自我的修养,而不是摆脱来自他人的外部约束。《论语》的许多话语可资佐证,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卫灵公》 15.15);“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4.17);“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1.16);“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论语·尧曰》20.1);“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 15.21),等等。《大学》里所展示的儒家“八条目”,其前五项,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展示了这种自我修养的过程,而其后三项,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被看作前五项所导致的自由状态在家、国、天下层面的拓展。
东方哲学的各个主要传统确实都把自我修养作为取得自由的途径。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是“真我是宇宙我”。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获取自由的方式就是去除虚假的自我,即那种把自我认作与世界隔离并与世界对立的实体的观念,而将真我与宇宙看作一体。佛教否认实体自我的存在,认为无论是所谓的真我还是宇宙我,其实质都是“空”。他们相信,苦难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的“执”,是渴望抓住那本来是空的自身。对于佛教徒来说,获取自由本质上就是摆脱这个“自我”的幻念,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到无执。道家主张通过“无为”“日损”“坐忘”“顺物自然而无容私”,以取得“道通为一”的“逍遥游”(自由)。①但中国化了的佛教和道家都反对极端的禁欲。与上述东方传统相比较,儒家是最积极和最具有建设性的。如果说其他三种东方传统都更多地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儒家则更多地强调主体性的构建。如果说这四种东方传统的目标都是“天人合一”,而且都是试图通过自我修养来达到天人合一,那么其他三种传统主要是倾向于通过减损自我从而达到不再有“物”“我”的对立,而儒家传统则更注重将自我从本来与禽兽区别“几希”的状态,构建为大写的人,通过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来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儒家的修身会让我们打消“吃酸葡萄”的欲念,因为有些“葡萄”确实是酸的,吃不得,但它也是让我们获得“吃天鹅肉”的本事,即能够“发而皆中节”。这就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了“积极自由”的概念。
二、作为积极自由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说是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按照伯林的意思,积极自由的关键在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从心所欲”毫无疑问包含“积极自由”的内容。②张佛泉在其《自由与人权》一书中曾以“从心所欲不逾矩”概括孔子所代表的自由观,认为儒家把自由看作人的内在道德生命状态,属于积极自由,和作为外在保护的、作为政治权利的消极自由不同。(张佛泉:《自由与人权》,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16,23—24页。)笔者认为,这种内在与外在、道德与政治的截然区分并不准确。两者的不同是倾向的不同和视角的不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从消极自由的视角去看。相比之下,儒家更为注重内在道德修养。
但其中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其本能所驱动的,则虽然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心所欲”,却还很难算是自由的。当一个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说他“失去了自控能力”。按照康德的观点,自由的“自”是人心中的理性部分,对它而言,人的欲望、情感等等都是外在因素。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来自自己的心理倾向,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自决自断(autonomous),而是在受其心理倾向的决定(heteronomous),因而也就不是自由的了。这种只把理性决断的主体作为自我,而将自己的情感、欲望都作为“他者”的观点,被伯林称为“城堡”式的自我观。住在城堡里的是那纯理性的自由意志,对它而言,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与来自物质世界和社会的各种影响都是外在的,受因果规律控制的。只有纯理性才是主体自身的习性和所有行为原则和指导方针的最终裁决者。①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Barbara Herma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0.
伯林不主张那样的自我观。他的“自我”是包括自己的欲望、情感的,这与他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相关。如果把欲望、情感作为外在的因素,而把理性看作真正的自我,这就为别人代表那个“真我”来限制我的欲望情感敞开了大门。他希望的是对自我欲望、情感的最大保护、最少干扰。但是他又承认,在逻辑上,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的主体概念最终会逼着人接受那理性的“真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最终会导致集权政治。
这里,语言的不同也反映了哲学思想的不同。在英文里,情感和欲望的主体是“heart”,理性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是“mind”,两个概念各自承担不同的功用。而中文的“心”字,则同时既是欲望和情感的主体,也是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所以“心”字不容易导向自我决断的理性那样的核心城堡概念。“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述很清楚地显示“欲”字也同时有欲望和意愿的意思。如果我们借用西方语言来分析的话,可以说这句话蕴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在七十岁以前,孔子的“心”里的心理倾向部分和理智意愿部分还未能完全一致。当头脑(理智意愿)告诉他“矩”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心(情感和欲望)仍想做“矩”以外的事情。因此,他的理智还不能让心牵着去为所欲为。他必须行使大脑的意志去选择正确的道路,以使自己不逾矩。到了七十岁,孔子才达到了心脑的一致,可以信赖他的情感和欲望了,因为他的情感和欲望已经通过修炼而变得不会再想要逾矩。
如果说中文不区分思想意志与心理倾向,缺乏明确的自由意志的概念,是逻辑上的含混不清,那么,它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不容易割裂心脑之间的联系。这或许应当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幸事,甚至是有智慧的洞见。其实像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任何一个系统,如果它是自洽的,就是不完备的,如果它是完备的,就不是自洽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之一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他论证道,自由意志只能是属于物自体的领域,换而言之,它属于信仰的领域,无法成为知识。在服从因果律的现象界,没法有自由,因为凡是在因果链中的事物都是不自由的。不被任何原因决定的第一因没法被理解,却又是构成完整的宇宙观和道德观所不可缺少的。这里的困难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论证来揭示:所谓的自由意志,是作出自主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或者是被更深层的原因决定的,如此则它并不自由;或者它是不被任何原因决定的,如此则它只是随机的发生,而随机发生即意味着不在任何主体的控制范围,因此也没有自由。这样的分析,逻辑上固然是清晰了,但是自为(自由)的世界与受因果律支配的自在世界就被截然割裂了,而且自为的世界就变成了只能信仰而无法理解的世界。为了接受自由意志的观念,从而使我们的体系完备,我们必须接受一个非常奇怪的形上学假设:有那样一个实体,它能够无端肇事,即在毫无原因的情况下肇始行为,而其自己的行为却又不是随机的偶发。
如果我们将积极自由看成对任何倾向的中立,即自由的主体不受自身任何倾向性的制约,那么绝对的积极自由恰恰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一方面要求主体不受任何约束,另一方面,这个要求本身又使主体的决断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受任何知识、品性以及其他成功履行任务所必须的素质的指导,所谓的“理性自我”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抉择。
孔子和其他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不把个人当作那样的中立选择者,也不认为主体可以脱离其品性和素质进行选择。不带倾向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我们假设有完全理性的、不受任何心理倾向影响的人,这人也一定会像那头“布里丹的驴”①布里丹(Jean Buridan)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他曾经写道:如果有两个选项被判断为是等值的,自由意志就没法打破僵局。它唯一能做的是悬置其决断,等待事态发生变化,直至正确的选项变得明确无疑。(Should two courses be judged equal, then the will cannot break the deadlock, all it can do is to suspend judgement until the circumstances change, and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is clear.)后人以调侃的口气把这个观点形象地描述为一头完全理性的驴,在它又饥又渴,却面临一堆干草一桶水的情况下,必然会因为不知道应该先吃草还是先喝水而死于饥渴。,饿死在两堆完全一样的干草之间,因为它找不到去吃一堆草而非另一堆草的理由。也许有人认为“布里丹的驴”是一个例外,因为很少有人会面临两个完全等质等值的选择。但是在任何理性的选择里,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倾向,他如何能找到选择一个目标而非另一个目标的理由呢?即便那两堆干草有区别,那头驴也必须是出于倾向于好的质量才能够选择那堆好的干草,否则他凭什么作此选择而不是相反?可见,倾向性的影响是自主选择不可缺少的依据。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不是一种对心理倾向的中立状态,而是一种修炼而成的自发性,一种无须内心挣扎就自觉自愿地倾向于符合道德规范的状态。这些倾向性包括从孟子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中生发出来的仁义礼智,以及在后天的家庭与社会教育下培养而成的礼节习惯。它们经过修炼可以深植于人心,以至于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可以据此而随心所欲,同时又能“不逾矩”,甚至“发而皆中节”。这种状态无异于道家的“无为”(或“无为而为”)。正如庄子的“庖丁解牛”里那个厨师庖丁能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达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儒家的修养目标也是使一个儒者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进程而进入“游于艺” (《论语·述而》7.6)的自由王国。
这种基于修炼的自发性有别于康德的所谓“绝对自发性”①参见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T. M. Greene and H. H. Hudson (tra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0, p. 45。。康德的绝对自发性是脱离于人的好恶倾向的纯理性自发性。儒家则认为,如果绝对自发性可以算作自由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修炼而成的自发性看作自由的一种状态。在康德的绝对自发性里,纯理性还没有与人的好恶倾向性达到一致,因此面临着被来自好恶的自然力量先决地排斥的可能。在儒家的修炼而成的自发性里,好恶是经过修炼的调整转化的,因此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的力量。它们通过主体的净化和重建从而与人们的道德理性相协调一致,变成了道德理性的化身或体身化了的道德理性。相对于康德的绝对自发性,这种协调使个体的道德行为更完整地出自道德主体自身,而在康德的绝对自发性那里,道德行为仍然随时可能与道德主体相对抗。
此外,如果自由意味着中立,那么主体对他的“选择”和“不作选择”本身也应该采取中立态度,并在这两者之间先中立地进行选择。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还必须对“选择作与不作选择”和“不选择作与不作选择”这两者本身再作出一个选择。这种后退显然是无穷的。结果只能是,除非在某点上他不再选择,否则他就无法作出任何选择!康德的绝对自发性依然是自发性——理性不可能作为无穷尽地上诉自己的终裁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孔子被问及一个人是否要三思而后行时,孔子说:“再,斯可矣” (《论语·公冶长》5.20)。显然,孔子知道过于犹豫不决也是一种约束。正如完全被盲目的冲动所驱使是缺乏积极自由的表现,没有任何倾向性驱使而茫然无所适从,同样是缺乏积极自由的状态。在这两种状况下的自我,都没有真正的自主能力。
儒家经修炼而成的自发性,就是这样的中庸之道。儒家修炼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将自己的选项不断缩小的过程,直到最后凭直觉就能自然地倾向于最好的选项。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确实具有“踢他一脚”的选项存在。这样的选项在存有论意义上是开放的,是他可以选择去做的。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项。他们的头脑里根本不会出现要去踢那孩子的念头。所以这个选项在他们的心里是关闭的、无意义的,根本就不能算是个选项。与一个确实有这样的邪恶意念,因而需要在心里选择不去踢那孩子一脚的人相比,那些无需选择的人是更加自由的。儒家的修炼,就在于将所有不恰当的选项一一从自我的倾向性中排除,以至于最后能无需选择,从心所欲而能不逾矩,甚至“发而皆中节”。他的自由就是他的“自然”。由于经过修炼后的自发倾向性是得到监控其心愿的头脑认可的,所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依然满足了伯林所谓积极自由的条件。有趣的是,在此意义上,儒家的自由可以说是“无需选择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境界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善,并自然地倾向于那样的善,而无需作出选择的那种境界。修炼有层度的深浅。越是修炼得好的人,就越自由;一个人越是自由,就越无需选择。如《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后者还需要付出努力,需要“择善而固执之”,前者则已经无需“择”了。“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就是柯普曼(Joel J. Kupperman)所敏锐地发现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儒家的圣人将没有选择可做,因为各种无价值的行为都已经不再是活的选项。”①Joel J. Kupperman, Learning from Asian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6.
由于在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句话里,此“心”是已经变为心理倾向的规范,陈汉生(Chad Hansen)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成了“描述心理学”,认为它实质上是对圣人的倾向性的描述。陈汉生由此而断定“儒家没有关于自由的学说”②Chad Hansen, “Freedo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Confucian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2,No. 2, 1972, p. 170.。葛瑞汉(A. C. Graham)说,要想在中国文化里寻找与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观念严格对应的观念是天真的。他指出,中文里“自由”相当于“自然”,即“自然而然”的状态。那里没有一个独立的用来限制和调整倾向性的意志。葛瑞汉用“自发性”翻译“自然”的概念,他说:“对于中国的道德哲学来说,所谓善就是最明智的人自发地喜欢的东西。”③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p. 302.
但陈汉生和葛瑞汉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这种自然并不等于失去自控,无法作出选择的状态。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从未出现“自由意志”的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没有关于人的自主和能够选择的观念。确实,如果那样的话就太奇怪了。儒家文献中经常出现“择”的概念。如《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7.22)“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4.1) 《中庸》里的“择善而固执之”,等等。如果把自由意志理解为“择”的能力,那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从头就不缺乏自由意志的观念。中文里没有heart和mind的区分,所以才没有出现仅仅作为自主选择的主体的自由意志概念。
其次,上述陈汉生和葛瑞汉所说的“自然”状态或者“自发性”是修炼有成的圣人达到的境界。在那个境界上,已经无需有“择”,因为圣人已经可以“从心所欲”,自然而然地“不逾矩”了,所以当然没有了能择的主体与他的心理倾向的区分。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缺乏自由意志概念是与其功夫的目标有关,而并不意味着认为所有的人都无需有择,或者说自由对所有的人都是其自然状态。如果承认自由是可以有程度之别的,那么圣人所达到的修炼而成的自发性便是最高的自由。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不自由。
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不一定有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即便有,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碰到两难困境。现实生活中确实经常发生两种善不能兼得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家的圣人不会像布里丹的驴那样饿死在两堆同样好的(或者同样糟糕的)干草之间,因为在饿死与随机选择两堆草之一,显然后者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西方哲学家中其实不乏对此的领悟。笛卡尔就曾把那种纯粹中立的自由称作“最低级的”自由。他写道:“中立,即找不到推动自己倾向于一边而非另一边的理由,是一种最低级的自由。它表示不完美,或者毋宁说是有知识的缺陷,或是某种否定。在我总是清楚地看见真和善的地方,我从不会考虑需要审理或选择的问题。因而,虽然我也许完全地自由,但我永远不会把它的原因归结为中立。”①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Donald A. Cress (trans.),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 81.
笛卡尔认识到了中立自由的缺陷。他主张的自由观也是被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所认同的观念,即自由是对永恒或必然的认识。但是这个自由观也有它的缺陷。郝大维(David L. Hall )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指出,这种“形式主义”概念的问题在于其所谓的真理是对永恒不变的存在的认识,而不是在关系当中变动生成的事物的知识。②David Hall &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97—98.更进一步而言,即便是对于在关系当中变动生成的事物的知识,也还是属于真理认知。用功夫哲学的语言来说,认识了真理还不等于就自动地获得了自由。还需要通过修炼而将知识体身化,成为“体知”了的倾向性或功夫。要获得游泳的自由,仅仅知晓所有的有关游泳的事实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在水中的亲身实践修炼。葛瑞汉就陷入了这样的局限。他认为儒家的圣人就是那些聪明人,而最聪明的人就是那些知道一切相关事实的人。③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 302.这种理解给儒家披上了一层理智主义的色彩。认识相关事实或真理的“智”不但不是儒家圣人或君子的唯一素质,甚至不是其最重要的素质。一个人必须对善有体认、体会,成为具身化了的素质和功夫能力,才是真正知善。圣人境界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以修炼为基础的自发性意义上的自由。一个知道所有相关事实却必须与自己的倾向性作抗争才能不走歪路的人,绝对不是儒家圣人的形象。孔子倡导的六艺包括了礼乐射御书数,其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培养素质,而不是获取知识的。他说过“知者不惑”,但他又加上“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9.29)。从儒家的观点看来,对获得自由而言,人的素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事实的认知。
三、作为自由之条件的功夫能力
回到伯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框架,我们会发现,这个框架当中缺了许多完整的自由观所必须包括的内容。其中最直观也最重要的,是自由的主体所需要的功夫能力。
假设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牢房里的囚犯不仅有自决能力,同时他也没有受到牢房的限制——他本来是可以径直打开牢门走出去的,只是因为他不知道牢门其实没锁,外面也无人看守,所以还呆在牢里。换句话说,这时唯一限制他自由的,是他自己的无知。他算不算是自由的?或者假设这个囚犯不是无知,而是因为极度虚弱,没有体力走出牢房,这时他自由吗?再假设他只要从同牢房的另一囚犯那里买到一个面包就可以有体力走出去,但他身无分文,买不了面包,他是不是自由 的?
伯林指出,我们一般不把智力条件、身体条件、经济条件之类的缺乏看作对自由的限制,尤其是作为“政治自由”的限制(他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政治自由),因为在他的语汇中,消极自由指的仅仅是没有来自人为因素的限制或强制。所以这位囚犯按照伯林的观念并不缺乏消极自由。他也不缺乏积极自由,因为所谓积极自由指的仅仅是其决断来自他自己。伯林也承认,类似我们上面例子中的囚犯那样的情况,无知、体弱、贫穷对他的限制一点也不亚于人为的限制,①参见Isaiah Berlin, Liberty, Henry Hardy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但是为了突出对不受他人(包括政府)强制干扰(即消极自由)的重视,“自由”概念在伯林那里被有意窄化了,以致本来应该纳入自由范围的因素被排斥在外。这么做一方面突出了他所强调的不受干扰和强制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其他可以限制自由的因素的忽视。按照这个消极自由概念,一个象棋大师和一个象棋新手有同样的自由。他们都可以自主地决定每一步棋怎么走。两个人面临的是同样的规则限制,也同样没有遭到任何外来的人为强制。但实际情况是,大师的棋艺功夫使他在棋盘上随心所欲地纵横捭阖、所向披靡,而新手却茫然失措,步步被动受制。从功夫的角度来看,那个大师和新手之间有天差地别的距离,而且这个距离完全可以说是自由程度的区别。那位大师处在一种令新手只能望其项背的自由境界。但是在伯林的语汇中,这位新手会被告知:他是自由的,他下棋的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所以他有消极自由。他也完全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也不缺乏积极自由。同样,在伯林的概念框架里,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和一个亿万富豪,一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和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一个明了善恶的人和一个善恶不分的人,都可以具有同样程度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但在上述例子当中,享受自由所必须的知识条件、身体条件、经济条件和道德素养等都被忽略不计了。
如李晨阳所指出的,在儒家看来,自由不仅仅是能够作出选择的自主能力,而且是能够选择“善”的能力。①参见Chenyang Li,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Freedom”,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64. No. 4, 2014, p. 912。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在儒家看来,自由不仅仅是“择”善的能力,还在于能够实现善的能力,甚至是无需“择”就能够从善为善实现善的能力。
让我们继续设想,前面说到的那个囚犯具备了自由走出牢门的所有条件:牢门没有锁,也没有狱警看守,他也不缺乏知识,不缺乏体力,知道只要伸手拉开牢门他就可以走出去。一句话,走出牢门对他来说很容易就能够做到。但他依然不走,因为他受到的教育告诉他,这样出去是不对的。按照伯林的观念,这个人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限制和强迫;他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也是自由的,因为呆在牢里不出去是他的自我决断。唯一使他不能走向自由天地的,是他自己的价值观。因为这个价值观是他自愿接受的,尽管他的行为有悖于他的真正利益,伯林的概念框架还是会说他具备了充分的自由。
如果他接受的是好的价值观,我们确实不会怀疑他的自由。假设我们的囚犯像苏格拉底那样,认为既然他是被合法的政府依照合法的程序判了他的刑,他就必须服刑,而不能自己逃跑,哪怕他实际上是无罪的。我们或许会对他的决断持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确实不会说他缺乏自由。相反,我们会说他有很高的道德境界,是真正的自主、自律,连出狱的欲望都没法抗拒他的理性自决。这在康德理论里是标准的自由自主境界。但是,如果他所接受的价值观是错的呢?如果那个牢狱是恐怖分子关押人质的地方,这个人质被洗了脑,接受了恐怖分子灌输给他的价值观,认为恐怖分子的事业是神圣的,所以他不应该逃跑。他也是自由的 吗?
伯林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按照伯林的逻辑,应该把价值观的对错和自由严格区分开来。即便这个人质的价值观是错的,但只要是他自主地留在了囚牢里,他的积极自由并不因为其价值观的错误而受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质不缺乏消极自由,也不缺乏积极自由。就其是否离开囚牢这一点而言,伯林可以说是对的,但是伯林的观点所不能包含的是,由于对善的无知,使这个人质丧失了他本来应该具有的免受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的自由,就像一个在初学钢琴时由于被误导而养成坏习惯的人丧失了成为优秀琴师的自由一样。这种自由的条件,在伯林的框架里也是缺席的。
或者,让我们设想,如果有人在一个奴隶不情愿的情况下把他带出牢房,通过教育改变他的观念,帮助他认识到他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其主人的财产,从而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情况又怎样?伯林会 说:
说我为着我自己的好处而被强制——这有时可能是为着我的利益, 而且这的确有可能扩展我的自由的范围; 这是一回事。说如果这是为我好, 那我就没被强制, 因为这是合乎我的意愿的, 我也是自由的……这却完全是另一码事。①参见伯林:《论自由》,第203页。
这“两回事”中的后者,显然是指消极自由。由于我是被强制的,所以即便后面等待我的是符合我意愿的东西,我在消极意义上还是缺乏自由的。那种强制即便会导致我的自由的扩展,但这改变不了当下我被剥夺了自由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伯林是非常正确的。但值得玩味的是前者,即“的确有可能扩展我的自由的范围”中的“自由”,究竟是指什么。它不是指积极自由,因为这里并没有涉及我的意愿受谁控制的事实。只要我自己控制着自己的意愿,我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始终是自由的。或许那“扩展”的自由范围指的还是消极自由的范围,比如那位牢房里的囚犯,虽然在被强制带出牢房这点上是缺乏消极自由的,但一旦出了牢房以后,就摆脱了许多消极自由的限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这也就是说,这种强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剥夺他的自由,当然也不是简单地“给予”他自由,而是兼具两者。但伯林想强调的,依然是对其自由的剥夺,而不是同一个行动也给予了他更多的自由。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某种重要的缺席。
四、作为自由之条件的他者
自由当然涉及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但他者在伯林的自由主义论域里主要是作为自由的限制者而在场的。萨特的一句名言是“他者是地狱”。伯林的消极自由就是指没有来自他者的干扰和强制,其积极自由就是对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尊重。
但是在儒家的论域里,他者却既可以是自由的限制者,也可以成为自由的条件。首先,他者对某些自由的限制可以是另外一些自由的条件。父母对幼童的监护是对幼童自由的限制,但没有那样的限制就不会有幼童健康长大成人后所享受的自由。一个人不可能一出生就完整地具备自主的能力,也不可能一旦具备自主能力,从此就一直处于完全自主的状态。人的一生从婴儿时期完全为盲目的本能驱使开始,到成长到理智的成熟,能够具备充分自主能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即便到了成熟的阶段,人的自主能力也不见得总是处于良好状态。当身体受到疾病的侵扰、生理周期的影响,或其他事故的冲击时,主体的自决能力也会有波动起伏。耄耋之年更是有常见的理智衰退出现。人的一天当中也会有疲惫松懈、精神不够集中,从而发生失手、失口之类的状况。要获得和最大程度地保持主体的良好状况,享受最大程度的自由,就不能仅仅依赖天赋和自我的修炼,还需要他者的帮助。同样,在社会层面上,个人的自由也需要他者的限制作为条件。交通规则是对我开车的限制,但没有那样的限制就不会有在良好的交通秩序里开车的自由。为了我安全行驶的自由,政府甚至规定我必须系安全带。这种“家长制”的交通法规显然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我不系安全带,危及的只是我自己,不造成对他人的威胁,政府凭什么强制我?”这背后的理由,确实与家长对孩子常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这是为你 好!”
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自立而“无需人加诸己”,是功夫的境界。在达到那个境界以前,人的自由通常还需依赖他人的制约和帮助。
有两个条件,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是需要有可供选择的不同道路,二是自由的主体需要具有他所面临的选项的信息。如果一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或者他有若干条路可以走,却只知道一条路,不知有别的路可走,那么此人等于没有走其他路的自由。但这两个条件在孔子那里都从未得到强调。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那“修炼而成的自发性”,不难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具有选项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存有论条件(existential condition)。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真正的(或者说高级的)自由,不是那面临选项的举棋不定,而是达到“无需选择”的自由,即凭借自身的功夫,能够自发地倾向于善。
当然,为此而事先在存有论意义上排除其他不好的选项,也是达到同样效应的方法。为了防止有人不排队入场,可以事先安置栏杆,让人只能顺着栏杆依次入场;为了防止有人吸毒,可以禁止毒品的生产和交易;为了防止有人滥用武器,可以禁止私人拥有枪支。①私人持枪权在美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虽然校园枪击事件频繁发生,但有不少人还是认为,私人拥有枪支的自由应该成为存有论意义上的选项。人们可以通过道德的自觉而不用枪支去犯罪,但是私人需要具有持枪的自由,以便他们受到侵犯的时候可以用以自卫。对于不成熟的儿童,排除外在的不良选项是必要的。人越是成熟,越不需要在存有论意义上去关闭选项,因为对于成熟的人来说,符合基本的行为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己的成熟度就在于他们在心里已经“关闭”了许多选项。哪怕没有栏杆,他们也会依次排队。哪怕没有禁止持枪,他们也不会滥用枪械。但在现实的社会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始终是完全成熟、完全理智、无需他人规范限制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在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或多或少地处于不够理想的状态。因此,即便在最最“自由”的社会里,也会有种种限制自由选项的设置。这些设置剥夺了人“逾矩”的自由,但也提供了人走正道的自由。对儿童无限制地开放所有的自由,是对他们严重的不负责任,无异于剥夺他们健康成长的自由。在一个人能够达到修炼而成的自如阶段之前,他仍然需要被“矩”约束,而这“矩”是导向他达到那自如阶段之所必需。赋予幼儿玩火的自由是愚蠢而危险的。玩火自焚的结果,非死即残。无论死还是残,都是丧失自由。从功夫论的角度看,人的功夫成长有一个过程。在达到一定的成熟水准之前,一个人还不能够理解遵“矩”的理由,所以功夫师傅通常是先让学生按照指导去做,不求甚解。为了防止学生被误导,功夫师傅也会阻止学生接触可能对他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这种指导甚至会是强制的,因为如果不强制,孩子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幼稚而失去享受许多自由的机会。一旦学生达到了一定的修炼水平,就会领悟教师以前为什么要他那样做。像今天的大众媒体中有“儿童不宜”背后的意图一样,如果不让孩子远离某些东西,结果只会是剥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可能。在《论语》中,有三处提到“四十”岁这个年龄阶段:“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2.4);“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9.23);“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17.26)。人在年轻的时候面临各种可能,有许多“自由”,因而“可畏”,说不定会非常出色,当然年轻人因面临各种可能的选项,也会有许多困惑,不知如何是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可能性渐次关闭。如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进入“不惑”的阶段,虽然心里或许还会有“逾矩”的倾向,但已经知道何为正道,能够自控,不会走歪道了。但如果接受了不良影响,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难以改变,没有了希望。同样是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前者是达到了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游于艺”的境界,后者则“其终也已”“朽木不可雕也”,孰自由孰不自由,当不难分辨。
当然,以上的论据都基于这样两个前提,即我们所说的对选项的限制和约束是善的,是最终有利于个人获得更为根本的自由的,而且我们所说的个人是需要那样的限制和约束的。这两点在现实中都不是必然的。对一般意义上理智成熟的(如年满18岁的)个人提供足够的选项(哪怕是对他不好的选项),让他自主决定,在实践上通常比一个强势的政府处处替人决定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来得更加有利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这一点是儒家完全可以接受的。
其次,他者也可以在更加直接的意义上成为个人自由的组成条件或构成成分。不少学者指出,儒家关于人的概念是关系型的,它把每个人都看作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纽结,而不是看作抽象的自主选择的主体。相应地,儒家也认为任何人都只有在这些关系中,并通过这些关系,实现其相应的自由。郝大维和安乐哲写 道:
西方社会理论极力支持个体绝对性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他们很难恰当地摆正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地位而不对自由和自主性的概念作出挑战。传统儒家的情况则相反。儒家明显地倾向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任何试图将个体相关性概念朝着个体绝对性概念的转换,都极大地威胁儒家社会观的建构本身。①Hall &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152.
按照安乐哲和先后与他合作的郝大维、罗思文的观点,儒家不承认有孤立于他者的独立个人,无论这个“他者”是指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同事、领导、社会还是天。一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是他自由的必要条件,正如水是游泳的必要条件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故事的比较来理解关系性与自由的联系。“二战”期间,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一位学生来找萨特征求意见。他告诉萨特自己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无法决定是应当离开法国加入抵抗纳粹的战斗,还是留下来照顾他那饱受战争摧残的年迈母亲。在看似不能同时履行的两个道德责任面前,这个年轻人左右为难,希望萨特能够帮助他作出决定。萨特对这个年轻人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做决定。伦理理论不能帮助他,因为他必须自己选择遵循哪一种理论,并决定在他的特定情况下怎样去诠释那种理论;本能或情感不能帮他作决定,因为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赋予他的情感以价值,而非相反;其他人也不能帮他作决定,因为他必须先选择去求助于谁,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他人提出建议前,他自己或多或少已经知道了他将得到什么样的忠告。所以萨特对那个学生的回答是:“你是自由的,去选择吧;换句话说,去创造吧!”①参见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93, pp. 24—28。通过这个例子,萨特试图说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是孤独的自由存在者。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只能通过自己的一个个选择去“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此意义上,人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着的“无”(nothingness),是成为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可能性。而且一个人每次作出选择以后,他又重新回归为“虚无”,成为新的选择的可能性。他可以坚持过去作出的选择,也可以放弃过去的选择而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由于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作出选择,他必然会感到孤独,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会因为需要不断作出选择而感到焦虑和绝望。作为人,唯一不能选择的是他只能承担起去选择的责任,也就是不断去创造自己。
萨特没有告诉读者那位青年后来怎么样了,但可以想见,面临这种“自由”,他确实会感到孤独、焦虑和绝望。有趣的是,在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堪与萨特的故事相提并论,结果却大异其趣。宋朝名将岳飞本来也会有与萨特那位学生非常相似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作为宋朝的将领,他有责任率军抗击金兵的入侵,但同时作为儿子,他又有责任留在家里照顾其年迈的母亲。然而与萨特的学生不同,他摆脱这个两难困境的办法不是来自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他母亲。岳母坚定地要求他保卫国家,还在他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 四个字来表示她的决心。有了岳母的这一态度,岳飞便不再面临前述的两难困境,因为留在家里已经不再是奉养母亲的孝行,反而成了违背母亲意愿的不孝之举。岳飞所面临的“选择域”已经不再是留在家里尽孝还是率兵抗金尽忠,而是留在家里,既不忠也不孝,或是率兵抗金,既忠且孝。
这两个故事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中国社会与法国社会的不同。从儒家的观点看来,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里,处在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孤独地面对各种选择的“无”。人所面临的“选择域”本身就是受其关系制约,由关系中的各方所共同规定的。正如罗思文所指出 的:
早期儒家认为不存在孤立的抽象自我。我是生活在特定关系中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且,在与这些角色相连的关系里,我与一部分人的关系又直接影响到我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以至于与其说我在“扮演”或“表演”这些角色,不如相反,按照儒家的观点看来,我就是我全部的角色。①Henry Rosemont Jr., A Chinese Mirror, Moral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91, p. 72.
换句话说,儒家观点会认为,像萨特那样把人视为绝对独立的、自我决定的个体的观点有根本的缺陷。无论是岳飞还是萨特的学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岳飞之成为一个孝子和一位民族英雄的事实,都不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没有岳母的参与,他不可能同时成为二者的楷模。岳母没有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消极地站在局外,等候儿子作出决断。岳飞可能面对的两难境地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困境,其解决也是通过人际关系。这个解决的决定因素不是岳飞决定接受母亲的帮助,而是母亲的帮助使他不再有两难困境需要决定。确实,岳飞的母亲也可能不提供帮助,但即使是那样,也不能改变岳飞和岳母都是整个问题域的构成成分,并共同导致了最后结局的诞生。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萨特提到的那位年轻人。这个青年选择去找萨特请教,是把萨特当作一位人生的导师。作为一个老师,萨特的回应不只是简单地给那年轻人提供了信息,而且也是对他采取的行为。萨特不是简单地告诉了那位年轻人他所面临的是孤独的处境,而是参与制造了他的孤独。他本来可以给那年轻人一些更实际的建议和帮助,比如提出不离开法国而参加抵抗纳粹的其他途径,以便同时照料母亲,或者帮助其母亲一起离开法国,甚至组织人一起帮助他照料其母亲,等等。即使经过所有这些努力,问题还在,也将不同于原先没有任何实质帮助的冰冷拒绝,把那年轻人放在孤独无援的境地。
依照儒家的观点,这两个故事的区别在于,在岳飞的故事里,关系中的个体因相互配合而使两难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在萨特的故事里,关系中的个体由于拒绝协作而加深了两难的困境。水可以淹死人(是人在水中的自由的限制),也是人畅游其间(即人在水中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同样,人际关系的处理,也是决定个人在相应的关系中自由与否的关键。脱离了水,就谈不上人在水里的自由,同样,脱离了社会关系,一个人也没法有在社会中的自由。为了在社会里获得自由,一个人必须处理好人际的关系,同时他的自由也取决于环境以及他人如何对待他。这就要求社会为个人的自由提供必要的条件,要求他人的合作,也要求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清醒认识,并将这些关系调节到最佳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12.11)其实也是关于如何获取自由的一种忠告。首先,如杨伯峻诠释的,“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5页。。臣子的自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行为。这绝不仅仅意味着君主放手不干预臣子,给臣子以消极自由的空间;它也意味着君主给予臣子以相应的权力,对其他臣子以相应的约束,以及提供臣子执行其职责所需的其他条件。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指出,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人们以为从此俄罗斯人民可以无需害怕政治迫害,充分享受自由了,但结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囚犯闹事越狱、铁路盗贼横行、士兵街头乞讨、输油管道爆裂、税务官员被杀(仅1996年就有26起)。政府太弱对自由造成的威胁丝毫不逊于政府过于强势而造成的威胁。没有了政府法律权威,债权人的权利就毫无保障。“要保障我们的自由,最好是保护那能够保障我们自由的合法政治权威”②“Russia’s Unhappy Experience Offers Americans a Lesson in the Meaning of Liberty”, The Baltimore Sun, July 4,1997, https://www. baltimoresun. com/news/bs-xpm-1997-07-04-1997185038-story. html, accessed 08/20/2019.。
其次,杨伯峻的诠释没有能够指出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意味着“要把君当作君,把臣当作臣,把父亲当作父亲,把儿子当作儿子”。当一个人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就可能失去作为儿子所能享受的自由(如得到父亲养育的自由)。儒家的道德修养虽然也说“无我”“克己”,但其目标不是被动地接受他者的约束,收敛自我,而是通过调节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增加自己的能量,将他者变成主体得以展示自我并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孟子通过自身的修炼经验发现,这不是简单的为道德信仰献身,因为他能够确切地感受到作为生命力的“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4B:14)孟子甚至认为这样的修炼可以使人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自由听上去相当神秘,但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好的厨师能够将身边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和与他协作的助手都变成自己随心所欲地制作美味佳肴的条件,如果一个好的企业家能够知人善任,灵活运用身边的各种资源,以在商场上如鱼得水,那么推而广之,一个有深厚修养的儒家圣人为什么不能在此意义上使万物都为其所用 呢?
当然,这也是基于两个并不必然的前提,即外部的条件确实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如岳飞的母亲之于岳飞),而个人自身有能力调动周围的人和物来实现自身的自由。这两个前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常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自主权利的保障就会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条件。
五、总结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伯林的框架是为了突出个人不受干扰的权利而创立的一套“简化拳谱”。在这个框架里,真正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即没有来自外部人为干扰限制的权利。他把“freedom”和“liberty”看作同义词,而“liberty”源自拉丁文的“liber”,意为“不受限制的”“解放”。作为自主能力的积极自由,其真正意义也是“不受他者的控制”。而且很明显,伯林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带有明显的警戒口气,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钻牛角尖,把“真正的自我”看作某种绝对理性,就会为专制政治打开大门。
伯林的框架及其所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对于保障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实现个性的解放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它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在这个框架里,消极自由只是作为权利,而不是同时也看作为自立的能力。在这样的概念指导之下,美国的青年人多有一种entitlement的心态,认为自由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却常常发现自己茫然不知该如何去运用这种自由。这样的自由概念把自主能力与其他能力,如知识、体力、经济条件等分开,把后者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似乎与自由无关,这就大大局限了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在这个概念下,他者也只是作为自由的限制者而在场,其作为自由的条件甚至自由的构成成分的作用也就被排除在外了。
相对于伯林的自由观,儒家对从外部保证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消极自由),确实是强调得很少。即便是子贡之“不欲人之加诸于我”及“我亦欲无加诸于人”,也都被看作自己修炼的成就,而不是权利。在这一点上,儒家可以从伯林等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助益。但儒家强调了伯林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忽视的功夫能力及他者对自由的重要意义。在儒家看来,自由不仅依赖别人不加诸我,也依赖我本身之无需别人加诸我。自由不只是人的权利,也更是人所需要经过努力去获取的能力。
儒家的自由观会认为,自由不仅是个或多或少的量的概念,也有或高或低的质的区分;自由不是越多越好,还要看什么样的自由值得拥有。儒家能够同意伯林,对不好的欲的限制仍然是对自由的限制,但会加上一句:限制和去除不好的欲是获得更好的自由之所必须。
伯林认为获取消极自由的途径是打破或取消外来的干预,儒家认为,不合理的限制需要打破,但获得消极自由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自我修炼,使合理的“矩”不再成为限制。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主体是有掌控自己意志与行为能力的自我,因而积极自由观很容易导致与心理倾向割裂的理性自我“堡垒”,儒家积极自由的主体是与心理倾向不可分割并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前者的自我在逻辑上容易导致茫然不知所措的“中立的自由”,导致萨特所说的孤独和绝望,后者指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理智与心理倾向的一致)所显示的修炼而成的自发性。前者将他者看作我的自由的限制,后者指出他者也可以成为我的自由的条件,甚至我的自由的构成本身。
虽然伯林的自由观总体而言因其上述缺失而显得贫乏和苍白,但是它作为框定自由的底线,即自由的最起码的要求,具有很现实的积极意义。它指出了人们可以要求社会提供的基本保护。很显然,这个框架没有包括通过自我修养以获得能力来开拓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也没有包括协同他者而“达己达人”,这些正是儒家自由观念能够对其作出纠正和补充之处。基本的自由可以说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更多更高的自由是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的成就。坚守底线和功夫的升华是互补的。没有基本权利的自由,就没有发展功夫的空间,既有的功夫也会在强制和干扰中窒息,无法施展;没有修炼,作为基本权利的自由是盲目的,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