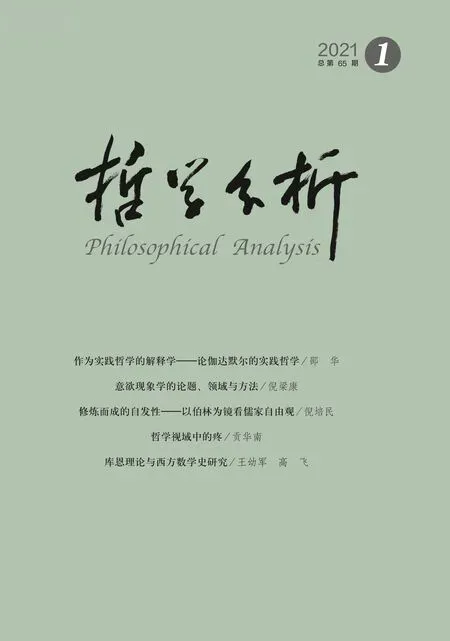库恩理论与西方数学史研究
王幼军 高 飞
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以下简称为《结构》)①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1962;2nd edition,1970. 中译本: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哲学理论,其中构建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以及科学革命的思想方法立刻在众多领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对于科学史界而言,其理论的魅力主要缘于两点:一是库恩所描绘的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的科学革命模式,这个模式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历史并不是一个科学事实不断累积增加的单一过程,而是充斥着因危机而导致的革命阶段,也就是新旧范式的转换,这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二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强烈的“反辉格史观”,库恩在该书引言中明确提出反对贯穿于20世纪科学教育中的以进步为主线的科学观,他倡导从历史中认识科学的本质,呼吁摒弃不足以反映科学真实历史的辉格史观。①Joan L. Richards,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L’esprithumai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Osiris, Vol. 10,1995,pp. 122—135.库恩理论及其所蕴含的崭新观念为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丰富性打开了大门,对科学史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库恩在《结构》中只是把革命模式的适用性限制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他未将数学纳入其革命理论的探讨之中,至于该理论对数学发展的适用性或有效性,他似乎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不过,鉴于其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巨大启发性,库恩理论也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数学史家的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该理论与数学史之关系及一些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以后的数学编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库恩理论究竟对该领域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在学界还鲜有人专门研究的问题。有感于此,本文将基于编史学的视角,遵循历史研究进路,聚焦于对近代西方数学史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和案例的分析评论,探讨库恩理论与西方数学史研究之关系的总体脉络。本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概述18世纪以来西方数学编史传统的形成,再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库恩理论对数学史适用性的争论进行辨析,最后探讨库恩理论对现代西方数学史研究转向和实践的具体影响。
一、西方数学史研究传统溯源
数学编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而数学史作为一门专业研究则兴起于18世纪初。当时,近代数学本身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于其他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数学及数学家的声誉和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这种状况激发了人们对收集和整理数学史料的重视。由于数学家在研究中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重复或使用他人的成果,因此,将荣誉归于应得之人成为数学历史的首要目标①德国数学史家施奈德(I. Schneider)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数学史研究的缘起与18世纪初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现的优先权争论有关,参见Ivo Schneide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ims,Results,and Future Prospects”, in S. S. Demidov, et al. (eds.), Amphora, Basel:Birkhäuser, 1992, pp. 619—629。;由此决定了早期数学史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史料的收集、编撰和整理,尤其注重描述相关数学知识是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做出的以及怎样做出的,强调记录编年细节以及刻画相关主题的概览。这种编年史风格在18世纪的英国数学家蒙特莫特(Pierre Rémond De Montmort)那里已初露端倪。蒙特莫特本人在其数学生涯中也曾深陷与德莫弗(Abraham De Moivre)关于概率问题优先权的争论。他在后期完全致力于数学历史的编撰。他认为,每一门科学、艺术和工艺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不仅可以将发现的优先权公平地归属于发现者,而且也有益于理解人类思想的整体进步历程;在所有的历史中,数学史是人类心智进步的最佳代表,因为数学是上帝在其造物中赋予人类优越地位的最好展示。蒙特莫特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完成一部古今数学通史。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他的数学史草稿也遗失殆尽,所幸他的数学史观在18世纪蒙图克拉(J. E. Montucla)的著作中有所体现。②Joan L. Richards, “Historical Mathematics in the French Eighteenth Century”,Isis, Vol. 97, 2006, pp. 700—713.
为数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细节进行详细记录的历史撰述风格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数学家达朗贝尔(J. R. d’Alembert)、拉格朗日(J. L. Lagrange)等人的推动之下,赋予数学史的崇高使命得以进一步加强——将数学事实的增加与人类的理性精神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联系起来。对拉格朗日和达朗贝尔来说,几何学(数学)是唯一具有严格确定性的知识:数学是人类所有知识的典范,它对人具有教化功能,这种作用在数学家身上被鲜明地体现出来。数学家,只有数学家,才能够实现理性的自主,才能体现人性中善的本质;接受过数学教育的民众将是开明的民众,进而“整个国家和民族将会受益于这种精神所迸发的光芒”。所以,伟大的数学家应该被铭记,作为展现人类心智、洞察力乃至文明不断进步历程的数学历史是值得研究的。③Judith N. Shklar, “Jean d’Alember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2,1981, pp. 643—664.这种数学史观在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著作中、在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决定论世界观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即人类的认知会逐渐地趋向真理的极限、接近真理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将人类所有智力活动领域数学化的过程。这种启蒙色彩的数学观和数学史观在蒙图克拉的第一部系统的数学史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①Jean-Etienne Montucla, 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2 Vols., 1758; 2nd edition 4 Vols., Paris: Agasse, 1799—1802.
蒙图克拉的鸿篇巨制《数学史》堪称启蒙运动的杰出贡献之一,该著作在精神上与当时的百科全书学派,尤其是与达朗贝尔和拉格朗日所倡导的思想紧密契合。蒙图克拉用来构建从古代到18世纪的宏大数学叙事的基本概念是“进步”,即数学史是一个人类理解力不断增长的线性发展的故事。“在所有科学中,数学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是最可靠、最持久的……它的发展从来没有被令人尊严蒙羞的挫败所打断,而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却比比皆是。”蒙图克拉将这种进步观念与乐观精神融入到数学史的写作中。他收集和审视了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料,所涉足的历史空间空前广阔:从古老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甚至是东方的中国,直到18世纪末的所有数学分支,包括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实用仪器的发明等。蒙图克拉对于数学史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关于数学编史方法、研究理念和目标等被后世的数学史研究者所继承。他本人试图完成一项宏大的计划:全面和精确地理解各个时代丰富而复杂的数学,为从古至今的数学描绘出一幅不断增长和进步的完整画卷,但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这项未竟的事业成为以后近两个世纪中的数学史研究者竞相努力的目标:尽可能完整和细致地描绘出数学知识向现代的数学体系不断进步的历程。这种数学史观成为了激发后世数学史研究的主要动力,也为以后相当长时期的数学史研究奠定了基调。
19世纪以来,数学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数学的发展史是真理事实不断增加累积的过程,这种数学编史观一直在数学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德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赫尔曼·汉克尔(Hermann Hankel)用一段形象化的语言将之描述出来,他说:“在大多数的学科里,一代人的建筑为下一代人所摧毁,一个人的创造被另一个人所破坏。唯独数学,每一代人都在古老的数学大厦上添加一层楼。”②H. Hankel,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Antrittsvorlesung, Tübingen, 1871, S. 25.这种信念的体现是内在主义的编史传统一直作为19世纪以来数学史研究的主流进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传统通过“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努力得以延续和加强。内史传统主导的结果是强化了数学史和数学学科的自然联盟③Philip Kitcher and William Aspra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 Brief and Biased History”, in Aspray and Kitcher(ed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Mathema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pp. 20—31.。长期以来,活跃在数学史研究领域的人主要是受过大量数学专业训练的人,包括一些数学家或者欣赏数学史的教育价值的人;前者的工作集中于数学各学科的主题历史,旨在收集不同时期的重要数学人物和事件的材料,并将之整理并置于一幅不断扩展壮大的图景之中。19世纪末期英国数学家托特亨特(I. Todhunter)、德国的康托尔(M. Cantor)和克莱因(F. Klein)等人的数学史著作是这种进路的典型代表。对于欣赏数学史教育价值的后者而言,代表着人类理性进步历程的数学史,可以成为吸引学生以及公众喜欢和理解数学的有效工具。这种认识促使了大量以教学和普及为目的的通俗数学史书籍和文章的产生:史密斯(David Eugene Smith)的《数学史》 (1906)是第一部提供这类材料的著作①David Eugene Smith, History of Modern Mathematics,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06.,其后,大量诸如贝尔(E. T.Bell)、博耶(K. Boyer)、卡约黎(F. Cajori)、伊夫斯(H. Eves)等人所著的数学通史皆承载着教育的使命。
至20世纪中期,西方数学史已在自己的一套编史体系和传统中运行了近两百年,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是引人注目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学史研究趋向发生了一些明确的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和反思其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比如,视野的狭隘性,方法的单一性,认识论上对数学和历史本质的理解以及研究主体的封闭性,等等。导致这种转向的因素众多,其中与20世纪中期兴起的反叛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不无关系;而库恩理论是这种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其影响最为彰显。
二、库恩理论应用于数学史研究的争论
相比于科学史领域,数学史界对于库恩理论的反应可以说是姗姗来迟。不过,至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问题还是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数学中是否发生过革命?基于上述所描述的数学编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数学观以及数学发展的图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数学知识的确定性以及数学结构的逻辑架构等本质特点就排除了库恩理论中最基本的部分——革命;数学在逻辑上是相容的,其变化必然是由一个个被证明的事实累积而成的,因此,库恩式的革命不仅在实际上不会发生,而且在原则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对数学的本质及其发展模式的传统认识由美国圣母大学的迈克尔·克罗(M. J. Crowe)教授在一篇关于数学的本质和数学革命问题的文章中明确地表述出来。
1974年8月,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举行的现代数学发展研讨会上,克罗提交了一篇题为《数学史变化模式的十条定律》的论文①该文随后在Historia Mathematica上发表。Michael J. Crowe,“ Ten‘ laws’ Concerning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Historia Mathematica,Vol. 2, 1975, pp. 161—166.,其中的第十条定律是:“数学从未发生过革命……”他解释道:“我对革命的否认是建立在对‘革命’的某种限制性定义的基础上的,在我看来,这种定义包含了这样一种规定,即抛弃或推翻数学中一个以前被接受的实体。”库恩的革命意味着旧的范式必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旧理论的某些部分在新范式中被视为不可通约、难以解释甚至是错误的。但数学的断言不同于科学的断言,数学定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真理的永恒性”,一个数学命题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性了。数学定理是从公理出发,运用纯逻辑的方法,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证明。随着数学学科的扩展,即使某些数学定理甚至某个数学分支的地位或重要性可能会发生改变,或许被新的研究趋势边缘化,但永远不会被抛弃或推翻,古老的定理永远不会消失。克罗认识到,数学中可能存在某些被抛弃的部分,但这种革命只会发生在数学符号、术语、方法论甚至其历史中,但不会发生在数学本体上;例如,非欧几何“确实导致了数学本质观的革命性变化,即数学哲学的革命,但不是数学本身的革命”②Ibid.。旧的内容(如欧式几何)以不同的方式保持着有效性,而新的内容只是与之并立共存。
克罗的这篇会议论文在数学史界激发了一场关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数学史适用性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立刻引来了两位数学史家的回应,最先给予回应的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约瑟夫·道本(J. W. Dauben)教授,在1974年8月举行的美国科学史学会年会上,道本在会议报告论文中给出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数学中发生过革命。③该文于1984年被收录于一个文集中:Joseph Dauben,“Conceptual Revolu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in E. Mendelsohn (ed.),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Scienc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p. 81—103。道本认为,对于“数学中是否发生过革命”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革命”这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必须对库恩所给出的严格定义进行宽泛化的重新解释,因为“没有理由期待数学这样的纯逻辑演绎的学科也会经历自然科学那样的变革或革命,特别是那种与库恩教授的‘反常—危机—革命’的框架模式相符合的革命”。在对“革命”概念进行改进和拓展中,他借鉴了科恩(I. B. Cohen)所阐释的从18 世纪政治语境中因袭下来的“革命”含义,再结合数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得出数学革命应该具备的以下几点主要特 征:
1.数学中的革命进展并不总是拒绝或否定旧的秩序。
2.新理论的革命性常常表现为因对旧理论框架和约束的突破而极大地扩展了理论范畴。
3.革命性发现的特征还体现在问题解决的能力中,新理论的问题解决能力更完备、更有力、更综合。
4.新发现在初期所遇到的阻力大小可以作为衡量其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基于对数学革命的上述理解,道本认为,数学史中不乏一些革命性的事件①道本对于数学革命含义的进一步解释及案例研究,可参见Joseph Dauben,“Are There Revolutions in Mathematics?”,in Proceeding of Multidisciplinary Symposium of Structures in Mathematical Theories,1990, pp. 205—229。,例如,不可公度量、微积分、非欧几何、集合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都是革命性的发现:它们不只是单纯地增加了数学的知识内容,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看待数学的方式;在每一事件发生后,数学已非比从前。在数学历史上,这些具有革命性的事件总是为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并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和更普遍的结果;在初始阶段,新的发现总是遇到较大的阻力,但会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直至最后,旧的数学再也难以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因此,数学知识即使是渐进累积的,也不表明它不能经历合法化的革命阶段;在这种意义上,渐进累积与革命并不矛盾。
柏林理工大学的赫伯特·梅尔滕斯(H. Mehrtens)教授对克罗的观点也提出了反驳。在1976年发表的《库恩的理论与数学》一文中②Herbert Mehrtens,“Kuhn’s Theories and Mathematics:A Discussion Paper on the‘New Historiography of Mathematics’”,Historia Mathematica, Vol. 3, 1976, pp. 297—320.,他讨论了库恩理论中的“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反常现象”“危机”“革命”等概念在数学史中的适用性,认为由“反常”到“危机”再进一步引发“革命”这种模式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编史学概念,“革命”一词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这个概念针对的是事件前后的权力和机构的合法性,这种隐含的政治类比很难用于数学历史的解释中。他进一步反驳了克罗将实体从形式中分离出来的观点,认为数学史中的有些事件或许可以被冠以“革命”之名,但根本不可能将相关的实体从具体形式中抽离出来。不过,梅尔滕斯补充说,尽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一般模式难以被完全套用在数学上,但其许多概念对数学编史是有借鉴价值的,其中最引起他关注的是“科学共同体”,他认为这个以学者群体为核心的社会学概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为在数学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学视角提供了基础,例如,通过聚焦于“数学共同体”的社会属性,可以将数学家及其群体的社会地位以及数学知识创造的社会维度纳入到数学史中,这有助于阐明数学成就与时代背景的关系。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和理解过去的数学家以及他们的努力和失败,相较于数学史研究中的主流倾向——仅仅根据当代标准去审视和评价过去,可以令人更公正和客观地对待数学的历史。
继道本和梅尔滕斯教授之后,相继有许多数学史家和哲学家加入这场由克罗所引发的争论中。1992年,英国数学哲学和数学史家唐纳德·吉利斯(Donald Gillies)将十几位参与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该议题的文章收载于一本题为《数学中的革命》的文集中①Donald Gillies (ed.), Revolutions in Mathema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这些作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几乎都没有否定在数学发展中存在一些具有“革命性的”发现,比如微积分、非欧几何或抽象代数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革命性变化的出现并未推翻旧的数学,当今学校的数学课本是古老的算术、几何和代数恒久有效性的见证,这些内容早在五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已经被实践过了,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数学学科的普遍基础。那么,数学是如何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呢?什么变化值得称为是革命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人看到了革命而另一些人却看不到,数学革命的体现是什么?数学发展的模式是什么? 等等,参与者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尽管如此,伴随着这场争论的进行,库恩理论对数学史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这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辩论,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学者陆续加入,库恩理论中所蕴含概念的新颖性和启发性以及其理论视野的可拓展性,为数学史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和空间。这预示了数学史研究的丰富性,而《结构》以后的数学史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结构》以后的数学史研究
在《结构》之后,更多学者将争议搁置一旁,致力于将库恩、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融贯于数学史的研究实践中。通过对传统数学史的局限性的反思,数学史领域的面貌得以革新。近半个世纪以来,该领域的基本理念、目标、方法和范畴,以及研究主体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因库恩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呈现出的内涵特质与学术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一) 库恩理论对于现代数学史研究的一个最直接和鲜明的影响是数学编史中对于数学历史图景的重构。这种研究所勾勒的数学发展图景远远突破了以往单调累积的线性发展图景,而这种突破主要是得益于对库恩理论中的一些相关概念(比如:范式或学科基质、革命、科学共同体,等等)的借鉴和拓展研究,这些思想概念为追溯数学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结构和有效载体。以下是沿这一进路所进行的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案例。
库恩理论中最为数学史家所关注和借鉴的一个概念非“革命”莫属。美国数学史家约瑟夫·道本和朱迪思·格拉比内(J. Grabiner)是以此为切入点重构某些数学分支历史的典型代表。两位学者皆基于被赋予新含义的“数学革命”概念,倡导在数学编史中构建革命性的变化图景,以此挑战传统数学史所描绘的过度简单化的图景。道本认为数学的发展可以同时兼具累积性和革命性,他所考察的康托尔(Georg Cantor)集合论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康托尔的工作并没有取代以前的理论,但它确实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增强了先前理论的能力。”①Joseph Dauben,“Conceptual Revolu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wo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Knowledge”,in Donald Gillies (ed.), Revolutions in Mathematics, 1992, pp. 49—71.康托尔在 19 世纪末创立的集合论引发了关于数学基础的广泛讨论,并间接促成了 20 世纪初数理逻辑的发展,进而导致后来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以及图灵(Turing)的理论计算模式的出现。集合论的语言已成为现代数学的基本语言,现代数学的面貌因集合论的出现而发生的变化堪称为革命性的,尽管如此,它并未造成新旧数学的不可通约性,今人仍然在阅读欧几里得或阿基米德的作品。②Joseph Dauben, George Cantor: His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of the Infinit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格拉比内借用了克罗曾提出的一个数学发展比喻模式:“过去的数学世界就像散布着的无数个城堡,它们曾经傲然耸立,也从未受到攻击而被摧毁,但却被当今活跃的数学家们遗弃了。”③Michael J. Crowe, “Ten Misconceptions about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in William Aspray and Philip Kitcher (ed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Mathematics,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1988, pp. 260—277.格拉比内对这个比喻进行了改进,她说,过时的城堡会被遗弃也会被摧毁,不过,原来的材料会被循环利用在新的建筑中,但这些砖块以及将它们粘合在一起的砂浆在新旧建筑中的意义和作用有着根本的差异。同一个形式或概念在不同的结构中有着不同的解释和意义,比如,如果仅仅将2 + 2 = 4或毕达哥拉斯定理看作一些砖块,那么这幅图景可能就是累积的。但是一堆砖并不能显示出建筑的美、秩序或功能,2 + 2 = 4可能永远是正确的,但在不同的时代和群体中,人们对它的解释和理解是不同的,它可能意味着具体的实物(例如水果)聚合,或意味着地图上的距离计算,或只是某个抽象群中的命题。因此她的结论是:“数学并不是一门没有革命的独特科学。相反,数学是人类活动中曾经发生过的破坏性最小但却最具根本性革命的领域。”她据此观点考察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法国的分析数学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其所导致的数学观的剧变,新的数学观对多种数学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她认为这种变化是法国18、19世纪数学发展中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性突破。①Judith V. Grabiner, The Origins of Cauchy’s Rigorous Calculus,Cambridge, MA: MIT Press,1981.
除了“革命”一词,库恩理论中另一被广泛讨论的核心概念是“范式”。在对这一术语的阐发和应用中,中国数学史家曲安京教授的研究视角别具特色。他将“范式”理解为学者共同体所关注的“问题域”,认为一门知识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新旧范式更替的革命模式,而是通过“问题域”的改变或扩张而实现的。基于这种理解,他提出了重构数学史路线图的思想,为此,他选取了在数学史上备受关注的伽罗瓦理论发展史中的两个典型的案例:以拉格朗日的代数方程理论为例,讨论如何根据对原始文献的解读,进行“路线图”重构的研究;然后以分圆方程理论为例,讨论高斯 (C. F. Gauss) 如何在拉格朗日路线图的引导下,构建自己的理论,并提出新的问题,由此理清了高斯理论的问题与方法之来源。②曲安京:《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一条路径——以拉格朗日与高斯的代数方程理论为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12期。
库恩理论中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也被众多的数学史研究者所借鉴。这个概念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个别的数学精英及其成就转移到数学家们所置身的共同体环境上,比如哥廷根、巴黎、柏林和剑桥等数学学派。相关的研究包括这些学派发起和资助特定的研究和培养特定类型的数学家的过程,包括其机构的运作、教育纲领等方面。这些研究业已成为现代数学社会史的主要内容,由此带来了传统数学编史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的变化:数学家本人及其数学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环境乃至社会因素的影响。
(二) 库恩理论中的反辉格史观也导致学界对传统数学观和数学史观的重新审视。近几十年来,在数学编史中这些基本观念的转变及其引发的研究趋势和实践的转向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与数学编史问题的讨论、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多样化、对数学历时性问题的重视等方面。
首先,研究主体对于数学的塑造价值在数学编史中得以强调和体现,数学知识的真理性、数学方法的严格性等方面的历时性愈来愈得到重视。这种趋向最先反映在70年代以来关于数学编史中“内在论者”(internalist)与“外在论者”(externalist)谁有能力书写数学的历史以及应该如何书写数学的历史等问题的辩论中。20世纪初,随着数学日益专业化趋势的发展,数学史研究越来越以数学家为主导。数学家倾向于把数学看作一个独立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知识体系,数学史成为他们塑造自我的工具,他们难以对其他群体的研究感到满意,主要是因为其他学者的知识背景与数学尤其是现代数学的距离。然而,自《结构》出版以来,库恩的反辉格史观促使人们意识到,满足数学家期望的数学史是有选择性的,数学家们倾向于以当代数学观为参照标准去重建过去的数学。1975年,历史学家温古鲁(S.Unguru)对由数学家所主导的数学史研究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Sabetai Unguru,“On the Need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Vol. 15, No. 1, 1975, pp. 67—114.,他认为已有的数学史研究只是用现代数学的符号和概念去解释过去的数学,将现代的数学思想和概念强加于过去的数学之上,例如,他认为在古希腊数学中根本不存在“几何代数”这个概念,它是由当代数学家从现代的代数符号、方法和概念中创造的。温古鲁认为,真正的历史方法应该基于对原始文本的理解去构建其来龙去脉,研究数学史不必要以接受现代数学的训练为先决条件,这种训练反而会成为理解过去的障碍,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具有时代误置的解释。温古鲁呼吁历史学家们对数学史方法论进行彻底的改革,倡导依据历史的、文本的、语言学的和哲学的证据而不是依赖现代数学的直觉展开对数学史的系统研究。温古鲁的呼吁激起了数学家韦伊(A. Weil)的反击,他在1978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一篇报告论文中给出了回应②André Weil,“History of Mathematics: Why and How”, in O. Lehto (ed.),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Helsinki, 1978,pp. 434—442.,该报告的主旨就是为数学家成为数学史研究的主体进行辩护。他认为,数学家是数学史的主要读者群体,为了追溯“后来出现在数学家头脑中的概念和方法的早期渊源”,数学史研究者接受全面的数学训练是必要的,因此数学家兼职作一些历史研究是他们最有回报价值的课题之一。他甚至质疑“数学史是一门介于历史和数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这种定位,认为数学史应隶属于数学学科的一个分支。③关于这场争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见Volker R. Remmert, et al. (eds.), Historiography of Mathematic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ham: Birkhäuser and Springer, 2010, pp. 1—8。
上述“内在论者”与“外在论者”的辩论表明,知识背景迥异的研究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这种争论也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数学史研究开始吸引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近几十年来,诸如数学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史家、社会建构论者、女性主义者等等众多身份迥异的学者参与了数学史研究以及相关著作的撰写,他们从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于文化等多种视角展开对数学史的研究,已促使数学史从一门边界清晰、相对孤立的学科转变为拥有高度开放性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
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的参与使得数学史研究的视域得以极大地拓展,其关注的目标不再单纯地聚焦于历史与数学本身的关系上。数学史研究开始被嵌入到其他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诸如数学与科学、社会、政治和教育等领域的关系、数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哲学和文化语境,等等。研究视域的拓展催生了众多学术专著和成果的涌现,这些成果不仅包括对于传统分支学科的新诠释,而且还包括了以往处于传统研究之外或较少受到关注的应用数学、概率论和统计学等分支的历史研究。①在过去几十年里,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历史研究状况比其他任何数学分支的历史更加具有体现现代数学史研究趋向的典范意义,体现库恩理论对概率统计史研究影响的部分成果收录于L. Kruger, et al. (eds.),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Vol. 1, Ideas in History; Vol. 2, Ideas in the Sciences, Cambridge, MA:MIT Press,1987。
库恩理论促使了对数学史研究的性质、目标和研究主体等方面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而且,库恩所倡导的将文本解读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的新史学方法也影响到了数学史研究。对史学方法论问题的关注使学界意识到了数学史研究单纯依赖数学文本的局限性。一般而言,数学的形式化表述大都将其背后的启发式直觉过程遮蔽了,为了重建缺失的启发式过程,近五十年来,数学史家对更广泛的原始文本和史料进行了挖掘和拓展研究,这些新尝试的成果反映在对许多经典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解释和更加细致的描述方面,艾斯帕瑞(W. Aspray)和基切尔(P. Kitcher)以期间出版的众多人物传记为例对此趋向进行了分析,诸如康斯坦丝·瑞德(C. Reid)所著的《库朗传》 (1976)和托马斯·汉金斯(T. Hankins)的《哈密尔顿传》 (1980)等。这些传记的作者们几乎都认识到全面挖掘和研究原始文献对于理解数学家和数学历史的重要性,比如:数学家之间的通信、未发表的手稿、专业协会的记录,以及与其他相关者的互动信息。这些作者在以现代的概念符号、严谨性、问题含义和学科边界等标准去审视过去的数学时,比其前辈更具有历史敏感性,他们的著作“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数学家思想的微妙且难以捉摸的性质及其思维模式的持续性和复杂性,这种意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数学的刻板印象”①Philip Kitcher and William Aspra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 Brief and Biased History”,in Aspray and Kitcher(ed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Mathema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pp. 20—31.。
四、结语
通过以上聚焦于近代西方数学史研究趋向以及对相关研究案例和成果的评析,可以看到,库恩理论对数学史研究的影响既体现在研究理念和研究目标的抽象层面,也体现在研究主体、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等较为具体的层面;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在20世纪后期西方数学史研究的一些转向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引发当代数学史研究趋向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受到当时西方社会智识氛围、历史或政治语境等纷繁复杂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到次第兴起的反叛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的冲击,而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只是引发这些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着眼于新兴的科学哲学思潮与自然科学史的关系方面,正如已有的大量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哲学框架可以涵盖对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解释。这种判断同样也适用于库恩理论与数学史的关系。尽管如此,对于长期被单一和封闭的阐释模式所束缚的数学史来说,库恩理论对该领域的视阈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革新等方面的借鉴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本文的意图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数学史研究价值的消解与否定。实际上,该领域的传统路径在当今仍然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仍是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路之一。②例如,美国数学家、数学史家M. 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即是一部传统数学编史风格的代表性著作:Morris Kline,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中译本: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张理京、张锦炎、江泽涵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本项研究旨在为数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既有差异也有联系,数学史研究不能完全抛开对相关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考察,数学史研究者若能敏锐地关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关系以及当代科学史研究的趋势,就可以为数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谋求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丰富的成果,使之拥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