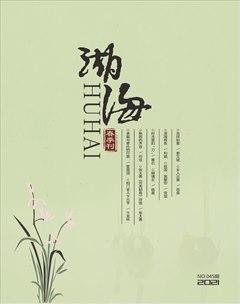蟳埔女(外一篇)
姚晨
凌晨四五点,泉州蟳(xún)埔码头早已是灯火闪烁,人声鼎沸了。
蓝色船舷的闽狮号和闽丰号渔船先后靠上了码头。各色海鲜便顺着滑索不断地降到岸边,几名女子迅速围拢上去,分类、上冰、码放……不一会儿,一溜新鲜鱼档便排放在了海岸。天色放亮的时候,顺着岸线,几十个鱼档已绵延成千米鱼市了,其场面蔚为壮观。
顺着档口走过去,可见各色品种的海鲜。有的档口鱼虾蟹贝,甚至乌贼海鳗和奇形怪状的三角鲎,五花八门玲琅满目。有的档口则专卖各色海鱼。码头上,到处都是头戴花环、身着艳丽服装的女人。她们承担着上货、议价、拖车,清洗打扫,收档等各种活儿。
前天晚上在这儿散步,不时遇见头插花朵的老妪坐在路边兜售零散海鲜,起初60元一斤的大个红蟹一路喊价到15块一斤也没人问津。虽然街区两边的海鲜酒楼是自家的,老公或者儿子也许就是海船上的船老大,但她们依然习惯于在风中吆喝。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使她们历尽幸苦,而这个千年遗留下来的古风早在她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这些身着彩装头戴花环的女子便是蟳埔女了。她们与惠安女、湄洲女并称闽南三大渔女。
泉州市东南的丰泽区有一片唐宋就集聚起来的渔村,千年来一直被唤作蟳埔村。蟳是一种带有大鳌的绛红色浅海螃蟹,应该就是前晚所见老妪叫卖的那种,埔则是闽粤人所说的水边平坦沙地。如今的蟳埔村,大约有7000多居民,不少老人和孩子依旧保留着老传统,住在老村庄,而绝大部分年轻人已经陆续搬进相邻的新型住宅小区。
生猛海鲜和花枝招展的女人们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制冰车队已经驶离,各种小货车、边三轮、摩托车也满载而归,码头只剩一些零星的生意了。喧嚣渐渐消去,蟳埔阿姨和姐妹们也很快就要转回到自家的院落。
姐姐绣珠和妹妹跃卿一边清扫着鱼档,一边等着姐夫过来把剩余的海货拉往菜市场。姐姐绣珠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妹妹跃卿的普通话也带有非常浓厚的闽南腔。聊天很吃力,但10多分钟的交流,还是让我对蟳埔文化有了直接的印象。作为“海丝文化”重要组成的蟳埔习俗共有三件宝:头戴簪花围、身着阔脚裤、住在蚵壳厝。
蟳埔女独特的头饰被称为“簪花围”,她们从幼时起,就将长发盘成海螺状,用淡雅的含笑、白玉兰、柚子花的花苞串成花环,随后点缀上鲜艳的粗康花、素馨花或者绢花,最后再从中横上一根象牙筷。据说,蟳埔村许多居民都是古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虽然已经完全汉化,但女人们依旧保持着这种中亚的装扮风格。
妹妹跃卿介绍说,蟳埔女头戴的鲜花多来自附近的云麓山。山下有一家姓蒲的阿拉伯后裔,种植了一山的各色鲜花。每天清晨,爱花成痴的蟳埔女就赶到村内市集,抢购云麓山中的鲜花。
当然也不一定什么时节什么日子都有鲜花,所以潯埔女的头饰分为生花和熟花两种。生花就是鲜花,娇嫩美艳,往往是小姑娘新媳妇佩戴,熟花则是指手工的绢花绒花,多是在外奔波操劳的阿姨大妈们佩戴。每年三月,妈祖巡香和祭祖的大日子里,蟳埔女会不分老幼,全体戴上生花,每个人头顶都像一片小花园,巡香的队伍便成了一条流动的花海。
天已大亮,姐夫开来一辆满载牡蛎的小货车,三人又齐力将剩余的海鲜搬上车,疾驰而去。我记住了姐妹俩的话,去村里看看她们的蚵壳厝。
村子距离码头不过2公里,传统的民居错落有致。巷弄里随处可见老阿姨坐在屋前娴熟地撬着海蛎,面前是一大盆新鲜的海蛎肉,身后是一堆剥落的牡蛎壳。和我搭话的老阿姨看起来有70多岁了,她16岁嫁到村里时,便头戴鲜花,接续上了蟳埔民俗,最初几年还陪着老公下海,后来就在家里挑海蛎卸海货干家务,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如今还能挑起几十斤重的海蛎。
眼前就是蚵壳厝了。建筑形制同传统的闽南红砖厝(厝,居家民宅)一样,花岗石的墙基,上下红砖砌出门窗内框,与之不同的就是蚵壳(牡蛎壳、蠔壳)的墙表。蟳埔当地有“千年砖,万年蚵”的老话,蚵壳厝冬暖夏凉,墙体坚固。海边多风潮湿,长年累月的风雨将它们洗刷得格外明丽。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过去大部分载满丝绸、瓷器的商船从蟳埔起航,沿着闽南沿海航行到达南洋,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岸。商船卸货返航后,如果是空船,则重心不稳,不利于远航。渔民们就将散落在海边的蚵壳装进船舱作为压舱石,回到泉州就随意堆放在蟳埔海边。
聪明的蟳埔人就地取材,拾起蚵壳拌上海泥筑屋而居,就这样,世世代代的蚵壳厝,无意间成就了一处建筑奇观。
泉州丝路萌起于商周,发展于春秋,定形于秦汉,昌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扬天朝国威,国家依然只许官商,严禁民间出海贸易。随着明末倭寇患甚,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保护海疆的作用,但严重阻碍了海丝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
离开蟳埔,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没有明清海禁,蟳埔,这个海上丝路源头的小渔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香港或者另一个上海呢?而蟳埔女。恐怕早已见不着了。
海蛎煎
牡蛎也叫生蚝,海边人习惯把生长在岸礁上的小个头牡蛎称为海蛎子。我出生在青岛,自然对海蛎子非常熟悉,栈桥边没少过我儿时敲食海蛎子的身影。
上初中时远离了大海,莫伯桑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又勾起了我对海蛎子的回忆。“一位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子撬开了牡蛎,他把牡蛎递给两位先生,他们又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了,蛎壳扔到了海里。”
小時候,家里日用的小金属散件都上缴了国家用于炼钢炼铁,自然少有于勒叔叔的坚硬小刀,撬开海蛎子的家伙只能选择手边已经开壳的大海蛎。海蛎子在平常人家里是上不了餐桌的,它们只能充当孩子们解馋的零食。小家伙吃海蛎子可没有贵妇人那么优雅。撬开一只蛎壳,极其迅速地俯下身子,趴在礁石上,努嘴对准,“嗞”地一声,鲜美的汁液连同蛎肉和散碎的壳渣被一口吞下,全然不去顾忌晚上会肚子疼。
海蛎煎的美味,却是多年以后在厦门的第一次品尝。那年一个初夏的午后,湖里特区的街边树荫下,年轻的我正和朋友用啤酒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这时,一位姑娘提着一只餐盒走了过来,说“刚才路过,见你们就叫了一份空心菜,太抠门了吧,正巧回去没什么事,就做了点小食给你们下酒。”这盒小食便是海蛎煎了。
姑娘名叫萍儿,长着闽南人少有的高挑身材,淡眉杏眼,一条又粗又长的马尾辫尤其惹人。不需过多描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写的就是她了。
当年的我大学尚未毕业,就和几个兄弟姐妹跑去了厦门,与其说是打工,不如说想体验一下经济特区火热的生活。萍儿成了我唯一称为师父的女子。和她相识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其实她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因为年纪相仿,我们之间一直像朋友般相处。她宿舍里几个女孩子都是闽南籍客家人,客家女人的标志性品格就是简朴和勤劳,在她们身上都有最鲜明的体现。女红自然不在话下,衣服破了扣子掉了都是师父们亲自织补,更令我赞叹的是,她们能用最简陋的厨具做出一些极其美味的小海鲜,沙茶鱿鱼仔、姜汁土笋冻、葱花爆花蛤,至今犹在眼前,海蛎煎更是其中最美的滋味。
海蛎煎起源的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当与郑成功抵御荷兰人有关,猜想这不过是想借名人造势,更易于推广流传吧,而我宁愿相信此菜出自后梁闽王王审知的庖厨,毕竟五代十国在唐宋之間,时间更早些,也正值海上丝路鼎盛之时。据说,闽南姑娘们都精于此菜,虽是小食,但海蛎煎在选料、火候和形质的把握上很见功底。而新媳妇的入门考验就是制作一份海蛎煎。如果端出的成品能让老婆婆满意,新媳妇就很容易赢得家中的地位。
晚春初夏,正是韭菜上市海蛎肥美的季节,和上厦门特有的薯粉、酱料,很方便就能做出一份海蛎煎,点缀着两朵火红的木棉,美女师父端入堂上,美色美味,鲜香滑嫩g,吃罢口留余香,实在叫人终生难忘。
此番鹭岛重游,又一次吃上海蛎煎,自然睹物思人。1990年初,在我离开福建时,萍儿曾带我去了她家,在漳州铁路职工宿舍周围转悠,当地特产片仔癀和水仙花完全没有见到。漳州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望不到尽头的铁轨,和铁道边我俩散步的身影。两天后的清晨,萍儿把我送上了返程的火车。挥手的瞬间,定格成了终生的想念。
后来听说她经历过一段坎坷的日子,最终嫁人去了台湾。希望当年的她曾经为老婆婆做出过上等的海蛎煎,祝愿她的一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