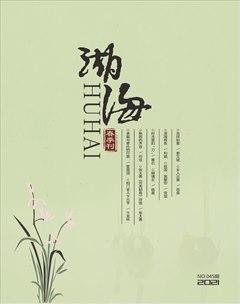乡人云喜
悠泉
云喜在一抔黄土下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后,一辈子的悲乐宠辱、好好歹歹就与他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刚听到云喜离世的消息时,我远没有当初听说云喜得了神经病时的震惊和伤感,反而有些为他高兴——与其疯疯癫癫地活着,整日处在一种自虐式的痛苦与毫无尊严之中,还真不如死了清净。
可年轻时的云喜不仅不是一个疯子,而且还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记得我中学毕业后在村里参加大集体劳动的那会儿,他是二小队的队长,同时还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刚满十八岁的我也就自然成为了云喜手下的一名民兵。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年代,农村的基干民兵也是预备军事主力,每年的冬闲时节和紧要时刻,军事训练和部队一样抓得很紧,我们经常要在大队办公室的院子前面吼吼哈哈地训练步伐、队形与刺杀。那时家家户户都要“深挖洞”,记得当时大队还挑选出了十个精干民兵组成一个班,由云喜带队参加了公社武装部组建的战备团。
云喜文化不高,脸膛黝黑,生就了一副笔直匀称的身材,眉眼俊朗,于不苟言笑的稳重中带着几分儒雅。云喜很爱整洁,一顶黄军帽和一身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虽然他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地训练,却总能保持一身净爽。或许好的容貌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所以他在指挥我们操练时,那些好说好动、喜欢嬉闹的男女民兵都是服服帖帖的,列队、步伐、起卧、投弹、刺杀,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认真。可换成指导员二根就不行了,二根虽然当过几年兵,可他个头矮,又有着向日葵般的一张大脸盘,训练时爱摆个谱,站在队前大话空话讲个没完,时不时地还爱敲打一下这个、挖苦一下那个。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都重,一听他站在前面嘚啵嘚啵个没完,心里就不服气了,大伙儿故意你推我搡、嘻嘻哈哈地气他,他发多大的火都没用。可是云喜一出现,大家马上收敛了,都变得规规矩矩的。云喜在公社的战备团里担任排长一职,除了我们大队的民兵班外,他还领导着另外两个大队的民兵班。云喜往队伍前面一站,玉树临风,号令严正,镇得住场面,公社武裝部长很是器重他,我们脸上也感觉很有光,毕竟我们来自于一个大队。
那时的云喜还没有结婚,理所当然也就成了许多大姑娘暗恋的男人。我和云喜不是一个小队,我是一小队,云喜是二小队。大队学大寨修水库时,决定把一条河的下游河道改造成为高产粮田,当时一小队和二小队合并在一起劳动。记得半晌歇息时,我们一小队的几个姑娘总爱往云喜身边黏,胆大的厚着脸皮逗他,胆小的则用眼睛偷偷瞟他,那些一闪即逝的眼神像是喷着火,热辣辣地灼人。云喜很烦那几个老往自己身边蹭的大姑娘,一次他扬着大嗓门对她们说:别老是急火烧毛地往我跟前蹭,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那一个一个的模样,我是一个都看不上,白送给我再倒贴钱,我也不会要你们。几个大姑娘叽里哇啦地一阵怪叫,都捂着脸噔噔噔地跑开了。
其实云喜那时已经暗地里说好了媳妇,女的是邻近大队的,他们的关系公开后不久,云喜就把她迎娶了回来。娶亲那天,整个大队的年轻人都去吃大锅饭,晚上都去他家闹洞房。云喜的媳妇有着一张月亮般明媚的脸,文静漂亮,听说粗活细活都能做,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原来云喜爹和云喜的老丈人都是石匠,两人经常一起给人修房子,都是不爱吭气的老实人,很对脾气,相互的家庭情况也都知根知底,于是他们在一块摆弄石头时顺便商定好了儿女们的婚事,后来的媒人只是跑了跑腿就成了。虽是父母主婚,可云喜和他媳妇彼此也是互相倾心。云喜媳妇的娘死得早,为了照顾爹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她一直拖到二十六岁才成婚。闹洞房那晚,我们一伙年轻人团结起来都斗不了云喜,我们一动硬茬,他就端起了连长架势,那时我们都是他的兵,他一拿架子黑下脸,我们就犯怵了。加上他不停地散发香烟,不停地往酒桌前推我们,最后是把我们的阵线彻底瓦解了。我们被灌了几杯后晕头胀脑的,于是乖乖地撤了。云喜也因此成为大队里唯一没有被闹洞房的人,他媳妇真是幸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场横扫中华大地的飓风也吹到了我那山旮旯里的故乡,原来一起扎堆劳动的乡亲们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起,在天空迷迷怔怔地飘浮了一阵后,最后七零八落地落在自家房前的山前山后、沟上沟下,农民开始包产到户,以分散的形式侍弄各家的土地和庄稼。
生活渐渐好起来,农村人的眼光也越来越活络,春种秋收大忙季节一过,男的或到国营煤矿打工挣钱,或到城里做生意,女人和老人则在家侍弄庄稼。没过几年,家家户户都买了三轮车或摩托车,渐渐地也都把原来的土墙房翻修成砖瓦房。下煤窑打工的活儿云喜不干,他说那纯粹是剥削,穷死了也不能去干,去干就是犯贱。可是当他看到别人家的日子荣荣光光的,心里又像喝了醋一样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于是就经常一个人嘟嘟嚷嚷地骂:都是他娘的软骨头,挣的钱再多也是臭的。又过了几年,方圆十里有好几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中专走了,就连原来因为儿女多连鞋子都穿不上的贵土,也靠养着一群羊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云喜的三个孩子都只上到初中,两个闺女先后出嫁,二十岁出头的儿子嫌父亲脑筋不转弯一根筋,云喜嫌儿子没骨气,爷俩尿不到一个壶里,一说话就瞪眼,最后儿子一拍屁股离家进城打工去了。云喜越活越不赶趟,他仍旧住在土墙房里,吃喝穿戴哪一样都不如别人,后来自己也觉得撑不住脸面了,在路上走着走着,看见有人来了就远远躲开。他媳妇说他一夜一夜地碾场一样翻过来覆过去地不睡觉,一会嗨一声—会嗨一声,一夜的长气。渐渐云喜就有了不由自主地嘟嘟嚷嚷骂人的毛病。村里的黑蛋先是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做了工头,开业那天请全村人喝酒,还请了乐器班子助兴,黑蛋专门派人来请云喜,云喜去是去了,可他站在酒桌前大喊:大家都别喝酒,这酒这菜有毒。接着便是一通骂骂咧咧,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心里有气,过了一段觉出不对劲了,和他说正事不是驴头不对马嘴就是干脆不接话碴,更让人惊异的是云喜不再躲人了,反而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然后挺胸阔步地往高处一站给大伙“做报告”,嘴里讲的都是天下大事,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精神亢奋,眼光四射。大家终于明白云喜疯了,彻彻底底疯了。
疯了的云喜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怕自己的老婆看不起自己跟别人跑了,因此他死死地看着媳妇,媳妇走到哪他跟到哪。媳妇娘家有事时,媳妇怕他跟去误事、丢人,于是躲开他悄悄走了,他知道后就抹脖子上吊来吓唬在家照顾他的闺女,闺女说出了她妈的去向,云喜立刻随后赶去,并于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搂住媳妇嚎啕大哭,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你不能不要我了、你不能跟人跑了之类的话。云喜媳妇羞得满脸通红,却又只能像哄孩子一样哄他,好一阵子才能把他哄得安静下来。
乡下人遇到这种事首先想到的是中邪了,于是赶紧请人摆治,巫婆、端公烟熏火燎地又唱又跳,鬼没驱走,云喜的病却更重了。医院也去了好几次,在里边住一段时间后情况好了一些,可一回村就又犯病了。
云喜的神经出问题时,我已经从学校改行到政府做了文秘,一次回乡下时正好碰见云喜在给众人“做报告”,他看见我回来,喊着我的名让我过去。看在过去交往的份上,也看在他的生病只能哄的份上,我乖乖走了过去。他突然指着我大声问:我是不是你的连长?我说是。他又问:你是不是我的兵?我说是。他把手指环绕一周后说:你们都是我手下的社员,年轻的都是我的兵,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顺着他说是是是。他越发来了劲,像个指挥员一样亮出当年指挥操练的架势,响亮地喊着口令让我们集合列队。我们做样子站好,他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站姿标准、声音洪亮地喊着:立正,稍息,向左转,齐步走。我看到他的脸因为亢奋而闪着亮光。就是那次回乡看见他后不久,云喜就卧床不起了,病得很重,没几天就丢下媳妇和儿女们走了。听云喜死时在他跟前的人说,云喜临走时对家人没有任何交代,而是一串愤愤不平的骂声。
云喜死后十年,他媳妇也走了,是睡觉“睡死”的,云喜两个闺女都嫁在外地,儿子媳妇孙子都在城里打工,所以家里只他媳妇一人。儿子曾经说过把她带到城里去,可她不愿意,一是过不惯城里的日子,二是想守着云喜的坟墓与老屋。左右邻居都搬家到新农村去了,原来的自然村里只剩云喜媳妇一人。村邻两三天没看见她的人影了,弄开门一看,才发现她早已死在床上。此事还惊动乡派出所来人勘验了现场,后来鉴定是心肌梗塞,睡觉后没再醒来。我听后心里一阵无来由的痛楚,人生无常,一个曾经像女神一样的女人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或许是云喜留下的罪过吧。
令人欣慰的是云喜的儿子生活得不错,他当年和父亲赌气出去打工,最开始一个月才二百元的工资,一年一年地打拼慢慢站住脚,一步一步地升成企业中层领导,并娶妻生子。我去年清明回家给父母烧纸时碰见了他,他也是专程回来给爹娘上坟的。云喜的儿子长得酷似当年的云喜,高高个子,相貌端庄,彬彬有礼。言来语去中看出他见过很多世面,有想法,有心胸,我想他一定还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