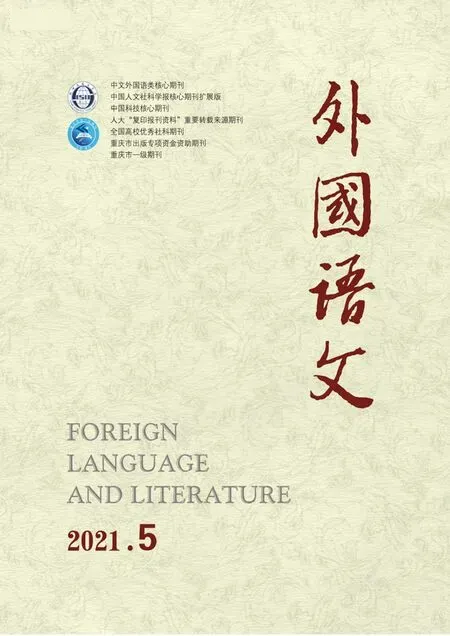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文赋》两英译本比较研究
王洪涛 王海珠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0 引言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所作的《文赋》以赋论文,是中国古典文论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自20世纪中期开始,《文赋》受到西方英语世界的密切关注,至今已诞生了由陈世骧(Shih-hsiang Chen)、修中诚(E. R. Hughes)、方志彤(Achilles Fang)、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黄兆杰(Siu-Kit Wong)、哈米尔(Sam Hamill)、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伯恩斯坦(Tony Barnstone)等人分别译成的八个重要英译本。在这八个译本中,哈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方志彤的译本与香港大学教授黄兆杰的译本别具特色,同时因两位译者对中国古典文论都有精深的研究而值得格外关注:方志彤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留在哈佛任教,讲授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理论等课程,其英译的《文赋》(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于1951年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14期上,后又再版并被多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收录;黄兆杰是牛津大学博士,长期在香港大学执教,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其英译的《文赋》(A Descriptive Poem on Literature)收录于其《中国早期文学批评》(EarlyChineseLiteratureCriticism)一书中,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作序,1983年在香港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方志彤译本与黄兆杰译本特色鲜明,风格各异:方译“语义精准”(程汇涓,2008:53),非常注重原文信息传达的充分性;黄译则旗帜鲜明地以西方汉学、比较文学专业的读者为对象,着力将译文塑成“可读性强的英文(readable English)”(Wong, 1983: xi-xiii),同时体现了译者“中西比较的思维和意识”(刘绍瑾,1998:94)。
目前中国翻译学界对《文赋》英译的研究十分薄弱,对方志彤译本与黄兆杰译本的关注则更少。程汇涓(2008)简析了《文赋》方志彤、黄兆杰、宇文所安及康达维等四个译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王光坚(2010)曾梳理过《文赋》的英译情况,考察了英语世界《文赋》研究的特征与不足,进而指出对《文赋》的英译研究既可为典籍英译提供借鉴意义,又可促进国内对《文赋》的研究走向深入。任增强(2013)简要综述了《文赋》在美国的接受与阐释情况,指出《文赋》英译的渐次出现有力推动了美国学界对陆机文学思想的阐发与探究。李凤琼(2016)分析了方志彤《文赋》英译本的大体特点,考察了方志彤与麦克雷什之间的互动以及麦克雷什对《文赋》的评论,认为麦克雷什通过阅读方译《文赋》在东方诗学中为西方诗学找到了呼应与支持。陈笑芳(2018)简述了陈世骧、修中诚与方志彤对《文赋》的译介情况及其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以上的少数研究成果简要分析了《文赋》在西方英译的大体特点,概述了《文赋》现有英译本的基本情况,但现有研究内容零散,多囿于事实堆砌,难以深入,未能剖析《文赋》各英译本在语言风格上的不同特点,也未能揭示《文赋》各英译本不同语言风格的具体成因。
鉴于此,本文选取《文赋》众多英译本中特色鲜明的方志彤译本和黄兆杰译本为具体的考察对象,以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为依托,对其进行深入的描写性、解释性比较分析,以考察方志彤与黄兆杰两位译者在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影响与制约下在翻译策略上作出的不同选择,并着重分析由此产生的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上所形成的不同特点,进而揭示两种风格译本的产生过程与形成原理,以期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译本描写与批评研究有所启发,同时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有所借鉴。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图里认为“规范”并非绝对的“客观法则”,也非纯粹主观的“个人风格”(Toury,1995:54;2012:65),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行为指南”:“从社会群体共有的普遍价值观或各种观念(亦即何为对与错,何为恰当与不当)转化而成的行为指南,这些行为指南切合且适用于特定的场景,明确告诉人们就某一行为而言,哪些是规定的或禁止的,哪些是可以容忍的或允许的。”(Toury,1995:54-55;2012:63)
图里明确指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Toury,1995:56;2012:61),进而将制约翻译活动的规范划分为三种类型:“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初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问题:前者包括影响文本类型或特定文本选择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是否为转译。初始规范与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等问题有关。图里指出,如果译者遵循源语规范,其译文就会呈现出“充分性”特征;相反,如果译者遵循译语原则,则其译文会呈现出“可接受性”特征(Toury, 1995:56-57)。操作规范指影响、制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和具体翻译行为的规范,包括决定译本完整性与实际布局特征的“矩阵规范”(matricial norm)以及影响译本语言与语篇等微观层面特征的“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Toury, 1995:58-59)。在图里看来,上述三种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先后顺序:预备规范在时间和逻辑上较之操作规范更早介入翻译活动(Toury, 1995:59),而初始规范作为一种“解释工具”也优先于其他具体的规范对翻译行为产生影响(Toury, 1995:57)。因此,预备规范最先介入翻译活动(王运鸿,2013:11),初始规范与预备规范二者先于操作规范在宏观层面上制约翻译行为,同时初始规范所形成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倾向又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抉择,而操作规范则在文本、语言等微观层面上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影响。
翻译规范本身无法进行直接观察,因此在翻译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重建。翻译规范的重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来自文本本身,即通过翻译文本本身来重建所有类型的规范,亦可通过文本分析库来重建各种预备规范;另一种来自文本外部,即通过半理论或具有批评性质的阐述,来进行重建规范(Toury, 1995:65;2012:87-88)。
近年来,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理论得到了翻译学界的持续关注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谢芙娜(Schäffner,1999:1)认为,在过去50年间众多的翻译研究核心概念之中,唯有规范概念一直以来被以不同方式拿来运用,其价值既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又引起了热议。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核心理论,翻译规范理论“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狭隘、绝对的弊端”(王运鸿,2013:11),引领翻译理论从静态的规约走向了动态的描写与阐释,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因为如此,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依托,对方志彤和黄兆杰英译的《文赋》两种译本进行描写性、阐释性的比较分析。
2 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文赋》两英译本的比较分析
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方志彤与黄兆杰的《文赋》“翻译文本”及相关的“副文本”和“元文本”(廖七一,2009:97-98)进行宏观、微观比较分析,会发现两位译者在预备规范制约下在文本选择上各有异同,在初始规范制约下表现出不同的翻译倾向,而在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由此使得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文本特征。
2.1 预备规范制约下方译与黄译的文本选择
图里的预备规范主要涉及翻译政策与翻译的直接性两个方面。方志彤与黄兆杰均将《文赋》直接从汉语译成英语,因此两者在翻译的直接性上并无差异。至于翻译政策对方译与黄译的制约与影响,则是异中有同。在图里看来,“翻译政策是指决定选择哪些文本类型甚或哪些具体文本在特定时间输入特定文化或语言的那些因素”(Toury,2012:82)。对于《文赋》的两个译本来说,对其产生影响的翻译政策既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包括微观的文学与诗学因素。
就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而言,方志彤英译《文赋》恰逢美国大力支持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翻译的有利时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的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开始设立资助项目,支持各大学教授日本和中国语言文化,翻译日本和中国文化文本。”(龚献静,2017:42)与方译类似,黄译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香港,而香港的翻译环境及翻译政策向来都是非常积极的,比如香港翻译学会会长陈德鸿教授就曾指出:“在研究翻译史中,我发现无论是英译中或中译英,香港是个主要基地……”(徐菊清,2017:135)
就微观的文学与诗学因素而言,方志彤与黄兆杰选择英译《文赋》主要都是出于对其诗学价值的考虑。方志彤在其《文赋》英译本前言中指出:“这篇凝练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国诗学雄文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堪与六世纪刘勰那篇论述更为全面的《文心雕龙》比肩。”(Fang, 1951:527)而黄兆杰则在历数了陈世骧、方志彤、修中诚等人的《文赋》英译后坦言:“本书对其进行重新翻译,是由于我认为论及中国诗学的宏阔精妙,《文赋》不可或缺。”(Wong, 1983:50)
具体到两位译者对原作底本的选择,则可谓同中有异。相同的是,方译和黄译均以艺文书局刊印的胡克家1809年重雕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選》卷十七所收录的《文赋》为底本。略有不同的是,方志彤在选择底本时,还参照了《文赋》的其他版本及相关文献,包括《四部丛刊》初编《文选》第十七卷六臣注本、《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初学记》卷二十一、《陆士衡文集》《文境秘府》《太平御览》《四部丛刊》本《文选》第十七卷李善注本及《四部丛刊》本《文选》第十七卷五臣本中收录的《文赋》等(Fang, 1951:562)。另外,方志彤还对所选底本的内容作了一些微调,比如将“诵先民之清芬”一句中的“先民”改为“先人”,将原文“意徘徊而不能揥”中的“能”去掉,将“亦非华说之所能精”中的“精”改为“明”等。这些微调,有的是出于韵脚考虑,有的是对其中意义解读的权衡(Fang, 1951:562-563),由此可见方译兼顾原文形式与内容的传达。
2.2 初始规范制约下方译与黄译的翻译倾向
方志彤和黄兆杰的翻译倾向受到初始规范的制约。方志彤倾向于源语规范,着力追求译文的充分性;而黄兆杰则倾向于译语规范,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两位译者所遵循的这种初始规范及其由此形成的翻译倾向,可以根据图里重建规范所提出的思路,在译本正文之外的附录、前言以及译本之内找到充分的佐证,同时也全面体现在其译文之中。
2.2.1 方译以源语规范为导向的翻译倾向
方志彤严格遵循源语规范,其译文注重对原文内容与形式的充分表达。译文与原文极小的出入,方志彤都在其译文附录中作了细致说明。在“附录I”中,方志彤指出:“我在文本中作了几处改动,在此必须作出说明:我所作的改动只是韵律层面,而非诗学层面。”(Fang, 1951:546)在“附录III”中,方志彤明确指出其目标是“不过分阐释陆机的《文赋》”(Fang,1951:559)。
细读译文,可以发现方译严格保留原文形式,充分传达原文内容,并未对原文作过多阐释。方译用词精美凝练,句式简短有力,对称平衡,富有气势,节奏感十足,而这恰与陆机《文赋》的精致唯美、音节匀称、词句成双成对、极具节奏美的特点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方志彤在《文赋》的英译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倾力传达原文的内容及语言形式,充分体现了其遵循源语规范和重视译文充分性的翻译倾向。
2.2.2 黄译以译语规范为导向的翻译倾向
黄兆杰的翻译倾向主要表现为其对译文可接受性的重视上。黄兆杰在其收录《文赋》英译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前言中称,其译文旨在将中国文论作品准确翻译为“可读性强的英文(readable English)”(Wong, 1983: xiii),为无法读懂原文语言的英语读者阅读《文赋》提供便利(Wong,1983:xi)。
细读黄译,会发现其译文语言地道流畅,用词生动灵活,句式丰富多变,语法严谨规范,可读性非常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兆杰在其译文尾注中广泛征引了利维斯(F. R. Leavis)、艾略特(T.S. Eliot)、华兹华斯(W. Wordsworth)等西方文学家、批评家的文学思想来解释陆机的文学思想,以此拉近译语读者与源语文本的距离,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由此可见,黄兆杰在《文赋》的英译过程中,遵循译语规范,在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方面下足了功夫,以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赋》的文学思想。
2.3 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共同制约下方译与黄译的文本特征
初始规范在宏观上塑成了译者的翻译倾向,而其充分性或可接受性翻译倾向又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抉择:“其初始性在于它高于那些更低层次、更具体层次的特定规范……任何微观层面上的决策都仍然可以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来进行解释。”(Toury,1995:57;2012:80)换句话说,初始规范影响了具体的操作规范,而译者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会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由此形成了译本相应的文本特征。
就《文赋》的方译与黄译而言,方志彤与黄兆杰的初始规范影响了其操作规范,形成了各自具体的矩阵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两位译者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由此形成了两个译本各自的文本特征。具体说来,方志彤与黄兆杰在初始规范影响下所形成的重视充分性或可接受性的翻译倾向,以及二者各自所遵循的矩阵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影响了其具体翻译策略的抉择,进而形成了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各个层面上的具体特征。
2.3.1 词汇层面的比较分析
在词汇层面上,方志彤与黄兆杰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对于原文词性、术语的英译处理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1)词汇的动态与静态
如前所述,方志彤以源语规范为导向,追求译文的充分性。在这种初始规范的影响下,方志彤遵循原文的篇章—语言规范,在词汇的翻译上紧跟原文词性,其译文与《文赋》原文一样,动态的动词、副词居多。黄兆杰则以译语规范为导向,重视译文的可接受性,其译文遵循英语的篇章—语言规范,多运用英语擅长的静态表现法,突出表现为频繁使用名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动词名词化等词汇表达方式(邵惟韺 等,2015:98)。
例(1)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方译:Shih(lyric poetry) traces emotions daintily;fu(rhymeprose) embodies objects brightly.
黄译:But poetry [shi] ought to follow the poet’s feelings and be ornate,
Rhymed descriptions [fu] should be physical delineations of objects and be trippingly eloquent.
在该例中,方译遵循源语语言规范,按照原文结构,将原文对译为“名词主语+动词+名词宾语+副词状语”结构,构成“主谓宾”动词谓语句,因此其译文中多使用动态的动词和副词;而黄译则更多遵循英语的语言规范,更多使用具有静态倾向的词汇,将原文第一小句的“绮靡”译为形容词“ornate”,将第二小句的“名词主语+动词+名词宾语+副词状语”结构译为“名词主语+ should be +形容词定语+名词+形容词词组”结构,构成主系表结构,因此其译文多使用静态的形容词和名词。
(2)术语的英译
在不同翻译倾向的影响下,两位译者对《文赋》术语的英译明显不同:方志彤以源语规范为导向,始终以原文本为中心,力求靠近原文,因此在英译其中的术语时先音译,然后在小括号里附以英文解释;而黄兆杰遵循译语规范,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以方便英语读者的阅读,因此英译时先给出术语的英文释义,然后在方括号里附以汉语拼音。
例(2)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方译:Ming(inscription) is comprehensive and concise, gentle and generous;chen(admonition), which praises and blames, is clear-cut and vigorous.
Sung (eulogy) is free and easy, rich and lush; lun (disquisition) is rarified and subtle, bright and smooth.
黄译:Inscriptions [ming], though brief, need be of wide application and written with warm gentleness.
Cautions [zhen] had best be pointed and coolly bold,
Glorification poems [song] are required to be relaxed and elegant in style,
Discourse [lun], as prescribed, are sharp-witted and easily comprehensible.
在例(2)中,方志彤和黄兆杰对《文赋》术语的英译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两位译者均对术语作了文内注释,进一步解释术语的含义,从而将中西诗学的话语表达形式并置齐观,增加了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不同的是,方志彤更注重译文的充分性,因此先用威妥玛式拼音对原文的术语进行音译,而后在小括号内作出英文解释;而黄译始终遵循译语规范,将译文的可读性放在首位,更加关照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其对原文术语的翻译首先是英文释义,然后在方括号内附以音译。事实上,方志彤与黄兆杰的这两种处理方法均贯穿于其《文赋》术语英译的始终。
2.3.2 句法层面的比较分析
方志彤与黄兆杰两位译者在初始规范的制约下分别形成了注重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两种翻译倾向,进而影响了各自的操作规范,尤其是其“语言表述方式”(Toury, 1995:58;2012:82),这一点在句法层面上有鲜明的体现。
《文赋》是典型的骈体文,讲究骈偶对仗,句法结构比较单一,多为简单的主谓宾结构或连动式谓语结构(其中多省略主语)。方志彤与黄兆杰在其初始规范、翻译倾向、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在句法层面上对《文赋》的英译表现各异:方志彤遵循源语规范,英译时着力保留《文赋》的骈体句式,努力再现原文的句法结构,因此其译文以主谓宾动词谓语句为主,少数情况下兼用分词结构;黄兆杰则遵循译语规范,并不完全复制原文的骈偶结构,往往将原文简单的主谓宾动词谓语句译为更合乎英语语言规范的句式,更多使用插入语、分词短语,其句法结构往往丰富多变,交替使用主谓宾、there be、分词短语、独立主格、倒装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等结构。
例(3)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方译:Taking his position at the hub of things, [the writer] contemplates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he feeds his emotions and his mind on the great works of the past.
Moving along with the four seasons, he sighs at the passing of time; gazing at the myriad objects, he thinks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He sorrows over the falling leaves in virile autumn; he takes joy in the delicate bud of fragrant spring.
With awe at heart, he experiences chill; his spirit solemn, he turns his gaze to the cloud.
黄译: Lingering at the centre of the universe, contemplating its dark mysteries,
Nourishing his sentience on the Classics,
Responding in deep sympathy to the change of seasons,
Surveying, with feelings coming and going in rapid succession, the world,
Sorrowing for the fallen leaves in autumn,
Gladdened by the pliant branches of soft spring,
The poet is chilled at heart by the thought of forest’s severity,
And elated by the sight of clouds.
在例(3)中,《文赋》原文由四大组、八小句对仗工整、内容相关、音韵和谐的骈句构成,其中第2、5、6小句为三个简单的动词谓语句,第1、3、4、7、8小句为五个连动式谓语句。对于原文的骈偶句式和句法结构,方译与黄译的处理方法各异:方译遵循原文的语言规范,极力保留原文的骈偶句式和句法结构,将原文八个小句译成了八个两两对仗、结构完整的主谓宾动词谓语句,并用三个简单句翻译原文三个简单的动词谓语句,用五个动词谓语句加分词短语、介词短语或独立主格的形式翻译原文的五个连动式谓语句;黄译则没有拘泥于原文的骈偶结构,而是遵循英语多用插入语、分词短语的句法规范,将原文八个小句合并译成一个长句,由六个现在分词短语、一个过去分词短语及一个并列动词谓语句构成,其句子内部各种结构长短有致,丰富多变,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2.3.3 篇章层面的比较分析
受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方志彤与黄兆杰在篇章层面上采取了较为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既表现在二者对译文的“切分”上,也表现在他们对“副文本”的运用上。
2.3.3.1 切分
图里所说的“切分”(segmentation)是操作规范中矩阵规范的具体内容之一,主要指将文本切分成不同的章、节、段等类似的形式(Toury,2012:82-83)。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方志彤与黄兆杰均对译文进行了细致的切分,但其形式不尽相同。
方志彤遵循源语规范,追求译文的充分性,因此根据《文赋》论点的展开情况以及全文句式(“四六文”)与音韵的变化情况将译文切分为16个诗节(以A、B…P为序),并为每个诗节添加了小标题(Fang,1951:528-529;李凤琼,2016:20)。与方志彤形成对照的是,黄兆杰倾向于译语规范,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为帮助和引导英语读者阅读、理解其《文赋》英译,他将译文切分为22个诗节,并且像英语诗歌一样用罗马数字“I, II, III…XXIII”为其排序但并不为每个诗节命名,从而使得整个译文在形式上看起来非常像英语诗歌,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2.3.3.2 副文本
图里指出:“译文中或围绕在其周围的‘副文本’(Genette,1997)中的省略、增补、变位以及对各种切分现象的操纵,也都可由规范决定……”(Toury,2012:83)由此可以推断,规范对围绕在译文周围的副文本同样会产生影响。“副文本”(paratexts)的概念最初由法国文艺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后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在翻译研究中,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且承载着译者的翻译思想(王琴玲 等,2015:81)。基于上述考虑,此处聚焦方译与黄译两个译本的引言与前言、注释与附录等副文本,以考察两位译者何以在初始规范、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下为其译文增补了不同内容的副文本,并在其中阐述了自己与所遵循翻译规范一致的翻译思想。
(1)引言与前言
方志彤始终遵循源语的篇章—语言规范,为其译文增设了《引言》(Introduction),对原作《文赋》的文论价值、文本特点,尤其是其句式特征进行了重点交代。方志彤指出,《文赋》中有131个骈句、105个六字句式和17个四字句式,由此得出《文赋》大体为“四六文”(Four-and-Six Prose)(Fang,1951:528)。另外,方志彤还借助引言介绍了《文赋》外译的基本情况以及自己翻译《文赋》的原因与方法。
黄兆杰倾向于译语规范,在收录《文赋》英译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一书的《前言》(Foreword)中就已说明其翻译观,即以译语读者为中心、以译文可接受性为导向;在《全书引言》(General Introduction)中,黄兆杰开篇指出其意在将原文准确翻译为“可读性强的英文”,结尾处阐发了其在译语规范制约下所形成的翻译思想,即作为一名译者,他要通过语言优美的译文告诉译语读者原文本语言很美(Wong, 1983:xxii)。与其初始规范相一致,黄兆杰在《文赋》译文之后增设的《引言》(Introduction)中,着重以西方文论为参照交代了其译文的理论建树及现代意义。
(2)注释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指出:“不注意《文赋》的独特用词,就无法理解《文赋》,而要理解其用词,就需要追溯其绵长的注疏传统。”(Owen,1992:76;宇文所安,2003:80)因此,无论就《文赋》的理解而言,还是就其翻译而言,适当的注释都是非常必要的。方志彤与黄兆杰遵循各自的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文赋》的英译中均使用了大量的注释,但其注释的内容和形式明显不同。
方志彤在其译文正文之后增添了五个附录,其主要内容是对原文本的韵律格式、字句、重要术语、所用版本、异体字等所作的长达20页的注释。方译中的注释非常详尽,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其以源语规范为导向、重视充分性的翻译倾向。
在关照译语读者阅读习惯,注重译文可接受性的翻译倾向影响下,黄兆杰在其译文后附上了《文赋》的汉语原文,以方便有汉学背景的读者(the sinological reader)阅读(Wong,1983:xii);同时他还添加了59条脚注,对《文赋》的一些关键术语、文论思想进行解释,其中很多解释是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展开的,以帮助西方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译文。
3 结语
本文借鉴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文赋》的方志彤译本与黄兆杰译本进行了描写性、解释性比较研究,揭示了两种不同风格译本的产生过程与形成原理。文章首先分析了方志彤和黄兆杰在预备规范影响下在文本选择方面的异同,然后考察了两位译者在初始规范制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翻译倾向,在此基础上结合操作规范剖析了两位译者在翻译规范制约下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并由此揭示了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文本特征。研究表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深刻影响了方志彤和黄兆杰两位译者的翻译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制约两位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其译本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方译遵循源语规范,更注重译文的充分性,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靠近原文;而黄译则遵循译语规范,更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因而更符合西方诗学的审美特征。另外需要指出,尽管本文对《文赋》两个译本明显不同的文本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但并不否认两个译本仍具有不少共性,比如两个译本均为诗体翻译,均在译后附加了详尽的注释,均属于严谨的学术翻译等。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突破了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樊篱,将所描写的翻译对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对其进行“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Toury,1995:28/2012:23),系统阐述了预备规范、初始规范、操作规范等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徐敏慧,2017:12)及其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作用,能够有力地解释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具体翻译行为,深入地揭示翻译文本的生产过程和形成原理,进而能够详细地描述译本的风格与特点,因此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译本描写与批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