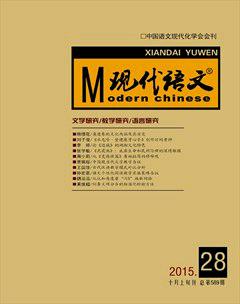陆机《文赋》的抄本及译本考述



摘 要:陆机《文赋》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较为系统的文学创作论作品,其成篇以来,最早以抄本形式流传。唐陆柬之书《文赋》为目前所见之最早抄本;此外,空海所编《文镜秘府论》亦选录《文赋》,此书长期作为抄本在日本流传。陆机《文赋》另一版本系统为《文选》本。自萧统编《文选》之后,《文赋》研究进入选学研究的范围,历代《文选》的刊刻本亦形成了《文赋》的《文选》本系统。《文赋》的第三个版本系统为近代出现的外文译本。各国学者将《文赋》译成了英、法、俄、韩等多种文字,使得《文赋》更为广泛地流传于世。
关键词:陆机 《文赋》 抄本 译本
一、引言
陆机所撰《文赋》是中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不少理论就是在《文赋》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文赋》启其端,《文心雕龙》《诗品》承其源,《文赋》的价值不言而喻。萧统《文选》收录陆机作品赋二篇、诗五十二首、表一篇、序一篇、颂一篇、论三篇、连珠五十篇、文一篇,其中赋壬第十七卷论文类选《文赋并序》。《文赋》研究因此进入选学研究范围。
北宋中期以后,《文选》形成以李善注版和五臣注版为主、各种版本并存的时代,学者对此多有考证,不一而足。陆机《文赋》除收录于《文选》之中,另有抄本流传,近世又有各国语言的译本。
二、《文赋》的抄本
陆机传世手迹只有《平复帖》,不见《文赋》。今所见《文赋》帖为唐陆柬之手书。唐张怀瓘《书断》评陆柬之云:
陆柬之,吴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议郎,虞世南之甥。少学舅氏,临写所合,亦犹张翼换羲之表奏,蔡邕为平子后身。而晚习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已后,乃备筋骨。殊矜质朴,耻夫绮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马不齐髦,人不栉沐。虽为时所鄙,回也不愚,拙于自媒,有若通人君子。尤善运笔,或至兴会,则穷理极趣矣。调虽古涩,亦犹文王嗜菖蒲葅,孔子蹙额而尝之,三年乃得其味。一览未穷,沉研始精,然工于效仿,劣于独断,以此为少也。隶行入妙,章草书入能。[1]
陆柬之(585-638)主要生活于唐高祖、太宗朝,比李善(630-689)早近半个世纪。陆所书《文赋》为书法名品,且成书年代较李善注《文选》更早,与刻本《文选》相比更是存在较多差异,故为世所重。
唐朝时期,另一种《文赋》抄本在日本流传,即空海所编《文镜秘府论》。空海(774-835)为日本僧人,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入长安学习,回国后编成《文镜秘府论》一书。该书收录中国南北朝至中唐诸多文学理论著作,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其中最早的完本有两种,一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本(据说是平安朝后期写的),二是高野山三宝院所藏本(也是平安朝后期写的)。”[2]空海生活年代晚于李善,有可能见到陆柬之《文赋》[3]和《文选》本《文赋》,故其《文镜秘府论》[4]所录《文赋》的底本值得注意。现将两种《文赋》抄本与《文选》本(底本为中华书局2007年影印宋淳熙贵池尤袤刻本)对照,校出如下70条:
以上所列各条,概而言之,可分为以下数类:
1.陆柬之《文赋》数条涉及避讳问题,可径直改正:“余每观材士之所作”,“材”,避家讳,父名“山才”;“咏廿德之俊烈”,“廿”,避唐太宗讳;“诵先氏之清芬”,“氏”,避唐太宗讳;“辞逞材以效技”,“材”,避家讳。
2.陆柬之《文赋》《文镜秘府论》与《文选》用字不同而于文意无碍者:以—之,乎—于,而—以,于—而。
3.陆柬之《文赋》《文镜秘府论》使用异体字而分别与《文选》不同者:沈—沉,採—采,瞚—瞬,按—案,岨峿—鉏铻,毫—豪,絃—弦,尠—鲜。
4.陆柬之《文赋》和《文镜秘府论》用字相同而与《文选》不同者:“余每观才士之所作”,两种抄本均无“所”字;“夫放言遣辞”,两种抄本均作“夫其放言遣辞”;“喜柔条于芳春”,两种抄本均作“嘉柔条于芳春”;“嘉丽藻之彬彬”,两种抄本均作“嘉藻丽之彬彬”;“耽思傍讯”,“耽”,两种抄本均作“躭”;“于是沈辞怫悦”,“怫”,两种抄本均作“拂”;“怀响者毕弹”,两种抄本均作“怀响者必弹”;“本隐以之显”,两种抄本均作“本隐以末显”;“思按之而逾深”,两种抄本均作“思按之而愈深”;“粲风飞而猋竖”,两种抄本均作“粲风飞而猋起”;“虽离方而遯员”,两种抄本均作“虽离方而遁员”;“炳若缛绣”,两种抄本均作“昞若缛绣”;“吾亦济夫所伟”,两种抄本均作“吾亦以济夫所伟”;“俯寂寞而无友”,两种抄本均作“俯寂漠而无友”;“徒靡言而弗华”,两种抄本均作“言徒靡而弗华”;“良余膺之所服”,两种抄本均作“良予膺之所服”;“顾取笑乎鸣玉”,两种抄本均作“顾取笑于鸣玉”;“顿精爽于自求”,两种抄本均作“顿精爽而自求”;“伊兹文之为用”,“之为用”,两种抄本均作“其为用”;“恢万里而无阂”,两种抄本均作“恢万里使无阂”;“仰观象乎古人”,两种抄本均作“仰观象于古人”;“理无微而弗纶”,两种抄本均作“理无微而不纶”。
5.陆柬之《文赋》和《文镜秘府论》两种抄本用字均误者:“漱六艺之芳润”,抄本均作“濑”。漱,《说文》:“荡口也。”濑,《说文》:“水流沙上也。”二者词义不同。[5]“物昭晣而互进”,昭晣,《说文》:“明也。”陆柬之《文赋》作“哲”,《方言》曰:“哲,知也。”《文镜秘府论》作“皙”,皙,《说文》曰:“人色白也。”“哲”和“皙”,与“晣”词义不同。“哲”和“皙”,与“晣”字形相距甚远,相比之下,“哲”和“皙”在字形上却较为接近。
由第四类和第五类可见,陆柬之《文赋》和《文镜秘府论》两种抄本相同并均与《文选》相异者共24条,占三分一强。二者应当有大量内容来自《文选》以外的文献材料。因此兴膳宏作了两个假设:1.“可以想象陆柬之和空海都不一定以《文选》为底本来抄写《文赋》”;2.“陆机的《文赋》在唐代除了收录在《文选》中以外,还有像陆柬之书那样仅为一卷的单行本流传下来。”[6]陆柬之所书《文赋》和空海《文镜秘府论》所录《文赋》的底本极有可能来自同一出处。
三、《文赋》的译本
自萧统《文选》选录《文赋》之后,《文赋》研究自然进入选学家的视野。《文赋》的《文选》本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从梁萧统(501-531)《文选》产生至唐李善、五臣注《文选》之时期;从唐李善、五臣注《文选》至宋刻本出现及以后之时期。历代《文选》的刊刻本亦形成了《文赋》的《文选》本系统。选学繁荣对于《文赋》等作品的研究又乃一大幸事。
到了近代,《文赋》继续受到关注,学者将《文赋》译成多种外文,形成了《文赋》的译本。1926年,俄裔学者马果里哀(G.Margoulies)出版《〈文选〉辞赋译注》(Le "Fou" dans le Wen-siuan. Etude et textes),其中有《文赋》的法译本和详细注释。1928年,奥地利汉学家查赫(Erwin von Zach)在《通报》(T'oung Pao)发表《关于马果里哀《文赋》之译文》(Zu G. Margoulies Ubersetzung des Wen-fu),他批评马果里哀的翻译,并发表自己的译文。[6]1944年,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B.M.Alexeiev)的俄文译本问世。1948年,《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收录加州伯克莱大学陈世骧《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封面上说:“本篇研究陆机《文赋》与其生平、与中世纪中国历史,以至与现代批评观念的关系,并以诗体翻译全文。”1951年,美国修斯(E.R.Hughes)发表陆机《文赋》英译本(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并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同年,哈佛大学方志彤发表英译《文赋》(Rhyme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Fu of Lu Chi (A.D. 261-303)),注释详尽,并附有押韵格式。1983年,香港大学黄兆杰在其《早期中国文学理论》(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发布英译《文赋》。1992年,哈佛大学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选录《文赋》,配有英译和精细的解读。华盛顿大学康维达系统地翻译《文选》,1996年出版其《文选》第三册,其中包含《文赋》英译本(Rhapsody on Literature)。1996年,美国伯恩斯通(Tony Barnstone)出版其英译《文赋》(The Art of Writing)。1999年,美国哈米尔(Sam Hamill)发表了英文全文译本(The Art of Writing),并配有他的序文。
阿列克谢耶夫是俄罗斯的汉学权威,曾于1906年至1909年造访中国。他把《文赋》当做打开中国古典诗学的钥匙,潜心于《文赋》的研究和翻译。在参考马果里哀法译本《文赋》的基础上,阿列克谢耶夫用俄语对《文赋》进行了全文翻译。俄文译本于1944年载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并遵循了他的两个原则:“一是逐字逐句地对译,不增减字句,甚至不打乱原文的词序;二是讲究韵律,努力传达原文中国式的声调和谐。”[8]他把《文赋》看做一种异质的文化产物,用“灵感”阐释陆机的创作理论,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陆机所谓之“应感”或“物感”与西方“灵感”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阿列克谢耶夫常对文本进行断章取义阐释的作法亦不可取。
1951年,修斯所译注《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由纽约Pantheon Books出版,[9]书的序言由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瑞恰兹(I.A.Richards)撰写。瑞恰兹认为:“西方的传统在于让我们感受极端的恐惧;获得的知识只是一种责难。而在中国却是满足。所以无须畏惧和质疑:‘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在序言的末尾说:“西方世界亦可以将‘操斧伐柯运用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之中。”[10]修斯著作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诗学传统和中西文艺比较的概述,第二部分为陆机行年考,第三部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赋》,第四部分为《文赋》英译,第五部分为《文赋》注释和评论,第六部分则讨论尚未解决的论题。修斯非常关注赋的对偶,对文中句式之变换均加注意。《文赋》序曰:“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犹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认为七字对七字的句式不仅改变了四字对四字的单一性,而且使得思想得以转换自如。修斯提到序言两次出现“每”字:“余每观”之“每”与“每自属文”之“每”。他认为第一个“每”与“余”相关,第二个“每”字则与非第一人称的“自”相关。其实,两个“每”字均指陆机本人,第二个“每”字言观他文知其用意、自作文则知之更加确切。修斯在此过度阐发。此类例子在文中较为多见,兹不赘述。
1951年,方志彤在《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文赋》译文(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 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其文是中文与英文结合,逐句翻译,注释详赅,较为精到。文末依据译文段落附有各段押韵格式,并附术语对照和校勘,论述完备。1983年,香港学者黄兆杰发布英译《文赋》,收录于其《早期中国文学理论》(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同样,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亦选录《文赋》并作了英译。
宇文所安译注《文赋》的体例和修斯极为相似,即逐段翻译后附注释和作者评价。他在书中说:“《文赋》的独创性至少部分来自于‘文这个主题与‘赋这种形式的结合。”[11]他关注《文赋》的篇章结构、铺陈、对仗、词性,其译注与中国古代的注疏形成鲜明对比。
1996年,康维达出版了其宏大翻译成果之《文选》第三册,包含英译的《文赋》。他细致研究了文体风格和各类措辞,采取在译文后加注的方式解释原文,当直译无法达到要求时,他就使用了意译,以达成“撰写一部能把中国文学的伟大介绍给西方读者的翻译”[12]的目标。
伯恩斯通的英译《文赋》是所有英译本中最为简略的,他将《文赋》原文分为22部分,并给每一部分拟定小标题,译文只给出了如下四个批注。1.“六经”,儒家经典。2.“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许早期的格律变化是基于古汉语的四声;中国传统的基本颜色包括白、黑、红、黄、蓝、绿。3.“是盖轮扁所不得言”,庄子讲述了轮扁与齐桓公相遇的故事。轮扁告诉齐桓公,他的手艺精微而难以传授,以至于不能用言语告知其子。语言是生活的表达。故而轮扁谓齐桓公所读之“圣人之言”实则“古人之糟粕”。4.“六情”,喜、怒、哀、乐、爱、恶,说法不一,有时增加“欲”为“七情”。
1999年,哈米尔发表了自己的英译本并序言。他认为陆机之所以引起国外众多诗人的关注,例如霍华德·莫奈洛夫(Howard Nemerov)的《致陆机》(To Lu Chi)、威尔纳(Eleanor Wilner)的《文赋沉思》(Meditation on the Wen-Fu)、凯泽(Carolyn Kizer)的《叩寂寞》(Knock Upon Silence),是由于庞德对《文赋》序言的精到评论。哈米尔着力于主要章节思想和意象的表达,以此构建诗意的释义。部分地方进行了压缩,部分地方则跳跃或加以微调。
台湾学者徐复观于1980年在《中外文学》发表《陆机〈文赋〉疏释初稿》,进行通篇注疏。1983年,杨牧(王靖献)以陈世骧的《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及徐复观的《陆机〈文赋〉疏释初稿》为基础,“参考唐朝以降至当代人所撰各种注疏,斟酌中西文学批评的重要观念,试为比类校勘,转益阐释。”这是第一部融合了中文传统译注和英文译本的校释著作,具有比较文学之意味。
1985年,韩国金世焕教授发表《〈文赋〉研究——注释一》,可惜通篇注译最终未能完成。1989年,柳汉英硕士学位论文《陆机文赋研究》,对陆机的创作论、文体论、修辞论加以分析,附《文赋》全文分析和译注。2001年,车柱环用韩语翻译《文赋》,引起了一定的关注。2010年,年轻学者李揆一发表《文赋译解》,对《文赋》作了详尽的注释、翻译和评析。
四、结语
以往对《文赋》版本的考辨多在于《文选》本之上,而《文选》各本尚存较大差异,更何况《文选》本与抄本之间存在的不同。如对抄本与《文选》本细加考辨,《文赋》单行本的轨迹可能会更加清晰。如拓宽视野,将《文赋》的接受放到世界文学与文艺批评之中考察,则《文赋》的外文译本亦具有较高的价值。外文译本和注释的关注点与传统训释多有不同,能够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
注释:
[1][唐]张怀瓘:《书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2][日]兴膳宏:《试谈文赋抄本的系统》,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3][唐]陆柬之:《陆柬之〈文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版,第11-63页。
[4][日]空海:《文镜秘府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9-175页。
[5]徐桢立在《余习庵遗文拾零》(《中国历史文献集刊》第5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5月版)中对唐人写本陆机《文赋》的作者提出异议,认为其作者非陆柬之。“赋中漱六艺之芳润,误漱为濑,明是不知文义人所书。乃为赵吴兴以次,或文章巨公,或书翰妙手,翕然推为陆思谏书,思之再三,殊不可解。第其笔法潇澹古质,的为唐代人书,又其摹兰亭序字,颇复似之。”对此,陈炜湛在《关于唐写本陆机文赋》(《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11-113页)中指出:“徐氏指出的漱误书为濑,实由二字草书相似所致。但写本中的别字远不止此。”不过,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陆柬之〈文赋〉》,陈氏所述“漱误书为濑,实由二字草书相似所致”的说法亦不准确。
[6][日]兴膳宏:《试谈文赋抄本的系统》,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154页。
[7]程汇娟:《陆机文赋英译探赜》,英语研究,2008年,第2期,第53页。
[8]李逸津:《俄罗斯汉学家对文赋的接受与阐释》,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52页。
[9]修斯之前,有四种《文赋》外文文本。修斯在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 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书中说:“With regard to Western literature bearing on the Wen Fu, there are four items to be noted. The first two are Dr. Georges Margoulies Le Fou dan le Wen-siuan(Paris,1926), with its translation and notes;also his learned Le Kou Wen chinois (Paris, 1926)。The third item is a translation in German by E.von Zach reported to me as contain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Richard Wilhelms China-Institute at Frankfurt (an earlier section of proceedings which was only issued to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The fourth item is Basile Alexeievs brilliant esquisse dogmatiqu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Paris, 1937)。”
[10]E.R.Hughes:《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D. 302, 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1年版,第ix-x页。
[11]王柏华,陶庆梅译,[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12][美]康达维:《文选浅论》,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黎思文 广东深圳 深圳大学文学院 51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