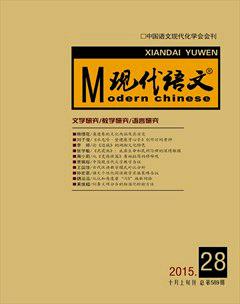《鸳鸯针》的历史反思与遗民情结
摘 要:经历过明清鼎革的吴拱宸,在《鸳鸯针》中表现出了明显的遗民情结,也表达了对明王朝命运的哀挽。作者将这种情绪寄于笔端,发泄了对旧朝的怀恋以及对其灭亡原因的反思,试图为旧朝找出“医王活国”之路。但面对个人出路问题作者却表现出了逃避心理,这体现了当现实与理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作者对于人生命运的怀疑甚至幻灭感。
关键词:《鸳鸯针》 遗民情结 反思 救国“药方” 逃避心理
《鸳鸯针》是清初的一部话本小说集,据王汝梅考证,其作者华阳散人就是明末清初遗民吴拱宸,作者的创作目的是为寻找“医王活国”之“药方”,以小说补救时弊。但亲身经历过朝代更替的作者又在作品中体现出了明显的遗民情结,表现出了对民族命运的哀挽和对故国的哀思,这种创作心理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同时也给作品打上了时代烙印。
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注重“华夷之分”,明清易代,异族入主中原,在这个时期“华夷之分”成为最强烈的汉民族之声。清初曾静在《知新录》中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1](P149)这着实反映了不少明遗民的内心情绪,国破家亡的伤痛与清初满族野蛮残酷的政策激起了他们的愤恨不平与反抗意识。这种民族情绪唤起了文人的创作激情,给清初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人们企图以创作来记录这段历史的巨变,对历史进行反思,更将人生的愤懑与理想寄情于笔端。因此,富有民族意识、忠君思想、眷恋旧朝情绪以及改革意识的遗民文人的作品在清初大量涌现,形成了最富时代精神的创作主题。
在这种环境下,亲身经历过王朝更迭的吴拱宸在创作《鸳鸯针》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民族情绪与遗民情结,主要表现在:
首先,作者将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均设置在明代,将情感倾注于前朝。小说第一卷第四回提到了明嘉靖年间严嵩之子严世藩的行径,第二卷《一枕奇》的时间背景是明英宗天顺年间,第三卷《双剑雪》是明崇祯年间,第四卷是万历年间。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明朝社会生活的熟悉与眷恋,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吴拱宸作为明代遗民并不承认清廷的正统地位,更不愿使用清历。这种创作心理在明遗民中相当普遍,如屈大均的《癸酉元日作》云:“虎视谁书秦正月,龙兴自纪汉元年。”王夫之在《走笔寄刘生思肯》中称:“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小说内容上大量涉及明清时事,作者对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记录,尤其是对战乱多有描写,真实再现了明末清初鼎革前后的社会动乱,反映了战乱中人民的生活状况,表达了作者对事件的认识与情感。小说四卷均以战乱作为背景穿插,第一卷提到:“倭寇作乱,浙江一带地方并无宁宇。经过地方,鼠逃鸭散。未经过的地方,鹤唳风声。大小男妇,东边的走到西边,西边又走到东边。山谷之中,啼号不绝。所在地方,皆负担载锅而立。”[2](P38)再现了战乱中人们四处奔波无所归依的情形;卷二提到袁公“原任太常寺卿,因弹了王振一本,挂冠回来”[2](P91),又提到高进之之兄“遭土木之变”,这指的是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而这次战役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振等宦官的专权和乱政。作者将这些事件穿插在小说文本的叙事中,表现了对明朝衰败原因的认识与反思。第三卷再次提到俺答祸乱和倭变,反映了作者对外族入侵的痛恨,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反清的民族意识。此外,第三卷里作者将李自成称为“李贼”,将牛金星称为“贼头”,又提到山东丁蔡两家起义将投靠了李自成的卜亨一行人马“杀个尽绝”,“此时,正值弘光登极南京,连夜押解过江”[2](P163),表达了对李自成起义的痛恨与对抵抗者的赞扬。第四卷写杨浩人作乱时的淫掳焚杀无恶不作,表现了“干戈丛里黑云飞,乱世人民如鸡狗”的生存状况。总之,小说中表现出的战乱状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历经明清鼎革的真实感受,与此同时,作者对明朝衰败的原因作了反思,并为明末战乱造成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深感痛心。
再者,《鸳鸯针》每一卷每一回的开头、中间还有结尾都出现了诗词歌赋,这些诗词歌赋除了用来评议人物、总结情节之外,更多的是为了追怀故国与表示不仕新朝的决心。甚至这类诗词歌赋有的在小说中并没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情节发展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就小说故事的发展而言,往往给小事件盖大帽子,因而显得较为突兀,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穿插曲折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倾向。第一卷第二回徐鹏子靠卖字赚钱养家,作者评价道:“不同乞食甘胯下,还似吹箫隐市中”[2](P28),正是一种孤傲的心态,曲折地表现了作者不受新朝嗟来之食的态度。接着作者又有诗云:“阮生易堕穷途泪,季布当年髡作奴。试看卫霍封侯日,暂屈终伸是丈夫。”[2](P29)诗中卫青、霍去病都是抵御外族侵略的历史英雄,徐鹏子卖字这件小事作者却以家国之事感慨,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意识。第二卷第一回时大来蒙冤入狱后作者又大发感慨,诗云:“张公吃酒李公醉,喜鹊乌鸦共树飞。漫道死生浑梦幻,他年重望帝城晖。”[2](P73)这实际上是作者对故国的思恋,“喜鹊”“乌鸦”实有清朝鸠占鹊巢之意。第四回讲了时大来与风髯子一文一武抵御外敌的行径,作者在开头就有一首《点绛唇》云:“大刀阔斧,千原血碧花纹古。恩怨都灰,寸心谁共数。青草黄沙,大抵英雄谱。尽胡越,江山块土,随分勋名补。”[2](P98)表明了只有文武并用才是共御外敌、定国安邦之策。且在高进之要誓死捍卫家国时又有诗云:“雀鼠争粟粒,英雄共死生。至今青岛上,杯酒吊田横。”[2](P103)作者将外敌比作鼠辈,将“粟粒”比作江山,强调如若抵御失败,则甘愿像田横不肯称臣于刘邦一样守义不辱。第四卷第四回范顺钱财散尽返乡,诗云:“相逢疑是梦,故国井疆非。化鹤重来日,千年丁令威。”作者借“丁令威”的典故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感慨。
二
《鸳鸯针》中流露出了吴拱宸的遗民情绪,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哀挽和对故国的哀思,而正是这种创作心理使这部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增强,对明王朝灭亡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同时作者企图以小说创作来“医王活国”,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救世”之方。
首先,对明王朝用人制度的反思。小说批判了明代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倡真才实学、文武并用的用人原则。第一卷中,胸无点墨的富家公子丁全贿赂考官偷换他人考卷而考中举人、进士,在得官上任后一味刻剥民财、穷奢极侈;第三卷中卜亨“因他家道丰厚,县府道都不消费力,关节打通,顺顺溜溜就做了个秀才。做秀才后,又连连丁了内外监,都不曾遇着岁考,哪里看得出破绽出来。”[2](P120)后让宋钰代笔取得元魁,中举后正赶上闯贼猖獗,卜亨便作了伪官。在描述这些行径时作者将科举制度批判与官场批判、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高层次上批判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又增加了全书的思想深度与社会价值。这些不学无术的假才子于国于家毫无用处,甚至会误国,而像徐鹏子、宋钰这等有真才实学者才可保家卫国。此外,小说还肯定了侠义强盗也可救国护国,肯定了他们的盗亦有道。第二卷中风髯子不仅具有劫富济贫的品质,而且以行盗的方式为朝廷效力,他认为“做好人,有好人的勋业;做歹人,也有歹人的品节。大丈夫即投胎在这里,也要为天公留些仁爱,为朝廷效些忠悃,为自家立些声名。”[2](P68)本卷第四回写到俺答进犯与倭变,全靠文臣时大来与武将高进之、风髯子凭借自身才能击退了外族侵略。作者在此明确表达了在国难当头时文武之才都可以为国效忠,朝廷应该广纳人才,第二卷入话言:“朝廷要破格用人,不可拘定那一流一途才做得官。这些人,得一官半职,鼓舞才能,国家还可以收得人之效。”[2](P59)这是作者“在国家危难时势下的新的用人观”[3]。
其次,对明朝官僚的品质进行了反思。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明朝官员的腐败无能、大敌当前的失职畏缩行为。第二卷第四回讲道:“俺答进了口子,逼近都城。该轮到兵部出头了。那有钱用的司官,都推委不去。时大来是不用一个钱的,单单推了他,做个头哨,他也不辞难。”[2](P106)任提学在西兵入关时畏首畏尾、藐寇玩兵,“唯知克剥军民,罔顾官箴行止”,时大来评道:“满长安,这样人也还多”,如若不是像高进之、风髯子这等贤才良将保家卫国,几乎就要丧失疆土。这实际上就是明末官员大敌当前时的普遍心理,这些官员在国难面前相互推卸责任成为明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作者塑造了像宋钰、时大来、高进之、风髯子这些清正廉明、具有运筹帷幄之才的官员,认为只有这些贤才良将才可使国家长治久安。
最后,作者鞭挞了李自成起义时望风而降者,褒扬了忠臣义士誓死救国的行径。小说第三卷第四回讲到卜亨为求荣投靠了李自成,祸害乡里,最终被起义军虏获的事。卜亨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产物,作者极力批判了卜亨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投降行径,不仅批判了科举制度,更是将矛头指向了明清易代时期官员们的变节行为。在第四卷入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古云:“三代以上之士,唯恐好名;三代以下之士,唯恐名好。”名你却不知,名字有两样:有名实之名,有名声之名。名实之名,如在自然香的,靛自然青的,梅子自然酸的,有了这副实料,后有那个名称。如靖国难的,叫做忠臣;负气节的,叫做义士;西子王嫱,叫做美人。这便是名实之名。[2](P113)
这番言论实际是褒扬了忠节义士,也只有这类人才名副其实,才能够名垂千古。像卜亨这类无耻之人正是作者所鄙视的,若多些像时大来、高进之等誓死救国的忠节义士,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也不会毁于一旦。
三
在遗民心态的驱使下,《鸳鸯针》对明王朝灭亡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反思,也探索了救国治国之方,体现了作者以道自任的人文关怀,然而对于个人出路,作者表现出了逃避心理。
明朝的灭亡、社会的动荡使许多文人士子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失去了信心,从而产生了对内心世界的反省与对外在世界的逃避心理。这时期不少人放弃了政治出路,或者选择遁迹山林,过着与世无涉的生活,或者选择诸如游幕、作馆、务农等生活道路,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大多数明遗民的心理倾向。在这种环境里,吴拱宸也不例外,“大约吴拱宸在崇祯九年虽中举,终未中进士,道路艰难曲折,入清后,隐居茅山。”[4](P352)从《明遗民诗·离虎丘》一诗中也可看出作者对凡尘中漂泊无依的倦怠,诗云:“万里风霜十八秋,姓名无地不淹留。长当佞佛微嫌发,何用为家半在舟。归思摇摇同野鹿,畏人切切似沙鸥。殷勤海涌峰边水,好载凄凉向北留。”[1](P108)在历经千辛万苦后作者也有了归隐的心理,企图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鸳鸯针》中有多处今非昔比的感慨,如第二卷提到“世风非古昔,步步费推敲”,同卷主人公时大来与风髯子功成名就之后欲归隐山林,说道:“如今恩荣已极,若不及早回头,未免犯不知足之辱了。”[2](P111)最后二人“驰驿荣归”,小说人物的归宿正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逃避心理。
总之,遗民心态是明末清初社会上长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文人作家们将这种情绪寄于笔端,发泄了对旧朝的怀恋与对其灭亡的反思,并为旧朝找出了“医王活国”之路。然而当作者以小说人物聊以自慰后,还是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于是毅然选择了无为而乐的归隐。这种既关注现实又走向归隐道路的创作,实际上就是以道自任的士人企图以文学创作关注、改变现实,借以实现自己的兼济天下之梦。然而激情过后,作家仍无法化解现实矛盾,故而作品中会流露出一种对于人生命运的怀疑甚至幻灭感。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的宗教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LGYCX1513]成果之一。)
注释:
[1]林堂,沈台芬:《雍正大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2]华阳散人:《鸳鸯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王言锋:《中国十六~?十八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4]王汝梅:《<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84年版。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金晓民.《儒林外史》与《鸳鸯针》[J].明清小说研究,2001,(04).
[3]居鲲.清初遗民情结小说初探[J].明清小说研究,2008,(03).
(杜明娜 陕西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