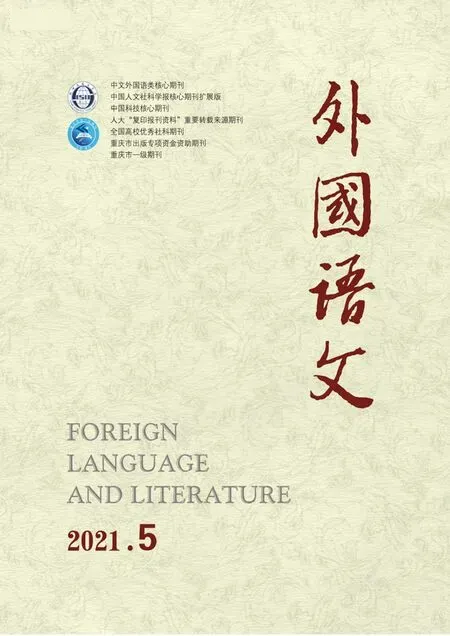《简·爱》中的孤儿成长模式对比分析
张丽
(重庆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54)
0 引言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作为孤儿的女主人公经历种种挫折后成长为独立的有自制力的女性。这部小说自1847年首版之后就轰动整个文学界,当时的英国评论家们纷纷给予了高度赞扬(盖斯凯尔,2012:181),是一部具有浓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的很多内容在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生活中能找到痕迹。当时的英国,受惠于工业革命,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在世界上可称头等强国(李宝芳,2015:1)。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也使教育也呈现出了大发展、大繁荣、大转变的景象(李荣亮,2016:34)。人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教育,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史无前例的重视,整个英国从家庭到学校都形成了重视儿童的社会氛围(李宝芳,2015:141-145)。英国在教育上的投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期(1840—1901),大量的财力投入学校的建设和教师的培训上(Albisetti, 2012:345; Floud et al., 1981:271)。教育对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当时的女性教育尚处在发展阶段,性别角色的分工使得女性的教育仍然是以贤妻良母为目标,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期待塑造出“优雅、纯真、温柔、顺从的理想女性”(马瑜,2004: 134)。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小说中的女性孤儿的成长体现出了时代的特点: 一方面父母呵护的缺失自然会凸显生存和成长的残酷面,另一方面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教育目标也会体现在这些成长中的孩子身上,要求他们通过教育成长为符合社会规约和期望的女性。
本文将分析和对比小说《简·爱》中两个孤儿简和阿黛勒的成长模式,简在经历了悲惨的童年后终于成长为一名有自制力的独立女性,阿黛勒则在更为宽松有爱的环境下成长为符合社会期望的女性。不同的生活环境导致她们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但成长结果都是符合社会规约的女性。简的原型是小说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她从小就极度缺乏母爱和父爱,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作为牧师的父亲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给孩子的陪伴十分有限。后来夏洛蒂·勃朗特在寄宿学校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生活条件极差,“变质、不卫生的食物”曾导致很多学生呕吐并患上了伤寒症(盖斯凯尔,2012:38)。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为小说中简的生活经历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文学虽源于生活,却也高于生活;小说既非全然实事,也非全然虚构(伊格尔顿,2018:2)。作者在小说中再现和升华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简·爱无父无母,在舅妈里德太太家和罗沃德求学时都曾遭受欺辱和虐待,却在学校遇到了给予她指引和关怀的同学海伦和老师坦普尔小姐,最终从一个古怪、冲动、感情用事的孤儿成长为有自制力的独立女性。小说中的另一个艺术形象阿黛勒,也是从孤儿成为符合社会规约的女性,但其经历却要顺利许多。虽然也缺少父爱母爱,却多了很多关爱,获得周围人们包括家庭教师简的关爱和指引,从一个任性虚荣的女孩成长为“讨人喜欢、懂礼貌的伙伴,和气,听话,很讲原则”的女性(夏洛蒂·勃朗特, 2010:454)。小说中的简是典型的底层孤儿,虽被里德家收养却未被接纳,被送去罗沃德这样残酷学校类似遭到抛弃,但她幸运地遇到了人生的指路人海伦和坦普尔,最终改掉冲动的缺点,成为当时社会期望的女性。阿黛勒是典型的上层孤儿,生活上物质富足,因为有家庭教师而更容易得到了关照和指引,即使偶然进入到严苛的学校也能很快从中脱身并重新选择更温和的学习环境。
1 社会底层的简和社会上层的阿黛勒
童年是懵懂的成长期,需要成年人的细心关照和指引。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父母应该是儿童的老师,支持他们的好奇心,回答他们的问题,通过鼓励而不是惩罚帮助儿童成长为理性、专注和有爱心的人(Clarke-Stewart et al., 1987:4-5)。小说《简·爱》中,主人公简和次要人物阿黛勒都是孤儿,依靠收养人生活。简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收养她的舅舅也很快去世,于是舅妈里德太太成了监护人。舅妈里德太太并不喜欢简,始终觉得她是外人。阿黛勒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收养的小女孩,她的母亲曾经与罗切斯特有过一段感情,但后来背叛了他,而罗切斯特并不承认这是他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小女孩是个“可怜虫”才把她从“巴黎的泥坑,转移到这里,让她在英国乡间花园健康的土壤中,干干净净地成长”(145)。简和阿黛勒的共同特点是都寄人篱下、没有父母的关爱。然而作为孤儿的处境却大不相同:简在里德家受到忽视和排斥,甚至有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连仆人也趋炎附势不喜欢她,在学校也受到校长的污蔑和体罚,她始终挣扎在社会底层;阿黛勒在桑菲尔德却有周围人的照顾,在物质上享受着上层的待遇,成长过程也得到关爱与指导。
1.1 简的艰难挣扎
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挑战,与环境逐渐磨合,从而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达到个体的成熟(李元,2021: 16)。孤儿简所经历的挑战是残酷无情的,有同龄表兄妹的欺负,有长辈舅妈的虐待,有仆人们的冷淡,还有校长的体罚。没有父母的呵护,简在里德太太家里经常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表哥约翰认为她就是家里的仆人,应该称呼自己为“少爷”,还常打她,“不是一周两三次,也不是一天一两回,而是经常如此”(6)。幼小的简对表哥的打骂习以为常,忍让却令表哥更加嚣张。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简躲在窗边看书,再次遭到了表哥约翰的辱骂,将书扔到简的头上,导致头部流血。简强烈反抗,而反抗却给她带来了更重的惩罚,她被里德太太关进了红房间,在愤怒和恐惧中昏过去,差点儿失去生命。通常来讲,孩子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反复发生的欺凌往往是因为没有人关爱这个被欺凌者。简经常遭受表兄妹的欺凌,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说话。里德太太介入孩子之间的冲突,自然偏向自己的儿子,使已被欺凌的简遭受了更大的委屈。简虽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却连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
身为孤儿的简不光遭到同辈的表兄妹的欺辱,还要以儿童的智力和能力来承受成人的碾压。有一次,简控诉里德太太对自己不好,自己死去的舅舅和父母会看得清清楚楚,从而激怒了里德太太,遭到推搡和耳光(26),随后贝茜又“喋喋不休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说教,证实我无疑是家里养大的最坏、最放任的孩子,弄得我也有些半信半疑”(26)。贝茜在里德太太家里算得上是最疼爱简的人了,但受到主人和周围其他女仆的影响,她也有伤害简的言行。贝茜如此长时间的责备,反复传达负面信息,让简都开始怀疑自己,这是精神上的打击。里德太太还在罗沃德校长面前污蔑她是一个说谎的孩子,而年幼的简自然是无力也不敢当面澄清。在罗沃德学校,校长布罗克赫斯特十分严苛,他听信里德太太的话,当众宣布简是个撒谎的人,并要求全校师生远离她:“你们必须提防她,不要学她的样子,必要的话避免与她做伴,不要与她交谈”,“这个女孩是一个——说谎者” (63-64)。随后简被罚在板凳上站半个小时,这样的体罚和当众羞辱带给她巨大的精神伤害。校长以自己的绝对权威当众否定和体罚简,这种打击程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难以想象,简认为这种伤害“非言语所能形容”(64)。罗沃德学校生活条件也很艰辛,学生们经常吃不饱,处于“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的状态(75)。简的悲惨童年主要原因是她的社会底层的孤儿身份,没有父母保护,虽被收养却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
1.2 阿黛勒的顺利成长
简的孤儿生活以悲惨为主色调,而小说中同为孤儿的阿黛勒却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阿黛勒虽然也是被领养的孤儿,但一直以罗切斯特家小主人的身份生活在社会上层,有管家、保姆、仆人照顾,有家庭教师,进了不合适的学校可以退出并重新选择学校。
阿黛勒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没有人打她或欺负她,罗切斯特家的管家、保姆和仆人们也没有歧视她。男主人罗切斯特多数时候不在桑菲尔德庄园,但是他回来时会给阿黛勒带礼物,这一点从阿黛勒盼望他回来,并敢于向他要礼物可以看出来。阿黛勒跟随罗切斯特和简乘马车出行,男主人也会跟她聊天玩耍。其间罗切斯特说要带简小姐去月亮上居住,阿黛勒以孩子的认真态度提出了很多困难说此事无法实施。这时罗切斯特也像小孩子一样和她说话:“你会怎么办呢?阿黛勒?动动脑筋,想个应付的办法。一片白云,或者一片粉红色的云做件长袍,你觉得怎么样?一抹彩虹做条围巾绰绰有余。”(266)罗切斯特用这样孩子气的话语与阿黛勒的互动,好似父亲逗女儿玩耍。虽为孤儿,阿黛勒由罗切斯特抚养确保了上层社会的生活。
阿黛勒住在罗切斯特的庄园里时,身为管家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对她没有丝毫怠慢并为她联系家庭教师。阿黛勒和费尔法克斯太太相处也很亲近,吃饭经常是在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客厅或者房间里,不像简那样常一个人在保育室里吃东西。平时阿黛勒也会在费尔法克斯太太身边玩耍,甚至会把小物件摆在她的膝上,这些小细节很能体现管家对阿黛勒的关爱。有一次阿黛勒生病了,费尔法克斯太太为她告假,让她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的炉火边的小椅子上(109)。费尔法克斯太太客厅的炉火,营造出了家庭的温馨氛围。对比简小时候,常常只能远远望着表兄妹们和他们的妈妈围绕在炉火旁,自己却被排斥在家庭团聚之外。对简而言“炉火就是家的象征”(Carlton-Ford,1988: 380),但她却被驱逐远离炉火,无法享受家的温暖;而阿黛勒却没有孤苦无依的经历,总能待在炉火边享受家庭温暖。
身为上层孤儿的阿黛勒有自己的家庭教师。简不仅仅教给阿黛勒功课,在感情上也很关心她。阿黛勒生病时,简给她带去好玩的玩具和好看的故事书,并且吻了她的额头来表达关爱(109)。当简得知阿黛勒悲惨身世后,不仅没有瞧不起她,反而决定更加疼爱她。简对罗切斯特说:
阿黛勒不应该对她母亲和你的过错负责,我很关心她。现在我知道她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父母——被她的母亲所抛弃,而又不被你所承认,先生——我会比以前更疼爱她。我怎么可能喜欢富贵人家一个讨厌家庭教师的娇惯的宠儿,而不喜欢像朋友一样对我的孤苦无依的小孤儿呢?(145)
阿黛勒上学也比简幸运。阿黛勒最开始上的学校校规严苛,不适合她的天性,她过得并不愉快。简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马上把她接回家,重新安排了适合她的校规宽容的学校,并经常去探望她,关心她过得好不好,缺不缺什么(454)。阿黛勒虽是孤儿却有一个相对温暖的童年,这与她所处的社会阶层是有巨大关系的,不用遭受物质上的匮乏和身体上的惩罚,学习则有来自家庭教师的指导并有选择学校的机会。
2 缺点的规训
维多利亚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社会繁荣,教育发展,社会重视对于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社会期望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人,重视对儿童进行规训与约束,使其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行与礼仪(李宝芳,2015:152-154)。女性可以得到来自家庭或学校的正规教育,但是当时这种对于女性的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或者职业化教育,而是为了她们能够更好地履行家庭妇女的职责,重点培养她们“顺从、从属的宗教信仰”(马瑜,2004: 134)。小说中的简和阿黛勒都有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之处,其缺点需要得到纠正,她们在寄养家庭和学校都分别受到了教育和纠正。
缺点的规训是人物成长的重要经历,规训缺点的人在成长小说中称为引路人,他们是指导青年人走出困境、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父母是最亲近的引路人,但孤儿没有,他们的引领者只能是其他长者、同龄人、教师等。毛新耕(2011: 11)认为引路人“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认知,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的轨迹”。在小说《简·爱》中,主人公简在规训缺点、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受到了消极引路人里德太太严苛的责罚,经历了更剧烈的痛苦,幸而得到海伦和坦普尔的正确指引;而阿黛勒有家庭教师的耐心指导,上学后也有机会很快从严苛的学校转入相对宽松的学校,这些保证了她更为顺利地改掉了缺点,也是身在底层的简无法企及的。
2.1 简冲动性格的修正
就当时的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而言,简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脾气古怪,性格冲动。在小说的开篇简就被舅妈惩罚独自在一旁待着,原因是仆人贝茜告了她的状,导致舅妈批评简吹毛求疵、刨根问底,还和大人顶嘴。小说中一直未曾说明贝茜告状的缘由,但从后来的故事中,可以得知贝茜是整个里德家唯一疼爱简的人。简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个里德家唯一疼爱她的人到舅妈哪里告了一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仍能明显地感受到简不讨周围人的喜欢,不符合大人对小孩子的期望。即使在最疼她的贝茜的眼里,简也是个独来独往、古怪胆小、怕难为情、狡猾又多心眼的小东西(36)。简的经历反映出一个身在社会底层的孤儿所要承受的诸多重负。
简最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是她个性上的冲动,这个缺点在她与表哥约翰以及舅妈里德太太的冲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表哥扔书打她,令她的“脑袋撞在门上,开了个口子,淌出血来,疼痛难忍”(7),此时简开始在言语和身体上拼命地反抗,失去理智,以至于自己都意识到“确实有点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9)。简的反抗本来是正当的,可过度冲动的举动却让里德全家上下都增加了对她的厌恶,最爱她的贝茜甚至都“不相信她的神经还是正常的”(9-10)。随后简与舅妈又有两次冲突,冲动情绪无法控制。第一次是她控诉舅妈对她不好会让天堂里的舅舅看得清清楚楚,令里德太太“惶恐不安,露出了近乎恐惧的神色”(26)。简当时意识到自己说这些的时候,“舌头仿佛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句话,完全是随意倾泻,不受控制”(26);第二次冲突是里德太太在校长面前污蔑她撒谎,简委屈地进行反击,毫无顾忌地控诉里德太太心肠狠,并威胁要让罗沃德学校的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所做所为。简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在舅妈示弱并表示想成为她朋友之后,她仍然情绪激动,继续控诉。成年后的简在反思这段经历时写道:
先是暗自发笑,感到十分得意。但是这种狂喜犹如一时加快的脉搏会迅速递减一样,很快就消退了。一个孩子像我这样跟长辈斗嘴,像我这样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怒气,事后必定要感到悔恨和寒心。我在控诉和恐吓里德太太时,内心恰如一片点燃了的荒野,来势凶猛,但经过半小时的沉默和反思,深感自己行为的疯狂……(35)
简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遭受虐待后进行反击可以理解,但事后她自己也意识到反击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气势汹汹。就当时的社会要求而言,冲动的性格并不符合未来贤妻良母的形象,必须得到规范和约束。
父母是儿童最亲近的引路人,帮助其改正缺点并促使儿童健康成长,但是简没有父母,监护人里德太太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第一位引路人。里德太太注意到了简个性冲动,并要求她加以控制和改正:“简,这些事儿你不理解,孩子们的缺点应当得到纠正。”“你好意气用事,简,这你必须承认。”(35)里德太太一针见血地指出缺点,也想要对简进行约束和规训,但同时对简存有偏见,无法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只会用关禁闭、打耳光、责骂、疏离等残酷方式进行惩罚和管教。在简的成长中里德太太作为一个引路人对简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自己也遭到简激烈的反击,至死不能释怀。
在离开里德太太之后,简终于有幸地遇到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积极引路人——同学海伦和老师坦普尔小姐。当简满怀委屈地向海伦诉说了自己遭受里德太太的不公正待遇后,海伦开导简要忘记伤害,那样自己也会愉快一些:“暴力不是消除仇恨的最好办法——同样,报复也绝医治不了伤害。”“等你长大了你的想法会改变的,现在你不过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小姑娘。”(55)海伦认为激烈的报复行为是不可取的,她在和简的交谈中输出了为世人接受的正确的处事态度。海伦自己也接受过惩罚,但她的态度却并不委屈愤恨,而是从容大度,仿佛英雄一般,海伦行动上的示范传递了睿智和力量。之后海伦更是多次陪伴在悲伤的简身边,开导简不要让仇恨压垮也不要“因为忧伤而沉沦”,并且能够直接地指出简的个性上的缺点:“你的感情太冲动,你的情绪太激烈了。”(67)可以说,海伦所指出的与点跟里德太太眼里看到的缺点是同一个,但里德太太粗暴的惩罚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令双方发生更剧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而海伦却用耐心的语言和从容的行动来指引简,更易于简的接受和模仿。老师坦普尔小姐也是简成长中一位重要的积极引路人,她“神态安详,风度庄重,谈吐文雅得体,这使她不至于陷入狂热、激愤和浮躁,同样也使看着她和倾听她的人,出于一种克制的敬畏心情,不会露出过分的喜悦”(70)。这样平和的处世态度与简的冲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了简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着简的个性向着平和克制方向发展。简在往后的人生中,都在实践着海伦和坦普尔小姐的人生哲学,不再提及在里德家受到的伤害与痛苦,并且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成年后在罗切斯特先生的庄园的种种举动表现出理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冲动。在罗切斯特看来,简的“理智稳坐不动,紧握缰绳,不让情感挣脱”(201),此时的简已经能够稳稳克制和掌握自己情绪的女性。后来简看望病重的里德太太时,诚恳地希望同她和好,在病床边给予她宽恕,单方面与这个造成她童年不幸的女人和解。尽管里德太太至死也没有原谅简当年疯狂的反击,带着对简的恨意离世,简却已经在成长中学会了克制自己冲动的情感。
2.2 阿黛勒的任性虚荣
按照当时的社会观点来看,阿黛勒也并不符合一个未来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小说中她与寄养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冲突却不尖锐。她外貌可爱,个性大方,没有什么大毛病,引路人也都给予她积极正面的影响,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剧烈的痛苦和冲突。阿黛勒在小说里出场的时候大概七八岁,有一头披到腰间的卷发和淡褐色的大眼睛,待人接物也很热情开朗。阿黛勒初次见到家庭教师简的时候,一点也不怕生,只需十来分钟的时间,话语就从简短的回答变成“叽叽喳喳地说开了”(100)。阿黛勒给简讲了自己如何来到英国,妈妈去了哪里,还主动唱歌和朗诵诗歌给简听。她对监护人罗切斯特也没有任何畏惧感,一见到他就跟他要礼物。她对管家费尔法克斯也没有一点疏远感,在她的膝头摆满了她的各种小玩意儿,同时用她所掌握的蹩脚英语,告诉她“自己有多开心”(129-130)。阿黛勒对待庄园中的大人们很热情,并不像简小时候那样古怪敏感。作为上层社会罗切斯特家的一员,她个性上的开朗外向也让她在庄园中的生活比简当年更占优势,整体上来说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
阿黛勒的倔强任性和对于外在美的虚荣追求却是她的“法国式缺陷”,这在小说中有多次提及。阿黛勒非常活泼,但由于过分溺爱已被宠坏,有时候会显得倔强任性(107)。比如罗切斯特要回桑菲尔德庄园的那天,“阿黛勒不大好教。她静不下心来,不住往门边跑,从栏杆上往下张望,看看能不能瞧一眼罗切斯特先生,随后编造出一些借口来,要到楼下去”(117)。这时她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罗切斯特评论她对服饰过于关注:“看上去多么矫揉造作。”(139)当桑菲尔德庄园宴请客人的时候,阿黛勒兴奋不已,总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一些。简给她一朵花“系在她的彩带上,她舒了一口气,显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满足,仿佛她的幸福之杯此刻已经斟满了”(172)。在当时的社会看来,阿黛勒的任性和对于外在美的过分追求是需要得到纠正的缺点,但并不是什么大毛病,简认为“她没有什么使她居于常人之下的缺陷和恶习”(107)。整个桑菲尔德庄园从上到下的人也都是比较包容的。监护人罗切斯特没有严厉批评和任何惩罚,只是认为这习气是从巴黎和她母亲那个地方带回来的,并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只需离开巴黎那浮躁的环境,在英国这样更好的环境中就能改过来。管家和仆人们也没有议论纷纷,都尽职尽责地照顾和关爱这个小姑娘。家庭教师简更是成了阿黛勒成长的重要引路人,用包容和耐心为其指导前进的方向。比如在学校的选择上,第一个学校太过严苛,就帮她另外选一所稍微宽松的学校,让她更容易适应。学校离家近,简经常去探望,关心她的日常生活。阿黛勒确实适合这种稍宽松的学校,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学习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她的法国式缺陷”,并最终成长为一个讨人喜欢、懂礼貌、和气、听话、讲原则的姑娘(454)。整体来讲,身处社会上层阿黛勒在成长过程中,缺点的规训温和而循序渐进,充满包容和爱。相比之下,身处社会底层的简童年冲动的缺点在恶劣的环境下被放大,产生出多次剧烈的冲突,对其身心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幸而遇见了海伦和坦普尔小姐给予正确的引导,简才能从痛苦中走出并改正了冲动的缺点。
3 结语
对比分析《简·爱》中孤儿简和孤儿阿黛勒生活遭遇和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她们都从不幸中成长起来,改掉了自身的缺点,成为符合社会规约和期望的女性。简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底层孤儿挣扎着适应社会的过程,她在儿童时期经历了身体上的虐待和精神上的摧残,但她有幸遇到能给她指引正确方向的同学海伦和老师坦普尔,终于克服了冲动的缺点,成长为有自制力的独立女性。阿黛勒是上层孤儿的典型代表,虽然也没有父母的爱护,但她并没有受到虐待和摧残,在更为温暖和宽松的环境下改掉了任性和爱慕虚荣的缺陷。她们都从孤儿成长为了符合当时社会期望的女性,尽管成长过程有着巨大差异。在维多利亚时期,来自社会底层的孤儿更多地遭受周围人等的恶意,自身的缺点也会被放大,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偶然有幸得到积极的人生指导;而身在社会上层的孤儿,仍然能保有优越的生存生活条件和教育上的选择权利,得到细心的照顾和恰当的指引。